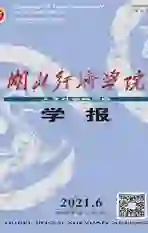我国新兴民事权利的衍生路径
2021-09-05王风瑞
王风瑞
摘 要:随着时代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不断觉醒,新的权利不断产生。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权利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本身就是不断产生的,新生权利并不是这个时代独有的现象。权利作为主体的利益诉求的一种表达,需求是权利产生的动机因素。人类的需求本身具有层次性,人类需求的层次性决定了基于需求产生的权利也具有层次性。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较高层次的需求才会出现。因此,法律在将新兴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的过程中,要根据权利的需求层次,优先满足较低层次的权利需求。尽管权利需求的层次不是绝对的,但是需求层次整体上反映了权利衍生的趋势,基于需求层次的权利新兴是民事权利衍生的主体路径。
关键词:新兴权利;民事权利;需求层次理论;动机
一、问题的提出
自近代以降,权利成为从社会到个人诉求的集中表达形式。作为整个民众持续的事业,权利在法权的斗争之中不断兴起,这种兴起不仅在于客观意义的法,且在于主体意义的权利,由抽象而具体。“这些‘新兴的权利事实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学范畴意义上的概念,它所表征和代表的实际上是一系列不同类型和性质的权利,因此可以说它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表征“权利束(丛)”的统合概念。”[1]5由于中国同世界法律发展的不同步性,在中国法域下所表征的“新兴权利”并非全部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演化,其中既包括了以“观念和思想方式存在的权利主张”“未经法律实证但具有社会实践真实性的社会性权利或者事实性权利”,亦包括了“法律实定化的权利”。[2]51
研究新兴权利,目的在于在对新兴权利认识和甄别的基础之上,对于具有合理诉求的表达进行制度化的确定,将主体诉求性主张转化为同时具有“客观法”与“主体权利”双重意义的具体权利。新兴权利作为一个集合性权利概念,有其内在的原生基础和层次分布。有些新兴权利已为广泛的法治实践所认同,仅由于我国权利体系形成的滞后性而未予以确认;有些新兴权利具有深厚的社会性基础,具有成为权利正当性基础,并对权利体系具有补充之效能;而有些权利仅为个体观念的假设性主张。明确新兴民事权利的衍生路径,从民事权利的衍生规律中探讨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哪些具有为制度所确认的必要性,以形成规律性的权利确认与制度保障次序与过程。
二、民事权利衍生的历史进路
民事权利体系作为一个开放性的集合概念,其外延是不断扩展的,权利的“新兴”也并不是信息时代特有的产品,民事权利体系是在权利衍生中不断完善的。人们的利益交互在社会演进的过程中不断变化,“权利体现了人们交往行为中的利益结构关系,法律规范中对权利的界定,理应是社会结构中利益关系的法律表达”。[3]44股权、知识产权、人格权均是社会结构调整中利益关系的重新表达。
民事权利作为权利范畴之中种类最多样、内容最繁杂、划分最统一、体系最完整的权利集合,尽管众多权利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出现,但是均很好的嵌入到了原生权利体系中去。基于权利客体,人身权与财产权的划分是一个周延的民事权利划分标准。
(一)財产权利的历史衍生
财产权利,是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直接及于经济上之利益,可分为物权、债权、无体财产权和集体财产权。[4]34~35传统权利体系下的内容并非体系建立之始既已存在,建筑物所有权因近代城市化进程中“住宅危机”而产生;无体财产权之中,知识产权是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发展支撑之后,由习惯转为制度保护的法律缔造;集体财产权之中,股权更以现代公司制度为必要条件,是公司制度下股东权能综合的一种集中表达。
19世纪以来,欧洲工业化加速了城市中心化,人口向都市的聚集造成了城市人口激增、地价飞涨、住宅缺乏。同时,随着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战后人口激增和不动产的投资乏力,土地立体化利用日间迫切。数人于共同土地之上区分所有建筑物,为土地利用率提高及基础设施高效配置所必要,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由此而逐渐形成,并为法律所确认。[5]5~15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产生源自于近代以来,人们对于土地的利用不仅限于横向的水平跨越,更向纵向延伸。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地上与地下相当空间的利用成为可能。因此,土地不仅在地表之上的有限范围内能够满足人的权利要求,土地范围内的纵向空间范围均已成为人们权利行使的空间。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在打破传统一物一权主义的旧框架中产生,空间成为物权客体,可被独立支配,呈现水平所有或利用的形态。[6]150法律对于空间的权利确认使得城市化进程中的“住宅危机”得以解决,住宅需求能够为基层群众所负担,满足了基层群众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无独有偶,知识产权、股权亦是在权利客体突破中产生的。传统所有权理论均是建立有体物的基础之上,无形资产缺乏权利保护的理论支撑。但是,在自然科学成为自然生产力的一部分之后,每个资本家充分意识到,“现代工业是凭借科学技术进行的产业,如果不进行生产工具的革新,资本生产就难以维济”,[7]57因此,要实现科学技术从研发者到生产者的转移。但是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真实世界中,市场虽能达到最佳配置,但这种程序代价也会极度高昂,因此有必要建立适当的产权体系,简化权利转让的法律要求,降低权利转让成本。[8]11而知识产权的所有者也意识到,知识产权的实现不用与传统物权所强调的对物的支配、管领和控制,而通常表现为知识产品的创造——使用过程,知识产品的创造主体和使用主体会分离。知识产权的非物质性和物化实现性决定了其可以物化于多个载体上同时实现,在现代技术的发展之下,对于知识产权的“占有”和利用极为便利,知识产权产品的“虚拟占有”和权能的多样性要求必须要建立弱化支配功能而强化利用功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9]65~69从英国《垄断法规》《安娜法》,到国际社会的《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现代知识产权制度逐步形成。
股权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物,以1694年英国成立英格兰银行为标志,股份制度正式进入历史长河。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使资本最低使用限额不断提高,这就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资本不得不闲置起来,这些急于寻找增值出路的闲置资本,构成了股份资本的重要来源”。[10]70资本家为生出更多的货币,将这些货币预付到企业之中进行生产。[11]223股东因对公司出资而享有份额,出资者对这些份额之上所享有的权利构成了股权。股权的客体——股份,是“每个股东享有的价值形态的公司资产份额”,[12]68是股东出资额在公司运行过程中由资本增殖或贬值转化而成的资产份额。股份以生产社会化过程中资本积累为前提,并且资本须以货币方式实现。在资本的货币实现过程中,信用制度成为整个运动过程的基础,成为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13]493~500
近代以来产生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知识产权、股权,从权利产生的动力需求来看,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为实现民众普遍居住之可能,知识产权为保障权利人智力成果资源所有权,股权为实现资本增殖,是通过货币与信用制度实现人类的财产安全。
(二)人身权利的历史衍生
人身权利不同于财产权利,其中蕴含着更多的伦理价值,在社会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民事主体的相互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基于新的伦理与价值判断的基础,人身权利处于新生与消亡的双向互动之中。在传统人格权立法之中,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为传统物质人格权所固有,自由權、市民权、家庭权、名誉权、贞操权为传统精神人格权之内容。[14]29~34但是随着近代民法的产生,市民权、贞操权已经消亡,而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产生。
姓名权作为决定自己姓名内容并对姓名符号专有使用的一种权利,其意义在于使特定自然人与其他人相区别,维持其在法律中的特殊存在,使人们能够在“一般交往包括法律交往中相互识别”。姓名权的客体不限于自然人的姓名,并包括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与特定人建立稳定对应关系并未相关公众知晓的笔名、艺名、译名、别号、字号、绰号或者其他符号。[15]50,52肖像权系个人就自己肖像是否制作、公开及使用的权利,其与姓名权有着相似的意义,同样表征一个人的外部存在,使其与他人相区别。同时,姓名权与肖像权同样有着商品化权的性质。公众人物的姓名、肖像因为其广泛的认知度而具有了转让的必要性,当其被用于广告目的之时就有了商品化价值,权利人对于自己创造的商品化价值可以进行控制并取得收益。[16]142姓名权与肖像也体现着人格尊严,权利人的姓名和肖像不得被任意篡改、歪曲以使其社会评价降低。
与姓名权、肖像权不同,隐私权作为一种绝对的消极权利,以个人生活安宁与私人空间为内容,其目的在于排除个人生活中的他人干涉。虽然隐私亦具有“民主社会的维持、个人的社会参与、对国家权力的限制等功能,”[17]179但是人的自由与尊严、不受他人支配与干涉仍然是隐私权作为私权的核心价值。
姓名权、肖像权作为兼具财产性与人身性的权利,其中的财产性权能重点在于维护权利人基于自身权利所享有的财产所有性,他人不得非法利用他人的姓名、肖像而改变该权利上财产利益的归属;隐私权作为一种单纯的人身性的权利,其与姓名权、肖像权中的人身性权能一样,在维护权利人人身安全的同时,也防止了他人对于权利人的道德侵害,为权利人构筑了道德保障的防线。
三、新兴权利的主体需求内容
权利的产生或消亡是社会发展在法律制度层面的映像,其动因在于社会主体及其诉求在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应经济结构之变动而趋于多元。主体在多元化利益诉求的驱动之下,对于自身各方利益关切日益敏感,各种诉求之间必然存在冲突与竞合,进而引发各种权利诉求的竞争与斗争。“也只有社会中客观地存在着基于主体为获得、保有或者处置一定的利益而进行的权利竞争和斗争,才有可能在法律制度的意义上将相应的权利诉求转化为现实的法律权利。”[18]14在诉求的规模与重要性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法律将斗争之中取得竞争优势和广泛认同的主体诉求转化为客观存在,转化的方式既包括了立法创制,也包括了司法确认。
随着人类进入信息化社会,信息的收集、存储、分享、使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数据存储由物理存储到虚拟存储的转变,大数据带来了全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个人的所有人身和财产信息均可以实现数字化的存在和表征。其中既包括了个人基本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生物基因信息等识别个人存在信息以及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婚姻状况等个人属性信息;也包括了上网记录、阅读记录、交易记录等“伴生个人信息”和个人偏好、工作表现、发展潜力等“预测个人信息”。[19]100,101虽然单个的个人信息不具备公共利用价值,但是当个人信息被收集、被整合成大数据,就形成了社会流通所需要的价值。[20]169广告软件、间谍软件以及电话销售使得商品化的个人信息成为一种独立的个人信息包,可以实现与其他商品交换价值的互换。[21]但是只要个人信息属于信息,它就不会成为纯粹的无形资产或者非物质资产,[22]个人信息权就不会成为单纯的财产权利。在个人信息同时具有自由、尊严、安全和财产的属性之下,个人信息便契合了私法保护的使命担当,具有了成为潜在权利的品质。其中既包含了隐私性的个人信息权和非隐私性的个人信息权,但是个人信息权中的隐私性权益不同于传统隐私权旨在防止他人干涉私人生活安宁,其目的在于确认个人的归属;虽然单个个人信息不具有财产价值,但是被整合之后便具有了财产属性,因此个人具有属于财产的构成元素,本质上是一种资源,个人信息权表达了个人对于资源所有性的一种确认。
信息时代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个人外部信息的权利化,更有人体内部信息的权利化,基因也逐渐成为一种权利诉求。基因作为“定义人类”的物质、“人类生命的蓝图”,基因科学的发展使得通过基因控制人类质量成为可能,人类种族进化完全可以从科学命题转变为社会和政治控制问题。[23]34,47这样一来,一些亚种群被迫遵守具有弱的“科学”相关性支撑的法规,这种理念对于理解以隐私为中心的现代科学政策至关重要,甚至有可能被烙上种族歧视的污名。[24]同个人信息权类似的是,基因作为一种生物信息,同样具有隐私权益与资源权益的双重属性。每个人对于其基因资讯的保密、秘密、交流和控制,有自主决定的权利;同时,基因一旦与人类相分离,就作为一种物而存在,在其控制人类潜能的价值覆盖下,就具有了交易价值,成为一种信息资源。[25]125~134不同于个人信息权,基因作为法律权利面临着“技术风险、社会风险、伦理风险和法律风险”,[26]60基因权的法律生成不仅是生物技术的需要,同时反映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在基因科技手段越来越渗透和控制着人类社会关系的当下,在利益集团对人类基因富矿进行近乎疯狂的发掘而不顾及其巨大风险的时候,为了人类尊严和社会正义的存续,除了宪法规范基于人性尊严的考量,更要在私法上对人类基因采取建构权利名份的强意义的法益立场。”[27]因此,基因权的法律生成不仅是个人基因资讯私密性的保护和基因资源所有性归属的确认,在人类控制人类种群繁衍的代际传递过程中,基因的改变意味着人类种群的非自然变更,这是对于人类种群本身的亵渎,因而,基因权反映的是人类自身要求尊重的需求。
如果将基因权定性为代际传递的终局性权利,那么性权利就是代际传递过程中的过程性权利。即使并非作为权利存在,作为事实存在的“性”也是权利需求的结果——是在打破传统“单一性别”模型,承认男女的生物差别的基础之上,性才成为了自然的、生物欲望的结果。[28]34,35但是,不同于动物本能的性行为,人的性行为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并且身体需求并非是其唯一功能,谋生、情感联系、建立稳定共同体都包含在其功能之内。但是,在性的本能——里比多的目的驱使之下,“阉割情结”“俄狄浦斯情节”都是里比多的发展趋势,都是其在对象上的“投资”。[29]228人类文明作为把人们集中到大统一体的文明,为防止文明内部冲突,必然要对性进行限制,“限制性生活的文明倾向与文明扩大文化领域的其他倾向一样明显”,家庭的建立于是就限制了纯粹基于性的爱,“建立家庭的爱既未放弃直接性满足的最初形式,也以目标受到控制的爱这种变更的形式继续在文明中发挥作用”,[30]100~102于是就有了“爱情”“慈爱”“友谊”的区分。但是近代以来,人文主义、任性解放思想的推动、现代性科学的发展对于性压抑的反对、商品经济时代对于自由化的崇尚、新的避孕器具、流产技术导致的对性交后果的消除,引发了近代的“性革命”,人们对于性权利的主张日益强烈。1997年通过的《性权宣言》规定了11项性权利,[18]161这11项性权利反映了人类不同层次的主体需求。性快乐权和性表达权,是人对于性需求的自然欲求,反映了人的自然生理需求。性自由权,性自主权、性完整权和身体安全权、性保健权,是人在性生活过程中对于人身安全和生命健康的保障;性自主负责生育选择的权利作为对于后代繁衍的选择,是家庭延续所承担的职能,是家庭安全的内在内容,其与人身安全和生命健康都是人在安全上的需求。性私权、性自由结合权反映了人类对于性亲密的一种自我选择,这是爱情的情感表达,是一种情感和归属上的需求。性公平权、以科学调查为基础的性信息权、全面性教育权,是性主体要求他人实现对自我性的尊重、以及自己在了解性的基础上对自己性的尊重的一种需求,是一种尊重的需求。
既然性表达权是人的基本生理需求的内容,那么基于对同性的性表达和性选择所形成的同性恋是否具有婚姻的权利呢?一般来说,“性的”意思主要包含“两性的区别、快感的刺激和满足、生殖能力、不正当需要隐藏的观点等”,但是有些人“并没有两性的区别”,“同性才能引起他们的欲望,异性丝毫不能引起他们的性刺激,甚至还会让他们感到恐惧”。[29]205,206同性恋者可能由于遗传因素造成,亦可能由于环境因素造成,是一种自然衍生的情感存在。婚姻制度作为一种对于性资源的分配制度,形成了夫妻双方对于对方性资源拥有和支配的一种国家确认,[31]但是这种分配制度设计之初就忽略了同性恋作为一种性选择类型的存在。婚姻制度作为社会关系的稳定剂,通过确立家庭关系使得两性关系趋于稳定。家庭关系从产生之初就是为了满足人类对于家庭秩序稳定的需求。同性恋虽然是当事人基于性自由选择的结果,传达了当事人对于性亲密关系的归属,但是同性恋者要求婚姻权利在于要求法律对于其形成稳定家庭的确认,是一种对于稳定、秩序和安全的需求。
既然人类在基因、性、婚姻上都可以选择,那么对于生存与死亡,是否具有选择的权利呢?更甚来讲,海德格尔曾言,人是向死的存在。既然人自生之始即处于向死的过程之中,加速这一过程能否被覆盖于权利的涵摄之内呢?毋庸置疑,作为内在原因的自主思想市场是自由权利证成的根本因素,外在原因仅在与避免法律制度的审查,[32]基于康德的自主权可以提供当事人对于安宁死亡选择的依据。但是这种自主选择仅在于自由,而非权利存在。“法律不可能禁止个人的自杀行为,法律无法约束自杀者的意志,自杀基本上属于道德领域的问题,而非法律问题。”[33]74如果权利是一种主体需求,“人权产生与存在的根本目的与价值在于满足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的愿望和需要”,[34]17无论主体需求属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与归属需求、尊重的需求,均是以生命为基础的需求。死亡意味着所有外部需求不再有任何意义,在所有外部需求因消失而具有满足的效果之后,人们便回到了自我的本源之上,生命不被干涉的内容是什么,这种目标的实现是人类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
四、民事权利主体需求的层次演进
人作为一个一体化、有组织的整体,人的需求也是系统性的。权利作为一种人类需求在法律中的映像,是人类需求實现的手段。但是人类需求作为权利诉求产生的动机,本身又成为权利实现的目的,需求的层次与演进路径决定了权利的演进路径。人的需求作为一个有意识的欲望,是需求实现本身的动机。由于人类智能以相对或者递进的方式实现需求,其在自然过程中就形成了一种优势等级、层次排序。
作为人类原始驱动力的往往是生理驱力,这也是人类需求的基点。人类的生理需求是独特而不是典型的,他们是可孤立且可定域的,他们既彼此孤立,又相对于其他层次的需求独立。例如饥饿、性欲,这种驱力通常是一个局部的、潜藏的躯体基础。同时,任何生理需求都承载着疏导其他需求的作用,如果所有需求都没有得到满足,那么生理需求之外的其他需求都可能全然消失。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安全类型的需求就会出现,其中包括了对于安全、稳定、依赖、保护、免受恐吓的需求,对于体制、秩序、法律、界限以及保护实力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有时体现在一种安稳的程序和节奏,其中潜藏着可预见的有序世界。如果生理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那么爱、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就会产生,并且以此为中心,重复着整个环节。如果爱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个人会强烈渴望建立一种关系,渴望在团体或家庭中有一个位置。在此之后,社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获得自己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评价的需求,即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尊重的需求,包括了基于成就的欲望基于评价的欲望。最后,在所有外界需求得以满足之后,人就会回到自我实现之中——一个人能够成为人身,就必须成为什么,必须要忠于自己的本性[35]1~41。
但是,自我实现并不是一种结局状态,自我实现者无一例外都献身于一项身外的事业,某种他们自身以外的东西,以追求那种固定的终极的价值——存在价值,这些价值像需求一样起作用,我们称之为超越性需求,包括人的真、善、美,还有圆满、单纯、全面等[36]204~212。
权利作为使得主体的要求、主张产生约束力的主观意义上的法,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个人主张的利益,包含了主体对客体加以支配的自由意志[37]65,66。虽然权利本身不是需求,但是需求是权利产生的动机,权利的内容取决于主体需求的内容。基于人类需求的层次性,人类权利的内容也具有层次性。传统民法中的物权、债权、婚姻权、身体权、生命健康权是为确认传统社会人类对于食物、住所以及性需求等的所有性以及规范人类获得食物、住所、性需求等的方式,保障人类生命体的基本存在,具有满足人类基本生理需求的功能。
近代社会以来,生产力的飞速提高使得人类的生理需求得以满足。一旦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求,人类就将在权利中表达下一个需求层次。一旦满足了所有基本需求或不足需求,那么人类就会趋向于追求更高的自我实现需求[38]。知识产权的产生,保障了人类对于智力资源的所有性,通过智力成果归属保障了权利人财产安全;股权则以投资为途径,以货币制度和信用制度为手段,实现了人类财产的保值、增殖,保障了财产的安全性;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等具体人格权的产生,使得人格利益如同资源归属一般得到法律的确认,同时,人类生活的基本尊严与生活安宁稳定的必要性也有了法律根据:近代权利产生的动机需求开始从生理需求向安全需求转变。
新兴民事权利的产生反映了人类需求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进入了更好的需求层次。个人信息权的本质在于“被遗忘”,即“不是一定时间后数据主体拥有了原谅自己的权利,或者主动让自己被社会遗忘的权利,而是社会选择在一定时间后宽恕、原谅、遗忘某个信息以及该信息主体的权利”。[39]181但是这种权利是可执行的,我可以要求删除,即使内容经由权利主体之外的人传播。[40]因此,个人信息权潜藏着个人要求社会自觉地退回社会所应坚守的信息界限之内,强调个人自我保护的权利进入到社会权力的范围之中,是安全需求之中一种高级形式存在。同性恋者的婚姻权看似是一种情感与爱的归属的需求,但是同性恋者婚姻诉求不在于性对象的选择与性的表达,而在于希望双方的关系能否得到国家的确认与安排,形成稳定的婚姻秩序,是对于关系稳定的制度依赖,是安全需求在情感上的表达。
性权利作为集合性权利,权利的多元性需求中既有基于“性冲动”而产生的“性宣泄”的生理需求,也有对于性表达过程中安全的需求,还有基于对象特定和精神幸福追求所产生的情感归属需求。[41]11~14随着基因工程对人类性信息的深入探索、通信革命引发的对于妇女和儿童的性剥夺,[42]人类普遍对于性有了进行全面了解和要求公平的需求,这种需求要求自己和他人在性的领域实现自我尊重和他人尊重,使得性权利随需求层次跨越到新的层次领域。
当我们的生存被时代很好地满足之后,我们开始思考死亡,虽然对此,我们只有一个选择——要么现在死,要么以后死,但是选择现在死是实现自我的一种需求吗?如果把死亡视为一种生物功能的现实,死亡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种恩惠,如果我们要尊重人的尊严,我们不仅必须改变对死亡的态度,还必须停止把死亡的过程留给机会和身体的逐渐解体。[43]如果死亡是生命的一种自我实现,那么死亡必须源于自我的本性,死亡应该是自我发展的自然过程,这种过程最自然的莫过于身体的自然消解。事实承认,生命权不包括死亡权,生命作为最高的社会价值,不仅涉及人,而且涉及国家和社会,并通过其影响社会。[44]当生命的存在已经不能被自我决定时,如果人们其他层次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那么必然会要求让生命回到本源之中。在死亡已经是生命不可避免的现时历程,人类的外在需求因为没有意义而归于消灭了,外在需求的消灭将产生与满足同样的效果。人类在外在需求满足之后,人类的需求便回到了对自我的实现,在死亡过程中对自我的实现。因此,安乐死展现了人在生命终极阶段的自我实现需求。
权利兴起作为主体需求的结果,需求既是权利新兴的动机,也是新兴的内容。需求的层次性决定了权利的层次性,“其根本原因是世界或宇宙本身就是以层次性的方式存在的”,权利层次是以“集体—外部”的类型存在的,[45]523部分群体的需求转化为对于权利的要求,权利要求逐渐进入法律,成为一种法律性的外部存在。在需求层次上,新型权利的需求层次呈现了从安全需求到个人实现需求不同的层次;从历史上看,权利衍生的路径也呈现了从低层次需求向高层次需求的演化。尽管这种需求层次进化不是绝对的、刚性的,但是民事新型权利的衍生路径总体上契合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五、基于需求层次的新兴权利法律确认
随着中国进入“权利的时代”,权利泛化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权利泛化现象源于主体的正当化诉求,作为一种权利的生长机制,权利只有被道德和法律所接受,被纳入制度的框架之中后,才具有正当性的基础。[46]1,7但是,哪些权利能够进入到制度框架之中,哪些权利不能进入,或者哪些权利优先进入到制度框架之中,哪些权利后续进入到制度框架之中,确是法律对于权利确认必须考虑的问题。道德允许与社会认同虽然是一个重要参考标准,但是基于社会认知的无法证成性以及主体间性的易错性,道德与社会认知的判断很难实现。然而权利本身具有被满足的层次性,从权利本身的层次来推测其确认优先性具有主体合理性。
权利入法的方式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激进式入法路徑,另一种是渐进式入法路径。但是激进式入法路径更多倚重建构理性,渐进式入法路径更多倚重演进理性,[47]31两种路径质的差异使得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无法重合。但是基于需求层次的权利路径是在考察历史权利自然渐进衍生的过程中,通过归纳总结,发现其契合需求层次理论,基于需求层次理论建构起来,很好地将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融合起来,实现了权利立法确认的理性基础优化。当然,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权利入法的方法,作为一种集合性和整体性的权利建构方法,能有效提升立法中权利规范的层次性、体系性,使得其他方法相形见绌。
虽然民事权利的需求层次不是绝对的、固定的,但是权利的衍生总体上符合了需求层次满足产生的规律;即使民事权利各个领域权利的需求层次呈现不平衡性,但是同一领域内,其权利衍生也是符合需求层次规律的。在较低级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较高级的需求就会出现,这些需求就会控制机体;当这些需求被满足之后,又有新的需求出现。因此,满足与匮乏就成为了同样重要的概念,他将机体从较低级的需求中解放出来,从而允许更加社会化目标的出现。[35]22立法对于权利的确认的重点在于对于低级层次需求的满足,在低级层次需求满足之后,人类才会出现更高层次需求的权利。在财产权领域,基于物权、债权对于人类食物、住所、财产等的确认保护使得生理需求的满足,具有安全需求属性的知识产权、股权、个人信息财产权才会产生;在人身权领域,在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人类生存必需的权利为法律确认之后,人类对于人身权利的要求才转向安全要求,比如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个人信息权,进而出现了情感需求和尊重需求的权利需求表达。
权利作为以个体为主体基础的结果,“个人的自我觉醒和独立产生权利思想及权利,而权利作为一种手段,其本身也是为了个人的目的”。[48]22新兴权利为主体的新需求而产生,为主体的目的而存在,新兴权利在入法的过程中,应当遵循主体的需求层次。个人信息权、同性恋者婚姻权以及性权利中的性自由权、性自主权、性完整权和身体安全权、性保健权作为一种安全需求,是一种较低层次的需求,立法应当优先考虑这些权利确认的需求。其中,个人信息作为一种法益已经为民法典所确认,但是在缺乏权利属性的明确指引下,个人信息的主动保护性功能不足;性自主权、性自由权在刑法强奸罪、猥亵罪的法益保护下亦有所体现,但是这种保护仅限于被侵害之下的救济,且这种侵害须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侵害,不具有权利所要求的确认、请求功能。但个人信息权利、同性恋者婚姻权、性自由权、性自主权、性完整权和身体安全权、性保健权作为一个中私人权利,处于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民事关系的民法之下将具有更低的运行成本,且使得权利的防御功能、受益功能和救济功能能够更有效地实现。[47]40,41
性私权、性自由结合权作为基于性而产生的权利,容易误将其作为基于生理需求所生之权利。不同于生理需求的性表达与接受,性私权与性自由结合权的根本内容在于性对象及其关系、行为的决定。文明的内部和谐性对于性的基本要求在于对性对象的区分和限缩,文明的内容决定了各种性关系的亲密程度与行为尺度。因此,性私权与性自由结合权是受到文明天然压制的,该两项权利的法律确认有待于考察文明的发达程度,而不能急于为法所确认。这也是情感与归属需求高于安全需求的根本要义。
对于基因权,现在人们多理解为基因编辑存在着对于后代人未知的安全风险,拒绝基因编辑在于预防和避免人类自身生物信息这种内在资源、环境生态面临的风险乃至危机问题,维护整个人类的自身安全。[49]90,91但是,即使基因编辑不存在风险,基因编辑是否具有可接受性呢?基因作为人类存在的基础,共同基因信息是人类形成命运共同体。基因改变在于对人类生命体的根本改变,是对人类根本的亵渎;而人类对于基因的了解是人类对于自身认知之需求。因此,基因权要求的是权利人对于自身的了解和人类作为“人類”这个生命体被尊重的权利,是一种尊重的需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伦理中需求的保护与法律中的需求保护不具有同步性,权利作为需求保护的最终确认,具有终极性和滞后性,在较低需求层次的权利被满足之前,基因权不具有被满足之基础。
安宁死亡权虽然是一种基于自我实现的需求而产生的权利,但是这种自我实现是一种被动的自我实现需求。“安乐死并非单纯地使人从生到死的转化,而是使死亡由痛苦向安宁的转化”,[33]73在死亡的必然实现过程中,其他需求并非因被现实的满足而产生自我实现的需求,而是其他需求因死亡的必然而归于消灭,呈现满足的状态。因此,安宁死亡权不具有权利需求实现的基础,暂时不具有成为法定权利的现实性。
六、结语
动机是权利产生的直接原因,权利的新兴源于动机需求的新生。需求的层次性使得人类呈现一定的层次性,虽然这种层次性的演进并非是绝对的过程,但是整体呈现层次性变化的趋势。由于权利集合的庞大,各领域的权利产生的需求层次不可能具有统一性,在权利诉求向法定权利转化的过程中,立法者、司法者不仅要考虑权利的现实基础,而且要考虑权利的需求层次,基于较低需求层次产生的权利应当被优先得到满足。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权利衍生路径,也是权利的入法路径。
参考文献:
[1] 姚建宗.新兴权利论纲[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2).
[2] 姚建宗,方芳.新兴权利研究的几个问题[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
[3] 谢晖.论新型权利生成的习惯基础[J].法商研究,2015,(1).
[4] 梅仲协.民法要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5] 陈华彬.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6] 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7] 曲三强.现代知识产权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8] [美]罗纳德.H.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M].罗君丽,茹玉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9] 吴汉东,胡开忠.无形财产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5.
[10] 卫兴华,宫玉松.关于股份制的发展历史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1).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2] 胡吕银.股权客体研究及其意义[J].法学论坛,2003,(4).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4] 杨立新.人格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15] 曹新明.姓名商标与姓名权客体冲突及合理避让研究[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9,(3).
[16] 五十岚清.人格权法[M].铃木贤,葛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7] 王泽鉴.人格权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8] 姚建宗.新兴权利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9] 邢会强.大数据交易背景下个人信息财产权的分配与实现机制[J]. 法学评论,2019,(6).
[20] 洪玮铭,姜战军.社会系统论视域下的个人信息权及其类型化[J].江西社会科学,2019,(8).
[21] Paul M. Schwartz, Privacy, Property, and Personal Data. Harvard Law Review[J]. 2004,117(2055):2069.
[22] ValeriuStoica. Ce SuntDatele Cu Caracter Personal[J]. Facultatea de Drept,2018,2018(1):214.
[23] [美]格兰特.斯蒂恩.DNA和命运——人类行为的天性和教养[M].李恭楚,吴希美,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24] Thomas Hale-Kupiec. Immortal Invasive Initiatives: The Need for a Genetic Right to Be Forgotten[J].Minnesota Journal of Law,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6,17(1):449.
[25] 颜厥安.鼠肝与虫臂的管制:法理学与生命伦理探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6] 王康.基因权的私法规范:背景、原则与体系[J].法律科学,2013,(6).
[27] 王康.基因权的私法证成和价值分析[J].法律科学,2011,(5).
[28] [英]韦罗妮克.莫捷.性存在[M].刘露,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15.
[29] [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文思,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7.
[30] [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文明[M].徐洋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
[31] 李拥军,付中强.性的自治与规制——在法律规则的视野下对性权利的一种解读[J]. 法治与社会发展,2012,(1).
[32] AlonHarel. What Demands are Right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Rights and Reasons[J].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97,17(1):105-106.
[33] 王晓翔.安乐死与死亡的自己决定权[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6,(6).
[34] 李步云.论人权的本原[J].政法论坛,2002,(4).
[35] [美]亞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6]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马斯洛论自我超越[M].石磊,编译,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6.
[37] Roscoe Pound.Jurisprudence,Volume IV[M].New York: 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59: 63-70.转引自张恒山.论权利本体[J].中国法学,2018,(6).
[38] Robert J. Zalenski and Richard Raspa.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A Frameworkfor Achieving Human Potential in Hospice[J].Journal of Palliative Medicine, 2006,9(5): 1121.
[39] 蔡培如.被遗忘权制度的反思与再建构[J].清华法学,2019,(5). [40] See Jeffrey Rosen.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J].Stanford Law Review Online, 2012,64:89.
[41] 李拥军.性权利存在的人性基础——中国当代性行为立法不能省略的维度[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3).
[42] See Donna M Hughes. The Use of New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for Sexual Exploita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J].Hastings Women's Law Journal,13(1): 128.
[43] Morris, Arval A. Voluntary Euthanasia[J].Washington Law Review, 1970,45(2):244.
[44] Diaconescu, Amelia Mihaela. Euthanasia[J].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Law and Social Justice,2012,4(2):80.
[45] [美]戴维.霍瑟萨尔,[中]郭本禹.心理学史[M].郭本禹,译.北京:北京邮电出版社,2011.
[46] 程燎原,作为方法的权利和权利的方法[J].法学研究,2014,(1). [47] 王庆廷,新兴权利渐进入法的路径探析[J].法商研究,2018,(1). [48] 刘卫先,自然体与后代人权利的虚构性[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6).
[49] 钱继磊.论作为新兴权利的代际权利——从人类基因编辑事件切入[J].政治与法律,20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