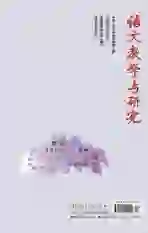《卖炭翁》叙事的三个维度
2021-08-27潘霄阳
潘霄阳
在“诗缘情”观念的影响下,人们特别注重诗歌的抒情特质,因此对叙事诗的关注略显不足,相比抒情诗,对叙事诗进行文本解读时存在的问题也更多。古代叙事诗将叙事和抒情高度结合,叙事诗是叙事的诗,也是诗意的叙事。从内容上来说,古代叙事诗取材于现实生活,作者以诗的形式记录历史变迁、社会动乱、人事沧桑。故本文以《卖炭翁》为例,立足于事、诗、史三点,从叙事中所寄寓之情志、通过艺术手法所表现之讽喻以及题旨中隐含的历史三个角度对《卖炭翁》进行解读。
一、叙事中寄情志
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中,充分显示了他高超的叙事技艺,题材集中是他叙事诗的特点之一,选材典型,“一吟悲一事”,但在诗中少议论,通常将情志寄寓在叙事之中。《卖炭翁》一诗集中刻画卖炭翁烧炭、运炭、卖炭、失炭的过程,借此反映宫市制度给百姓带来的苦难。白居易以第三人称口吻作冷静的客观叙事,将强烈的感情寓于其中,不露声色,通过对事件的叙述将主观意志自然地流露出来。诗人不同的叙事节奏背后是对老翁的同情和对宦官的斥责。全诗共十句,其中六句是对老翁的描写,细读发现,作者在叙述老翁烧炭、运炭的经历时,叙述节奏缓慢,且卖炭翁的动作也表现得很慢。一是老翁烧炭慢,诗歌首句云“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诗人用一句概括了卖炭翁伐薪烧炭的过程,但对如何烧炭稍有了解便知,无论是伐薪还是烧炭,这一过程是漫长而又艰辛的。老翁要在山林深处砍柴伐薪,再将其一捆一捆背下山,这一过程对老翁来说无疑是极其艰难的,但这仅是烧炭的开始,造窑烧炭更是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在高强度的劳作下,两鬓斑白的老翁在烟熏火燎中变得面色灰沉,十指尽黑。除了烧炭慢,运炭也慢。老翁年老体衰,衣衫单薄,又加之“夜来城外一尺雪”,往来赶车的人马早已将路上的积雪变成了冰冻的车轮印,老翁牵着牛,拉着千余斤的炭,到了“日已高”之时,走得“牛困人饥”,方才行至南市。此时积雪已经融化,疲惫的老人在泥水中休息。作者的“镜头”对着卖炭翁时,所有的叙述和动作都变得缓慢,似乎作者陪着老人经历了这一过程,一起伐薪烧炭,辛苦攒下千余斤,一步一滑的往宫市赶去。老翁的慢拉长了他的艰辛,也蕴含着作者对老翁的同情,无论多么疲惫,等到开市,木炭卖完,老翁的日子总还是有希望的。下句转入对宦官的描写,作者的叙事节奏加快,相比卑微的老翁,宦官们的动作和神态就潇洒了许多,从“翩翩”一词可见宫使骑马来的速度之快、状态之轻松自如,他们不仅来得快,与卖炭翁的交易也很快,“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把”、一“称”、一“回”、一“牵”,短短两句诗之内,宫使完成了一系列的强买(掠夺)。宫使快速出现、快速宣读、快速掠夺,这速度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熟练动作的背后,是宦官权力之大,掠夺次数之多,受害人数之广。故使者的“快”,更体现的是他们的残忍,三言两语将卖炭老翁漫长的等待和希望迅速扑灭。诗歌虽以“卖炭翁”为题,题下序“苦宫室也”,点明诗的题旨,但诗人在诗中并未直接表态,而是将褒贬融于叙事之中,诗的讽喻意味不言而喻。
叙事诗将叙事与抒情统一,诗人在叙事中寄寓情志。中国古代的叙事诗大多为“尚用”之作,自《诗经》起,已有采诗以“观风俗、知薄厚”的惯例,到汉代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至唐代新乐府秉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思想。即重视其社会功用,通过记叙典型事件,以表达作者创作的意旨。叙事诗既然是“诗”,必然区别于其他叙事文体,严羽《沧浪诗话》云:“诗者,吟咏性情也。”[1]因此,诗必然拥有诗的根本品格——抒情,否则,诗这一特别的叙事体式将与小说、戏剧、散文的叙事混淆。《春秋说题辞》云“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虑为志,故诗之为言,志也”[2],由此可见,在诗歌创作中,事与情的关系紧密,记事为手段,而抒情是目的。就叙事诗而言,事件是诗中最关键的部分,但抒情是诗的特质,叙事诗中仍有抒情,只不过作者多将情隐含于事的背后,以达到“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3]的效果,读者细品事件背后之旨,以优于创作者直白无力的情感表达。正如唐代刘知幾《史通》所言“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褥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4]在叙事中“用晦”,“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可以达到“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5]的目的,在玩味中体会“言有尽,而意无穷”。故对叙事诗的文本解读在厘清所叙之事的基础上,要发掘诗人寓于诗背后的情感,察兴寄之情志。
二、艺术手法中见讽喻
白居易的讽喻诗以“讽谕之诗长于激”的特色而突出显著,与其在诗中运用的各种艺术手法息息相关。《卖炭翁》作为典型的讽喻诗,也体现着白居易讽喻诗在语言艺术上的风格与魅力。在《卖炭翁》一诗中,白居易以旁观者的口吻作客观叙述,叙事真切,在映衬、对比和人物形象塑造中见爱憎。全诗贯穿的对比艺术是体现讽喻的重要手法,诗中的对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人物形象的对比,共有三重,第一重是外貌上暗淡与光鲜的对比,老翁常年烧炭,脸上是烟熏火燎的印记,手上是炭火的痕迹,两鬓间满是花白的头发,生活给老翁的底色是白、灰、黑。而宦官和他的爪牙,一出场就是黄衣和白衫,对比老翁衣着光鲜,色彩明亮。形象上强烈的颜色对比暗喻着他们的生活状况,暗无天日与光鲜亮丽。第二重对比体现在两者的动作上,正如前文所说,宫使的“快”残忍地将老翁的一点一点积累起的希望打破,一快一慢之间人物立见高下。第三重对比是言语的对比,隐含在作者塑造人物的方式之中,作者在描写老翁时,采用了外貌描写、动作描写和心理描写,而塑造使者形象时,除了外貌描写和动作描写,还有语言描写。两者对比,老翁在故事中始终没有发声,他默默地砍柴、烧炭、运炭,即使最终被抢,也只能无奈又无声地收下“半匹红绡一丈绫”,沉默着接受生活无所寄托的结果,而嚣张的使者,又是“称”,又是“叱”。一言一默中,尽是老翁的无可奈何,有苦难言。其次叙事结构上的对比,全诗共十句,前六句是作者对老翁形象的渲染和经历的铺叙,而诗的最后却只用“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短短一句点染故事的结局。老翁历经艰难制成千余斤炭火,他将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于这车炭上,但他的希望在宫市一“叱”、一“牵”中全部破灭,这强烈的对比之下,是作者对贫苦百姓的同情和压迫者的痛恨。除此之外,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凸顯了《卖炭翁》一诗的讽喻意味。作者塑造老翁形象时,既有外貌描写,又有心理描写。“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寥寥几笔勾勒出老翁的形象特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心理描写,将黑暗社会环境下底层百姓扭曲异化心理的刻画得入木三分。寒冬腊月,无衣蔽寒,老翁期盼天气转暖才是正常心理,然而,他却希望天气更加寒冷,多卖炭以求自保。底层百姓的生存之难在这种无奈的心愿和天寒无衣的生活苦况对比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诗人对老翁的悲悯之情油然而生。
诗歌内容的表达寄托于诗歌的形式,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是叙事诗有别于抒情诗的特点。如何叙事,如何塑造人物形象对主题表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叙事来说,一定的价值取向决定一定的叙述视角,而视角又影响了事件展开的方式。在对叙事诗的解读中,叙事视角和结构往往容易被忽略,但诗人叙事的视角和建构事件的方式中隐藏着诗人对事件的态度。塑造人物在叙事文学中十分常见,外貌、动作、语言是人物塑造的惯用角度,诗歌因其篇幅有限对人物的塑造难以面面俱到,因此寻找诗人塑造人物最有意味的形式,由此切入解读人物形象,能够有助于理解人物对诗旨的作用。含蓄和“隐”是诗的重要特点,在叙事诗中也有所体现,诗歌的形式作用于内容表达,叙事线索、详略分布、细节刻画、典型塑造等都是诗人表达主旨的途径,故解析诗人所用之法能够深入地把握诗歌主旨。
三、题旨中见历史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就这四类诗歌,白居易最看重的是讽喻诗。白居易的讽喻诗反映了中唐社会的状况,同时,中唐社会的社会形态也是白居易创作讽喻诗的源泉。在《卖炭翁》中,白居易将镜头聚焦于老翁,记述老翁的悲惨经历,与他写实的文学观念分不开,白居易认为诗歌应是“补察时政”,正如他在《新乐府序》中所言“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6]他继承了《诗经》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同时这也与他当时谏官的身份和政治理想有关。白居易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左拾遗即为谏官,有直接向皇帝进谏的机会。当时和谐的君臣关系推动了白居易讽喻诗的创作,唐宪宗即位后,展现出虚心纳谏、励精图治的强烈愿望和决心,标榜“纳谏思理,渴闻谠言”。《新唐书》说:“宪宗刚明果断,自初即位,慨然发慎,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卒收成功。自吴元济诛,强藩悍將皆欲悔过而效顺。”[7]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白居易作为谏官十分尽责,在《初授拾遗》中有这样的两句“惊近白日光,惭非青云器。天子方从谏,朝廷无忌讳”。[8]只有“天子方从谏,朝廷无忌讳”的客观条件,谏官才能发挥它的作用,白居易虽云“惭非青云器”,但内心深处应为“当为青云器”的宏愿。故至元和五年,写下了《新乐府》50首及《秦中吟》等讽喻诗。白居易以《卖炭翁》记录当时宫市制度迫害百姓之史。宫市是唐德宗贞元时期的一大弊政,即宦官到市场强买,用价值不对等的物品换取百姓的货物,或直接空手掠夺,是对被统治阶层的压迫。韩愈有文记载“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来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自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9]唐玄宗后期,募兵制兴起,地方权力扩大,军事局面转为外重内轻,中央无力控制,安史之乱后,各地自专,不听朝政,形成“藩镇割据”,藩镇势力对中央政权影响极大,致使宦官势力不断扩大,百姓苦于宫市,谏官御史数奏疏谏,但“宫市亦不为之改易”。《卖炭翁》中老翁的经历则为当时百姓之苦的典型事例,诗中“黄衣使者”即为宦官,“白衫儿”则为宦官说指派的白直,他们用“半匹红绡一丈绫”强买千余斤炭,并勒令老翁向北将炭送入宫中。唐代绢帛可当做货币使用,但钱贵绢贱,如此交易实在欺人太甚!老翁只是当时苦难百姓的一个缩影,这背后是中唐时期腐朽的政治和黑暗的社会。孟子有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0]在孟子笔下,理想王国应为“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而《卖炭翁》中的老翁在常年的烧炭生活中满面灰尘,十指乌黑,即使终日劳作,仍换不来身上衣裳,口中食。衣不蔽寒,食不保暖是老翁生活的常态。朔风凛冽,大雪风飞,老翁衣着单薄,却希望天再冷一点。这样的生存状态与“七十者衣帛食肉”相差甚远。仅从诗句中解读百姓苦于宫市,未免有些单薄,在历史背景的支撑下,用更广阔的视角看待所叙之事,所陈之史,对读者理解诗中寄寓的讽喻及诗人对底层百姓的同情更有一助。
“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意旨始终与‘史相联”[11],诗可为史的载体,记录历史,同时阐述诗人心中的道义。“诗史”一词简明地将诗与史联系在一起,“诗史”出现在唐代孟棨《诗本事》“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12]。孟棨将杜甫作品的特征描述为“推见至隐,殆无遗事”,即对自己的经历叙述得十分详尽。诗除了记录个人的经历以外,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思想,也将时代痕迹烙入诗中。在叙事诗中,当诗人呈现某一故事时,直接展现的是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一段历史记忆,叙事诗描写的人物、事件所表现的思想、情感,都与社会紧密相关,叙事作品也可看作是生活的“镜子”。叙事诗诗人通过对一位现实人物人生经历的描述,选取典型事件、塑造典型人物,通过对个体悲剧的书写,映射出整个时代的盛衰。叙事诗“以诗传史”的特点决定了在叙事诗的文本解读中,诗歌所记之史的重要性,挖掘事背后的隐含的历史并揭示所陈之史的意义定对解读文本有所裨益。
叙事诗的文本解读,有别于抒情诗与其他叙事文体,解读时只突出“诗”或“叙事”失之偏颇,故既要把握叙事诗作为叙事文学的特点,理清所记之事。也要结合我国古代叙事诗记史的作用,体察历史。同时要回归于诗歌的特质,探究艺术手法对诗歌题旨表达的作用,三重角度的结合更能凸显叙事诗独特的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688.
[2]毛亨,传,(汉)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M]//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点校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
[3]刘勰著,郭晋稀注译.文心雕龙[M].长沙:岳麓书社,2004:388.
[4][5]刘知几撰,黄寿成校点.史通[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52,52.
[6]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36.
[7]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13.
[8]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35.
[9]韩愈.顺宗实录(卷2).丛书集成初编(第38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4.
[10]杨伯峻,杨逢彬导读注译.孟子[M].长沙:岳麓书社,2019:8.
[11]程相占.中国古代叙事诗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
[12]孟棨.本事诗,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