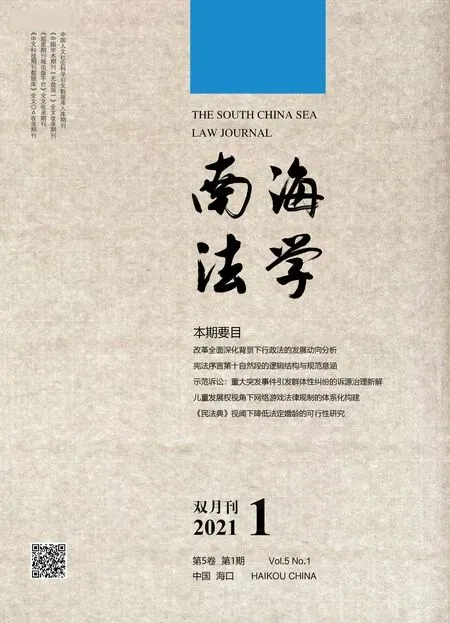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的逻辑结构与规范意涵
2021-08-16崇文瑞
崇文瑞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北京海淀 100089)
引言
宪法序言是“熔炼”了历史陈述、国家目标、国家政策的文本,其与宪法正文在结构形式和文本内容上泾渭分明,如何解释序言构成一个实质的解释学问题。在宪法序言中,第十自然段具有特殊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现实仍在运行的组织实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序言中少见的明确描述的“制度”形式。①其他“制度”表述有:“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基于前文所述的特殊性,本文将对第十自然段进行解释活动。对第十自然段的解释涉及以下问题:为何要在序言中安排第十自然段?第十自然段的文本是依照何种逻辑或结构组织成段的?第十自然段的各句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文本中所涉概念有何含义?各句发挥何种效力,如何发挥其效力?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理解新中国的政治构成,有助于理解中国宪法的基本背景。
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是以三个核心概念为内容的语句集合,这三个核心概念分别是“爱国统一战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除必要引用外,以下简称“人民政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除必要引用外,以下简称“政党关系制度”)。相关宪法研究有三个特点:第一,部分学者惯于通过宪法史和政治宪法学的路径研究第十自然段相关概念背后隐含的政治结构、主权结构或治权结构;①参见翟志勇:《八二宪法的生成与结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76—88页;高全喜、田飞龙:《协商与代表:政协的宪法角色及其变迁》,《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143—154页;韩秀义:《人民政协本体意涵的宪法学阐释——以“一体二元三维”为框架》,法律出版社,2016。第二,在三个宪法概念中,人民政协和政党关系制度得到了更多的学术关注,②参见郭道晖:《政协:社会权力与准国家权力》,《法学》2008年第3期,第42—48页;胡筱秀:《国体与政体之间的关系研究——兼论人民政协制度的定位》,《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9期,第75—86页;王中伟:《人民政协宪法化问题的比较法研究——从国外成文宪法中的特设机构谈起》,《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第46—51页;周刚志、刘佳威:《“人民政协”宪法性质之法理辨析》,《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6年第4期,第34—39页。统一战线的宪法研究则较少;③参见阿力木·沙塔尔,胡弘弘:《“爱国统一战线”的规范意义及规范体系构建》,《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第69—75页;祁小敏:《宪法中“爱国统一战线”新发展的规范阐释》,《晋阳学刊》2019年第6期,第116—120页;任杰:《爱国统一战线是宪法确立的政治制度》,《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65—69页。第三,近年来的研究存在进一步微观化倾向,最为突出的作品是陈赛金先生对“人民团体”概念宪法原意的研究。④参见陈赛金:《人民团体在法律中的指代范围应符合宪法原意》,《法学》2020年第6期,第110页。
本文旨在根据宪法文本对序言第十自然段作解释与评注工作,注重发掘第十自然段在宪法序言中的特殊地位,研讨第十自然段语句之间的内在内联,解释第十自然段中重要概念的规范意涵。对于效力问题,笔者主要采取规范性效力和执行性效力⑤“规范性效力”包括“依据性规范效力”和“解释性规范效力”,“执行性效力”侧重“序言的相关表述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规制价值。”规范性效力主要通过宣示来发挥法律确认功能,执行效力主要通过立法性实现机制、规范效力传导机制和软法性实现机制来发挥其功能。更具体的内容,参见郑毅:《〈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效力论》,《法商研究》2017年第4期,第41—51页。的二分法来确定第十自然段每一句的效力,并特别关注其可能的裁判规范性。⑥参见钱宁峰:《论宪法序言的裁判规范性》,《金陵法律评论》2008年秋季卷,第70页。
本文的制度意义在于,现实中相关组织与制度的完善要在“依照宪法法律和政协章程准确定位的基础上”⑦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第2版。,本文对文本的解释过程与结果实际上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组织与制度的规范依据;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宪法序言中政治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分野⑧“中国法治和宪政的发展道路应该是政治的归政治,法律的归法律。具体地说,应着力发展日常的具体的法治,以此训练司法的专业能力,提高司法在宪法结构中的地位和独立品格,在原则问题、价值问题、政治问题、议事形态问题上应走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宪政主义道路。”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第486页。以文本的具体分析为前置工作,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的特殊研究也有助于为宪法序言的一般理论提供素材。
一、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的逻辑结构
“结构解释”或称“体系解释”,一般是指“每一项共同体的法律条款都必须根据其上下文及法律的整体结构而获得一致解释”。⑨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14,第200—201页。由于此处并非探索序言第十自然段在特定案件中的解释结论,所以仅讨论第十自然段作为文本的结构存在与结构特点。首先,序言第十自然段被立宪者在形式上构造成具有整体外观的自然段,因此第十自然段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判断其在宪法序言结构中的地位。其次,序言第十自然段内部的语句在内容上具有关联性和差异性,须判断不同语句之间的关系,探讨语句为何采取现行形式排序。
(一)序言第十自然段与宪法序言的逻辑关系
一般认为,宪法序言第一到六自然段属于历史叙述、历史经验,第七自然段陈述“国家的根本任务”,第十三自然段规范宪法地位与作用。但第八到第十二自然段的意义可作不同解读,第十自然段也可以展现出这两种微妙的理解差异:
第一种理解认为,第十自然段中的内容是实现序言中国家任务的条件之一。该观点的理由是:第七自然段为国家任务,第八、九自然段为“阶级斗争”和“国家统一”的宪法任务,①“序言历史经验之后的一系列宣示与叙说,不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抑或是‘阶级斗争’与‘统一祖国’的宪法任务,乃至于为完成上述任务的统战、政党、民族和外交政策等逐项保证条件,都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宏大叙事,同时也是对上述问题的根本性回应与解答。”张薇薇:《宪法序言:政治宣示抑或宪政理想——以我国现行宪法序言的完善为中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87页。第十自然段第一句明示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依靠能团结的各类力量,而且第十自然段正好在序言有关国家任务的描述之后,所以第十自然段中的内容构成完成国家任务的条件。②参见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第85页。基于团结功能和团结价值的分析,参见张劲:《团结宪章——宪法的中国意义》,《政法论坛》2014年第1期,第3—16页。这种理解在1954年宪法序言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③“序言的第四个自然段规定了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基本条件……尽管在序言中没有具体规定统一战线的功能,但这一宪法地位的表述,实际上肯定了以后社会发展中统一战线的作用。”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第384页。但现行宪法只能依靠自然段的顺序作出该推测。
第二种理解认为,第十自然段是一种对阶级关系、界别关系、政党关系等人民内部关系④《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2020年修订)第3条:“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是……积极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加以规范的政策性⑤参见田飞龙:《宪法序言:中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江汉学术》2015年第4期,第34—35页。或制度性规范,这是从本体意义角度进行的。例如,认为第十自然段是“对国家建设赖以依托的宏观政治制度的坚持”,⑥韩秀义:《人民政协本体意涵的宪法学阐释——以“一体二元三维”为框架》,法律出版社,2016,第123页。认为“统一战线与政治协商”是“作为基本的执政方略发挥作用……作为基本的政治制度发挥作用”。⑦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学术月刊》2003年第4期,第22页。这一点在1978年宪法序言中有所体现,1978年宪法序言第六自然段在描述完统一战线后继续写道:“要加强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在全国人民中努力造成……”亦即,统一战线有特定的存在理由。
按照第二种理解,第十自然段是宪法正文施行的政治事实前提。宪法是有关国家存在与国家运作的法,宪法正文所规范的基本权利和国家机构以国家的存在为前提,“国家是一种状态,确切地说,是一国人民的状态……人民作为与其自身直接同一的实际在场的实体,构成了一个政治统一体。”⑧[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272页。宪法第2条第2款旨在说明,人是基于人民身份成为政治统一体的一分子;宪法第33条旨在说明,人是基于国籍而成为公民,基于公民身份而享有宪法规定的形式平等和基本权利。但是基于人民身份而产生的政治统一体存在两个风险:第一,人民内部可能因为文化、民族的差异影响政治统一体的稳固性。第二,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存在,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不是所有阶级的先锋队;人民可能因为阶级差异影响政治统一体的稳定。因此第十自然段是在寻求各种途径来强化本国人民的同质性以稳固政治统一体。①从这个角度来说,第十一自然段也是为了提高国民的同质性。参见卡尔·施密特对“民族性平等”的分析,[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306—309页。一方面,第十自然段将存在差异的人民统和在“爱国”的属性下,另一方面执政党通过领导、协商与其他政党、群体代表进行联合,从而将执政党对无产阶级、工农联盟的领导扩展到对所有阶级的领导。
(二)第十自然段内部条文的逻辑结构
第十自然段共四个复句,其推进的逻辑结构如下:
第一句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该句宣誓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作为目标除了依靠工农联盟和知识分子外还需要其他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实现这个基本理念,后续三句提供了富有层次性的解决方法。
第二句明确写道,中国“已经结成……爱国统一战线”,这是在陈述中国共产党原本使用的政治联盟和政治策略,这种策略是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具体化,基于历史经验,当延续这种政治策略时,第一句中基本理念被预想为可以实现的——“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
第三句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组织实体(会议)或场景(协商的场所)来实行统一战线。第三句在两个层面使得爱国统一战线更加具体:首先是主体的具体化,原本抽象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劳动者、建设者和爱国者可以通过人民政协的机制转变为具体的个人;其次是团结行为的具体化,团结行为在人民政协中被解构成“拥有参与会议的基本资格”“代表特定政党、团体或群体参与会议”“在会议上政治协商”。会议使得统一战线具体化的同时,实际上也缩小了统一战线的范围——未参与人民政协的人员仍旧被视为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保留参与人民政协的可能。
第四句描述的是“多党合作”,即党与党之间的关系,这种描述剥离了第二句中的“人民团体”,也剥离了不具有政党属性的其他被团结群体。第一句进一步缩限了统一战线的对象,将政党关系作为重点描写的对象。
这四句逻辑关系的图示如下,其中的圆的大小主要是统战对象在种类上的差异。但严格地说,人民政协不能完全包容政党关系制度的所有内容,政党关系还包括实践中发展的其他政党间交互行为,详见后文对第四句的释义。

图1 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内部条文的逻辑结构
二、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的规范意涵
以下对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规范含义的阐释将以现行宪法的条文为中心,以逐条释义的方式进行。第十自然段共四个复句,本文按照文本内容将其分别命名为“文本目的之句”“‘爱国统一战线’之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句”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句”。
单一复句的解释主要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是复句的性质或地位界定,第二是复句的具体释义。具体释义过程中侧重讨论以下问题:基础概念的释义,该复句与宪法其他文本的关系,宪法对政治命题的澄清,复句的效力等。
(一)文本目的之句
本句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文本目的”之句主要为后三句提供文本层面的前置合理性,即立宪者通过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认知,为政治理念(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实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政党关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供除规范本身以外的其他论证,其类似于其他立法中的立法目的。
本句对目的的描绘并不构成一种当然的事实或者具备约束性的规范,其更近似于一种基于某种前提下的立宪者假定。从后三句的具体描述中可以看出,这种假定一部分来自历史经验,即中国共产党认知到统一战线理念、人民政协和政党关系制度发挥的历史作用,并预想其能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发挥作用。①后三句对历史的追溯分别是:第一,“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第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
(二)“爱国统一战线”之句
本句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
1.文本的性质或地位界定
第一,“爱国统一战线”之句陈述了执政党领导社会的方式。“统一战线的范围愈大,党的领导得以延伸的领域也便愈广。”②秦前红、刘怡达:《中国现行宪法中的“党的领导”规范》,《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24页。第二,“爱国统一战线”之句为理解人民政协和政党关系制度提供基本理论背景。
2.具体释义
(1)“爱国统一战线”
“爱国统一战线”属于政治概念,③参见秦前红、刘怡达:《中国现行宪法中的“党的领导”规范》,《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24页。是用于展现具有纲领差异性、属性差异性的团体、人群在政治上的关联性,中国共产党将其定性为政治“联盟”。④《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2020年修订)第2条第1款:“本条例所称统一战线,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
“爱国统一战线”在文本中首先被建构为一种拟制的社会事实或者社会关系,文本中被形容为“已经结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战线的发展同时依靠一套方法论指导,因此“爱国统一战线”也是一种政治理念。
(2)统一战线的领导者
统一战线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爱国统一战线也是中国共产党建构的政治概念,爱国统一战线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局势①1954年宪法时,统一战线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75年宪法时,统一战线为“革命统一战线”;1978年宪法时,统一战线仍为“革命统一战线”,但相对1975年宪法,78年宪法的团结对象更多;1982年宪法修改为“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前的修饰词主要与执政党对政治形势的判断有关。与现期目标②当中国共产党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其便于2018年将共同推进该目标的爱国者团结进爱国统一战线。的看法,中国共产党适时将其理解或认可的目标与群体加入统一战线理念中。由于中国共产党自行决定统一战线的目标和范围,所以很难依据该语句中的历史陈述和未来展望来评价执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否违宪。
(3)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
本句对爱国统一战线参与主体的描述上存在分层:第一层是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第二层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下文简称“四类统战对象”)。
虽然宪法并没有描述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具体是什么,但是党派和团体属于拟制群体,会以特定名称命名以人格化,而四类统战对象则属于对人的客观属性的描述,不具有特殊性;进一步说,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指向的是已经形成稳固架构的组织,是结社的结果,而四类统战对象指向的是符合属性描述的不确定个体。从上述意义来看,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与四类统战对象不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基于结社形成的社会团体所能保障的统战对象是边界稳定的,而基于属性描述的统战对象是边界不稳定的,因此四类统战对象是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补充。
在微观层面上,执政党选择哪些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作为统战对象是执政党的政治选择,宪法不能提供评价标准;此外,四类统战对象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事实上导致无法借由四类统战对象的分类来评价执政党是否进行了合宪的统战工作。③现行的统一战线工作范围与宪法的描述也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可参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2020年修订)第5条。
(4)“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
由于实践中可以确定参与建国和参与政治协商会议的八个民主党派,④人民政协中与党派有关的团体或组织一共有10个,除了中国共产党和无党派人士,剩下的8个民主党派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所以民主党派的外延一般不会产生争议。问题在于“人民团体”是指哪些团体?
《人民团体在法律中的指代范围应符合宪法原意》一文认为:人民团体是指八家人民政协的组成单位,⑤它们分别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除了前注提到的10个组织,此处提到的8个团体,政协对剩下的代表使用“界”“特邀”和“特别邀请”来命名。参见中国政协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2021年5月1日访问。其主要理由是“从文义分析可知,人民团体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而统一战线的主要组织形式是人民政协,所以人民团体是人民政协的组成部分(单位),这是宪法含义。”⑥陈赛金:《人民团体在法律中的指代范围应符合宪法原意》,《法学》2020年第6期,第113页。其他理由还有:政协代表可以区分为以组成单位为名义的参会代表和以个人名义参会的代表,个人名义参会代表的单位是参加单位而不是政协的组成单位;全国政协组成单位在七届十二次常委会后稳定为8个团体,具有稳定性;《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一共有23个群团组织,分别是参加人民政协的8个团体和15家免登记团体,其中人民团体享有一些特殊的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权力;等等。人民团体相对于其他群团组织具有两种特殊的特征,第一是其属于政协固定的组成单位,具有较高的稳定性,第二是人民团体与政协中的其他党派一样具有高度的政治性。①参见陈赛金:《人民团体在法律中的指代范围应符合宪法原意》,《法学》2020年第6期,第114页。其隐含的推论是: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主要具象化形式,政协协商实践中稳定地以“团体”名义参与人民政协的团体是“人民团体”。本文认为,这种体系解释对于现行文本是成立的。②但是对于历史文本并不成立,例如1954年宪法序言第四自然段对统一战线的描述“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与人民政协没有对应关系。
(5)“爱国统一战线”与宪法序言第八自然段构成内容上的对应关系
宪法序言第八自然段蕴含的规范意味是:国家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不在内部进行大范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③参见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法律出版社,2018,第87页。但要和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继续斗争;爱国统一战线条款则要求持续地进行团结活动,以形成更加广泛的统一战线。因此爱国统一战线客观上弱化了国内阶级之间的对立,但是有助于反对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
基于历史解释,这种观点也是成立的,因为1954年宪法序言第四自然段的第二句明确写道:“今后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6)本句的效力
本句具有依据性规范效力,即确认和宣示了这一政治事实——党通过统一战线形成政治联盟将其领导权扩展至其他阶层和群体。本句可以通过立法性实现机制和软法性实现机制实现其执行性效力,例如通过《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予以实施。
(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句
本句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1.文本的性质或地位界定
第十自然段第三句规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五个分句,本句承接了“爱国统一战线”之句,为“爱国统一战线”提供了具象化的组织形式,并为人民政协的存在提供宪法依据。④1980年11月中旬,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宪法研究室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的十二条建议,其中第十一条表示应规定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它更有发展的趋势。这么大的一个组织,不见于宪法是不合理的。建议在宪法序言中列入统一战线问题,并在具体条文中反映人民政协的地位、职权和地位。”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第580页。中国政治学会与会者对宪法的修改意见包括“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需要加以明确”。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第601页。
2.具体释义
(1)“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现行宪法中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历史作用描述得非常抽象,需要追溯到1954年宪法对人民政协的规定:中国宪法发端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制定源自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的“号召”⑤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第27页。,这种“号召”意味着制宪行为不是以全体国民的政治平等①有关民主制的平等概念,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300—313页。为前提进行的,因此斯大林曾向刘少奇预警,②斯大林对刘少奇说“《共同纲领》也不是人民选举的代表大会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同意的东西。人家可以说你们国家没有法律。……如果人民选举的结果,当选者共产党员占大多数,你们在组织政府时给其他党派以恩惠,这样对你们更好。各党派在选举中如落选了,你们不应使统一战线破裂,你们应继续在经济上和他们合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537—538页,转引自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第66—67页。表示《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可能产生政权的合法性与合宪性风险。③参见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第67页1954年宪法修补了《共同纲领》的制宪风险,因为1954年宪法的制定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系由全民普选产生,普选则以全体国民的政治平等为前提。④“普选权不是民主式平等的内容,而是作为先决条件的平等的结果。全体国民被预设为平等的,只有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必须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平等的表决权等等。”[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301页。因此,可以认为《共同纲领》的制宪基础被1954年宪法的制宪基础吸纳了,体现在文本上则是1954年序言第三自然段详细描述了宪法与《共同纲领》的紧密关系⑤1954年宪法第三自然段第2句:“这个宪法以一九四九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1954年宪法的《宪法草案初稿说明》中写道:“宪法草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宪法草案在起草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共同纲领,在序言中说,宪法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而在内容上有新的发展。”参见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第107页。。这种描述客观上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国家与社会主义阶段的国家联系起来,表明虽然它们在某些原则上存在些许差异,但是仍旧属于同一个政治统一体,制定新宪法没有导致国家的变更。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统一战线组织”的关系
“统一战线的组织”的外延大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应理解为“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⑥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07,第68页。,因为还存在其他的“统一战线组织”,例如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统战部,⑦参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2020年修订)第9条:“党中央以及地方党委设置统战部。统战部是党委主管统一战线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党委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参谋机构、组织协调机构、具体执行机构、督促检查机构,承担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协调关系、安排人事、增进共识、加强团结等职责”。妇联、侨联、中华和平统一促进会,海外联谊会。⑧参见陈赛金:《人民团体在法律中的指代范围应符合宪法原意》,《法学》2020年第6期,第113页。政协是“主要组织形式”或者“有广泛性代表的统一战线组织”。⑨参见陈赛金:《人民团体在法律中的指代范围应符合宪法原意》,《法学》2020年第6期,第113页。此外,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孙起孟提出“草案中‘作为这个统一战线的主要组织形式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提法不妥。他说难道还有次要的组织形式?政协既是这样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次要的是什么就不好捉摸了。政协也不能说是‘组织形式’。建议改为‘作为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633页。现行宪法未依照上述表达,说明政协的确不是统一战线的唯一形式。
序言表明,政协组织作为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目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对历史上主要组织形式的沿用,这种沿用剥离了部分“历史作用”,政协的“国家机构色彩明显褪去”,⑩参见马一德:《论协商民主在宪法体制和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第104—206页。但仍旧存在剩余的“重要作用”在今后发挥。
(3)政协的“政治协商”
序言中的“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是对人民政协工作范围的说明,但序言文本并没有就政协的具体职能或者其重要作用的发挥方式加以详细说明,对其职能的具体说明首先来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从文本所展示的名称来看,人民政协也是政治协商的组织形式,①参见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50页。其工作职能就是“政治协商”。需要对“政治协商”作一个框架性界定:
“政治协商”中的“政治”决定了人民政协的工作游离于宪法确定的常见的法框架中的内容——不属于基本原则条款、国家目标条款,与基本权利规范体系无关,与国家机构的组织架构无关——其属于政治过程、政治行为、政治活动。在划定人民政协工作“疆域”的同时,“政治”协商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排斥“法律性”的存在,政协中讨论的问题国家机构不得染指,这些问题由领导者与其他主体自行决定,反之,政协也只能进行政治决定,不得侵犯国家机构的既有权限。②“通过政治协商会议的隔离作用,使党际之间的分歧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间化解,从而使得统一的意志能够进入到人民代表大会之中,这从每年的党的会议、政协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顺序就可见一斑。”翟志勇:《八二宪法的生成与结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87页。
历史解释支持这一文本解释结论,胡乔木在1982年4月12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介绍说道:“对某一个问题的决定,如果人大常委会采用一种意见,而政协又是另一种意见,那么权力机关就不一致了。全国人大做决定,不发生协商的问题。党派之间的协商亦不能同权力机关的职能相混淆。……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如何发挥,则应由政协章程规定。正如共产党的作用很重要,但没有必要写入宪法,而是在党章中去规定,道理是一样的。”③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第664—665页。
在该层意义上,政协和中国共产党的行为属性应作统一理解,“党的领导”条款和人民政协机制是一种隐含在国家机构“骨骼”后的权力行使和政治决策机制,宪法只是明示或者暗示了其政治存在并肯定其定位,但是两者的行为都不得超越宪法的明文规范。
在前述讨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判断人民政协的性质。人民政协属于中国宪法中的政治机构。④许崇德:《统一战线在宪法中的地位》,《群言》2003年第5期,第11页。“政治机构”是与宪法中的“国家机构”呈现对应关系的一种存在。⑤类似观点的文献,可参见浦兴祖:《关于准确把握政协功能的思考》,《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12期,第36—38页。认为人民政协是中国政治主权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位阶上隶属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参见韩秀义:《人民政协本体意涵的宪法学阐释——以“一体二元三维”为框架》,法律出版社,2016,第166—167页。认为政协领导人应视为国家领导人的观点,可参见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认为政协是不享有国家权力的半国家机构、半社会机构的观点,可参见郭道晖:《政协:社会权力与准国家权力》,《法学》2008年第3期,第42—48页。宪法不评价政治机构的政治过程、政治行为,不赋予其法律效果,也不确保其政治决策必然会成为国家机构的决定,只保障它的存在。
实务中出现的相关案例可为这一观点提供一个注解。在高某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哈尔滨市委员会一案中,高某对哈尔滨市政协强制拆除其房屋及安置补偿事宜不服将其诉至法院。一二审法院及再审法院的判决理由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其地方委员会不属于行政机关,其对高某房屋的强制拆除及安置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①参见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黑行申307号。其他案例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京0105行初432号。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对政协职能的规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②目前施行的《政协章程》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1982年12月11日通过,在1994年3月19日、2000年3月11日、2004年3月12日 和2018年3月15日由人民 政协全国 委员会会 议加以修 正。《政协章程》序言第三自然段对政协的界定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后文简称“《政协章程》”)序言第八自然段写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活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的准则。”《政协章程》由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通过,对于《政协章程》与宪法有关的相关内容,可视为中国共产党及其统战对象对《宪法》第十自然段的解释。因此《政协章程》是理解本句中相关问题最为合适的政治文件。有必要结合宪法与《协商章程》的规定作进一步讨论。
根据《政协章程》第3条第1款的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第2、3、4款分别对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与参政议政进行了解释。
《政协章程》第3条第2款对政治协商作如下定义:
“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地方的重要举措以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进行协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可根据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提议,举行有各党派、团体的负责人和各族各界人士的代表参加的会议进行协商,亦可建议上列单位将有关重要问题提交协商。”
第3条第3、4款分别对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作如下定义:
“民主监督是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改革举措、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情况,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解决落实情况,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等,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协商式监督。
参政议政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
《政协章程》采取的定义方式并非外延与内涵等较为明确的定义方式,这种定义方式导致了相关概念的外延丧失了客观化与形式化的品格与标准,③参见韩秀义:《人民政协本体意涵的宪法学阐释——以“一体二元三维”为框架》,法律出版社,2016,第304—305页。进而致使了三种职能存在交叉之处。具体体现在:
第一,职能的范围上存在交叉。“政治协商”中的“国家大政方针和地方的重要举措以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可以包括“民主监督”中的“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改革举措、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情况,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解决落实情况,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等”,也可以包括“参政议政”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而后两者之间也存在交叉的可能。
第二,职能的表现形式上存在交叉。《政协章程》并未在定义政治协商时说明协商的具体表现形式,只是说明“进行协商”“根据提议……进行协商”以及“提交协商”,协商本身作为一种工作方式存在;而在定义民主监督时,将其形容为“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协商式监督”,在定义参政议政时,将其形容为“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提出意见和建议”。《政协章程》在后文进一步具体化了政协委员们的行为,例如第44条第(三)项中规定的“协商讨论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提出建议和批评;”第(四)项中规定的“听取和审议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和其他报告;”第(五)项中规定的“讨论本会重大工作原则、任务并作出决议。”而这些表述既可以和政治协商的定义相互对应,也可以和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定义相互对应。
总体来看,《政协章程》对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采取了混沌的界定方式。本文认为,从词义来看,协商是一个中性描述,意在“共同商量以取得一致的意见”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2016,第1449页。,这是一类交互行为。这一类交互行为可以适用于参与政治、议论政治(参政议政)当中,也可以适用于监督活动(民主监督)中,但是不管是“参政议政”还是“民主监督”,它们都是“政治”活动,所以这两个职能只是概念上或者宣传上的冗余。
(5)本句的效力
本句具有依据性规范效力,即确认和宣示人民政协作为主要统一战线组织的政治事实。本句具有解释性规范效力,即“序言作为该法解释依据时所体现出的规范功能”,②郑毅:《〈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效力论》,《法商研究》2017年第4期,第45页。本句为解释“统一战线之句”的部分概念提供了解释依据。③一个典范是陈赛金先生对“人民团体”概念的研究,参见陈赛金:《人民团体在法律中的指代范围应符合宪法原意》,《法学》2020年第6期,第110—123页。
本句具有执行性效力。首先是本句可以通过《政协章程》来具体实施;其次是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与人民政协召开的相关宪法惯例结合,推论出人民政协应按照惯例每年举行一次,不按照该频次召开人民政协存在违宪风险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句
本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1.文本的性质或地位界定
本句规范政党之间的互相关系,同时说明了其他政党参与国家治理的方法。本句是对统一战线中的政党关系、人民政协中政党关系的制度化概括。
本句与序言第七自然段、正文党的领导条款组合构成我国政党制度的完整论述与宪法依据。
2.具体释义
(1)作为政党关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概念是一个偏正结构,中心语和语义重心是“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对该制度领导者和领导权的描述。
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概念相比,“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更侧重描述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概念是围绕“政治协商”而形成的,其假定的参与主体更加广泛;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则将“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绑定,只有拥有政党身份才可以进行“政治协商”并进入该制度的调整范围。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本句所涉制度的论述中心是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有文献直接将其简称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政党制度》,2007年11月16日第15版。但除了此种简称,还有一种倾向是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认定为我国的“政党制度”。②《政协章程》即采取了这一描述,《政协章程》序言第六自然段写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另参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2020年修订)第12条第1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这两种简称虽然在形式上不至于产生误解,但是其所指向的实际内容可能是存在差异的。
我国现行宪法文本对政党事务的规范一共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这一部分内容以往主要由序言第七自然段③序言第七自然段第一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序言第七自然段第三句:“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作为论证基础,2018年修宪后则可由党的领导条款结合序言第七自然段作为论证基础。第二,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以及基于这种关系客观上产生的参政党对国家事务的可能影响,这一部分内容主要由宪法第十自然段作为论证基础。④这是基于党与国家关系、党与党关系的一般论述。围绕党的领导条款展开的规范体系研究,可参见秦前红、刘怡达:《中国现行宪法中的“党的领导”规范》,《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22—27页。因此,当描述我国(宪法)的政党制度时,不能仅描述政党间关系这一部分,而忽略党与国家关系的论述。⑤例如张千帆教授在《宪法学导论》一书有关“政党与宪法”的讨论中,不仅仅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人民政协等内容,还描述执政党、参政党与政府的关系等内容。参见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2014,第435—440页。因此,在命名上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描述为“政党制度”,要么忽略了宪法第1条第2款第2句的规定,要么便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扩大解释,使其与宪法第十自然段相悖,例如国务院新闻办便认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等执政党与国家关系的内容。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政党制度》,2007年11月16日第15版。
因此,本文认为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概括为“政党关系制度”更符合宪法文本。
(2)政党关系制度与统一战线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涉及政党间关系,这属于统一战线理念需要调整的关系之一,政党关系制度将此类关系定型为制度形式,用该句表达政治承诺并加以规范。有观点认为“统一战线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基础与理论基础,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与制度形式”⑦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学术月刊》2003年第4期,第21页。。该观点的前半句符合宪法文本,但后半句不够精确,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只体现了统一战线中有关政党关系的内容,未体现政党关系以外的其他统战群体。
(3)政党关系制度与人民政协的关系
政党关系制度与人民政协不具有完全对应关系。“人民政协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摘要)》,《中国统一战线》2006年第4期,第4—6页。人民政协的某些协商活动是执政党与其他非政党界别间进行的,政党关系制度不包括该内容。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合作也不局限于人民政协这一单一形式,而是会基于多党合作实践逐渐生成其他政党间交互行为,例如召开民主党派内的参政议政工作会议、为政府提供参政议政成果、编发专报、提供信息,②中央统战部网站:《民间杭州市委会抓“实、深、新”促进参政议政提质增效》,http://www.zytzb.gov.cn/czyz/352353.jhtml,2021年5月1日访问。在法院、检察院工作情况通报会上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③中央统战部网站:《河南省委统战部召开省法院、检察院工作情况通报会》,http://www.zytzb.gov.cn/czyz/350253.jht⁃ml,2021年5月1日访问。等等。
(4)政党关系制度的“政治协商”
第十自然段的第三句和第四句都使用了“政治协商”概念,政党关系制度的“政治协商”在文本上应与政协的“政治协商”作同义理解,即确定多党合作属于政治行为,宪法不予评价,但保障其存在。由于参与者作为政治机构可以自行发展人民政协和政党关系制度的制度细节,所以“政治协商”主要因其所处的场景而产生差异。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第13条规定:“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无党派人士是政治协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参加政党协商。……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以及其他方面的协商。”因此协商活动按照发生的场景被区分成了多种形式,在人民政协上发生的被称为政协协商,在政党间发生的被称为政党协商。
(5)本句的效力
本句明确宣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协协商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事实,其作为基本政治制度被宪法所确认,因此本句具有依据性规范效力。本句传达出的规范意涵包括“课以国家不得阻碍和放弃党际合作协商的消极义务,以及有效促进党际合作协商的积极义务”④秦前红、刘怡达:《中国现行宪法中的“党的领导”规范》,《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因此本句具有执行性效力,违反消极义务完全停止政党间合作的行为存在违宪风险。此外,本句也可以通过《政协章程》达成其执行性效力。
结语
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是实现序言中国家任务的条件之一,也是强化人民同质性、扩展执政党领导权、稳固政治统一体的政策性或制度性规范。第十自然段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目的导向,以“统一战线”的历史策略和政治理念为理论背景构建的文本,文本中提供了两种具象化“统一战线”的制度,分别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构建并阐释的政治概念,“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以特定结社结果为特征,“四类统战对象”则以属性描述为特征,“爱国统一战线”之句与宪法序言第八自然段具有对应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主要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在现行宪法框架下,“政治协商”职能限定了政协组织的政治机构属性,宪法不评价政治机构的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不赋予其法律效果,也不确保其政治决策必然会成为国家机构的决定。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解为政党关系制度更符合宪法文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句与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党的领导条款构成我国政党制度的规范基础,政党关系制度与人民政协描述的统战对象和统战方式不具有严格对应关系。
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规范的内容属于重要的政治话题,以往多有学者们以此为论证材料,从宪法史或政治宪法学的角度,讨论党与国家的关系、我国的主权与治权结构。①代表性的作品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第485—511页,另可参见翟志勇:《八二宪法的生成与结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76页;陈端洪:《宪治与主权》,法律出版社,2007;韩秀义:《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世界——以“宪法常识”为核心》,《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第38—48页;韩秀义:《人民政协本体意涵的宪法学阐释——以“一体二元三维”为框架》,法律出版社,2016。考虑到宪法序言的文本特点和第十自然段的文本内容,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注定很难如正文一般在基本权利案件、国家机构权限争议中大放异彩,但第十自然段是宪法的组成部分,本文对第十自然段的释义至少可以对部分概念和理论争议提供基于宪法文本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