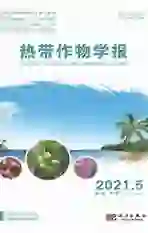SSR分子标记鉴定橡胶树F1真伪杂种
2021-07-20李文秀贺军军张华林罗萍
李文秀 贺军军 张华林 罗萍



摘 要:早期快速鉴定橡胶树F1杂交子代,获取真杂种对橡胶树优良品系的创育和遗传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橡胶树优良品系‘PR107和‘93-114进行杂交,获得杂交组合子代,以亲本作为模板从104对SSR引物中筛选出3对多态性引物对35株杂交子代进行真实性鉴定,结果表明:35株杂交子代均鉴定为真杂种苗;筛选出的3对多态性引物都具有较高的杂种鉴定率,并验证了1对引物鉴定真伪杂种的可靠性,后续可作为橡胶树杂交子代真实性鉴定的理想SSR分子标记。
关键词:橡胶树;SSR分子标记;杂种鉴定;杂交育种
中图分类号:S794.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Early and rapid identification of F1 hybrid progeny of Hevea brasiliensis and acquisition of true hybrid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reation and genetic research of H. brasiliensis. In this paper, ‘PR107 and ‘93-114 were used to hybridize, and three pairs of polymorphic complementary primers were selected from 104 pairs of SSR prime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ll 35 hybrid progenies were identified as true hybrid seedlings. All the three pairs of polymor-phic primers screened had high heterosis identification rate,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genuine and false hybrids was verified by one pair of primers, which could be used as ideal SSR molecular markers for the authenticity identification of rubber tree hybrids later.
Keywords: Hevea brasiliensis; SSR molecular marker; hybrid identification; hybrid breeding
DOI: 10.3969/j.issn.1000-2561.2021.05.015
巴西橡胶树(Hevea brasiliensis)原产于巴西亚马逊流域,为多年生大戟科(Euphobiaceae)落叶乔木。橡胶树产生的乳状汁液是可再生的天然橡胶,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耐磨性和可塑性,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在军工、化工、医疗等行业用途十分广泛,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橡胶树育种实践中,一个优良品种的选出一般须经过有性杂交,有性杂交是通过雌雄授粉相交而结成种子来繁殖后代的方法,橡胶树有性繁殖一般有两种方法:人工授粉和自然杂交[1]。橡胶树为常异花授粉作物[2],天然杂交率在4%~50%之间,自交不衰退且其有性生殖的后代会发生遗传变异,性状会发生分离,在杂交F1代即可进行筛选重组优良个体。同时,由于橡胶树基因型高度杂合,杂交育种实践中,选择实生后代的工作量大,非生产期和育种周期长,加上橡胶树有性繁殖过程中容易因自交、串粉、机械混杂等因素造成真假杂种混杂,使橡胶树育种工作效益降低。所以,对橡胶树杂交F1子代进行早期快速鉴定,对橡胶树杂交育种工作的开展和优良品系的创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F1杂种真假鉴定的方法有形态标记鉴定、生化标记鉴定、细胞标记鉴定和分子标记鉴定等[3],其中,分子标记鉴定不受时空影响,具有快速、准确和方便等优点[4]。随着分子技术的发展,分子标记已广泛应用于植物育种的各个方面,特别是SSR标记(simple sequence repeats,简单重复序列),相比于AFLP、RAPD和RFLP等标记,其在单个微卫星位点上就可做共显性的等位基因分析[5],重复性高、可靠性强、多样性丰富,被广泛应用于植物杂种后代的鉴定,如在水稻[6]、大豆[7]、沙田柚[8]、苹果[5]等多种作物品种纯度鉴定中得到应用。在橡胶树上,早期品种鉴定的方法是选择正常生长的营养器官及花、果、种子等外部形态特征进行甄别[1],但由于橡胶树遗传基础狭窄,形态学鉴定方法易受主观因素影响,存在天然的弊端;如今随着分子技术快速发展,分子标记也开始应用于橡胶树无性系的鉴定,如Low等[9]和Besse等[10]利用RFLP标记指纹图谱对橡胶树品种进行鉴定,Saha等[11]利用4个微卫星标记逐一区分了27个无性系品种,谢黎黎等[12]利用SSR标记构建了中国87个橡胶树无性系的DNA指纹图谱,但利用SSR分子标记鉴定橡胶树杂种F1子代的真伪性并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以橡胶树品种‘93-114为母本,品种‘PR107为父本,授粉杂交获得的F1杂交子代为材料,通过筛选获得特异SSR标记,并鉴定杂交子代的真伪,为橡胶树杂交育种的早期鉴定提供简单、快捷的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材料来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湛江实验站收集保存的‘PR107(父本)和‘93-114(母本)的后代群体资源,共35份材料,于2016年建立亲本和后代群体的初级系比试验区,试验区分为3个小区,每小区按照株行距为3 m×3 m随机种植亲本和子代群体,每份资源相邻种植3株,共3次重复,从每份材料中隨机挑选1株,共35株单株作为试验材料。
1.2 方法
1.2.1 DNA提取 参考安泽伟等[13]的方法对橡胶树基因组叶片DNA进行提取。用1%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纯度与浓度,原液于?20 ℃保存备用。
1.2.2 引物筛选 SSR引物:104对SSR引物中,24对来自Souza等[14],4对来自Saha等[11],5对来自谢黎黎等[12],71对来自Gouvêa等[15],由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每对引物都进行重复扩增。利用母本‘93-114和父本‘PR107作为DNA模板对合成的104对引物进行筛选。
1.2.3 引物鉴定真伪杂种可靠性验证 挑选3个非‘PR107(父本)和‘93-114(母本)来源的橡胶树品种作为对照,验证引物鉴定真伪的可靠性。
1.2.4 SSR-PCR体系 PCR扩增反应在TaKaRa TP-600 PCR仪上进行。采用10 ?L反应体系:DNA模板1 ?L,ddH2O 4 ?L,4 ?L mix(2×Taq DNA Polymerase,2×PCR Buffer,2×dNTP),上游引物和下游引物各0.5 ?L。反應条件为:94 ℃预变性5 min;94 ℃变性30 s,复性30 s(温度以引物最适退火温度而定),72 ℃延伸30 s,35个循环;72 ℃延伸7 min。
1.2.5 PAGE凝胶电泳及检测 采用6%聚丙烯酰胺凝胶对PCR产物进行电泳,电压180 V,电流80 A,时间为60~90 min。
2 结果与分析
2.1 橡胶树杂交子代的获得
以橡胶树品种‘93-114为母本,品种‘PR107为父本,授粉杂交获得F1杂交子代。通过形态观察发现,F1杂交子代叶片表型差异较大,如叶色、叶缘波浪、叶柄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异(图1)。本研究所用的亲本‘93-114和‘PR107表型性状大部分类似,同时,这些杂交子代在表型上与亲本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无法用形态学鉴定的方法进行鉴定,需开展更深入的分子方面的鉴定。
2.2 橡胶树真假杂种子代鉴定引物的筛选
以橡胶树品种母本‘93-114和父本‘PR107作为DNA模板对合成的104对引物进行筛选,引物多态性频率为31.73%,合适的条带多态性引物仅有3对。根据电泳条带呈现的结果,104对引物中没有扩增明显条带的有9对;61对引物在父母本能扩增出相同大小的条带,没有多态性;有多态性引物对数为33对,多态性频率为31.73%,经过多次重复,最终确定了在双亲中均有多态性的引物IAC-HV06、IAC-HV10和IAC-HV33用于杂交子代的鉴定,引物序列见表1,结果见图2。从图2可见,3对引物都为共显性标记,在亲本间的条带差异较大,是比较理想的真伪杂种鉴定引物。
2.3 橡胶树杂交子代的分子鉴定
引物IAC-HV06对35个杂交子代单株的鉴定结果显示(图3A),所有单株材料都具有双亲带型。从引物IAC-HV10的鉴定结果可以看出(图3B),25号没有扩增结果,其他检测材料都带有父本特征带型。引物IAC-HV33检测结果显示(图3C),材料2、3、9、10、25、32、33、34号被鉴定为母本带型,其余27个材料单株都具有双亲带型。
比较3对引物鉴定结果发现,35株单株被鉴定为真杂种苗,真杂种率为100%。一般认为,同时具有母本和父本特异性条带的杂合型个体才为真杂种。但种子收获自母本时,只要具有父本的特征带即可认定为真杂种[16]。另外,橡胶树是基因型高度杂合的植物,亲本为杂合体;在减数分裂形成配子的过程中,标记位点的DNA区域可能会由于同源染色体间的交换而导致扩增位点改变,从而使得母本或父本的标记条带在子代中消失。所以不能指望仅用1对引物来单独鉴定后代真伪,应是同时用多对引物进行检测,只有多对引物检测不出父本带型的才可能是伪杂种。从本研究中可以发现引物IAC-HV06可以一次性将所有杂交子代鉴定出来,都为真杂种,鉴定效率达到100%;引物IAC-HV10可将34株材料鉴定为真杂种,鉴定率为97.14%;在引物IAC-HV33扩增结果中看出,8份材料为母本带型,其余27株材料都具有双亲杂合带型,可确认为真杂种,鉴定率为77.14%。3对引物都具有较高的真杂种鉴定率,后续可作为橡胶树杂交子代真实性鉴定的理想SSR标记。
2.4 引物鉴定真伪杂种可靠性验证
为了验证引物鉴定真伪杂交子代的可靠性,挑选鉴定率最低的引物IAC-HV33,以非‘PR107(父本)和‘93-114(母本)来源的橡胶树品种作为对照,进行引物可靠性验证。从图4可见,‘PR107(父本)和‘93-114(母本)来源的杂交子代能扩增出父本的条带,为真杂种;而非‘PR107(父本)和‘93-114(母本)来源的材料1~3号没有扩增出父本带型,可能为伪杂种,说明引物IAC-HV33鉴定真假杂种较为可靠。
3 讨论
开展橡胶树杂交子代早期鉴定,获得真实的杂种是开展杂交育种及其他遗传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杂交育种是创育橡胶树优良品系的一个常规方法,是培育橡胶树新品种的重要途径[1],由于橡胶树为多年生木本植物,非生产期长,有必要开展橡胶树杂交子代早期的鉴定工作,剔除假杂种,提高育种效率。同时,加上橡胶树本身杂合性高,生产杂交子代中容易受机械混杂或自花授粉的影响,从种质资源的角度看,应用分子标记对杂交种进行早期的鉴定,有利于材料质量的保证和种质资源的充分利用。另外,早期快速鉴定出橡胶树杂交真杂种,也能为指纹图谱和遗传图谱的构建等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鉴别橡胶树F1杂种真假,传统的方法是根据形态的差异进行识别,由于橡胶树遗传基础狭窄,表型差异不大且不好分辨,传统辨识方法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随着技术的发展,鉴别F1杂种真伪将会有更多便捷、可靠的方法。目前大多数真假杂种鉴定方法是利用SSR分子标记进行鉴定,SSR分子标记具有快速准确的优点,被广泛应用于不同作物[17-19]的杂种鉴定。鉴定的过程首先是筛选亲本多态性SSR引物,同时该引物在杂种后代中表现为多态互补性引物时,可进行杂种后代的鉴定。由于SSR标记为共显性标记,相比于AFLP和RAPD分子标记,具有简单、效率高等优势,且在理论上1对引物即可完成鉴定。但SSR分子标记在实际操作中利用1对引物鉴定杂种真假有可能存在误差,如本文利用SSR引物对F1杂种进行鉴定,出现不同引物鉴定同一样品出现不同鉴定结果[20],其原因Powell等[21]和Gianfranceschi等[22]指出是利用SSR标记检测基因高度杂合的个体时,可能会出现哑等位基因,导致无法表现共显性;或者是双亲特异性条带消失,出现特异性条带等现象,其原因可能是橡胶树亲本为杂合体,在减数分裂过程中,标记位点的DNA区域可能会由于同源染色体间的交换而导致扩增位点改变,从而使得母本或父本的標记条带在子代中消失。所以在应用SSR标记进行鉴定真伪的过程中,不能仅用1对引物单独鉴定后代真伪,应是同时用多对引物进行检测,如本研究利用3对多态且互补的引物同时对35株杂交后代进行鉴定,其结果才更加真实可靠。
本研究中,橡胶树品种‘PR107是初生代无性系,具有优良的抗性耐性特征描述,以‘PR107为亲本,先后选育出的品种有‘热研7-33-97‘云研77‘大丰95等;品种‘93-114是原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粤西试验站于1967年从无性系‘天任31-45和‘合口3-11杂交子代中选育的次生代无性系,抗寒力强,抗风能力好,通过有性杂交期望筛选具备双亲优良性状的品种资源。抗寒和高产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橡胶树选育种的重要方向,选择抗寒的亲本和高产的亲本进行有性杂交过程中工作量大,且容易出现杂株,利用SSR分子标记技术在苗期进行早期快速鉴定,有利于提高育种效率,同时通过鉴定得到的真实杂种为后期开展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和遗传图谱的构建提供材料支持。因此,本研究通过筛选多态性引物,鉴定橡胶树品种‘PR107和‘93-114的杂种子代真实性,可为今后开展重要性状的QTL定位以及橡胶树真假杂种鉴定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黄宗道, 何 康. 热带北缘橡胶树栽培[M].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1987: 341-345.
[2] 唐冰霞, 王 英, 高和琼, 等. 巴西橡胶树热研7-33-97品种45S rDNA的FISH分析及定位[J]. 热带生物学报, 2015, 6(3): 246-249, 268.
[3] 李德军, 邓 治. 分子标记在橡胶树研究中的进展[J]. 热带农业科学, 2013, 33(11): 46-50.
[4] Hopkins M S, Casa A M, Wang T, et al. Discovery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olymorphic simple sequence repeats (SSRs) in peanut[J]. Crop Science, 1999, 39(4): 1243-1247.
[5] 蔡 青, 姜立杰, 张晓明, 等. 苹果主栽品种的SSR分子标记鉴别[J]. 中国农学通报, 2007(7): 129-134.
[6] 苏顺宗, 黄玉碧, 杨俊品, 等. 利用SSR鉴定水稻杂交种子纯度的研究[J]. 种子, 2003(1): 23-25.
[7] 田 蕾, 关荣霞, 刘章雄, 等. 用SSR标记鉴定大豆杂交组合F1的方法研究[J].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2008, 9(4): 443-447.
[8] 韩国辉, 向素琼, 汪卫星, 等. 沙田柚杂交后代群体的SSR鉴定与遗传多样性分析[J]. 中国农业科学, 2010, 43(22): 4678-4686.
[9] Low F C, Jaafar H, Tan H, et al. Recent adva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lecular markers for Hevea studies[J]. Journal of Natural Rubber Research, 1996, 11(1): 32-44.
[10] Besse P, Lebrun P, Seguin M, et al. DNA fingerprints in Hevea brasiliensis (rubber tree) using human minisatellite probes[J]. Heredity, 1993, 70(3): 237-244.
[11] Saha T, Roy B C, Nazeer M A. Microsatellite variability and its use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cultivated clones of Hevea brasiliensis[J]. Plant Breeding, 2005, 124(1): 86-92.
[12] 谢黎黎, 黄华孙, 安泽伟, 等. 基于SSR标记的橡胶树无性系鉴定方法的建立[J]. 热带作物学报, 2009, 30(9): 1314-1319.
[13] 安泽伟, 黄华孙. 一种提取橡胶树叶中总DNA的方法[J]. 植物生理学通讯, 2005(4): 513-515.
[14] Souza L M, Mantello C C, Santos M O, et al. Microsatellites from rubber tree (Hevea brasiliensis) for genetic diversity analysis and cross-amplification in six Hevea wild species[J]. Conservation Genetics Resources, 2009(1): 75-79.
[15] Gouvêa L R L, Rubiano L B, Chioratto A F, et al. Genetic divergence of rubber tree estimated by multivariate tech-niques and microsatellite markers[J]. Genetics and Molecular Biology, 2010, 33(2): 308-318.
[16] 谭美莲, 严明芳, 汪 磊, 等. 蓖麻杂交种的SSR鉴定及遗传变异分析[J]. 西北植物学报, 2012, 32(8): 1539-1546.
[17] 唐建民, 周世良, 成明昊, 等. 用RAPD和SSR分子标记鉴定小金海棠F1代杂种实生苗的研究[J]. 中国农学通报, 2006(2): 36-40.
[18] 董 静, 张运涛, 王桂霞, 等. 五叶草莓与凤梨草莓种间杂交F1代的形态学及SSR标记鉴定[J]. 西北農业学报, 2010, 19(11): 145-148.
[19] 程保山, 杨加银, 洪德林. 5个粳稻杂交组合及亲本的SSR多态性分析[J]. 西南农业学报, 2010, 23(6): 1790-1793.
[20] 吴学尉, 崔光芬, 吴丽芳, 等. 百合杂交后代ISSR鉴定[J]. 园艺学报, 2009, 36(5): 749-754.
[21] Powell W, Machray G C, Provan J. Polymorphism revealed by simple sequence repeats[J]. Trends in Plant Science, 1996(7): 215-222.
[22] Gianfranceschi L, Seglias N, Tarchini R, et al. Simple se-quence repeats for the genetic analysis of apple[J].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 1998, 96(8): 1069-1076.
责任编辑:沈德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