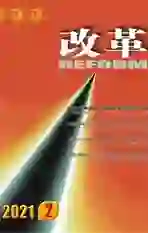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实践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2021-07-19李珒包晓斌
李珒 包晓斌

摘 要:协同治理是跨越单一主体边界的治理活动。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有效利用了先决条件,确立了协同驱动因素与主体衔接机制,构建了职责明晰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了中央政府主导的横向合作的协作过程。同时,也存在着如下问题:协同组织的结构性效能发挥有限;协同主体的多元参与和协同形式的多样性不够;协同主体致力于协同的主动性不足;协同治理效果的可持续性有所欠缺。为推动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应推进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优化协同环境;充分利用京津冀地区的区位优势,突出协同治理特色;优化协同结构,强化整体功能;创新协同形式,提高协同效率。
关键词:协同治理;大气污染治理;京津冀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02-0146-10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环境领域突出表现为人民对优质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增加与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早在201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组完成的《中国民生指数环境保护主客观指标对比分析》报告就指出:环境治理绩效存在两个反差:一是“污染物减排数据与环境质量的反差”;二是“环保工作绩效与公众感觉的反差”。出现反差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质量变化趋势稳中有好但改善缓慢,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速度在快速上升”[1]。
近十年来,我国区域(尤其是联防联控重点区域)的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绩效在稳步提升,但其提升幅度在缩小[2],且多呈现以重大事件应对为导向的运动式治理特征。在某些特定时间段,大气污染物浓度的大幅下降让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有效性备受称赞[3]。但这些重要时间节点之后,大气污染物浓度和污染预警的再返场及其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和常态化又使得区域协同治理绩效的可持续性受到一定质疑[4]。
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为重点区域环境问题的解决和改善做了大量工作,出台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我国环境问题的解决应立足环境治理实际和治理实践,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环境治理路径。协同治理强化了政府部门之间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行动,最容易体现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有效路径。本文立足于协同治理的基本框架,对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实践进行系统反思,以期寻求区域环境治理的解决之道。
一、协同治理的理论演进
“协同治理”是跨越单一主体边界的治理活动,已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研究和实践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80年代初现于物理学家笔下[5]、经由治理者们在实践中的运用和推广,公共管理中的协同治理理论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对协同治理的概念界定和框架内容的构建。学者们对协同治理的概念尚未有定论,但均试图从协同治理的主体、途径(过程)、结果等环节进行剖析。一般而言,依据参与主体的不同,协同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聚焦于政府内部部门,宏观层面则将政府视为一个整体,关注其与企业和社会主体之间的协同行为和关系[6-7]。就协同途径而言,Thomson认为,协同的途径是通过“正式或非正式谈判”[8];Bryson等认为,协同的途径是“两个或以上政府部门通过信息资源共享、实力互补和共同行动”来实现协同目标[6];Ansell & Gash则认为协同的途径是“吸纳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并同意集体决策”的过程[9]。虽然不同学者对协同实现手段的界定不一,但其共性在于均强调了该途径的非强制性参与和共识目标的达成。这一阶段,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协同治理的条件问题。协同治理条件包括一般性外部先决条件和初始条件。前者包括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客观资源条件等外部环境因素,后者则更加聚焦于协同的内部条件,包括制度环境影响下协同主体间关系(依存度)、主体对于协同目标的共识和认可、主体过去参与协同的实践经历、在此之上的领导关系(可被理解为处于领导地位的主体的领导力)等。对于初始条件所着重关注的主体间关系,部分文献也专门予以关注,探讨了通过权力的部分出让而组成协同组织的“分权式”与“集权式”协同结构的区别及其有效性。协同治理理论早期的分析框架更加关注协同的内外部条件,但相对弱化了这些条件与最终的协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第二个阶段,协同治理的内部条件和协同结果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Emerson等提出的协同治理框架将协同系统扩展至更加宏观的环境中,将资源条件、政策与法律框架、政治与权力条件等因素纳入协同的决定因素,并将领导力、主体间的依存度等因素从协同系统环境中剥离,整合成为影响协同的内部动力源——有原则的参与、共同动机的引导、共同行动的能力,并将其与外部环境构建起了有机链接,进一步明确了内部动力因素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最终协同结果的影响机制,阐明了此前所弱化的因果关系[7,9]。
多年来,学者们基于协同治理视角探索新时期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新方法,在各国的实践中丰富着协同治理理念的应用情境和领域。其中,区域合作尤其是区域环境治理获得了较多关注。区域内各协同治理主体的行为逻辑是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协同是各主体通过协商后产生的行为,协商的过程便是各主体的博弈过程[10],反之则是仍维持各辖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各主体的行为逻辑及其产生原因便成为影响博弈结果、左右协同成功与否的关键。例如,分权式的协同结构也带来了政府间的竞争,使得政府有时会忽视短期内有碍于经济发展的环境整治。Maler发现,政府间合作的受益方是整个区域[11]。区域内各不同主体之间的经济发展、治理能力、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并非区域内的全部行政区均能在协同之后获取比不协同时更多的收益。这是在某些时候部分地区政府不選择协同行为,或者区域协同治理失效的原因。
对现有理论框架所共同关注的内容进行整合,可得到本文的基本分析框架(见图1,下页),主要包括先决条件、初始条件、协同结构、协同过程和协同结果。协同条件一般指外部环境,如问题的复杂性与协同行为的适用性、客观资源条件等;初始条件指内部的协同驱动因素与主体链接机制,如对于协同主体的明确、协同目标的共识、权威文本的宏观架构、主体间的依存度、领导力等,多通过制度环境所塑造;协同结构指协同的组织载体;协同过程主要包括交流机制、参与方式等;协同结果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失败[12]。这些要素自成体系却又相互关联,共同决定了协同结果。
针对我国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学者们进行了诸多探索和分析,内容包括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11]、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有效性[3]、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的优化途径[13],等等。这些分析对于我国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具体问题的解决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它们忽略了对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全面系统分析。
二、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实践探索与成效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实践开展了十余年。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环境保护部等《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强调京津冀是开展联防联控工作的重点区域,要“建立统一规划、统一监测、统一监管、统一评估、统一协调的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近十年来,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理念和要求不断出现于中央文件之中。中央发布的专门针对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问题的文件就有十余个①。这些文件对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进行了规范。在中央政府和区域内各省份共同努力下,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有效利用了先决条件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先决条件是由该区域大气污染问题的复杂性、协同行为的适用性、客观资源条件所决定的。第一,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问题较为严重,且污染扩散具有无序性。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城市群得以形成,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区域污染问题。其中,重工业产业较为集中的京津冀地区成为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污染扩散的无序性及其与传统行政区划的不匹配使得传统环境属地治理的弊端凸显。第二,主体协同应对大气污染成为区域污染治理的必要措施。大气污染有着跨域传输的特点。京津冀三省市地理位置交织,且京津冀地区北部海拔较高,东部和南部地势平坦,西北部山区不利于大气污染的扩散,因而污染物较易在京津冀地区集聚。第三,京津冀地区的区位优势使其获得了较多的中央关注。这一关注亦可被视为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重要资源,有助于更加高效地调动区域内主体参与协同的积极性,迅速推进协同进程。大气污染成为京津冀地区共同关注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协同共治成为必然选择。同时,京津冀地区之间的府际关系以及我国特有的中央统一领导优势等条件,为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先决条件。在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实践中,中央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得到了京津冀地区内各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
(二)确立了协同驱动因素与主体衔接机制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实践具有明确的主体、明确的共识性目标、明晰的主体间关系和确定的领导力,确立了协同治理的驱动因素和主体衔接机制。
明确的主体要素是协同治理实践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概念。2013年国务院印发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建立“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界定了“协作机制”的基本框架,明确了参与者——由区域内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参加。在中央后续下发的多数文件中,京津冀地区的主体要素均沿用了这一表述。
共识性目标是协同治理主体的内在需求。区域内各省市面对着共同的环境问题,需要改变传统的属地治理方式,实现统一协调行动。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实施前,各省市的治理方式是属地治理,缺少统一的行动和协调措施。尽管多年来三省市做了大量工作(三省市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通过车辆限行、煤改气等措施进行大气污染物排放整治),但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对大气污染问题的解决自然成为其共识性目标和要求。2011年印发的《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明确了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的目标和措施。在2010—2020年下发的多数文件中,均有对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具体目标的明确,这些目标成为京津冀地区协同治理主体共同行动的驱动因素。
在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实践中,协同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这是因为,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组织是由中央政府发起的。例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明确“以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省(市)人民政府为主体责任,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协调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2018年调整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由于其在更长时间内被稱为前者,因而本文沿用这一名称,后文简称为“协作小组”)有多个中央部门参与,一定意义上代表着中央政府并行使协调职能。中央政府是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动力源,通过机制的成立、政策的实施,推动京津冀地区内各省份形成协同治理的合力,为这一协同实践创造初始条件。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初始条件特点鲜明,协同主体在中央领导下结成了伙伴关系,促成了协同组织目标的明确、主体间统一行动和政策执行的高效率。
(三)构建了职责明晰的内部治理结构
在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中,协同的结构性表现在权力和职责分配的结构性之中。参与协同组织的主体要素包括了区域内的七省(区、市),同时包括了环境、能源、财政、发展改革委等中央部门。协同的组织机构是“协作小组”,此外还设置了专家委员会。为了便于对“协作小组”成员结构进行理解,根据职能定位,我们可以将“协作小组”成员进行分类:将区域内七省(区、市)称为责任主体,中央部门称为职能主体,“协作小组”称为领导主体,专家委员会称为参谋主体。
协同组织的不同成员有不同的分工,从而形成了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的内部协同机构。“协作小组”受中央政府委托负责“协调推进,分解任务,落实责任”;“环保部负责统筹协调,会同有关部门对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和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指导督促各地大气污染治理和重污染天气应对落实”;“省(市)人民政府为责任主体”。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辖区治理行为分权结构体现了权力分工与集中相统一、空间分权与职能分权相统一的特点。
(四)实现了中央政府主导的横向合作的协作过程
协同结构决定了协同过程。协同过程是协同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是协同结构的动态表现。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协同过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协同过程中的主体互动关系;二是协同的内涵,因为协同本质上是协同主体间的互动[10]。
从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主体间互动关系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一是协同治理的责任主体、领导主体、职能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中的主体互动是以中央政府及其委托的“协作小组”为核心的。“协作小组”负责“协调推进,分解任务,落实责任”。同时,通过会议形式和其他方式了解、收集责任主体的信息建议,形成决策部署。这一层面上的互动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二是责任主体之间的互动。从理论上讲,责任主体之间的互动是协同治理的主要关系[10]。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是在“协作小组”的主导下实现的,体现了协同治理统一行动的严格性特点。例如,2015年5月,“协作小组”在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2015年重点工作》,划定了包括北京、天津、廊坊、保定、唐山、沧州六个城市在内的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核心区域,并开展结对合作(北京结对廊坊、保定,天津结对沧州、唐山)。北京市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别支持河北4.6亿元、5.02亿元。2017年4月,京津冀三地联合发布了环保统一标准——《建筑类涂料与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标准》。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主体之间协同内涵较为丰富。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提出了这一内涵,包括“统一规划、统一监测、统一监管、统一评估、统一协调”。2011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充分发挥环境保护部际联席会议的作用,促进部门之间协同联动与信息共享”。2013年发布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指出,要“研究协调解决区域内突出环境问题,并组织实施环评会商、联合执法、信息共享、预警应急等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这一点在2015年、2017年的文件中予以了重申)。在具体协同治理实践中,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内涵更为广泛,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统一目标、规划和标准的制定;统一监测的实施和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和共同预警应对突发事件;财政政策的实施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等等。当然,这些协同内涵的实施一般要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和认可。
总体上看,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实践体现出如下特征:一是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和“协作小组”的权威;二是严格的政策落实和统一行动。从效果上看,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成效较为明显。
三、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实践困境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具备了较为完整的条件,内部协作结构和主体关系结构亦较为清晰,其协同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从协同治理的基本理论出发考量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实践,可以发现仍然存在一定问题和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我们认为,问题主要包括协同治理主体自身的主动性、互动关系的秩序性及其结构性效能的发挥等方面。
(一)协同组织的结构性效能发挥有限
协同组织的依据在于其内部组织结构产生的整体性功能。协同组织的整体性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京津冀协同治理组织在其效果上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应看到这些成效更多是中央政府组织的结果,而不是协同组织自身功能发挥的结果。
2010年以来,国务院下发的涉及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文件有数十个,其中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占据较大篇幅的文件有13个,针对京津冀地区协同治理的专门性文件有7个。2013—2015年召开的6次专门会议均有多个中央部门的代表参加,其中3次有负责相关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参加。《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中明确由环保部、发展改革委、工信部等十部门参与组织协调工作。国家相关部门的参与体现了中央政府对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重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京津冀地区协同治理组织自身效能发挥的不足。
协同组织的结构性和效能取决于组织自身的制度安排、权力分配,主要是组织成员自身的主动性及其行动的秩序性与一致性。协同组织的协同功能本质上要求协同组织具有众多单一主體更大的功能和作用。在这里,主体的主动性和行动的秩序性至关重要。实际上,在京津冀协同治理实践中,从事件的发起、组织,到推进、评估,均有中央政府的参与。在我国,任何一个协同组织均不可能脱离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而独立开展工作。在现阶段的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实践中,还缺少责任主体之间的谈判、沟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协议、权利义务关系等。协同组织的内部沟通和谈判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制度安排,是这一组织结构型功能发挥的重要表现。
(二)协同主体的多元参与和协同形式的多样性不够
协同组织的治理目标和任务可能是单一的,但协同治理组织的主体角色应该是多元的。尽管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的责任主体是区域内省级人民政府,但在主体参与方面应该具有多元性。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区域内部行业之间应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横向联合;缺少各责任主体所在省市的企业、民间组织等组成的应对大气污染治理的联合组织;地方政府与企业及社会民众之间的沟通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主体的协同形式应该具有多元性。实际上,对于这一问题,中央早已有所设计。例如,《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指出,要“完善政府负责、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环境管理体系”,“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环境保护的指导、协调、监督和综合治理。发展改革、财政等综合部门要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财税、产业、价格和投资政策”。
协同组织在目标设计、发展规划、统一监管、信息共享、财政税收、产业结构调整、价格和投资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果。但严格来讲,这些成果是在领导主体层面上出台的统一性措施,而不是责任主体协商的结果;这些措施具有多样性,但实现手段主要是行政性的。
我们了解到,多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乡村养殖户,对京津冀地区环境保护政策持肯定态度,但在区域政策实施过程中与民众沟通还不够。在采取的措施方面,多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方式相对单一。协同组织多元主体的参与以及多元政策措施的实施是建立信任的重要渠道,在大气污染治理中尤为重要。公共性困境涉及社群內的全部成员,而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于全部成员的共同努力[14],这也是协同主体应该多元化的主要原因。
协同主体的多元参与与协同形式的多样性本质上是一致的。政府依靠民众、团结民众共同行动,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三)主体参与协同的主动性不足
协同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其成员主动共同做事和主动做共同的事,这两个方面均不可或缺。协同组织的行为路线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协同主体之间经过沟通达成共识,进而上升为协同治理组织的共同意志[12]。否则,协同组织将不复存在。
从协同主体对“协作小组”的主动协作来看,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仔细考察便会发现,其成就取得主要来自中央政府的主导和职能部门的部署。各协同主体的主要任务在于落实中央政府(或“协作小组”)的安排。2010—2019年中央发布的有关文件主要是在安排任务和制定计划,“协作小组”部署的任务也主要是中央政府委托或主持的结果。从我们收集的文件来看,中央政府部署的任务明确而具体。例如,2014年发布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限期治理方案》明确了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甚至将492家企业、777条生产线或机组的名单、监管目标等内容都规定得十分详尽。
从协同主体之间的主动性来看,京津冀地区内各协同主体之间存在着沟通、交流、合作、帮扶等行为,但这些行为多由中央政府主导。例如,2015年北京和天津与河北的结对合作便是如此。
协同主体的主动性问题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一是环境治理困境;二是治理激励问题;三是治理能力问题。如果主体协作的主动性不够,协同治理的主要动力源便来自协同组织之外,如中央政府。这样,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效果便会大打折扣,治理效果亦可能面临不可持续问题。
(四)协同治理效果的可持续性有所欠缺
协同治理效果的持续性是评估协同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总体效果体现了我国治理能力和传统制度的优势。但是,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中的问题——主要是协同组织内部活力问题,导致协同治理效果可持续性不够。如何防止运动式治理、保持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效果的持续性,从而降低治理成本,是强化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难题。
四、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是中国特色治理理念下协同治理实践的典型形式。从协同治理理论的基本特征来看,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具有一般协同治理理论要求的基本要素和协同治理的基本特征。但是,京津冀地区协同治理实践也打上了中国治理理念的烙印。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实践突出了中央权威、执行严格和效率较高的鲜明特点。从协同要素、协同结构及其运行来看,中央政府对京津冀地区环境治理的重视和参与,使各行为主体之间的行为统一、相互协作,显示了中国特有的制度优势,开创了协同治理的新视角。从我国协同实践发展的角度来看,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表现出了协同组织结构性功能不足、主体性因素单一、内在驱动力不足、治理效果持续性不足等问题。破解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困境,应重点从四方面着手。
(一)推进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完善协同环境
协同组织的出现往往是为了应对某一种或几种具体的问题,但协同主体解决问题的行为往往超出了这些问题的范围,这是事物关联性和整体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此意义上,整体性、协同性、合作性具有相同的话语背景。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实践与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相关联,因而其必然要以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为基础。大气污染治理的根本性问题总是发生在生产和社会领域,解决问题的出路也必然要在这一领域中寻求。经济社会一体化过程中协同关系和组织系统的建立与完善能够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提供相互沟通、动态发展的桥梁和组织保障。大气污染中的协同治理需要协同主体之间的沟通和动态发展[8],需要协同主体建立在组织基础之上的统一行动[10]。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是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主体沟通路径和组织发生的土壤。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能够提供和扩大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主体共识,强化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目标理念。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中的规划设计、方案制定等工作,要坚持大气污染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一致、和谐发展的理念,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纳入规划之中,在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过程中实现京津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充分利用京津冀地区的区域优势,突出协同治理特色
京津冀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空间位置优势。这一优势能够得到国家政策、生产组织、科学技术、社会力量的关心和支持,便于集中力量、形成共识、先行先试。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要充分依靠中央政府的权威,坚持区域整体性和协同组织一致性的理念。在各协同主体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强化政策和方案的落实;强化主体之间的结对帮扶,促进共同发展。要利用和争取国家政策的扶持,坚持整体发展与区域发展相结合的理念。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涉及首都北京和国家整体污染治理问题,在财政、金融等方面给予支持,率先实现产业转型和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至关重要。京津冀地区集中了国家重要的科技力量,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具有实现科技治理、科学治理的有利条件。协同组织和各协同主体利用好专家委员会的作用,可以实现科学治理、联合治理。我国的制度优势在于强大的动员能力。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容易得到民众的支持,形成治理共识,取得和强化协同合法性。在治理实践中,应注重主体之间的共识建设和信任机制建设。
(三)优化协同结构,强化整体功能
协同关系重视的是协同组织的功能,但问题须从内部结构方面予以解决。京津冀协同治理的整体性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重要原因在于内在结构不合理。
京津冀地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责任主体所在的空间区域、产业布局、科技发展、经济实力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组织行为的角度来看,组织成员的差异性决定了组织内部结构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到组织整体性功能发挥的问题。因为组织成员的发展差异性决定了其需求的差异性,对组织成员需求差异性的满足是成员协同行动和维持组织统一性的基本前提。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的结构性与空间结构是一致的,这是由于这一组织本身具有区域性特点。北京市应该强化其核心地位,对协同的发起、目标政策的制定、统一行动的方案起到发起者和领导者的作用;天津和河北应发挥其次核心地位,积极参与事件的发起和政策的制定;其他各省份要积极行动,维护组织的统一性行动。当然,作为核心的北京要利用其经济、科技优势积极帮扶其他省份,在协同行为中实现不同成员的权利义务关系,彰显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整体优势。
(四)创新协同形式,提高协同效率
协同组织绩效的提高是与其协同形式密切相关的。过于单一的协同形式往往不能满足协同成员的要求,会影响协同效果的实现。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应该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扩展协同思路,不断创新协同形式。在经济协同方面,应配合国家和“协作小组”出台的财政、税收、金融政策,搞好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规划,重视大气污染治理中经济互补性发展,开展多层面的经济合作[15]。对于区域内围绕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经济发展合作项目,要给予财政补贴、金融优惠、政策奖励等。
在政治协同方面,要落实中央政策,强化协同组织的统一行动。同时,充分利用我国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广泛集中民众的智慧和建议,并在协同组织内部进行交流协商,取得共识,增强协同意识。
要坚持统一执法、信息共享等行之有效的做法,结合地方实际创造灵活多样的协同形式。激发并吸纳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协同治理,实现以政府为中心的多主体参与式协同。进一步整合、优化市场和社会资源,调动社会各界的参与积极性,吸纳社会元素进入协同治理的实践中。例如,在某些领域,应积极发挥市场的作用,激励企业参与环境治理[16]。社会组织等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作用已得以彰显,应通过制度设计、激励社会元素在环境保护和治理中发挥相应作用。调动社会各方的力量,形成以政府为中心的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模式,这有利于区域协同治理绩效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组.中国民生指数环境保护主客观指标对比分析[J].发展研究,2014(10):39-42.
[2]刘华军,雷名雨.中国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困境及其破题思路[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10):88-95.
[3]马万里,杨濮萌.从“马拉松霾”到“APEC蓝”:中国环境治理的政治经济学[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10):16-22.
[4]孟庆国,魏娜,田红红.制度环境、资源禀赋与区域政府间协同——京津冀跨界大气污染区域协同的再审视[J].中国行政管理,2019(5):109-115.
[5]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M].凌复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8-9.
[6]BRYSON J M, CROSBY B C, STONE M M.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s: propositions from the literature[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6, 66(1): 44-55.
[7]EMERSON K, NABATCHI T, BALOGY S.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11, 22(1): 1-30.
[8]THOMSON A M. Collaboration: meaning and measurement[D]. 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 2011.
[9]KOSCHMANN M A, KUHN T R, PFARRER M D. A communicative framework of value in cross-sector partnership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2, 37(3): 332-354.
[10]FINUS M. Stability and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the case of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In FOLMER H, & TIETENBERG T(Eds.), The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3/2004: a survey of current issues[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2005.
[11]MALER K G. The acid rain game. In FLMER H, VAN IERLAND E(eds.) valuation methods and policy making in environmental economics[M]. Amsterdam: Elsevier, 1989.
[12]BRYSON J M, CROSBY B C, STONE M M.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s: needed and challenging[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5, 75(5): 647-663.
[13]蔡嵐.粤港澳大湾区大气污染联动治理机制研究——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的视域[J].学术研究,2019(1):56-63.
[14]PRAJIT K, DUTTA R, et al.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 Economic Theory, 1993, 3(3): 413-426.
[15]郭施宏,齐晔.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模式构建——基于府际关系理论视角[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3):81-85.
[16]李珒.协同治理中的“合力困境”及其破解——以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实践为例[J].行政论坛,2020(5):146-152.
Abstrac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s an activity across the boundary of a single sector.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air pollu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has made effective use of the preconditions, established the linkage mechanism between the collaborative driving factors and the main sectors, constructed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with clear responsibilities, and realized the collaborative process of horizontal collaboration led by the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limited structural effectiveness of collaborative organizations, insufficient diversity of sectors and collaboration forms, the lack of the initiative of collaborative sectors in collaborative efforts, and the lack of sustainability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ffects. The policy suggestions on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air pollu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are as follows: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improve the collaboration context; make full use of the regional advantage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to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ptimize the collaborative structure and strengthen the function; innovate collaborative forms to improve the collaborative efficiency.
Key word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governance of air pollu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