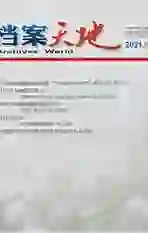静默与崇高
2021-07-19王东梅
王东梅
冯至,原名冯承植,字君培,河北省涿州市人。
他是“五四”时期著名的“浅草”社和“沉钟”社成员,在30年代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散文和小说也有独特的成就。
他是我国久负盛名的德语文学专家,对中国古典文学也有专攻,是资深的杜甫专家。他对新中国的外语教学,外国文学的研究和文艺创作,都作出了贡献,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但是,“一切的形容,一切喧嚣”,到他身边,有的就化成了他的“静默”。
“何曾一语创新声”
冯至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破土萌生的诗人。1920年, 15岁的冯至就与同学办起了《青年》杂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边缘摇旗呐喊,开始了70年的文学生涯。翌年,创作了《绿衣人》,反映了他16岁少年过早的成熟和对社会人生的忧虑。不久,他进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学习,同时以极大的兴趣写诗(还写散文、小说、翻译和评论),反映内心的苦闷和彷徨,抒写对爱情的憧憬与渴望,富有情韵,自领风骚,受到了文学史家王瑶等的好评。鲁迅更是独具慧眼,称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40年代初,冯至创作了别具一格的《十四行集》,被朱自清称为“新诗的中年”(《新诗杂话》)。如今,它已被譯成英、德、意、日、荷兰、瑞典等多种文字。
50年代开始,冯至以满腔的热情赞美建国后的新气象和忘我劳动的人民。从1985年起,他继续进行那一贯的对人生和宇宙的探索,而且毫不留情地抨击了腐败和封建,内容题材更有开拓和创新。
冯至还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散文家。比起他的诗,冯至的散文更能反映他的心灵和风格。真诚、纯洁、有情韵、有意境,是诗化的散文,代表作是早期的书信和40年代的《山水》。《乌鸦——给M弟》情真意浓,催人泪下;《山水》是另一种形式的《十四行集》,是诗人当时人生境界和文艺思想的反映,在文化史的意义上极有价值。
作为一个小说家,冯至的作品太少,但手法和技巧却领一代之先——以情绪的流动为中心,注意情境的渲染。从《仲尼之将丧》《伯牛之有疾》到40年代的《伍子胥》等,你会感到80年代的现代派热,其实在他的小说、诗歌里早已“热”过。
但是,他自己却说:“工力此生多浪费,何曾一语创新声”。
“我不是学者”
经过“五四”洗礼的作家们,大都“学者化”,冯至亦不例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
青年时期他在北京大学度过6年的美好时光,虽然专业为德文,却选修了国文系的很多课程,认真地听鲁迅、沈尹默、黄节等名师的课。1930年又去德国留学5年,1935年获取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国。
抗战以后,他即开始了对杜甫的研究,80年代初,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杜甫传》——新文学史上较早的文学家传记。60年代初,他以北大西语系主任身份负责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主持的高校文科教材中文组的工作。
与杜甫研究差不多同时,他又攻研歌德,1948年出版了《歌德论述》一书。此后,在此基础上,在恩格斯观点的影响下,经过近40年的努力,又写下了一系列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光辉和学识光芒的论文,后结集为《论歌德》出版。
还在北大学习时,冯至就开始了翻译生涯。曾翻译过歌德、里尔克、海涅、尼采、席勒等著名的德语文学家、思想家的作品近百万字,写下了精深的论文。他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编委会主任。
但他却说:“我不是学者,没有写过一定水平的学术著作”,更否认自己是个翻译家。
“当时只道是寻常”
冯至集诗人、散文家、杜甫专家、德语文学专家和翻译家于一身,在国内国际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但是他却说:“自念生平,没有参与过轰轰烈烈的事业,没有写过传诵一时的文章”。他喜欢用清人纳兰性德词中的一句来概括自己的平凡:“当时只道是寻常”。凡是熟识他的人都会发觉他诚挚宽厚的人品和虚怀若谷、严谨严肃的学风。
《歌德论述》在当时已达到很高的水准,但他在序中却说:“不是研究,没有创见,只求没有曲解和误解”。他对鲁迅无限景仰,但从不提起鲁迅对他的评价,而当别人提起时,他总是诚恳地说:“我不是杰出的抒情诗人,更不是最杰出的。你千万不要这样说。”对研究他的人,他先是劝你“不要花时间,不值得”,而当你继续坚持时,又反复提醒你要客观,不要溢美,不要影响到别人。当你按响门铃后,他总是及时地开门,和善地说:“请进”,把你引到客厅,让座,还亲自为你斟上一杯茶。然后,他平等平静地与你说话,接受你的提问和采访。你始终感觉不到自己是在与一个名人谈话,倒象与自己的父辈、祖父辈,在夕阳西下时,坐在院子里,随便地对话。
《论歌德》是他几十年歌德研究的结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他在书前却用1万多字的篇幅,叙述了自己歌德研究的历史,分析不同时期的局限,对不能进一步深入研究表示遗憾。学者的真知灼见,学者的人格和品格,都可见一斑。
对待文学和人本身,他崇尚的实际也是摆脱世俗浸染、能够反映本来面目的真实。他说,“诗人之可贵,不在于几首好诗,而在于用诗证明了他的真诚的为人的态度。”不难看出,在冯至眼中,立人高于作文,作文反映立人,于是,有了为人所称道的人品和学风。
“等待着新的眺望”
“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对光明的向往,真理的追求,是比较执著的,但大都经过长期的跋涉甚至曲折。在上世纪20年代,冯至不满现实,却又目无光明,不知路在何方。但在鲁迅、杨晦等师友的帮助下,他又无时无刻不与自己的悲观作斗争,不甘被黑暗所吞没。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终于唤醒了冯至。从1942年起,他越来越关注现实和社会,开始用杂文来抨击时弊,后来,更冒着风险,夜间收留一个遭到通缉的学生。1945年,在著名的“一二·一”运动中,他与进步师生一道,同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行为作斗争。惨案发生后,他不顾生命危险,写出了著名的诗《招魂》——
……
正义,快快地到来,
自由,快快地到来,
光明,快快地到来。
当时,这首诗就被镌刻在四烈士的墓碑上。
抗战以后,冯至又积极投入北平人民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和争民主的运动中。1947年,他又写了一首盼望新中国的长诗《那时一个中年人述说“五四”以后的那几年》:
……
如今走了20多年,
却经过无数的歧途与分手;
如今走了20多年,
看见了无数的死亡与杀戮。
那时追求的在什么地方?
如今的平原和天空,
依然映照着5月的阳光;
如今的平原和天空,
依然等待着新的眺望。
他在回忆录中说,那时虽然说不清楚新中国是什么样子,但是总觉得将来比现在好,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正是基于这种心理,第二年他在有名的“四月风暴”中,站到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前列。
为镇压学生运动,1948年4月7日,北平警备司令部下令逮捕学生自治会理事柯在铄等12人,限校方于次日中午12时前交人,否则将派兵包围。这天,学生们齐集北大民主广场,圍成一层层保卫圈,以血肉之躯,以献身中国民主运动的大无畏气概,把12人围护起来,高喊“一人被捕,全体坐牢;一人受审,全体投案!”的口号。在这紧急关头,冯至受全体教授的委托,来到了学生中间,说“我们全体教授誓死支持你们的要求!”这时,冯至已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眼昏昏,心里更光明”
歌德说过,老人永远是个李尔王,意思是说老人思想僵化,头脑糊涂。但冯至却说:
我不愿说老人是个李尔王,
也不愿看痴呆的老寿星,
我欣赏浮士德失明后的一句话:
眼昏昏,心里更光明。
这是他患白内障后所作,虽然有自我解嘲的味道,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年过古稀的冯至在新时期改革大潮中的表现。
粉碎“四人帮”后,冯至壮心不已,又热情地投入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恢复了《世界文学》,主持制订了新时期最早的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修订了《马克思文艺理论丛书》等三套著名丛书的选目和计划,主持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编著工作,还频频出席国内国际有关文学创作、研究、翻译的各种会议。即使在退下来以后,仍一如往日,积极工作,努力著述、翻译和创作,参加和主持有关的文艺活动。
他是一个老诗人,在中国传统的诗歌土壤里长大,受到“五四”新诗的洗礼,曾受到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 ,他以热情又冷静的态度和成熟的眼光对待五光十色的新诗及其评论,不以势压人,不哗众取宠。
冯至是一个外国文学专家,也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起成长的现代作家, 学识深邃,经验丰富,但从不乱发议论,特别是在各种文艺思潮不加选择地纷拥而来之时,他能冷静地对待这些思潮,提出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看法。早在1983年,当各种“新名词”开始狂轰滥炸之时,他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学术讨论会”上提出“要慎重地使用西方的文学术语”,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他又反对极端和偏狭,说“1958年毛主席提出‘两结合,是很有意义的。”他认为现实主义是多种多样的,不能乱贴标签;对于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他不顾各种新理论的冲击,从文学史的角度论证,无论是“反映”“阐释”还是“理想”“都离不开现实”,各种创作方法都是自然产生的,互有联系的,“文学上的任何主义强调到了极端,到了绝对化,就会走向反面”“象征本是文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可是提倡象征主义,把象征绝对化了,尽在联想、比喻上耍把戏,这样喧宾夺主,也就丢掉了现实”。
他是1956年入党的知识分子党员,解放前不仅在德国留过学,还曾到过欧洲亚洲许多国家,解放后又曾十几次到欧洲、亚洲、北美访问,这使他有所比较和鉴别,认定祖国就是母亲,希望在于改革。1984年,他曾参观珠江三角洲,目睹了改革的巨大成就,情不自禁地写了《银湖夜思》一文,不仅歌颂改革,还以一个离国35年回到大陆的朋友的亲身感受,说明改革开放的正确。在文中还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特别强调要防止和反对海外及港澳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
1987年,经历了无数个寒暑和风雨的老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又一次地把自己与祖国联系在一起:
我曾喝过海外的水,
总象是一条鱼陷入泥沙;
我曾踏过异国的土地,
总象是断线的风筝飘浮在空际。
好也罢,不好也罢,
只有一句话——离不开你。
倾诉了对祖国深沉的爱。就在这一年,他把联邦德国国际文化协会奖励的1万马克全部献出,作为德语文学奖基金,以奖掖后进,促进与德国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而对于各种腐败现象,他更是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愤慨,在晚年并不很多的诗中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揭露和抨击,如《神鬼和金钱》《我痛苦》《我不忍》《剪彩》等,都深刻地反映了他对腐败现象的不满,表现了一个作家、学者和教授对民族前进中问题的关心和忧虑;表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对改革事业的负责精神。
1989年8月至10月中旬,冯至因患胸膜炎,住北京协和医院治疗。1993年2月22日,于北京去世。
惟其静默,也才崇高。与那些声名显赫的人相比,冯至的名字并不被一般的中国人所熟知。但是,他的创作,他的学术造诣,他的人品,他的学风,他对祖国的感情,他对人生道路的抉择,却很能代表“五四”以来渴望祖国走向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崇高,在静默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