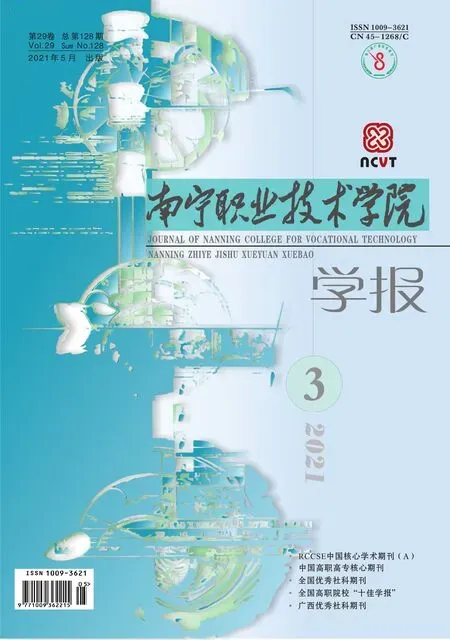广西槟榔习俗研究
2021-07-18崔康辉
崔康辉
(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7)
槟榔因其特有的下气、消食、提神等功效,在岭南部分地区颇受人们倚重和欢迎,并衍生出与槟榔相关的社会习俗。学界有关岭南地区槟榔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槟榔文学和婚嫁习俗两个方面。如罗端繁、范玉春从社会风俗和医用功效两方面,指出槟榔在岭南人民的婚礼、待客、祭祀、消瘴等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1-2];宋德剑认为槟榔作为粤东客家地区婚俗的礼制载体,与客家人重视“象征意境”、槟榔的谐音象征宾临吉祥、生物属性象征忠贞不二也有密切联系[3];温艳指出岭南地区适宜种植槟榔、岭南人民普遍食用和利用槟榔,是形成岭南槟榔文化的基础条件[4]。付广华、黎玉玲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黎族食用槟榔的历史及其槟榔文化的深刻内涵[5-6]。广西地处广义上的岭南地区,但以往关于岭南地区槟榔习俗的相关研究中,经常将广西一带而过,不作详细研究。广西境内的槟榔习俗亦有其自身的特点,本文拟探析广西地区的槟榔习俗,以揭示古代广西槟榔习俗兴起、盛行及衰落历程,并分析其背后的社会原因。
一、广西槟榔习俗的兴起
槟榔属棕榈科植物,在亚热带地区广泛生长,其种子亦多称为槟榔,最早被广泛用于医药。目前有关槟榔的明确记载,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杨孚的《异物志》:“槟榔若笋竹生竿,种之精硬,引茎直上,不生枝叶,其状若桂,其颠近上未五六尺间,洪洪肿起,若瘣木焉。因拆裂出若黍穗,无花而为实,大如桃李,又棘针重累其下,所以卫其实也。剖其上皮,煮其肤,熟而贯之,硬如干枣,以扶留、古贲灰并食,下气及宿食白虫消谷,饮啖设为口实。”[7]此书主要记载了东汉交州一带的物产和民族风俗,地域包含今天的两广及越南北部,较详细地记载了槟榔的性状、功效及食用方法。其中“饮啖设为口实”,说明槟榔因其下气消食的功效,已经开始成为今两广及越南地区的一种日常食物,广西嚼食槟榔的习俗至迟在汉代已经开始兴起。
相比《异物志》,晋人嵇含所撰《南方草木状》,对槟榔树及果实的性状、食用方法和功效等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载:“槟榔树高十余丈,皮似青桐,节如桂竹……叶似甘蕉……叶下系数房,房缀数十实,实大如桃李,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卫其实也。味苦涩。剖其皮,鬻其肤,熟如贯之,坚如干枣。以扶留藤、石贲灰并食,则滑美,下气消谷。出林邑,彼人以为贵,婚族客必先进,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一名宾门药饯。”[8]这一记载详细描绘了槟榔的形状,指出主要出产于林邑,介绍其食用之法以及效用,而且特别记录了槟榔作为一种比较珍贵的婚俗食物,用以招待婚礼上的贵客。至宋代后,有关广西槟榔习俗的记载逐渐增多,内容也更为广泛。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记载,“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还有专用的容器——槟榔盒[9]310。罗大经《鹤林玉露》亦记载,“岭南人以槟榔代茶”[10]。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所称“瘴”“皆由山溪源岭瘴湿毒气故也”[11]。宋人周去非在询问当地人为何嗜食槟榔,他得到的回复是因槟榔能辟瘴、下气、消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罗大经《鹤林玉露》亦称槟榔可以御瘴。从现代医学研究的成果来看,岭南气候湿热,死亡的动植物极易腐烂,病菌繁衍旺盛,且林多树密,空气流通不畅,产生的有害气体不易散发。人体在湿热环境下易出汗体虚,一旦吸入则至患病[12]。槟榔因其特有的除瘴功能为当地人民所青睐。此后的文人笔记、官方记载多将槟榔食用流行的主因归于其能消瘴。至明清时期,时人亦多持此观点,如明人谢肇淛认为“闽、广人食槟榔,取其驱瘴疠之气……槟榔破症消积,殊有神效”[13]。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记载,槟榔“实能辟瘴气,故土人日日早食”[14]。嘉庆《平乐府志》记载:“槟榔能下气、消食、化痰,故岭海之人多食。”[15]民国《邕宁县志》记载,槟榔能“除一切风,下一切气,通关节,利九窍,补五劳七伤,健脾调中,除烦破症,疗诸疟,御瘴疠”[16]。
广西的槟榔习俗起源固然与其消瘴功效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从其他一些史籍记载来看,槟榔习俗的盛行还有其他原因。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槟榔中所含有的槟榔碱和槟榔次碱,可能是导致槟榔嚼食依赖的重要神经活性物质”[17]。嚼食槟榔可成瘾,宋人周去非所记载的“宁不食饭,唯嗜槟榔”“中下细民一日费槟榔钱百余”[9]311现象,应不是夸大。罗大经刚到岭南时,还不能接受槟榔,“居岁余,则不可一日无此君矣”[10],他赞扬槟榔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饥能使饱,饱能使饥,嚼食槟榔可以使人在醉醒饿饱的感受之间相互切换。明人谢肇淛也说“余食后辄饵之,至今不能一日离也”[13]。清朝道光年间编成的《白山司志》记载:“土人晓起,即嚼槟榔。”[18]也从侧面证明此习俗近乎成瘾。因此,槟榔本就有着消瘴的功效,加之独特的嚼食依赖性,使得食槟榔成为更广泛的饮食习俗。
有学者认为长期嚼食槟榔会使牙齿发黑,而部分地区和民族又以“黑齿”为美,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槟榔习俗的传播和流行[19]。大略考察,关于“黑齿”最早记载应为《管子》,书中谈到:“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牂牁、不庾、雕题、黑齿(皆南夷之国号也)。”[20]此后,史书中有关黑齿的记载,大多为古部族或古国名。具体缘何以黑齿命名,似与其齿黑有很大的关系。但究竟是因为崇尚黑色而故意染黑,还是常嚼槟榔变黑,目前没有明确记载和研究。一些记载虽将黑齿与嚼槟榔相联系,但更多是一种猜测。元朝的农书《树艺篇》就记载槟榔“与灰同食,令人齿黑,故有雕题黑齿之俗,实祛辟瘴气”[21]。广西虽为历史上黑齿国或黑齿部族的可能地点之一,但以黑为美或以黑齿为美的习俗并不普遍。有关广西黑齿习俗的明确记载见于《嘉庆一统志》:“在柳城县上油峒,俗似瑶,而语言各异。犽女,马平柳城皆有之,黑齿黥面,绣额为花草蛾蝶之状。”[22]亦无明确提及其黑齿为嚼槟榔所致,不过考虑柳城县为槟榔习俗的分布区之一,不排除这种可能。
二、广西槟榔习俗的盛行
至迟从宋代开始,槟榔习俗在广西已较为盛行。虽然此时食槟榔的习俗在广西较为普遍,但槟榔并非唾手可得。广西并非槟榔的主产区,历史上广西的槟榔产区主要在今天的南宁、梧州、贵港等地,分布范围十分有限。一直到民国,仍是“槟榔价昂,且少出售”[23],可见槟榔属不易获得之物。
珍贵的物品一般在隆重的场合和仪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槟榔在广西的待客习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前述嵇书所载槟榔用于招待婚客;《岭外代答》记录了岭南地区以槟榔代茶待客的习俗;明代谢肇淛《五杂俎》记载:“《本草原始》曰:宾与郎皆贵客之称,交、广人凡宾客胜会必先呈此。”[13]《南中八郡志》记载:“槟榔,土人以为贵,款客必先进。”[14]清人吴震方《岭南杂记》载,岭南“客相见,以此先茶”[24]。道光《白山司志》载,土人“凡请客,以箬叶包槟榔一块,外粘红签,写某人某辞者,将槟榔送回,不用柬贴也”[18]。光绪《郁林州志》记载:“俗重槟榔,宾入门,奉茶后,即献槟,若仓促,可无茶,不可无槟。”[25]民国《陆川县志》载:“客至,普通以茶、烟、槟榔相款,凡往来问好,俱以槟榔为敬。”[26]可以看出,自晋代以来,广西有关槟榔用于待人接物习俗的记载不绝于书,甚至一度取代茶叶,成为待客的首选,更足以证明槟榔习俗在广西的流行程度。
明清以后,广西很多方志和文献都记载有用槟榔作为结婚聘礼的习俗。槟榔婚俗的分布区,与广西比较严重的烟瘴区分布基本是重合的,除西北山区无瘴、少瘴之地鲜有分布,使用地区几乎遍布整个广西(见表1)。婚礼崇尚吉祥喜庆的寓意,槟榔谐音宾郎,都是对人的敬称,以槟榔作聘礼,表明男女双方喜结连理,男方家人今后成为女方家尊贵的客人。且槟榔树干无枝,象征新人爱情忠贞不二,槟榔“叶下系数房,缀数十子”[14],又有多子多福之意。槟榔也代表了一定的经济价值,广西本地槟榔产量不高,其经济价值超越本地的其他物产,故而槟榔在一定程度上是重礼的象征。此外,广西临近越南、海南等槟榔主产区,外地运输而来的槟榔既提高了本地供应量,又使其价格不至过高,使槟榔成为一种价格略高、但消费得起的稀罕物。

表1 明清至民国时期广西槟榔婚俗记载
三、广西槟榔习俗的衰退
民国时期,广西部分地方槟榔习俗仍较为流行,且一直延续至1949年。反观当下,广西的槟榔习俗几近消失。而历史上同有槟榔习俗的湖南、广东、台湾、海南等地,至今仍有不少槟榔习俗的遗存。
民国时期广西槟榔习俗已开始发生变化,槟榔在婚俗中由明清时期的定聘之礼发展为提亲之礼。定聘礼相比提亲礼,要更加隆重,从定聘礼转为提亲礼,一定程度上是槟榔在婚俗中重要性衰减的表现。清末以后,婚礼越来越重金钱、首饰等高价值的实物,槟榔虽然仍有出现,但数量很少,已然成为一种传统延续的象征。近代新式礼仪传入,西式婚礼一度盛行,虽然一时难以直接深入乡村,但对传统婚礼的冲击已初现端倪,在传统婚礼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槟榔也不免黯然失色。民国以来,政府不断推进社会风俗的改进,中央政府力推“新生活运动”,广西地方政府亦提倡新风尚,宣传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嚼槟榔虽不算是陋习,但“啮之,齿尽作红色,唾滓于地如血”[27],既不卫生,也不雅观,与政府要求和社会流行的新风气格格不入,而新式礼仪和卷烟等新式消遣物的传入更加快了广西槟榔习俗的衰退。
广西历史上虽是较为严重的烟瘴地区,但经过长期发展,特别是明清政府对广西大力度的开发,使得人口急剧增长,至“嘉庆、道光年间,广西的山林荒野已开垦到相当程度”[28],以至于“嘉庆以后,广西即开始出现土地问题和人口问题”[29],大规模的土地、山林开发和人口的急剧增长,使得瘴气赖以存在的环境范围不断缩小,其对人们的影响也逐渐减弱。至近代以来,广西的瘴气逐渐消失。这样,多用于消瘴的槟榔其重要性亦随之下降。
另外,槟榔虽然具有消瘴的独特功效,但在广西的产区分布并不广泛,人们消瘴也不可能只依赖槟榔一物。乾隆《马平县志》载:“辣椒味辛辣,生食之,可消水气,解瘴毒。”[30]乾隆《梧州府志》载,杨桃“状甘酸而美,能辟岚瘴毒”[31]。民国《来宾县志》记载:“先温酒微醉,或啜薄粥,捣姜泡汤饮,行时烧烟吸之,或口含姜片,令馨香馥郁,否则嚼鲜槟榔,皆可抵御。”[32]总而言之,酸、辣、麻等具有刺激神经的提神之物,对御瘴都有作用,而杨桃、辣椒、烟丝、生姜等物,相比槟榔,在广西的产区分布广泛,几乎遍布全区。这些廉价易得的土产相比槟榔而言,实际使用率应高于槟榔。所以文献多记载,来客时才以槟榔招待,日常则较少食用。
槟榔最早是作为药材为人们所熟知,谚语云“是药三分毒”,虽有夸张,但却告诫人们,要警惕药物的副作用。而对于槟榔的副作用,古人早已有所警惕。周去非认为:“常欲啖槟榔以降气,实无益于瘴。彼病瘴纷然,非不食槟榔也。”[9]313王询推测:“按《本草》所载:槟榔性不甚益人。《丹溪》云:槟榔善坠,惟瘴气者可服,否则能病,真气有开门延盗之患。”[33]民国《三江县志》载:“土人多体瘠面黄,盖槟榔为患,习而不觉尔。”[34]可见槟榔作为下气之物,适量食用有利于消积通气,过量则会使人精气过度发散,不利于身体健康,古人对其已有较为清醒的认知。
从地理、经济因素来分析,广西虽然有适宜槟榔树生长的自然环境,但并不普遍。广西四周多山,海拔800米以上山地面积约5.6万平方千米,平原和台地面积仅占土地总面积的27%[35]。海拔较高的山地其气温与丘陵、平原地区相比,普遍较低,不适宜槟榔的生长。相比荔枝、龙眼、杨桃等物产,槟榔产量又很低,经济效益不高,民众缺乏种植动力。所以,即使槟榔习俗在广西的流行范围很广,但种植范围始终没有扩大,不能进一步支持槟榔习俗的延续。
此外,广西始终没有形成槟榔产业体系,这也是广西槟榔习俗迅速衰退的重要原因,与湖南形成鲜明对比。湖南同为非槟榔产区、烟瘴区,但大约在乾隆末年已经形成“成体系的槟榔业务”[36],民国时期又顺应时代变迁,改进槟榔制作方法,其槟榔产业延续至今。而槟榔在广西仅止于直接应用,一直未能形成产业,未能就槟榔本身进行更深入的开发,这似与广西的开发程度较低和非重要商道有很大关系。外地商人入境少,食用群体扩大的可能性较小,而本地的食用和使用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方式,受外来影响小。这种传统的习俗,一旦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极易被冲击乃至解体,以至于卷烟等西式消遣物传入以后,很快就取代了槟榔。
槟榔因其独特的消瘴作用,至迟在汉代广西已形成食用槟榔的习俗。明清之时,槟榔习俗在广西一度盛行,槟榔成为广西人民接待客人、婚礼过程中的重要物品。同时,随着这一时期中央王朝对广西的不断开发,瘴气逐渐消失,广西“由流放谪贬之地、蛮烟瘴雨之区一变而为‘内地乐土’”[37],槟榔的消瘴用途逐渐被淡化,加之长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人们更重视槟榔的礼制意义。民国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环境的变化,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槟榔习俗迅速衰退,至今近乎完全消失。广西槟榔习俗这一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广西社会的发展水平。因此,槟榔虽小,却是广西历史进程的一大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