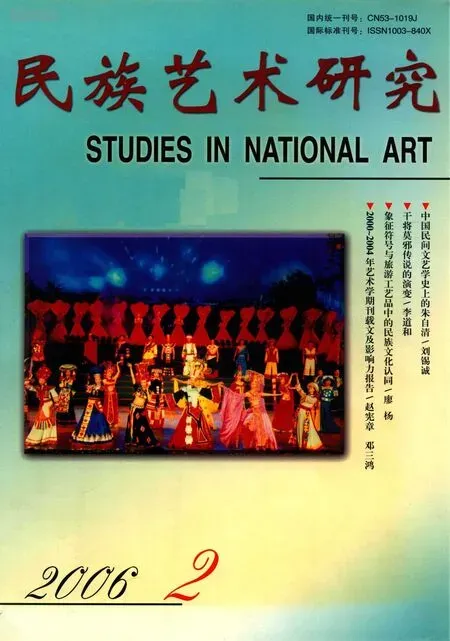全球化视域下的艺术界考察与实验民族志书写
——2020年度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动态及热点评述
2021-07-12陈韵
陈 韵
艺术人类学是一门跨界学科,其核心议题离不开对艺术与人类学之间关系的探讨。西方艺术人类学起始于“原始艺术”研究,其核心是对差异性(difference)、异质性(alterity)或者说是他性(otherness)的解码与翻译。这种对“差异性”的强调与纯粹“他性”的想象维系着早期艺术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后工业化、消费社会、科技爆炸直接动摇了早期艺术与人类学关系的基础。随着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渗透,“我们”与“他们”、“原始”与“现代”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曾有着“原始”意味的土著艺术被席卷入当代艺术界,而曾作为“他者”的土著艺术家、艺术评论家与策展人也在全球艺术领域内不断发声与活动。针对这种现象,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George E.Marcus)与弗雷德·迈尔斯(Fred R.Myers)认为,虽然对差异性的讨论仍然是艺术与人类学关系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需要在新的社会文化场景中重新思考艺术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①[美]乔治·E.马库斯、弗雷德·R.迈尔斯主编:《文化交流:重塑艺术与人类学》,阿嘎佐诗、梁永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对于艺术人类学研究来说,这意味着研究视域的拓宽:从单一地对“原始艺术”的关注,拓展到了对更为丰富的社会场景——当代艺术界的关注。随着全球艺术界进一步被“去西方中心化”,地方性艺术势力崛起,新的艺术界秩序被重新建立。①Thomas Fillitz,Anthropology and Discourses on Global Art,Social Anthropology,Vol.23,No.3,2015,pp.299-313.这其中不仅包括了一些地方性的当代博物馆、艺术基金等专业艺术机构的建立,地方性艺术双年展、艺术博览会等艺术活动的出现,也包括土著艺术家跻身当代艺术家行列,或以艺评家、策展人的身份,不断加入主流对话。当代艺术人类学研究者面对的田野正是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艺术界,这其中涉及诸多复杂交错的问题。诸如:艺术品作为商品在流通过程中牵扯到的生产、交换、价值、美学象征等问题;对艺术中挪用(appropriation)现象的追踪与再解释;地方艺术形式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包括土著艺术家如何获得“当代艺术家”这一身份的合法性,以进入国际艺术市场;传统艺术符号与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再建构之间的联系;当代艺术与人类学实践在方法论层面的相互合作与借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与艺术人类学研究视域拓宽相对应的,是民族志形式的不断创新。这与当代艺术的转型密切相关,当代艺术家已经从纯粹地对形式、技法的追求,转变到了与文化批判相关的观念生产。可以说,在文化批判的领域内,当代艺术家与人类学家相遇了。当代艺术的实践方式给了人类学家以灵感,他们延续着《写文化》之后对民族志书写方式的批判与反思②参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主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将当代艺术与人类学的手法相结合,探索如何使得民族志书写和拍摄与研究者、主体、受众之间的对话互动变得更为活跃的方式。在这种新的互动模式中,资讯人(informant)不是被解释的对象,而是主动为自己说话③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ed.),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and Politicsof Ethnography.25th anniversary edi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新的实验民族志挑战着传统以文本为基础的书写权威,用一种超文本、多模态、多感官的方式展开。
一、实验民族志:超文本、多模态、多感官的知识生产
当代人类学实践常常将民族志理念融入当代艺术、策展等方式中。这类民族志呈现为一种超文本、多模态、多感官维度的样貌,我们可以称之为实验民族志。2020年的艺术人类学相关出版物延续了对实验民族志的进一步探索。而这种实验民族志的产生,与当代艺术创作与民族志写作方法的改变有很大关系,下面简略追溯一下实验民族志产生的背景。
“二战”之后,随着都市文化的迅速蔓延,人们开始汇集到一个被压缩的都市空间内生活,社会交往因而变得频繁④[法]尼古拉斯·伯瑞奥德:《关系美学》,黄建宏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面对这种变化了的社会情境,艺术家们开始“以整个人类互动及其社会背景为理论视野”⑤[法]尼古拉斯·伯瑞奥德:《关系美学》,黄建宏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进行实践,以艺术创作为载体对眼前的社会进行批判与反思。这一类的艺术实践具有极强的参与性、合作性、对话性,因为艺术家常常需要与不同的人群合作,探索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法国艺术策展人、艺术批评家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将这一类艺术实践定义为“关系艺术”⑥[法]尼古拉斯·伯瑞奥德:《关系美学》,黄建宏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或者称为“合作艺术、社会参与艺术、社区艺术或对话艺术”⑦Thomas Fillitz and Paul van der Grijp(ed.),An Anthropology of Contemporary Art:Practices,Markets,and Collectors.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8,p.31.。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代艺术家已经从对自然的再现模仿,对于形式、技法、表现媒介纯粹性的追求,转变到了对哲学观念的探讨和对文化现象的批判。至此,当代艺术本身也同人类学一样,迈入了一种文化生产领域。这种艺术观念的转变导致了艺术创作方式的改变,艺术家开始进入社会关系情境中展开田野调查,当代艺术实践的这种“民族志转向”(the ethnographic turn)①参见[美]哈尔·福斯特:《艺术家作为民族志者》,载乔治·E.马库斯、弗雷德·R.迈尔斯主编:《文化交流:重塑艺术与人类学》,阿嘎佐诗、梁永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9—368页。与人类学家的工作方式产生了某种重叠。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人类学家开始反思传统民族志的书写方式②这种民族志的反思浪潮以1989年《写文化》的出版为高峰。,并探索民族志表达的多种可能性。马库斯认为,民族志的研究方式为人类学学科在传统的边界之外拓展了新的可能性,也为人类学带来了新的合作伙伴。③George E.Marcus,Ethnography:Integration,see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ethnography-integration.当代人类学家或是与艺术家进行合作,或是化身为策展人④关于人类学与策展的专著,参见Roger Sansi(ed.),The Anthropologist as Curator,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20.,用当代艺术的形式进行知识生产。
(一)表演民族志
玛雅·斯托瓦尔(Maya Stovall)的《酒类商店剧场》(Liquor Store Theatre,2020)源于一个观念艺术和人类学结合的视频项目,该艺术项目于2017年参与了惠特尼双年展。在视频中,斯托瓦尔在底特律的酒类商店附近跳舞,以此为契机触发了与周围邻居的对话。她在对话中询问人们对底特律这座城市的看法,这一谈话涉及当地历史、经济、美学、政治、社会、性、种族主义等方方面面。⑤Maya Stovall,Liquor Store Theatre,Duke:Duke University Press,2020.通过亲身参与的艺术项目,作者思考了民族志、艺术相结合进行知识生产的可能性。
“酒类商店剧场”项目的运营是一次基于城市研究的民族志考察,更是一场沉浸式戏剧的演出,这场戏剧舞台上的表演者是艺术家兼人类学家与受访者。这种方式颠覆了传统的田野考察方式,也改变了人类学家与资讯人(informant)之间的关系。在斯托瓦尔的民族志考察中,人类学家与资讯人之间最开始是表演者与观众的关系,他们交谈是由一场舞蹈行为引发的,而在传统的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与资讯人之间的交流往往是以正式或非正式的访谈形式展开。斯托瓦尔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志参与方式,也为当代艺术人类学实践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同样是表演艺术与民族志的融合,《我从不孤单,或奥波尼基:俄罗斯残疾人的民族志戏剧》(IWas Never Alone,or Oporniki:An Ethnographic Play on Disability in Russia,2020)也为实验民族志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样本。正如马库斯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所说的,在人类学传统中,在一个限定的地理范围内进行田野考察并完成民族志书写一直是人类学家职业工作的核心内容,它标志着人类学家是否通过了“成年礼”,从而获得职业资格⑥George E.Marcus,“Foreword:The Play’s the Thing”,in Cassandra Hart,Iwasnever alone or oporniki:An ethnographic play on disability in Russia,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20.。但是随着当代的田野场域边界不断被打开,民族志的书写方式也拥有了更多可能性,像哈特布莱的当代戏剧民族志或表演民族志就是一种人类学研究的新模式,它的呈现超越了文本空间,进入一个由田野考察、剧本写作、舞台剧表演、视频网站等元素复合一体的新维度。
《上演文化邂逅:阿尔及利亚演员赴美巡演》(Staging Cultural Encounters:Algerian Actors Tour the United States,2020)提供了一个新的跨文化批判视角,即作为文化直接产物的戏剧,可以在流通中如物一般被人类学家所研究。过去因为经济、交通、科技一系列原因,诸如戏剧这类别的巨型体量的文化产物并不能在一个广阔的空间中流动。因为全球化,各国之间的剧团、舞团都可以自由往来,当这样一种巨型体量的文化产物从本土进入全球之后,它面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对象,这其中产生的跨文化翻译与解释问题,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类学家所面临的一类全新问题。全球化背景之下的跨文化交流与翻译一直是人类家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往往是追随着物品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种种挪用现象来进行论述。
(二)策展民族志
2019年末出版了一本专门探讨当代策展与人类学实践的论文集《作为策展人的人类学家》(The Anthropologist as Curator)。①Roger Sansi(ed.),The Anthropologist as Curator,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20.人类学家策展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西方国家,中国的人类学家也有意或无意地介入了策展领域,成为策展人。②参见方李莉:《人类学与艺术在后现代艺术界语境中的相遇》,尚未出版。作者在文中谈到了其多次策展的经历。艺术家兼策展人阿曼达·克鲁格里亚克(Amanda Krugliak)、摄影艺术家理查德·巴恩斯(Richard Barnes)与人类学家杰森·德莱昂(Jason de León)合作了展览“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克鲁格里亚克与巴恩斯在论文《“例外状态”展览中的人类学与艺术:展览的演变》(Anthropology and Art in State of Exception:The Evolution of an Exhibition,2020)中深入探讨了这次展览的由来、发展及演变过程。
“例外状态”一词来源于同名政治理论,形容的是法律与政治之间的灰色地带,策展人在此借用这个名字来探讨美国非法移民的问题。人类学家德莱昂针对美墨边境的秘密移民问题,进行了名为“无证移民项目”(Undocumented Migration Project)的人类学项目。③Amanda Krugliak and Richard Barnes,Anthropology and Art in State of Exception:The Evolution of an Exhibition,Theory in Action,Vol.13,No.2,2020,pp.16-30.策展团队从德莱昂的民族志中获得对这一主题的概念和初步印象,同时加入了观念和美学维度的考量。展览用艺术装置的形式将收集到的物件呈现出来,用平凡物品来讲述生命故事,揭示主题本身的特质(比如生命的易逝性)。其他展出的装置中还有对移民的采访视频,通过这些视听材料,让移民们直接发声。可以说,策展成为当代人类学家影响社会的一大利器。
(三)行走民族志
行走(walking)是当代艺术家实践的一种形式,它是一种“不可预知的风景”,是对乌托邦的寄托。艺术家们通过漫无目的且不计时间成本的行走,来反抗与挑战日益机械化与异化的现代社会中不断加速的对于时间、金钱、效率的追求。在此意义上的行走表现出乌托邦与政治的属性④Roger Sansi,Walking utopias.The politics of walking in art and anthropology,Social Anthropology,Vol.29,No.1,2021,pp.141-155.。同时,艺术行走也启发了人类学家。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人类学系的罗杰·桑西(Roger Sansi)在最新的论文《行走的乌托邦。艺术行走的政治与人类学》(Walking utopias.The politics of walking in art and anthropology,2020)中以“行走”为切入点,结合其自身的民族志写作经历,比较了艺术行走与“行走人类学”之间的差异。
桑西认为,艺术行走的内涵发展于艺术理论中,更具政治性,它一方面作为对未来乌托邦社会的设想,另一方面通过在城市与自然景观中的行走,来完成对权力关系和流动性的批判。⑤Roger Sansi,Walking utopias.The politicsofwalking in artand anthropology,Social Anthropology,Vol.29,No.1,2021,pp.141-155.与此同时,行走人类学则不那么热衷于乌托邦与政治的概念。⑥Roger Sansi,Walking utopias.The politicsofwalking in artand anthropology,Social Anthropology,Vol.29,No.1,2021,pp.141-155.桑西认为,这是因为行走人类学是隐性的政治,因为它在更广泛层面重新思考了人类学实践,但这种隐性的政治是否是“乌托邦的”还有待思考。⑦Roger Sansi,Walking utopias.The politicsofwalking in artand anthropology,Social Anthropology,Vol.29,No.1,2021,pp.141-155.总体来说,桑西的这篇论文延续了他在《艺术,人类学与礼物》(Art,Anthropology,and the Gift)⑧参见Roger Sansi,Art,Anthropology,and the Gift,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5.一书中的写作方式,围绕着一个特定概念(比如“礼物”或“行走”),来探讨艺术与人类学在实践与理解层面的边界与差异。
在当代艺术中,对技法的追求已经让位于观念的表达。因此,就像策展人与人类学家之间的职业壁垒已经变得模糊似的,艺术家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当代人类学家面对的艺术作品不再是让他们困惑的“天才之手”的创造,而是像“行走”“寻常物”等日常生活情境中触手可见之物和行为。因此,人类学家介入当代艺术变得更为容易,桑西的这篇文章更是让我们看到了实验民族志的一种新的可能性,即人类学家通过实践当代艺术,来探讨围绕着艺术与人类学关系的一系列问题,而这类主题也是当代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艺术人类学理论的回溯与创新
(一)经典艺术人类学理论的反思与应用
盖尔的《艺术与能动性》(Art and Agency: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1998)是一本重要的艺术人类学理论著作,在其面世的20余年间持续引发着学界的广泛探讨。对于盖尔来说,艺术人类学是对“调解社会能动性的客体(objects)周围的社会关系”①Alfred Gell,Art and Agenc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p.7.的研究。他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定义了“艺术”,认为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人类学研究的“艺术客体”(art object)②Alfred Gell,Art and Agenc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p.7.。基于这样的认识,盖尔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重点“从客体所意指的关系,转向了研究客体内在的关系(relations immanentwithin the object)及其理论意义。”③Susanne Küchler and Timothy Carroll,AReturn to the Object,London:Routledge,2020,p.xiv.
苏珊·屈希勒尔(Susanne Küchler)是盖尔的学生,现任伦敦大学人类学和物质文化教授,她与蒂莫西·卡罗尔(Timothy Carroll)在教授艺术人类学的课程时使用了《艺术与能动性》这本书,并在教学过程中对盖尔的理论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测试、批判和发展。《回归客体:阿尔弗雷德·盖尔、艺术与社会理论》(A Return to the Object:Alfred Gell,Art,and Social Theory,2020)一书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屈希勒尔与卡罗尔认为,在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漫长历史中,客体(the object)一直居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次要地位,只被简单地当作一种替代性的客体化(objectification),或者仅仅是人类过去行为的足迹,抑或是仅仅被解释为符号的容器。④Susanne Küchler and Timothy Carroll,AReturn to the Object,London:Routledge,2020,p.xiv.因此,作者认为对“客体”这一概念需要进行重新评估,他们对围绕着盖尔核心理论的一系列重要概念诸如能动性(agency)、指示符(index)、原型(prototype)等进行了深度辨析。同时,作者将盖尔的理论放入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加以思考,呈现了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南希·芒恩(Nancy Munn)等著名人类学家的理论与盖尔理论之间的联系性。通过这样的写作方式,作者意在追踪盖尔思想的源头与意图,并激发其思考更多的可能性。
同样是著名人类学家的学生,帕梅拉·弗里斯(Pamela R.Frese)和苏珊·布劳内尔(Susan Brownell)在其主编的著作《课堂中的体验和表演人类学:伊迪丝·特纳和维克多·特纳的遗产》(Experiential and Performative Anthropology in the Classroom:Engaging the Legacy of Edith and Victor Turner,2020)中,对其老师特纳的理论进行了解读与延续。仪式一直以来便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仪式使隐性的文化真理、矛盾和难题得以艺术地体现和表现”⑤Pamela R.Frese and Susan Brownell(ed.),Experientialand Performative Anthropology in the Classroom:Engaging the Legacy of Edith and Victor Turner,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20,p.2.。作为著名人类学家,特纳以其对仪式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他提出了“社会剧场”的概念,并与著名先锋戏剧理论家理查·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一起,为体验和表演人类学作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课堂中的体验和表演人类学》是基于课堂经验,对特纳的表演民族志理论应用于教育领域的一种反思。作者认为,“表演促进了一种‘体验式学习’,将更多传统人类学和民族志对社会和文化的观点转变为特殊的经验现实”⑥Pamela R.Frese and Susan Brownell(ed.),Experiential and Performative Anthropology in the Classroom:Engaging the Legacy of Edith and Victor Turner,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20,p.2.,同时,“这些‘参与式学习’的练习超越了传统的教育方式,可以极大地增强学生对民族志文本中描述的真实人物的理解,促进体验式和想象式的学习方式。”①Pamela R.Frese and Susan Brownell(ed.),Experiential and Performative Anthropology in theClassroom:Engaging the Legacy of Edith and Victor Turner,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20,p.2.
表演与民族志的结合不仅促进了当代人类学的研究与表达,同时,也在重塑着教育模式。传统的人类学学者主要是通过眼睛(阅读文献)与嘴巴(谈话、作报告等)这两条感官渠道接受训练。将民族志式表演(ethnographic performance)作为一种工具融入教学,使得民族志主题获得表演性再创造,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们打开了不同的感受渠道,进入一种体验式的、多模态、多感官的全新人类学受训模式。
(二)应用艺术的人类学视角探索
人类学的视野与方法论不仅对于纯艺术(fine art)学科具有启发性与实践意义,同时更是启发了更为广泛意义上的艺术实践,比如应用艺术(applied art)。
《语境中的设计人类学:设计物质性与合作思维导论》(Design Anthropology in Context:An Introduction to Design Materiality and Collaborative Thinking,2020)一书探索了设计人类学这一跨学科领域,作者亚当·德拉津(Adam Drazin)认为,“物质文化不仅是设计的结果,而是设计工作的核心。”②Adam Drazin,Design Anthropology in Context:An Introduction to Design Materiality and Collaborative Thinking,London:Routledge,2020,p.11.而物质文化研究起源于人类学,设计与人类学在此就产生了对话的可能性。在当今的消费社会之中,设计不仅是为了获得实用功能、美观,同时设计本身也与消费者的社会地位息息相关。可以说,设计创造的是一种文化产品,而设计也因此开始转向一种社会研究。德拉津在书中分析了设计的“社会研究转向”③Adam Drazin,Design Anthropology in Context:An Introduction to Design Materiality and Collaborative Thinking,London:Routledge,2020,p.5.这一历史现象,同时,还探讨了如下一些议题: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如何理解设计文化,设计人类学的工作方式,设计人类学作为一种道德活动,等等。
从德拉津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设计本身也拓宽了当代人类学的研究关系和工作模式。在设计人类学中,设计师往往需要往返于田野点与设计工作室之间。在此意义上的民族志,不仅仅是参与观察式的田野工作,同时,设计工作室(studio)也可以成为一种“侧面/横向民族志”(lateral ethnography)④Adam Drazin,Design Anthropology in Context:An Introduction to Design Materiality and Collaborative Thinking,London:Routledge,2020,p.7.。
三、书写土著艺术:土著学者加入竞技场
对土著艺术(或称原始艺术)的研究,一直是传统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之一。在西方人类学历史上,有诸多研究流派都从不同角度对原始艺术的性质、范畴、意义和内涵进行辨析。⑤参见李修建:《原始艺术:西方艺术人类学的核心范畴》,《民族艺术》2020年第5期,第158—168页。克利福德认为,由西方主导的“艺术—文化体系(art-culture system)自19世纪以来主宰了欧洲和北美洲对于艺术与文化工艺的分类与鉴定标准”⑥[美]詹姆斯·克里弗德:《路径:20世纪晚期的旅行与翻译》,YOTAKAK译,苗栗县: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135页。,其中也包含了对原始艺术分类解释系统的主导权。
这样的情形随着地方性文化的复苏与原住民振兴运动的兴起发生了改变。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当代艺术界也已成为土著艺术家、批评家和策展人知识生产的重要场所。⑦[美]尤金妮亚·基辛、弗雷德·R.迈尔斯:《艺术终结后的艺术人类学:对艺术—文化体系的质疑》,陈韵译,尚未发表。一些土著策展实践都标志了这一转向,例如在圣达菲举行的《纪录片和现场线》(Documenta and SITElines),以 及 连 续 三 次(2016—2018年)在纽约维拉李斯特艺术政治中心举办的、名为“土著纽约”的土著艺术、策展和批评活动。①[美]尤金妮亚·基辛、弗雷德·R.迈尔斯:《艺术终结后的艺术人类学:对艺术—文化体系的质疑》,陈韵译,尚未发表。正如克利福德所言:“这些(土著)团体并没有如预期的,在现代化的同质化趋势或在全国性的文化熔炉中消失。他们目前的作品都无法轻易被归纳到普遍对艺术或文化的定义中。我认为这些团体都参与并且颠覆了这场具有主导性的艺术文化游戏。”②[美]詹姆斯·克里弗德:《路径:20世纪晚期的旅行与翻译》,YOTAKAK译,苗栗县: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135页。
《了解土著艺术》(Knowing Native Arts,2020)是一本来自内部批判视角的著作。书中关注的内容包括了“土著艺术学术的核心框架(包括博物馆和学院的机构)、土著美学分析的形式、土著艺术在新的全球和数字领域内的接受范围,以及根据当前美国印第安人策展授权的展览实践模式。”③Nancy Marie Mithlo,Knowing Native Arts,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20,p.17.正如作者所言:“我们所认为的‘艺术’(art)的流通和解释提供了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集体思考当前的全球现实。”④Nancy Marie Mithlo,Knowing Native Arts,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20,p.16-17.土著艺术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研究领域,而且是一个批判视角,透过土著艺术作品,可以审视我们当前世界面临的集体时代危机——不平等、环境灾难、健康差距、混乱、贫穷、仇恨言论和暴力行为等等。在一个土著自决时代(Self-Determination Era)⑤注:自决时代(1968年至今)的特点是民权运动的爆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自决时代迎来了新一轮部落领导浪潮。全国各地的活动家利用政治、法律和民事手段迫使美国正视其对美洲土著人的虐待历史。参见https://library.law.howard.edu/civilrightshistory/indigenous/selfdetermination.,土著艺术的存续不仅扩大了艺术史的讨论范围,同时,人类学家们正是追随着土著艺术活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批判领域——一个土著艺术参与全球的艺术界。
同样是带有土著血统的学者,西澳大利亚大学伯恩特基金会研究员格蕾琴·斯托尔特(Gretchen M.Stolte)在《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艺术:昆士兰州北部身份生产的人类学》(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Art:An Anthropology of Identity Production in Far North Queensland,2020)一书中关注了土著艺术与身份生产这一主题。她关注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的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艺术作品,并用丰富的民族志细节来阐释土著艺术家如何理解和表达他们的文化遗产。这其中涉及对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如何定义土著身份?什么样的当代土著艺术品被认为是“正宗的”?土著身份的认定又如何影响观者对艺术品的判断?⑥Gretchen M.Stolte,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Art:An Anthropology of Identity Production in Far North Queensland,London:Routledge,2020.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斯托尔特以其亲身经历入手,探讨政府对于“土著身份”的认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了土著艺术家。⑦Gretchen M.Stolte,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Art:An Anthropology of Identity Production in Far North Queensland,London:Routledge,2020.斯托尔特的民族志关注到了当代土著艺术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以及意义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这一重要主题。
2020年土著艺术界还迎来了重要的展览项目。展 览“克 劳 族 妇 女 和 战 士”(ApsáalookeWomen and Warriors)由土著策展人尼娜·桑德斯(Nina Sanders)策划,分别在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Feld Museum)与芝加哥大学纽鲍尔学院(Neubauer Collegium)展出。⑧Nina Sanders and Dieter Roelstraete(ed.),ApsáalookeWomen and Warriors,Chicago:Neubauer Collegium,2020.展览围绕着克劳族人⑨注:克劳(Apsáalooke,常称为Crow),住在美国黄石河和大霍思河上游的美洲土著,现有大量居于美国蒙大拿州。的艺术创作展开,汇集了博物馆馆藏中首次公之于众的克劳部落早期彩绘和装饰盾牌,以及克劳艺术家和工匠的当代作品。展览不仅展示了克劳文化丰富的历史与其独特的世界观,同时当代克劳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通过文字、图像、声音传达了其对未来的展望。⑩Nina Sanders and Dieter Roelstraete(ed.),ApsáalookeWomen and Warriors,Chicago:Neubauer Collegium,2020.
通过将古董、土著工艺品与当代美国土著艺术家作品并置的方式,策展人让我们看到了土著艺术的“同时代性”(coevalness)①注:同时代性,或译为“共生性”。关于更多“同时代性”的含义,参见[德]乔纳斯·费边:《时间与他者》,马健雄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首先,承认土著艺术是与我们同一时代的;其次,土著艺术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值得注意的是,桑德斯是菲尔德博物馆启用的首位美洲土著策展人。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土著策展人、艺评家加入了对土著艺术的书写队伍中,这打破了传统的西方学者主导模式,让我们看到了对土著艺术解读的内部视角。土著学者与西方学者在解读土著艺术时会有何不同,这一问题仍待思考。
四、连接地方与全球:艺术界的民族志考察
贝克尔的“艺术界”(art worlds)观点认为,艺术不只是单纯的审美创造,而是一种复杂的、嵌入社会关系网中的生产活动。②参见[美]霍华德·S.贝克尔:《艺术界》,卢文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艺术界与艺术市场中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现象吸引了人类学家的目光,将其当作文化研究与批判的场域。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特·普拉特纳(Stuart Plattner)认为,让人类学的厚描手法介入艺术市场分析具有优势,可以加深对艺术市场的理解,并且认为对艺术市场的民族志书写会成为未来人类学研究的一大趋势。③[美]斯图尔特·普拉特纳:《艺术人类学:研究视野与当代趋势》,李修建译,《艺术探索》2017年第5期。随着非西方艺术④笔者注:此处指的是传统以欧洲-北美为中心的主流艺术史叙事之外的区域。力量的崛起,地方艺术界也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关注,这其中充满了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全球力量的博弈。
土著艺术作为澳大利亚艺术形象的代表,成为国家“软外交”的利器,在国际上代表了国家地位与身份。但与此同时,当代澳大利亚艺术界却存在着种种不稳定,比如:政府对艺术项目的资助标准存在争议,如何判定土著艺术本身蕴含的价值?作品的市场价值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吗?土著艺术在融入主流艺术界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摩擦,土著艺术家如何在一个白人引领的艺术界中生存活动,实现其话语自治权?⑤参见Deborah Stevenson,Tony Bennett,Fred Myers,and Tamara Winikoff,Introduction:The Australian Art Field-Frictions and Futures,in Tony Bennett,Deborah Stevenson,Fred Myers,TamaraWinikoff(ed.),The Australian Art Field Practices,Policies,Institutions,London:Routledge,2020,pp.1-11.以上种种问题都是《澳大利亚艺术场域:实践,政策,机构》(The Australian Art Field:Practices,Policies,Institutions,2020)这本论文集的写作背景。这本书的写作受到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对法国艺术场域的理论分析的启发。艺术场域不仅由各种机构组成,而且还包含了相关人员制定的政策、策略,以及布尔迪厄所谓的“惯习”(habitus)。⑥Pierre Bourdieu,The Rules of Art: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书中汇集的论文涵盖如下这些议题:国家和国际艺术市场;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的艺术实践;社会关系和机构及其在当代澳大利亚艺术中的作用;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制度和资助方案以及土著艺术和土著艺术家的创作。⑦Tony Bennett,Deborah Stevenson,Fred Myers,Tamara Winikoff(ed.),The Australian Art Field:Practices,Policies,Institutions,London:Routledge,2020.
澳大利亚当代艺术场域面临的挑战让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仍然处于全球化的进程中,新的世界秩序还未被建立完。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新旧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艺术界里的体现便是来自国际与地方市场之间基于意识不同而产生的摩擦。当今的艺术人类学研究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全球化世界中的种种复杂化问题。而人类学的厚描手法具有深入分析这些复杂化问题的能力,正如普拉特纳所说的,“人类学所秉持的深入的厚描方法,将会极大地推动对于艺术市场的研究。”⑧[美]斯图尔特·普拉特纳:《艺术人类学:研究视野与当代趋势》,李修建译,《艺术探索》2017年第5期。
由纽约大学人类学和美国研究教授阿琳·达维拉(Arlene Dávila)撰写的《拉美艺术:艺术家、市场和政治》(Latinx Art:Artists,Markets,and Politics,2020)将目光聚焦在美国艺术界中的一个独特群体——拉美裔艺术家及其创作之上。拉美文化是美国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拉美裔艺术家的创作也是美国艺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拉丁美洲裔人类学家,达维拉为全球当代艺术市场提供了一个内部批判的视角,她通过对艺术家、艺术商、评论家、策展人等拉丁艺术专家的大量采访,探索了拉美艺术和艺术家视觉化的问题。①Arlene Dávila,Latinx Art:Artists,Markets,and Politics,Duke: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2020.这本书的出版恰逢美国移民矛盾与民族分裂危机甚嚣尘上之时,透过对当代拉美艺术的审视,作者探讨了有关艺术多样性、文化定义、种族、地缘政治等复杂的问题。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代西方艺术人类学关注场域的转变,而那些迫切的、当下的、时事的问题也被纳了人类学家的思考之中。同时,我们还看到,采用艺术人类学这种跨学科的复杂、开放、实验的知识生产手法,可以更为有效地反映,甚至帮助不同的利益群体更好地理解彼此,化解当下复杂而变化的世界中不断产生的全新问题和挑战。
《达喀尔艺术:达喀尔双年展与当代非洲艺术创作》(Dak'Art:The Biennale of Dakar and 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Art,2020)这本书以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艺术双年展“达喀尔艺术”(Dak'Art)为切入点,从历史角度考察了塞内加尔当代艺术的兴起,同时辩证地批判了双年展的目标及运作,质疑其是否创造了具有非洲地方特色的实践模式。②Thomas Fillitz,Dak'Art:The Biennale of Dakar and 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Art,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20.
当代艺术的概念是如何影响地方艺术界的?同时地方传统艺术又是如何与当代艺术进行融合,从而进入国际市场的?这些都是全球化的艺术世界中产生的重要问题。菲利茨认为,“全球艺术”(global art)这一概念非常重要,它是当代文化批判的一个切入点,同时也是人类学介入地方艺术界考察的一个重心。首先,“全球艺术”这一概念关注西方艺术史之外的、一度被边缘化的艺术形式。其次,“全球艺术”专门研究任何艺术世界的当代艺术。③Thomas Fillitz,Anthropology and Discourses on Global Art,Social Anthropology,Vol.23,No.3,2015,pp.299-313.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崛起的地方艺术界内,“当代艺术”是地方文化参与国际对话的有力通行证之一,同时,作为“当代艺术家”的地方艺术家也得以在国际艺术市场上取得合法身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何分析当代艺术的地方性特色”④Thomas Fillitz,Anthropology and Discourses on Global Art,Social Anthropology,Vol.23,No.3,2015,pp.299-313.成为艺术人类学者关注的一大问题,关于此,《达喀尔艺术》一书作出了很好的示范。
结 语
如果说传统的人类学家面对的是与现实世界割裂的、遥远静止时空中的“原始社会”的话,那么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一切问题都在迅速地发生着,这其中充满了传统与现代、地方性与全球性力量的博弈。人类学家如何观察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遇到的种种社会问题?人类学知识又如何能够打破单一学科的壁垒,进行有效的传播?面对这些问题,艺术成为当代人类学家观察与表达其思想的一个有效工具。2020年艺术人类学的相关出版物反映了如下研究趋势。
第一,当代人类学知识的生产与表现手段也在适应时代的变化,呈现出一种超文本、多模态、多感官维度的实验民族志模式。其中,诸如舞蹈、戏剧、行走等当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以及更为综合的策展方式都成为人类学家探索的工具。
第二,经典艺术人类学理论在新的时空场景之中得到了延续性思考。著名人类学家盖尔、特纳的学生们分别对其导师的理论进行了发展性的批判研究。同时,设计人类学出现了新的理论专著。从中可以看到,在面对一个问题复杂化的当代世界,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交流与融合是一种趋势。人类学对文化的独到分析影响并扩展了艺术学研究的深度,而艺术本身也在给予人类学以灵感,不断开拓着人类学家的工作方式。
第三,如果说早期人类学家对艺术的关注集中于“原始艺术”“民族艺术”等或边缘社会中的艺术现象,并未参与主流艺术的书写的话,那么当代性使得主流与非主流、高雅与低俗、精英与民间等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间隔开始消融,那些一度被阻隔于主流艺术史书写之外的地方性艺术形式,跨越了“历史的藩篱”①[美]亚瑟·丹托:《在艺术终结之后:当代艺术与历史藩篱》,林雅琪、郑惠雯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10年版。,进入到当代艺术中去。人类学家对艺术的观察也随之进入了主流艺术的写作②参见方李莉:《人类学与艺术在后现代艺术界语境中的相遇》,尚未出版。。与此同时,对于土著艺术的书写,也打破了传统西方学者的主导模式,土著人类学家、策展人、艺术评论家等纷纷迈入了“书写土著艺术”这一竞技场,用多种视角解读着土著文化的历史与变迁、困境与未来。
最后,面对一个秩序被重建的全球艺术界,人类学家们对非洲、澳大利亚、美国等不同的地方艺术界进行研究,分别从国家政策、艺术机构(艺术双年展、拍卖行)、艺术家群体等角度入手,就当代艺术的地方表现、艺术与政治、艺术家的身份等问题进行探索。同时,对当代艺术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审美问题,转向了围绕着艺术创作、生产、消费过程中一系列复杂的社会与文化问题。而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当代艺术界,人类学的厚描手法在深入进行文化批评的层面具有其独特性。因此,对当代艺术界的观察将会成为艺术人类学一大研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