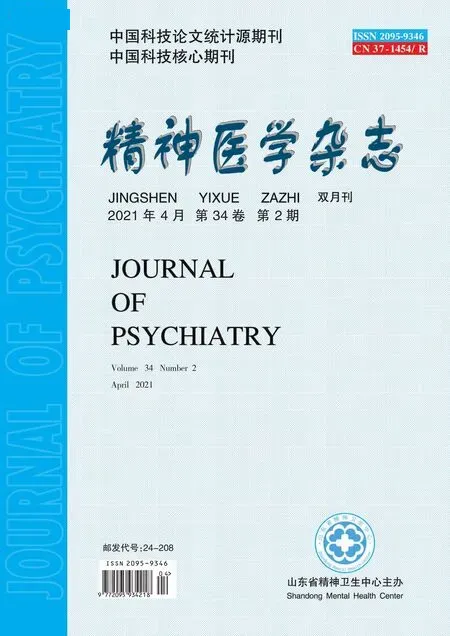心理干预改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家长焦虑抑郁情绪的对照研究
2021-06-23范丽伟
范丽伟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是一种在儿童期常见的异常行为疾病,在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CD-11)中属于神经发育性障碍,主要表现为注意力的明显不集中、不分场合的活动过多、缺乏对冲动行为的控制、情绪易激动、学习成绩普遍较差等[1]。有国外文献指出,ADHD的患病率一般在3%~6%,男孩明显多于女孩[2]。ADHD作为一种最常见的儿童行为问题之一,不但明显影响患儿的正常学业和家庭生活、严重影响患儿的正常社会人际交往,而且还有可能对患儿家长的心理状态产生较为明显的不良影响[3]。本研究主要针对ADHD患儿的家长,评估患儿家长存在焦虑、抑郁的状况,并利用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对存在抑郁、焦虑症状的家长进行干预,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自愿原则,随机选取2018年1月~2019年12月在两家综合性医院儿科及一家精神卫生中心门诊就医的ADHD患儿及其家长。入组标准:(1)入组患儿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IV)中ADHD的诊断标准[4];(2)入组家长需为患者直接监护人,并且为主要生活照料者,每位患儿仅入组一位家长;(3)患儿年龄为6~12岁,家长年龄为18~60岁;(4)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5)患儿的病程>6个月;(6)家长签署本研究的书面知情同意书;(7)患儿需排除严重躯体疾病、其他精神障碍共病者,家长需排除严重躯体疾病、严重精神障碍、严重心理问题者,患儿及家长近期均无重大生活事件经历。研究已经伦理委员会审核并通过。
共计入组ADHD患儿800例以及800名家长,最终完成全部研究的有ADHD患儿785例以及785名家长,完成率为98.13%。其中:(1)患儿:共785例,男671例,女114例;年龄7~12岁,平均(9.31±1.79)岁;病程7~18个月,平均(13.59±5.41)个月;(2)家长:共785名,男361名,女424名;年龄29~57岁,平均(36.73±10.36)岁;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高中289名,本科355名,研究生141名。根据随机数字法,将存在焦虑和(或)抑郁情绪的236名家长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接受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对照组不接受心理干预。两组的一般情况为:(1)干预组:入组118名家长,男52名,女66名;平均年龄(35.91±11.12)岁;初中及高中37名,本科50名,研究生31名;对应的118例患儿中男109例,女9例;平均年龄(8.94±1.54)岁;平均病程(12.87±6.04)个月;(2)对照组:入组118名家长,男54名,女64名;平均年龄(36.05±12.45)岁;初中及高中33名,本科55名,研究生30名;对应的118例患儿中男106例,女12例;平均年龄(9.12±1.87)岁;平均病程(13.03±6.86)个月。上述各项指标,两组间经过统计学分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评价量表 (1)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5]:主要用于评价个体近1周内的焦虑状况,共20个条目,每条目分为1~4分共4级评分,标准分≥50分即视为存在焦虑症状;(2)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5]:主要用于评价个体近1周内的抑郁状况,共20个条目,每条目分为1~4分共4级评分,标准分≥50分即视为存在抑郁症状。
1.2.2 研究流程及效果评价 首先由经过严格专业培训的精神科医生及儿科医生对就诊患儿进行专业诊断,向确诊ADHD患儿的家长讲明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并取得书面知情同意后,对符合入组标准的家长完成入组,所有患儿均接受速效剂哌甲酯系统治疗(初始剂量5 mg/d,为晨起一次服药,后根据病情变化,剂量调整至10~30 mg/d,剂量增加后为晨起、午间两次服药)和常规的护理措施,整个研究过程中,患儿不可接受其他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家长不可接受精神科药物治疗和其他心理干预。对已入组的家长进行SAS、SDS量表评定,根据SAS、SDS的评分结果,分别计算焦虑症状和抑郁症状的发生率,并将存在焦虑症状和(或)抑郁症状的家长按照随机数字法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儿沿用之前的治疗护理方案,干预组家长在此基础上接受3个月的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3个月干预后,对干预组和对照组家长再次进行SAS、SDS量表评定并对两组中的患儿进行效果评价[6],根据SAS、SDS量表评分降低程度将疗效分为4个等级:降低≥75%为痊愈(主要症状消除,学习和日常生活能力得到显著地提高),降低50%~75%为显效(主要症状明显好转,学习和日常生活能力有一定提高),降低25%~50%为有效(主要症状有改善,但学习和日常生活能力不稳定,需要家长的协助和督促),降低<25%为无效(症状无好转,学习和日常生活能力低下)。治疗有效率=(痊愈人数+显效人数+有效人数)/总人数×100%。
1.2.3 心理干预策略 将干预组家长进行分组,每组8~12人,分别进行心理干预,心理干预每周进行一次,每次约60 min,共进行3个月。主要内容包括:(1)健康教育讲座:主要内容为ADHD的相关知识,包括流行病学特点、病因及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及鉴别诊断、治疗原则、病程特点、预后、常见药物不良反应的表现及处理原则等;(2)家长培训:主要内容包括给家长的良好支持环境、学习掌握解决家庭问题的常用方法、如何制定奖惩方案、如何有效避免与孩子间的矛盾冲突的技巧、如何正确应用阳性强化及适当惩罚的方法等;(3)交流和反馈:干预者与家长进行平等、有效的交流,针对家长在所学方法的实施过程中反馈出现的问题,进行耐心解决和答疑;(4)安排专门人员与家长保持电话联系,对患儿的病情保持动态掌握和了解,并向家长给予及时的指导;(5)做好随访工作,追踪观察患儿的病情变化以及家长的心理状态变化。
1.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1.0进行数据的输入、整理、分析,统计学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t检验、卡方检验等,检验水准为P<0.05。
2 结果
2.1 ADHD患儿家长的焦虑、抑郁情绪状况 在最终完成研究的785名家长中,焦虑、抑郁情绪的检出情况为:(1)根据SAS评分结果,有220名家长存在焦虑情绪,焦虑情绪检出率为28.03%;(2)根据SDS评分结果,有165名家长存在抑郁情绪,抑郁情绪检出率为21.02%;(3)根据SAS和SDS评分结果(SAS和SDS中任一量表标准评分≥50分即纳入),有236名家长存在焦虑和(或)抑郁情绪,检出率为30.06%。
2.2 两组患儿干预后疗效比较 干预后,干预组患儿痊愈43例(36.44%),显效37例(31.36%),有效18例(15.25%),无效20例(16.95%);对照组患儿痊愈18例(15.25%),显效27例(22.88%),有效38例(32.21%),无效35例(29.66%)。干预组治疗有效率(83.05%)高于对照组(70.34%)(χ2=5.334,P=0.021)。
2.3 两组家长心理干预前后SAS、SDS评分比较 干预后,两组家长的SAS、SDS评分均较干预前降低(P<0.05),且干预组家长的SAS、SD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家长(P<0.05)。见表1。

表1 两组家长心理干预前后SAS、SDS评分比较
3 讨论
国内外研究显示,ADHD是一种内在因素(例如遗传等)和外在因素(例如家庭环境等)共同作用下出现的常见儿童期精神障碍,两类因素相互影响和作用,而家庭因素则对ADHD的起病、转归、康复、恶化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一般民众对于疾病的偏见,尤其是对相关疾病知识的认识不足和误解,容易导致家长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7~9]。本研究结果显示,ADHD患儿家长的焦虑症状检出率为28.03%,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1.02%,均处于较高的水平,提示ADHD家长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抑郁症状。分析其原因,可能是:(1)随着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要求越来越高,许多ADHD患儿病程长且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和学习成绩差等状况,学校常因患儿学习成绩差等原因给家长施加压力,从而使家长出现担心、自责,这些不良的心理状态更加容易使家长出现焦虑、抑郁情况;(2)许多ADHD患儿经常出现多动、冲动症状,打扰或干涉他人,甚至部分患儿还会出现破坏和违抗等行为,无法正常融入集体活动、与他人相处困难,为此经常会被带上“坏孩子”的称号,这些因素都有可能会使家长产生更多的心理压力,从而出现焦虑、抑郁等症状;(3)ADHD患儿使家庭生活方式和节奏都发生巨大变化,家庭经济支出的增加和经济负担的加重,以及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都会使家长承受更多的压力,从而造成患儿父母产生较多的诸如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另外有国内学者指出,许多患儿家长缺乏对疾病的了解和认识,当患儿出现多动和一系列异常行为时,往往不知所措,认为孩子这些行为与自己教育不当有关,产生自责、无助和罪恶感,并导致焦虑、抑郁的发生,甚至加重患儿的病情[10]。有文献指出[11],教养方式与儿童ADHD也有密切关系,当父母教育方法不对,如过分溺爱、粗暴、辱骂和家庭关系不和谐等都是影响患儿发生问题行为的因素。所以,针对ADHD患儿家长,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还是很有必要的。本研究结果显示,对ADHD患儿家长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既可以有效改善家长出现的焦虑、抑郁症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患儿治疗的疗效,这与国外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2]。分析其原因:(1)ADHD患儿家长所出现的焦虑、抑郁情绪,多是由于对ADHD疾病本身的不了解甚至是误解等而导致的,在这种误解的基础上,极容易出现家长对于孩子的现状烦恼以及未来预后的消极观点,尤其是家长对孩子目前异常行为的无能为力,而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不仅可以为家长有针对性地普及相关的专业知识,消除家长对于孩子目前异常行为的误解和排斥,而且病程、预后等专业知识可以使得家长对于疾病的可治疗性和良好预后有一定的认识,对于治疗重燃信心,更重要的是在干预者与家长的交流和反馈中,还可以帮助家长掌握很多解决现实问题且可行性高的教育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的焦虑、抑郁情绪;(2)当家长的不良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并掌握了一些正性的教育方法后,ADHD患儿在与家长日常相处时,不再接受之前的简单、粗暴的指责、批评方式,而是转换为一种更为和谐、平和、冷静的养育方式,这种转变不仅可以营造一种更为良好的家庭环境,也使患儿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不良心理刺激,这种较为宽松、和谐的家庭环境,有助于ADHD患儿配合相应的药物治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整体疗效;(3)ADHD患儿症状的有效缓解,可以让家长对于目前干预方案的认可程度进一步提高,更加提升其对于疾病良好预后的信心,依从性大大提高,促使其应用更佳的养育方式对待患儿,这不仅可以进一步消除家长可能出现的焦虑、抑郁症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患儿整体疗效的提高。所以,在对ADHD患儿进行必要药物治疗的同时,进一步关注家长的心理健康,并给予一定的心理干预措施,不仅有助于消除患儿家长的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还可以进一步提高ADHD患儿的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ADHD患儿家长存在一定的焦虑、抑郁症状,心理干预不仅可以有效改善家长的焦虑、抑郁症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患儿的疗效。对此应引起医务人员的高度重视,给予ADHD患儿及家长更多的关心和帮助,重视患儿的成长和治疗,使其与其他儿童一样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