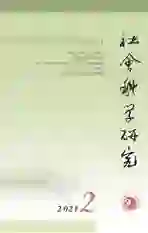连续与断裂
2021-06-06焦洋
〔摘要〕 20世纪80年代末,河北南部邯郸市武安县固义村举行的“捉黄鬼”活动引起了当地民俗学者的注意,华北这个普通乡村内的民间宗教活动得以展现在大众视野中。随后,固义村元宵节期间举行的“捉黄鬼”活动被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中,成为“北方现存的最古老傩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固义村民口中,村内举行的“捉黄鬼”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实际上,此项活动并未有任何档案资料的记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曾因政治运动一度被中止,直至80年代末期方才恢复,这背后反映出的变化值得深思。考察固义村元宵节期间“捉黄鬼”活动所展现的延续性与断裂性,可以看出清末到当代中国华北一个普通乡村内宗教活动的变迁,及其所反映的民间宗教活动与权力变迁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捉黄鬼”;华北乡村;傩戏;黄河文化;乡土社会
〔中图分类号〕K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2-0194-10
〔作者简介〕焦洋,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候选人,澳门 999078。
2008年2月23日,《燕赵都市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武安固义村的傩戏〈捉黄鬼〉》的文章,报道了位于河北南部的一个小村子——固义村在正月十五期间村民自发举行的“捉黄鬼”活动。文章写道,正月十五临近天亮之时,大鬼、二鬼与跳鬼“在手持柳棍的村民簇拥下开始在村里村外踏边”,寻找在村内作祟的黄鬼,负责将“黄鬼”捉住并游街,最后将其驱赶至村边的空地上接受“阎王”的审判。①在接受审判之前,活动中负责沟通不同界域的“掌竹”开始念词,细数“黄鬼”犯下的罪行,最终,“黄鬼”被“阎王”判以剥皮抽肠的极刑。“黄鬼”被处刑之后,固义村村民们开始举行各类节庆活动,如旱船、秧歌、打拳等,庆祝新一年的到来。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最后写到,固义村举行的“捉黄鬼”活动“虽然是一出沿街演出的哑剧”“一段民俗表演”,但其“最早出现在夏商时期,距今已有3000年历史。……是古老的黄河文化的重要遗存”。②然而实际上,即便是参与活动的村民也不能肯定“捉黄鬼”活动出现的时间,只能含糊地表示家中长辈还在世时,村里便一直举行这个活动,但又回忆,在20世纪50到60年代,村中的“捉黄鬼”活动一度被中止过,直至80年代后期,这项活动才恢复,至于被恢复的契机为何,村民并不知晓。③在当今的固义,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捉黄鬼”活动已不再具有最初的宗教性意味——驱逐邪恶,祈求丰收与平安,看起来更像是一场为吸引观光者而进行的民俗表演活动。同时,对于参与其中的固义村村民来说,与其说是仪式的参与者,不如说是活动的表演者更为恰当。④那么,这项作为古老黄河文化遗存的“捉黄鬼”活动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其中是否有过变化?在这些变化背后,又蕴藏了哪些被我们所忽视的事实?
关于武安固义“捉黄鬼”活动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研究侧重于分析“捉黄鬼”活动的性质,反映了彼时民俗学者对于此项活动的关注重点。作为“捉黄鬼”活动的首位研究者,杜学德在文章与论著中对此进行了描述、分析⑤,但没有考证“捉黄鬼”活动的历史背景,也没有借此来探讨华北地区乡村社会的变迁问题。历史学者欧大年在研究河北乡村仪式时提及固义村的“捉黄鬼”活动,然而其研究内容大部分与杜学德相类似。⑥赵世瑜认为明清时期,在华北地区,作为服务于“社”并将社区内家家户户包括进去的诸如“捉黄鬼”等信仰活动,对于地方社会具有一定的整合与凝聚作用。赵世瑜并对“捉黄鬼”这一活动背后蕴含的功能进行了分析,使隐藏在此之下华北乡村社会更深层次的结构面貌得以展现出来。⑦但是,赵世瑜没有分析清朝之后此项活动的发展变化,也没有看到“捉黄鬼”这项活动在新时代中所展现的特征,以及在这个时间段内出现的延续性与断裂性。海外学者杨庆堃认为中国社会的宗教基本可被划归为“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与非制度性的“弥漫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活跃在中国乡村内的民间宗教活动属于缺乏系统组织机构与经过专业训练的神职人员的“弥漫性宗教”。此类宗教活动通常与人们的世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并散落在世俗制度与社会秩序的方方面面,从而使其得以在急速变动的中国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的稳定性。⑧杜赞奇则从“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al nexus of power)的角度分析华北乡村地区的民间信仰与宗教活动,认为此类民间信仰活动同水利组织、宗族等文化符号与国家权力共同维持着华北乡村社会的运行。⑨杨庆堃与杜赞奇的研究均没有脱离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的框架,强调了权力和象征在复杂的文化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⑩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文将关注时间点置于清末至当代中国(20世纪初至八九十年代),通过分析晚清至当代中国华北乡村社会中一个普通民间宗教活动的发展与变化,试图回答下列问题:第一,固义村所举行的民间宗教活动“捉黄鬼”为何不见于地方志记载之中;第二,“捉黄鬼”这一活动出现了哪些变化,其所能反映出来的延续性与断裂性为何。由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人口流动率小,社区间往来少,转变缓慢,相对孤立的地方性熟人社会,故而人们多将关注的目光集中于变化剧烈的城市地区。B11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才是中国社会文化构成的基石。尽管自清末到民初,由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化缓慢,我们很难识别出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所发生的改变,但中国的乡村社会确实经历着一定程度的改变,诸如具有现代意义的初等学校在农村社会出现,这些变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士绅所扮演的角色。B12而当1949年10月一個崭新的政权建立起来之后,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诸如权力结构重塑等更为剧烈、迅速的改变。尽管固义村“捉黄鬼”这一民间宗教活动的档案资料缺乏,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地方志与社会调查的资料中,来找寻此类民间宗教活动存在与传承的动机,以及通过此类宗教活动乡土社会与权力阶层间的博弈,同隐藏在这些活动背后华北乡村社会的变迁。
一、 一个普通村庄的宗教活动——“捉黄鬼”
固义村的“捉黄鬼”活动通常于农历正月十五举行,每隔三年举行一次。因活动中的戏本最早写于清朝末年,故村民将此活动上溯至清末。在活动正式举行之前一年,村内四个社(南王户、东王户、刘庄户、西大社)派出成员组成委员会(通常是活动中的重要扮演者)筹措经费,并安排活动的具体执行情况。之后,在农历十二月初,委员会成员到村南的庙内将活动的主神——“白眉三郎”——请到村内的仙殿之中,进行祭拜。正月十四日下午,活动的所有参与者装扮起来,绕行整个村庄一周,谓“亮脑子”(目的为确保第二天活动顺利进行)。正月十五日凌晨,“大鬼”与“二鬼”扮演者分别从村内的仙殿出发,跨越火盆,手持柳棍,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围绕村庄走一遍,谓“踏边”。其后,两个探马按照相同的方向和顺序到村周围的其他庙内将龙王、老奶等神明雕像共请至村内神庙中,分列于白眉三郎之旁,称为“迎神”。请神事毕之后,活动中各类节目参与者在村内街道依次摆开,谓“摆道子”。之后,在天色朦胧时分,“大鬼”“二鬼”“跳鬼”与“黄鬼”分别进入街道中间,开始做勾引“黄鬼”的表演。“大鬼”在前,“二鬼”在后,“黄鬼”处于中间畏缩不前,“跳鬼”则前后跳动驱赶“黄鬼”。期间,如有村民家内有病人,或意欲驱逐屋内灾邪,可将“黄鬼”请入自家中,再由“大鬼”“二鬼”与“跳鬼”将“黄鬼”驱逐出去,意为家中灾疫已除。如此,进进退退,往返三遍至午时,“大鬼”“二鬼”“跳鬼”将“黄鬼”驱赶到村南空地搭建的审判台前。在审判台上,由掌竹唱念词,阎王对“黄鬼”进行审判,最终“黄鬼”被处以剥皮抽肠之刑。刑罚之后,村民开始表演各类庆祝节目,如花车、武术、旱船等。到正月十六日,此次活动的社首带领委员会成员先到村南举行祭祀虫蝻的仪式,而后至村北进行祭祀冰雨的仪式。与此同时,在村内,村民们继续进行节目表演与赛戏活动。正月十七日晨,社首带领委员到村外南边的奶奶庙进行完表仪式,更换下届活动社首,并将此次活动的收支结余转交至下届社首,活动中角色的扮演者到社首家里祝贺——谓“过厨”。至此,固义村元宵节“捉黄鬼”活动结束。
虽然固义村村民称“捉黄鬼”活动历史悠久,但是地方志中对于此项活动却没有确切的记载。在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中,想要传达世代累积的生活经验,以及相关的生活活动,文字并不是必需的媒介,民间歌谣、宗教活动等都可以用来传情达意。B13即便到了今天,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不需要文字记载的传统习惯依然具有十分强大的效力。对于这些传统,“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便成了人们生活中所谓的“仪式”。B14这些仪式,一些被记录了下来,上升为区域范围乃至国家祭典,如邯郸圣井岗铁牌祈雨仪式等,更多的是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的传统社区内代际间传承,没有文字记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文字并不是从基层上发生的”,“最早的文字是庙堂性的”,因此,文字记录并不能成为某项活动是否存在的唯一证据,尤其是在缺乏文字基础的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B15在分析“捉黄鬼”等社区活动时,我们必须将视线转至活动本身,从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去勾勒其轮廓,从其所体现的延续性与断裂性来探索其本身的真实性。B16
如果要考察固义村“捉黄鬼”活动的源起及发展历史,首先要了解历史上的固义村。固义村现坐落于河北省南部邯郸市三十公里以南的冶陶镇武安县。明清时期,武安县属彰德府,民国时期,政府废置府、道等行政单位,以区划分县,武安县被分为四区,固义村属于第四区,为河南省一部分。B1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50年代,武安县被划入河北省邯郸市。
武安县自明至民国时期,共修有方志四次,清朝时,固义村第一次出现在《武安县志》之中。彼时,固义村名为“顾义”,属顾义里,除此之外,并没有关于固义村更多的描述。B18至民国时期,《武安县志》中才开始出现关于固义村的文献描述资料。据记载,彼时固义村位于猛虎河与南洺河之间,紧邻通往武安县城的大路。村内共有250户家庭,1084名村民,村民大部分为王、马、丁、李四姓,村内有36公顷农业耕地。大部分村民从事农业生产,但由于村庄紧邻通往县城的道路(武邯马路),村内也开有若干小型旅店,供过往旅客使用。1930年代末,村内有一所初等学校,共有56名学生。B19尽管成书于民国时期的《武安县志》已经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固义村,其所提供的信息仍然十分有限,关于“捉黄鬼”这项活动更是没有任何记载。那么,为何有着“悠久”历史的“捉黄鬼”仪式却不见于《武安县志》之中?
一方面,从“捉黄鬼”活动举行的范围上看,由于没有出现联庄的现象,因此可以将其定义为社区内的宗教信仰活动。社区内宗教活动的产生与发展,与彼时的自然、社会环境及村庄形态等密不可分。从外观上看,直至今日,固义村四周仍然以高高的围墙圈起,东南西北围墙上各有一阁楼,下面开有洞门,至夜间洞门关闭后,整个村子宛如一座堡垒,保护村内居民不受盗匪、军队等外部势力袭扰。19世纪晚期以来,在频繁的地方起义与军阀战乱的影响下,生活在华北地区的农民们构筑起泥土堡垒以储存粮食,躲避战乱。B20当入侵者进逼时,无物可抢、无所驻足、无人可掳,同时,堡垒四角塔楼可内置枪手,使其难以入侵。B21在这种不稳定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华北地区的村社一直处于相对孤立与封闭的状态中。这种状态一方面可以保证村社的安全与稳定,另一方面使得这种地缘组织需要一种集体性活动来达到凝聚社区的目的。B22这种活动通常带有宗教色彩,旨在教化社区成员,增加对参加成员的震慑力,避免成员间的分裂。同时,也正是由于晚清时期华北乡村社会相对封闭的状态,此项活动在村社范围内被代际传承着,用以维持社区的秩序与稳定。
另一方面,县志的修纂通常由当地官绅发起,用以记录地区的历史、现状,有着一定的范式和体例。从现存的县志来看,绝大部分地方志修纂于明清时期。明永乐之后,官方开始发布修志命令,并附修志条例,要求地方官遵行;至清康熙年间,更是要求各省、府、州、县勤修方志。B23但方志的修纂由于体例、范式甚至经费等原因,在内容上受到一定限制,只能记录对当地影响较大的事件与活动。同时,所载之事亦是经过地方官选择的,而类似固义村“捉黄鬼”的活动,由于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往往不能登官修地方志的“大雅之堂”。到了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在農村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破除迷信的运动,这些扎根于乡村社会内部的民间宗教活动更是在官修地方志中消失了“踪影”。然而在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中,习俗惯性根深蒂固,固义村元宵节期间所举办的“捉黄鬼”活动虽然没有官方文字的记载,但是对比其在志书中的“消失”,与其在固义村内的存在、发展、一度中断以及恢复,本身就是20世纪初以来华北乡村社会变迁一个很好的说明。
二、“消失”的仪式——固义村与“捉黄鬼”活动
虽然固义村的“捉黄鬼”活动并未见于《武安县志》之中,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其在历史上的存在。B24官修方志中,记录了历史上武安县形形色色的庙宇与宗教活动。成书于1622年的《武安县志》,记载在明天启年间,武安县共有69座大型庙宇,到了清乾隆时期,武安县内庙宇的数量几乎增长了一倍,至102座。B25这些庙宇不仅规模恢宏,还经常性地进行翻修。如县内建于明洪武年间的城隍庙,仅明朝便翻修了6次,至清顺治时期,又重新修整了3次。B26除了对县内的大型庙宇进行记载与描述外,方志也记载了武安县许多小型庙宇、神坛等,以及县内每年举办的各种各样信仰祭祀活动。例如,每年上元节时,县内都会举办包含各种表演项目和娱神项目的赛会,供人们祈祷、祭拜、游玩。B27故而,志书记载武安旧俗“尚鬼,多淫祀”,南乡祭拜白马天神、马奶奶神,四乡多祭祀张爷等神祇,这些民间神祇“名目繁多,不可殚记”。B28同时,“工商各业皆有专祀”,且“典礼隆重”。B29由此可见明清时期武安县民间宗教信仰之兴盛。
而武安县彼时所面临的自然环境则直接影响着种类繁多的宗教庙宇与信仰的出现。通常来说,过去的官方资料,诸如地方志等,会对当时当地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型灾害进行记录。比如,修于民国时期的《武安县志》记录了彼时发生于武安县的几次特大旱涝灾害。这些灾害不仅毁坏了大量农田,更是使得整个县几乎颗粒无收。在此种状况下,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卖儿鬻女,换取粮食。特别是民国九年(1920年),武安县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旱灾与蝗灾,农民只能依靠政府组织的救济机构提供的粮食存活下去,许多农民丧生于此次自然灾害之中。B30除了这些记录于官方资料中的大型自然灾害,对于武安县的居民来说,他们每年都会面临一些小型自然灾害的侵害,这些灾害使得本就处于温饱线边缘的华北乡村社会频繁遭受饥荒之苦。B31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朝至民国时期《武安县志》所记载的自然灾害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是蝗灾。相较于其他自然灾害,蝗灾之所以引起农民的极度恐慌,除了它们难以实施人为控制外,还由于其能在短时间内毁坏所有农田的收成。B32基于蝗灾对农业生产带来的灾难性损害,帝国政府通常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来祭祀虫蝻之神,如祭祀虫神刘猛等。B33除了官方修建的虫蝻庙外,地方村社也会组织力量修盖庙宇与祭坛来祭祀虫蝻之神。在固义村的“捉黄鬼”活动中,便有祭祀虫蝻神的行为,“黄鬼”所代表的象征意义之一便是蝗旱灾害。在此种自然环境的影响下,即便志书中未曾记载,固义村内产生驱逐灾疫、祈求平安与丰收的“捉黄鬼”活动也不足为奇。
此外,在传统中国社会,由于交通与信息的不发达性同行政体系的制约,中央政府不能有效掌握地方社会的动态。明清时期,地方上最低一级的行政单位是县,而县所辖的不同村庄则以里甲的形式组织起来。尽管从表面上看,地方社会看似是在统一皇权的控制之下,但实际上由于官吏调任制度与选官制度的限制,地方社会实际上是在胥吏差役、乡村士绅与宗教领袖的控制之下。到了清朝,由于人口的增加迅速(四百年内增加近九千万人口),更是限制了中央皇权对村庄的有效控制。B34这样看来,虽然从表面来说,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受到源于横暴权力皇权的统治,但是这样一个政权不得不受到来自农业帝国的经济约束以维持自身的统治。故而,从人们的实际生活上看,这种皇权统治是松弛并且微弱的,甚至可以说是挂名的。B35在山高皇帝远的情形之下,乡土居民通常将切身的公事让渡于从社会合作的角度衍生出的同意权力,以及基于社会继替过程中得出的教化权力来决定。B36
一个十分实际的例子是离武安县不远的定县。清朝之时,定县的县衙人员组成包括了一名知县、一名典史、一名巡检、一名县丞以及若干吏目,这些少数的地方行政人员需要负责管理县内近两万人口。B37换句话说,就实际情况来说,定县的知县只能控制县城内出现的一些重大事件与活动,至于散布在县内其他遥远地区的村庄,根本无暇顾及。与此同时,从1901年至1928年,定县的知县(县长)频繁更换,28年之中更换了25位。B38这从侧面说明了,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许多普通村庄是依靠其自身的权力结构在进行日常的运作,其中便包括了宗教领袖及其所组织的各种民间宗教信仰活动。有趣的是,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皇权统治的明清时期,国民政府统治下的现代时期也依然如此。
与定县类似,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武安县内。民国时期,武安县内共有45名警察负责维护县内的公共秩序,而整个武安县的面积却超过了2000公顷。B39换言之,这45位警察需要负责维持散布在县内的所有村庄的秩序,而就《武安县志》的记载来看,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恢复并改进了里甲制,但从实际实施的情况来看,由于彼时频繁的战乱与地方冲突,除了在其有效统治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通过此种改革有效地控制中国范围内的每个地方,更不用说散落在各个角落的村庄。B40可以说,从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自有一套运行法则,民间宗教信仰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事实上,直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中国的乡村社会中,民间宗教信仰及活动一直发挥着重要影响。B41这从国民政府在废除乡村社会中的封建活动时所遭遇的巨大阻力中可以看出。1928年,为了限制民间宗教活动之于地方社会的影响,武安县政府拆除了一部分庙宇,禁止了一部分民间宗教活动的举行,但是在村庄内,各种小的庙宇、神坛依旧存在,各种宗教活动依旧活跃。最终,在县内民众的抵制下,县政府不得不恢复了一部分庙宇与民间宗教活动。B42故而,尽管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县志未曾提及固义村举行的“捉黄鬼”活动,但至少在20世纪早期,政治环境便已经为河北乡村居民组织宗教活动创造了条件。B43
与此同时,对于固义村来说,通过类似“捉黄鬼”的宗教活动,其内部得以产生内在的联系与互动而成为一个时而松散时而紧密的有机体,使村社内的权力组织得以运行。B44与南方发达的宗族村落不同,华北平原上大部分是由多姓组成的村落,除少数单姓村落外,有时即使村内有一定规模的宗族组织,也不能如同南方尤其是华南地区的宗族组织那样在鄉土社会发挥管理与控制职能。B45曾任清朝刑部江南司郎中,后升任广东惠州府知府的直隶武强县人张渠,在《粤东闻见录》一书中称,“吾乡乃邦畿之地,以卿大夫而有宗祠者尚寥寥无几,其尊祖睦族之道反不如瘴海蛮乡,是可慨也”。由此可见,在华北平原上的乡村社会中,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占统治地位的并不普遍。B46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的,在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意义上的差序,即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B47这种年长对年幼的强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组织内部的团结与稳定。相对地,在华北地区的传统乡土社会中,血缘组织并不占优势,地缘单位也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故需要一种集体性的活动来巩固社区凝聚力,由此诞生了各种民间宗教活动来限制地缘社区内成员间因生产、生活而起的冲突与竞争,并以此为一种权力方式来保证地缘村落得以运行。这些民间宗教活动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不仅具有巫术支持实际农作活动的作用,而且社区的成员们对于这些宗教活动往往带有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行的信念,从而使村社内部得到凝聚,如固义村村民们认为“不参加祭祀演出,在新的一年里本人和家庭都不吉利,不顺畅,甚至还会出事”。B48综上可以看出,固义村元宵节期间举行的“捉黄鬼”活动“消失”于明朝到民国时期《武安县志》之中,可能是由于此种民间宗教活动多“附会流俗”,故而“祀典不载”。B49但县志中记载的各种各样的宗教庙宇与形形色色的宗教活动,却从侧面说明了彼时民间宗教信仰及其活动在武安县居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无论是从外部的自然与政治环境,还是村社内部的权力作用角度来看,类似“捉黄鬼”的民间宗教活动在华北的乡土社会中自有其活跃的土壤,我们无法仅因其缺乏文献资料记载便否认这一活动在固义村代际传承的可能性。
三、 “存在”过的仪式——“捉黄鬼”的延续性与断裂性
尽管从明朝到民国时期的《武安县志》并没有关于固义村“捉黄鬼”活动的相关记载,但是从“捉黄鬼”这一活动本身所展现出的延续性与断裂性来看,我们可以确认此项活动确如固义村村民所说,其在村内有着一定代际传承的历史。由于“捉黄鬼”活动的核心在于对“黄鬼”的驱逐与审判,因此弄清“黄鬼”这一角色在活动中所代表的象征含义,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活动的延续性与断裂性。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建立在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之上,即这一事物或者行为会在大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B50若要多数人认同同一象征具有同一的意义,则要求他们必须处在相似的环境中,有着相同的经历。B51在固义村“捉黄鬼”活动中,“黄鬼”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象征含义,其一是诸如蝗灾、旱灾等自然灾害的代表,另一种含义则是代表了不孝顺父母的子女。B52“黄鬼”的第一种象征含义,展现了此项宗教活动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所具有的对于农业生产的支持作用,同时也蕴藉了这一活动举行的初衷与最主要目的:驱除灾疫、祈求神明保佑村内来年丰收与平安。“黄鬼”所代表的另一种含义——不孝之人,则表现了这一活动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教化权力影响所发生的转变。
首先来看“黄鬼”的第一层象征含义——蝗旱等自然灾害。此种象征意义的出现与华北地区的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研究表示,从晚明开始,直至清初,北半球的气候相比更寒冷一些。B53彼时,台风频繁袭击中国南部的广东地区,中国的北方地区则出现了大规模的干旱。B54在此种极端天气的影响下,蝗灾与饥荒相继出现在华北地区,使得绝大多数生活在华北平原的农民一直徘徊在最低温饱线边缘。仅在明嘉靖一朝,华北地区便出现了29次大规模的自然灾害。B55根据修于明清时期的《武安县志》“灾祥志”,同一时段武安县也遭受到数次大规模的蝗灾与旱涝灾害的袭击。B56
毫无疑问,处于武安县南部的固义村也遭受到自然灾害的袭击。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在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当灾害来临时,人们通常会祈求神明庇佑来度过这一艰难时期,这也是巫术在支持农业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因此,在“捉黄鬼”活动中,“黄鬼”——象征着旱灾与蝗灾等自然灾害——最终被“大鬼”“二鬼”和“跳鬼”捉住,并被送至阎王,处以剥皮抽肠之刑,象征了厄运与灾害最终被神明从固义村驱逐,村民们的生活得以平安。今天,虽然巫术对农业生产的支持作用已无复当初,但在“捉黄鬼”活动中我们依然可以找到此种象征寓意,如驱逐“黄鬼”依然是为了来年土地有个好收成,即便粮产已不是固义村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活动中“黄鬼”可被要求进入需要驱逐疫病的村民家中,而当其从村民家中被驱逐出去则代表了厄运和疫病从此户人家中被驱逐,因此,“黄鬼”这层象征寓意可体现“捉黄鬼”这一活动的延续性。
此外,在“捉黄鬼”活动中,“阎王”“掌竹”等主要角色的扮演者为家庭所继承,活动中所用的道具、面具等也是从长辈手中传承下来的(虽然在1987年被恢复以后,部分面具遭到了严重的损毁),此种继承关系也可被视为此项活动所具有的代际延续性。B57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活动中象征着灾害与厄运的“黄鬼”的扮演者,总是由乞丐或者外村人来担任,而非由固义村村民出演,以前在演出结束后付给扮演者一些干粮,现在是直接付与扮演者一些补助费,这也是此项活动延续性一个十分有趣的证明。
更为重要的是,从过去到现在,固义村“捉黄鬼”这一活动的举行均与经济活动的影响密不可分。元末,由于战争的影响,中国北方地区人口骤减,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明初,新建的皇权政府开始人为地迁徙民众到饱受战乱影响的地区垦荒,这些移民不仅带来了家族成员,还带来了习俗与他们崇拜的神灵。B58固义村村民称其祖先就是明朝时从山西洪洞县迁徙而来。到了清朝,康熙、雍正皇帝相继颁布赋税政策,华北地区的人口呈急剧增长态势,故而同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华南地区的宗族村落相比,在华北乡土社会中,多姓村落与分散的小农经济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B59因此,民间宗教活动出现在北方乡土社会之中,用于巩固群体内的凝聚力。B60而在华北地区的传统乡土社会中,农业生产频繁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人们为了祈求粮产的丰收不得不借助神明庇佑,因此在“捉黄鬼”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黄鬼”所代表的最初象征含义背后的经济因素的驱动。此外,华北平原的冬季,由于干旱、少雨,农作物的生长受到限制,人们通常在此时不事生产。志书曾载,武安居民多“勤劳业务”,终年在田间劳作,“无敢休息”,“惟至旧历正月,新年甫过,农事未兴”,居民“无所事事”,因而“多寻娱乐”,“歌舞酬神”,其中多有“高跷、竹马、彩船、武术、秧歌”等,“皆农民自相扮演,且行且歌”,虽花费财资甚巨,“亦所不计”。B61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在农闲之时,武安县居民才会举行酬神娱乐之赛会,与固义村“捉黄鬼”活动举行的时间相一致。综上可以看出,與经济因素相联系是“捉黄鬼”这项活动最初出现的动力,也是此项活动得以延续下去的缘由。
到了当代中国,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影响下,乡土社会的权力组织屡次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土改前基层保甲长,转向由选举产生的政治觉悟与积极性较高的贫苦村民,再转向改革开放后可以带领农民走向市场经济的村民,而后转向当代村内相对有经济基础的村民。在此种剧烈变迁的影响下,尽管固义村的“捉黄鬼”活动中断过一段时间,但重新恢复后,其举行的驱动力——与当代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活动相联系——并没有改变,只是以回到过去的形式与当下社会环境相联系,建立起这项活动的合法性。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市场经济进入中国社会,并逐渐成为人们行为的风向标。同时,受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兴起的民俗学主义的影响,90年代,中国学者同地方政府开始共同挖掘乡村社会中残存的习俗文化,赋予其新的民俗学面貌,来扩大当地文化与经济的影响力。B62由此,地方上兴起了种种民俗活动,吸引游客,拉动当地经济,经济因素对此类活动的驱动不可小觑。此外,尽管到了当代,农业生产活动已不再是固义村村民的唯一生活来源,但对于自然的敬畏以及希冀粮产丰收的传统依然存在,故而经济因素的驱动一直在延续着。而这种与经济活动的紧密联系既可以看作是一种延续性——希冀粮食生产丰收,也可以看作是新时代出现的一种断裂——通过学者的直接参与、民俗知识的普及,活动发生了变异。
与“黄鬼”所代表的最初含义相比,另一层象征寓意:不孝子女,则可被视为“捉黄鬼”活动的一种断裂。如上所述,明清时期,高高在上又相对遥远的统治阶层既希望通过宗教活动对基层的乡土社会,尤其是相对偏远的乡土村落加以控制,同时又忌惮非正统宗教信仰及其活动的发展对其统治产生不利的影响,故而统治阶层需要通过不断灌输正统儒家观念的“德”,即使用教化的权力,来强调其统治的正统性,并约束在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们的行为。但是这种来自中央政权所提倡的作用于个人身上的“德”的权力,与民间宗教信仰中希冀借此度过危机的“灵”的权力并不一致,有时甚至相互违背,这从民间宗教信仰并不为地方士绅所提倡这一点便可看出。B63活动中“黄鬼”所代表的这一层寓意与其最初的寓意——蝗旱等灾害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更多强调的是传统社会中村民应该遵守的秩序,以及需要培养的德性。B64
盡管修于民国时期的《武安县志》记载固义村靠近通往县城的道路,但是在1921年武邯马路修筑成功之前,其仍然是一个相对偏远、封闭的传统村庄。不仅固义村的位置相对偏远,整个武安县在明清时期均属于“偏远之区”,其“居乱山之中,冈陵坡陀,道途险隘”,县内“俗陋民愚”,因而多“迷信神权”。B65同时,方志记载直至民国时期,固义村仍有百分之九十的村民以农业生产为生。对于这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的普通村民来说,通过宗教活动中的戏曲表演,如《杨家将》宣扬忠君的戏目,可以培养其对于权力的敬畏之感,以达到社区稳定的目的。B66因此,在固义村“捉黄鬼”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长坂坡》等表达忠义思想的戏文,也可以看到“黄鬼”所代表的另一层象征寓意——不肖子孙——所展现出来的建筑在教化权力基础上的儒家思想。这种对于“德”与“孝”的强调,意为“无违”,即承认年长者的权力,可被视为维持乡土社会稳定的一种手段。B67然而对于固义村的“捉黄鬼”活动来说,这种教化权力附加的另一层象征寓意,使得活动最初祛除灾疫、祈求丰收顺遂的目的产生了名实之间的分离,展现了其中的断裂性。B68而这种断裂性在随后的社会变迁中产生了进一步的分离。
在民国时期,尽管没有直接的文字资料证明,但是从彼时武安县宗教场所与宗教活动所出现的一系列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民主与科学观念开始渗入地方乡村社会,对“捉黄鬼”活动产生了影响。B69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是在河北定县。彼时,定县县长孙绪发开始着手清除县内的封建迷信活动,并将一些宗教庙宇改为行政办公地点或者初等学校。到了1928年,定县的庙宇由原来的435座减少到104座,这种变化显示出新的行政力量之于传统乡土社会的影响。B70与之相类似,成书于1940年代的《武安县志》也对国民政府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造活动进行了记录。县志载,早在20世纪初,接受了西方现代化知识教育的官员便开始将武安县的庙宇改为警察署与初等学校。如民国初年,武安县政府将县内的关帝庙改成初等小学,妙觉寺改为女子小学,东岳庙改为初等中学,此外,还将火神庙改建成警察署。B71同时,县政府停止举行一些宗教活动,如农历春节时禁止举行赛会,祭祀城隍等宗教活动亦被取消。B72虽然我们无法确切得知“捉黄鬼”受到的影响,但是亦无法否认在如此社会环境之下,这项活动没有产生一定的名实分离。1937至1945年,日本对于中国北方的占领与控制,同样削弱了地方社区的传统。一些村庄内寺庙只在1937至1938年间举行过节日庆典,同时,日军常将庙宇改造成军营,导致宗教场所的毁坏与宗教活动的中止。B731945年爆发的国共内战,使得原本凋敝的村社,继续被破坏。
到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新政权开展的政治与思想运动的影响下,固义村的“捉黄鬼”活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50年代,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开展了从上而下的思想和组织运动,不仅改变了原有的乡土社会结构,如设立村民委员会,改变了原来的乡村权力结构等;同时,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共产主义思想观也随之渗入乡土社会中。在这些运动的影响下,传统乡村社会中存在的“封建”思想观念需要被破除,还要树立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唯物主义世界观B74,存在于乡土社会中的民间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首当其冲。此种风气在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达到顶峰。尽管一些处于偏远地区的乡村社会依然存有诸如算命、端午节赛龙舟等活动,但总体来说,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活动在这个时期均被彻底中止。B75据固义村村民回忆,村内的庙宇在此时期遭到了毁坏,而“捉黄鬼”活动也在这个时期被中止。B76
这种时间上的断裂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过时”的“捉黄鬼”活动虽然得以恢复,却产生了新的变化。当活动被恢复之时,虽然面具、服饰等道具保存了下来,但是已经严重损毁,村民们不得不根据老年人的回忆重新制作了一套新的面具。B77其后,在当地民俗学者的帮助下,此项活动不仅被宣之于文章,成为北方知名的民俗活动,更是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此时的固义村“捉黄鬼”活动不仅改变了其举办时间,由三年一次改为不定期举行,在新任县领导到任时,村民们还会应要求举行;同时,活动的一些组织者已经搬到城市生活,只有在举行活动时才会回到村内,对他们来说,“捉黄鬼”不再是为了生产、生活,而是变成了表演。更为重要的是,活动的主要目的也发生了改变,从驱逐灾疫、祈求丰收到表演仪式以吸引民俗爱好者,“捉黄鬼”从“封建迷信活动”摇身一变为“民俗文化”,成为当地政府和村民的一种文化资本。“捉黄鬼”活动的断裂性反映出来的是乡土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改变——中央政权通过政治、经济与思想三个方面得以将其权力触角彻底深入乡土社会之中。B78综上可以看出,在当代,“捉黄鬼”活动看似与过去有着一定的继承性,但实际上,原来的传统已经不能有效地满足人们的生活,这种名实之间的分离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增加。
四、 小结
固义村首次出现在地方志中是在清乾隆年间。彼时,固义村写作“顾义”,行政区划上属顾义里。B79同时,方志载顾义里过去被称为“在洛”,下面囊括了牛围头、张家庄与顾义等村。尽管清朝所修的《武安县志》没有对顾义进行详细的描述,但是记录了彼时武安县没有充裕的水井,村民们不得不从其他地方挑水进行农业灌溉一事,从侧面说明了武安县干旱、无常的自然环境。B80在此种自然环境的影响下,宗教活动在农业生产中所起的支持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到了民国时期,《武安县志》对固义村有了更为详尽的记载,不仅记录了固义村的人口数量、土地以及交通等情况,更是对村内村民的基本生活情况进行了记录。虽然此时方志中对于固义村的描述丰富了起来,但是我们依然没有找到关于“捉黄鬼”这一宗教活动的相关信息。
尽管固义村的“捉黄鬼”活动“消失”于方志中,但是志书却记录下彼时武安的风俗,“春秋而降,淫祀渐兴,巫觋迭起”,虽历代名贤“立辟谬妄,卒不能禁”,甚至乡间士绅大夫亦为之所惑。B81此外,书中亦载武地居民常祀各路神祇,乡间有“关帝、龙神、药王、文昌、土地等”,其“名目繁多,不可殚记”,但因这些民间神祇大多“附会流俗”,故志书“祀典不载”。B82由此可见,彼时武安风俗“尚鬼”,不仅县城“每年清明、七月十五、十月朔”等有神明出巡,城乡士民皆“提灯送迎”,乡间也会祭祀各种神祇,如白马天神、马奶奶等,乡民家中更是祭有“家堂、天地、灶王、钟魁(馗)、门神、马王等”。B83故而,固义村的“捉黄鬼”活动未见于志书中,大抵因其在传统帝国时期被视为“淫祀”,同时因其与志书内容体例不甚相符。但在彼時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我们并不能就此否认此种民间宗教活动的存在。
固义村的“捉黄鬼”活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政治运动一度被中止。到了80年代末期,随着此项活动被当地民俗学者发掘,引来了全国的关注。其后,此项活动更是被称为“北方最古老的傩戏”而闻名遐迩。虽然志书中未曾记载固义村的“捉黄鬼”活动,但其活动本身所展现出的延续性与断裂性,便是“捉黄鬼”活动在固义村一直被代际传承的证明。从当代举行的“捉黄鬼”活动来看,其延续性表现在活动本身、参与活动的人、活动的目的等方面的延续。但同时,这一活动又有着显著的断裂性,表现在当代活动举行的时间、活动参与者的生活轨迹,以及活动作用的变化上。这些变化使“捉黄鬼”本身的功能也随之发生改变——由去除灾疫、祈求丰收平安的信仰活动转变为当代民俗爱好者的经济文化行为。同时,活动中的一些“迷信”行为被去除,活动更加符合当代政权对民俗活动的规范。从固义村“捉黄鬼”活动的延续性与断裂性我们不仅可以看出随着乡土社会的改变,信仰活动所发生的变化,同时可以从中看出民间宗教活动与权力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
从晚清到民国,通过影响民间宗教信仰活动,建立在横暴权力基础上的中央政权一直试图深入由教化权力和同意权力共同作用下的乡土社会,但真正实现这一目的的却是在剧烈社会变迁中所出现的时势权力——中共政权所建立的政府,这种时势权力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直接将触角深入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之中。B84而对于在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来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总是能通过民间宗教活动及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与中央权力进行协商。在当代中国,尽管固义村的“捉黄鬼”活动被民俗学者以新的形式进行了重新定义,并赋予了新的身份——民俗文化,但对于固义村村民来说,他们依旧可以通过这种“被发明的传统”来获得关注与利益,同时,亦可通过此种活动来与当地政府进行另一种形式的互动。由此可见,无论是在传统帝国时期还是近现代民主政权时期,固义村的“捉黄鬼”活动都不可同国家权力、社会环境割裂开,即便此类宗教活动在官方资料中“时隐时现”。这种在社会变迁中被保存下来的民间宗教活动,作为一种文化手段或方式使乡土社会从过去到现在得以游离、周旋于统治者的文化权力之外,并通过其延续性与断裂性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① ② 《武安固义村的傩戏〈捉黄鬼〉》,《燕赵都市报》2008年2月23日,http://news.sina.com.cn/o/2008-02-23/025813459772s.shtml,2020年3月5日。
③ 根据作者2015年12月25日于固义村对活动中“阎王”扮演者李姓村民的采访。采访时,李姓村民已过不惑之年,据其回忆,其祖辈父辈一直是活动中“阎王”的扮演者,在活动恢复后,此角色传给他继续扮演。
④ “捉黄鬼”活动表演的性质在后文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体现出来,如活动周期不再由社首及组成的委员会决定,而有时是由当地的干部决定。同时,村内黄鬼基本由外村人扮演,日挣5000元工资。《扮演傩戏〈捉黄鬼〉的黄鬼演员日挣5000元,钱再多当地人也不扮演》,2018年3月2日,http://k.sina.com.cn/article_6426053835_17f05cccb001003scn.html?cre=tianyi&mod=pcpager_china&loc=37&r=9&doct=0&rfunc=100&tj=none&tr=9,2020年3月5日。
⑤ 杜学德:《武安傩戏》,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杜学德:《巫傩文化的奇葩——武安傩戏》,《百科知识》2012年第3期;杜学德:《武安固义的社火傩戏〈捉黄鬼〉》,《节日研究》2011年第2期;杜学德、林兵:《固义古村与社火傩戏——寻访河北古村古镇(四十一)》,《当代人》2011年第10期;杜学德:《冀南巫傩文化概述》,祭礼·傩俗与民间戏剧——98亚洲民间戏剧民俗艺术观摩与学术研讨会论文,1998年2月;杜学德:《固义大型傩戏〈捉黄鬼〉考述》,《中华戏曲》1996年第1期;《冀南固义大型傩戏〈捉黄鬼〉述略》,《民间文学论坛》1994年第3期。
⑥ B43 B73 B77 范丽珠、欧大年:《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的民间信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6-89、76-77、68、88页。
⑦ 赵世瑜:《明清华北的社与社火——关于地缘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的关系》,《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31-258页。
⑧ B33 B41 B44 B72 B74 C. K.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pp.20-21,69,341、350,70,67-68,388.
⑨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此外,还有从戏剧、民俗、符号学等角度对“捉黄鬼”的研究,如何石妹:《从武安傩戏看中原傩的存留特征》,《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朱少波:《符号学角度下的河北武安“捉鬼”傩俗——以固义村“捉黄鬼”和白府村“拉死鬼”为研究个案》,硕士论文,中国海洋大学,2011年,等。
⑩ Helen Siu, “Key Issues i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 View from ‘South China,”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 no.13(December 2014), pp.174-188.
B11 B13 B15 B36 B47 B50 B51 B67 B84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19-26、85、103-104、115、23-24、23-24、128、125-130页。
B12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2, Late Ching,1800-1911, Part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576-580.
B14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85页。费孝通在书中“礼治秩序”一节中将“传统”定义为“社会所积累的经验”,“维持礼的规范”,这些“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生活的需要”。
B16 对此,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认为,“研究这些民间信仰的早期状况和后来发展之间的联系可能要依赖地方口头流传的传统”,具体见范丽珠、欧大年:《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的民间信仰》,第62页。
B17 B19 B30 B32 B39 B42 B56 B71 杜济美:民国《武安县志》,1940年铅印本,附志卷一,附志卷二,第9卷,第1卷,第1卷,第4卷,第1卷,第5、7卷。
B18 B27 B79 B80 夏兆丰等纂:乾隆《武安县志》,清乾隆四年刊本,卷3,卷10,卷3,卷6。
B20 B21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池子华、刘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99页。
B22 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地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通常是以血缘关系来团结社群各分子。具体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18页。
B23 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的起源、特征及其史料价值》,《史学史资料》1979年第2期,第3頁。
B24 与之相类似的例子出现在Kenneth Pomeranz关于邯郸圣井岗的研究中。圣井岗的龙神庙原本不为正祀,直至其在清朝被上升为官祭之前,一直只是村民间自发求雨祭拜的仪式,不被方志所载。在Kenneth Pomeranz看来,这种民间宗教仪式从淫祀上升为官祭,反映出民间与中央政权关于德与灵、地方与中央的冲突。而这种折中地“承认”祭祀的行为,在20世纪国民政府与中共政权更直接地介入地方大众文化之前,成为调和地方社会与中央政权冲突关系的一种方式。Kenneth Pomeranz, “Water to Iron, Widows to Warlords: The Handan Rain Shrin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Late Imperial China, vol.22, no.1(June 1991), pp.62-99.
B25 李椿茂等纂:天启《武安县志》卷6,明崇祯增刻本;夏兆丰等纂:乾隆《武安县志》卷8。
B26 李椿茂等纂:天启《武安县志》卷6;夏兆丰等纂:乾隆《武安县志》卷8。
B28 B29 B49 B61 B65 B81 B82 B83 丁世良、赵放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65,465,465,469,471,468、471,465,465、471-472页。
B31 李明珠:《华北的饥荒:国家、市场与环境退化(1690-1949)》,石涛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2页。
B34 B58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 224、120-121页。
B35 从社会冲突的角度来说,权力存在于不同社会团体或者阶层间的主从关系之中,即在上者用权力去支配、命令在下者,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而这种横暴的权力模式往往是中央集权的发源地。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03-104页。
B37 B38 B70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5-96、136,98-100,417、422页。
B40 根据定县的社会调查,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定县的官员从未超过55人,但是定县的人口却增长至4万,这种官员之于人口的比例使得地方政府无法有效地治理地方社会。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96-98页。
B45 关于此,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中分析了后夏寨村,虽然其是一个相对典型的宗族式华北乡村,但是在多次战乱、灾荒和移民的影响下,其宗族组织在村内失去了根基。由此可见,在华北的乡村地区,即使是宗族势力较强的村庄,其村内的权力结构较南方宗族型村落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第81-82页。
B46 张渠:《粤东闻见录》,程明校点,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9页。转引自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9页。
B48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3-24、84-85页;杜学德:《武安傩戏》,第52页。
B52 杜学德:《武安傩戏》,第108-109页。
B53 全球气候研究指出,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寒冷期:一次发生于1650年,一次发生于1770年,最后一次发生于1850年,见John P. Rafferty, “Little Ice Age,” Encyclopdia Britannica, March 5, 2020, https://www.britannica.com/science/Little-Ice-Age, 2018 September 10.
B54 Kambiu Liu, Caiming Shen and Kinsheun Louie, “A 1,000Year History of Typhoon Landfalls in Guangdong,Southern China, Reconstructed from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ary Records,” in Annals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91,no.3 (September, 2001): 453–464.
B55 陈高傭:《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1327-1359页。
B57 关于活动道具与扮演者传承的资料均源于笔者2015年12月25日对村民的采访。
B59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第259页;范丽珠、欧大年:《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的民间信仰》,第65页。
B60 与固义村“捉黄鬼”活动相类似的是武安县内另一村落白府村于正月十七日举行的“拉死鬼”活动。这类活动都动员了全村居民参与,虽然活动的起始时间并不确定,但是其在社区内所起到的作用却是类似的——通过驱逐灾疫来达到凝聚社区的目的。朱少波、孟华:《从武安傩中的“鬼”符号看两种文化本源模仿方式——以固义村“黄鬼”和白府村“死鬼”为研究个案》,第二届证据理论与科学国际研讨会论文,北京,2009年7月,第484-497页。
B62 民俗学主义,主要是指某种民俗文化事象脱离原来的生存空间,以新的功能,为了新的目的再现的概念,即第三者对民俗文化的利用。其后,2003年,日本学者将民俗学主义定义为:“人们轻易挪用民俗文化要素,通過只保存表面部分的表演和传统性的自我扮演,来满足那些生活在都市的观光客等人的怀旧心理或需求的状况与现象”。见西村真志叶、岳永逸:《民俗学主义的兴起、普及以及影响》,《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6期。
B63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p.278; Kenneth Pomeranz, “Water to Iron, Widows to Warlords: The Handan Rain Shrin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p.63.
B64 Kenneth Pomeranz, “Water to Iron, Widows to Warlords: The Handan Rain Shrin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pp.93-94.
B66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p.45;费孝通:《乡土中国》,第85-86页。
B68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28-129、137-138页。之所以说其产生了断裂性,是指这种寓意与相关宗教活动出现的本身并没有产生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必然关联,而是为了满足主观某欲望或目的而出现的。
B69 与之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民国时期对圣井岗的崇拜之上。到了民国时期,官方越来越少提及圣井岗在祈雨方面的神迹,并弱化了传统帝国时期统治者的德行对于神迹的影响。Kenneth Pomeranz, “Water to Iron, Widows to Warlords: The Handan Rain Shrin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pp.91-92.
B75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p.389;比如在高默波笔下,即使在“文革”期间,其所在的高家庄依然举行了赛龙舟等活动,见Mobo C. F Gao, Gao Village: Rural Life in Moder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pp.162-164, 231, 241-245.
B76 根据笔者2015年12月25日对“阎王”扮演者李姓村民的采访,其称在小时候父辈曾经停止举行这个活动,彼时其听父辈提及,村内的几个平时供村民崇拜的庙宇也都受到影响被关闭。
B78 根据笔者2015-2017年对固义村的采访,其中一位嫁入固义村的媳妇说,活动并不总是三年举行一次,在其嫁进来的期间,有时即使没到三年也会被要求举办。同时,保存活动面具的社首大部分时间会与孩子一起生活在邯郸市,只有过年过节或者举办活动时才回村内。
(责任编辑:许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