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昂贵的一句话:这次不一样
2021-05-30郭荆璞
郭荆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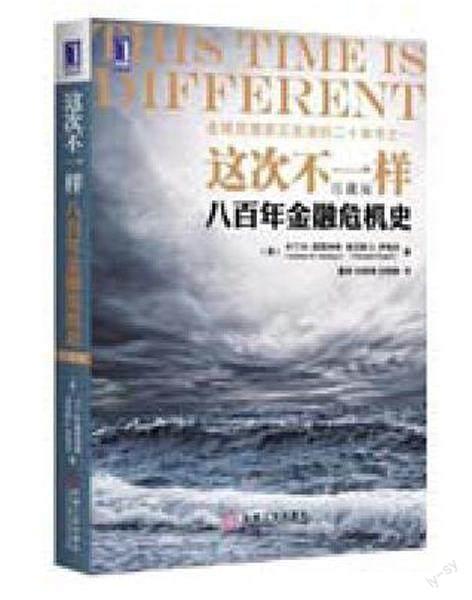
卡门 M. 莱因哈特 肯尼斯 S. 罗格夫/ 著
债务不耐——金融危机是如何发生的?
在上一部分的评述当中,我们应当特别关注“债务不耐综合症”的存在。
债务不耐是指部分国家制度结构和政府体系存在固有的问题,使得政府在面临支出无法被税收覆盖的时候,一次又一次求助外债,最终形成的综合症状。也可以说,债务不耐就是想要靠借债来降低税务和支出矛盾压力。政府债务的基础是对政府的信心,因此债务规模扩大、利率上升、信心丧失构成螺旋形恶化的形态,导致政府偿还意愿降低,并最终导致政府违约。
危机触发因素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自我实现的挤提,而“债务不耐综合症”提示我们,金融危机的启动因素可能存在着路径依赖,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并不是一种均衡状态,也不会像一些理论叙述的那样,当一些前瞻性指标出现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出现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发生一般都伴随着螺旋形的自我强化。
这可能与评级机构的思考方式有关。在评级机构看来,历史比现状重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部分国家,即便在相对低的债务水平上,也会有较高的遭遇债务不耐症状的风险。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了债务不超过该国GNP的60%的安全阈值,旨在保护欧元系统免遭政府违约的冲击,但是莱因哈特與罗格夫的研究则指出,安全的债务阈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违约和通货膨胀的历史记录,违约和贬值的历史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债务忍耐上限,很多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即使在30%的债务/GNP比率附近就会违约,而当代的日本,可以在债务水平远高于其GNP时仍然保持偿付能力。
然而历史也是很容易被遗忘的。很多人认为现代主权违约只是发生在拉美和少数欧洲穷国的现象,这大概是因为拉美给人留下的印象太差了。事实上即使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欧三国都出现过大规模的违约,而短短20年后,这些国家就被当作是“幸福的典范”,其违约的历史被国际市场投资者轻易的遗忘了。
显然,除债务规模/GNP之外,还需要其他指标。
《这次不一样》的两位作者定义了金融危机指数(BCDI,0~5):即系统性银行危机、货币危机、通货膨胀、外债违约、国内债务违约5种危机在某一年同时发生的数量加总。为了深入研究部分持续时间较长的危机,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对危机的定义和处理当中,引入了围绕违约发生时间创建的7年的窗口期,即危机核心1年和前后各3年,并对整个窗口期计算金融危机指数。
债务危机的影响
5种危机中最严重的往往是政府债务违约,即外债违约和内债违约。
由于通常是由债权人决定债务合同的全部条款,因此适用国外法律和国际法律的债务才是外债,也就是说,外债的“外”并不是购买债券的投资人来自国外,或者债券发行的货币是外币,而是适用法律是外国债权人所在国的法律,或者在存在有多国债权人的情况下适用国际法律,这样才是外债。
与之相对,一国政府在本国法律管辖权下发行的所有债务,即为政府国内债务,无论债权人的国籍或债务的计值货币。管辖权在债券发行国的国内还是国外,这是决定内债外债的核心因素。
外债的根本弱点在于缺乏一个超国家的法律框架来确保债务合约面对不同国家的政府时能够保持效力,能够在外债违约时保护投资者的唯有投资者自己的谨慎和对历史的充分研究。
不仅没有合适的国际法律体系来保证外债不会违约,对于外债违约的强制手段同样缺乏,历史上虽然出现过新生国家因为债务偿付的问题又失去来之不易的主权的案例,但是目前的国际政治环境,已经不大可能出现占领另一个国家以敦促其偿还外债的情况。
事实上外债的完全违约在实际中较为罕见,债权人在似乎即将到来的曙光当中,可能会等上几十年才能够得到部分偿付,有历史记录的最长的外债违约,可能是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的苏俄,对此前沙皇俄国的外债做出的违约。
与外债相比,内债违约则隐蔽得多,政府与国内法律相结合,总是能找到规避债务的途径。莱因哈特与罗格夫的研究显示,1900-2007年,所有国家国内债务的平均占比在40%-80%之间波动,其中的特例是荷兰、新加坡、美国等几个特殊国家,几乎全是内债(根据债务人国家法律发行),部分原因是其相对稳定的货币体系和在国际收支当中的特殊地位。
作者同时也指出,一次违约并不是末日,识别债务不耐的主要因素是一国违约和高通货膨胀的历史记录,反复出现的违约或者高通胀才是陷入债务不耐循环的标志。
债务国真正面临的,是一场更加根深蒂固的偿付能力和偿付意愿危机,债权人往往很难区分偿付能力和偿付意愿的区别。如果债权人充分相信债务国在长期内会偿还其债务,债务人是很难陷入短期流动性危机的,包括2008年至今不断扩大债务上限的美国政府。总会有人给好的债务人展期短期债务的。这也提示我们,外债违约的时候,债权人事实上也不是无辜的,他们也必须改变自身的投资纪律。
在谈到21世纪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两位作者提出金融危机平息之后,无论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都必须反思自身的财务和投资纪律,出现各种形式违约的国家需要找到以非债务的形式补充资本的渠道,这样才能防止本国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继续出现重复违约,陷入债务不耐循环。债权人与债务人有时会面临多重均衡,双方需要在违约之外寻找新的解决途径。
国际借贷中违约的影响包括:导致违约债务人借贷的上限(也就是未来能借到的钱)降低,债务国海外资产会被扣押、贸易中断、债权国的单方面司法行动打破国家安全协议和联盟影响FDI(资本外溢),也影响发达国家的知识外溢。
外债违约往往伴随着对债务人的国际资本市场限入,也就是说频繁发生违约的债务人很难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持续融资,莱因哈特与罗格夫将这种限制进入视作一种症状,而非病症的根源,他们隐晦地表达了一个观点,即资本市场的态度表征了国家的稳定程度,很少犯错。
他们同时也指出,对外账户数据普遍被认为比其他宏观经济数据更真实,尽管存在系统性低估。
理性和理想的国际资本市场,应当可以识别一个国家的制度性缺陷,并且在制度性缺陷导致一国出现债务不耐,对经济产生实质性的阻碍的时候,及时撤出在该国的投资。
我们可以推论:1)制度等因素导致贫富不均,而不是资本劳动比;2)资本市场一体化带来的风险分散收益有限;3)新兴市场资本流入周期是顺周期的,固有的制度性缺陷不能消除,那么一个国家就无法走出债务不耐的循环,外界的资金对这样的国家来说是春药也是毒药。
要想克服债务不耐问题,一个国家必须有着良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纪律,政策制定者应该在长时期内维持很低的债务水平,同时进行更多的基础结构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和贸易,不能依靠更多的债务来解决眼前的债务,而是依靠经济增长和公平分配来消化更多的债务负担。
这样我们就回归到了18世纪的外债性质上,至少在部分意义上,外债是用来应对突发支出的,外债水平过高意味着突发情况出现就借不到钱了。
债务国在违约之后不仅将损失资本流入和外国直接投资,往往也会损失伴随FDI而来的知识外溢,这可能在更长远的时间上对一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损失。
在清楚了外债内债的区别之后,莱因哈特与罗格夫给出了危机的定量定义:通货膨胀危机,“二战”后高于40%年率,“一战”前高于20%;货币贬值危机,“二战”后高于25%年率,“二战”前高于15%。
商品价格核心经济变量包括,经常账户赤字、真实GDP、名义GDP、金融中心的短期和长期利率。
通货膨胀危机和货币贬值危机,都和历史上的货币减值(也就是货币中贵金属含量下降)一脉相承,在现代纸币不能减值,会以转换的形式来实现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常常相伴而生,之后是货币减值和转换,就像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的危机之后常常是银行危机一样。
在现代,新兴市场发生的主权国家外债违约危机比银行危机要多得多。
银行危机往往伴随着股票泡沫的破裂,虽然股票泡沫相对好度量,但是房价泡沫,包括破裂的房价泡沫都是不好度量的。银行危机仍然常见,而主权债务违约随着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发展逐渐减少的现象,可能来自于外部政治锚機制,例如欧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