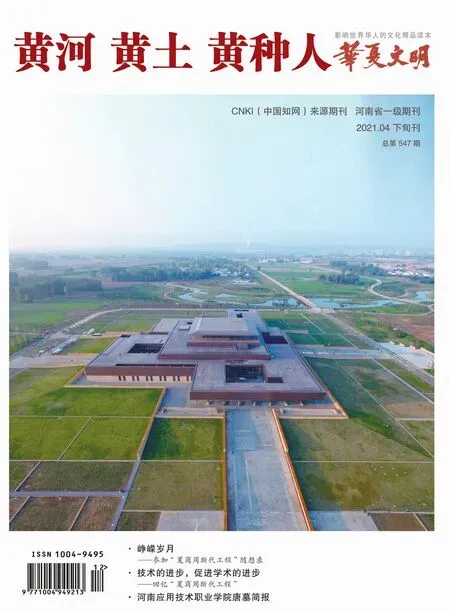苏州黑松林出土孙吴石屏风画臆释
2021-05-26程义
□程义
1997 年5 月, 原苏州博物馆考古部在苏州虎丘黑松林抢救性发掘了三国时期孙吴墓葬五座。在主墓M4 中出土两套石屏风, 屏风两面均有石刻线画。其中一块石屏风保存相对完好,是该时期石刻文物中的精品。 此石刻出土后就一直存放在苏州博物馆库房内,未能发表和研究,最近在清理库房时才得以仔细观察。这块屏风出土时平置,倒地的一面画像已经漫漶不清,很难区分正反面。 因为三国绘画,特别是孙吴绘画材料极其匮乏[1],所以这块石屏风就显得异常珍贵。
这块石屏风纵73 厘米、横71 厘米、厚5.5 厘米,一面保存良好,画面以阴刻线条描绘人物与纹饰,另一面也有阴刻人物图像,但已漫漶不清。 屏风左右及上部边沿饰以云气纹, 画面分上中下三层,每层间以帷幔分开,由下至上刻画如下。下层:由右及左为三人一山,分别为右侧一人,头戴平巾帻,身着交领长袍,疑似右手持戟;带剑者两人,头戴无帻之冠,右二佩剑于右侧,右三佩剑于左侧,身背包袱,两人呈奔跑状;远山一座,呈“工”字形,曲径通幽,云雾缭绕,山峰高耸入云,接入中层。但山和人物比例悬殊,人比山还显得大一些。中层由左至右共四人,左二似乎为主要人物,身着交领长袍,推测为女性,双手自然伸展呈讲话状,其余三人或拱手,或呈凝神倾听状,皆朝向左二;最左侧描绘长方形柱状物,接通上层。上层由左至右亦四人,左一佩剑于右侧,推测为侍卫,惜面部漫漶不清,似乎面朝右;左二佩剑于左,居画面中间,推测为该层主要人物,双手平推,表情威武,气宇轩昂,与右侧二人交谈; 右侧二人装束和下部中间二人相同,但未佩剑。 (封三)
为了整理当年的考古资料并撰写相应的发掘报告,我们组织了一次研讨会,会后由姚晨辰先生在《中国文物报》上将该屏风图像进行了披露,他认为:“这类呈‘工’字形的远山,天柱稍简略,曲径通天,为描绘西南方昆仑仙山的典型形象,画像石中位于仙山之上的人物形象有西王母或东王公或周穆王等, 这也与屏风边沿的云气纹完美地统一起来, 这件屏风可能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仙境中的人物故事画”[2]。
通过观察和分析, 我们认为这个图像中既没有西王母的龙虎座,头部也没有戴胜,并且女性位于中层,这不符合西王母的身份。 从东汉末年西王母东王公镜上的图像来看,这个解释并不很贴切,人物和故事情节很难对应起来。
为此经过进一步的推敲, 我们认为这是一幅历史鉴戒图, 其画像内容应该是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的故事。 试将我们的理解分析如下,以作为抛砖引玉之用,并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1.没有榜题:内容与格套
人们在研读各类视觉材料时,经常会遇到一些没有题目的作品。 但这并不影响大家对画面的解读。 与之相反,读者很容易判断出画面内容的主题,比如中国画里常见的岁寒三友、携琴访友、四季山水。 我们之所以能够不通过文字就可以判断这些视觉材料的内容, 是因为这些内容已经形成一种定式,即所谓的画式或格套。 邢义田注意到:“汉代画像不论石刻或壁画常见标示画像内容的榜题。也有些石刻预留了榜题的位置,实际并未刻字。 为什么画像有些有榜题,有些没有? 一个尝试性的解释是,因为汉代的画像有一定的格套,不同的内容会依一定的格式化呈现, 因此只要熟悉这些格套,不需要文字榜题的帮助,就能够了解画像的内容,大家熟悉的,就不需要榜题……凡是较不熟悉,或不以榜题帮助,无法明确传达画像特定意义的,就必须标以文字,加以说明。因此,格套式的画像,如不加榜题,所要传达的应该是当时一般人所共同理解的意思……可是千百年后, 我们已经不熟悉汉代家喻户晓的‘热门故事’和‘热门人物’”[3]。
邢义田的研究我们认为是恰当的, 也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在研究没有榜题的画像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这是什么“格套”,换言之,这是当时哪种流行的图式?
因为这幅石刻画是一个随葬的背屏, 所以它的内容我们需要朝两个方向去考虑:丧葬或实用。它既可能是专门为丧葬而制作的一件随葬品,也有可能是模仿现实生活而做的一件复制品或缩小版模型。通过对其体量的考察,我们更倾向于这是一件模仿现实生活的背屏。也即是说,这个画屏是死者生前起居中的一件家具。对于画屏的功用,巫鸿认为 “可以把屏风当作一件实物, 一种绘画媒材,一个绘画图像,或者三者兼具”[4]。 因为这个屏风是和石案石几成套出土的, 所以它显然是三者兼备的。
2.可能的题材
因为没有榜题, 所以我们无法确知画像的内容。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东汉三国时期的画像石内容对其进行考察。 汉代绘画内容除了大量的装饰性图案外,通常包括道德宣传和神仙信仰两大类。道德宣传关注现实世界,神仙信仰关注未来世界。这两类图像既是实用建筑的装饰内容, 也是丧葬艺术的主角。巫鸿曾经指出,正面和侧面像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崇拜的偶像,一个是故事的人物。 与之相对应的, 偶像型要和观者发生联系组成一个崇拜和被崇拜关系, 而侧面像人物总是沿着画面向左或右行进。一幅图中的人物都是互相关联的,他们的姿态具有动势, 并表现出了彼此之间的呼应关系[5]。这幅屏风画,所有的人物都是侧身像。如前所述,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具有明显故事情节的内容,并且和已知的汉代画像石内容很难对应,和当时流行的以东王公、 西王母为主的神像世界更难对应。 因此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一幅用于道德宣传的故事画。 因为这是死者生前每天要面对的一幅画,画面以训诫为主也颇符合屏风的功能。 “图像之设,以昭劝诫”,汉代以来视觉艺术中出现了大量的历史故事、烈女义士之类的内容,正是这一社会风尚的反映。
《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载:“曹植有言曰: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异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臣死难,莫不抗节;见放臣逐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昔夏之衰也,桀为暴乱,太史终抱画以奔商。殷之亡也,纣为淫虐,内史挚载图而归周。燕丹请献,秦皇不疑;萧何先收,沛公乃王。 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 是以汉明宫殿,赞兹粉绘之功;蜀郡学堂,义存劝戒之道。马后女子,尚愿戴君于唐尧;石勒羯胡,犹观自古之忠孝。 岂同博弈用心,自是名教乐事。 余尝恨王充之不知言,云:人观图画上所画古人也,视画古人如视死人,见其面而不若观其言行。 古贤之道,竹帛之所载灿然矣,岂徒墙壁之画哉!余以此等之论,与夫大笑其道,诟病其儒,以食与耳,对牛鼓簧,又何异哉!”[6]唐代张彦远不厌其烦地引用前人论断,旨在说明古代绘画和训诫关系密切,并不是简单的图像而已。但是训诫的内容非常多,三皇五帝,节妇烈女,高节妙士……纷繁复杂。 如果要判断这幅石刻线画的内容, 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尚无疑是重要的参考体系和线索。
3.孙吴政权的社会环境:危机与教训
这座墓的时代我们根据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已经可以确定属于孙吴时期。 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社会环境也和孙吴政权相关。 孙吴政权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一个地方政权, 和北方曹魏政权不同的是, 孙吴是由北方大族迁入江东而建立的一个割据政权。 因此孙吴统治集团面临的压力一方面来自北方的曹魏,另一方面来自江东当地。孙吴经过赤壁之战后,逐渐形成了魏蜀吴鼎立的局面,但是曹魏对江东集团的压力一直存在。此外,作为一个外来的军政集团, 如何笼络和驾驭当地的旧族和新加入的山越势力, 也是摆在孙吴集团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所以说,孙吴政权一直存在内外两种压力,一旦处理不好,随时都有亡国的可能。 面临如此压力, 孙吴君臣必须也必定在寻找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身处吴越旧地的孙吴政权,最直接也最广为流传的历史教训莫过于夫差与勾践的故事。 夫差与勾践故事的梗概大致是:吴大败越国,越国臣服, 夫差穷兵黩武, 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终“三千越甲终吞吴”。这个胜败转换的故事对孙吴政权有着非常现实的警示意义。赤壁之战,取得暂时的胜利(吴败越),如果不励精图治,即有可能发生翻转被曹魏灭亡(越灭吴)。
曹魏的压力人所共知,不需多言。江东土著山越和孙吴的关系更是令孙吴高层人士惴惴不安[7-9]。山越在史书中又被称为 “山民”“山寇”“山夷”“山贼”“越贼”,山越是最常见的称呼。依胡三省的解释“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通鉴》卷五十六“汉灵帝建宁二年”条)。 这些人从战国末年一直到唐初,出没山林,叛服无常,和政府关系摇摆不定。 如陈寿所言:“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逸外御,卑词魏氏。”[10]1395山越不但难以控御,而且作为孙吴敌对势力的曹魏政权并没有忽视这股势力的存在, 进入3 世纪以后,曹操经常企图与山越接触[11],试图利用山越牵制孙吴。这一局面也和吴越楚三国之争颇为近似。孙吴政权以“吴”为国名,而山越确是“越”之余绪[12],因此山越的叛服和春秋末年吴越之争的局面颇有类似之处。
孙策去世之际对张昭等言“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10]1109。 陈寿认为孙权的行为与勾践极其相似:“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 ”[10]1149这些都说明,魏晋时期,吴越史事对江东人影响之深刻。 面临内外双重压力的孙吴政权,在政治宣传和训诫方面,吴越旧事无疑是最经典的,也是最容易流传的内容之一。因此以吴王夫差和勾践的故事作为案例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4.勾践灭吴的流行与演绎:《春秋左传》—《史记》到《越绝书》—《吴越春秋》
春秋吴越之争的梗概是: 起初吴王夫差打败越国,接着剧情发生翻转,越最终灭吴。这是非常著名的历史事件, 在战国时期就已经作为历史教训,出现在文献里,甚至在北方蛮夷之国中山国的青铜器铭文里也出现了。 这段历史我们目前最熟悉的剧情是:吴王夫差打败越王勾践,伯嚭接受越国的贿赂,越王勾践奉上西施、郑旦两个美女,吴王夫差就接受了越王勾践求和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伍子胥极力反对,但夫差听信谗言接受了求和。夫差进一步骄奢淫逸,穷兵黩武,赐死伍子胥。 而越王勾践励精图治,最终战败夫差,逼迫夫差自杀。
如果我们将先秦文献和汉魏六朝文献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个故事是可能层累地形成的,特别是西施、 郑旦二美女和伍子胥力谏这个情节的加入很具有代表性。 如果清华简《越公其事》记载可信的话,那么从《史记》以来,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就已经开始文学化。学界对此已有深入的研究,一般分为历史叙述和文学演绎两类, 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将两类文本排比如下。
第一类以《左传》《史记》为历史叙述代表,《国语》略加修饰。
《左传》:“吴将伐齐,越子率其众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馈赂。 吴人皆喜,唯子胥惧,曰:‘是豢吴也夫! ’谏曰:……反役,王闻之,使赐之属镂以死。 ”[13]
《史记》:“越王勾践率其众以朝吴,厚献遗之,吴王喜。 唯子胥惧,曰:‘是弃吴也。 ’谏曰:……吴王闻之,大怒,赐子胥属镂之剑以死。 ”[14]
《国语》之《越语上第二十》:“‘……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 请勾践女女于王, 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越国之宝器毕从! 寡君帅越国之众以从君之师徒。 唯君左右之……’夫差将欲听,与之成……越人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国之罪,又有美于此者将进之。 ’太宰嚭谏曰:‘嚭闻古之伐国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 ’夫差与之成而去之。 ”[15]568
清华简 《越公其事》:“……赶登于会稽之山,乃使大夫住(种)行成于吴师……吴王闻越使之柔以刚也,思道路之修险,乃惧,告申胥曰:‘孤其许之成。 ’申胥曰:‘王其勿许。 天不仍赐吴于越邦之利,且彼既大北于平邍,以溃去其邦,君臣父子未相得,今越公其胡又带甲八千以敦刃皆死? ’吴王曰:‘大夫其良图此……今我道路修险,天命反侧。岂庸可知自得?吾始践越地以至于今,凡吴之善士将中半死矣。 今彼新去其邦而笃,毋乃豕斗,吾于胡取八千人以会彼死? ’申胥乃惧,许诺。 吴王乃出,亲见使者……使者返命越王,乃盟,男女服,师乃还。 ”[16]
第二类以《越绝书》《吴越春秋》为文学演绎代表。
《越绝书》:“越(王)乃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曰:‘昔者,越王句(勾)践窃有天之遗西施、郑旦,越邦洿下贫穷,不敢当,使下臣种再拜献之大王。’吴王大悦。申胥谏曰:……吴王不听,遂受其女,以申胥为不忠而杀之。 ”[17]
《吴越春秋》:“十二年,越王谓大夫种曰:‘孤闻吴王淫而好色,惑乱沉湎,不领政事。因此而谋,可乎?’种曰:‘可破。夫吴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献美女,其必受之。 惟王选择美女二人而进之。 ’越王曰:‘善。 ’乃使相者国中,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 饰以罗縠,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 乃使相国范蠡进曰:‘越王勾践窃有二遗女,越国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谨使臣蠡献之大王,不以鄙陋寝容,愿纳以供箕帚之用。’吴王大悦,曰:‘越贡二女,乃勾践之尽忠于吴之证也。 ’ 子胥谏曰:‘不可, 王勿受也……’三月,吴王召见越王入见,越王伏于前,范蠡立于后。 ”[18]
把上两类文献做一比较, 显然文学演绎类的情节更为曲折,也更为丰满,这符合古史辨学派的所谓层累形成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发现, 在战国秦汉时期, 二位越女并不是故事的主角,但到了东汉六朝时期,西施、郑旦开始成为这一故事的主角,并且将伍子胥力谏的情节具体化,在《史记》《左传》等历史文献里没有详细描写的情节和人物,这时候都被刻画出来。文学演绎自然不是真正的历史, 但是它有着非常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就像现在普通民众对三国史的认识,文学化的《三国演义》要比正史《三国志》广泛得多,而且也深信不疑, 并对人们的道义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关公信仰。
《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的作者及成书年代众说纷纭, 但大致不出东汉晚期到六朝这一历史时期。东汉时期中原遭受战乱和天灾的摧残,与之相反,江东开发开始加速,江东豪族开始崛起,这是江东产生记录当地历史的动力,《越绝书》《吴越春秋》的编撰正是对这一需求的回应。由于《越绝书》《吴越春秋》结合汉代儒学精神,又将吴越先王先贤的事迹精心整合和演绎,以达到弘扬先王事迹,阐发兴亡成败之理的目的, 相比艰涩的经传和正史, 这种整合和演绎具有更强的民间性而得以广泛流传,并一直流传至今。 因此,虽然史传比文学演绎更准确,但文学演绎更容易流传,也就更容易成为社会风尚和传统。
如前所述,文学演绎相对于史传,对这一历史场景的关注主要在于增加了更加引人入胜、 广为流传的西施、郑旦二越女等情节。我们将这一场景做一简单描述:越王勾践和范蠡告别文种,带领二越女前往吴国投降, 吴王夫差贪恋女色, 准备接受,而忠臣伍子胥力谏不可,但吴王不听建议,并因此疏远逼杀伍子胥。吴王夫差因为贪恋女色,刚愎自用,不听伍子胥的建议,最后落得个国破身亡的下场。 这一历史场景涉及的人物有: 吴王夫差(昏庸好色)、伍子胥(忠臣)、越王勾践(忍辱负重)、范蠡(机智多谋)、西施和郑旦(女色)、文种(忠臣)。 忠臣昏君、谋士女色,这是多么活生生血淋淋的历史教训啊! 比起史传的记载有趣生动多了!虽然带有更多的想象,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鉴戒效果,流传和影响力自然非同小可。
5.本图式的流传与人物比对
按照汉魏六朝时期广为流传的故事版本,我们很容易将画中人物和情节进行比对。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上层右侧未带剑的二人和下层右侧奔跑的二人。 这两人冠式、服饰基本一致,只是动作不一样,最明显的差别是上层不带剑。我们认为这二人就是下层的二人跑到了目的地, 然后去会见某人。而上层中间的那位人物显得气宇轩昂,正在和右侧两人在交谈。 上层最左侧的人物虽然有些漫漶,但有一个细节非常关键:他的剑柄朝向和其他三位佩剑人物均不一样, 应该表达的是不一样的动作。这一画面使我想起了吴王镜①此类铜镜多发现于江浙地区,如上海博物馆编《炼形神冶莹质良工——上海博物馆藏镜精品》第51、52 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 年,原定名为伍子胥镜;另有王士伦编、王牧修订《浙江出土铜镜》图版第25、26 号,文物出版社,2006 年。上忠臣伍子胥拔剑的动作。 (图1)我们将上层四个人物从左往右分别确定为伍子胥、夫差、勾践和范蠡,那么整个画面的人物对应当如下: 底层, 右一为文种,二、三为勾践和范蠡;中层,右一吴国内官,中间二人为西施、郑旦,左一为吴国内官。 底层左侧的山是一个标识,既代表吴越之间的距离,也代表以此为界,分为两个场景:上两层为吴国境内,下层为越国境内。 因此整个故事情节可以叙述为:1.下层。 范蠡、勾践告别文种,前往吴国投降。 2.中层。 西施、郑旦被贡献给吴国后宫。 3.上层。 吴王夫差接受越国美女和投降,伍子胥坚决不同意,甚至有拔剑自杀的动作。拔剑的动作显然是虚构,在吴王面前,即使再怎么强烈抗议,都不可能直接拔剑,以武力胁迫国王或自杀。 但在汉魏时期,为了增强故事的情节性和对抗性, 这个情节确实是这一视觉图像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层的四位女士可能有些难以理解, 但在襄阳擂鼓台一号汉墓的漆奁上即有西施、郑旦的故事。 据张瀚墨研究,器底一组被标记为图像F 的画面就是包括西施、 郑旦在内的四位[19]。 因为漆奁和铜镜都是圆形的,和屏风的形状不一样, 所以画师在构图和内容取舍方面做了调整, 但这一故事的骨干情节依然清晰可见,非常难得。
6.结论

图1 上海博物馆藏吴王镜拓本
黑松林三国墓地出土的石屏风线画的内容极有可能是孙吴时期非常流行的历史鉴戒画内容,其故事梗概来自当时高度文学化的春秋吴越历史的演绎。 这幅石刻线画的内容虽然还不能最终确定,但其绘画技法,特别是流畅刚劲的线条、人物姿态准确的刻画都为我们认识孙吴绘画提供了非常关键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