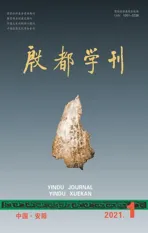《清华简(七)·晋文公入于晋》中的军旗考论
2021-05-25洪德荣
洪德荣
(郑州大学 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1)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先秦兵学和军事学的相关研究中,关于制度的问题,过往主要以传世文献作为重建先秦制度的基础及根据。而除了传世文献,商周金文对于古代军制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与军事有关的铭文早已成为独立的研究论题,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其中与旗类有关的器物作为赏赐物已见于西周金文,(1)如商艳涛:《西周军事铭文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对军事铭文做过整理与讨论,如常、旗、旜、旟、旐或与“物”字相关的字形都见于西周金文,也可印证孙诒让提出的“五正旗四通制”之说。参邬可晶:《西周金文所见有关“九旗”的资料》,《中国经学》(第十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5-144页。因此出土文献材料对于探究古代旗帜制度,也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在出土的简帛文献中,有一类关于先秦旗帜的材料值得注意,材料公布以来也有不少学者进行过讨论,但从先秦兵学的角度而言,仍有再讨论的空间。
二、简文校读
近人对于古代旗帜制度的讨论颇有成果,如林巳奈夫细致地探讨关于旗的形态,高木智见亦对旗帜的图案及内涵进行讨论,杨英杰也对旗帜的意义做过讨论。(2)(日)林巳奈夫:《中国先秦时代的旗》,《史林》1966年第49卷第2号;(日)高木智见:《关于春秋时代的军礼》,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31-169页;杨英杰:《先秦旗帜考释》,《文物》1986年第2期,第52-56页。在新出楚简中关于旗帜的记载,可以为有关研讨带来不同的诠释角度。
《清华简(七)·晋文公入于晋》简5到简6是关于旗帜的叙述,(3)竹简材料的情况可参马楠:《<晋文公入于晋>述略》,《文物》2017年第3期,第90-92页。先将简文抄录如下:

原整理者认为“旗物”为诸旗统称,《周礼·大司马》:“辨旗物之用。”《周礼·乡师》:“四时之田,以司徒之大旗致众庶,而陈庶以旗物。”《周礼·巾车》:“掌公交车之政令,辨其用与其旗物而等叙之。”《周礼·司常》:“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颁旗物。”《周礼·司常·九旗》:“日月为常,交龙为旗,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孙诒让据金榜《礼笺》说,以为“通帛为旜,杂帛为物”“全羽为旞,析羽为旌”系诸旗通制,“日月为常”色纁,象中黄,“交龙为旗”色青,“熊虎为旗”色白,“鸟隼为旟”色赤,“龟蛇为旐”色黑,各象五方之色。“通帛为旜,杂帛为物”,通帛谓縿斿一色,纯色,故尊于杂帛。(4)原整理者之说及简文的通读隶定皆出自李学勤,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中西书局,2017年。下同,不再出注。如有其他诸家之说再引用讨论。

是以《说文》言旗上有熊形,盖因旗的作用就在于标示、象征,因此可作为士卒聚集的地点,也是构成军事行动中的军队信息体系。但笔者认为以旗的作用及本义而言,不同典籍所记载的内容与简文所言不一定能完全对比的上,甚至同样用于军事的旗帜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记载之中,都有不一样的图像象征与表义功能,以材料本身的文字记载去做解读,在其记载的内部体系及背景中去考虑,这是考察简文中的军旗制度很重要的视角。

在考古发现中,河南淮阳马鞍冢的战国晚期车马坑出土过一种贝旗,旗为红色,旗一面每组用八枚海贝,旗另一面每组用四枚海贝,用线缀成四瓣的花纹,排列整齐。旗纹饰是由海贝缀成,整理者称其为贝旗。(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马鞍塚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0期,第12页。而军旗本身的表意作用除了颜色,图像更是一大关键。如《礼记·曲礼上》:
前有水,则载青旌。前有尘埃,则载鸣鸢。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前有挚兽,则载貔貅。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其主要叙述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为军队进军所遭遇的情况,及对应的旗号图像,二为左右前后方位的应对,用意在于分辨各军,以利指挥。而《管子·兵法》也有类似意义的叙述:
九章:一曰举日章,则昼行。二曰举月章,则夜行。三曰举龙章,则行水。四曰举虎章,则行林。五曰举鸟章,则行陂。六曰举蛇章,则行泽。七曰举鹊章,则行陆。八曰举狼章,则行山。九曰举韟章,则载食而驾。九章既定,而动静不过。
但两种材料对于同一情况下采取的旗号是不同的,如遇到行水,《礼记·曲礼上》为青旌;《管子·兵法》为龙章。
另如《墨子·旗帜》的记载:
守城之法,木为苍旗,火为赤旗,薪樵为黄旗,石为白旗,水为黑旗, 食为菌旗,死士为仓英之旗,竟士为雩旗,多卒为双兔之旗,五尺童子为童旗,女子为梯末之旗,弩为狗旗,戟为旌旗,剑盾为羽旗,车为龙旗,骑为鸟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书者,皆以其形名为旗。城上举旗,备具之官致财物,之足而下旗。
同样也以颜色与图像表示事物的现象及状态,可见旗帜的表意具有材料中自己的表达体系,这也是解读先秦军旗问题需要注意的可比性与相似性之间的辨别问题。

原整理者引郑玄注“交龙为旗”,以为“诸侯画交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复也”,谓二龙一升一降。
谨案:就简文分析,“升龙”即“师以进”;“降龙”即“师以退”,以“升”对比“进”,是语意的引申转移,“升”指物体的移动由下而上,并有登义,“进”则指平行的向前移动。相对于“退”而言,“降”与“退”同样也是语意引申转移。因此就简文言,图像的内容亦不难想见。至于郑玄注“交龙为旗”的“交龙”《释名·释兵》言:“交龙为旗,旗,倚也,画作两龙相依倚也,通以赤色为之无文采,诸侯所建也。通帛为旃,旃,战也,战战恭己而已也。三孤所建,象无事也。” “交龙”指两龙相依交会,龙首一在上,一在下,也是一种表意的方式,与简文所记载的“升龙”“降龙”自然为不同的旗帜。

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清华七整理报告补正》石小力又补释认为“豫”,整理者如字读,训为预备。今按,豫可读为舍,训为止息。楚简“豫”字多读为“舍”,如《上博四·曹沫之阵》18-19:“臣之闻之:不和于邦,不可以出豫(舍)。不和于豫(舍),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战。”军队住宿一夜为舍。《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引申可指军队休息,《汉书·韩信传》“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颜师古注:“舍,息也。”《管子·兵法》:“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偃兵”即“师以舍”。(8)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清华七整理报告补正》,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2017年4月23日。
程浩亦补释认为整理报告于“豫”字无说,而按照楚简的用字习惯,或应将其读为“舍”。清华简《系年》屡见“豫”字,如“楚王豫围”(简42)、“秦人豫戍”(简45)、“楚人豫围”(简117)等,这些“豫”很明显都应读“舍”,意为释放、舍弃。然而《晋文公入于晋》中这个“豫”字的涵义,似乎还不能完全与《系年》等同。从上下文来看,简文用以描述不同旗帜作用,往往是一组反义词。如简6“为升龙之旗师以进,为降龙之旗师以退”,升龙与降龙分别对应的是师的“进”与“退”。以此类推,这里角龙与交龙所对应的“战”与“舍”应该也是相对的概念。实际上,上博简《曹沫之阵》中就有这样的用例,其云:
既战复舍,号令于军中曰:“缮甲利兵,明日将战。”(《曹沫之陈》简50)
从中可以看出“舍”是与“战”相反的动作,有止战之意。《孙子·军争》“交和而舍”,贾林注“止也”,即是此意。陈剑先生认为《曹沫之陈》中的“豫”皆当读为“舍”,意为“军队驻扎”(动词)或“军队驻扎之所”(名词)。所谓“军队驻扎”,亦可引申为休战、止战。简文“为角龙之旗师以战,为交龙之旗师以舍”,意思就是用角龙旗时出师交战,用交龙旗时止战回营。(9)程浩:《清华简第七辑整理报告拾遗》,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2017年4月23日。

关于本段简文原整理者无详说,王挺斌指出简文“旧”的用法与上博简《孔子见季桓子》22号简“迷(悉)言之,则恐旧吾子”、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13号简“女(汝)慎重君葬而旧之于三月”一致,都读为“久”,训为久留、等待之义。这种“久”的训释古书较为少见,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学者关注;陈剑先生在解释《孔子见季桓子》22号简“迷(悉)言之,则恐旧吾子”之“旧”的时候就曾疑惑犹豫,后来读书会举出《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寡君以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为证,这才确定“旧吾子”当即读为“久吾子”。简文这种带有军事色彩的“旧(久)”,可以和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五名五恭》“轩骄之兵,则共(恭)敬而久之”之“久”合观。(10)程浩:《清华简第七辑整理报告拾遗》。
而简文中所载的以日月为旗号,原整理者亦无说法。日月之形常出现于旗帜之上,典籍有记载,如《周礼·春官·宗伯》“日月为常。”郑玄云:“王画日月,象天明也。”《释名·释兵》:“九旗之名日月为常,画日月于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日月”在典籍及文化意义中象征天地及天道秩序,《礼记·郊特牲》:“旗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荀子·天论》:“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也有学者认为日月与兵学文化中的“避兵”有关,如《兵避太岁戈》中的神灵脚踏日月。而李零也认为古代的避兵符以太一、北斗和日月为主。(11)李零:《“太一”崇拜的考古研究》,《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35页。耿雪敏认为军旗上以日月为章,与《兵避太岁戈》上的日月图案一样,具有避兵的含义。(12)耿雪敏:《先秦的军旗与兵阴阳家》,《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2年第12期,第47-51页。任慧峰也认为军旗不仅在战争中具有实战作用,并且由于其可以体现古人信仰,而在古人心目中具有了沟通神灵、保佑平安、提高胜率甚至杀伤敌人等特殊功能。(13)任慧峰:《先秦军礼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10页。
笔者认为“日月”在典籍中记载十分丰富,可知与文化思想有密切关系,但简文中的日月与避兵之间并无关连,而是应更直观的去思考旗帜上日月的意义,简文既然说“日月”象征“(师)以旧(久)”那么“日月”象征的应该是时间的经过,典籍中也会以“日月”表示时间之意,如《论语·雍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论语·阳货》:“日月逝矣,岁不我与。”由此可见,简文中的旗帜图像应是以日月表示时间的经过,而象征部队停留过久,不利于战事。

原考释者言熊、豹对应《周礼·司常》“熊虎为旗”,与《周礼·大司马》《司常》所载职级相合。
谨案:在前文已经讨论,旗帜图像在不同的时空环境记载中不一定具有可比性,就本段简文而言,以“熊”表示大夫出,以“豹”表示士出,就具备了用动物间不同的大小特质表示不同的身份阶级。首先,“熊”“豹”都是典籍常见的猛兽动物,如《大戴礼记·五帝德》:“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而以动物表示诸侯大夫的等级之别,如《周礼·天官·冢宰》:“司裘:掌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献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献功裘,以待颁赐。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皆设其鹄。”又如《论衡·乱龙》:“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土龙亦夫熊麋布侯之类。四也。”
以上都是以动物表示身份等级的差异,因此简文此处的旗帜,应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如《白虎通德论·乡射》:“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熊为兽猛巧者,非但当服猛也。示当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诸侯射麋者,示达远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何?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何?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


王宁认为“荛”二字当读“獌”或“獟獌”,亦即《尔雅·释兽》之“貙獌”,《说文》:“獌,狼属”。或云“貙虎”。“侵粮者”疑当读“侵掠者”或“侵略者”,指外出作战、侵掠敌国的士卒。(20)王宁:《清华(七)〈晋文公入于晋〉初读》,武汉大学简帛研究网论坛,2017年4月28日。


三、结语
通过出土文献中军旗材料的记载,以及对传世文献的对比,可以发现旗帜的图像与形制本身带有因地因时表达意义的特质,虽然部分的旗帜材料仍具有其共通性,但自成系统仍是先秦旗帜展现的特色。而对于先秦军旗的研究有助于先秦军事学及旗帜制度的深入探讨,《清华简(七)·晋文公入于晋》中的军旗,是很宝贵的文献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