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词重拾文化自信
2021-05-24刘英团
刘英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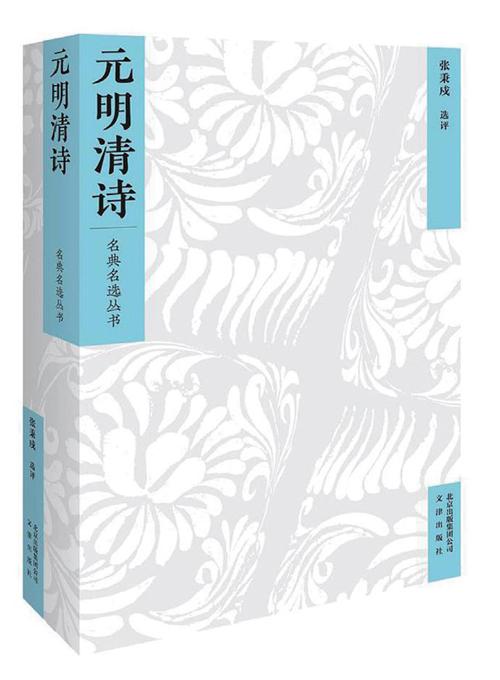

词起源于民间,始自唐,兴于五代,而盛于宋,“其后,历元、明、清三代六百三十余年,虽有兴替起落,但始终呈现多姿多态”(马兴荣《论元明清词及词的鉴赏》),至少“并不等于说宋以后的词坛便完全衰败,无可诵读之家,无可撷取之作”。元明两代词道式微,这是事实,而入清之后,词又出现了再造辉煌的局面,这也是事实。“由于距宋未远,仍可以说代有才人,不乏佳作,也正是元词的一脉余绪,才有清词中兴”(王广超《元词论纲》)。著名文化大家张秉戍认为,“在(元明清)这七百多年里,三朝之中,优秀的词家,优秀的词作,仍是层出不穷,其中不少的诗人词作全可与宋之大家相媲美。”《元明清词》选评元明清三代词人百二十家,词作二百首,不仅使读者从不同风格、流派的词人词作感受到元明清词的成就及其审美价值,这些具有代表性、可读性的词人词作又从某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面貌。
元词是词史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地域性、民族性使其具有独特的风格、自身的文化意义及文学特质。元朝词作成就最大者,首推元好问,著有《遗山集》四十卷,存词三百七十余首。他的词具有“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者矣”(刘熙载《艺概》),又具豪放、婉约两种风格:“蕃艳其外,醇至其内,极往复低徊掩抑零乱之致”(况周颐《蕙风词话》)。词人白朴、王恽、魏初、刘敏中、郝经都曾受益元好问,故有“大抵元词之始,实受遗山之感化”(吴梅《词学通论》)之说。在《元明清词》中,张秉戍选评了元好问、耶律楚材、白朴、卢挚、张弘范、刘因、赵孟俯、腾宾、虞集、张翥、宋褧、倪瓒、萨都刺等词人的作品,所涉题材非常宽广,既有“怀古慨今,叙说凄清”,又有“忆旧伤别,抒写感愤”,更有“托物言志,寄托悲怀”,如段克己、段成己兄弟,金末进士,入元不仕,拒做贰臣,诗词多“狂诗颠酒”。
“作词之难,难于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中。大约空疏者作词,无意肖曲,而不觉仿佛乎曲。有学问人作词,尽力避诗,而究竟不离于诗,一则苦于习久难变,一则迫于舍此实无也。”正如《窥词管见》开卷所云,一时代的各种文体之间,往往存在彼此影响的互动关系,不同时代文体互动的特征亦有差异。“承诗启曲者,词也”(沈谦《填词杂说》)。“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胡适《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元词诗化、曲化,大凡个人怀抱、人际交往、游赏品物、社会百象皆可见诸词人笔下,许多词记俗事、写常情,未尝不是词体开放的积极尝试。元末词人倪瓒善用白描,赋词具有画意,寓典雅于清丽,一句“伤心莫问前朝事”“怅然孤啸”,既充满不堪回首的沉重,又“豪迈超逸”“悲壮风流,独有千古”,纵“南宋诸巨手为之亦无以过”(陈廷焯《大雅集》)也。
所谓词亡于明、明代无词,显然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它是对明词价值的全面否定,而这种“全面否定”又盖因明朝文人不能再凭诗词登科入第所生之抱怨。其实,“明词创作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贫瘠,九百余种词调虽无法与宋词之丰富性(宋词计人同调异名者有1490调<刘尊明、王兆鹏《唐宋词的定量分析》>)相媲美,却也足以呈现百花齐放、姹紫嫣紅的瑰丽风姿”(王靖懿、张仲谋《论明词用调对宋词的继承与新变》)。作为千年词史的一环,明词上承宋元之余绪,下开清词之中兴,虽有诸多弊端,然并非一无是处。就明词论明词,从明初的邵亨贞、刘基、杨基、高启、瞿佑、史鉴,到明中期的文征明、杨慎、吴承恩、李攀龙、徐渭、王世贞、王锡爵、汤显祖、俞彦,再到明后期的袁宏道、沈宜修、叶小鸾、王彦泓,一直到标志着明词的辉煌终结的陈子龙、王夫之、夏完淳、柳如是,等等。他们的词不仅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通过张秉戍选评的“元明清词”还证实了“词亡于明”或“明代无词”的论说是武断的、不可信的。“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明人张蜒在《诗余图谱·凡例》中首次把“豪放”“婉约”对举,“尚属首次,为后世词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批评范式”(赵银芳《金至明词“豪放”“婉约”接受述要》)。
“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而再振于我国初,大畅厥旨于乾嘉以还也。”正如清人陈廷悼《白雨斋词话》卷一所言,清“文字狱”残酷迫害了不少汉族文士,但有清一朝,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繁荣,统治者也有一些笼络人心的举措,学术文化有较大的发展,词坛也非常活跃,加之阳羡、浙西、常州等词派的迭兴,形成了清词的兴盛。在《元明清词》中,张秉戍首先选评了王夫之、屈大均、吴伟业、徐灿等代表人物的词作,“这时期的词仍是明词的继续”(马应荣《论元明清词及词的鉴赏》)。其中,王夫之著述甚多,诗、词、文皆工,有词集《鼓掉》《潇湘怨词》,“多写亡国之悲,即使是写景、咏物的词也无不包含故国之思,而且信笔所至,往往突破传统限制”;屈大均为“岭南三大家”之首,著有《道援堂词》《九歌草堂集》,“其词具有辛弃疾悲壮风格”;“闺秀工为词者,前则李易安,后则徐湘苹”(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女词人徐灿(字湘苹)“善属文,并精书画”,著有《拙政园诗余》三卷。“南宋以来,闺房之秀,(惟其)一人而已。(陈维崧《妇人集》)”
“古来一代文章事,自有风骚翰墨臣。(宋·姜特立《怀古》)”清词发展三百年,其间名家辈出,流派迭见。一是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把词和经、史等同”,内容丰富,风格多样。高佑记《湖海楼词序》说,阳羡词派“纵横变化,无美不臻,铜琶铁板,残月晓风,兼长并擅,其新警处,往往为古人所不经道,是为词学中绝唱”;二是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宗尚南宋,师法姜(夔)、张(炎),崇尚醇雅,标举清空”,顺应了康雍乾三朝“清真雅正”的衡文标准,奠定了清词“复兴”的基础;三是以张惠言为开创者的常州词派“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张惠言《词选》),进一步推尊词体,推动词学的全面发展。在《元明清词》中,张秉戍还选评了不为词派所左右的彭孙遹、曹贞吉、王士祯(禛)、顾贞观、纳兰性德和贺双卿(女词人)等著名词人的作品。我认为,仔细品读邓廷桢、林则徐、龚自珍、蒋春霖、王鹏运、文廷式、郑文焯、张景祁、况周颐、朱祖谋、王国维、梁鼎芬、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吴梅、秋瑾等晚晴词人的作品,掷地有声中,词人们对家国前途的忧虑及抵抗侵略的豪情更激发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