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胡守真教授
2021-05-17乔富东
乔富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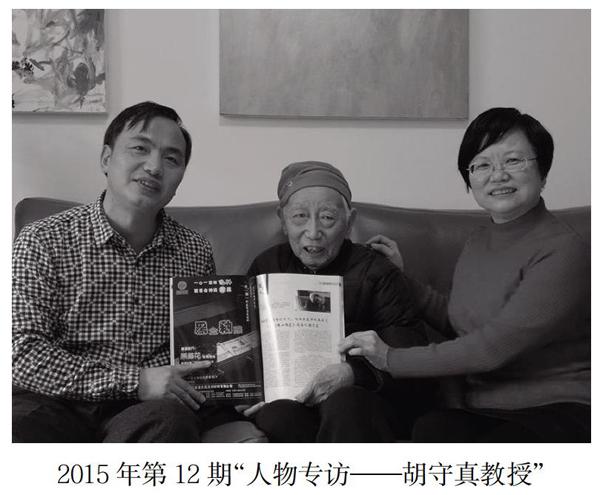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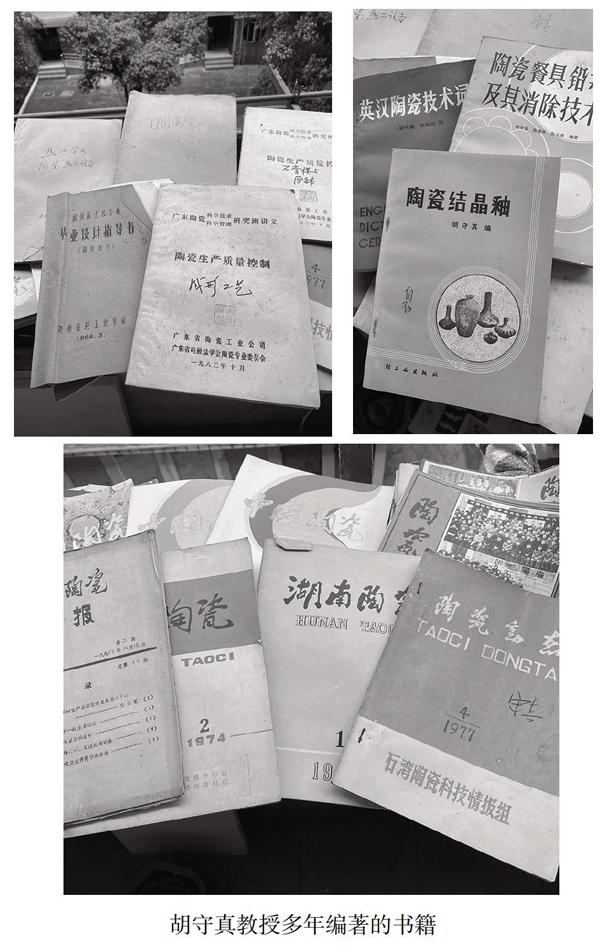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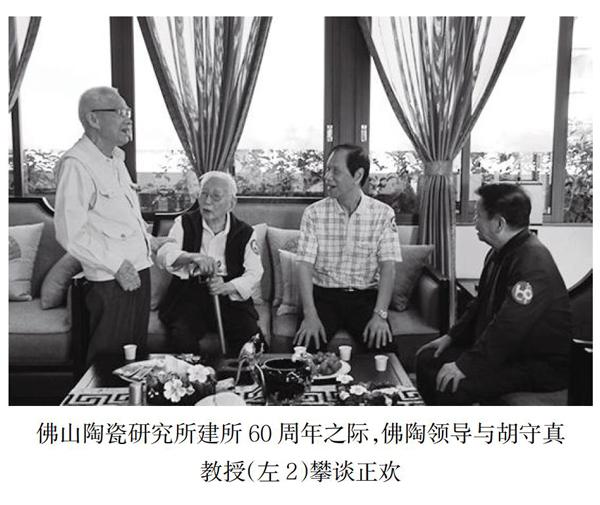
最早认识胡守真教授,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1989年,胡守真教授刚刚从广东省轻工学院退休。其时佛山建筑陶瓷发展如火如荼名扬天下。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亟需一本技术性的杂志期刊供技术人员进行交流。于是,在当时佛陶集团和佛山市陶瓷研究所领导的倡议下,胡守真教授、刘康时教授等,一起创刊发行了《佛山陶瓷》杂志。当时的杂志,还没有“广告收入”一说,从经济角度讲是纯粹的“亏本”买卖。
胡守真在日记中写到:“我想这事(办杂志)可以做,交谈十分仔细,从内容谈到每期要多少钱一本,等等。因为在校搞了《轻工教育》,我的英汉陶瓷词汇(掌握比较多)在校排版印刷十分熟悉,他(所长)拍板,每期(开办费用)伍仟元之内,这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杂志社的编辑经常跑到佛陶集团属下陶瓷厂找科技人员约稿。我当时在佛山建国陶瓷厂生产车间一线工作,在催稿的压力下时常把一线基层碰到的技术问题和解决方案写出来,通过杂志发表出来给科技人员分享;调入技术科之后,又经常接触工艺标准、产品标准制定之类的工作,也免不了要解决全国各地的产品售后服务碰到的问题;这些稿件发表后,许多读者来电话或者来信深入探讨,一时间成了“热点话题”。
一来二去,从“积极投稿作者”到“优秀作者”直到进入“编委”名单。
一年一度的年终“编委会”是少不了的保留节目,这时候,胡教授往往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们这些业余兼职编委畅所欲言,对杂志的改进提出意见,对第二年的行业形势作出预判,然后圈定一些题目,作为来年约稿的基调。
认识胡教授之后,就经常见到胡教授了。当然以前也经常“见”,可惜大家是陌路人,这种见就是“无视”下的擦肩而过。他往往是星期二、四、六从广州坐长途车过来佛山,然后再转到佛山石湾的公交车在“榴苑路”站下车,步行前往陶研所,下班亦是如此。我们往往是在下班的徒步走路的时候碰到,匆匆相互打个招呼。再有段时间,杂志走上正轨后胡教授只有星期四才过来看稿子。
胡教授给我的印象,夏天短袖、灰裤子、凉鞋,秋天一身中山装,冬天一顶鸭舌帽、一条厚实的围脖。只有两样东西四季不变:鼻梁上架的一副眼镜,右手一个不离手的简易绿色手挽袋;袋子里永远是几样东西:厚厚的一叠稿件、眼镜盒、老式的墨水笔。当然,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一头灰白的头发,最后变成了满头银发,但是一直非常浓密。
当时的佛山陶瓷,发展势头很猛,很多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应用到生产,所以有时候我们下班碰到,胡教授第一时间迎上来,拉住我的手,好像生怕我走掉。问起这些新的知识,我就得停下匆匆的脚步,从前往后一五一十地讲个清楚;胡教授一米六左右的身高,看到他仰望我的眼神,我知道那是一种对新知识的渴望,只得放下急着回家的打算,把问题耐心讲清楚。等进入这种状态,一不小心三十分钟过去,误了班车也是经常的事。
2012年,机缘巧合,我进入《佛山陶瓷》杂志社工作。之后,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主编和社长职务,和胡教授的接触一下子多了起来。
我们每逢中秋节、春节前,都会去老教授在广州的家拜访。往往一落座,教授给我们泡上一壶上好的茶,话题就止不住;聊一个小时是经常的事,超过二个小时刹不住车也是有的,中午找个僻静的茶餐厅之类,又延续了攀谈的时间。
在阳光下,点燃一支烟,品着好茶,听胡教授讲过去工作的故事,是一大享受。
例如,花大价钱引进国外进口设备,为了在装配安装之前搞清楚机器的结构和尺寸,三天三夜不睡觉,人工测绘,为完成“国产化”提供第一手资料;年轻的胡守真顺利完成任务后,连续酣睡十几个小时,一觉醒来,喝一碗皮蛋瘦肉粥,“那是真香啊!”。
又比如,他的学生中,有个学生做到广东省省长,见了面,是像学生时期直呼其名好?还是叫某省长好?最后斟酌,直呼其名显得唐突,叫省长我们又不是上下级工作关系,最合理的叫法是姓名加同志,既不显得陌生,其他不认识的人听见了也不显得特别,最关键两人亲切。
类似的故事一讲一箩筐,普通话和白话来回转换。
胡教授身上有两样品德我最佩服:其一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专业学习和追求精神,他的专业知识,永远在更新当中;有时候,他还会上下横跨40~50年,比较一些专业标准的变化情况,一些名词术语的变化沿革情况;熟悉他的人,称他是陶瓷工艺“活字典”。其二是知识分子的倔强和“实话实说”精神。很多大学生,一旦毕业进入社会,往往逐步丢弃专业,把精力花在处理和领导关系方面,或多或少会沾染“拍马屁”等习气,也会在行为习惯上“媚上”。在上世纪60年代,胡教授分配到省级机关工作,当时“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现象。老一辈知识分子碰到的问题是:如果作为外行的领导,在描述专业领域时候说了错误的“外行”话,你应该怎么办?胡教授的做法是——當面指出来!
为什么这么做?当面指出来,领导往往会“难堪”或者“下不来台”,但是脸红了,也记住错误了,下次就改了;如果不当面指出,领导在更大的场合讲错,就会给整个单位和集体“难看”甚至造成损失。胡教授讲述这些案例的时候,经常引得我们哄堂大笑,直到笑出眼泪。这些领导,往往初时对胡教授讨厌甚至惧怕,后来体会到他的用心,又感激和感谢,最后成了真心朋友。
后来有堂堂清华、北大校长,电视直播的时候在全国人民面前念错字词,引发舆论轩然大波的故事,印证了真正爱护领导,千万要当面指出错误,不可一味地“媚上”。
有段时期(大约2015年左右),媒体上争论紫砂煲“究竟是用天然的矿泥制造好还是用普通泥加了铁红色料制造的好?”。大体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天然的好”观点,主要是讲天然矿泥制造的紫砂煲,历史如何悠久,制作工艺如何手工,甚至可以入“非遗”保护,对人的身体有百益而无一害。一种是“阴谋论”,添加了铁红、锰红色料的泥料,一样可以制作紫砂煲,而“天然”论者揭露市场上90%是添加颜料的现代化产品,对人体有害,其阴谋是不择手段争夺市场,搞得消费者“人心惶惶”,不敢再买紫砂煲,最后大家都没有的做。一时间,狼烟四起,争论纷纷,煞是热闹。胡守真教授特地给杂志社写来一封信,讲述他的观点:所有的争论,不能带任何感情色彩,都应该回归到日用陶瓷的产品标准上来,最重点的就是“有害金属溶出量”!天然紫砂泥越来越少,普通瓷泥添加色料是大势所趋,但是归根到底,无论如何都要符合食品日用瓷的产品标准。我看了胡教授的手写两页纸,观点鲜明,论据充分,提纲挈领;如拨云见日,似扬汤止沸。两派争来争去,原来都没有争论到点子上啊!端的是——黄忠上马,廉颇领兵,宝刀不老,痛快痛快!
《佛山陶瓷》杂志新入职的编辑,有一段时期,都要拜胡教授为师,进行科技稿件编辑基本要领的培训。一篇科技论文,从题目到摘要、关键词、论点论据结论、参考资料,科技计量单位,英文字母大小写等等,胡教授几乎是耳提面命手把手地教。编辑人员实习两个月后独立工作审稿,稿件最后交给胡教授复审,往往也会审出不少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不是硬性规定的层面,而是关乎到科技和专业“素养”层面。这时候,我们体会到的,就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细心钻研、长期关注专业之后,建立的一种“直觉”。这些直觉是对专业有兴趣的、又在这个行业“浸润”足够长的年代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人才能有的高度。
我们做事做人往往讲:要严格要求,但是实际把关的人如果知识水平不够高,“严格”二字就成了空话。所以,要感谢以胡守真、刘康时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在《佛山陶瓷》创刊之初,就形成了对稿件和刊物严格把关的风格,并被一直传承下来。
胡教授在《佛山陶瓷》创刊30周年(2017年,时年88周岁)和佛山陶瓷研究所建所60周年大庆(2018年,时年90周岁),都积极要求参加,我们单位专门派车接送,老人家亲自到会;已届耄耋之年,我们一直担心老人家的身体,见面看到的胡守真教授,依然精神矍铄,满头银发,眼神如炬,记忆力惊人,很久不见的熟人直接喊出名字。
再往后,我们就微信沟通和视频接触多些。
进入八十五周岁之后的胡守真教授,给我的印象,一不“忌病”,二不“避死”。经常分享一些战胜疾病、“久病成医”的辩证治疗经验。有一段时间,我们“静默”了很久没有联系,突然接到胡教授的视频说:你知不知道?前一段时间,我“死”过了!民间的说法,死过复活的人,往往“骗”过阎王爷,能再活很长时间,我们两同时哈哈大笑。然后说他住院抢救的故事,心中坦然面对,死神不收留,又能“活蹦乱跳”下地活动了。
長寿而有质量的生活,是我们的追求,胡教授是我们的榜样。
2021年三月八日上午,胡教授的亲属发微信,老人家在医院抢救并下达了病危通知;到了下午三点五十分,胡教授在医院病逝。
人到中年,参加过很多次葬礼,眼泪已经不那么容易流了,但我还是在接到消息后为胡教授的离去流下了眼泪:我们又少了一位亦父亦师型的长辈,能在嘻嘻哈哈、谈笑风生之间,受到教育,明白世间的道理。
在胡教授以九十四岁高龄驾鹤归去之际,送一幅挽联表达我们的敬意:
传道受业解惑桃李满天下师生来往须抱朴,
约稿编辑付印杂志誉佛山科技交流宜守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