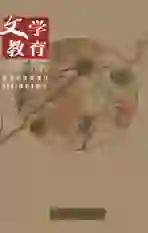布罗茨基《小于一》美学初探
2021-05-08毛欣然
内容摘要:《小于一》是布罗茨基自传和诗学批评性的散文集,文章分析了布罗茨基在《小于一》追求的美学主张,即死亡美学和孤独美学。诗人通过死亡探讨虚无,只有到死,诗人才会盖棺论定,诗人在死亡中看到自己的自画像。在高压政治中,诗人的自保能力让位给了美学,成为疏离于同代人的时代的孤儿。
关键词:布罗茨基 《小于一》 死亡美学 孤独美学
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是苏俄裔美籍犹太诗人。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小于一》是一本基于文学批评的散文集,他批评了许多俄国和外国的诗人,并且把“我”鲜明地融入其中。2014年《小于一》的权威译本问世,获得了许多奖项,轰动了中国文学界。《小于一》是布罗茨基诗歌的延续,如同散文是诗歌的延续。“小于一”这个标题的含义,根据布罗茨基在自传性散文《小于一》中自述:
时间的流逝并不怎么影响那个实体。获得低分,操作一台铣床,在审讯时遭毒打,或在教室里大谈卡利马科斯,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你长大成人,你不能不感到有点惊骇。一个孩子对父母控制他感到不满,与一个成年人面对责任时的恐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你不是这些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你也许是小于“一”个。(《小于一》)
这就是篇名“小于一”的出处,在一个集权和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下生存的人,不是完整的人,因为人性是被剥夺的。
很久以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最不公正的国家。那国家被一群生物统治,这群生物用所有的人类标准来看,应被视为退化的生物……那文明已不存在了。(《小于一》)
这就是作品的背景基调和布罗茨基的心态基础——不公正,压抑的政治环境。
“美学”是由德国鲍姆嘉通提出的,他把“美学”定义为感性认知的学科。美学(Aesthetics)一詞在古希腊的意思是“人的感觉”。所以美学是研究人的情感、感觉的。人的种种感觉,最终抵达的是情感和心理。本文主要从死亡和孤独两个方面分析布罗茨基在《小于一》中展现的美学追求。
一.死亡美学
“美学对于死亡的探讨,以呈现在心灵中的死亡意象作为本质对象,以体验与想象的心理功能作为主要的认识方法和理解手段。”①也就是说,死亡美学关照的是以想象为途径的对于死亡的情感和感觉,以及相关的哲学思考。洛特曼说:“也许,除布罗茨基外,再无任何一位诗人如此沉浸于对虚无——死亡的思虑。”②布罗茨基对于死亡美学的追求,在《小于一》里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生命的定论——死亡
林语堂曾说:“当我们承认人类不免一死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时间消逝的时候,诗歌和哲学才会产生出来。”(第三章·三《论不免一死》林语堂《论生活的艺术》湖南文艺书本社2018年)通过死亡,我们会反思生命,进行哲学思考,诗歌也如此产生。
我一直都无法辨别任何地标,更别说浮标了。如果有任何像地标的东西,那也是我自己无法承认的东西——死亡。(《小于一》)
只有死亡才能成为我辨别的标志,人生到盖棺才能论定?布罗茨基在《小于一》中全篇使用反讽,而自己也是反讽对象之一。获得文学上最高的奖项,从一般人看来,文学必然能够代表布罗茨基,而他本人并不为此自豪。生命是流动的、无定形的,变化当中必然无法辨别或标识什么。只有死亡,生命到了尽头才会停止流动、成形,才会成为定论。死亡是终极的。
因为死亡作为一个主题,永远产生一幅自画像。(《在但丁的阴影下》)
死亡作为布罗茨基喜欢的母题,并非以恐怖的形态出现,布罗茨基喜欢谈论这个话题,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畏惧,亦没有对生的留恋。布罗茨基全程以理性的态度谈论这个话题,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喜爱的情感。诗人晚期的作品,尤其是加入了亲人逝世因素的诗集,确实体现了诗人定居的气息。诗和哲学是具有相通之处的。对于死亡主题的描写,体现了诗人对于自己全面的总结。
记忆,我想,是一个替代物,替代我们在愉快的进化过程中永远失去的那条尾巴……你记得愈多,也许你就愈接近死亡。(《小于一》)
记忆和死亡,人出生是白纸,经过了各种事情的,就走向了死亡。死亡不可避免,常人往往不愿意提及,哲人却喜欢思考它。“诗人的作品和诗人一样,也有其生命。诗的生命有两种,一种是外部生命,即一首诗的留存于世;一种是内部生命,即一首诗从开头一行到最后一行的延续。因此,阅读一个诗人的作品,我们就是参与这个诗人的死亡,或是其作品的死亡。”③
“诗人之死”这个说法听上去总是有点儿比“诗人之生”更具体。也许这是因为“生”和“诗人”作为词语,其正面含混性几乎是同义的。而“死”——即便作为一个词——则差不多如同诗人自己的作品例如一首诗那样地明确。不管一件艺术作品包含什么,它都会奔向结局,而结局确定诗的形式,并拒绝复活。在一首诗的最后一行之后,接下去便什么也没有了,除了文学批评。因此,当我们读一个诗人,我们便参与他或他的作品的死亡。(《文明的孩子》)
死亡是明确的。生很含混,死亡却是陈安落定的必然。哀歌所描写的对象不是现在,而是往西,这是一种时间问题,逝去后以死亡作为形式所呈现出来的生活。死亡是肉体上的阴阳相隔,而精神上,亦具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死亡和结局具有相似性,死亡是诗和诗人的结局。
有人通过他的诗歌,通过他生命的行为和通过他死亡的质量来铸造伟大的散文。(《文明的孩子》)
死亡的质量也就是诗的质量。生有和意义有时是通过死来传达的,通过死亡的虚无而达到诗歌生命的的永存。死是人不可避免的终极主题,死亡美学出于对人类生存的关注,死亡美学更关注诗意和审美的永恒。对于布罗茨基来说,死亡不是终结,而是新生的开始。
2.诗人的自画像——哀歌
布罗茨基喜欢用题材作为诗题,他以“哀歌”为题的诗有很多首。“哀歌”这种诗歌题材源于古希腊的挽歌。其特点是篇幅和句式较长,节奏韵律缓慢,情感表答为顾名思义以悲哀、凄婉为主。王尔德认为“在欢乐和欢笑的后面,或许还有粗暴、生硬和无感觉的东西,但在悲哀之后始终是只有悲哀。痛苦与欢乐不同,它不戴面具”④。
我那时还年轻,特别热衷于作为一种体裁的哀歌,尤其是自己周围没人死,没机会写。所以我怀着也许比对其他任何东西更大的热情来读哀歌,而我常常想,该体裁最有趣的特征,乃是作者们都不经意地试图画自画像——几乎每一首“悼诗”都充满(或玷满)这种自画像成分。(《取悦一个影子》)
布罗茨基认为为别人所写的哀歌其实是诗人的自画像,通过盖棺论定来评价一个人来表达出作者本人的各种思想。哀歌也是一种死亡主题,也是诗人的自画像。“哀歌教会他的是‘长歌当哭,必在痛定之后‘的感觉,他总是将创伤对象化。”⑤布罗茨基把哀歌成为诗歌最充分发展的体裁,哀歌是诗歌的地标,任何悼亡诗,都包含一个自画像的因素。如果哀悼的对象碰巧是一位与作者具有无论是真实还是想象的纽带关系的同行作家,且这种关系太强烈,使得作者难以抵挡认同哀悼对象的诱惑。
我们了解更多的是作者和作者对自己可能的消亡的态度,而不是实际发生在被哀悼对象身上的事情。(《一首诗的脚注》)
当哀悼对象是一位作家,那么哀歌自画像的性质就更明确了,像诱惑一样使作者难以抵挡。作者在为诗人写哀歌时,其实所描绘和表达的是自己的思想,或者说为自己写哀歌。
诗人之死不只是一种人类的丧失。最重要的是,它是语言本身的一出戏剧:也即语言经验不足以表达存在经验的戏剧。
除了具体的、已死去的里尔克之外,诗中还出现了一个形象(或理念),也即一个“绝对的里尔克”,他已停止作为空间中的一个肉体,变成永恒中的一个灵魂。这种移动是绝对的、极大化的移动。诗中女主人公对这个绝对对象、这个灵魂所怀的感情——也即爱——也是绝对的。此外,对这爱的表达方式也是绝对的:极大化的无私和极大化的坦率。这一切只会创造一种诗学措辞的极大化张力。(《一首诗的脚注》)
死去后变成永恒的灵魂,变成绝对化,极大化的诗学张力。死是生的虚无,是精神的绝对对象,它代表了一种灵魂的美和升华。在诗人的世界里,死亡象征美与自由,它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达到了极大化的美的张力。布罗茨基崇拜语言,语言本身高于诗人的生命。
还有——除了那被抛弃感——出于一种内疚感:我活着,而他——更好的人——却死了。但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哪怕是异性诗人)的爱并不是朱丽叶对罗密欧的爱:悲剧不在于没有他存在是不可想象的,而恰恰在于这样的存在是可想象的。这种设想的结果是,作者对她自己也即仍活着的人的态度,就更无情,更不妥协。(《一首诗的脚注》)
更好的人死去了,不如他的却活着,诗人的爱死去了,这样的她活的态度更无情。爱人的死使他更坚定不妥协,内疚感成为了她战斗的力量。所以诗人间的爱超越普通的爱情,比死亡更可怕的是要坚强地、无情地活着,担负起两个人的使命。
为她有某种先验性的悲剧调子,有某种隐藏的——在一首诗中——哀号。
极度的绝望和疏离共冶一炉。……因为一个人的去世排除了任何适当反应的可能性。(难道艺术总的来说不正是这种难以获得的情绪的替代物吗?尤其是诗歌艺术?而如果是这样,则难道“诗人之死”这一诗歌体裁不是某种合乎逻辑的神化和诗歌的目的吗,也即在因的祭坛上献祭果?)……疏离既是这首诗的方法,又是这首诗的题材。(《一首诗的脚注》)
有时候悲剧是先验的,必然的,西方文学传统中悲剧是最崇高的。哀歌,尤其是对于诗人的哀歌是具有神化的,是诗歌的目的。而其表达的方法是疏离,而疏离、死亡、悲哀本身又是题材。
他的生,以及他的死,是这文明的一个结果。诗人的伦理态度,事实上还有诗人的性情,都是由诗人的美学决定和塑造的。这就是为什么诗人总是发现自己始终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他们的死亡率则表明那现实把它自己与文明隔开的距离。(《文明的孩子》)
美学决定和塑造了诗人的伦理态度和性情,所以诗人是孤独的。诗人们为了维护心中最高的美学,奋起反抗,步入死亡,他们与文明隔开。所谓的文明指的是专制制度下用来愚民的东西。
布罗茨基所崇尚的美学,是超越生命的,为了美学,诗人放弃自我保存。他的美学与政治紧密相关,在对于超越生死的美学的赞美的同时,是对俄国政治高压的反抗。铁腕政治被作者描写得十分丑恶,反抗诗人则是被作者盛赞的英雄。
英雄、悲剧、崇高——都是西方美学的传统内容,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布罗茨基和他盛赞的诗人就是这样的时代英雄。死亡、悲剧、哀号、绝望、疏离都成为英雄必须背负的责任。
里尔克之死便会带有一种抽象性质,而茨维塔耶娃纯粹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会反抗它。结果,死亡便成为一个猜测的对象,恰如里尔克的生活是猜测的对象。也就是说,“你的死”这说法最终只会像“你的生”一样不适用和无意义。但是茨维塔耶娃走得要稍微远些,而在这里,我们来到了我们可称为“向上升的疏离”和茨维塔耶娃的告白的起始:
我早就把生死加上引号
如同已知道是空洞的闲话/谣言。
对作者来说,“生”与“死”似乎是语言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尝试适应这场灾难,更有甚者,尝试以大致这样一些话来贬低这场灾难,也即它无非是“已知道是空洞的闲话/谣言”。(《一首诗的脚注》)
她乞灵于死亡,以死亡来作为这种或那种感情紧张的解决办法,现在死亡变得太真实了,使得任何感情都显得微不足道。它从修辞变成无辞可修。(《哀泣的缪斯》)
死亡有时候会被诗人作为修辞运用,但是如果真正的死亡来临,而且是大量的死亡,修辞变得毫无意义。
作为一个主题,死亡是诗人伦理的绝佳试金石。这种“纪念”体裁常常被用于行使自怜或作形而上学之旅,隐含生者下意识地觉得自己优越于死者,大多数人(生者)优越于少数人(死者)。阿赫玛托娃完全不是这样。她使她的死者特殊化而不是普遍化。(《哀泣的繆斯》)
生者优于死者吗?从求生者的角度是这样的,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一般人乐生恶死。然而,如果从更高的视角俯察人类,静观所有生与死,的道德结论未必如此。生者不必然优于死者。这是从哲学高度,上帝视角观察得到的结论。诗人超越世俗,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所以对于诗人来说,死比生更有价值。
二.孤独美学
布罗茨基敢于打破传统,对于传统,他当然有继承,但是对于常人毫无怀疑的传统、权威,布罗茨基都是敢于以自己的眼光重新审视,作出自己的判断,并且打破他所认为不好的传统。
结果是这样一种效应,也即一个声音愈是清晰,听上去就愈是不和谐。没有合唱团细化于是这种美学孤立获得了物理维度。当一个人创造了自己的世界,他便成为一个陌生的身体,所有的法律都针对他:重力、压缩、排斥、歼灭。(《文明的孩子》)
真理、真知往往曲高和寡,先知是孤独的,结局也往往悲惨。如果一个人接近了真理和先知,他可能遭受政治迫害。布罗茨基对于孤独的崇拜源于童年经历和政治环境,作为犹太后裔,布罗茨基从小处处受到歧视——不能拥有一般人的待遇,即使优秀也被剥夺应有的权利。“压迫——反抗”的模式在布罗茨基身上完美体现,种族歧视和独裁政治塑造了时时处处反讽的《小于一》。布罗茨基很孤独,他没有在孤独中死亡,而是在孤独中爆发。
他那自我保存的本能,早已让位给他的美学。是曼德尔施塔姆诗歌中那巨大的抒情张力使他远离同代人,并使他成为他的时代的孤儿——“全苏联规模上恶无家可归状态”。(《文明的孩子》)
诗人从孤立中获得了自我,然而却成了政治和法律的靶子,布罗茨基本人就是如此。但是诗人没有被打倒,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孤独。为了美学而孤独,诗歌与美学高于自保,甚至高于生命和自由。美学是诗人的生产方式和最高追求,是诗人的信仰。曼德尔施塔姆如此,布罗茨基亦然。
他不属于任何“群”:加勒比海没有什么群,除了鱼群。你会情不自禁要把他称为形而上学的现实主义者,但话说回来,现实主义本来就是形而上学的,相反亦然。(《涛声》)
布罗茨基所推崇、崇拜、赞美的诗人是孤独的,不合群,他们是孤独的英雄,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真理维护者,孤独、魅力、崇高……寂寞。具体而言,《小于一》中的孤独美学体现在对流亡主题的抒写和对诗人寡妇的评论中。
1.流亡的孤独
“流亡”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是很多人所向往的自由,而布罗茨基却并非主动追求,1972年他被当局驱逐出境,他给勃列日涅夫写信:“我虽然失去了苏联国籍,但我仍是一名苏联诗人。我相信我会归来,诗人永远会归来的,不是他本人归来,就是他的作品归来。”流亡、孤独、困苦成了布罗茨基的一部分,深深侵入他的作品。
他们的个性是他们流亡生活的原因之一,而流亡又加强、深化了他们的个性;他们在与自己诗中“独自的主人公”一同捍卫诗的价值和诗人的尊严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他们鲜明的诗歌特色。⑥
“布罗茨基流亡,首先要面对的是文化认同危机和创作的失语状态,虽然后来布罗茨基赢得了西方世界的普遍认可和尊重,但面对不同的文化环境,确立自己的写作坐标并一以贯之地保持自己的独特性是有难度的。”⑦所以布罗茨基的作品中呈现出浓重的孤独意味。
马克思的名言“存在决定意识”,觉得只有在意识学习掌握疏离的艺术时,这个说法才是真的;之后,意识便独立自主,并可以决定和忽略存在。(《小于一》)
布罗茨基高度推崇诗歌,又很崇拜语言,诗歌是至高无上的语言形式。之歌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它拥有自身的意识,遗世独立的自主意识,甚至可以忽略存在。“文学特别是诗歌对布罗茨基而言是与生命融为一体的。”⑧高境界的诗人都把诗歌与自身的生命结合,自身的流亡也是诗歌独立的标志。布罗茨基的流亡在形而上的层次上是主动的,疏离使得意识能够脱离或者说忽略存在而独立自主,这就是疏离的作用,所以作者热衷于逃跑,自我疏离,流亡,原理祖国的独裁政治,在逃亡和自我流放中找到自我价值。
2.寡妇的孤独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是俄罗斯诗人奥斯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然后有四十二年时间成为他的寡妇”。曼德尔施塔姆是布罗茨基非常敬重的诗人,他甚至认为对方比自己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他并没有想要如此堂皇,也不是仅仅要报复那个制度。
实际上,她的身份是由文化、由文化最好的产物塑造的:她丈夫的诗作。她试图保存的,并不是关于他的记忆,而是这些诗作。她在四十二年间成为的,并不是他的寡妇,而是这些诗的寡妇。(《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1899—1980):讣文》)
称为诗的寡妇,诗对于这些诗人来说超过生命、超过爱情,是最重要的。在生存都称为问题的时代,诗人为了使诗保存下来,使用背诵的方法,这些诗真可谓是诗人的生命了。爱情中的殉情很让人感动,用自己的后半生殉了代表这份爱的诗,更使爱情和生命都获得了超越,进入了更高的层次。
她是文化的寡妇,而我想,她最后爱她丈夫远甚于她最初嫁给他。(《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1899—1980):讣文》)
寡妇,当然是孤独的,但却不是陷入孤独丧失自我,而是在孤独中成为了诗。丈夫死后,丈夫的诗成了自己的记忆,化成了自己的一部分,死亡和孤独使之升华。
诗歌是最民主的艺术——它永远从零开始。在某种意义上,诗人确实像一只鸟儿,无论栖息在什么树枝上,它都可以鸣啭,希望有听众,哪怕听众只是一群树叶。(《涛声》)
独裁政治是不民主的,即使表面宣扬,而是诗歌才是最民主的。“《诗》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入鸟乎!”(《大学章句》)⑨孔子从鸟的有所居止联想到人的安身立命之所。鸟栖息在树枝上,而儒者要在仁、敬、孝、慈、信等美德上棲身。布罗茨基把诗人比作鸟儿,诗人有自己的追求,即使代价是孤独,也不会放弃。发声者都希望有听众,中国古人追求“知音”,作者希望有听众,如同雅乐阳春白雪,如同先知哲人般的诗人也不可能有广泛的听众。诗人渴望发声,渴望把心声传递给众人,但是如果不能实现,诗人宁愿孤独。
沃尔科特既不是传统主义者,也不是现代主义者。任何现有的主义和随之而来的主义者都不适合他。他不属于任何“群”。(《涛声》)
最高等级的诗人必然是孤独的,离群索居,不能为外在各种标签所限制。
这行诗在听觉上和地形学上都从抽象地理的“svet”向上飞,飞向那简短、呜咽般的“krai”(边缘,王国):世界的边缘,一般的边缘,朝向天上,朝向天堂。……这行诗以结尾部“s novym krovom”(新避难所快乐)告终,既是语音的,又是语义的,因为“krovom”的语音实质与“godom”的语音实质几乎相同。……这个词被放置在太高处了。它作为世界边缘的一个避难所的意义和作为一个可以回去的家——一个庇护所——的意义,与“krov”交织在一起,而“krov”意思是天堂:地球的普世天堂和个人的天堂,灵魂的最后避难所。(《一首诗的脚注》)
布罗茨基在对玛琳娜·茨维塔耶娃《新年贺信》“新年快乐——世界/光——边缘/王国——避难所!”的赏析中从语言学、听觉、视觉等多方面阐释,诗歌营造出向上飞,朝向天堂的意境。词语本身被放置在太高之处,成为了人类灵魂最后的避难所。词语和意象都指向孤独,脱离世俗,飞到一个极高的所在。虽然是在分析别人的诗句,布罗茨基本人心中也希望通过孤独到达高处的灵魂天堂。
布罗茨基敏感又特立独行,一生坎坷经历各种苦难和迫害,却从未放弃对诗和美学的追求,他用反讽构成的《小于一》中孤独地追寻人类存在的哲学与诗意。虽然处处表现对死亡的赞美与热忱,但诗人绝非是悲观的,他以死亡的永恒填补生存的空虚,终究成就了实实在在的“虚无”,并在虚无中找寻人类自己丧失的灵魂。
注 释
①颜翔林:《死亡美学》,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Гордин Я.А..Иосиф Бродский и мир[M].Москва: Звезда,2000.15.
③列夫·洛謝夫著,刘文飞译《布罗茨基传》,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
④(英)奥斯卡王尔德;孙宜学译:《狱中记》,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14页。
⑤张驰:《约瑟夫·布罗茨基诗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第22页。
⑥张驰:《约瑟夫·布罗茨基诗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
⑦毛欣然:《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学观和美学观浅议——从散文集〈小于一〉谈起》,《出版广角》2018年第24期。
⑧毛欣然:《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学观和美学观浅议——从散文集〈小于一〉谈起》,《出版广角》2018年第24期。
⑨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
基金项目:2019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资助项目(SXJZX2019-001).
(作者介绍:毛欣然,博士,现任职于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