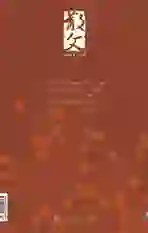我的夏德尔,我的泽库
2021-05-07辛茜
辛茜
到泽库
2019年7月4 日,张青松紧紧握住泽库县司法局让忠局长有力的大手, 接受了藏族小伙洛桑扎西献给他的白色哈达。从此, 张青松这位“全国律师界十大新闻人物”,成了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的一名“1+1法律援助者”。
从西宁到泽库驾车四小时, 让忠局长带着他们到达泽库县时,已是晚上九点多。灯光下,闪烁的泽库县城迷离宁静,张青松有点诧异,有些遗憾。这么美丽的地方,怎么能说是到了边远贫困地区? 回去了怎么向组织、向父老乡亲们交代?
一夜过后,缺氧的痛楚向他袭来,他浑身无力,头晕头疼恶心。吃红景天、止疼药,不洗澡,各种办法都用过了,还是难受。他才知,泽库实在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地方。
“泽库”藏语称“夏德尔”,意为“鸟冻得发抖的地方”,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贫困程度最高、最艰苦的地方,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三千五百米以上。早年,为泽库县政府选址的一班人马来到泽库,放眼远眺,极目细看,只见满天飞雪,白茫茫一片,只有一块地方平坦且不见积雪, 便毫不犹豫地选定此处为泽曲镇,建设中才反应过来,之所以无雪,是因为这里是风口,雪被大风吹走了。
张青松发现,泽库这个地方,既神秘又简单。这里一年有四季,每天也有四季;这里看不到庄稼地,处处是草原;这里的人大多是藏族,不会说汉语。站在广阔深远的天地中,看着那些善良纯朴的脸,很难想象这里的人和法律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这里也是世俗人间:包工头们欠着民工工钱;离婚的藏族夫妇为争夺项链上的红珊瑚打着马拉松官司; 一个牧民酒后捅了别人一刀; 几个小伙子结伙偷了别人的牦牛和摩托车……
总算有了审听案子的机会。法官是藏族,被告是藏族,辩护律师是藏族,张青松根本听不懂,像傻子一样,像看了一场没有字幕的外国片。要想办案子必须学藏语,他暗下决心,刻苦努力。可惜一段时间后,还是只会说你好“逮猫”、再见“逮猫”、谢谢“尕真切”。随后,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办案并不重要,重点是得留下办案的人:培养离不开故土的律师, 而自己是来不及学藏语的,也不一定能留下。于是,张青松请求搬到草原上住。
家人
洛桑扎西一家对张青松的热情, 远远超过了对洛桑扎西的。几天后,张青松在家里比洛桑扎西还舒服自在, 每天早晨七点半起床,洗漱之后骑马到大帐篷里吃早餐。早餐一般是酥油茶、糌粑、馍馍。他吃的时候,孩子们都瞪着眼看他,一直到他吃完为止。然后他再骑马回到自己的小帐篷,驾车大约四十分钟到司法局上班。下午五点半下班后开车回到大帐篷, 帮助家里照看牦牛。真实的情况是:牦牛不需要照料,既不上访也不闹事,每天都情绪稳定地吃草。但是他每天都要去关心下,摸摸牦牛的头,摸摸牦牛的尾, 主要是担心家里人说他只吃饭不干活, 主要是呆呆地看著夕阳下的草原,在绚丽的色彩下,如何变成一幅油画,再变成一幅版画、铅画。
来之前, 张青松就听说过黑帐篷与白帐篷的故事。但是, 他住的就是一顶白帐篷,这完全限制了他的想象力。实际上,他更愿意住传统的黑帐篷。黑帐篷用黑牦牛毛搓绳编织而成,纯手工,工艺复杂,冬暖夏凉。以前, 藏地牧民大多住在这种帐篷里。后来,有些厂家抓住商机,用结实耐用的白帆布生产帐篷,实惠方便,大多牧民就不再用手工制作黑帐篷了。但是,黑帐篷对藏地牧民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 所以很多牧民还是以家中拥有一顶黑帐篷而骄傲。
黑帐篷里有一个土质的炉子, 燃料为牦牛粪。除了取暖,炉子还起着分界线的作用,晚上睡觉时女的睡左侧,男的睡右侧。
家里最疼张青松的是阿妈。她六十九岁,一生磕了一百万个头,现在还能直腿弯腰触摸地面。阿妈有八个孩子,加上孙辈、重孙辈约三十八人, 她老人家好像也算不清楚。家中最年长的是阿姐, 是阿妈的姐姐,全家人都跟着阿妈称呼。藏历六月十七阿姐的八十大寿, 全家人正全力以赴准备这个盛大聚会,张青松更是期待万分。阿妈说, 张青松来他们家就是她的第九个孩子,所以她的子孙们就都叫他大哥。张青松还有一个藏语老师名叫夏吾昂措, 至今没搞清是哪一个弟兄的孩子,虽然只有九岁,但藏语特别棒,只是讲课不太认真。张青松买了好多零食给她, 她还是漫不经心地多数让他自习。张青松的体育老师叫夏吾措吉,是三妹妹的孩子,专门教他跳锅庄,学费是一大包糖。夏吾措吉比夏吾昂措认真,不厌其烦地给他示范动作, 而且从来不嫌他笨。家里力大无穷的是二哥彭措,没上过学,却能帮助活佛整理讲义,还出版过个人诗集。二哥不会汉语,却对张青松讲了很多话,应该是些很深奥的佛学理论。自从张青松不请自来加入这个大家庭, 大哥的地位明显受损,只能屈居第二。大哥是宁玛派僧侣,从小出家,终身不娶,现在正潜心研究藏医。
阿姐的八十大寿
藏历六月十七日(公历7月19日)是阿姐的八十大寿。阿姐过寿的藏服,同样靠手工缝制。承担这项工作的是四哥和夏吾才让,为此,张青松完全被藏族男人的细腻勤劳感动。而即使这样,藏族女人的任劳任怨、辛劳勤快更让他惊叹,简直无法形容。但针线活是男人的事,她们绝对不做。
阿姐爱美,对她的新衣服非常期待。如果给她拍照片, 她总是朝张青松挥挥手:“等等吧! 等穿上新藏服。”
此后,宾客们陆续到达。谁来得早谁最诚心, 福气也最大。每个宾客除了赠送礼物,还要伴以歌舞。同时,阿姐要回赠礼物,家人们也要伴以歌舞。阿姐的回礼是一碗花生。一碗又一碗。从晚上十二点到第二天凌晨,阿姐回了三百多碗花生,说明来过三百多位客人。客人有熟悉的,也有不太熟悉的。
黑帐篷是庆典的中心。盛装的阿姐像女王,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地望着暗色中的吉博日神山。礼后, 客人们陆续进大帐入座,喝茶、饮酒、吃肉、聊天、唱歌、跳舞……笑声不断, 歌声不断, 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
夏吾多杰是唐德村最受欢迎的年轻人之一, 他一本正经地对张青松说:“如果你认为我们天天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你就错了。其实藏族人本来不喝酒,当年文成公主把酒和酿酒技术带到藏区, 只告诉我们酒好喝,却忘了告诉我们喝多少,所以我们不按斤喝,而是按天喝,高手可以连续喝七八天。后来,我们才知那种感觉叫‘醉。‘醉不好,所以现在多数藏族人不喝酒。当然,重大喜事另当别论。吃肉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按传统,每月有八天绝对不吃肉,藏历四月整月不吃肉,平时尽量少吃肉,不是不爱吃,其实是舍不得吃。吃肉只能吃牛羊肉,不能吃小动物的肉……众生平等,不能杀生;人要生存就要吃东西,高原上除了肉没有什么吃的,怎么办? 尽量少杀生。一头牦牛可以让很多人吃饱,因为它大;很多条鱼才能让一个人果腹,因为它们小。”
夏吾多杰的话让张青松长了见识,连连点头。难怪, 平时藏族的主食主要是糌粑。如果你是一个好人,女主人会在你的碗里放很大一块酥油,加上奶茶。黄澄澄的一层酥油漂在奶茶上,喝上一会儿后,把青稞面放进碗里,用无名指搅拌,揉捏成团做成糌粑。对于长期吃糌粑的藏族人来说,吃完糌粑后,盛糌粑的碗要干净得如同新碗,如果碗里还有糌粑残渣,要用舌头舔干净,否则会被视为对食物的不敬。开始,张青松很习惯。但有一天,他突然想起,小时候在老家山东农村, 吃过面糊糊后不是也一样舔碗的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也就表现得从容、坦然了。阿姐、阿妈看到后很是满意。
当然,八十大寿这样的庆典,肉是充足的,酒是管够的。
法会和赛马
有一天回家,发现少了两顶帐篷,其中包括自己住的那顶白帐篷。张青松心里一震,以为家里嫌弃他,嫌他领来了太多陌生男女, 所以把帐篷藏起来了。因为前段时间,有很多朋友假借看望他,实则为了旅游常来泽库,而他在激动之余,又常常忍不住带朋友们来帐篷小住,吃家里的肉、糌粑、酸奶,欣赏家里的牦牛和美景。
经过小心翼翼地求证, 才知帐篷被移到法会和赛马会去了。
法会,就是大家聚到一起听活佛讲经、念经。有的活佛学问很深,一讲讲好几天,所以就要把自家帐篷迁到讲经的地方住下来听。活佛用藏语讲经时,不明觉厉的声音不绝如缕,使人震颤。张青松曾苦苦央求一位听了三天法会的人给他说说活佛都讲了些什么,那人沉思片刻:“活佛说,要孝敬父母,不要老看手机。”
泽库的马叫河曲马, 中国三大名马之一。藏地牧人家中都养马,张青松家就有四匹,主要用于比赛,现在已经很少有人骑马放牛放羊,取而代之的是摩托。赛马分为部落赛、村赛、乡镇赛等等,就像内地的足球比赛,一言不合就来一场。乡镇举办的赛马活动比较隆重,配有歌舞、拔河、摔跤,一搞就是三天。
参赛的马以年满三岁最好, 骑手的体重必须超过五十公斤。阿姐送给他的赤兔马正好三岁,张青松的体重也符合条件,但遗憾的是,比赛过程中,如果骑手从马上掉下来不算成绩。所以,思前想后的张青松只能忍痛让别的骑手骑着他的赤兔马参赛。
赛马几乎吸引了全乡镇牧民, 司法局不失时机地带着他们进行普法教育。完全不用担心, 牧民们绝不会把普法书籍垫在屁股底下坐着看表演。藏族人对文字极其尊重, 凡是有字的纸一律不会坐在屁股底下,不管认识不认识。
拉雅死了
中秋节,泽库下了一场大雪。还不到三岁的拉雅被狼咬死了。按说, 这场雪不算大。第二天一早,草原就变得黄绿相间。山脉白雪连绵,与蓝天相映,清洁、美丽。
张青松想, 地毛角乎家的拉雅很可能是被美景吸引,独自走了出去,走得太远,远离了自家的草场,再也没有回来。被发现的时候,拉雅已经死了,身体左侧的肉被吃掉,露出了肋骨。
,露出了肋骨。一般来讲, 牦牛群里如果有一头壮硕的头牛,狼袭击牦牛的事件就不会发生,而且狼根本斗不过它。头牛,是牛群里最牛的公牛,对外震慑狼群,对内团结伙伴。高原上的野牦牛自由奔放、身体健壮、精力充沛,很受母牦牛的崇拜, 有些母牦牛会忍不住跟着其他野公牛私奔。头牛发现了就会和野牦牛打一架, 以维护家庭的完整和自己的权威。牦牛性情温顺,一般没有攻击性,但是如果把它惹急了, 追到天边都要把你顶死, 求饶都没用。这就是传说中的牛脾气,所以狼轻易不敢惹牦牛,但是像拉雅这种脱离集体的落单者,很容易被狼钻空子。
牧民当然希望頭牛把野生母牦牛带回家,但成功率不高,因为野牦牛不大喜欢安逸平稳的生活。所以,公牛长大后一般就放到草场上不管了, 而母牛则需要每天下午按时赶回家拴好,不是为了防止它私奔,而是为了挤奶。牦牛奶是高热量食物,营养丰富,藏族人的大多数食物里都有奶制品,所以他们身体强壮。张青松一直想学挤牦牛奶, 却遭到扎西吉大姐的拒绝。理由很简单,牦牛奶只能女的挤,男的挤不出来。他对此将信将疑,想问原因,又怕别人说他没学问,只好闷在心里。
拴住了母牛,公牛就不会走远,因为第二天拴牛的地方,会多出很多牦牛粪。用晒干的牛粪烧火,飘出的是草香味。一个“大神”说,牦牛粪冒出的烟对眼睛非常好,可以治近视。于是,张青松趴在牛粪炉子上熏了三天,双泪长流,结果仍然近视。除了做燃料,牦牛粪还有很多用途。它不仅是草地的养料,防止高原沙漠化,还有着杀虫护草的功效。高原土层中有专门以草根为食的害虫,对草地破坏极大,但牦牛粪恰巧能够毒杀这种害虫。高原上的蚊子很大,被咬后久久难忘, 但只要有牦牛粪的地方就绝对没有蚊子。没放过牧的人不知道,羊吃草是将草连根拔起, 牦牛吃草是用牙齿将草的茎叶切断,不影响草的再生。有时候,张青松很坏, 对来看望他的朋友说:“牦牛吃的是冬虫夏草, 拉的是延年益寿的六味地黄丸。”就有朋友把捡到的牛粪往嘴里塞。
地毛角乎是家中老四的媳妇, 和许多藏族人一样,说不准自家有多少头牦牛,但只需要看一眼牦牛群,就知道谁没回来,而每一头牦牛都有自己的名字。地毛角乎非常勤劳,但也不能防止悲剧的发生。拉雅的死给家里造成的损失不是太大, 但牦牛被咬死总不是一件好事。
泽库的藏族人不仅不杀生,还要放生。放生是佛教传统,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忌日庆典,都要放生。被放生的牦牛只是在脖子上系一个标志,就表示被赦免了,既不能杀, 也不能卖, 还要继续在自家草场上养着, 直到终老。牦牛的自然寿命大约二十岁,放生牛越来越多,但是草场有限,以致能卖的牛越来越少。以张青松家为例,全家有大约二百头牦牛, 其中放生牛六十头左右,也就是说只有一百多头有经济价值。最狠的算老二彭措,他有十五六头牦牛,全部放生, 家里还供着两个上大学和中学的孩子, 只能做点小生意筹集学费和凑凑合合地过。
拉雅之死,不悲不喜,乃修行境界。放弃物欲,安贫乐道,是一种生活态度。哪怕只剩下一顶帐篷,藏族人也不会觉得穷。“现在我们的生活好多了,政策好,政府好……”这样的话,从藏族人的嘴里说出来是非常真诚的。
在泽库做律师
9月15日,泽库开始供暖。室外活动大大减少,终于谈到律师事务。在泽库,第一次有人叫张青松“臭嘴巴”,他羞愧地刷了三次牙,戒烟一天。但是依旧挡不住被天天叫“臭嘴巴”,这让张青松倍感苦恼,几乎要怀疑藏族同胞是否对律师职业有偏见了。之后才知,藏语“律师”,发音近似“臭嘴巴”。
在县司法局大厅上班后, 张青松受到了欢迎, 来咨询和寻求法律援助的人络绎不绝,有时候会出现排队等候的情况。七八两个月,张青松共接待咨询一百四十四人次,代写文书三十六份,受理案件三十一件……当然, 这些工作主要由张青松的另一个“1”———洛桑扎西同学具体操作,张青松在一旁指导观察。除了咨询、办案,党委、政府、学校、公检法纷纷请张青松给他们讲课。一段时间后,走在路上的张青松被很多人认出来,老远就喊他“臭嘴巴”,张青松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是蛮重要的。
有一天, 一位藏族阿哥的孩子要到天津一所学校上高中, 找到了张青松:“听说天津只吃海鲜,没有馍馍和糌粑,吃不惯海鮮会不会挨饿?”张青松轻松地告诉他:“问题不大,天津有麻花。”但是藏族大哥还是在犹豫能否让孩子去天津。还有一天,一位当地藏族青年搭他的车去西宁。路上藏族青年心事重重, 叹息如何保留藏族文化:“藏族人搬到山下住,藏族人连锅庄都不会跳了,糌粑都不吃了。”他另有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女友是汉族。家人根本不同意,不让他们结婚,说要保证血统的纯正。此次去西宁,就是要做分手的事。张青松一边开车, 一边对他讲:“和一个女孩分手有多种可能,如果不爱她了,就是借口;如果真爱,民族不同就不是什么事。古老的传统文化都在博物馆里。汉族的、藏族的都一样。过去吃糌粑用泥碗,现在你还用吗?过去去西宁骑马、走路, 现在你不是在坐我的汽车吗? ”青年连忙制止:“张律师,你,你不要说了,我心里有点乱。”
有一天,一位虔诚的宁玛派教徒、藏族兄弟,要到他这里坐坐。聊着聊着,这位藏族兄弟说,女儿考上了大学,没钱缴费,希望张青松能给他女儿资助。没有经过任何考虑,他爽快地答应了,但是他要把这件事谈清楚:“你为什么穷? 为什么没钱给孩子上学? 你养的牛呢? ”
藏族兄弟说:“我本来有很多头牦牛,后来都让我给放生了, 剩下的几十头全部送给了寺院。”
张青松就和他谈宗教、佛法。最后发现, 其实藏族兄弟懂得并不多。说到不解处, 他便说:“喝吧, 喝酒, 这个问题先不谈。”于是就喝,喝到醉了,倒下了,什么也不知道了。
其实, 有很多学成回来的藏族“九○后”很有想法,想做点事,但碍于老人的反对,什么也做不了。想多养几头牦牛。老人说:“养那么多干什么,你想杀生吗? ”“卖给别人,别人吃了,不是一样在杀生?”县上也有机灵的年轻人, 稍微动点脑子就能赚钱。其中一位卖酸奶的,坐在张青松的屋子里,一边喝酒,一边低下声音说:“政府对我们藏族人太好了,只要做生意就给钱。我一年卖酸奶赚一百万,政府给我补贴三百万,我一年能赚四百万! ”张青松心头一惊,盘算着自己是否也该改行卖酸奶。
刚来的时候,很多朋友问张青松,你那里到底需要花什么钱?我们来赞助。到了后才发现, 没有花钱的地方, 大家关注的医疗、教育、道路、水电,政府全包了,连学费都免了。如果管得太多,他们就会有依赖,所以藏地扶贫,需要自己真正觉悟,否则,钱花完了就完了。但是,任何一件事都不是孤立的,是相互联系的。这中间的每一件小事也许不大,可终究会起到作用。有记者曾经不断地追问:您给泽库带来了什么变化?张青松只能回答:“一个地方的法治建设不可能因为来了一个律师就健全了。但是,我做就是了。”
2020年9 月19日, 张青松就要离开草原,离开洛桑扎西一家,离开他以前从不知道,现在却刻骨铭心的大泽库了。临走,阿妈为他选了一头膘情不错的牛放了生。家里大大小小几十人, 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宴会。张青松身穿藏服,脚蹬皮靴,头戴镶有金边的“松沙”帽,与家人不停地合影、拍视频、吃肉、喝酒、唱歌、说笑,一直闹到深夜。迷迷糊糊中,他想起有一天,阿妈专门为他留的厚厚的奶皮, 那是从刚下过牛崽的牛乳里挤出的第一口奶; 想起了他四处玩乐几天不着家时,阿姐打发孙子、孙女给他打电话,到县上找他,让他回家和阿妈一起转玛尼筒、包饺子、念经。张青松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再见,大泽库!
请收下我的律师袍, 让泽库的第一个律师穿在身上;再见卓玛,草原上盛开的蓝白花,是我硬硬的胡楂儿;再见家人,阿姐您念过的每一遍经文,都在我内心吟唱;再见牦牛,听见阿妈呼喊我的名字,你要回家偎依在她的身旁。再见,我的夏德尔。再见,我的泽库。我,还在高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