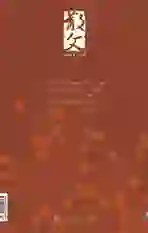在大巴山的褶皱中
2021-05-07陈霁
陈霁
大峡谷
太阳初升, 层层叠叠的山脊在阳光下闪耀,西边的山体却融化在浓重的阴影里。一明一暗,刀砍斧切,是对比强烈的巨幅版画。一条名叫前河的小河,就陷落在阴影的最深处。它由东向西,与大巴山圆弧垂直。如果说大巴山圆弧是一张弓, 前河就是搭在弦上的箭。
大巴山圆弧是地壳运动中南北板块挤压的结果。前河经年累月地流淌,手术刀一样拦腰剖开大巴山, 把深藏地壳之下的那些三明治或者千层饼状的层理, 完整地袒露开来。于是,那些千奇百怪的褶皱,像大自然鬼斧神工打造的岩画或者壁画, 就一幅一幅地挂在大峡谷那些绝壁上。于是,百里大峡谷就成为百里展线,百里画廊,成为雄甲天下的“褶皱博物馆”。
太阳慢慢升到了高空, 阳光像金色的液体泄漏下来。行走在谷里的“一线天”中,世界在晦暗与光明之间频繁切换。枯藤从悬崖上垂落, 供那些山妖和树精从天上降落,或者攀上高天。绿色的水流蛇一样在峡谷底部游走, 给雄性的大山增添了几分阴柔。一团阳光落在水里,水中光洁的卵石历历可数。一些鱼, 主要是当地人说的沙鳅鱼, 一拃多长, 像是从齐白石的画幅里游来。到了急流处,它们突然扭动身段,银光一闪,消失在山崖下幽暗的深潭。还有娃娃鱼,大咧咧地趴在石头上晒太阳,直到人走近,才扑通一声滚落水里,瞬间消失。
这是严格保护的生态区。没有了人这个最大天敌, 水族们在这里已经与食材无关,与人的食谱无关。它们是风景的组成部分,只服从于大自然给它们的那些定义。
走出“一线天”,峡谷稍微拓宽,阳光终于普照两岸。秋树斑斓,溪流凝碧,沙滩银光闪闪。许多硕大的卵石,散布在河道里像是一些滚动的巨蛋。上面包裹的苔藓色彩鲜艳,华美,夸张,金黄与碧绿交融,让人想起张大千或者何海霞的金碧山水。最精彩处还在那些刀砍斧劈的绝壁上。这里像极了国画大师竞技场。披麻皴、雨点皴、卷云皴、牛毛皴、折带皴、大斧劈皴和小斧劈皴,各种皴擦的技法熔于一炉。再加上晕染、泼墨、泼彩。似乎傅抱石、李可染、林风眠和黄永玉,甚至李唐、范宽、马远、倪云林,都在上面各显神通。
在峡谷里,我忽然想起了樊哙。
樊哙是刘邦手下的一员猛将。鸿门宴上,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紧急关头,他挺身而出,舍命护主,这是他的高光时刻。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就在峡谷附近,一个现今叫樊哙镇的地方, 樊哙曾经在这里经略数年,训练了一支以巴人为主的虎狼之师。正是这支生力军,为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朝立下了不世之功。
汉,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因为有了汉, 才有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
宣汉,宣扬汉朝之威。一个很有历史质地的县名,让一方土地显得厚重起来。
遥远的祖先
到罗家坝是三年前,夏至刚过。
那天,太阳明晃晃地悬在头顶,照耀着一个万物疯长的季节。
大山脚下, 宣汉县境内的兩条大河———中河与后河汇流于此, 在崇山峻岭之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冲积平原。水稻、玉米, 还有田埂上见缝插针种下的黄豆和绿豆,汇成无边浓绿,遮蔽了大地。尤其是那一片玉米,一人多高,茁壮得不像草本不像秸秆, 更像是密匝匝的森林———大自然把憋了许久的能量尽皆注入其中, 放肆生长的劲头似肉眼可见。它们无风自摇,飒飒有声,像是有来自地下的什么精灵附体。
朝北走,直到河边,才有一块裸露的土地。醒目的油黑,是绿色的无缝天衣揭开的一角。土地平整,泥土细碎,几个老汉老妪在用锄头继续敲打坷垃———他们像绣花一样侍弄土地。河水碧绿,流动在浓浓的柳荫之中,流速像这里的时光一样缓慢。一只渔舟,也可能是渡船,在远处轻轻漂荡。这让画面美得很不真实, 像水彩画, 画的是梦境,是世外桃源。
村头。树荫下的石条上,坐着十来个留守老人。他们脚上套着清一色的塑料拖鞋,双手叠放在膝上,态度安详。有一句没一句的话语,轻轻的,像交谈,更像自语。看见一个陌生人走过来,他们脸上也波澜不惊。
一位年纪最大的大爷告诉我, 包括他在内,这里的居民清一色姓罗。
罗氏,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乃黄帝后裔。他们世代编织罗网,捕鸟为生,曾经是周天子的臣属。
春秋时期, 这是一段让人眼花缭乱的历史。虽然进入了文明社会,但大大小小国家的行为依然像丛林里的掠食动物, 弱肉强食,用武器说话。一个个强人,一个个霸主,像原野上的花朵一样次第绽放,又倏忽凋零。罗人首领曾经给周天子当过养鸟的饲养员———虽说好歹也是个京官, 但是这活太不入流,沾不了高层政治的边,周天子一不高兴就把他撵走了。罗人不得已依附于楚,但楚是一只爱吃窝边草的兔子,瞅准机会就对它张开大口,露出利齿。
面对灭族之灾,罗人四散奔逃。其中一支,翻越神农架,来到大巴山深处。精疲力尽的时候,首领见早已远离繁华,也远离了危险,而这个群山环抱的冲积小平原,沃土深厚,碧水如练,却是一派亘古的荒凉。尤其是,原始森林里百鸟鸣啭,翩翩翻飞,让他想起张网捕鸟的祖业。于是,首领大叫一声“天不绝罗”,下令族人停下,升起炊烟,烧荒播种。于是,罗人一脉就此落地生根。
两千年后的元末,也是战乱。江西南昌的一罗姓人家,兄弟四人,属官二代。他们将祖传的一个金盘一分为四,各存一块,然后挥泪分别。其中,除老大留守家园以外,其余三兄弟结伴逃生,辗转寻来罗家坝。他们见当地人也姓罗,并且,他们彼此都在族谱里看到了共同的血脉源头, 于是这一族人就留了下来, 像一瓢水掺进了罗家坝这个水缸。久而久之,罗家坝人已经分不清自己具体的来历。他们只对那只金盘记忆深刻,都认为自己才是金盘的主人。
肥美的水土让罗氏一族人丁兴旺,人才辈出。其中最显赫的,是乾隆嘉庆之间的罗思举。他本为一介农民, 三十出头的时候,适逢白莲教兴起,遍地烽烟。于是,他主动加入乡勇。凭着超人的勇敢和聪明,冲锋陷阵,屡建奇功,他成为一代名将,先后出任过四川、贵州、云南、湖北和湖南的提督,死后被赐太子太保,谥壮勇公。后来的曾国藩, 差不多也是复制了罗思举的路线图而终成大器。只不过,曾国藩有体面的出身,在中国闹出了更大的动静而已。
罗家坝的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世代代,他们在脚下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用犁和锄头朝大地深处翻了又翻, 几千年都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1975年冬天,几个庄稼人在地里踩瓦泥,准备烧瓦盖房。随着水向下渗透,他们的双脚也随着湿泥越来越下陷。突然,有人大叫一声———他的脚被尖利的石片或者是瓦片划伤了。像是连锁反应,随后好几个人都踩到了硬硬的尖利的东西。他们的双手在湿泥里小心翼翼地摸索, 差不多每一个人都从脚底下掏出了东西。赤脚上田,经过冲洗,他们才发现手里的东西都是古物:有的是长满绿锈的铜器, 有的则是莫名其妙的陶片。
他們知道铜是可以卖钱的, 于是他们继续在地里掏, 一掏就掏出了几十件青铜的刀、剑、矛之类。这是意外之财,他们把它们作为废金属拿到供销社换了酒喝。
一位民办教师听说了此事, 觉得事情并不简单,报告了县里有关部门。于是,经过考古团队的发掘, 一个秘密终于大白于天下———
就在那些树林、庄稼、农房、猪圈和牛棚的下面, 层层累积着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春秋战国和秦汉两朝的大量文物。
这是四川盆地在三星堆、金沙遗址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那些巨量的石器、陶器和青铜器,那些兵器、礼器、工具和生活器皿,它们证明了小小的罗家坝,不但是宣汉的前身东乡县治故址, 很可能还是巴人曾经的故都之一。
巴人
剽悍的巴人,在我的记忆里,有名有姓的唯有巴蔓子。
在巴国国势衰弱的时候,时逢内乱,巴蔓子从楚国借兵平叛。当然,借兵的条件是苛刻的———骄傲的将军, 被迫答应割让自己镇守的三城。事后,当楚国来使要求他兑现诺言的时候,他拔剑在手,大呼一声:“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随后自刎,割头以授楚使,从而保全了巴国疆土。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巴国英雄, 从此在人们关于巴人的想象里屹立不倒。
还有一个有名有姓的人:苏妲己。在宣汉人的远古叙事里,这位超级美女,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姑, 家住罗家坝那样依山傍水的某个村落。家乡的山水给了她美丽和灵性,也给了她大山的狂野。在巴国苍生生死存亡之际,她挺身而出,像蔡文姬、王昭君和文成公主那样走进异国宫廷, 以自己的美貌摆平强敌。在宣汉人看来,苏妲己并不是那种妖异的“红颜祸水”,而是一个为国捐躯的圣女贞德式的巾帼英雄。
秦统一, 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像水滴落入华夏的大池,巴人也随之消失。
但是,在后来宣汉人的身上,我们至今还可以依稀看见古代巴人血液的奔流。
土家人是巴人的后裔, 宣汉是土家族的聚居地。
不过,我以为,不仅仅是土家人。今天的宣汉人, 谁敢说自己血脉的上游和巴人毫无关系? 每一个宣汉人,都有权利、有理由说自己是巴人的子孙。
农耕时代,大巴山区是苦寒之地,有限的土地难以承载人口的繁衍。生存的艰难和竞争的激烈决定了巴人的古老基因,大巴山的山民们拥有最热的血、最硬的骨头以及最不安生的灵魂。民不聊生的社会,反叛的在这里一定会燃烧起燎原大火。巴人要么揭竿而起,高举义旗攻州掠县;要么劫富济贫,呼啸山林占山为王。中国的每一次动荡,在这里都可能掀起惊天巨浪。
翻开嘉庆时的东乡县志, 里面有太多关于造反、叛乱和匪患的痕迹,也有太多勇士、烈女和孝子故事的记录。
风暴过后, 就像罗家坝那些回填了泥土、重新种上庄稼的土地,人们擦干血迹,拍净身上的泥土, 依然老老实实地过自己的日子。历史,就这样一页一页地翻过,积淀出一个广袤深邃的宣汉。
在宣汉, 背二哥曾经是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
一个背架子,一个打杵子,一条通往山外的崎岖小道,让大巴山里的宣汉,得以将经济的血脉与无比宽阔的外部世界接通。
在宣汉城里, 本县学者桂德承给我讲了他父亲桂攀书的故事。
当年,背二哥桂攀书他们要背的,主要是来自万县的盐巴、桐油和从南方水路运来的瓷器、洋布和百货。从南坝场出发,经虾爬口、官渡、固军坝、竹峪关、紫阳、安康,最终的目的地是西安。路途遥迢而崎岖,一趟下来,要三四个月的时间。路上常常还有抢匪,所以背二哥们必须成群结队地走。大的商号,还可能夹带贩运鸦片,武装押运。
荒无人烟的崎岖山道上, 一两百人的队伍, 每一个人都有山一样的货物压在身上。这样一支队伍在大地上缓缓移动,那是多么令人惊叹的场景啊。
背二哥每天面对的都是艰辛。顶风冒雪的冬天尤其苦不堪言。虾爬口出去就是牛背梁,冰雪天路滑,他们只好滞留南坝街上,大家打牌,摆龙门阵,甚至找小妹儿,等天气好转冰雪消融才重新上路。
桂攀书身材魁梧,力气惊人,外号桂大汉。那种两百多斤重的毛边锅,身强力壮的背二哥也只能背一口,但他却要背两口。他的打杵子也比普通人大出一号, 只消朝人前一站,就是一种威慑。自然而然,桂大汉成了背二哥的领袖。
尽管他带的队伍越来越大, 积攒的钱越来越多,直到1949 年,他距离地主的梦想还有一步之遥。
桂攀书, 这个名字凝聚着桂大汉的人生希冀。他没有机会读书,但是只要一坐下来,就要缠着那些识字的人,向他们学习求教。日积月累,他竟有了初步的阅读能力。
让他欣慰的是, 他的儿子桂德承后来通过读书,成为县文化馆的干部,一个受人尊敬的地方学者。所以,十几年前,昔日的背二哥桂攀书, 手里捏着一本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