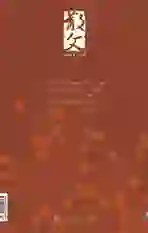十字街,与钉婆婆
2021-05-07王晓莉
王晓莉
字街这个地方,怎么说呢,其实就是硕果仅存的老城区缩影。挨挤得密密匝匝、低矮的棚户,每一家的门都朝着街道敞着。木质结构的房屋有着“随手扔根火柴都可能引燃”的隐患。线路凌乱,细细观察可以发现是不同时期接上去的。电表盒子也不像现在的新型小区, 整整齐齐一大排挂在墙上,而是上一个,下一个,哪儿有空当就在哪儿挂一个。弄得墙上像挂了很多炸药盒。乱归乱,生活却是便利得很,因为卖什么的都有。不用出街,一日三餐吃穿用度全可以在这街上搞定。卖米粉和面的小门脸,毫不起眼,门口却总是围一圈年轻的孩子,一边拿着手机低头刷刷刷,一边等空位,原来那是一家网红店。不长的一条街,光“房屋中介”就有五六家,你就知道这儿的房屋无论租还是售卖都是很俏的。就算你是某种“少数派人士”,比如信佛的,也不用跑到苏圃路上的老佑民寺去。十字街正中央位置就是“观音阁”,它是南昌唯一的女尼道场。每到佛教的几个重要日子,十字街就陡然多了许多人。他们来上香,祭拜,脸上满是兴冲冲和虔诚。有一年元旦,我特意起早去了一回, 不大的天井里摆满了信众供奉的平安灯,整整齐齐的像阅兵方阵。那些灯都是红色的底座,黄黄的灯光,像一小片布满星星的天空,很是梦幻。当然,另外有些日子我也来过这里,一次是为生病的弟弟,一次是为父亲,还有一次是为自己。在蒲团上面朝观音大像拜下去,再起来转一圈,或是往功德箱里做个小小的布施。两边有笑口常开的布袋和尚,没有人不爱他;还有韦驮护法。护法一向怒目圆睁着,可是我知道他也是慈悲的神。
正对“观音阁”的马路对面,还有一家市立精神病院。有时我觉得生活真是无处不偶然,却又无处不充满隐喻。寺庙安抚人的灵魂, 精神病院则修治人的精神———尽管能否治好存疑。而这两处竟然恰好面对面! 所不同的是,观音阁任意人的进出,精神病院则总是门庭紧锁, 这使它成了十字街上的一个例外。我每次经过,总是深吸一口气,仿佛它跟我有某种难以言喻的关系。
差不多到了2014年,有一天我买菜路过十字街,突然发现街口安上了竹篾子做成的那种围挡。围挡上张贴着“观念一变天地宽征迁片区开新篇”“拆迁政策是根本真诚服务是保障”诸如此类的标语。我绕到围挡后面, 突然发现这条街已经面目全非。因为大部分房屋已搬空,整条街初现出一种废墟的规模, 远看有点像好莱坞战争电影里搭出来的那种又大气又荒凉的布景。我有点惊住了,赶紧往里走。只见有的房屋墙体上用蓝色笔写了数字编号,代表即将拆除;有些则是大红色笔写的“征”字,里面的人家还在生活。晾晒了形形色色的衣服,小車、电动车还停在门口,还有老人家在门口休闲……但是一切就是都不一样了。哎呀,要拆迁了吗? 我还没来得及把十字街熟悉个遍呢。我这样慌乱地想着,在十字街连走了两个来回。电动车经过身边时带起很多土,我也不想躲避。我看见还有“房屋中介”开着门,还在营业,可是都要拆了,它“中介”啥呢? 我想不明白。我又看见那家网红面汤店,居然还有客人在吃。女店主在炉前烹饪,男老主人(可能是她父亲或公爹)在那里就着一堆煤灰慢慢做蜂窝煤。烧煤虽然脏,可是比烧煤气省钱得多。我并不饿, 还是急急地进去, 点了一大碗米粉吃。我想,再不吃,就吃不上了。
到了那年深秋,天已经很凉,是要戴围巾的季节了。十字街只剩下几户人执意不走。那么大一片土地上,那几家就很显眼。而且怎么看都有点凄惶。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在身后催着似的活,其实是很累的吧?我去那里逛时这样想。那几户居民眼神警惕,有的远远看见,会从他那边绕过一些土堆或是废品堆,赶过来打量一下我。见我戴眼镜,会议论说:“是不是记者? ”但看我的样子又不像。我什么设备也没有。
这样我就认识了钉婆婆。她是那不肯搬走的几家中,屋子最为“豪华”的。那是一所木质的两层老宅, 本就发出年深日久的气息,现在在这片正在经历拆迁的土地上,它还是那样完整、一点不松懈地存在着,就显得相当孤僻,以及不合时宜。那是下午,钉婆婆门是敞着的, 我刚从一家搬空的人家转悠完, 顺势就半只脚踏进她一尺来高的木门槛。脚还没放稳,就见一个矮小的老太太从廊道里急急出来, 冲着我一声喝:“做吗呢做吗呢!”她个子只有一米四多,但因为全身都是骨骼,丝毫没有肉,就显得很“硬”,颇有太湖石的种种特征:瘦、漏、皱、透。我被震慑了,这才反应过来是自己逛了太多“无主”屋,现在误进了一家“有主”的。我忙忙地说,我小时候住过这样的房子,很多年没住过了,所以想看看。老太太才略微放松了警惕。但是明显也很不欢迎我这样的人。我赶紧退出来。一枚传说中的“钉子”,我在心里说。所以我在心里把她叫作“钉婆婆”。
后来我去了几次, 发现随着拆迁的日益完成,钉婆婆的门扉再也不打开了。但是我还是看得到有人在里面生活的气息。有电视和自来水的声音。这时候已经有建筑工人入内施工了。这些工人在了解我只是一个闲逛者之后, 总是乐意向我介绍各种事情。有一天有个建筑工告诉我,钉婆婆的丈夫从前是开米店的,赚了钱建了这栋屋。钉婆婆是妾, 目前大房老婆的儿子和她一起守在这幢屋里。大房儿子还没有娶妻。我想到从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那时我还小,在南昌的干家前巷、三眼井一带住着,准确地说我住的地方是叫“南海行宫”———我现在想起这个名字就要发笑, 有种置身《西游记》或是可能遇上观音娘娘的感觉。但是那个地方就是叫这个名字。现在也还在。那里一栋一栋全是钉婆婆这样的老屋,每栋老屋里,都有一个这样的钉婆婆。
从拆迁到真正开始重新建设, 这中间有一段空当。几乎没有人从十字街穿过了,城中心居然有这么大块空地, 除了捡破烂的,几乎看不到人。
捡破烂是非常好看的。破铜烂铁不说了,木头、大大小小的纸箱、塑料薄膜、旧家具,还有电脑主机……在拾破烂的人眼里,就没有没有用的、换不来钱的东西。它们形状、大小、用途各异,可是经过拾破烂的拾掇摆弄, 就服服帖帖地聚拢在了三轮车或加长改装了的电动车上。就像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组成一个旅行团,经过导游的引导,彼此相处也很好。在十字街这样拆迁的地方捡破烂, 如果你有两把力气收获就更大了。很多旧钢筋都要用力去拉扯, 打架一样,最后总是捡破烂的打赢,钢筋就乖乖地躺进三轮车里。所以在十字街巡来巡去的拾废品的,必定是男人。而且很奇怪,多是上了点年纪的。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大哥在那里拉废弃的钢筋,“搏斗”了很久,总有一刻钟,才有一根钢筋到手。那时是黄昏,他瘦削而紧致的身影仿佛陷落在建材垃圾里,后面是灰扑扑的夕阳,没有耀眼、喜悦的光泽,只有一丝悲凉往外渗,悲凉中又生出一些力量来。
我看多了,也产生了捡的念头。我觉得这活真是不错,让世界多一点有用的物品,少一些可以避免的垃圾。当然那位大哥以可以卖钱为准则,我则是专意于捡“好看”的。我撿到了一个广口青花花缸,一看就有年头了,只有中腰位置有一道很长的,但不细看并不会发现的裂痕, 这大概也是它的主人丢弃它的原因。但其实它一时半会儿也并不会裂开。而且它那么大那么美。我弄回家, 发现和我家放米的白瓷缸可以配成一对情侣缸。那只青花米缸是我外婆留下的。捡来的这只我用它放字画卷轴,非常文雅。我又捡了一只大约是用于腌盐菜的小口广肚泥坛, 我设想插一大把干芦苇在里面会很摇曳多姿; 另外我又和丈夫抬了一截樟树树干回去, 它看上去是一棵樟树最中间的一段,是樟树最好的一段年华。最后我在看上去是一户人家厨房的位置还发现了一只巨大的深褐色水缸, 应该是有年头了,把头伸到缸上面,感到凉飕飕的阴寒,好像时间躲在里面很久,没有出来。我想象它种满睡莲,或者单纯做摆设放着的样子,十分想要搬回家里。但是太沉重了,没有一辆小车愿意运它。家中似乎也没有放这么大只缸的空间。
这中间我突然生了场不小的病,住院、手术、复查,以及修复心情,耗费了大量时间。十字街我很久都忘记去了,净顾着与疾病周旋,终究没被打垮,但也改变很多。改变之一是看见有人写生病的文字, 总是跳过不看。人们深重经历过的黑暗事物,例如恶疾,例如丧失之痛,当“克服”过它之后,就有“一览众山小”的某种隐秘体验。就这样,快有两年我没有想起十字街。
到了今年, 不知怎的我又惦念起钉婆婆了。仿佛“她还在不在那里”这个问题对于我重又变得重要了。经过十字街口的时候,最初拆迁时用的看上去很廉价的围挡,已经更换成好看的绿色围挡。周围高楼迅速地林立起来, 从前那条低矮的十字街快要被完全覆盖掉了。
夏天的时候, 十字街与我家相反的北边那头,“王府井购物中心”落成。很快它就成了南昌新景。听说开张那几天车都停不下了。人们动辄说“王府井”而省略掉“购物中心”几字,仿佛置身北京似的。“王府井”落成, 我唯一高兴的就是里面六楼有个影院。这是离我家最近的一家。此前我看电影得跑到象湖附近的一家影院去, 因为人少僻静,那个小影厅常年弥漫着淡淡的霉味。电影还没散场, 清洁工就手持扫帚站在一边等。我每回去都得思虑半天。现在十字街“王府井”开张,我与丈夫立即去里面看了一场姚晨主演的电影《送我上青云》。姚晨在电影里的生活非常戏剧, 一下子得了恶性肿瘤, 一下子又去一个云雾缭绕有如秘境的地方给企业家父亲写传记———为了赚三十万治病的钱。电影最后是姚晨站在墙垛口,当风的位置,对着青天“哈哈哈”了三声,意谓把生活的晦气一“哈”了之。我说不上来这个电影好还是不好, 但是以后能够只用二十来分钟的时间去“王府井”,看上大银幕,对于我而言就是高兴的。
看完这个电影我更想念钉婆婆了。因为她家实际上就在“王府井”的后面。看姚晨的那个影厅如果有窗口, 说不定就是对着钉婆婆家, 没准我还能看见她在天井里走动,像块移动的太湖石。我因此在家里念叨了几次, 我丈夫则说通往钉婆婆家的那条路已经完全封锁了, 进不去了。我不相信。我也说不上来我想从十字街从钉婆婆那里得到些什么。但是有时候一些看似与自己完全不相干的人事, 其实对我们意义重大。有一天下午天突然变得很凉快,一点也不燠热了, 我就决定趁此好天去十字街会会钉婆婆。果不其然,街口围挡后面一个守卫模样的人喊住了我,说那边路不通的,他大概以为我是要去“王府井”———看来我丈夫说的也没错。我说我就随便逛逛。他也没拦我。等我走了一段,我发现我已经快要不认识十字街这条路了。几乎所有的老房子都消失了,拆迁的建筑垃圾比以前更多,但是同时又拉进来了许多新的建材, 待用的混凝土预制板弯翘翘地堆得到处都是。路两旁已经新起了许多崭崭新的小区房。推土机和钢吊车有好几台在不同地点施工。有小哥开着“京东快递”的送货车从身边穿过,往施工人员的临时住宅那里去。真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快递。路边三三两两的大废墟小废墟上, 还是有流浪狗翘着它的尾巴路过,还有老鼠、鸟这些活物。废墟上还多了一种两年前这里还不曾存在的新事物———共享单车, 准确地说是共享单车的某部分。这些黄车有的坐垫被拧掉,无头骑士一般倒在那里; 有的两个轮胎被不知什么力量拧成了两股麻花; 还有的只剩一个黄色的车杠子。单车的“尸体”全都裹满了尘土,像长途跋涉之后牺牲在了这里,且无人掩埋。有一只车胎插了一部分在地里,牵牛花遍布它全身, 绿色的藤蔓, 紫色的花朵。在一片荒芜之中,那坚硬的轮胎遍布柔软的绿植, 像出自美院学生之手的作品一样有几分动人。我对着它拿手机拍了又拍。
我略带惊讶地一眼就看见了钉婆婆的家。在那么大一片工地当中,所有人生活其中的、旧的、能拆的部分,都已经被彻底拆除了———是在为起来一个新的、 更加坚固与豪华的, 也是供人生活其中的世界而准备。就在这么一个背景下,钉婆婆那幢她经营米业的丈夫留下的、古旧的两层老宅,还完整地留在那里,还是那么孤僻、不合时宜地门扉紧锁———当然会被我一眼看见。 周围几十层的新楼,衬托得它更为低矮,不堪一击似的。但又似乎更为倔强。我发现它唯一变化的是比两年前多加了一道铁栅门。透过铁栅往里看, 漆黑的廊道尽头有只干净的木凳子摆放着。除此什么也没有。我不死心,又绕到屋后去,也没有看见什么。又退后几步往二楼阁楼看, 还是不能判断钉婆婆是否在里面。但是我有了新的发现,我看见从她二楼阁楼的背后长起了一棵笔直的构树,非常高,有一层楼那么高。这是两年前没有的。这使钉婆婆家显得像是三层楼了。构树生命力很强,水泥缝、石崖边随处可以存活下去我是知道的。我家旁边就有一排, 它的每枚叶子都有一个各不相同的缺口,成为辨识它们的最好特征。
一个头戴安全帽, 长得像二人转演员宋小宝的建筑工过来,问我干吗。我说我两年前来过,当时还有个老婆婆住在里面。他立即以一种掌握了第一手情报的得意神情告诉我,老婆婆还在里面,生活得好好的,有个儿子陪着她。我“啊”了一声,却什么其他话也说不出,这是十分复杂的一声“啊”。
于是和他东拉西扯关于十字街的种种。他用手画了围着钉婆婆家的一圈,说,你沒看出来,这里建材这么多,这里到时候就是地铁口嘛,明年大概地铁就通了。
原来钉婆婆家这个位置是在地铁口。那……那她家怎么办? 我没问出口。但是“宋小宝”猜到了我的意思,他说,还没到时候嘛,到时候就有办法了。
我与这位“宋小宝”的聊天最后陷入了这样一个境地: 对这个看似与己无关的钉婆婆以及她像一枚钉子守住木板一样的行为,我们随意地谈论着,却又使用着一种因为省略一些主语、宾语,省略一些动词而意思有些隐晦的语言,彼此却又都明白。
我拿出手机拍钉婆婆屋顶那棵笔直得像把尺子、直刺青天的构树。“宋小宝”觉得无趣,说,这有什么拍的呢?他连问了两遍,见我只是有点尴尬地笑,也没回答,他就回他的临时工棚去了。我是没法回答他我为什么要拍。我不能跟他说我觉得这看上去有点特别———本来是很凡庸的一棵树,因为长在这样一个荒凉与热闹兼有的拆迁地, 因为它的某种唯一性———几乎所有的绿树都被销毁或是挪走了, 它显得非常不一般起来。
树长到了钉婆婆家的房顶正中央,住在里面的钉婆婆和她非嫡亲的儿子也不嫌碍事去剪截掉它,而是选择与树共生共存。这里的用意大可回味。我想我是理解钉婆婆的。时代在往前冲,像“王府井购物中心”那样的新的东西不断生出来,叫人心蠢动,叫人目不暇接。但是那些在骨子里并不是我们的。我们路过,看一会儿,终究还是要离开。我们只能抱着残存的、与自己一起长起来又一起老下去的东西活。像屎壳郎抱着粪蛋子。像平凡的树盘踞了未拆的屋顶。像钉婆婆, 世界已经收缩成了她先夫遗给她的屋子那么大的地方。
我们每个人都是钉婆婆, 或者都在成为钉婆婆的路上。
我还是时常去十字街这片废墟走动。这么一大片无人的土地供我随意溜达,不会人挤人,也不用花一分一毫。这让我充满欣悦。如果说城市也有荒野,这就是。谁不喜欢荒野呢?哪怕只是一刻。可是我知道好日子也不多了。就像那个矮个子“宋小宝”说的,最迟明年地铁就要从这里通过了。会有站台,写着“三号线”“四号线”,会有各种箭头,使人不致迷路。漂亮,豪华,人来人往,可是那是跟我没关系的。
我从废墟回到家, 坐在我的一堆书当中。这等于是从一个废墟到了另一个废墟中,因为书也是废墟,一个时间的废墟,一个由纸张、各样思想以及各样文字建材组成的废墟。我虽然也生病,但是不会也不可能像姚晨那样,站在城墙垛口对风大“哈”三声,生存的晦暗与阴霾就一散而尽。我感到我和捡破烂的大哥,和钉婆婆更为相似。甚至可以说,我们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守着各自的续命之物,在废墟中,或是被废墟包围。可是我们也还活得津津有味, 甘之如饴,还有各自所看重的和所不屑的。我们抹掉脸上一把灰,四顾茫茫。可是低下头来,也有心静如水的片刻。在那片刻中,我们小憩自己奔波不已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