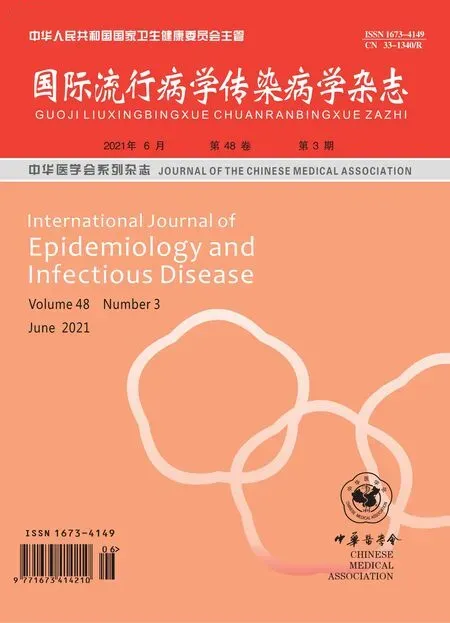解决HIV感染者晚发现的策略:以综合性医院为中心开展全病程管理治疗
2021-04-17林铃李太生
林铃李太生,2,3
1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100730;2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艾滋病研究中心100730;3清华大学医学院生命科学院,北京100084
自1996年联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combined antiretroviral therapy,cART)问世以来,AIDS已由不治之症逐渐转变为类似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内科慢性病,大部分感染者在cART后可获得免疫重建,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降低。2016年,我国开始推行AIDS发现即治疗的策略,早期启动cART防止疾病进展并减少HIV在人际间的传播,但由于AIDS的潜伏期长,发现后往往进入晚期,这些晚发现的病例不仅治疗效果不佳,还可作为传染源进一步传播病毒。2015年,我国AIDS患者新报告病例数115 465例次,晚发现病例的比例为35.5%;至2019年,我国AIDS患者新报病例数增至151 250例次,晚发现比例增至37.5%,晚发现病例仍有50 000余例。由于晚发现患者CD4+T细胞计数较低,导致住院率上升,机会性感染和肿瘤的患病风险增高,增加了医疗保健的费用,且未抑制的病毒载量带来了高传播风险,即使经过有效的cART,晚发现患者的预后也不及早期开始cART的患者[1]。晚发现患者不论是对于疾病的预防控制亦或自身治疗和预后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也是我国如今面临AIDS防治的一大挑战。本文总结了我国AIDS患者晚发现的情况,分析AIDS患者晚发现的原因,并依此提出可行的解决策略。
一、国内外AIDS晚发现患者流行特征
AIDS晚发现患者目前缺少全球性的统计数据。2010—2016年,COHERE和EuroSIDA队列评估了17个欧洲国家晚发现病例的情况,结果显示,48.4%的新诊断AIDS患者为晚发现病例[2]。Lee等[3]于2020年发表了一项针对15个英格兰和威尔士AIDS服务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31.5%的AIDS患者为晚发现病例。拉丁美洲来自CCASAnet 6个中心2001—2014年登记的新患者中有56%表现为AIDS定义性疾病[4]。2008—2017年澳大利亚的数据分析显示,39%的新发病例为晚发现病例,晚发现病例中52%的患者具有AIDS定义性疾病,并且澳大利亚本土居民的晚发现比例(34%)较移民比例低(47%)[5]。我国2006—2012年期间,新诊断的AIDS患者中有58.8%为晚发现病例[6]。广西壮族自治区是我国报告HIV/AIDS病例数排名第二的地区,其2012—2016年期间新诊断的HIV感染者中有70.2%为晚发现病例,45.1%具有AIDS定义性疾病。晚发现的患者中男性异性恋者和女性吸毒者占比更高,相对于在自愿咨询门诊检测并确诊的患者,在医院诊断的HIV/AIDS患者晚发现的比例更高[7]。1997—2012年,北京协和医院共收治279例住院治疗的HIV感染者,其中有72例(26%)是在北京协和医院确诊的,新确诊患者的CD4+T细胞计数中位数仅为26个/μL,超过一半的患者至少有一种AIDS定义性疾病,其中常见的机会性感染依次为耶氏肺孢子虫肺炎、活动性肺结核、巨细胞病毒视网膜炎、食管念珠菌病和肺部念珠菌病[8]。晚期AIDS患者可能辗转多个医院的不同科室进行就诊,虽然从开始就诊到确诊的平均时间从2002年之前的91 d下降到2009年的39 d,但仍超过1个月[8]。2016年以后,我国HIV感染者晚发现的比例基本没有变化,2016—2019年分别为36.1%、35.4%、36.1%和37.5%,新报告的晚发现人数逐年增加。
二、AIDS晚发现的原因
我国CDC担任了HIV感染筛查的主要任务,每年筛查1亿多人次,筛查主要人群为感染HIV的高危人群。值得注意的是,非高危人群但具有高危性行为的HIV感染者对于HIV筛查的意识仍有待提高。我国60岁以上AIDS新发病例,从2010年4 751例上升到2019年的29 763例,占比从7.4%上升至19.02%;青年学生的新发病例占比自2011年的10.4%上升至2019年的21.7%,包括妇女、异性恋者和老年人在内的非传统意义上的风险群体更有可能在HIV感染后出现延迟检测和诊断。德国柏林的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2009—2013年共有270例HIV感染者在AIDS期被诊断,其中有21%的患者至少出现1种AIDS定义性疾病,且在此前曾寻求医疗帮助但并未接受HIV相关的检测,其中女性和非男男性接触者的比例较高[9]。既往研究分析了荷兰确诊较晚的风险因素,发现异性性传播与确诊较晚有关[10]。根据中国国家流行病学数据库的数据显示,1985—2009年新确诊的患者中有41%在AIDS期被发现。值得注意的是,30%新发病例的诊断来自医院系统,而不是中国CDC系统的自愿咨询和检测(voluntary counselingand testing,VCT)站点[11],在医院诊断的这些患者AIDS期的比例更高[12]。
相较于高危人群前往VCT站点主动筛查,非高危人群在感染HIV之后出现症状更有可能被动前往综合性医院相应科室就诊。大多数HIV感染急性期的症状并不特异,较轻微可自行缓解,在高危行为后出现发热、咽痛、盗汗、恶心、呕吐、腹泻、皮疹、关节疼痛、淋巴结肿大及神经系统症状时,如及时就医进行筛查可在早期发现HIV感染,但由于症状的非特异性,大部分临床医生对患者应该筛查HIV抗体并不敏感。从急性期进入无症状期后,筛查的概率大大降低。AIDS期的情况更为复杂:当HIV感染者进入AIDS期后,常因各种并发症首诊就诊于不同的临床科室,若为常见的AIDS定义性疾病则接诊医生较容易进行HIV感染的排除筛查,比如耶氏肺孢子虫肺炎等机会性感染性疾病或卡波西肉瘤等肿瘤性疾病,但正是由于AIDS期免疫系统防线被破坏,患者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以致难以识别。分析1997—2012年于北京协和医院住院并新确诊的AIDS患者,其中发烧是最常见的症状 (85%),其次是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68%)、复发或慢性腹泻 (21%)、口腔念珠菌病(18%)、复发性肺炎 (13%)、水痘带状疱疹感染(10%),最后是视力损害(8%)。实验室血常规检测提示患者具有不同程度的淋巴细胞减少、贫血、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等[8]。尽管从就诊到确诊的时长缩短,但很大一部分患者在确诊时仍然处于疾病晚期,且患者此期间常常有不止一次的就医经历却并未接受HIV相关检测。未接受cART和CD4+T细胞计数<50个/μL是与HIV感染者死亡最强相关的两个危险因素[13],因此提高医疗人员对HIV感染者的识别并给予相关的检测筛查是很有必要的。
此外,有研究发现中国流行的HIV基因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性传播感染的HIV人群中,循环重组株 (circulating recombinant form,CRF)01_AE的比例显著增加。自2006年以来,CRF01_AE现已成为我国最流行的基因型[14]。CRF01_AE亚型与非AE亚型感染者相比,疾病进展更快,从感染发展到AIDS期所需的中位时间约为4.8年[15],这可能与CRF01_AE亚型的AIDS患者中CD4+T细胞的共受体CXCR4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亚型有关,且男男性行为AIDS患者可在感染早期出现共受体从CCR5到CXCR4的转变[16]。HIV感染者全人群的潜伏期约为6~8年,CRF01_AE亚型的感染者潜伏期明显缩短,提示了这部分患者需要更早被识别和诊治。
三、“三驾马车”策略
中国的AIDS从1985年首例报道至1998年流行呈上升趋势再到2003年开始国家免费治疗,各地的CDC在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2008年,各级CDC重点解决发现和筛查患者及初步治疗的问题;2008—2015年,诊疗工作逐渐向传染病医院转移,主要承担推广规范化抗病毒治疗的任务;2015年至今,诊疗重心再一次向综合性医院转移。CDC、传染病院和综合性医院在HIV感染的防治上逐渐形成了“三驾马车”并进的趋势,新的时代需要多学科合作解决HIV感染的并发症、长期存活乃至根治的问题,综合医院作为一匹“新马”在新时代的任务中更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
2013年北京市新发HIV感染者病例中有58.3%在医疗机构被检出[17],提示大型综合性医院的HIV检测也可成为发现感染者的有效途径。CDC设立的VCT站点因高危人群的主动检测意愿扩大了主动筛查的新发病比例,同时,不能忽视非传统高危人群的被动筛查,而这一部分工作将由医疗机构人员通过识别并主动提供检测来完成。2003—2014年北京协和医院门诊与住院部共进行了HIV抗体筛查715 421人次,初筛阳性1 012例,占0.14%,确证阳性776例,占0.11%。检测阳性率从2003年的0.05%至2014年的0.17%,逐年上升,患者就诊的科室主要为内科、急诊、皮肤科、外科、五官科及口腔科、妇科、体检中心,其中内科占比超过50%[18]。提高综合医院各科室临床诊疗人员对于HIV感染者非特性症状的识别以及在手术治疗、侵入性操作前进行HIV抗体的筛查将有助于早期发现HIV感染者,有效降低晚发现的比例。即使感染者CD4+T细胞较低,出现了各种复杂的感染和临床情况,提高临床医生对HIV感染的认识,缩短患者就诊时间、减少就诊次数,也有助于患者获得相对较好的临床结局。
ART延长了HIV感染者的生存寿命,同时也改变了HIV感染者的疾病谱。AIDS定义性疾病的减少,HIV相关非AIDS定义性疾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迫切需要多学科合作展开疾病的全程综合诊治和关怀护理。HIV相关非AIDS定义性疾病治疗成功与否成为决定预后及降低死亡率的重要因素。目前仅以CDC和传染病医院进行AIDS抗病毒治疗或预防已不适应AIDS流行的趋势,AIDS诊疗重心应考虑由专科医院向综合医院转移。2018版中国AIDS诊疗指南中首次提出了HIV感染全程管理的概念,攻克AIDS需要多学科综合协作,共同支持[19]。当前AIDS防控的“三个90%”的目标虽未在2020年达成,但“四个90%”的目标已然提出,其中第4个90%目标即90%治疗后病毒抑制的HIV感染者能够获得较好的生存质量并回归社会。未来AIDS的诊疗工作或可以综合性医院联合各级CDC及传染病医院的形式开展,建立以综合医院为主体的国家AIDS临床中心:以各级CDC在流行病学防控的积极作用为基础,保证传染病医院对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的推广工作,发挥综合医院对于HIV感染者全病程管理模式的优势,为HIV感染者提供更好的防治和诊疗服务,提高生存质量。
四、结语
HIV感染者发现晚是我国目前治疗AIDS的一个主要难点和挑战。AIDS诊疗重心向综合性医院倾斜,在综合性医院进行筛查以早期发现病例成为当下降低HIV感染者晚发现比例的一个重要措施。不仅如此,感染者进入AIDS期后复杂的病情导致患者辗转不同医院、不同科室就诊的现象也提示了综合性医院以感染科为中心开展不同临床科室多学科合作诊断AIDS的重要性,并为患者在长期治疗后因HIV相关非AIDS定义性疾病的诊疗提供更好的治疗措施和管理。CDC、传染病医院和综合性医院将成为“三驾马车”共进的形式,综合医院将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可以为AIDS患者从流行病学、临床治疗到预后管理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