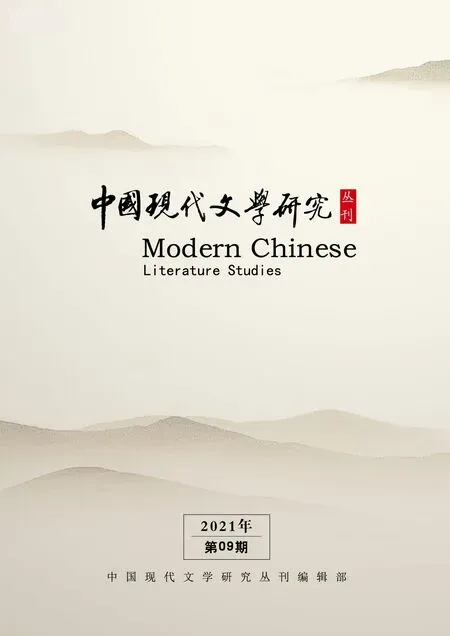京派师承关系的多重意蕴※
2021-04-17陶梦真
陶梦真
内容提要:相对于一般的文学社团流派而言,京派的组织形式较为松散,概念也不够明晰,而师承关系构成了我们重新理解京派的一个视角。京派中师承关系具有多重意蕴:首先,它广泛地存在于京派文人之中,通过校园环境、文学刊物及社交集会等多种形式凝聚起京派文人的交流与延续;其次,师承关系也带来了京派边界的流动与成员的复杂,尤其体现在京派文人对青年作家的深刻影响;最后,师承关系直接参与了京派的文学史建构。
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中,京派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严格来讲,它并不符合一般文学社团或文学流派的定义。首先,它不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拥有统一主张和明确成员的文学社团,京派并未提出独立的章程、固定的成员名单以及共同的文学口号,它的组织形式相对松散。其次,京派成员的内部差异较大,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苦雨斋文人更多表现出传统士大夫作风,书写湘西世界的沈从文更富有乡土气息,而留学欧美的朱光潜、梁宗岱等知识分子则更加洋派,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文学文化背景,因而文学追求与创作风格也并不一致。最后,很多“京派”成员并不承认自己的“京派”属性,在1930年代引发广泛讨论的“京海之争”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认领“京派”的称号,被视为京派作家的萧乾、师陀等也曾公开否认京派的存在,或否认自己是京派成员。这就使得京派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特殊的面貌,一方面文人之间有着频繁的交往与较强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又没有形成鲜明的边界和明确的群体意识。从师承关系的角度审视京派,我们发现它不仅构成了京派文人的交往方式,凝聚了京派文人的群体力量,推动京派边界的复杂流动,还在文学史意义上直接参与京派概念的建构。
一 存在与凝聚
京派虽然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社团流派,但它作为一个文学现象或文人群体,客观存在于文学史的发展建构中,确是无可争议的。当下对京派的定义往往依据文人的不同来源、文学风格的不同特点,将其划分为几个部分,这中间存在一个共性,即:北平大学师生的身份,这一共同身份所带来的师承关系不仅广泛存在于京派文人群体之中,还对京派的凝聚和建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对京派成员的划定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提出,京派的主要成员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二十年代末期语丝社分化后留下的偏重讲性灵、趣味的作家,像周作人、废名(冯文炳)、俞平伯;二是新月社留下的或与《新月》月刊关系较密切的一部分作家,像梁实秋、凌淑华、沈从文、孙大雨、梁宗岱;三是清华、北大等校的其他师生,包括一些当时开始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像朱光潜、李健吾、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萧乾、李长之等。这些成员的思想、艺术倾向并不完全一致。”1吴福辉在《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京派小说选〉前言》一文中指出:“‘京派’可以导源于文学研究会滞留北方,始终没有加入‘左联’的分子。逐渐地,清华、北大、燕京几个大学的师生合成了一个松散的群体,先后出版了带有初步流派意识的《骆驼草》《文学月刊》《学文月刊》《水星》等刊物。”2再如许道明在《京派文学的世界》中强调京派应包括这样几部分人:其一是1920年代末语丝社分化后留下的一批作家;其二是现代评论派、新月社留下或与之关系密切的作家;其三是坚守《浅草—沉钟》阵地的一些作家;其四是北大、清华等校的师生,主要分布在平津和山东。3综合考察以上几种对京派的研究与界定,大致不脱离语丝社后期、新月社后期以及清华、北大等北平大学师生的范围。而实际上,无论是以周作人、俞平伯、废名等为代表的后期语丝社,以梁实秋、沈从文、叶公超等为代表的后期新月社,还是以朱光潜、梁宗岱、卞之琳、何其芳等为代表的大学师生,他们或任教,或就读于北平的高校,都满足北平大学师生这样一种身份。师承便构成了京派文人中最为广泛的人际关系。
师承关系首先影响到京派文人之间知识的传授和思想观念的传递。课堂之上,老师直接向学生传授知识、学问,学生有选择地吸收老师的思想观念,能够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的师生之间便构成了师承关系。除了院系正常开设的课程之外,还包括演讲。而在课堂之外,一方面,北平各大学的校园文学社团颇为盛行,大大小小的学生社团为了增强影响力和组织性,往往会邀请老师作为指导,如周作人、胡适等都曾是新潮社的指导老师;另一方面,师生之间并不拘泥于授课交流,学生可对“心仪”的老师书信自荐、登门拜访,老师也可对“相中”的学生扶持称许、多加提点,在这般交流之中逐步形成思想观念或文学主张上的某些共识。师承关系的达成往往不会仅停留于课堂之上,而是渗透在日常的生活交往之中,例如书信往来、聚餐集会等。1920年代,周作人身边就围绕着废名、俞平伯等密切交往的弟子,此外,周作人还通过授课、讲演、书信往来等各种形式结识了不少青年学生,提携并影响了凌叔华、梁实秋、冰心等人的文学发展。1930年后与俞平伯、废名、冯至、梁遇春、徐祖正、沈启无等学生共同支持起《骆驼草》刊物,构成了京派文人较早的活动空间。
其次,师承关系也对京派刊物的创办及影响力的扩大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媒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报刊杂志逐渐成为文化权力的象征,知识分子的话语若想实现正当化与权威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力,通常离不开报刊杂志等媒介的宣传力量,而籍籍无名的青年作家很难得到发表文章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作家如果得到前辈作家的指导与扶持,就会比较顺畅地走上文学之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前辈作家进行密切的交流往来,在文学思想与创作理念上受到前辈作家的影响。以文学刊物为中心也构成了现代师承关系的一种类型。
沈从文是在诸多前辈学者的提携下走上文坛的,1920年代,郁达夫在沈从文生活无依时为他声援并推荐发表他的文章,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他的作品,胡适聘任他为中国公学讲师,为他解决生活、工作中的诸多问题等等。进入1930年代以后,沈从文也逐渐将这种师长辈的提携之情传递给下一代年青作家。其通过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教学平台,《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等刊物媒介,以及自己在文坛的声名,为诸多青年作家写序、修改文章、谋求作品发表和文集出版的机会,经他扶持发展起来的青年作家有卞之琳、何其芳、萧乾、汪曾祺等,他们日后都成为京派延续的中坚力量。既无背景,也无声名的青年作家,只能凭借着热情和执着四处投稿,如沈从文一般凭借着运气与才气获得赏识并成为文坛大家的毕竟是少数,还有更多的文学青年因投稿无门,不得已而改弦更张,另谋出路。在师承关系中,老师大多是文化权力的象征,他们掌握着文学刊物或人脉资源,能够为学生的发展提供相应支持,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给予一定的指导和修正,从而达成影响与认同。这种互动并不仅是青年学生受益,对老师的办刊理念和文学主张都是一种支持。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人事层面的推举和扶持。这种方式虽然不涉及观念的传承,但在文学资源的获取与文学平台的提供方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为师承关系的发展和建构提供了基础。如胡适运用自己在文坛的地位及资源扶持了不少京派文人,尤其是力排众议,聘请高小学历的沈从文担任中国公学的老师,教新文学和创作。1930年,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携眷北上,并于1931年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这一变动深刻影响了京派文人群体聚集交往的局面。胡适北上之后带动徐志摩一同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同时其在任职期间聘请了朱光潜、梁宗岱、梁实秋等多位学者,为京派文人群体的凝聚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平台。
二 流动与复杂
师承关系在凝聚京派文人,推动京派代际传承等诸多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师承关系是一种开放流动的关系,它既不具有永恒的凝聚力,师生之间在人情上、观念上都会发生分歧或转向,也不局限于一一对应的师生之间,学生不必仅跟随一位老师,老师也可以培养多位学生。这在一方面使得京派形成了相对宽松的氛围,另一方面也导致京派边界的模糊化和动态化。
京派周边也有很多青年左翼作家,他们或多或少与京派文人之间存在着师承关系,王西彦就是其中之一。王西彦与沈从文的师生缘分开始于小说《车站旁边的人家》,这篇小说创作于1933年上半年,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王西彦在《我的第一篇小说》中回忆:“我把稿子装进信封,投寄给天津一家大报的文艺副刊,去试一试难测的命运。大概是第五、六天吧,总之不满一周,编者的回信就来到了,他很快给我写了一些鼓励的话。随后,小说也很快就被刊登出来。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命运原来并非难测,尝试竟然能换取成功。”4王西彦在此文中明确提出,《车站旁边的人家》是他的第一篇小说。但据王西彦的学生艾以发现,王西彦在发表这篇小说之前,“已在多家报刊上发表了《残梦》《铃凤姑娘》《冬夜》《高六嫂》《仇》《大愚哥哥》《野菊花》七篇小说。此外,他还翻译了《询问》(契诃夫著)、《奖章》(Fyederie Butat著)两个短篇小说以及若干篇散文、小品、读书笔记等”5。他认为,王西彦的第一篇小说是发表在《橄榄月刊》第三期上的短篇小说《残梦》,发表时间是1931年7月5日。
不管艾以对“第一篇小说”的考证是否精准,在《车站旁边的人家》发表之前,王西彦已经发表过几篇原创小说,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为什么他要将《车站旁边的人家》视为自己的第一篇小说?作家对第一篇作品的认定往往意味着对其文学创作起点的考量。从刊物媒介来看,创作于1931年的《残梦》发表于南京线路社出版的刊物《橄榄月刊》,这一刊物在影响力与传播度上自然都不及《大公报》。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王西彦认为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这篇小说正式开启了他的创作生涯。这篇小说发表之后,王西彦开始时常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由此加入了以沈从文为核心的不定期聚会。
这样的聚会使得作家与青年能够进行充分的文学交流,作家在谈话中自然地传达自己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态度,青年不经意间受到感染或影响,群体的认同感就这样生发开来。王西彦回忆沈从文在集会中表达的文学观念:第一是一种文学态度的坚持,要专心写作,集中全部的精力于文字之上;第二则是文学功用观的表达,文学的首要职能便是为艺术;第三是文学技巧的启发,需要磨练运用文字的功力。沈从文有着极为严肃的文学态度,他反对文学的玩票、白相,反对文学的差不多现象,实际上都基于这种对文学纯粹、严肃的态度。此外也使得青年收获更多的文学人脉资源。除了组织青年作家,沈从文还会邀请相熟的名家好友,如王西彦便在这样的聚会上结识了陈源和凌叔华。这也是沈从文拓宽青年作家文学资源与文学视野的一种方式。
王西彦尽管是一位左联作家,但凭借与沈从文的交流与交往,以及对沈从文文学艺术观念的理解与接受,他坚信沈从文并不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刻意站在左翼文学阵营的对立面,而恰恰是因为他对政治的不敏感,他对文学艺术的纯粹追求,导致他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置于斗争之中。细读《宽厚的人,并非孤寂的作家——关于沈从文的为人和作品》一文,王西彦的情感之真挚、深沉实在令人动容,文中细数恩师对自己的帮助,交往的细节,充满了对沈从文人格与文风的尊重与向往。尤其是对沈从文文艺思想的理解和体察,让人不禁感慨,反倒是一个左联作家对沈从文的体察更为包容,更为细致,更为贴切。
如王西彦这般围绕在沈从文周围的青年作家有很多,而且其中不少都是左联作家,如杨刚、李辉英、田涛等,他们不是京派作家,但的确深受京派的扶持与影响。看上去这些青年作家属于左联,应该是与京派对立的关系,但就实际影响而言,这些左联青年在踏上文坛之初对京派文人有着相当程度的认同感和依赖性,甚至可以说是京派文人引领他们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还有一些青年作家一直被视为京派的新生力量,如当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读书的青年学生,还有部分已经成名的青年作家,他们几乎完全是在京派师长辈的提携、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如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萧乾、林庚、芦焚等。但他们往往并不承认自己是京派成员。以卞之琳为例,京派的前辈作家对卞之琳的提携与关怀几乎可以说是面面俱到的。卞之琳最初写诗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当时徐志摩讲授英诗这门课程。此时卞之琳的诗作大多经由徐志摩推荐,发表在闻一多、梁实秋、朱湘等主编的《诗刊》上。卞之琳的第一部诗集《三秋草》也是在沈从文的资助下出版的。京派文人对卞之琳的提携还体现在不遗余力地支持他的文学事业,推广他的作品,扩大其文学影响力。如1934年秋,10月10日《水星》月刊创刊,卞之琳负责编辑工作,编完一卷共六期。这期间,李广田陪同卞之琳赴八道湾周宅,向周作人约稿,周作人慨然应允,不久即写成《骨董小记》(刊载于1934年《水星》第1卷第2期)、《论语小记》(刊载于1935年《水星》第1卷第4期)。1939年1月21日,卞之琳写成短篇小说《红裤子》,后发表于昆明《今日评论》,被叶公超译成英文,发表于英国《人生与文学》,被卞之琳在西南联合大学的同事白英编入伦敦1946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集》,后来又被收入美国王际真编的《中国抗战小说选》。卞之琳的诗集《三秋草》出版后,朱自清还为他写了批评文章,介绍这部诗集。
卞之琳感念京派师长对他的指导与扶持,他曾回忆自己的诗歌风格受到闻一多的影响:“这阶段(指1930—1932年大学毕业之前)写诗,较多表现当时社会现实的皮毛,较多寄情于同归没落的社会下层平凡人、小人物。这(就国内现代人而论)可能是多少受到写了《死水》以后的师辈闻一多本人的熏陶。”6总体而言,卞之琳在这一阶段与新月派文人走得比较近,尤其是学习闻一多、徐志摩新诗观念,讲求格律,诗风整饬,断行均齐。但他似乎并不认为自己是京派中人,他在总结自己写诗的不同阶段时,提到1933年至1935年“主要在郑振铎、巴金这两位热情人的感染和影响下,我开始在学院与文坛之间,‘京派’(这里用的不是当时流行的自高或被贬之词)与‘海派’(这里不含贬义,不是当时真正的所谓‘海派’)之间,不论见面不见面,能通声气,不论认识不认识,相处无间”7。卞之琳说自己是在“京派”与“海派”之间,虽然没有排斥京派,但也隐含了自己不属于京派的意思。这一总结是在“京海之争”尘埃落定,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之际进行的回忆,相对客观地表达了卞之琳的态度。
卞之琳对京派文人的感念主要基于学生时代各位师长的提携之恩,而到了1930年代后期,卞之琳的诗风发生了比较明显的转向。1938年,卞之琳同何其芳及沙汀夫妇共同访问延安,在延安“邦家大事的热潮里”8写诗,结集为《慰劳信集》。不同于早先“古镇的梦”“断线的风筝”“悲哀的种子”“暮色苍茫的古镜”等带有浓郁的象征意蕴和情感色彩的丰富意象,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在题材内容和诗歌风格上都有了明显的转变,例如诗歌书写的对象有《给前方的神枪手》《给修筑飞机场的工人》《给一处煤窑的工人》等,诗歌采用的意象有“子弹”“起身号”“金丹”“海洛因”“白面”“毒药”等等,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尊重与同情,充满了对苦难现实的书写,充满了对胜利未来的向往。但《慰劳信集》并不等同于一般的抗战宣传诗,卞之琳对意象的运用,对情感的重视,对诗歌形式的试验仍然渗透其中。这一转变显然与卞之琳亲历延安风貌有关,但同样重要的,是卞之琳师承的文学理念也已经悄然发生了转向。
京派青年一代作家的模糊态度有着颇为复杂的情况,在师承关系的影响下,他们曾经有过共同的文学追求或文学活动,甚至形成了彼此认同的文学观念,但是后来或者转承他师,或在某种影响下思想倾向发生了转变,抑或原本就蕴含着不同的文学追求,受到某一因素的激发而显露出来,彼此之间的凝聚力就不那么强烈了。这就造成了京派内外存在一支边缘化的力量,他们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介于是京派和不是京派之间,但毫无疑问地与京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这种联系正是通过师承关系凝聚且传递的。
三 追忆与建构
师承关系不仅存在于京派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还直接参与了京派的文学史建构。京派的文学史建构离不开京派中人,尤其是当年的学生辈对师辈及京派的回忆。20世纪80年代前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文学地位逐渐得到了公正客观的评价,学界出现了沈从文研究热潮,这离不开思想解放的时代大环境的影响。首先是海外汉学家对沈从文的研究对大陆学界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如1979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分别在中国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该著对沈从文与鲁迅的介绍篇幅基本持平,甚至沈从文的分量要超过鲁迅,这在令大陆学界震惊的同时也引发了更为深刻的思考。此外,还有金介甫、傅汉思等美国汉学家都对沈从文的生平著述与文物研究进行了介绍,并促成沈从文在1980年访美。而在这之后,大陆学界对沈从文的重新评价与再认识,离不开京派中人对沈从文京派时期的追忆。
1980年,朱光潜应《花城》编辑的邀请,写了一篇谈沈从文的文章《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发表于《花城》1980年第5期。这篇文章回忆了他与沈从文朝夕相处的时光,并且认为,在军阀横行的黑暗时代,“在北方一批爱好文艺的青少年中把文艺的一条不绝如缕的生命线维持下去,也还不是一件易事”9。在朱光潜看来,京派是有着独特的历史功绩的,对于在黑暗时期维持文学的命脉做出了重要贡献。朱光潜此文正如标题一样,是将沈从文的人格与他的文艺风格结合在一起,以沈从文手写的书稿为例,说上面总是密密麻麻的一片蝇头小草,“我觉得这点勇于改和勤于改的基本功对青年作家是一种极宝贵的‘身教’,我自己在这方面就得到过从文的这种身教的益处”10。应该说,自沈从文被定性为“粉红色文人”,对沈从文的评价多是负面的,朱光潜此文不仅为沈从文正名,也为京派正名,拉开了大陆学者重新认识、评价和定位沈从文的序幕,同时以历史参与者的身份讲述京派的存在,使得京派浮出历史地表。除此之外,对沈从文的追忆与再认识更多得益于沈从文的学生,如1989年出版的《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除了收入巴金等同辈人的回忆文章,马悦然、金介甫等海外研究者对沈从文的追忆及研究外,其余参与纪念文集写作的赵瑞蕻、王辛笛、常风、卞之琳、荒芜、王西彦、严文井等,大多数都是沈从文的学生,他们有的不是京派成员,但与京派关系比较近。
在诸多京派的学生辈作家中,萧乾颇为积极地参与了京派的文学史建构。萧乾不赞成“京派”这种说法,1989年他在接受王嘉良、马华的采访时说道:“我觉得用‘京派’的概念来包括当时活动在北京一带的作家,本身就不很科学”,“划分文学流派,当然可以考虑地域的因素,二三十年代,在北平一带的确聚集过一批作家,经常聚会的地方是来今雨轩,常去的作家有朱光潜、梁宗岱、沈从文、杨振声、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吴伯箫、严文井等。但这些作家的文学见解和创作特点并不是很一致的。讲文学流派,不能只考虑地域因素,主要看作家间有共同的创作倾向,共同的创作特点等等”。仔细探究萧乾的意思,他其实并不否认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一带存在一个作家群体,他显然不认可“京派”的说法,却也在无意中开列了一张京派成员的名单。
1989年12月9日,他曾致信严家炎“承惠赠新作《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非常感激。我首先自然先拜读了关于京派的那章,深感你持论公允,敢于冲破五十年代的框框。尤其对沈从文的评价,甚是精辟大胆。不过三十年代在一道写小说的,如芦焚、祖春(名字我一时记不起)似也可提一笔。此外,冰心的小说算不算京派?还有林徽因”11。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专门有一章“京派小说”,从京海之争讲到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汪曾祺等京派代表作家,萧乾读后感念严家炎对京派及沈从文的公允评价,同时为严家炎补充了芦焚、祖春(应为刘祖春,曾在沈从文的帮助下在北京大学旁听,后考入北京大学,早期作品多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冰心、林徽因这样几位作家。
除了列举京派成员的名单之外,萧乾还补充了诸多京派发展的历史细节,纠正研究的一些偏差。如1995年12月14日萧乾致信吴福辉:“你在书中一处说‘大公报文艺奖金’为‘京派奖金’。我想向你提供一点背景。当时评委及我自己都注意到这个京海派问题。三个奖中最重要的为小说。最初京、海以及在武汉的凌叔华都同意把小说奖给《八月的乡村》作者萧军。但他通过巴金向我表示不愿接受,所以才改给芦焚(师陀)。为了向你更正此点,我曾特意函李小林,请她向巴老核实。顷来过电话,说确是萧军向巴金表示不愿接受。想来是出于政治立场。巴老一再强调萧军本人拒绝接受。因此,至少我们原本的出发点并不想把它搞成为京派奖金。”12后来吴福辉的确在研究中运用了这一史料,纠正了原本“大公报文艺奖金是京派奖金”的观点,并得出结论认为是左翼文学阵营将“大公报文艺奖金”从淡化派别之争的出发点,推向了突出流派壁垒的结点。
师承关系在许多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中都存在并发挥作用,如东北作家群几乎是在鲁迅的扶持下登上文坛,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师承关系,但师承关系在京派中的存在是最为广泛,也是最为持久的,是最具凝聚力,也最富流动性的,尤其是在文学史意义上参与了京派的建构,这在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中是较为特殊的。从师承关系的角度探讨京派,不仅仅是为京派找到一个自洽的逻辑,更为现代文人群体的建构提供一种新的范式的思考。
注释:
1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2 吴福辉:《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京派小说选〉前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4期。
3 许道明:《京派文学的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4 王西彦:《我的第一篇小说》,董大中编《我的第一篇小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6页。
5 艾以:《追忆恩师王西彦——王西彦先生逝世五周年祭》,《海上文谭》,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61页。
6 7 8 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卞之琳文集》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7、447~448、451页。
9 10 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朱光潜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91~492、492页。
11 萧乾:《致严家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九日)》,《萧乾全集》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2页。
12 萧乾:《致吴福辉(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萧乾全集》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