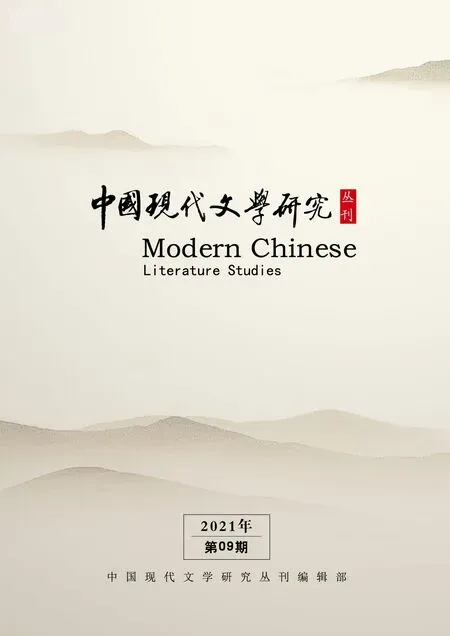论北美新移民华文小说中的亲缘关系叙事※
2021-04-17朱旭
朱 旭
内容提要: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西之间的双向互动,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聚焦作为家族文化核心的亲缘关系叙事,对原生民族与民族文化重新审视,强化着民族认同感。通过对婆媳关系的书写,重估传统人伦,强调东方式亲缘伦理是共通的情感归宿和精神家园的融汇;透过父与子的冲突,重构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史诗,突破东、西文化的迷踪,重拾文化身份;自我与家族关系的呈现,则突破内部框架,将家族中的亲缘关系向外拓展,个体出走意味着从既定关系中脱离,进而重新塑造主体,并尝试建立一种新型人类关系。这样的亲缘关系叙事由此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范式:在保留充满生命活力的血脉的同时,彰显传统之精韵,重构充满现代精神的人类关系。
新时期伊始走出国门的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对于母国传统和民族文化认同有强烈的切肤之感,更直面中国社会的转型与融入世界的大潮,他们对于小说中亲缘关系的书写,接续“五四”对旧家族制度的反省,也在同源异流的书写中尝试对东方伦理人情的曲线回归。重视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的文学创作与母国文学乃至文化传统的历史联系,“重视这种历史关联,通过系统总结,在不同时代作家相近或相似的创作经验之间,建立一种历史联系,形成一种经验的谱系,无论是对于已有经验的传承,还是对于新经验的创造,都有重要的意义”1。这样的尝试并非为封建家庭文化正名,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家庭亲缘关系进行更新乃至重构,当然这种尝试是从民族本身的特点出发,又熔铸进了现代精神与世界意识。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的家族亲缘关系叙事——这一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是伴随着中国文化、文学现代性的进程而生发,和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节拍而跳动的。在充分汲收中国古典文学素养与“五四”现代文学精神的基础上,熔铸进西方现代文学精髓,试图跨域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想象,融汇进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也是海外新移民作家们在全球化时代,通过家族叙事进行文学艺术探索,通过对原生民族与民族文化的重新审视,强化着民族认同感。
一 婆媳关系:传统人伦的价值重估
“一般意义上讲,我们认为家族文化主要由三个不同层面构成,一是它的人伦秩序层面,即家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体现的一种尊卑上下、贵贱长幼的伦理秩序……存在于家庭中的等级秩序无疑是社会政治生活中君臣关系的折射。二是它的道德情感层面,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的家庭伦理……三是它的价值理想层面,家庭不仅体现为具体的生存场所与人伦关系,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价值上的终极关怀,人们对家的感情既表现为对具体家庭的眷恋,有时也把它视为精神的家园与情感的归宿。一个人的无家可归更多的情况下意味着精神上的无所归依。”2在小说创作中,一旦涉及亲缘关系的书写,上述三个层面无法完全剥离开,呈现交织缠绕的状态。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在进行亲缘关系叙事时,既大胆暴露家庭等级秩序的不合理,也能看到其中蕴藏着具有独特东方韵味的家人间的脉脉温情,更能深入价值理想层面,洇染出对于情感归宿和精神家园的终极命题,从而重估传统人伦。
在家庭中,每位成员身份的确认,一方面因为血缘得以天然认定;另一方面,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成员之间则通过命名而使身份得以确定。亦即在被命名身份这个层面而言,它与符号学所谓的“象征秩序”在功能上具有一致性。婆媳是本无血缘的两人,通过命名得以获得身份的确认。中国传统伦理规约之下,婆媳之间形成了显著的等级关系。在封建家庭中,被赋予的身份决定了个人在家庭中所处的位置,因而儿媳妇们对于婆婆的言行不敢也不能反抗。
在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下,对家庭伦理,尤其对婆媳关系进行书写,并非为封建家庭伦理正名,而是从民族本身的特点出发,熔铸进现代精神与世界意识的更新,重估传统人伦。从而深入价值理想层面,洇染出对于情感归宿、精神家园追寻的人类终极命题。
张翎的长篇小说《金山》对于婆媳之间相处的书写,并未将麦氏简化为脸谱化的恶婆婆形象,而是饱含着悲悯之情。用抒情的笔调,将婆媳二人对于家园的坚守,展现得动情又动人。如果说麦氏和六指的婆媳关系还有些许温情存在其间的话,那么沈宁《泪血烟尘》中姚凤屏与婆婆之间的相处,则完全是封建家长制对人戕害的典型例证。小说的前半部分详细叙述了姚凤屏与婆婆一起生活在乡下祖宅时的生活,将婆媳间的交往刻画成典型的封建婆媳关系,但在田方岳立业后要求出去单过等关键时刻,婆婆表现出的通情达理,又显示出家庭温情的一息尚存。姚凤屏对婆婆的尊重,以及小说后半部分重点叙述的,姚凤屏每每在危机时刻表现出来的坚强与韧劲又让人心生敬佩之情。女性在传统中国家庭中的地位尽管弱于男性,但她们顽强的生命力却更胜一筹,她们在封建家庭中浸润的就是封建文化,三从四德、三纲五常更是将传统家庭中的女性束缚。但在这种不利于自身的环境中,东方女性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精神力度却是十分震动人心、令人动容的。
如果说张翎的《金山》和沈宁的《泪血烟尘》中的婆媳关系,是典型的封建家庭模式的话,那么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中所描写的冯婉喻与婆婆冯仪芳之间的关系,则承续的就是《金瓶梅》《金锁记》等对畸形社会下“欲魔”的凸显。六指、姚凤屏、冯婉喻是东方文化中典型的“大地圣母”形象,她们隐忍、坚韧,包容着一切,宽容着一切。她们的婆婆又是典型的封建家族的婆婆,她们宽待儿子,苛待儿媳,甚至用打骂来管教儿媳。尽管在这些小说中,都细致描绘了“恶婆婆”对儿媳们的苛待乃至虐待,但作者们在继承“五四”作家们对封建家族文化大胆暴露,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基础上,更将重点放在了这些女人,这些典型东方女性对家庭的坚守之上。
二 “父与子”:家国同构的寓言
西方从原始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中国形成了由“家”及“国”的社会格局,亦即“家国同构”,并在此基础上绵延千年。所谓“家国同构”是指“天下与家的互文互喻关系。这种关系蕴含着中国文化结构的基本隐秘,并规定着受这种结构制约的中国文化人(文化文本的创造者)的主要行为模式”3。在这种观念甚至说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下,中国小说对于亲缘关系的书写,力求以家庭成员的生命感悟、命运遭际,和家庭、家族的兴衰盛亡,隐喻整个社会、国家的命运。“五四”时期对于家族中亲缘关系的叙事繁盛,与社会、国家的阵痛形成某种同构。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小说中的家族内部的亲缘关系叙事,在与“五四”时期的民族国家隐喻形成共鸣的同时,还要面临更为复杂的景象:具有新潮思想的年轻一代不仅要如“五四”时期一般挣脱象征封建传统桎梏的传统家庭,还要突破东、西文化的迷踪找到自我的文化身份认同。因而,在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下,在特定年代里,由历史引发的家族成员内部的隔膜和由文化冲突引起的代际冲突便相互缠绕在一起。
质言之,北美新移民作家在其小说实践中,尝试着将家族历史与种族历史有机融合,从一个全新角度写出了20世纪中国现代化史诗。这不仅沟通了“五四”现代文学创作,更与20世纪末中国大陆当代文坛相连接,其中具有鲜明的民族国家意识和历史线索,用个人家族写民族国家的企图心也显而易见。同源异流的家族叙事因而呈现出鲜明的“家国同构”性。而在这其中,对于父与子之间关系的书写显得尤为突出。
“父”与“子”不仅是家庭单元中的亲属关系,更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对文化层面乃至社会政治制度层面权力关系的一种隐喻。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逐步发生变迁,传统封建文化滋养下的“家”也历经从旧到新的解体与再生成过程。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家庭变迁于是成为社会转型的象征,家庭中“父”与“子”之间以及社会、国家中“父”与“子”之间的复杂、朦胧的关系成为作家们争相摹写的对象。“父子问题浮出水面,是新旧文化转换一个方面的现象,因为父子这个意象,作为政治的隐喻、纲常的表述、孝的具体实现等等,都在这个意象的涵盖之中”4。
袁劲梅的小说《忠臣逆子》就是典型的以写家庭中的父子冲突来映射社会变革。戴家一代代的“子”忤逆一代代的“父”,从“我”曾爷爷到“我”儿子,戴家五代人都先后历经了父子冲突,尤其是儿子忤逆父亲。从爷爷到“我”都在不断地忤逆自己的父亲,遵循的是同样的中国社会革命的逻辑,似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的自我解剖的不断推演,尽管有西方文化的影响,终归还是中华文化内部的调试。与冰心《斯人独憔悴》中的颖石、颖铭,巴金《家》中的觉慧等对于“父”的反叛类似。到了“我”儿子这一代,忤逆的逻辑依凭有所改变,是在东、西两种文化体系的对照下进行的反抗。但剥去表象的外壳,内核却是一致的:反抗“父权”。戴氏家族五代,一代一代不遗余力地革上一代的命,这种“进步”与“革新”不仅是戴家的历史,也是中国近现代的风云变幻史。在戴氏家族一族之中反复换位、不断颠覆着的是“进步”与“反动”、“忠臣”与“逆子”、“革命”与“反革命”等相对相生的“戏局”。家族中的一代代忤逆,不仅是家族中的父子冲突,更与社会“革命”对照、同构,似乎都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自我循环境地。
在上述意义上观照,“父”与“子”的对立乃至冲突具有了一种更加深广的历史寓言性与文化象征意味。袁劲梅通过书写戴氏家族子孙不断“忤逆”的家族史,纵贯整个中国20世纪的国族史,不仅自我解剖更是横跨东、西,掺杂着从外部审视母国的视角。这与胡适当年提倡的易卜生的“救出自己”异曲同工。在书写中国经验的时候,袁劲梅以家族的父子冲突隐喻家国的“革命”历史,更是一种对于原生国族文化的沉痛反思。作为跨文化生存的新移民作家,袁劲梅虽然毫不留情地对故土的传统文化、国民性等进行批判,但她不仅依然对故土满含深情,潜藏在文化基因中的母国的民族性也仍然使其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家国同构”不仅是一种具象的书写策略,更是抽象的独特的中华民族意识、思维方式的体现。
严歌苓《陆犯焉识》、张翎《金山》中的“父子冲突”并没有明确的父亲与孩子的矛盾对立,“父亲”作为抽象的力量是落后思想的象征。“子”处于被建构的更重要的位置,他们代表的是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和先进的力量。《陆犯焉识》中的“父子冲突”被置于政治的敏感场域,呈现了政治风云对亲情和人性的戕害,更是反思这背后所体现的深层文化考量。尽管陆焉识最后被平反而归来,但代际间的隔膜始终无法消磨,父子、父女间的情感沟壑依旧未能弥合。张翎的《金山》在跨域、跨文化的书写中,展现华人移民一代与二代的冲突,这样的“父子冲突”不仅是代沟的问题,更掺杂进了故土文化的认同感与民族归属感问题。家庭中的“父子冲突”作为小说叙事的表层结构,指涉的是移民们这一散落海外的孩子群体,对于抽象层面“父亲”,即民族国家和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问题。
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一方面在民族情感上眷恋养育自己的故土;另一方面,又深受异质文化中的浸淫,于是对于母国的民族文化不仅仅限于单纯的认同,而是自内而外进行观照和反省,甚至不惜与“父”“冲突”,以“逆子”的姿态对民族文化发起猛烈的批判,希冀通过文化批判尝试着努力建构民族文化的新范式,非对故国母族不深情无法做到。正如张翎曾言:“放下《金山》书稿的那天,我突然意识到,上帝把我放置在这块安静到几乎寂寞的土地上,让我在回望历史和故土的时候,有一个合宜的距离。这个距离给了我一种新的站姿和视角,让我看见了一些我原先不曾发觉的东西。”5
“父”与“子”的冲突,呈现出人物与家族内、外人物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从而巧妙地将家族与国族放置在一起呈现。在这个繁密的大网上,家族、社会以家族中的人为核心,完成了家庭伦理的政治化和政治的伦理化,实现了家国同构、由一家而见国家的政治性寓言。
与“五四”时期文学创作中“父子冲突”的书写有所殊异的是,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打破了传统家族文化是阻碍个人解放、社会进步之力量的叙事模式。他们将以家族文化为基石的中国传统文化构建成维系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力量,这一力量也是建构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文化资源,从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民族国家想象之途。“父”与“子”是家庭关系中的亲属关联,既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新、旧文化的隐喻,又有在东、西文化间徘徊的意蕴存在;既是海外华人对中国经验的回望与隔着时空距离的观照,也是他们作为世界公民对人性和普世价值的体察。父子的冲突具有了一种更加深广的历史寓言性与文化象征意味。
三 自我与家族:新型关系的尝试性建构
婆与媳、父与子,是家庭内部亲缘关系的重要内容,二者分别代表了家庭内部亲缘关系确立的两种方式。而自我与家族,则突破内部框架,将家族中的亲缘关系向外拓展,将个人与整个家族置放于关系网中进行考察。胡适在论述易卜生的戏剧时认为,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是其作品中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从中胡适发掘出“健全的个人主义”哲学为当时中国之所极需,并进一步提倡《玩偶之家》中娜拉的言行,“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6。同样处于中国社会的转型阶段,面临文化、文学与西方深入的交流互动,与“五四”时期的作家们相比,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无疑注定面临着更多重的困惑。除了来自传统的羁绊与滋养的相对相生,他们的成长背景更为暧昧不明:“共和国传统”教育贯穿他们的青春期;正值青年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壮年时期赶上198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出国潮,便又开始经历东、西文化的拉扯,乃至商业文化的侵蚀。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与具有十足吸引力的新鲜东西相互搅拌、杂糅,难以言说、难以辨明的混沌感萦绕着华人新移民作家们。与汤亭亭、谭恩美等从小接受美国教育的华裔二代不同,这一代北美新移民作家在中国接受了完整的义务教育乃至高等教育,都是在个人价值观成型后才离开中国前往北美。与於梨华、聂华苓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台湾赴北美留学的移民作家不同,北美新移民作家们对于故土中国的情感不仅仅是文化眷恋、文化乡愁,对于社会变革有更有深刻的现实感触,具有强烈的在场感。于是,在这样厚重、复杂、快速新变的背景下成长、成熟起来的北美新移民们,对于自我的认知是更为复杂又显得更为迫切的命题。
第四,“两童”制度、政策层面存在的其他问题。主要包括:1.家庭监护、家庭支持缺位,国家替代监护未能及时跟上,导致许多未成年人处于“失管”状态;2.对于犯罪未成年人的转处措施不足,受制于成人适用的刑罚种类和刑罚结构,过多适用成人的刑罚方法处理未成年人案件,对未成年人复归社会造成许多负面影响(如服刑期间交叉感染,有了犯罪标签影响以后的就学、就业等);3.对于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实施危害行为的未成年人干预手段不足,且欠缺社会支持体系;4.针对问题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导、行为干预等社会专业机构严重不足;5.相关工作人员缺乏必要培训,缺乏应有的保护意识,致使未能在成人社会中广泛形成保护未成年人的意识。
由是观之,“离家出走”便成为寻找自我、张扬自我第一步。
在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下,回望故土的中国经验书写,是典型书写范式。接受新潮思想的年轻一代以“离家出走”的方式宣扬与家庭的决裂,并非北美新移民作家的新创,从晚清到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家族叙事中,“离家出走”式书写就屡见不鲜。这种试图通过“出走”来获得内在和外在新生的模式,在时间坐标轴上与中国现代文学形成观照,在空间坐标轴上又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主题7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北美新移民作家笔下“离家出走”模式的书写,尽管大多返回到中国经验的视野中进行观照,又沉潜到历史的沟壑里进行挖掘,但并非单纯对封建家族文化的大胆揭露与反抗,更熔铸进重构社会和主体之间关系的重要文学命题。
巴金的《家》中塑造的是一个具有启蒙意义、现代精神的个体如何从旧式传统家庭出走,鲁迅的《伤逝》又恰恰证明了这种出走缺乏社会土壤,所谓的现代主体也并未做好足够充分的准备重构个人与家庭、社会的关系。张翎的《花事了》的叙事时间与《伤逝》《家》有部分的重合,又将叙事时间向前扩展,从而将“离家出走”的叙写扩充出了结局的多种样态。花吟云第一次所谓离家出走,其实算不得真正意义上对封建家庭的反叛,而是带有个体尝试性的重建个人与家庭、社会的关系。这种尝试是绵软的、带有妥协意味的。两年后,花吟云果真返回,结果却是亲姐姐已经与自己昔日恋人结婚并育有儿女。于是出走后又归来的花吟云选择了再次出走,这又一次的出走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横竖了无牵挂了”。
李彦的《红浮萍》更将个体的离家出走,与个体的内在裂变相联结,成为个体调试与家庭的关系,建构新型家庭、社会关系的重要尝试。女主人公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中,幼时的雯曾与族中一堂姐相伴玩耍,不过各方面资质都平平的堂姐自不如雯一般众星捧月,雯在学校出尽风头,堂姐连嫉妒的资格都没有。不过一切改变就缘自堂姐的“离家出走”。因为反抗包办婚姻负气离家出走,原本被雯压了一头的堂姐荣耀归来,不仅碾压了雯的自豪,更在政治运动中保护了自己的原生家庭免遭查抄。从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到投入与陕北高官的婚姻,对于雯的表姐而言,这不仅仅是个人婚姻的选择,更是两种生活方式,两种与社会关系建构的不同方式,两种社会形态下个体自我的不同内在属性。
我们无法得知雯的堂姐如何进入这场婚姻,这场婚姻又是否美满,但薛忆沩在其长篇小说《空巢》中,为此类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典型性的婚姻模式掀开了神秘的一角。只不过在《空巢》中,离家出走反抗包办婚姻的是男性一方,薛忆沩这样的安排颇具深意,突破了离家出走是女性解放的书写传统,将问题延伸至普遍性的中国青年的选择和出路问题。同为那个风云际会年代的青年人,共同面临的问题是:用何种方式来处理个人与日益“规定化”“统一化”的生活情境之间的关系;在当时那个渐趋一体化的社会中,自我的张扬是个伪命题还是有可实现的空间。
如果将《伤逝》作为张翎《花事了》、李彦《红浮萍》、薛忆沩《空巢》的一个前文本来进行比较阅读和分析,就会发现在《伤逝》中,子君和涓生通过“离家出走”宣示了个性解放、张扬自我的诉求,是启蒙话语的建构,个体自我与旧家庭、社会形成一种对立关系。更进一步,鲁迅以感伤主义式结局反讽了这种“离家出走”的虚幻性。也可以理解为,在鲁迅所在的那个历史时刻,个人解放、自我张扬,并建立一个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自足的“家”是社会解放的一种指向性的诉求。只不过《伤逝》的尝试并没有成功,但这丝毫不影响这样的尝试体现出对这种“家”之建构的愿景。在张翎、李彦、薛忆沩笔下小说中的那个历史坐标,个人解放和自我张扬已内化为一种社会话语,无论在何种程度上实现,都已经突破了旧家庭传统文化的桎梏,不再受到封建家族文化的强烈拘囿。吊诡的是,在那个历史时间坐标中,封建家庭文化形式上的被摧毁,政治话语似乎又取而代之成为一种新型的个体自由、自我张扬的囿限场。
“横向关注他者世界是近代以还中国文化与思想的主潮,能够转向纵向瞩目自我世界,这自然是百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个质变”8。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对于家庭伦理亲缘关系的书写,谱就的是东方式伦理人情迂回归返的招魂曲。他们对于中国家族模式及其背后的文化隐喻的书写,秉持着现代化重构的立场。这种重构并非完全推翻重造,而是在保留充满生命活力的血脉的同时,彰显传统之精韵,建构充满现代精神的人类关系。就在这种现代化改造和重构中,既坚守住了民族性的血脉,又融入了现代美学风貌,形成了独特而充满生机的文学态势,这样的尝试对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来说,也无疑具有启迪意义。
注释:
1 於可训:《当代文学创作经验亟待进行系统总结——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21届学术年会上的发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
2 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3 李军:《“家”的寓言——当代文艺的身份与性别》,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4 陈少华:《阉割、篡弑与理想化——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父子关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5 张翎:《金山》,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6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现代书店1953年版,第6页。
7 参见陈晓明《汉语文学的“逃离”与自觉——兼论新世纪文学的“晚郁风格”》,《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2期。在此文中陈晓明梳理了西方现代文学的内在逻辑演变,从而提出“逃离是西方文学的一个内在经验”。
8 闫海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国际化与民族化转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