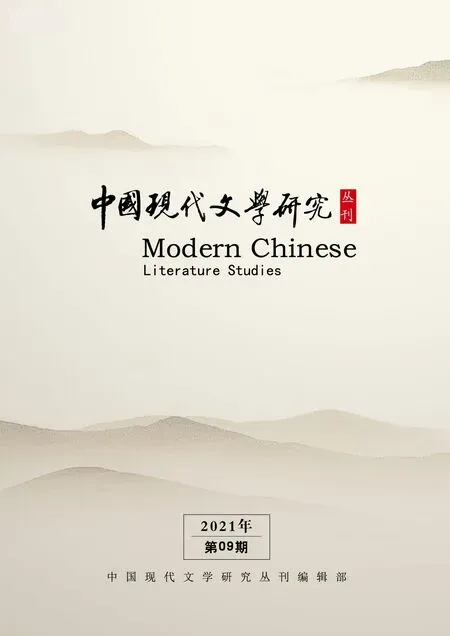启蒙与审美:《子夜》的现代性张力
2021-04-17张辉
张 辉
内容提要:在中西文化碰撞和民族救亡的历史语境中,茅盾对现代中国的现实性书写呈现出启蒙理性与审美感性交织的现代性品格。《子夜》执着于对人的解放与现代都市全景式的理性剖析,并探寻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子夜》反思启蒙现代性,关注都市文明病症,追寻审美救赎。在《子夜》中,启蒙现代性遮蔽下蕴含着审美现代性的反叛,这两股现代性力量构成了茅盾小说的现代性张力。茅盾在现代性体验中的文化想象与伦理道德建构的复杂性,成为一种隐蔽的力量,构成《子夜》现代性张力的心理动因。
现代性是一个充满激变与张力的多元复合体。卡林内斯库明确区分了两种同根同源的现代性:一是社会现代性;二是审美现代性,二者之间剧烈冲突又密切联系。社会现代性延续启蒙运动的传统,推崇理性与科学,宣扬人文主义、实用主义等观念,通常被称为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是作为对启蒙现代性批判与反思的面貌出现,它追求平面化、碎片化、多元化的旨趣,反抗统一秩序与普遍性暴力,关注内在灵性和感性欲望的抒发,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相呼应。“五四”前后,中国现代文学呈现出两种现代性的双重追求。中国化的启蒙现代性成为一个巨大的事实性存在,在1930年代初期最为成熟的作品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然而,借思想文化符号与价值体系的变革以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成为五四知识分子的优先选择。因此,五四文学又表现出明显地对现代主义所代表的审美现代性的试验倾向。
作为新文学的先驱,茅盾具有的强烈的感时忧国情怀,以及对中国现代都市的独特体验,成就了《子夜》多元的现代性品格。然而,《子夜》现代性的多元化特征因过度地政治阐释而被遮蔽于潜文本中。在历史语境与个人审美经验下,尽管茅盾的文学创作有着对宏大叙事的倾向性但又呈现出复杂的文本隐喻。具体而言,在《子夜》的现代性表达中,作家的个人信念与狂热的民族意识融合,内在的家国身份认同外化为对现代化中国的复杂感受。这种复杂的心理投射到文本中,呈现出两种现代性力量的纠缠,即启蒙现代性的缺失、渴望与焦虑同时又导致审美现代性的遮蔽与反叛,这两种现代性呈现对抗又共存的张力关系,构成《子夜》的现代性特点。
一 启蒙话语的主体性诉求与现代性焦虑
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现代性是吸收西方启蒙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和特定历史语境中孕育而生的。西方启蒙理性、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等观念,在新文化运动中掀起思想浪潮,并逐步被赋予具有中国特征的阐释。中国启蒙现代性中的人的解放问题始终与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保持内在的逻辑关系。尤其到了1930年代,救亡成为主旋律,民族意识与政治需求加剧了知识分子对现代性追求的焦虑。这一时期,从政治实践转向文学创作的茅盾,具有强烈的感时忧国情怀和民族国家体认。茅盾对启蒙现代性追求的启蒙主体意识与现代性焦虑意识充分体现在小说《子夜》中。
《子夜》的启蒙现代性对于人的解放的追求,主要体现在茅盾以“人”为中心的启蒙主体意识表达。作为革命文学家的茅盾,寻求以思想文化变革来实现个人解放与中国现代性发展之路,具有强烈的现代启蒙主体意识。一方面,茅盾在步入文坛之初,就提出新文学作家主体应革新陈腐的、非人道的旧意识,发扬独立、自由和人道主义新思想。另一方面,茅盾主张新文学表现的对象主体不再是“非人”状态的、制度化的人,而应该是具有自主意识、时代性的人。茅盾主张文学家应该创作“人的文学”,“这样的文学,不管它浪漫也好,写实也好,表象神秘都也好;一言以蔽之,这总是人的文学——真的文学”1。这种“人的文学——真的文学”观念,强调文学对社会的责任,实质是主张文学创作的启蒙理性原则与人道主义价值观,《子夜》是这一创作思想的代表作品。
茅盾将以“人”为中心的启蒙主体意识作为理论支点,在《子夜》的创作实践中塑造众多复杂的中国“现代人”形象。突破政治标准与阶级分析的视角局限,从人的现代性角度透视茅盾笔下的都市社会人物,更能窥探小说潜在的启蒙话语诉求。《子夜》中的人物是现代化的、时代性的、主体性的“人”。吴荪甫展示出一个有现代思想的企业家的优秀品质和理想抱负,也被赋予生不逢时的悲剧命运。茅盾在《子夜》中还以戏谑的笔调刻画处于现代化对立面的封建旧人吴老太爷、冯云卿、曾沧海等,穿插叙述这些封建个体如何淹没在现代化洪流中。茅盾全景式描写社会的人和事,又始终关怀现代人个体的命运沉浮,呈现出中国社会个人本位逐渐取代传统家族本位的现代化观念的转变。《子夜》书写的人是个体性与群体性统一的人,是血肉丰富的具有自主意识的“现代人”。然而,茅盾对人物的评价衡量是以是否有利于革命发展与民族国家建构为标准的。人的命运与社会的时代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茅盾在人道主义和政治革命需求的价值标尺间摇摆,因此茅盾对于人的自我选择的表现充满矛盾和焦虑。
《子夜》的启蒙现代性追求的焦虑意识,一方面表现在中西或者传统与现代对立的焦虑,另一方面表现在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问题上的焦虑。《子夜》中启蒙现代性焦虑之一,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及中国与西方的对立所产生的焦虑。《子夜》的序曲部分,茅盾用大量笔墨写吴老太爷进城。发疯的汽车、高耸的摩天建筑、鬼怪般的霓虹灯跳跃在荒诞诡异的十里洋场中,这种充满刺激和活力的现代光影声色,带给现代人无限快感,却让封建“古老僵尸”窒息晕厥。现代机械赞颂的神话以强大的力量摧毁腐朽的封建文化。另一位移居上海的乡绅冯云卿在公债市场上倾家荡产。同样,横行乡里的“土皇帝”曾沧海最终被农村革命浪潮所打倒。茅盾对封建秩序的全面溃败的书写中,既有一种对传统落后的怨恨情绪,又有一种强烈的反西方现代性的情绪。
《子夜》的启蒙现代性追求的另一重焦虑是在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问题上的焦虑,即在民族国家现代性主体缺失的情况下,选择何种道路拯救民族危亡,发展现代中国。《子夜》的宏大叙述与主题构架有作家先行的意识形态和主观意图,又依托于客观真实的社会文化语境与中国历史场景。茅盾在小说后记中明确指出,他创作《子夜》的意图与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有关。小说通过对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悲剧结局的书写,喻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民族资产阶级这种反帝反封建的品格与中国革命的目标是相同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资本与手段是建立在对工农阶层的剥削之上的,吴荪甫对待工农阶层极为残酷无情。为了挽救自身危机,吴荪甫加深对工人阶层的剥削,从而激发工农革命浪潮。吴荪甫与工农革命的对立,实质上是现代性选择之间的矛盾。一种是以吴荪甫为代表的以发展民族工业而使中国走上民族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性选择;另一种是通过工农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性选择。在政治意识形态支配下,茅盾对工农革命的现代性之路的理性选择与坚定信念是明确的。但是,茅盾对民族资产阶级悲剧命运的书写,充满了伤痛、感慨与纠结,其实是对民族独立富强发展道路艰难探索的焦虑之感,也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对启蒙现代性追求的焦虑。
现代性追求的主体性意识与焦虑意识影响着茅盾对文学表达形式的思考,这种形式的写作方式能够真正达到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目的。以文学的方式来表达外在的客观历史叙事时,作家的主观自我与文学主体性地位如何,茅盾在具体地文学实践中始终犹疑不定。茅盾在以意识形态限制文学审美形式来表现社会现象以解决社会问题时,生成了一种内在的矛盾心理,在《子夜》中呈现出两种现代性的矛盾关系。
二 现代主义叙事与审美现代性的反叛
“‘现代性’的贬义同它相反的褒义在一种不稳定关系中共存,这种关系反映了两种现代性之间更大的冲突”2。所谓“现代性”的“贬义”及“褒义”即相对于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而言,波德莱尔被视为审美现代性概念的原创者和文学实践者。从五四开始,波德莱尔的作品《巴黎的忧郁》《恶之花》等被译介到中国,作为审美现代性呈现方式的现代主义,也随着西方众多的文艺思潮引入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一部分作家对美学范畴上的现代性进行文学的先锋试验,尤其是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所代表的海派作家,运用现代主义技法书写上海的十里洋场,具有鲜明的审美现代性品格。茅盾的《子夜》同样是对上海都市景观的书写,然而,小说中所显现的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现代性问题的关注占主导地位,以至于其美学概念上的现代性被遮蔽。
《子夜》中,在启蒙理性的大叙述下,仍然可以看到作家个人对都市体验的疏离感与矛盾感的主观表达,让文本显现出另一种审美现代性品格。启蒙话语中对自我与个人命运的关切被置于民族家国的遮蔽下,导致作家在自我和社会关系处理上产生矛盾心理。狂热的民族信念和爱国之情与对中国罪恶境况的怨恨情绪纠缠在一起,造成作家内在世界与外在现实产生巨大的疏离感,这种主体心理的紧张性为创作开拓出个体的美学空间。
一方面,《子夜》的审美现代性体现在茅盾对资本现代性社会的都市病症剖析与批判,即对启蒙现代性的“贬义”面的反思。在《子夜》中,茅盾运用现代主义手法描绘现代都市光怪陆离的现象,呈现了现代人精神的颓废、压抑与苦闷,人际关系的扭曲等现代病症。人的异化是《子夜》关注现代人内在精神,批判资本社会工具理性的另一重要方面。在《子夜》中,茅盾往往将这些都市人物推向艰难选择的环境,来叙述人物的内心独白和意识流露,从而窥探面临都市现实时人物的内在精神世界。吴荪甫强奸吴妈的情节描写,是茅盾表达人物现代病症的妙绝之笔。资本社会令人窒息的生存空间带给人的焦虑、暴躁、疯狂和抑郁都在这一情节得到具有冲击力的表达。暴躁与愠怒充斥吴荪甫内心,罢工工潮、益中公司等周遭所有的不如意都化为野蛮的冲动,他如同正待攫噬的猛兽一般扑向吴妈来满足性的发泄,而后却不自知。这一设计表现出资本社会的挤压下,即使是强悍的工业英雄也无法解决自我苦闷,变异为兽性的“非人化”肉体去释放巨大的抑郁。茅盾运用失去理智狂暴发泄的一幕,透视吴荪甫内心因饱受现代疏离感和抑郁感折磨而造成的人性压抑与异化。可以看到,《子夜》在表现资本社会启蒙现代性追求的焦虑之时,又呈现出对启蒙现代性荒诞与丑恶面的审美现代性批判。
另一方面,《子夜》的审美现代性体现在茅盾对现代人的关怀与审美救赎的探索。茅盾试图为孤寂焦虑的现代人寻求精神家园,为挣扎于异己环境中的现代人探索救赎之路,即回归感性,解放自然。回归感性,回归对人的情感世界的观照,拯救工具理性过度发展导致的人性失衡;解放自然主要指解放人的本性和人的生存环境。《子夜》中四小姐吴惠芳的精神路径和人生选择,是茅盾对现代人的精神关怀与人生的救赎的探索。初到上海,现代都市复杂喧嚣的生活令吴惠芳头晕目眩,既有畏怯又有诱惑。吴老太爷猝死之后,传统的心灵家园丧失,都市生活逐渐令她产生一种无名的惆怅。同样有着失意怅惘情绪的范博文触动了她少女的情怀,都市男女的谈笑戏谑的交往也刺激了四小姐性意识的觉醒。摩登女青年张素素戳破《太上感应篇》的荒诞以及范博文的软弱,为四小姐指引人生自由的去向:去读书,学习新知。摆脱资本社会世俗规则与道德逻辑的束缚,回归感性,解放自然人性,这是茅盾给予现代女性的一种乌托邦的审美世界的想象。同样,茅盾给《子夜》的结局安排也有一种审美隐喻。小说的结尾,吴荪甫最终没有用手枪自杀,而是打算去避暑吹海风,摆脱金融战场,回归到自然浪漫的海滨住所,寻求人的自然放松状态。这种审美理想的设定是茅盾为精神萎靡的现代人与现代社会重振精神、回归活力的审美救赎。
三 现代性张力的文化心理动因与思想辨识
中国现代性思想的生长不仅是西方现代思潮强势影响的结果,同时也伴随着中国知识分子自身内在观念的革新。这种现代性体验的复杂性的最深层原因就是对待传统的态度,即文化现代性的传统型悖论影响知识分子的思想价值的建构。在共同的现代性体验基调之上,中国知识分子有着作为个体自我的差异化态度与价值判断。《子夜》中的现代性思想与价值取向是茅盾生存境遇的独特体验在文本中的呈现。这种体验包含着茅盾个人对中国现实的文化想象与理智情感等在内的直觉体验,并构成茅盾的个人思想取向、价值判断、审美情感等人生意义的层面。《子夜》中所呈现的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意识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正是源于茅盾对待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复杂“态度”,即他在现代性体验之下其文化想象与伦理道德观建构的复杂性。茅盾的文化想象与精神建构等在内的心理结构的不确定性与矛盾性成为一种隐蔽的力量,构成小说《子夜》现代性张力的深层文化心理动因。
《子夜》现代性张力的深层文化心理动因之一就是茅盾的传统儒家伦理观与现代资本新伦理观在认知中国现代性过程中的冲突。无论从文学家身份还是从其他层面来看茅盾个人,“茅盾的矛盾,最本质的,就是中国儒家文化(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理性精神与西方主流文化(西绪弗斯、堂吉诃德、浮士德)的理想理性精神以及个性主义精神的冲突”3。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对新思想、新伦理的吸收与建构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文化的强力遗传。这种现代性文化诉求的矛盾现象,具体到作家个人就是其内在新旧价值体系此消彼长不断地较量。茅盾在《子夜》现代与传统的叙事结构中糅入伦理道德判断,呈现出一种儒家化的现代观念结构。早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茅盾在回答编译所的孙毓修老先生的问题时说道:“我从中学到北京大学,耳所熟闻者,是‘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涉猎所及有十三经注疏,先秦诸子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昭明文选》,《资治通鉴》,《昭明文选》曾通读两遍。”4儒家文化中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观,无疑对茅盾所提倡的文学“为人生”、注重文学社会功能等文学观产生深刻影响。另外,随着中国现代性的发生,现代资本社会中的物质主义打破传统宗法社会道德体系。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伦理精神与传统道德有着天壤之别,资本主义改变了社会经济文化格局,给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文化伦理也影响着茅盾的文学观建构与创作实践。
《子夜》中处处可见现代都市新旧伦理交锋的道德困境与价值失衡。企业家吴荪甫怀有民族抱负与英雄气质,但在事业受挫时又展现出疯狂、暴戾与荒淫的野蛮。杜竹斋不顾宗法人伦关系,两面三刀,利益至上,最终倒戈令吴荪甫一败涂地。金融资本家赵伯韬骄奢淫逸、肆无忌惮,却有着封建腐朽的处女性癖好。封建乡绅冯云卿出生书香门第,在资本面前也罔顾封建伦理道德,牺牲女儿贞操换取公债投资消息。实质上,茅盾所真正批判的正是外来资本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中的消极因素所导致的现代都市病症。然而,这些消极腐朽的文化往往伪装成进步现代性,造成现代性探索中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矛盾与道德困境。
在《子夜》文本中,茅盾不仅充分表现了以金钱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俗伦理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冲击,更意识到资本主义文明中畸形与野蛮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毁灭。茅盾在《子夜》中赞叹机械文明推动现代都市的发展,也清醒地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深受封建小农经济、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的挤压,最终难以为继。中国都市现代性发展的“悲剧”境遇,从历史层面来看,内外交困的经济政治环境使得启蒙现代性追求充满焦虑。而更深层的内在原因,茅盾尚处于对现代性认知与诉求的思想彷徨状态,对现实书写中表现出对现代文明接纳又疏离的矛盾情绪模式,构成作家主体自我对都市文化的审美观照,呈现出《子夜》的审美现代性批判特质。无论是传统儒家伦理泯灭人欲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都成为中国现代性良性发展的阻碍,现代中国亟须寻求解救民族危难、振兴中华的真理。
《子夜》现代性张力的深层文化心理动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茅盾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建构中国现代性的艰难探索。《子夜》的创作正表明茅盾已经有意识地尝试运用科学理性反思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外来资本主义伦理,并且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建构对中国现代性的想象。茅盾在《子夜》中呈现的现代都市中传统与现代生存体验的矛盾感与道德崩塌的失落感,实质上是茅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研究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精神文化问题所必然会产生的心理认知状态。不同于新时期的保守派或激进派思想,茅盾用科学的眼光看到了现代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积极与消极因素矛盾杂糅的状态,并且在此认识上寻求解决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精神良方。
茅盾以辩证的理性思维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彻底摒弃封建旧伦理,但是保留注重社会客体的实践理性精神,并以此与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价值观结合,形成他早期的文学观与创作观。在《子夜》构思与创作前后,茅盾写了一系列文学论文,论文中的观点包含茅盾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和指导新文学发展方向。在《关于“创作”》中,茅盾指出“五四”新文学在内外矛盾中没有得到健全的发展,但是“五卅”革命运动之后中国文坛转向新阶段,“这就是一九二八年起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运动”5。茅盾将“五卅”视为新阶段民族革命运动的开端,也是无产阶级文学启蒙思想的起点。茅盾认为“文艺家的任务不仅在分析现实,描写现实,而尤重在于分析现实描写现实中指示了未来的途径。所以文艺作品不仅是一面镜子——反映生活,而须是一把斧头——创造生活”6。正如茅盾在《子夜》中描绘现代都市文明的腐朽、颓废后,又添加农民暴动和工人运动内容,这实质上是暗示中国即将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工农革命新道路,也坚定对于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方向。
然而,在《子夜》文本创作中,茅盾倾注心力描绘现代中国外部世界的巨变,同时也表现出中国社会思想意识发展变化滞后性。内化的儒家观念与传统实用思维,使得其始终以现实经验为基础来接受西方理论,即以现代中国的现实需要为基础来建构民族想象与价值秩序。然而,现实经验无疑总是被现实规定或局限。中国传统思想崩塌造成信念的缺失,传统中带有普适意义的优秀思想未能进行现代性转换,而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尚不够成熟。正如茅盾在回顾早期创作的心理状态时谈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7这正反映在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困惑。当时茅盾的文化心理带有强烈的反思性和探索性,他对于中国社会现代性追求的苦闷、迷失与矛盾的心理状态在《子夜》中有着鲜明的审美呈现。
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难以在短时间确立一个新的、稳定的、理想的民族国家信条,来应对多元化剧烈变化着的现代工业化社会。因此,即使茅盾在主题先行下创作《子夜》,在文本实践中仍表现出他作为文学家的主体在现代性体验之下文化想象与道德建构的矛盾性。中国现代化历史语境下,茅盾复杂的现代性体验与多元化思想成为内在心理因素,造成《子夜》两股现代性力量的纠缠。
结 语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表达中既有对中国化的启蒙现代性的渴求,又呈现出审美现代性的反思。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从未有过“纯粹的唯美主义”,中国现代作家对于现代都市的现代性书写都带有双重性,甚至是多元性。毕竟,历史时代空间、现代都市空间与作家创作空间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现代性本身是现时性的、变化着的,对文本中现代性的认识也存在着开拓新空间的可能。革命文学家对现代都市的书写中所隐藏的审美现代性是不容忽视的。都市现代化发展带给茅盾复杂的精神体验与多元化思想的冲击,导致其内在文化想象与伦理道德建构的矛盾性,在文本实践中呈现出对两种现代性的矛盾态度。正如茅盾小说《子夜》,在鲜明的启蒙现代性遮蔽之下蕴含着审美现代性的反叛,这两种现代性的张力特征构成《子夜》的现代性价值。在谈及文学与现代性关系问题时,伊夫·瓦岱认为:“评论界的任务之一应该是去明确和分析美学现代性(我们很乐于在某些特殊的作品中看出它)与历史现代性(它高高在上,随意摆布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些具有自己特有的表现形式的作品与我们生活的时代所特有的历史状态之间的关系。”8对《子夜》为代表的革命文学的现代性价值的研究,能够揭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如何与特定历史状态发生关系并产生影响,以期探寻建构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与现代性方案。
注释:
1 茅盾:《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
2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0页。
3 曹万生:《茅盾内在的文化矛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0年精编》(作家作品研究卷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4 茅盾:《茅盾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5 茅盾:《关于“创作”》,《茅盾全集第十九卷·中国文论二集》,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314页。
6 茅盾:《我们所必须创造的文艺作品》,《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20日。
7 茅盾:《创作生涯的开始——回忆录〔十〕》,《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8 [法]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田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