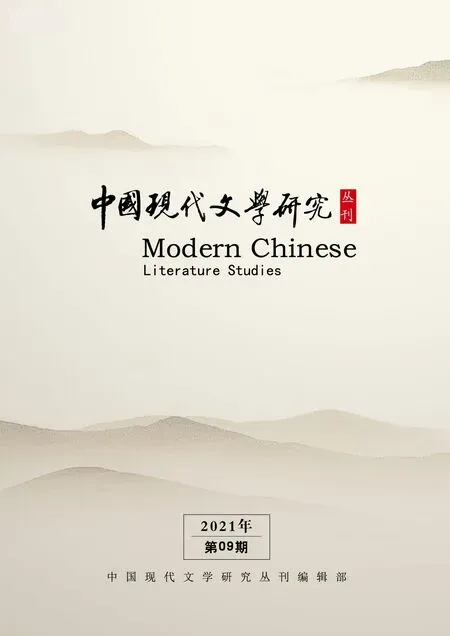论中国当代新生代小说影视改编的形象重塑
2021-04-17曹文慧
曹文慧
内容提要:新生代小说中人物形象从文学虚构转换为影像画面的“逼真现实”,导演通过对小说人物自身状况的现实定位,以人物的行动充实现实处境以及演员的扮演来实现。人物在改编中的“变异”体现出改变原著小说的主题格调,烘托主要人物以及强化情节曲折性等功能性指涉。人物增删以扩充情节容量,创造清晰的情节线索以及开阔作品的内涵视野契合大众消费文化的诉求。人物形象的重塑须注重人文内涵与娱乐需求的内在平衡,适度创新,以实现人物形象从小说美学到影视美学的成功转换。
中国当代新生代小说亦被称为“晚生代小说”,于1990年代崛起于文坛,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鲜的写作经验。新生代小说有很多作品都被翻拍成了影视作品,较早可追溯到陈染的小说《与往事干杯》,导演夏钢在1994年将其改编为同名电影。此后这一现象处在逐渐升温之中,如东西的《我们的父亲》、叶弥的《天鹅绒》、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等。这些文学作品借此在更为广阔的传播平台上,以影像化的形式参与了当代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建构,不仅拓展了影视剧的题材创作与类型创新,也为当前影视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文学的影视改编史上,影视艺术不仅从文学那里学习叙事经验,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也成为重要的借鉴方面。由于文学与影视的介质不同,人物重塑意味着将文学人物的模糊性、想象性、复杂性、多义性、飘浮性、丰富性、作家想象改编为影视人物的形象性、清晰性、现实性、性格化、确定性、单义性、真实感、简单化以及演员扮演。当代新生代小说的影视改编在人物形象的影像转换上呈现出多元化的表现形式与深度,提供了多元化的改编路径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一 文学形象的影像转化:从虚构到“现实”
小说表现的“现实”为艺术现实,人物形象作为具有文学气质的虚构形象,充满作家的主观创造性,呈现方式自由而灵动。由于影视艺术需要模拟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或者艺术空间,小说中人物的影像化将由想象的主观性升华为现实客观性,受到多重现实因素的制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设计感。
下面以新生代小说具体的改编文本为阐释对象,从三个方面考察人物形象从“虚构”到“现实”的具体表现形式。第一,对人物自身现实状况的填充。某些被改编的新生代小说秉持冷静审视的态度,关于某些人物的描写呈现出哲理化的写作形态。影视剧具有的“逼真现实性”使得编导对于此类人物的处理往往首先对人物进行现实状况的定位,以给予观众明确清晰的观影体验,这一点对于改编为电视剧来说尤为重要。“由于电视剧强调逼真,多用实景拍摄,采用近景较多,声画同期合成,因此,在局部、细节的描写和表演上要求真实地符合生活原貌,使观众在欣赏的过程中,产生身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电影虽然也要求逼真性,但由于二者演剧和观剧的方式不同,欣赏环境不同,可以说,电视剧对逼真性的要求更高”1。如东西的《我们的父亲》中关于父亲的描写简约而抽象,“我们的父亲就在我妻子的呕吐声中,敲响了我家的房门。我看见我们的父亲高挽裤脚,站在防盗门之外,右边的肩膀上挎着一个褪色的军用挎包”2。小说中的父亲形象通过概括性的描写及家里人转述达成,无容貌描写,对人物心理也亦未着墨很多,对儿子儿媳及女儿女婿的描写也是片断式呈现,整篇小说因东西的独特叙述以及对人物的碎片化呈现而具有特别的味道,小说弥漫着一种独特的感伤情绪。改编的电视剧《我们的父亲》对小说中的人物进行了现实的定位。我们的父亲改为善良朴实的农村老汉秦元生,儿女们分别为警察秦巴拉及儿媳妇应兰、医生秦艺芳及女婿范文浩等。人物的现实状况为应兰怀孕,女儿的婚姻出现危机,小儿子还没有成立家庭,秦元生来到城里为儿女们分忧解难,从而展开了一系列故事。金仁顺的《水边的阿狄丽雅》中,我们对于小说叙述者“我”的了解在阅读中逐渐修补成一位具有双重身份的女人,她的独特经历对爱情与婚姻产生了重要影响。改编后的电影《绿茶》中女主角名为吴芳,比较文学硕士生,朗朗是她的另一个化身。可见,影视剧中人物的发展需要来自现实力量的支撑,文学作品为塑造人物所直接或间接呈现出来的各种暗示,在改编后的影视剧中需要通过影像转换将其真切地展现出来。第二,以人物的不断行动充实人物的影像世界。作家在虚构人物形象时拥有高度艺术自由,以展现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形象。相比于小说中人物形象的虚构与自由,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则呈现出某种现实开放性。人物通过不断的行动来扩充拓展现实生活,呈现出具体性与立体化的现实,使人物成为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行动元”,利于观众的接受与认可。“在电影艺术中,人物的主观形态受到极大的削弱。人物不是经由自身进行自我了解,而是借助对外在事物的认识以及别人对自我行为的反应,来认知以及组合个人形象”3。不仅电影艺术有这样的诉求,电视剧对人物的日常现实的填充更为需要。改编的电视剧《我们的父亲》,着重以人物的行动来充实人物的现实生活及与他人的关系。如老父亲秦元生,冒险做线人帮助大儿子秦巴拉,担心柳晓露介入孩子们的婚姻生活,然而老父亲并未得到儿女们的理解和支持,反而经常受到误解和委屈,老父亲在儿女们的眼里成为一个“看不见的人”。这部电视剧将小说中原本碎片化的人物进行现实定位后,通过人物各自的行动以及情感的发展来建构起了一个全新的故事,将这一家人的故事通过活生生的人物行为展现出来。可见,以人物的行动来充实影像世界是影视人物塑造的重要艺术法则。第三,影视演员的承载。当小说人物进行影像转换时,读者想象中的文学人物在影视剧中将由一个确定的演员进行扮演,观众对于人物的想象将被导演对演员的选择而固化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小说中的人物被影视剧中的演员所承载,演员的选择与扮演将直接关系到受众对影视作品的接受与否。演员的容貌、外形、修养与气质在某种程度上将成为文学人物形象影像化转换之后重要的“显影”,将对所扮演的人物形象产生重要的影响。演员真人扮演的人物形象将人物从虚构的文学空间带回影视剧中的“艺术现实”空间,深刻影响着影视作品的故事内容与艺术价值。影视演员对人物形象的再塑造须契合影视作品的主题内涵与形象追求,呈现人物的个性品格、心灵世界与精神气质,重塑成功的人物形象,这是观众能否认可、接受与喜爱的关键所在。
当小说中的人物从虚构走向影视剧中的“模拟现实”时,编导对人物自身现实状况的填充、以人物的行动来充实人物的影像世界及影视演员的承载都是重要的转换方法。值得关注的是,转变过程中难免出现弱化人物深度的现象,造成人物的简单化与平面化,影视编导人员应引起足够的警惕。
二 形象的“变异”处理:人物重塑的功能性指涉
“在进行改编时,同样的故事一般而言意味着有着大致相似的事件过程,同名的人物、相类的人物特征以及同样的文化母题。但是由于一些细节的改变,人物形象和小说主题会出现变化。”4考察新生代小说的影视改编,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改编中人物形象发生了不同程度上的“变异”,而这一变异又彰显出深层次的功能性指涉。
根据改编后人物形象所指涉的功能性进行分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改变原著小说的主题格调。主要表现改编中某些人物在思想、情感以及行动上发生变异,使得改编的影视剧具有迥异的思想内容。如艾伟《风和日丽》中的米艳艳和东西《耳光响亮》中的冯奇才。《风和日丽》里的米艳艳是位坚强乐观、懂人情世故且勇于付出、敢于承担的贤妻良母角色,属于静态式人物,她的性格和情感世界一直处在较为稳定的发展之中。电视剧中的米艳艳则发生了较大变化,被改写成一位动态且不断行动着的人物,拥有悲剧命运而不断觉醒的女性角色。米艳艳这一小说人物形象的“变异”处理改变了原小说的主题格调,使原小说所关注的杨小翼女性个人成长史转换成以杨小翼、刘世军以及米艳艳三人情感纠葛为主要内容的情爱伦理剧。东西《耳光响亮》中冯奇才这一人物形象在电视剧中也发生了变异。冯奇才的转变成为温暖牛红梅的正面力量,这一人物形象的转化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文学母本忧伤沉郁的风格特色,呈现出一抹让人释怀的感动。第二,烘托改编后影视剧中的主要人物。这种情况主要是指某些次要人物变异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自己的行动、思想和情感对影视剧中的主要人物进行衬托或是对照,以此将主要人物的特色更加有力地凸显出来。如毕飞宇《青衣》中的柳若冰。柳若冰的出现来自筱燕秋的回忆,这段往事是筱燕秋在奔赴决定她命运的宴会之行时联想到的。此时的柳若冰在筱燕秋的回忆之中是作为悲剧人物出现的,呈现出一种青衣命运的苍凉感。电视剧《青衣》中的柳若冰被改为一位活在现实生活中的前辈青衣柳若云,和老团长魏笑天有着一段为世俗所不理解的恋情。柳若冰的这一变化对照并烘托了主要人物筱燕秋的戏梦人生,表现出两个戏骨女人的独特生命体验与心灵轨迹。第三,增强影视剧情节的曲折性。主要体现在某些人物的变异不仅扩充了影视剧的故事容量,故事情节也更加曲折动人。人物的改变犹如打开一条崭新的情节线索,使人物的命运以及影视剧的故事发展更加引人入胜。如何顿《我们像葵花》中的章志国、麦家《风声》中的潘翰轩。《我们像葵花》中章志国的变异处理增强了影视剧情节的曲折性。章志国在小说里是比冯建军大三岁的社会青年,同名电视剧中的章志国一心追求张小英,后章志国担心张小英意外怀孕影响仕途迫使张小英退伍,结局是冯建军和张小英历经重重磨难走到一起。章志国这一人物形象的改编烘托了冯建军和张小英对待爱情的纯真追求,影视剧的情感发展愈发扣人心弦。《风声》中潘翰轩的变异改编也增强了影视剧情节的曲折性。潘翰轩改为裘家三少爷,他冒名沈耀辉继续以“老鬼”的代号潜入敌人内部,最后潘翰轩恢复记忆后从顾晓梦父亲那里获得了重要名单。目前,改编后的谍战剧一改先前谍战剧类型中谍战历史意识形态化、谍战人物脸谱化以及情节逻辑平面化的特点,以求真的眼光改写现代谍战历史,以丰富的想象编写现代谍战故事,同时以多维的视角塑造现代谍战英雄,创作了新型的谍战影视类型。改编后的谍战剧不仅对谍战历史进行了再现与反思,而且对谍战人物进行了深度的人性挖掘,将谍战人物还原为正常人,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创新后的谍战剧不仅有力地参与了当前影视文化市场的竞争,而且还满足了观众的红色怀旧心理。
新生代小说的新质素与影视作品需求的故事化情节以及富有生活气息的个性化人物之间具有某种内在契合性。“新生代小说中的叙述者大都被还原为以主人公形态出现的与作者具有生命同构性的世俗性、欲望化的生存个体,他们以口语和本色的生活语言讲述着一个个当下的生活故事,这些故事有着原初、真实的生命气息和粗糙、质朴的形态”5。正是因为新生代小说对于崭新艺术空间的开拓,人物形象的再造展现出广阔的改编空间。影视编导对于人物的重塑体现出改编的智慧、技巧和策略,人物的“变异”处理体现出多种功能性指涉,尤其对于次要人物的改写,将小说中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人物转化为能引领情节发展甚至改变文学母本思想内涵的重要角色,从而延伸、拓宽并深化了对小说人物形象进行再解读、再阐释与再创作的审美想象空间。
三 人物形象的增删:大众消费文化的诉求
随着1990年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市民社会的形成,市民或阶层迫切需要与之相应的文化产品来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随着互联网以及影视艺术等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大众文化向市民阶层的传播和普及。作为当前大众文化生产与传播的重要来源,影视作品满足着大众阶层的娱乐需要与心理需求。新生代小说的影视改编遵循大众消费文化的诉求,影视改编原则体现在适度消解或者淡化深邃复杂的主题思想或具有复杂人性的人物形象,并进行适度的人物增删,以通俗易懂的故事与线性叙事模式为艺术特色,深刻影响着新生代小说影视改编的面貌和格局。
新生代小说的影视改编中,人物的增加和删减是比较常见的改编现象。导演对于人物增删的处理为影视剧的人物塑造提供了多样化的改编路径,体现了大众消费文化的诉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扩充改编后影视剧的情节容量。如电视剧《我们的父亲》中增加了问题女青年柳晓露,使这一人物带动了很多情节的发展。电视剧《风声传奇》中增加了新四军驻上海的秘密联络官沈耀辉、军统局南京站站长顾绍廉、顾老太、吴雅茵、话剧演员简易白及秘书杨月等人物,使得谍战故事充满悬念引人入胜。自从麦家的《暗算》改编成谍战电视剧以来,《潜伏》《风语》以及《悬崖》等谍战电视剧便热播荧屏,这一影视文化市场的热点与当下大众消费文化的诉求是分不开的。“当下的主流观众对几十年前血雨腥风的地下战争普遍缺乏感性认识与集体记忆,因此,今日之谍战片多是作为满足无历史感的主体进行历史消费的一种文化商品”6。改编后的谍战影视剧将红色革命剧杂糅了情爱、悬疑、推理等商业元素,满足了当下观众的红色怀旧心理与消费需求。第二,删除某些人物以创造清晰的情节线索。如电视剧《风和日丽》中删减了杨小翼的外公外婆、范嬷嬷、卢秀真、舒畅、北原和伍天安等,使电视剧中的情节线索更加清晰,利于观众在情节的线性叙述中理解故事的发展。第三,增加人物以开阔影视作品的内涵视野。如电视剧《妈妈的酱汤馆》(改编自金仁顺的《爱情走过夏日的街》)中增加了安平原的爷爷和姑姑、妈妈李淑香、吴大婶、李在全,以韩国青年安平原寻母为线索,将亲情和爱情交织起来,展现了一幅人间真情的图画。电影《三月花》(改编自荆歌的《猫捉老鼠》)中增加了厨师赵刚,使桃花收获了真爱,一改原著中阿凤的悲惨命运。电视剧《青衣》中增加了筱燕秋的好友裴锦素,开阔了这部电视剧的故事宽度与艺术视野。裴锦素这一人物形象隐喻着充满烟火气息的世俗人间,衬托出筱燕秋为戏死生的悲壮苍凉,升华了筱燕秋戏梦人生的艺术追求与精神境界。
当前,大众消费文化的诉求使新生代小说的影视改编彰显出鲜明的商业性与娱乐性特征,以增删人物形象、添加商业元素以及圆满的结局吸引观众。与此同时,某些新生代小说深刻隽永的主题思想被削弱,充满复杂人性色彩的人物归于平淡,人物形象的改编上呈现出潜在地自发性与统一性,失却了艺术敏锐感以及创造性改编的艺术力量,使某些新生代小说的影视改编陷入了重复与雷同的局面之中,难以实现艺术突破与自省。如何让更多的新生代小说人物形象深入人心,获得观众的接受与喜爱,推动新生代小说的传播和当代中华新文化的建构,是当下影视工作者们必须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新生代小说在影视传播过程中对于人物形象改编的艺术经验体现出导演对于文学人物影像化转换的创新和思考,提供了多元化的改编路径和宝贵的实践经验,也为文学人物的影视剧改编提供了自省与反思的契机。影视工作者在人物形象的改编中须注重改编的创新性、艺术性与审美性,提升影视作品的人文价值与艺术品格。“在当下的娱乐需要和精神渴求、自身感悟和原著内核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7。编创观众接受并喜爱的人物形象,创新多元化的改编思路,实现人物形象从小说美学到影视美学的成功转化,创作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新时代中国影视作品,推动我国影视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1 盘剑主编《影视艺术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页。
2 东西:《你不知道她有多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3 陈林侠:《从小说到电影:影视改编的综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页。
4 杨晓河:《昆德拉话剧改编变奏论及其启示——以老舍小说〈二马〉的话剧改编为参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
5 吴义勤:《自由与局限——中国“新生代”小说家论》,《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6 叶航:《〈听风者〉:从改造“经典”到涂抹“红色”》,《电影艺术》2012年第6期。
7 张丽军、李佳卉:《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电影改编的美学理念探寻》,《电影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