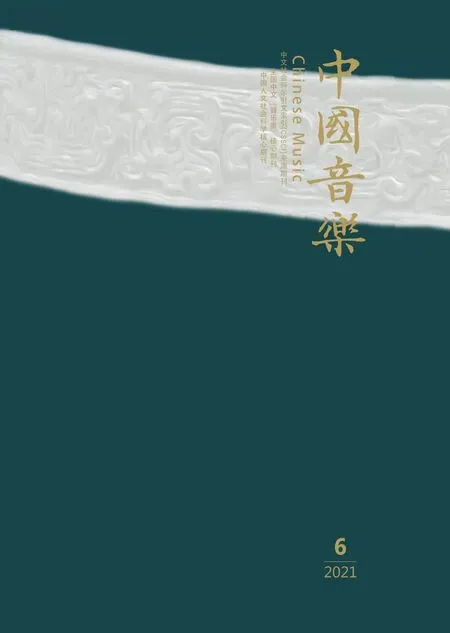从涓子到李贽
——“三‘心’一线”之古琴美学史意义
2021-04-17○毛睿
○ 毛 睿
以琴治心,古人谓之“琴心”。无论是先秦涓子的“琴心说”或两汉班固等人的“琴禁说”,亦或明代李贽的“琴心说”,都涉及了“心”的问题。何者为“心”?古人有很多论述,如,管子:“心也者,智之舍也。”①〔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63-270页。荀子:“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②〔清〕王先谦:《荀子集解》(解蔽篇第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页。董仲舒:“心之所之谓意。”③〔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第七十),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2019年,第366页。孔颖达:“总包万虑谓之心。”④中华书局校:《十三经注疏》(第一册 周易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2页。王阳明:“心者,身之主也。”⑤〔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语录二·答顾东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1页。可见其内涵非常丰富。“心”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很多当代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有所阐述,如《游心太玄》⑥参见徐复观著;刘桂荣编:《游心太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⑦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心》⑧参见张立文:《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心体与性体》⑨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⑩参见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哲学主体思维》⑪参见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心灵超越与境界》⑫参见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情感与理性》⑬参见蒙培元:《情感与理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国古代意识观念的产生和发展》⑭参见刘文英:《中国古代意识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心灵哲学与文艺美学》⑮参见胡家祥:《心灵哲学与文艺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哲学范畴史》(下)⑯参见童浩:《哲学范畴史》(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儒家心性论》⑰参见韩强:《儒家心性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心灵学问——王阳明心学》⑱参见赵士林:《心灵学问——王阳明心学》,昆明:云南出版社,1997年。等。今综理其说,可知中国文化里的“心”,不仅是一个生理器官的肉团心,也是一个思虑的器官、情感的器官及伦理的器官,即包含了情感、意志、思虑、愿望、道德、伦理的一个综合体,与心性问题、情感问题及意志问题均有深刻的关联。正如哲学家方东美所言:“人类以心的体用为主脑所发泄的生命功能可分两方面观察:一属理,一属情。依理着想,心的历程带动生命,遂起思虑测度,发为系统知识。所谓“正心”(the rectification of mind),“尽性”(the fulfilment of life),“诚意”(the sustainment of intention),“致知”(the achievement of knowledge),乃属于理的一贯生活。就情着想,则心的作用斡旋生命,引发创造冲动,此为高雅的精神人格。所谓“存心”(the preservers of mind),“养性”(the cultivation of nature),“达情”(the satisfication of emotion),“遂欲”(the refinement of conspicuousness),乃属于情的一贯生活。”⑲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0年,第149页。本文所要讨论的三“心”,正要从此层面上展开,其涉及音乐思想、音乐美学。联系琴的美学,则如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论琴心所言,有杀心、疑心、悲心、思心、怨心、慕心,可谓是心法多门,取用非一⑳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四《经术·礼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00-401;390页。,但如方东美所说,无非是就情着想,乃属于情的一贯生活。以本文所论,就琴的美学展开来讲,就有道家“啬心”、儒家“德心”和李贽“道—禅心”,可以说,正是这三“心”的关系串联起了两千多年的古琴音乐美学史脉络。
一、先秦涓子“琴心”之特质
学者一般认为,涓子是老子的弟子,即道家门人,其“琴心说”要联系道家思想考察。在笔者看来,涓子的“琴心”是指“道心”或“啬心”,亦可称“道—啬心”,即返回人的自然本心,保持一种“啬”的状态或本然虚静状态㉑虚静,作为中国美学的重要概念,首先由刘勰提出,但源于老庄。虚静一词,初见于周厉王时代的大克鼎铭文“冲让厥心,虚静于猷”,本指宗教仪式中的一种谦冲、和穆、虔诚、静寂的心态。老子认为虚静是观察生命本原、体悟永恒规律的先决条件。参见朱志荣编《中国美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道家强调“道法自然”,认为道的本性是静寂的,人心若近道,则天性自然是寂寞无欲。饶宗颐先生的“援道入儒”“儒道互渗”,曾解作为乐器的“瑟”为老子哲学中的“啬”,更是新意叠出。㉒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四《经术·礼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00-401;390页。在他看来,琴、瑟是可以通论的。“啬”这个字,在古文字中是指种田的农夫,原来有草字头,有去芜求纯之义。老子之重视啬,不仅说的是“治人”(政治),也说的是“事天”(哲学)。笔者联系音乐,尤其是琴乐,把它展开后称为“啬的美学”㉓毛睿:《饶宗颐琴学一瞥:涓子“琴心”与道家“啬”的美学》,《人民音乐》,2018年,第11期,第36页。,啬即归一、去芜、守静、求道,也即道家美学的一般内涵。关键在“去芜”“去杂”,“去”古文可解为“弃”(《集韵》),其本意有“离开”(《广韵》)、“去除”(《集韵》)、“失掉”(《增韵》)、“放弃”(《说文解字注》)等含义;而“禁”有“忌”(《说文》)、“止”(《广雅》)、“戒”(《唐韵》)等含义,可见“去”或“啬”也含“禁”的意思。正如古代文献常常把琴、瑟并列通说,琴之“禁”与瑟之“啬”,也是可以打通并说的,都与琴的美学有关。但为什么琴、瑟会出现跟“啬”有关的含义呢?这与中国音乐哲学有深刻联系,思考这个问题要从哲学的层次上讨论。饶宗颐先生认为“啬”就是道家的“朴”。朴,即本色不加雕饰,大道归朴,朴散为器,也就是道散为器。器是指具体的事物,如琴、瑟,道是所有具体事物存在的原因,或者是道理。㉔罗艺峰:《中国音乐思想史五讲》“导言”,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278页。因此,朴就是道,而道是无色、无味、无声、无所不在的,所以当我们把啬(瑟)联系朴、道的哲学概念思考的时候,也就可以归结为一种琴的哲学,这个哲学要求的是清空所有的污垢,就像农夫作田要把田里的杂草稗子除掉一样。琴道的归一,无论是琴还是瑟,都归到了心胸的纯净无垢,心量的空阔不羁,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不同于音乐美学史家蔡仲德先生等人把“琴禁说”与“琴心说”视为正反命题的观点㉕参见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修订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按这个思路就不可能有“啬的美学”,也不可能是“朴”,从“啬”的美学意义上来说,涓子的“琴心”只能是“道心”或“啬心”。
二、两汉班固等“琴心”之内涵
两汉时期,关于“琴心”的解释,由道家的意义变成儒家意义了,即由“道心”演化为“儒心”,这个“儒心”我们可称之为“德心”,它强调的是琴对人的道德教化作用和思想行为规范,从某种意义而言,正是饶宗颐先生指出的,是“从消极的方面推阐”。两汉时期这一类论述尤多,如西汉刘歆《七略》:“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㉖由春秋到汉,记载上有颂琴、雅琴等名称。“颂琴”之名出《左传·襄公二年》:“穆姜择美槚,自以为榇与颂琴。”汉代有雅琴,《汉书·艺文志》:“《雅琴赵氏》七篇,《雅琴师氏》八篇,《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可惜其书俱逸。古代乐器冠以雅颂的名号的,像《仪礼》有颂磬。同样,琴瑟亦有颂瑟、雅琴。雅琴二十三弦,颂瑟二十五弦(见《三礼图》)。雅瑟、颂琴却不知弦的数目。大概雅琴、颂瑟都是配合《诗经》雅颂而制的。古人读《诗经》不是当作文字来欣赏,而是兼作厚人伦美教化之用,所以雅琴是与儒家有密切关系。参见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四《经术·礼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97页。东汉班固《白虎通·礼乐》:“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这种思想的渊源可追溯至先秦《左传·昭公元年》医和“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已慆心也”的观点,而东汉桓谭《新论·琴道》“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将此命题又做了进一步阐释㉗〔汉〕桓谭(?—56),东汉哲学家、经学家。汉成帝时任乐府郎,《后汉书说·桓谭传》说“性嗜倡乐”“颇离雅操,而更为新弄”。其著《新论·琴道》反映了东汉古琴美学思想,认为琴的形制效法天地,能“通万物而考治乱”,能“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认为“琴之言禁”,“八音广播,琴德最优,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对琴曲的“操”和“畅”做了儒士修身性质的附会解释,其言:“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谓之‘操’,操似鸿雁之音;达则兼善天下,无不畅,故谓之‘畅’。”这一观点对后世文人音乐美学思想有深远的影响。。
一般而言,“禁”字的含义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禁,凶吉之忌也。”汉代琴论中的“禁”,往往也作禁止、忌讳之意,是指用雅琴来禁止淫邪之心。在中国思想史上,汉代是儒家思想最为发达和强调的时期,在音乐美学上以“中和”为审美观成为主导的思想意识,在此背景下,儒教与琴理相交,以琴正心这种理论在汉代非常流行就可以理解了。汉代人将“德”作为乐的本体,《乐记》所谓:“德音之谓乐。”按汉代乐论思想,儒家这个“琴德”的观念,其内涵主要有“廉”“清”“志”“和”等,且都与“琴心”有关。琴作为正性之具内含性理,东汉李尤《琴铭》:“琴之立音,荡涤邪心;虽有正性,其感亦深。”弹琴的意旨,主要在养廉隅,“廉隅”喻指端方不苟的品行,而非只求声音之美,所以在古代乐论中,琴瑟作为弦乐器,其代表的德性是“廉”,弹琴即“鸣廉”,廉以立志,故闻琴瑟之声,便会想到志义之臣㉘《乐记·魏文侯》:“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引自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修订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339页。。古人还将琴的最高境界总结为“太清”,如汉代文人、也是琴家的蔡邕的《琴歌》:“练余心兮浸太清,涤秽浊兮存正灵,和液畅兮神气宁。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踔宇宙而遗俗兮,眇翩翩而独征。”㉙此歌见蔡邕所作《释诲》的篇末。“太清”在儒家思想里是极高的情志境界。而如何获得内涵极为丰富的琴德?儒家思想提出了“禁”的方法,也即“正性”“养心”“涤秽”“练心、“遗俗”等思想道德规范;甚至在演奏动作、音乐行为方面,也有“禁”,且衍及历代琴人琴论,如刘向《琴说》有“弹琴七要”,其说要求正襟端坐、目不斜视、手势规范、轻重合适、吟猱入韵;进而有精神上的追求,蔡邕《琴操》要求“修身理性”、天人合一,情趣韵味要高雅;在琴的声音上,唐代薛易简《琴诀》强调“声韵各有所主”;北宋崔遵度《清笺》提出“清厉而静,和润而远”的境界;成玉磵《琴论》对琴乐有“调子贵淡静”的观点;到明代的虞山派,更以“清微淡远”为时代的风格等等。这一思想延及后世,影响巨大,历代琴论中此类言论甚多,但都体现了儒家以琴修身、以“德”为核心内涵的“琴心”追求,且无不是“琴禁论”的思想余脉和发挥。北宋欧阳修在《赠无为军李道士景仙诗》曾提出“理身如理琴,正声不可干以邪”的琴论思想,这个“理身”“正声”的古琴美学观念,可视为琴禁论的确解。汉代以后两千年来,“琴禁论”几乎成为古琴美学的唯一思想而影响了无数文人琴家,虽有其他的观点,但声音十分微弱。从音乐思想史的视野来看,对比前文道家“啬的美学”,儒道“琴禁论”的美学思想分野就十分清楚了,两汉“琴心”的核心是“德”,也即“德心”。
三、明代李贽“琴心”之意义
先秦道家涓子的“琴心说”,在历经两汉时期班固等人的“琴禁说”转向后,到明代李贽的“琴心说”,表面看,似乎呈现出一种回归的趋势,但“心”的含义却有所不同,不再是单纯的“道心”,而是掺杂着禅宗精神的道禅合流之“心”。“琴心说”的思想路径可以表达为:先秦涓子“道(啬)心”→两汉班固等“儒(德)心”→明代李贽“道—禅合流之心”。
李贽的“琴心”(吟其心),的确与涓子和班固等不同。其《焚书·琴赋》引《白虎通》的“琴禁说”而反言之:“余谓琴者,心也,吟也,所以吟其心也。人知口之吟,不知手之吟;知口之有声,不知手亦有声也。”㉚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708页。显然有一个从“心吟—口吟—手吟”的由情志到行为的过程,是通过琴心而反映出的带有思想情感的心吟。什么是“吟”?“吟其心”又作何解?按《焚书·琴赋》可知,李贽所谓“吟”,也即音乐美学意义上的“表现”“抒发”,是以琴来表现或抒发思想情感,“吟其心”就是以琴表现、抒发“心”的内涵。舜操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而“思民愠”,这是舜的琴心;微子伤殷将亡,而援琴作操吟之于手,此乃微子之琴心;文王既得后妃而吟有琴曲《关雎》“乐而不淫”,这是文王之吟;汉高祖作“大风歌”乃依瑟而歌,其声慷慨,此乃是汉高之吟。李贽强调对于音乐表演美学有更具体意义的“心殊则手殊,手殊则声殊”的命题,“心”(情志)不同则“手”(表现)不同,“声”(琴乐)更不同。总之,“吟其心”,即以琴表现“心”的内涵。
一般而言,李贽的思想固然有反儒倾向,也明确有对道家思想的体认,但就古琴美学思想而言,其“琴心”却不只是单纯的“道心”,而是掺杂着禅宗精神的道—禅合流之“心”,即“道—禅心”。何以如此说?首先与明代的美学思想有极大关系,李贽作为“主情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其音乐美学思想的归属命题,有很多前辈、同侪都有所论及,如《中国音乐美学史》(修订版)㉛同注㉕。与《从李贽说到音乐的主体性》㉜参见蔡仲德:《从李贽说到音乐的主体性》,《音乐研究》,1987年,第1期。、《中国古代音乐审美观研究》㉝参见叶明春:《中国古代音乐审美观研究》,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古琴美学思想研究》㉞参见苗建华:《古琴美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中国古代音乐美学》㉟参见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对李贽“琴者心也”音乐美学思想的探究》㊱参见王维:《对李贽“琴者心也”音乐美学思想的探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从〈琴论〉看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㊲参见胡健、张国花:《从〈琴论〉看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求索》,2007年,第5期。、《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及其基础》㊳参见徐海东:《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及其基础》,2011年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声音之道可与禅通”——李贽音乐美学思想中的禅宗精神探微》㊴参见程乾:《“声音之道可与禅通”——李贽音乐美学思想中的禅宗精神探微》,《音乐研究》,2009年,第6期。等。要言之,以上观点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以蔡仲德、叶明春、苗建华等为代表的“道家核心说”,即认为道家思想乃李贽音乐美学思想的核心,儒家只是其表面;第二类,以胡健、张国花等为代表的“情欲美学核心说”,其在蔡仲德的基础上将反儒核心说推进一步;第三类,以修海林、王维、徐海东等为代表的“儒家核心说”;第四类,以程乾为代表的“道禅核心说”,认为李贽的音乐美学核心思想除了道家外,也受南禅宗影响较大。本文以为,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就古琴美学来说,以道—禅为底色,执道家以批儒,用禅法而解缚,总之是求精神(心)的自由,所谓“发于情性,由乎自然”。
笔者以为,李贽这里的“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道家之心。李贽的“琴心说”建立在其“童心说”基础之上,按李贽,“童心者”,真心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他认为,做任何事情,只有按照“童心”的意愿才真实,才有意义,而一切的美与艺术都必须是“童心自出”,只能出于我而非他人,如“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所以要“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故“障其童心”。这个认识源于道家,《老子》的“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二十八章》)与“含德之后,比于赤子”(《五十五章》);《庄子》的“卫生之经……能婴儿乎”(《庚桑楚》)与“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秋水》)。可见两者都以“婴儿”“赤子”为善为美,所谓“法天贵真”,主张“反(返)其真”以保持人的最初本然之心。
第二层是禅思之心。李贽之“琴心”或“吟其心”含禅宗思想。李贽曾自言信佛禅,“弟学佛人也,异端者流,圣门之所深辟……”㊵李贽:《答李如真》,载于《焚书》增补1,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55页。在音乐美学上,有“声音之道可与禅通”之论(其说见于《焚书·征途与共后语》),有学者认为对于李贽而言,禅不仅是思想,还是方法,“禅通过修道、悟道,追求无名、无际,超越万物,寻求佛性,达到心灵解脱。音乐也是通过有声之乐去寻求超越物质、感悟心灵,达到心物合一的精神境界”㊶2009年6月12日上午,罗艺峰在嵩山少林寺经堂,宣讲《禅宗中国少林问禅百日峰会——漫谈中国古代的琴禅》一文时所言。。甚至以为李贽的“童心说”与禅宗识心见性的“本心说”是相通的。㊷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第713页。本文以为,最能说明琴思与禅思相通之处的,声稀节疏、淡而深邃的古琴音乐最能够表达禅的境界,禅道正好用音乐来作为自己的象征。所以北宋琴人成玉磵在其《琴论》中说:“攻琴如参禅”,清代空尘和尚《枯木禅琴谱》以为能够“以琴喻禅理”。如此,联系明代思想和李贽本人的思想构造,就不难明白李贽所谓“吟其心”的“琴心”是可以与禅心相通的。概而言之,李贽的琴心,即含道,亦通禅,可谓之“道—禅心”,其内涵与先秦涓子“琴心说”和两汉“琴心说”不同。
四、“三‘心’一线”观念之古琴美学史价值
饶宗颐先生《涓子〈琴心〉考——由郭店雅琴谈老子门人的琴学》一文最早谈到涓子“琴心”的问题㊸见饶宗颐:《涓子〈琴心〉考——由郭店雅琴谈老子门人的琴学》,《中国学术》,2000年,第1期。,在笔者看来,这既是一个琴的哲学即琴道问题,也是一个美学史的问题。在中国音乐美学史界,最早提出“琴心说”问题的是先师蔡仲德先生,他讨论了汉代班固等人的“琴禁论”和明代李贽提出的“琴心说”,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㊹同注㊷,第718-719;719页。。但饶先生此文发表后,本文认为“琴心说”的首次提出可以由明代李贽提前至先秦涓子,笔者意欲将涓子“琴心”、两汉“琴心”和李贽“琴心”联系起来做一美学史的思考。
“三心”之间的区别在于:先秦涓子之“心”为“本心”,只须回归,而回归本心的方法是“啬”,即去芜去杂,用的是“减法”,道家讨论音乐哲学问题,用这种思想方法来使情志意欲减少,达至“静”的状态,乃至于在音乐上追求无声无欲,“大音希声”,其“心”必回归本初,这是在哲学的层面探讨“心”;两汉班固等人之“心”为“德心”,方法是“禁”,即是礼乐教化的结果,用的是“加法”,加以各种人为规范和思想规制来禁忌情志意欲,这是在道德伦理的层面建设“心”;明代李贽之“心”为“道—禅合流之心”,方法是“吟”,是要求音乐自由抒发情性,也如禅家的“解粘去缚”,这个“粘”和“缚”就是外加的规范,是道家、禅家坚决反对的,这也是在道德伦理的层面思考“心”。本文作者认为,正是这三“心”一线串联起了两千年古琴美学历史脉络,先秦涓子与明代李贽都近道,可通,但涓子是纯道(佛禅尚未入华),李贽杂佛禅,故涓子“啬”,李贽“吟”,一个是归一,一个是放开,此其不同。涓子之思只与先秦儒异,要求反其天真,回归本心;李贽之思执道反儒,以禅为法解粘去缚,获得心的自由。但如蔡仲德先生所指出的,李贽的思想基本倾向不是儒家的,而是道家的㊺同注㊷,第718-719;719页。,本文更进一步认为,李贽的思想还可以认为是受到禅思想的影响,是有道—禅底色的。
从“琴心”入手看待两千年古琴美学思想史,可以更清楚地认识琴的哲学——美学本质,也可以更贴近地认识琴的音乐文化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