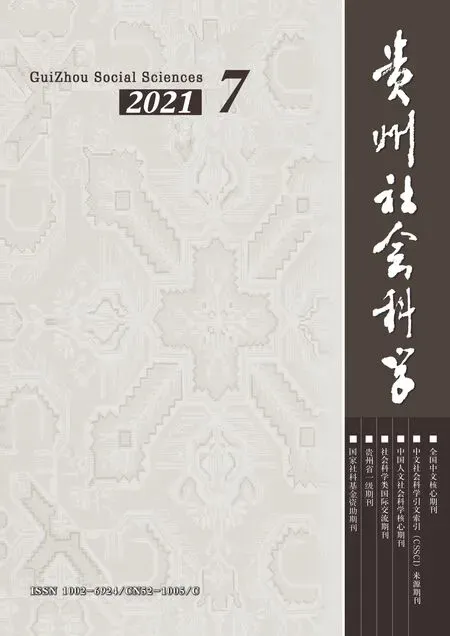数字资本主义、数字劳动、数字政治
——基于大数据时代的共产主义发展视阈
2021-04-15王寅
王 寅
(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数字资源是一种无形的资本价值资源,它的产生、发展不可避免地将人类带至数字化的流体世界。数字技术已经从价值理念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乃至学习方式,从更深逻辑层面而言,它的创新发展必将促进世界社会形态的演变和递归,从传统的商品拜物教开始上升至数字拜物教,从传统的物的异化递归至人的异化。数字业态的形成和发展正一步步吞噬着我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预示着一种全新的社区形式、参与式文化、网络行动主义、分布式民主以及人类思维运行方式的彻底改变。诚然,数字形态的发展亦带来了数据剥削和数字殖民化的裂变,不仅将人类置于社会发展的数字单调性体态之中,而且以一种无形的监控形式将人类牢牢地固化于数字技术的枷锁和桎梏中,从而扩大了数字统治,使人类于无形中进入了生命政治治理和数字算法的现代性网络循环回路之中。于此,立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面对现实数字世界的螺旋式上升发展势景中,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深度考量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对社会向度的数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向度的数字劳动、政治向度的数字政治予以重新认知和构析。其左翼代表学说包括大卫·钱德勒(David Chandler)、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和保罗·雷克雷特(Paul Rekret)的数字资本主义;凯丽·贾勒特(Kylie Jarrett)、菲比·摩尔(Phoebe Moore)和杰克·L·邱(Jack Linchuan Qiu)的数字劳动,以及乔蒂·迪恩、保罗·格鲍德(Paolo Gerbaudo)和托尼·内格里的数字政治。因此,对当今数字资本主义的建构,有必要挖掘其数字主客体发展矛盾,将危及社会凝聚力和民主实践发展的隐性剥削和统治结构予以解蔽和解构,从而开启共产主义发展的生命政治历程。
一、社会向度:数字资本主义的逻辑布展
众所周知,社会是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阵地。丰富多彩的数字化发展形式将数字融入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大数据时代,数字资源被誉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资源。数字组成的数据流在无形中将人类生活开始数字化,并以一种无差别的数据化程式规律渗透到人类的学习工作生活之中。随着数字技术的全球漫游,传统上的主体/客体、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公共/私人、消费/生产、时间/空间、思想/身体、劳动/休闲、文化/自然、人类/后人类的二元结构开始发生改变,以数字生产方式为代表的“数字革命”开始将人类带至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万维网等数字化时代。正如曼努埃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所言,在千年之交,“网络社会”的崛起意味着一个“新世界正在形成”,“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了信息主义的出现,作为新社会的物质基础”[1]。此处所指的网络社会就是一种数字社会,它在无形中促进了社会的革命性变化。在研究数字技术所引致的社会性变化时,我们有必要对促动社会改革和发展的数字资本主义和大数据资本主义予以深度诠释。
数字资本主义和大数据资本主义是数字社会发展的重要形态和生产方式,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必须将大数据资本主义的研究置于其中,否则会产生系统性分裂。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福克斯已经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钱德勒和雷克雷特也对此研究颇多,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对于福克斯而言,数字资本主义就是一种新型的数字劳动,在发挥数字技术的强大引擎作用的同时,也蕴含着一种潜在的资本积累和数字剥削。对此,福克斯认为我们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人本主义才能使人类回到世界的中心。对于钱德勒而言,大数据资本主义在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不自觉地将数字技术引入了数字政府的建设上,从而引发了人类世(Anthropocene)数字治理的新难题。对于雷克雷特而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模糊了人类的边缘,数字媒介的介入使人类文明越来越多地“像半机械人”,从而使人类进入一种了“后人类主义”的发展势景。
福克斯教授是数字研究领域的专家,对数字资本主义、数字劳动、大数据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作了精细分析和阐述。其著作包括《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互联网与社会:信息时代的社会理论》《社会媒体时代的文化与经济》《大数据资本主义时代的卡尔·马克思》等。福克斯认为,大数据时代的数字资本主义面临着数字资本与数字公地之间的矛盾,要想实现数字资本主义的正向发展就必须重新唤醒马克思主义,重新正视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福克斯认为,马克思已经预言了信息经济的出现,“资本的利润需求创造了提高生产力的需要。技术进步使科学、技术和知识与生产的关联度逐步提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数量变成了信息资本主义的新品质。”[2]55-56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技术辩证法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当今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从概念上预见了互联网,他写道:“所以随着这种异化的发展,在它本身的基础上,人们试图消除它:行情表、汇率、商业经 营者间的通信和电报联系等等(交通工具当然同时发展),通过这些东西,每一单个人可以获知其他一切人的活动情况,并力求使本身的活动与之相适应。”[3]这一构想预示着互联网将成为一个集信息、通信和社交网络于一体的全球系统。在数字资本主义中,网络数字生产力与阶级关系之间存在对抗。网络数字技术创造了新的商品化和开发形式,并带来了新的积累问题。但是,作为商品的数字信息也具有抵抗商品化的特征。因此,数字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将在数字公地与数字商品之间产生对抗性矛盾。于是,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就必须全面揭示大数据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功能性作用。大数据本身作为一种生产资料并没有错,但在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时,就无形中充当了资本主义攫取资本利益的工具。甚至在一定层面,大数据充当了资本家进行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财富资本。毕竟数据的流通过程中,资本家为了实现数据流量的集成化增值,开始以一种隐蔽的手段将大数据收集、存储、控制和分析,其目的并非合理化利用,而是将数据资源打包销售或外包给其他大型数字公司,进行资本的价值增值。当然资本增值只是物质财富的积累而已,但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经过数据分析的数字资源已经成为资本家控制人身自由的手段,甚至在无形中已经将公民的个人信息泄露,从而导致公民人身自由的无形绑架和勒索。大数据资本主义的信息监控行为已严重危及到人类的身心健康,甚至造成生命代价。
或许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已经从数字异化转变为人身异化了,唯有数字监控才能实现数字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对此,福克斯认为,数字资本主义不仅奴役了人类的数字劳动生产力,而且将人类牢牢地控制在数字劳动的无形枷锁中,以实现人类劳动力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双重增值。达拉斯·斯迈斯的受众劳工理论认为,广告赞助媒体的受众是无报酬的受众工作者,他们从事的劳动创造了一种受众商品。垄断资本主义下的物质现实是,大多数人的非睡眠时间都是工作时间。 在下班时间中,最大的一块是观众的时间,这些时间被卖给广告商。[4]而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代理商就是Facebook和Google,他们利用这种劳动力以及获取观众信息的大数据商品,从而实现了资本的价值增值,同时也在无形中加重了经济剥削,实现了“数字垄断”。
诚然,“数字剥削”和“数字垄断”只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显性剥削而已,在其深层结构内部,数字资本主义背后的算法治理技术更是从实质上隐藏其剥削性。大企业集团和个人为了实现数字的超级流动和快速流变,在保持其市场化运行的同时,对后台的数字平台予以监控,调整数字算法规则和频率建模,对其优质数据和高性价比数据以超出市场运行规律的方式予以重新定义和计算。其目的就是要控制精英资源,从而攫取数字资本的最大价值。所以,数字资本主义是一个“符号运营商”,它直接控制着物质流的指示性符号流动,进而实现数据资源的流量增值。对于福克斯来讲,破除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桎梏逻辑,就需要将数字资本主义置于社会发展的层面去加以引导,将数字算法治理纳入数字资本主义的实体化运行过程中,全面打破数字垄断,构建符合市场主体的新型算法治理体系,从而有效实现数字资本主义的正向发展。
钱德勒教授对现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有其自己独到见解,对大数据时代的数字有着人文主义的处世思考。其著作包括:《人类世数字治理:相关机器的兴起》(Digital Governance in the Anthropocene :The Rise of the Correlational Machine)、《现代统计力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modern statistical mechanics)、《运动》(Campaign)、《构建全球公民社会》(Constructing global civil society)、《重新思考道德外交政策》(Rethinking ethical foreign policy)、《重新思考人权:国际政治的批判方法》(Rethinking Human Rights: Critic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等。对于数字资本主义而言,钱德勒教授指出数字资本主义牵涉数字与世界的发展关系,要摈弃传统的二元发展逻辑,将人类世数字治理视为是一种整体性和动态性,超越二元论并实现新形式的治理社会和数字化形式的本体论。
在钱德勒看来,数字治理是一种高度依赖新技术在数据分析中的应用的新型治理模式。数字治理正通过非现代本体论(non-modern ontologies)不断发展。所以,数字治理不是试图“解决”问题或适应社会、实体或生态系统,以期更好地应对出现的问题和冲击,而是“寻求通过感知和响应出现的过程来建立关系理解如何在当下提供帮助”[2]23。因此,对数字治理应侧重于对影响的响应性治理,而不是着眼于表面的根本原因。只有将数字治理视为一种提前的治理行为,才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实现治理效果的最大提升。然而,数字治理必须实时反馈不断来跟踪人类行为的影响,从而实现治理能力的提升。当然,数字治理也涉及行星互动的意外影响,毕竟数字信息的产生来自于卫星遥感系统发出的智能化信号。言外之意,数字治理是在发挥行星空间运行技术的逻辑运动中,将其行星互动的意外影响纳入其人类世的日常行为之中。当然,人类行为的后果可以通过受行星空间技术而影响的网络来实时追踪和监控,这种追踪具有网络技术的自动化敏感性和主动连接性。网络技术是空间遥感技术的智能化反应,而人类世则是具有感官意识的成像和反馈功能。两者之间通过空间遥感技术的智能化联结,将数字实然地对接于网络智能化平台,人类的意识也相应地追踪于其中,从而形成了数字治理的网络自动化联接和人类世的日常感官能动反馈。这就是所谓的反馈回路治理。其目标不是追踪主客体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实现循环回路的智能化效果治理,从而将人类世与空间遥感技术置于一个良性循环回路之中,实现了人类世的数字化治理。换句话说,这种数字主客体的良性循环将人类从“数字逻辑”的数据统治中解放出来了,实现了机器(技术)与人类世的谐融共生。但这里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需要加强人类的感知能力,促动与网络空间技术的互动,进而实现人类世与网络遥感界的紧密联系。但前提是要提升反馈循环网络的技术能力,才能实现人类世与网络遥感界的共建共享共促共生。正如拉图尔(Latour)的框架认为,感知效应的能力对于揭示人类世间看不见和未知的相互联系至关重要,涉及以“强烈的禁令”来“追踪并不断地追溯所有这些回路所形成的线路”所必需的技术和监管机制:循环可追溯并公开可见,这样“无论您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什么反应,循环……都会使您承受重担,成为需要考虑的力量”。[5]为此,只要将人类世的行为影响和不可预见的行星互动影响全面捕捉,才能实现科学化的数字治理。
由上所述,大数据资本主义对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技术功能的抽象连接取代了有意识的阐述、社会谈判和民主决策。”[6]言外之意,数字技术的自动连接功能取代了人类对其社会交往的言语行为,毕竟言语行为不具有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合理性和精准性,只有发挥数据的精准制导作用才能促进社会交往的民主化运行。换句话说,“信号段的自动连接取代了命令的对话阐述,而适应取代了共识”[6]。算法治理通过模式识别而不是知识创造或解释行为来回应或适应数字资本主义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对于钱德勒来说,数字资本主义已经超越人类世的变革性影响。通过标志性的“符号学”,机器技术实现人类的自我表达,开始与现实世界的“真实语境”进行情感交流。所以,技术的人类世就是一种从“象征性符号”走向“权力符号”的超人类感官和语言的智能化表达。在数字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社会结构和思想的新业态中,传统的“认知资本主义”开始无法表征数字资本主义的理论内涵和现实导向。相反,数字资本主义开始打破现有的“数字客体、数字主体”的传统二元分层结构,实现了主客体的客串,进而将人类世引致从“工作”到“过程”以及从“服从”到“奴役”的转变。这里需解释的是,从“工作”到“过程”指数字技术导致的不自觉承认,即人类开始适应主动求变的过程性自为自觉。同理,从“服从”到“奴役”指人类开始由顺从数字技术的指令性模式开始导向被数字技术“奴役或殖民”的应然实然状态。哈维在其最新著作《马克思、资本与经济理性的疯狂》中阐述了数字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作用。“数字最初被认为是开放生产共同体的协作生产的一种解放体制,现已转变为一种过度剥削制度,资本可以自由地以此为基础。大资本(如亚马逊和谷歌)对高技能劳动力生产的免费商品的肆意掠夺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会延续到所谓的文化产业中。”[7]看似数字技术实现了对人类劳动力的彻底解放,将人类从桎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了,实则将人类变相地引致数字技术的“数字剥削”和“数字殖民”中进行深度剥削而已。但是,哈维强调说,大数据已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崇拜物。尽管大数据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海量的数据将人类陷入了数字化的“异构”之中,不可能实现数字技术的全面治理,毕竟人类还是要归于日常生活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大数据资本主义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第一,大数据资本主义低估了权力和资本的连续性。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危机已成为欧盟等发达国家所认可的合法化危机,所以资本主义需要继续发挥专制统治权力来实现数字资本的高度垄断和合法化所有。第二,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导致静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型。换言之,资本主义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和进化的系统,它通过剥削劳动力、社会斗争和危机来生存和发展。虽然数字技术实现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但这种稳定的、隐性的数字技术将经济、政治和社会导入其静态的发展模式,貌似数字静态化流动,实则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持续性剥削力。
数字技术的出现和差异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资本的有机组成。当然,数字机器、数字资本和数字劳动的出现是当今资本主义分化的一种表现,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方面。然而数字技术所延展的数字模式,不可避免地将人类带至计算性的单一化发展模式,人类除了数字,还有道德、情感、伦理等世俗化的人类深层认知。然而,这种由机器算法所导致的数字治理将人类误入了生命数字的歧途。人类的寿命开始陷入数字生产的逻辑,单一化的数字模式将寿命计算为:零、一和数量(zeros, ones and quantities)。因此,人类必须介入机器算法治理,毕竟纯粹的机器智能化数字治理只会造成数字的隐性剥削和实然统治,甚至将人类拖入其数字拜物教的异化状态。
有鉴于此,数字技术的生产逻辑昭示人类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数字技术的社会化功能,大数据资本主义是数字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品质。数字技术在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消极力量。这一点在马克思那里也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机器”一章中,马克思曾经肯定了这样的客观事实:“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8]
诚然,人类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中亦获益良多,人类因数字技术而开始走向共同性的团结互惠发展,走向合作共存的解放发展。于此而言,数字技术是人类解放的数字动能运输装置,在实现人类解放和发展的同时,也促动着生产关系的变革。正如福克斯所表述的那样,数字和大数据资本主义是一种对抗性的社会形态,在加深异化和剥削的同时,也提升了解放的潜力。[9]数字资本主义并非正义的化身,在提供机遇的同时,也将人类置于一种社会结构分裂的挑战境域。在服务人类走向社会性发展的关键维度上,开启了人类政治文明的解放时代。
二、政治经济学向度:数字劳动的逻辑视差
在大数据时代思考数字资本主义是时代之向、社会之需、人民之盼。对数字劳动的研究应秉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规律,在全面分析劳动价值理论的同时,坚持数字导向,将资本主义劳动价值规律与数字劳动的逻辑演判规律相接榫,深化数字劳动的逻辑视差分析,从而揭示数字资本主义发展走向。对于数字劳动的研究,目前贾勒特、摩尔和邱林川三人各有特点。对于贾勒特而言,她主要关注社会再生产的女权主义,以数字家庭主妇为视角,分析理解数字媒体用户在数字经济中的作用;对于摩尔而言,他认为数字技术控制了人类看不见的劳动领域,将一切工作场所都施以监控和捕捉,从而使人类情感劳动置于一种量化危险和电子追踪状态;对于邱林川而言,他认为数字革命非但没有实现人类的解放发展,反而将人类置于一种数字奴役状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iSlave。为此,他意欲坚决打破新旧奴隶制,实现后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类尊严发展。
对于贾勒特而言,资本主义存在许多不同类型的劳动,包括大量的无偿劳动和再生产劳动。贾勒特的数字家庭主妇隐喻将女性再生产工作的女权主义理论与数字工作联系起来。Twitter用户和失去工作的新闻记者都可以被理解为共享信息,他们被认为是贡献不稳定价值、无偿劳动力和交流劳动的数字工作者,从而为数字平台增加了商品价值。因为对劳动的无偿剥削就是平台实现价值增值的手段。因此,数字劳动隐性剥削在无形中将女性置于不利地位,甚至沦落为数字生产的“奴隶”。诚然,数字劳动的再生产远不止于女性再生产工作中。在福克斯看来,“在软件公司中,不仅生产软件商品的软件工程师都是生产工人,还包括秘书、清洁工、管理员、会计师、市场商人等。生产性劳动会产生剩余价值。”[10]里基茨把价值狭隘地看成是由股票经纪人和企业家创造的,而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则描述了所有其他维持人民社区但在资本主义结构中受到剥削的劳动。[2]121实际上,劳动本身只是人类谋生的手段而已,但如果将劳动数字化,置劳动于数字媒体平台,劳动就充当了资本主义进行商品交易的工具。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这种数字化的劳动力一旦演变成价值赋能,其造成的劳动剥削会更为严重。因为,数字媒体领域的劳动剥削是一种变相的经济剥削,不存在劳动力的解放,充其量只是将劳动力剥削隐蔽于数字剥削的“生态系统”之中罢了。
于此,数字劳动研究就是一种数字与劳动的深度结合而形成的新型研究领域。对数字劳动研究应纳入其对平台介导的零工经济中的工人、社交媒体用户、社交媒体有影响力者以及各种工作方式进行深度剖析的范畴。从表层结构而言,数字技术介入劳动力貌似是一种劳动的解放,是一种“生态劳动力”。但从深层结构属性来看,数字技术介入劳动力则变相地将劳动力出卖给数字媒体平台。劳动力在数字技术的智能推动下处于一种更加危险的境地,甚至在无形的数字化生产中将一般劳动力演变为“消费者劳动力”,最终导致数字剥削的合理化运行。这里所谓的“消费者劳动力”,指的是劳动者创造的文化产品在上传至数字平台上时,被数字资本家无偿征用和异化的价值增值方式。当然,劳动者的个体数据资源则潜移默化地成为了数字媒体公司产生剩余价值的基石。
在贾勒特看来,数字劳动的延展就不得不提及妇女数字劳动。在资本主义的女性主义生产关系中,女性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品相而实现自身劳动价值的增值。说到此,在当代数字劳动平台的中介逻辑下,摩根·默特维尔(Morgane Merteuil)认为,平台的作用类似于皮条客,它们为工人和客户之间的交易提供中介,从中抽取利润,并为劳动的执行提供特定的规则。默特维尔甚至还认为,为理解平台经济中的劳动力提供最佳模式的不是我所说的数字主妇,而是数字妓女。[11]基于此,贾勒特对默特维尔的评价虽然有失偏颇,但不可否认的是,“数字妓女”的隐喻更准确地描述了受资本主义逻辑约束的平台经济中主观意识的俘获程度。“妓女”的隐喻反映了资本主义在人的生命逻辑发展层面控制和剥夺了人的隐私空间,尤其是最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底层民众。数字资本主义控制的不仅是人的肉体,而且在更深层面压制和剥削了人的精神力量。从此,数字化的程式化模式将人类置于一种监控状态和剥削世界之中。
对于摩尔而言,数字技术控制了人类看不见的劳动领域,将一切工作场所都施以监控和捕捉,从而使人类情感劳动置于一种量化危险和电子追踪状态。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在今天依旧运行,数字监控技术的发展以一种更加量化的方式将劳动者置于监控之下,揭示了劳动过程中以前无法衡量的方面,例如情绪、疲劳、心理健康和压力。从一定层面来讲,工人对于管理层是透明可见的,而管理层对于工人是不可见的,也是无法量化的,这就导致了数字监控技术的天然藩篱。数字技术的呈现方式也是有阶层的,下层阶级沦为了上层阶级进行“数字殖民统治”的工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上层阶级通过智能化的数字监控平台赢得了生活乐趣的笑资。毕竟上层阶级不是为了生存方式而监控,而是在实现一种双重的价值增值,其一,通过数字监控,获得了物质资本的价值增值;其二,通过数字监控,赚取了精神资本的人生福利。
为此,在现实的生产关系中,监控情感劳动并非易事,但成像的监控映像数字资料实际上也是一种数字商品,经市场化的运作,其价值在无形中成倍增值。所以说,上层阶级赚取的不仅是下层阶级的劳动价值,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剥夺了经过数字监控劳动技术所窃取的视频影像资本。于此,下层阶级在服务上层阶级或垄断集团的生产过程中,必须控制情感劳动,将私人情感隐藏于心,否则只会造成精神产品的偷袭和“殖民化”。
基于此,不稳定的数字化工作者,经过平台中介的实体化监控,丧失了其自主性和发展性,非但未能赚取高额工资,还将自身沦落为市场化的“演员”。正如摩尔在其文章《数字化工作场所中的有效风险、控制力和抵抗力》中所描述的那样,“由于不稳定的数字化工人不断追逐下一个‘演出’,生活的空间和时间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遥不可及的。”[2]127实际上,数字化工作者所追逐的“演出经济”也是一种“零工经济”,只不过“演员”在数字化媒体的平台上充当了数字资本主义的赚钱工具而已。这种“零工经济”在现实生产关系中也被视为一种需求经济,它的运营基于一系列新的在线平台,人们在这些平台上使用数字化界面进行劳动力买卖。言及于此,我们就有必要对这种新型“在线平台”予以阐释,它指的是共享经济或在“人类云”(human cloud)中工作的平台,包括Upwork、ODesk、Guru、Amazon Mechanical Turks、Uber、Deliveroo和Handy等,其在欧盟数字单一市场术语中称为“在线平台”。胡斯将这种类型的交流和工作称为“众包”,并将其定义为“通过在线劳动交换组织的有偿工作”[12]。众包促进了公司的劳务外包,并为自由职业者和自雇者工作引入了新的平台,并且这种趋势在国际上正在迅猛发展。但是这种平台经济依赖自雇合同,因此,工人无法获得常规的就业福利,例如医疗保健或产假。工人几乎没有法律保护,平台旨在减少雇主的责任。所以,“演出”工作的这些特征极大地加重了流众的身心负担,导致情绪焦虑和恐慌。技术员工必须为市场主体的变幻莫测和生活的艰辛做好一切准备,否则只会将自己置于失业惯性,他们必须同意作出改变,为数字平台的智能化运营而不断作出自身的运动惯性,就如同流众一样。当然,他们的行踪时刻处于平台中介的跟踪和反馈之中。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死循环,流众因数字化的流变性和监测性而陷致工作、生活、学习的无序状态,进而导致身份的模糊和杂乱。然而作为自营者的流众也处于数字平台的完全监控之中,甚至有些自营者无法在平台注销身份信息,导致信息泄露而暴露其隐私性和位置追踪。
总之,这种“演出”工作引致自营者事先必须具备一系列的素质,包括良好的体态、抗打击的心理素养和耐心等。表面看是一种新型的数字生产关系,实则仍旧是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关系的社会再现过程而已。在数字化和“演出”工作中,平台发展的必然性优先于客户,甚至高于客户。而作为有生命的流众在无形中被绑架于无生命的机器之上,从事着最繁重的低级苦力,在无形中也兜售了自己的情感劳动。作为控制数字平台的上层阶级则从实质上控制了流众的物质劳动和情感劳动。毕竟流众无法将自身的情感劳动以数字化的形式加以创造和增值。在数字化劳动生产关系中,上层阶级不断地加快数据监测、收集、筛选、分析、销售等,其目的是抢占数字资源制导权,以充盈的数字资源为依托,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将流众纳入“数字圈地”的集中化运营模式,其形成的回路是一种封闭性闭合回路。当然上层阶级的目的并非赚取一时的高额利润,而是将其置于一种闭合性的封闭剥削之中,最终实现资本的最大价值增值。在这个过程中,控制数字平台的上层阶级亦在不断地加大投入以提升其机器智能力,这样受雇者貌似感触到生产力的提升方便了其自身发展,而实际上,受雇员工则牢牢地束缚于数字平台而无法自拔。当然,流众可以自由退出,但无合同签约的成本也是高昂的。毕竟信息已经泄露,源源不断的推销和悦己软件会不时地将数字信息推送给公众。貌似公众享受了“视听经济”,但公众却将网络流量贡献于自身的眼睛或耳朵,这就是利润的互动增值和关联价值。
所以,稳定的数据流是产生稳定流众的直接来源,而稳定流众的诞生和加入则促动其稳定的循环回路。这种封闭型的环形闭合体系就是资本价值增值的超级驱动力。表层的人机依附关系貌似简单,抑或是归化其所属的自治空间。但深层逻辑的人身依附规律则从本体上和实质上将人类置于恶性循环之中,传统的工作生活场域也在无形中嵌套于数字资本的环形闭合回路之中,人类的体力劳动(物质劳动)和智力劳动(情感劳动)也在数字化的浪潮中走向了资本的隐性剥削和“数字殖民化”。
于是,“数字情感”的控制和抵御功能就呼之欲出了。情感劳动和物质劳动同属于数字劳动的剥削范畴,只不过物质劳动是一种显性的实体存在,而情感劳动是一种隐性的超然存在,两者都实现了数字劳动的价值增值,但情感劳动创造的价值则是一种稳定的、深层次的内隐价值,上层阶级利用数字监控技术将下层阶级的情感劳动出售给原本属于下层阶级的东西而实现了数字资本的增值。所以上层集团和阶级不但剥削了下层人民的物质劳动,而且剥削了其精神劳动(情感劳动)。基于此,下层阶级的“数字抵御”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始:第一,使用个人智能设备;第二,启动数字技术个人隐私平台保护建设,具体包括:加快国家数字平台立法建设,提升数字工会监管能力,抵制黑客入侵和应用程序APP泛滥化运营,实施自我跟踪项目建设,减少监视;第三,实施平台公众监控战略,将超级数字平台纳入公众监控范畴,强力推进对大企业集团和数字专家的监控,避免无形数字垄断;第四,建立国际数字劳工公约,加强国际劳工组织建设,构建全球工会联合会;第五,加强数字审计建设,实施动态化跟踪;第六,强化数字人文建设,构建新型算法管理,实现算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七,加强数字员工培训,全力保障合法利益;第八;全面发展绿色无公害数字技术,促进数字遥感自动化监测;第九,加快数字员工反馈体制机制建设,全面提升数字员工幸福感和压力测评意识,进而提高数字生产力;第十,实施数字第三方监控平台建设,构建绿色数字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平台中介过滤功能,建立高素质的数字化运营队伍。
总之,数字劳动技术并没有错,而是数字劳动技术充当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本人”。实际上,数据技术的使用以及权力关系的不透明化加剧了科学管理的难度。智能化的生产力带来了不切实际的人类欲望,进而将人类的注意力绑架于数字化的生产关系之中。所以,恶性循环就是人类欲望愈多,其注意力愈高,而注意力的上升则会将人类束缚于数字经济的环形循环之中,导致人类负债增多。相应地,数字负债则进一步加剧了人类注意力的分散和永久性,从而导致永久的不满足欲望回归。归根结底,人类也应担负起数字劳动的技术公害性构镜者,在满足自身欲望的基础上,合理有序发展数字技术,规制数字运行模式,控制数字量化标准,将数字技术施以定性定量的集成化分析,从而全面促动数字劳动生产关系的合理化建构。
三、政治向度:数字政治的生命解放
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向度就是要推进数字公共空间、建立公共空间社会。人们在切实而富有社会运动性的数字政治中,实现人类孜孜追求的生命政治解放和价值旨归。对于数字政治的研究,目前迪恩、格鲍德和内格里三人各有特点。对于迪恩而言,她提出了交流资本主义的概念,试图借助数字网络技术的力量来实现一种后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解放和人类发展,即通过交流资本主义的交流循环回路将人类社会的所有内容进行封装、分析和出售,从而加快数字生产力的解放,进而走向全体人类自由而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对于格鲍德而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人类引至一个共同的发展平台,即数字平台。人类借助平台进行社交活动,从而形成了一种数字化平台作为交流和组织的新型政党形式,即平台党,亦称为数字党。所以平台党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自我解放和发展的后资本主义时代,大数据的自由流通和超级领导者、超级基地的出现使人类开始走向横向发展的民主化政治实践。
乔蒂·迪恩是美国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教授、费舍尔性别与公正研究中心主任。自从数字网络技术的兴起,迪恩一直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从最初的博客理论到后来交流资本主义的提出,无不倾注了迪恩的心血,无不印证着迪恩的学术研究历程。在迪恩看来,“数字化”已经将人类引入了交流资本主义的势景。而交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发展形式,在其循环回路中促动着资本积累的快速进行。对此,交流作为交流资本主义的核心,在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消费、流通等环节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回路作用。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网络媒体、人工智能、物联网、万维网、5G通讯技术等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交流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交流已成为积累的资源、手段和工具。正如迪恩自己所言,交流资本主义在提出之前,已经有学者称其为认知资本主义,但迪恩更愿意使用交流资本主义一词来称谓。其原因在于,交流资本主义是发挥“交流”在数字技术中的核心作用,如同迪恩在其作品中常用的“回路”(Circuit)一词一样,具有流动性和畅通性,其行为方式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阻拦和羁绊。故其名曰“交流资本主义”再正确不过。正是交流资本主义的循环回路性和自由流通性,交流资本主义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数据资源的互动性发展,包括交流互动所生成的元数据、社会关系及其他关联性资源等都无一例外地囊括其中,进而促动一切有利于人类自由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动能运聚和政治解放。
言及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大数据时代的交流资本主义作逻辑分析。交流资本主义为个体的自发政治行动提供了基础设施,包括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等。但个体通过发送推特、电子邮件、微信、博客、QQ签名等活动不自觉地将自己卷入交流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活动中。当然貌似这些行为与政治关联度不强,但实则通过自己签名化的信息就在无意中贴上了个体参与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标签。这就产生了一种幻象政治,即许多人开始觉得现实政治不靠谱,无法参与现实政治实践。于是,在复杂多变的网络信息领域,公众选择的领域就更为广阔和海量了,个体开始主动识变、求变、应变,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数字网络技术的交流循环回路之中,从而实现物质资本和精神需求的双丰收。诚然,在交流资本主义的数字化信息生产过程中,卫星、光缆、大数据、智能服务器、GPS/BDS全球导航系统都无一例外地加速了这种智能化运营和交易,实现了数字化生产、数字化服务,从而将资本快速地循环至极少数超级大资本家手中。由此可见,交流资本主义是一种去主体化的智能系统运作。其行为方式就是要实现一切生产要素的自由化流通,将交流过程中的主体性障碍剔除,实现人民主体力量的壮大。这就不自觉地将交流资本主义的经济动态发展为一种政治化的运作模式。
在迪恩看来,政治主体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缺口,因为人民是政治的主体(所谓的人民,是指分裂的人民;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人民,而不是作为民粹主义整体的人民)。[2]175在交流资本主义的构境中,如何实现交流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必须借助政治,实现一种政治主体的解放。否则人民永远不可能在政治上出现,换句话说,“人民”不是本体论范畴。人民只是作为一种集合的子集,作为一种权利而存在。在我们的印象中,人民试图以文件、社会惯例和组织的形式表明自身的存在而已。实际上,在迪恩眼里,真正的人民都是其作为代理人存在。所以,意欲实现人民作为共产主义的主体性结构力量,就必须发展人民主体。但如何打开政治主体的缺口,将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集体性力量,是一道必须解决的难题。回到迪恩的观点来看,他认为,“作为社会特征的经济、生产方式——无论是数字化的还是非数字化的——并不能决定政治主体。”[2]176所以,要想实现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集体性力量,就必须建构一种群众性政治实践体系。
正如迪恩所言:“群众具有破坏性、创造性、不可预测性、传染性和临时性。他们不会忍受。”[2]176如果要实现群众的集体性力量,就要积极团结群众,这是进行政治活动的有利因素。只有将群众相互团结在一起,才能凝聚一种共产主义发展的集体性力量。在《群众与权力》(Crowds and Power)一书中,伊莱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将群众出现的时刻描述为“放电”(discharge)。在这一刻,所有属于群众的人都消除了他们的差异,感到平等。[13]基于此,群众如何获得政治归属感,就在于群众是否获得了平等主义的感觉和实质。
所以说,群体性的大规模集中,将会产生集聚效应,使群体在高度密集化的兴奋中将自身效应释放于此,各种释放所引起的身体和精神放松随之而来,自由解放的潜意识随之上升。在这种势景之下,集体享受平等主义的共同归属感从此油然而生。当然,这种暂时性的自由解脱并不会持续太久,随着群体性集聚的脱离,绝对的平等状态也归化为个体性的对立差别。但在高潮“放电”中,“绝对平等的状态”取代了个体化的区别。言外之意,平等主义的“放电”是产生群众平等状态的内因,只有个体性的平等意识上升至集体主义时,平等才能名副其实。实际上,平等感觉的自由时刻更是一种共同价值理念的超级升华。卡内蒂认为,群众的平等助长了所有对正义的要求。而且在迪恩看来,“平等作为一种归属——而不是分离、权衡和衡量——是赋予对正义的渴望‘能量’(卡内蒂术语)的东西。群众集中了平等和对正义的渴望(因此实现了马克思与工厂联系起来的功能)。”[2]177从群众对平等主义的渴望来看,群体性运动(但并非暴力事件)就是一种人民运动。只有发动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力量,平等主义才能有效实现。然而对于资产阶级而言,人民是一种可怕的力量。他们试图消灭人民主权,修复人民与资产阶级产生的裂痕,利用数字媒体将人民的注意力分散,从而达到消灭人民主体间性的内驱力。
正因为如此,左翼的使命就是要团结分裂的人民主体,将其诉求、主张、问题等予以现实性回应。而作为社交媒体就是要鼓励和反映人民诉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诚然,交流资本主义则将群众的多样性、混乱和不确定性视为燃料或动力,试图分散其群众的力量。基于此,对交流资本主义应持以怀疑态度,将交流资本主义的流变性消灭至萌芽状态。
然而,交流资本主义却产生了群体性效应,具体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类型,例如:朋友群、粉丝群、同事群;日用品和一次性用品群;大数据群;因网络经济不平等而失去工作、家庭、生活和未来的群,等等。这种群体性的长尾效应需要从“幂律分布”(Power Law Distributions)的角度来加以解释。在迪恩看来,交流资本主义刺激了产生幂律分布(或电力法分布)的网络生产。它依赖于一般领域或公地的创造和圈闭,其特点是自由选择、增长和优先附加。这样就随之产生了共同性的“一”和在顶部的“一”。这里需要解释说明的是,此处的“一”是一种交流资本主义产生的共同性主体力量,其属性具有“归一性”和“统一性”特征。但是交流资本主义在创造“一”的同时,势必造成了数字网络主体的不平等性和差异性。正如阿尔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Albert-Laszlo Barabasi )所表明的那样,复杂的网络遵循权力法分配的链接。第一名或给定网络顶部的项的链接数量是第二位的项目的两倍,后者的链接数量超过第三位的链接,因此底部和底部的链接差异很小,但顶部和底部之间差别很大。[14]换句话说,名流和上层阶级在数字媒体中的粉丝占据了上风,而普通大众则占比很小,极少得到关注。正如迪恩所言:“大众媒体用‘80/20规则’、新经济的‘赢家通吃’或‘赢家通吃’的特征以及‘长尾’等术语来表达了复杂网络的幂律结构。”[2]179
所以说,不管何种网络领域,诸如百度、推特、亚马逊、谷歌等,它们的网络内容都不重要,重要的反而在于以数字为媒介的资本主义垄断了交流渠道,以至达到一种新的奴役和剥削。在迪恩看来,交流资本主义的主要驱动力就是交流,交流在数字信息和媒介流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交流的交换价值远远大于其交流行为的意义和使用价值。因为只要在数字技术的循环回路中,交流就是数据流,交流就会产生数据资源的价值增值。更重要的是,在交流过程中,交流的信息资源可以共享,实现了价值在循环流通中的几何级增长增值。在这样看来,交流资本主义就是发挥数字在交流过程中所蕴含的海量性、速度性和流变性,来实现一种集成化的、复合式的、幂律分布排列的强大结构力。言及于此,迪恩所追求的集体性就是借助于交流资本主义的强大幂律分布规律来实现其自身的政治理想,即将交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集聚群体全面整合于交流回路的循环轨道,通过群体的集中化效应来实现自身政治发展目标。所以数字政治就是数字交流资本主义与政治的程式化结合,一种数字交流的循环回路促进群体的结构性裂变,从而实现群众力量的发展和壮大,最后凝聚成共产主义的磅礴之势,即建立共产主义的主体性建构:人民主权力量。正如迪恩所言:“在复杂的网络中,这个体积,这个数字,在幂律分布中是分层组织的:一对多。”[2]179这句话正好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在数字化网络技术的运行中,海量数据的呈现就是实现一种分层组织的结构化运行,遵循幂律分布规律。当然,迪恩之目的并非要实现交流资本主义的“一”对“多”效应,而是要借助数字的交流价值来为人民的解放作以叙述。毕竟人民集体性的发展不是靠交流的资本主义的循环回路就可以实现的,迪恩就是通过数字技术的循环回路实现其人民群体的海量性发展,从而揭示其“一”的归化状态。此处“一”意指共同性和集体性,是一种统一的团结状态。而相对应的“多”是指一种离散化的、流众般的分离状态。当然,迪恩的政治理想就是要聚合“多”,发展“一”。总之,欲求人民集体性的回归,必须顺应共产主义的势景,在其数字交流的循环回路中,加快数字流动(当然这里的“数字”并非实然的“算法数字”,而是隐喻其群体的“群众数字”。)循环,从而打开政治缺口,将群众性的集体性力量释放出来,进而促进人民主权力量的回归,即实现政治的人民解放。当然在数字群体裂变的过程中,唯有加快数字交流循环,才能引起数字的裂变,进而引致群体的集约化响应和政治解放动能的“放电”。
当然,在交流资本主义运行过程中,其交换价值的交流贡献使交流产生了各种形式的个性化和奇异化。为此,在数字技术的交流中,应该将各种资源和价值实现集约化管理,将资源和权力集中于一体,从而实现“民主集中制”。在迪恩看来,集中和民主并不矛盾,只有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才能实现人民民主的领导力和凝聚力;反之,只有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方可实现群众动能的运聚和内驱力的释放。所以,迪恩强调的新型民主是一种集体性的民主意识,它通过群体性的民主交流,将群众凝聚于一体,既顺应民意,又关注群众诉求,是一种既发挥群众高度统一的政治引领力,又实现人类政治解放的个性表达力。
迪恩作为西方左翼激进学者的代表,她的思想跟西方其他左翼与众不同,她一直坚持在发挥群众的集体性作用,建立人民主权力量的共产主义主体结构的前提下,全面建立政党制度,积极发挥共产党的领导力。在迪恩看来,先锋党(The vanguard party)是一种政治组织,对于带领人民群众实现自身解放道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指南性的战略引领作用。但是,哈特和奈格里则认为,与生物政治劳动相适应的政治形式必须是民主的、合作的、自治的和横向网络化的。先锋党是不够的、“抱残守缺的”,因为它看起来不像当代生物政治生产的网络。[2]180虽然,数字网络表面看是一种自由选择、优先依恋的智能化网络,但迪恩坚持认为,数字网络不可避免地在最被选择和偏爱的人和许多不被选择和偏爱的人之间产生巨大差异。“网络交流表面上具有的创造性、合作性和民主性特征并不能消除等级制度。”[2]180相反,网络则根据用户的自由选择固化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并以此强化了网络等级制度。所以说数字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满足主体间性利益的同时,也无形中将人类绑架至数字网络的等级制度之中了。因此,数字网络产生的政治形式不可能是横向的、民主的,而是一种金字塔式的权力法运行结构。数字网络仍旧是大企业利益集团或上层阶级的代理工具,其民主仍是表面化的幂律分布,其不平等性也随之产生了赢家和输家、少数和多数。
在日常网络互动中,现在正出现了一种奇特景观:人们通过Twitter、搜狐、阿里巴巴、百度等网站上的热门话题标签实施斗争策略。在网络上,“标签提供了共同的名称,作为斗争的地点;当它们成为趋势时,它们就会从网络上数百万未读、不受欢迎的推文的长尾中脱颖而出。”[2]180随之网络用户根据自身喜好开始选择性的在自身朋友圈进行网络转发。在转发和点赞的过程中,网络看似没有实施纵向营销战略,实则在经过朋友圈(微信、QQ、Twitter、博客、微博、抖音、快手等)的大规模转发和评论发酵中,将隐形的标签开始热门化、传播化,从而造成了实质上的不平等。当然,一些原本正能量的话题标签因为无法产生大规模的数据流而造成信息滞后发展,进而淹没于数字网络的滔滔洪流之中。鉴于此,复杂的生物政治生产网络结构必须发挥先锋党的重要引领作用,才能更好地促进现代政治形式的正向发展。这正好印证了迪恩所叙述的,“新兴等级制度的事实表明,一个新兴的先锋很可能是在生物政治条件下斗争所必需的政治形式,也就是说,交流资本主义。”[2]180
但如何实现交流资本主义的政党领导呢?这就需要借助数字网络的平台,建立平台党和运动党,毕竟网络是一种隐性的超然虚幻体,在有效消除网络等级制度的前提下,应建立一种发展全球公民权和获得平等公地的政党平台。虽然,在迪恩看来,“当代网络不仅会产生少数和多数的权力法则分布,而且会产生新兴的等级制度——尤其是从政治运动中已经出现的先锋派和实践的角度来理解时,这表明了党组织的出现方式。”[2]181于此,网络平台就应势而生了。在数字网络平台的奠基下,各种共同的名称和符号就会海量地在网络平台出现,群众因兴趣和价值利益开始走向聚合,网络平台的聚合化和响应化功能也随之发挥。正如迪恩所言,“当地方政治和议题政治通过一个共同的名称联系在一起时,一个地区的成功将推动整个斗争。单独的行动变成了它们自己加上所有其他的行动。他们灌输热情并激发模仿。”[2]181在此意义上的网络政治就会因共同的理想信念而走向虚拟化的政治实践行动。
但是,网络行为的力量并不表征现实的实际行动。数字网络毕竟是虚幻的共同体,如何将数字网络中的集体性发挥出来并以实际的聚合而开展行动,这是网络革命斗争所深度考量的。于是,迪恩坚持认为要发展政党制度,以政党形式引领革命斗争的有效开展。为此,在交流资本主义中,共产主义的革命斗争就需要发挥共产党的引领力来整合,集中和组织群众建立共同斗争理论;就需要将“新兴的等级结构(标签、共同的形象、共同的政治形式,如职业甚至政党)发展成为竞争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2]182只有这样,共产主义之势景才能势如破竹,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全球性开展。
但也有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出现了,正如宝琳娜·坦巴卡基(Paulina Tambakaki)指出的那样,“当谈到如何设想被剥削者甚至墨守成规者的崛起时,人们对他们崛起的能力提出了质疑,因为他们被主导他们的体制和话语严重削弱了能力。”[2]185言外之意,交流资本主义确实产生了群众,而且这些群体更倾向于集体主义,毕竟交流资本主义满足了为其发展的平等主义主张。但是在交流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那些为数字资本主义所监控的剥削群体和墨守成规者就成为了体制机制的附属品,他们不敢为其伸张正义、不能担当责任,在无形中沦为了交流资本主义的顺从主义者。所以,实现交流资本主义的主体间性发展和主体性建构就是一道难题。为此,必须加强交流资本主义的主体性建构,克服个性化发展倾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共同力量。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主体性建构和集体性发展。
四、结语
大数据时代的数字技术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颠覆性技术革命。数字技术引发的数字资本主义、数字劳动、数字政治等数字化资本运营形式将人类带至了后资本主义发展时代。人类开始从经济驱动式发展转向生命政治解放的人类世。数字技术引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历史性变化,数字主体、数字客体不再遵循传统的主体间性发展,而是在循环回路的主客体反串之间走向了数字技术的异化统治。当然,数字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实现革命性发展力量的同时,也带来了“数字剥削”和“数字殖民”的桎梏。尽管钱德勒和福克斯开拓了社会向度的数字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将资本主义引入了数字技术的发展轨道,但数字技术引致的社会性灾难也是无法避免的,数据垄断、数据剥削、数字殖民化、算法治理等考验着数字时代的“数据人”。对于贾勒特、摩尔、邱林川的数字政治经济学向度的数字劳动发展模式,从一开始就倡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规律,但基于数字技术所扭曲的劳动价值规律将数字劳动变成了数字妇女劳动和数字情感劳动,人类彻底沦为了数字iSlave的奴役状态,数字劳动正成为一种新兴阶级附庸关系。而迪恩、格鲍德和内格里的政治向度的数字政治开始将人类导入了后人类主义发展的政治解放时代。其数字与政治的结合推动了社会运动和平台党的迅速发展,迪恩试图通过交流资本主义来实现一种交流资本的数字生产力解放,进而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但交流资本主义亦须通过数字平台的网络化运营才能实现资本的循环流通,这不可避免地产生超级领导者所建构的平台党发展体系,其动能发展仍将数字剥削隐约其中,人类终究逃脱不了数字技术革命的困囿。基于此,对数字资本主义、数字劳动、数字政治的分析并不能代表事物发展的逻辑演变规律。对大数据时代的共产主义考量应该基于社会向度、政治经济学向度、政治向度的充分榫接,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有规律地、合逻辑地、依规制地促动大数据时代的数字技术合理化建构和绿色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