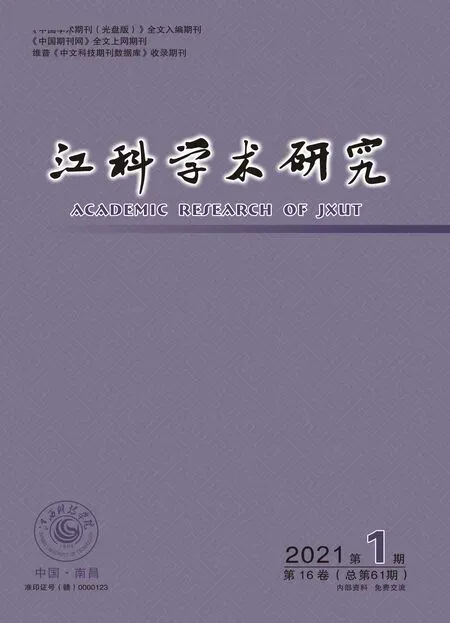张爱玲的创作经验与许地山之关系考
2021-04-14孙可佳
孙可佳
纵观张爱玲的小说,故事的发生集中在两座城市:一个是她的出生之地上海;另一个便是香港。1943年,23岁的张爱玲以一个发生在香港的传奇故事《沉香屑·第一炉香》登上文坛,惊艳开场。她在《茉莉香片》的开篇中写道:“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她将书中的人物安排在香港的大背景中,对这里的灯红酒绿、人情冷暖有着透彻的观察,皆因她与香港的因缘。
1939年“欧战”爆发,本来考取了伦敦大学的张爱玲改到香港大学注册入学。自此在香港求学3年,直到1941年因太平洋战争返回上海。这三年之间她未有任何文字发表,但自此之后,她却在20世纪40年代的文坛中焕发出一生最为耀眼的光芒,终生再难超越。有理由相信,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求学的3年经历给予了她重要的文学创作经验——《沉香屑》、《茉莉香片》、《倾城之恋》都与香港有关,与香港的大学生活有关。
就在1941年,另一位身在香港的新文学先锋与世长辞,他便是时任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任教授的许地山先生。作为文学研究会与《小说月报》最早的创办者之一,许地山本在燕京大学任教;后被燕大的教务长司徒雷登解聘,于1935年受聘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任主任教授,一直工作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几个月,因劳累过度而病逝。
在当时香港的殖民地环境里,香港大学聚集着来自中外的师生。而当时港大聘中国人为教授,仅有医学院王宪益和许地山两位[1]。许地山早在1925年便出版了《缀网劳蛛》《商人妇》《空山灵雨》《无法投递之邮件》等确立文学风格和重要地位的新文学著作,加之在宗教学领域的盛名,是香港大学极为耀眼的文化名人。从1935到1941,也正包含了张爱玲在港大求学的3年;有理由怀疑,张爱玲在香港大学(当然也可能是此前、此后)吸收了来自许先生的创作经验,聆听过许地山的课程,受到过他的教诲,对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前人对此未有确论,更甚少研究,但在涉及到张爱玲的香港经验之时,也有个别研究者关注到了许地山。一文是黄康显的《灵感泉源?情感冰原?——张爱玲的香港大学因缘》,载于《香港文学》1996年4月第136期,论述了张爱玲与港大的因缘,提供了张可能受教于许地山的诸多重要线索;另一文是邵迎建的《女装·时装·更衣记·爱——张爱玲与恩师许地山》,载2011年第1期的《新文学史料》,主要分析了散文《更衣记》,考察张爱玲的创作与许地山的传承关系。
下文在此二文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分析,考察并证实许、张二人在文学创作上的渊源。
一、许地山张爱玲师生关系考
遗憾的是,据张爱玲回忆,当年港大“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我看苏青》)[2]这段充斥着张氏典型的强烈宿命感的文字,表明了直接证明许、张师生关系的证据已不可考,只能依靠间接的证据和推断。
张爱玲笔下也未有对许地山的提及。她仅有两次谈到自己在港大的老师;在《烬余录》中她回忆了港大时期的历史教授英国人佛朗士(N.H.France):“对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没有多大同情”,“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字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非常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可是他死了——最无名目的死。”[3]佛朗士是一位对中国很有好感、支持抗战的国际友人;他在太平洋战争中被征召入伍,某日黄昏回军营时被哨兵莫名打死。张爱玲另一处提及也是在《我看苏青》中:“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发愤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我能够揣摸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样功课总是考第一。有一个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他给我的分数。”[4]香港人习惯,对老师的称呼有中外之别,若是中国人便叫“老师”,若是外国人便依“sir”的习惯称“先生”,所以虽不能确定是谁,但恐怕是外国老师。这样看来,两处线索都与许地山无关。
有趣的是,佛朗士是许地山的同事兼好友,更经常出入许家。据许地山夫人周俟松晚年回忆:“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地山基于旧恨新仇,奋身走出书斋,奔向街头,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一九三八年,孙夫人,在香港担任‘保卫中国同盟’的领导人……地山虽不是‘保盟’成员,但由于志同道合,与孙夫人过往甚密。特别是她的助手,‘保盟’的司库,英国人法郎斯(此处指的便是佛朗士)先生,也是香港大学教授,与地山是同事和朋友,他经常来我家联系,商讨募集物资及运输线路等问题。法朗斯先生后来在香港对日作战时牺牲了。”[3]这一点值得注意。
既然张爱玲笔下无线索可循,那便考察许地山这边。港大中文学院自1927年创设以来,因时代关系,偏于记诵之学。许地山来港后进行了大胆改革,把课程分为文、史、哲三组,不但讲政治史,还讲文化史、宗教史等。据夫人周俟松回忆,许每周在中文学院任课时间都在20小时以上,因人手关系,文、史、哲的很多课程都由他亲自讲授[4]。1985年接掌港大中文系主任的赵令扬也说:“在学术方面,许地山教授是梵文专家,所以在中文学院期间,曾开过有关梵文的课程,也曾以英语讲授‘中国服饰史’,至于其他文、史、哲之课程,许教授因人手关系,自己负起了大部分的教学工作。”[5]许地山授课负担如此之重,课程如此之多,他又是新文学作家,博学通才,热爱文学创作的张爱玲无论是从兴趣上,还是修课要求上,都应该是听过许先生课的。据上文提及的黄康显的研究,张爱玲选修的组别是Group C1,头两年须修读英文、中国语文及文学、翻译与比较、历史或逻辑。前三项是必修的科目,最后一项张爱玲必然选择了历史,否则不会认识佛朗士;而许地山在历史课程上开课丰富,名气也大,且从他与佛朗士的关系来看,二人必在历史课程上多有合作,故而张爱玲听许地山讲课的确定性就更大了。更值得一提的是许地山的“中国服饰史”课程。张爱玲自称“clothes crazy”[6],在《童言无忌》的“穿”一节中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对服装的热爱:”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2]如此热爱服装的张爱玲怎能错过许地山这门“中国服饰史”课程呢?果然,《更衣记》与许地山文章之间的渊源就证明了这一点,邵迎建对此已有详述,下文将继续展开分析。
推测至此,尽管种种证据都指向了许地山与张爱玲的师生关系,但也不禁发问,既然许地山在张爱玲的创作经验中有如此重要的影响,何以张笔下丝毫不见其踪影?对此邵迎建认为:“从不言及这位恩师或许也正如她一贯所为,对于自己生命中铭心刻骨的人和事始终不发一言,只在‘虚构’的小说中,透出些许蛛丝马迹。”胡兰成便如是。黄康显的文章里也举出了《茉莉香片》的例子:“《第二炉香》与《茉莉香片》提及的华南大学,根本就是香港大学的影子,特别是后者的中文系,言子夜教授可能就是许地山的化身。”《茉莉香片》是张爱玲以弟弟张子静及自己家庭为背景写的,主人公聂传庆父亲缺失父爱,便将希望寄托在言子夜教授身上,饱含着张爱玲自身的家庭创伤和“寻父”情结。文中的文学教授言子夜年过四十五,瘦削身材,穿一袭中国长袍,留过学,热爱中国文学和中国,这些特征都与许地山吻合,况且许地山也是港大唯一的中国文科教授。黄康显认为,既然言子夜是主角所理想的父亲形象,那么也许也正是许地山在张爱玲心中所占的位置。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但是言子夜身上的诸多特征的确有着许地山的影子,也许正是生活经验在创作中的某种投射。
以上所分析的,归根结底还都是在证据不足的基础上做出的推断。何况即便能确证张爱玲层受教于许地山,也不能就此说明二人的创作渊源。所以,还是要到张爱玲的作品中找证据。
二、张爱玲与许地山作品之间的联系
(一)两处酷似的文字
张爱玲正式登上文坛是以《沉香屑:第一炉香》开篇的,文章连载于1943年4月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杂志,5月又有续作《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篇发生在香港的传奇故事彼此毫不相干,前一篇讲的是:上海女学生葛薇龙求学香港,求助姑母富孀梁太太,在声色犬马中迷失自己,成为乔琪和梁太太谋取钱财和男人的工具;后一篇则是,因母亲蜜秋儿太太故意使女儿与性知识隔离,而造成两个女儿靡丽笙与愫细的婚姻不幸,以及两个女婿佛兰克丁贝与罗杰安白登被逼自杀的悲剧。将这两个故事联系在一起的是两个极不寻常的开头: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沉香屑:第一炉香》)[7]
在这里听克荔门婷的故事,我有一种不应当的感觉,仿佛云端里看厮杀似的,有些残酷。但是无论如何,请你点上你的香,少少地撮上一些沉香屑;因为克荔门婷的故事是比较短的。(《沉香屑:第二炉香》)[7]
《第二炉香》的末尾也呼应道:
煤气所特有的幽幽的甜味,逐渐加浓;同时,罗杰安白登的这一炉香却渐渐地淡了下去,沉香屑烧完了,火熄了,灰冷了。[7]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中回忆:“这样的小说开头,在当时的上海文坛也是很少见的。”[8]
但这罕见的、于沉香之中说故事的创意,却与许地山《空山灵雨》中收入的一篇300字小文极为酷似:
妻子说:“良人,你不是爱闻香么?我曾托人到鹿港去买上好的沉香线;现在已经寄到了。”她说着,便抽出妆台的抽屉,取了一条沉香线,燃着,再插在小宣炉中。
我说:“在香烟缭绕之中,得有清谈。给我说一个故事罢。不然,就给我谈佛。”
妻子说:“故事、佛,我也不会说。”
“你就随便说些你所知道的罢,横竖我们都不大懂得,你且说,什么是佛法罢。”
“佛法么?——色,——声,——味,——香,——触,——造作,——思维,都是佛法;惟有爱闻香的不是佛法。”
“你又矛盾了!这是什么因明?”
“不明白么?因为你一爱,便成为你的嗜好,那香在你闻觉中,便不是本然的香了。”[9]
虽说许文意在说佛,但这取沉香线、在“香烟缭绕”之中说故事的意境,正如张爱玲“沉香屑”的原型。张爱玲的《沉香屑》,似接着《香》讲下去的故事。
同样是《空山灵雨》,我们再看许地山的这篇《你为什么不来》:
“有什么呢?她听到末了这句,那紊乱的心就发出这样的问。她心中接着想:因为我约你,所以你不肯来;还是因为大雨,使你不能来呢?”[9]
而在《小团圆》开头,有这样一段被无数“张迷”奉为经典的话:
九莉快三十岁的时候在笔记簿上写道:“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10]
这段描写与许地山的《你为什么不来》何其酷似。即便张爱玲并非是照着许地山的原句原样借鉴;而如若在青年时代曾特别关注过许地山的文字,那么在张爱玲创作的历程中,曾印刻在记忆中的殊为喜爱的字句,自然会成为创作源泉,在笔下自然流泻。
(二)《更衣记》与《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
如若以上两处举例还只是只言片语的酷似,那么《更衣记》与许地山《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之间的因缘关系则是极有说服力的。
对此二文的考证,学者邵迎建已有详细的考证和分析。下文对《更衣记》、《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及二文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补充一些必要的细节。
《更衣记》乃是张爱玲“一文二作”,在此前有英文原作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刊于1943年1月的《二十世纪》。这是一个英文刊物,由德国人克劳斯·梅涅特Klaus Mehnert于1941年在上海创办。主编对张爱玲及这篇长达8页的散文赞赏有加,文章前写有两段按语,称张爱玲为“如此有前途的青年天才”。对所附的12幅表现清末至40年代的女性发型和服装的张爱玲亲笔插图,称赞道“还画出了富有表现力的插图”。《更衣记》刊于1943年12月《古今》第34期。比较这两篇文章,有许多不同之处。前者既是英文,便带有一种对外国人介绍的口吻,叙述以服饰史的描述居多;而《更衣记》则完全淡化了介绍的口吻,增添了许多张爱玲独有的深刻见解。张不是照搬原文,《更衣记》不是服饰史的论文,着力于从“穿”的形式中去看日常百姓思想的转变及浮世变迁,延伸到了女性精神史的发展和社会的沧桑巨变。张爱玲此后也在不断推动服饰成为小说人物的独特话语。
再看许地山的《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早在少年时候,许地山就能做一手好工艺。在燕大求学时,年方弱冠的许地山亦能自己设计服装,穿着自己设计的“长仅及膝,对襟不翻领的棉布大衫”,被视为怪人。后来为了编写一部从未有过的《中国服装史》,年轻的许地山已开始着手搜集大量有关服饰的古画影印本、人物木刻画像和各种照片,也做了不少翔实的校勘和考证。1935年5月11日,天津《大公报》的星期六副刊《艺术周刊》第32期开始连载《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后陆续在5月18日33期,5月25日34期,6月1日35期,6月15日37期,6月22日38期,7月20日42期,8月3日44期,分八期连载完毕。文中所附的百余幅图片,见于1935年6月22日的天津《大公报》;洋洋洒洒数万言,有条不紊地叙述了自清入关以来,中国妇女的服饰和变化,特别是就近代中国同时并存各种各样的女装进行排列和解析。许地山在文章开头说:“本只就个人底癖好和些微的心得略写出来,日后有本钱,当把它扩成一本小图册。”可见他是有计划要写服饰史的。同年9月许地山赴港以后,对服饰史的研究仍在继续。据香港学者卢玮銮《许地山在香港的活动纪程》一文:1939年11月10日许地山为香港“中英文化协会”演讲《三百年来的中国妇女服装》,报导见于次日的香港《星岛日报》[3]。另外,许地山还有《女子底服饰》一文,发表于1920年1月11日《新社会》第8号,内容与《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相近。
巧的是,正是在许地山演讲发表的两个月之前,张爱玲进入港大。既然许地山讲“服饰史”是信而有征,就读港大的张爱玲旁听许地山这门课程的可能性更大了。同时,许地山对服装的沿革及受社会生活与经济政治影响的看法,可能引起张爱玲相当程度的共鸣。
邵迎建的论文将“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与《近三百年来底服装》进行对比论证,也是持如此观点。简单提炼邵文的论点,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在结构上受许文影响很大,内容上也有承袭,特别在“高贵然而沉闷的发型”、“所谓旗装”、“20年代后的幻灭”这几节,表现得十分明显。对比张爱玲的诸多手绘插图,也可看出与许先生之文所附插图之间的联系。
许地山说,“社会生活与经济政治都与衣服的改变有密切的关系”,又说,“近五十年来,上海实是操纵中国妇女装饰的大本营。”[9]回望张爱玲的《更衣记》,将时装变迁处处落笔在中国人的心理上,从清初到民国的每一次社会变动,在女人的穿着打扮上全有体现。文章既有女性在形象观察上的细致入微,又有难得的机智见识,甚至说必须要对晚近的服装史有深刻的体认——通过分析,恐怕正得之于许地山的启发。
三、张爱玲与许地山创作风格的关系
比较张爱玲与许地山的创作风格,更可发现诸多酷似之处。
(一)“生本不乐”与命定苍凉
许地山受佛家“人生苦”思想的影响,文章中总有一种宿命式的悲哀在其中,他在《爱的痛苦》、《爱就是刑罚》、《美的牢狱》等文章中都有所阐述。《空山灵雨》弁言说:
生本不乐,能够使人觉得稍微安适的,只有躺在床上那几小时,但要在那短促的时间中希冀极乐,也是不可能的事。[9]
这本集子“开卷的歌声”《心有事》更以哀怨之笔写道:
心有事,无计问天。
心事郁在胸中,教我怎能安眠?我独对着空山,眉更不展;
我魂飘荡,犹如出岫残烟。想起前事,我泪就如珠脱串。独有空山为我下雨涟涟。我泪珠如急雨,急雨犹如水晶箭;
箭折,珠沉,融作山溪泉。做人总有多少哀和怨:
积怨成泪,泪又成川!……[9]
忽略背后原因,张爱玲的文章也总笼罩着悲剧的苍凉:葛薇龙、曹七巧、郑川嫦、许小寒……无不是悲剧女子,即便是白流苏这样落得不错的结局的,却也不那么痛快。张爱玲自己说:
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自己的文章》)[2]
张爱玲与许地山虽都有“生本不乐”的哀怨风格,但究其形成却各有各的原因,与人生经历等有着密切关系。张爱玲恐怕一定程度上受到许地山的影响,包括佛教的影响——否则许小寒恋父的悲剧故事不会起名做“心经”。
(二)爱恋与女性主题
在主题上,许张二人也有相似之处。许地山笔下多写婚姻与恋爱故事,他所刻画的春桃、玉官等一个个女子形象,写尽了底层女性的痛苦与悲哀。他在《无法投递之邮件》中借主人公之口说:
我自信我是有情人,虽不能知道爱情底神秘,却愿多多地描写爱情生活。我立愿尽此生,能写一篇爱情生活,便写一篇;能写十篇,便写十篇;能写百、千、亿、万篇,便写百、千、亿、万篇。[9]
如陈平原所说:“这虽是小说语言,倒也被许地山付诸实践。‘五四’新文学作家偏爱爱情题材的不乏其人,但象他那样一本正经地‘宣誓’,并且真的一贯始终的却甚为罕见,一本《空山灵雨》,沈从文称为‘妻子文学’。一本《缀网劳蛛》,由男女之情扩展为人类之爱。”(《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3]
对于“男女之情”的主题和女性人物的刻画,张爱玲的偏爱和擅长无需多言,曹七巧、白流苏等等一干人物皆是明证。她自己也说道:
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自己的文章》)[2]
(三)因袭古典
新文学作家之中,受西方、日本等海外文学影响者甚众,当然新文学的发生本身就与世界文学的传入和译介有关;另一方面,很多作家也继承了来自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的经验和特征,甚至独树一帜。
张爱玲的叙事经验中有《红楼梦》、《海上花》等古典小说的影响。语言上的相近读来便了然,同时在情节和人物上,也或多或少带着点古典小说的“宿命”味道。所谓“在普通人里找传奇,在传奇里找普通人”,仍然有着古代传奇的影子。《金锁记》随处是《红楼梦》里旧家族的影子,《花凋》的主人公郑川嫦也被她自己称作是“现代林黛玉;《第一炉香》里写睨儿,“还是《红楼梦》时代丫环的打扮”。张爱玲笔下的种种悲剧人物,即便如何挣扎,最终都逃不过希望的破灭——葛薇龙的一次次挣脱失败后,只得对梁太太说“你让我慢慢学呀”;聂传庆对言子夜的企求破灭了,陷入更为病态的心理……而诸如《连环套》之类的小说,索性任由主人公服从命运的捉弄,连挣扎也不必。
许地山的小说虽有更为形而上的宗教意旨,也因袭了古典小说的宿命味道。在其笔下,人的一生,往往逃不了定数,脱不了传奇架构。生死不自知,一切天定数,他笔下的人物时刻都处在一种困窘、动荡的环境之中。《命命鸟》中的敏明和嘉陵虽情投意合,却被家人以迷信的缘故横加阻挠;《商人妇》中的惜官虽勤俭持家,却逃不过却逃不过被丈夫卖掉的命运,在处处“生本不乐”的悲剧中,他所选择的却不是五四新文化先驱的战斗态度,而是佛道的知命、安命的处世观,就像《缀网劳蛛》中的尚洁,她默默承受、坦然面对,才感动了丈夫痛改前非。总的来说,许地山萧散自然的文风,并不像同时期的新文学作家那样有着浓厚的舶来味道,倒更符合中国古典小说的“说书人叙事”的方式。
这样看来,许张二人的风格相近之间更有某种因缘承袭的可能性。当然以上论述仍有推测的成分,进一步的确证,还有赖于更多确凿文献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