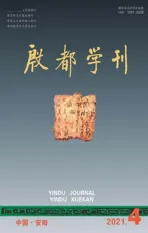荀子的《诗经》阐释学探析
2021-04-14康国章
康国章
(安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荀子名况,字卿,赵人。赵国地属三晋,儒学底蕴深厚,身为孔门十哲的子夏曾居西河而传授儒学。三晋学者向来以视野宏阔而闻名,善于吸收各门派之长,如商鞅由魏入秦力主变法,就体现出三晋士人儒法并重的思想特征。战国末期的三晋儒术进一步向经天纬地的政治层面靠拢,遂有力主礼法并施的荀卿,“荀卿的出现,是战国时代三晋之地儒学发展的最大成就”(1)马银琴:《子夏居西河与三晋之地〈诗〉的传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在《诗经》学术活动上,荀子前承孔门诸子,后启汉代四家诗,作用非同一般,“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2)(清)汪中撰,李金松校笺:《述学校笺》,中华书局,2014年,第453页。。
一、荀子《诗经》学的渊源
荀子的《诗经》学素养渊源有自,很可能与子夏的《诗经》学术活动有着密切关系,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3)(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华书局,1985年,第70页。《荀子》一书中引用有“传”类的文字,如《荀子·修身》云:“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杨倞注曰:“凡言‘传曰’,皆旧所传闻之言也。”(4)(战国)荀况著,杨倞注:《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页。又如,《荀子·大略》云:“《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5)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年,第462页。俞樾《曲园杂纂·荀子诗说》认为,荀子说解《诗经》时提到的“传”就是根牟子的《诗传》,“所引传文,必是根牟子以前相承之师说”(6)(清)俞樾:《春在堂全书》(第三册),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54页。。
子夏曾在西河传授《诗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7)(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0年,第1747页。。《魏世家》谓“文侯受子夏经艺”(8)(汉)司马迁:《史记》,第1490页。。《礼记·乐记》云: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问溺音何从出也?”子夏对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云:‘诱民孔易。’此之谓也。”(9)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第548-551页。
据《论语·八佾》“绘事后素”云云,孔子曾盛赞卜商论诗给予他极大的启发,则知子夏之《诗经》学智性十足。《韩诗外传》卷5第1章载有子夏和孔子论诗的相关文字:“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曰:‘《关雎》至矣乎!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虽神龙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书图,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叹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地。《诗》曰:‘钟鼓乐之。’”(10)(汉)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164-165页。《韩诗外传》卷2第29章云:“子夏读《书》已毕。夫子问曰:‘尔亦可言于《书》矣。’子夏对曰:‘《书》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弟子所受于夫子者,志之于心不敢忘。虽居蓬户之中,弹琴以咏先王之风,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亦可发愤忘食矣。《诗》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疗饥。’夫子造然变容曰:‘嘻!吾子殆可以言《书》已矣。’”(11)(汉)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第72-73页。子夏之学为《毛诗》源头,《后汉书·徐防传》云:“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12)(南朝·宋)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第1012页。《毛诗正义》曰:“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1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69页。
二、荀子《诗经》阐释的语言学基础
荀子善于《诗经》阐释,不仅与子夏以来的《诗经》学术传统有关,还与战国以来语言学蓬勃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有关。战国初期的墨子提出了语言学范畴的名实观,《墨子·经说上》云:“名:物,达也,有实必待文多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14)方勇译:《墨子》,中华书局,2015年,第345-346页。稍微年长于荀子的公孙龙子,更是重视“名实相称”“名称相分”,《公孙龙子·名实论》云:“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即是说:“彼此者,以示万物分别之界也。盖名正而后万物之彼此乃不混;设吾谓而人皆应之,即可知其当矣。”(15)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中华书局,1963年,第60页。公孙龙子特别“讲求析辞,注意词法的细微差别”。(16)胡奇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页。在《白马论》中,公孙龙子提出了“白马非马”的逻辑命题:“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形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17)黄克剑译注:《公孙龙子(外三种)》,中华书局,2012年,第42页。荀子整合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实理论,在孔子的正名观、墨子的名实观、名家的名实辨析论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正名理论,他说:“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18)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360页。;“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19)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367页。
荀子的《诗经》解释实践与其语言学思想应该具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性。战国晚期,面对天下即将一统的社会现实,必然会有某种相对威权性的《诗经》解释脱颖而出,这与荀子所说的语言具有约定俗成性具有相同的文化趋向,《荀子·正名》:“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20)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362页。解释经典文本的语言文字,要做到明确而无歧义,使人不易误读。经典文本不但需要学者不断地去完善释文,还要倚仗当权者的强力推广,方能转化为人们普遍遵守的文化准则——“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荀子·正名》)有了统一的文化准则,百姓才有可能安分守己,最终达致天下太平——“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其民悫,悫则易使,易使则公。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如是,则其迹长矣。迹长功成,治之极也,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荀子·正名》)
三、荀子解释《诗经》的儒学根基
1.隆礼义而杀诗书
荀子是战国晚期的儒学大师,也是先秦诸家之学的融会贯通者。据《史记》记载,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21)(汉)司马迁:《史记》,第1842页。。齐文化本来就具有质朴实用的特征,《史记·鲁周公世家》云:“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22)(汉)司马迁:《史记》,第1275页。管仲以法家而闻名,同时也重视礼治,《管子·牧民》云:“国有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23)李山译注:《管子》,中华书局,2016年,第4页。齐桓公田午创稷下学宫,促进了百家争鸣,先后有驺衍、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等不同门派学者适齐讲学,“分别针对治国之道提出议论、各抒己见,间接促成各项政治改革与变法运动,因而带动社会政治形态之具体变革”(24)林素英:《荀子王霸理论与稷下学之关系》,《管子学刊》2019年第2期。。
在与稷下学者进行论辩过程中,荀子汲取百家学说之长,提出了以儒家礼义思想为主的王霸之道,《荀子·王制》云:“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而强矣。”(25)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121页。《荀子·强国》云:“彼国者亦有砥厉,礼义节奏是也。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26)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50页。又云:“礼义则修,分义则明,举错则时,爱利则形,如是,百姓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谓道德之威。”(27)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51页。又云:“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人知贵生乐安而弃礼义,辟之是犹欲寿而歾颈也,愚莫大焉。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28)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55-256页。那么,礼是如何产生的呢?《荀子·礼论》云:“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29)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300页。
荀子特别重视礼的作用,与他把礼之义涵看得比较宽泛有关,钱穆《国学概论》说:“礼者,要言之,则当时贵族阶级一切生活之方式也。故治国以礼”(30)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4页。。荀子认为,要想成为明君,就要尊崇力倡礼义之道的儒学大师,“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荀子·儒效》)相对于礼义践行的迫切与紧要,诗书之学乃位于其次,“《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荀子·劝学》)荀子甚至提出“杀诗书”的说法,“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荀子·儒效》)“杀”是“减杀”的意思,“杀诗书”即是降低诗书相对于礼而言的社会地位。“杀诗书”不是因为诗书无关紧要,而是说不能死读书,“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荀子·劝学》)诗书之学的作用在于“隆礼”,彼此有着主次之分,“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飡壶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荀子·劝学》)
2.明道征圣宗经
“道”的内容涉及治国、修身、人际关系、天人观念等多个层面,概言之,则可区分为“天道”和“人道”。道家多言天道,而儒家多言人道。在天道方面,西周初年周公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主张,孔子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孟子谓“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孟子·尽心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说:“荀子在儒家中最为特出,正因为他能用老子一般人的‘无意志的天’,来改正儒家墨家的‘赏善罚恶’有意志的天;同时却又能免去老子、庄子天道观念的安命守旧种种恶果。荀子的‘天论’,不但要人不与天争职,不但要人能与天地参,还要人征服天行以为人用。”(3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50页。荀子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相对于天道,荀子更为重视人道,“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者人也,善藩饰人者也。”(《荀子·君道》)
荀子从“性恶论”出发,在道德修养方面提出“化性起伪”之说。怎样才能“化性起伪”呢?荀子把孟子的“尊德性”转化为“问道学”。具体来说,一是要靠人生践履,“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荀子·大略》)他要求人们把个人的成长置于国家治理背景之下,试图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礼法制度来限制人的自然欲望,最终为国家治理营造出良好的生态关系。二是要靠知识学习。荀子把《诗经》纳入人生修养的程序之中,使之具有了绝对的经典意义。《荀子·劝学》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32)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7-8页。在荀子看来,《诗经》充盈着圣人之道,《荀子·儒效》云:“尽善挟治之谓神,万物莫足以倾之之谓固。神固之谓圣人。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乡是者臧,倍是者亡。乡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33)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102页。《诗经·国风》多言情爱,有失之于淫佚者,《小雅》常为疾上,有失之于怨恨者,荀子却总是能够从中汲取有利于修身为礼的积极因素,如《荀子·大略》云:“《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34)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462页。
四、荀子解释《诗经》的基本方法
荀子强调《诗经》的意义在于明道,为学者切勿追求以《诗经》博取世人眼球,《荀子·大略》云:“不足于行者说过,不足于信者诚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诗》非屡盟,其心一也。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35)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457页。《荀子》一书引用《诗经》辞章凡80余处,居先秦诸子之冠,且多据诗以论礼义。荀子擅长把解诗寓于用诗当中,他“像作家那样将引诗转化为一种比喻的修辞手法,将《诗》像富有哲理的格言或民间谚语、俗语一样看待和使用,以加强自己的论证、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36)魏家川:《先秦两汉的诗学嬗变》,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70页。。
从引诗形式来看,荀子最擅长“先议后引,议引结合”。例如:
(1)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诗》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谓也。(《荀子·劝学》)
引诗见《小雅·采菽》,用以说明君子应当不骄傲不怠慢,谨慎行事。“匪交匪舒”《毛诗》作“彼交匪纾”,《郑笺》:“彼与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则非有解怠纾缓之心,天子以是故赐予之。”王引之《经义述闻》曰:“‘彼交匪纾’者,匪交匪纾也;‘匪交匪纾’者,言来朝之君子不侮慢,不怠缓也。襄二十七年《左传》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荀子·劝学篇》‘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引《诗》曰‘匪交匪纾,天子所予’,是‘彼交’作‘匪交’之明证。‘交’或作‘儌’,成十四年《传》引《诗》‘彼交匪傲’,《汉书·五行志》作‘匪儌匪傲’,又其一证矣。”(37)(清)王引之:《经义述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64页。
(2)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故君子隆师而亲友,以致恶其贼。好善无厌,受谏而能诫,虽欲无进,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贤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恶人之贼己也。谄谀者亲,谏诤者疏,修正为笑,至忠为贼,虽欲无灭亡,得乎哉?《诗》曰:“噏噏呰呰,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此之谓也。(《荀子·修身》)
引诗见《小雅·小旻》,用以揭露小人“亲谄”“疏谏”的恶劣品性。《孔子诗论》第8简云:“《小旻》多疑,疑言不中志者也。”(38)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第261页。陈戍国《诗经校注》说:“诗中‘我’得不到重用,为国事献谋献策而‘不得于道’,他无疑做了‘不中志者’。《诗论》说得不错。”(39)陈戍国:《诗经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第250页。“噏噏呰呰”《毛诗》作“潝潝訿訿”,《毛传》:“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称乎上。”《郑笺》:“臣不事君,乱之阶也,甚可哀也。”《尔雅·释训》云:“翕翕、訿訿,莫供职也。”郭注:“贤者陵替奸党炽,背公恤私旷职事。”(40)(清)郝懿行:《尔雅义疏》,中华书局,2017年,第437页。
(3)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此之谓也。(《荀子·修身》)
“礼仪卒度,笑语卒获”语出《小雅·楚茨》,大意为:礼仪全都合法度,说笑全都合时务。荀子用以说明由礼则治则和的道理。
(4)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故学也者,礼法也。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之谓也。(《荀子·修身》)
引诗见《大雅·皇矣》,用以说明安于礼法和顺从老师的重要性。《孔子诗论》阐释《大雅·皇矣》曰:“‘怀尔明德’,曷?诚谓之也。”(41)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第261页。安于礼法和顺从老师讲的都是一个“诚”字。《郑笺》解释“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云:“其为人不识古,不知今,顺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诚实,贵性自然。”
(5)故曰: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诗》曰:“物其有矣,惟其时矣。”此之谓也。(《荀子·不苟》)
“物其有矣,惟其时矣”语出《小雅·鱼丽》,意思是既要有其物又要得其时,荀子用以说明人们的言行贵在合乎礼义。《诗序》云:“《鱼丽》,美万物盛多,能备礼也。”
(6a)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谓也。(《荀子·不苟》)
(6b)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诗》云:“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此之谓也。(《荀子·非十二子》)
(6c)人习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职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乱,兼听齐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则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胑之从心,夫是之谓大形。《诗》曰:“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此之谓也。(《荀子·君道》)
“温温恭人,维德之基”语出《大雅·抑》,意思是:谨慎谦和的君子一定是具备了坚如磐石的道德根基。荀子三次引用此诗,意义指向皆不相同,可以说是从多方面阐释了君子品德的内涵:在《不苟》中,“温温恭人,维德之基”言君子应具备中庸文雅的道德品质;在《非十二子》中,言君子应该“端然正己”“不为物倾”;在《君道》中,言君子在位则应该善政任贤。
(7)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故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诗》曰:“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蒙。”此之谓也。(《荀子·荣辱》)
引诗见《商颂·长发》,意在说明有仁者在位则礼法完备,礼法完备则天下大治。“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蒙”《毛诗》作“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庬”,《毛传》云:“共,法。”俞樾《荀子诗论》云:“《毛传》训‘共’为‘法’,与荀子意合。‘小共大共’谓大小各有法度,即上文所谓‘贵贱之等,长幼之差’也。”(42)(清)俞樾:《春在堂全书》(第三册),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56页。“骏庬”为“庇护”义,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窃考《荀子·荣辱篇》引作骏蒙,《大戴·将军文子篇》引作恂蒙。……‘为下国恂蒙’犹云为下国庇覆耳。《荀子·荣辱篇》‘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下引《诗》此句为证,则恂蒙有群相庇荫之象。”(43)(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第1178-1179页。
(8)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穷:为上则不能爱下,为下则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穷也。乡则不若,偝则谩之,是人之二必穷也。知行浅薄,曲直有以相县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穷也。人有此三数行者,以为上则必危,为下则必灭。《诗》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屡骄。”此之谓也。(《荀子·非相》)

(9)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抴。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抴,故能宽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诗》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谓也。(《荀子·非相》)
引诗见《大雅·常武》,用以说明兼容之术的重要性。君子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则四方来服,天下大同。俞樾《荀子诗论》云:“以此说‘同’字,‘同’之为义大矣。毛公无传,孔《疏》述毛意,以为‘与他国同服于王’,其义转浅。”(44)(清)俞樾:《春在堂全书》(第三册),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56页。
(10)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如是则贤者贵之,不肖者亲之。如是而不服者,则可谓訞怪狡猾之人矣,虽则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诗》云:“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此之谓也。(《荀子·非十二子》)
引诗见《大雅·荡》,用以说明仁者当以礼义安天下,兼以典刑威服奸滑之人。《郑笺》云:“此言纣之乱,非其生不得其时,乃不用先王之故法之所致。老成人,谓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属。虽无此臣,犹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无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诛灭。”
《荀子》中还有一种较为常见的用诗方式,即“议中夹引,边引边议”。如:

引诗见《小雅·小明》。“嗟尔君子,无恒安息”犹言“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犹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神之听之,介尔景福”犹言“知明而行无过矣”。“神”之“化道”犹君子向学——博学则无过,无过则无祸,此即为“景福”。《孔子诗论》第25~26简:“《小明》,不……忠。”(45)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第270页。通篇观之,《小明》颇多怨言,故《诗序》云:“《小明》,大夫悔仕于乱世也。”
(2)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螾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荀子·劝学》)
引诗见《曹风·鸤鸠》,荀子用以说明君子凡为事皆当用心专一。《孔子诗论》第22简云:“《鸤鸠》曰:‘其仪一氏,心如结也。’吾信之。”(46)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第268页。《诗序》云:“《鸤鸠》,刺不壹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3)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义屈信变应故也。(《荀子·不苟》)
引诗见《小雅·裳裳者华》,用以说明君子当根据道义屈伸进退。朱熹《诗集传》释之曰:“言其才全德备。以左之,则无所不宜;以右之,则无所不有。”(47)(宋)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2017年,第246页。《孔丛子·记义》云:“于《裳裳者华》见古之贤者世保其禄也”(48)王钧林、周海生译注:《孔丛子》,中华书局,2009年,第45页。。
《荀子》用诗一般为明引,但也有个别暗引的现象。如《荀子·大略》云:“故《春秋》善胥命,而《诗》非屡盟,其心一也。”“《诗》非屡盟”系化引《小雅·巧言》“君子屡盟,乱是用长”之语,王先谦《荀子集解》云:“言其一心而相信,则不在盟誓也。”(49)(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第490页。
荀子还是一位文学大师,善于钩稽故事,在故事中引诗证言。如《荀子·大略》云:
子贡问于孔子曰:“赐倦于学矣,愿息事君。”孔子曰:“《诗》云:‘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事君难,事君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事亲。”孔子曰:“《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事亲难,事亲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妻子。”孔子曰:“《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难,妻子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朋友。”孔子曰:“《诗》云:‘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朋友难,朋友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耕。”孔子曰:“《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耕难,耕焉可息哉!”“然则赐无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圹,皋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此则知所息矣。”子贡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50)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461页。
故事中五次引诗,“温恭朝夕,执事有恪”语出《商颂·那》,“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语出《大雅·既醉》,“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语出《大雅·思齐》,“朋友攸摄,摄以威仪”语出《大雅·既醉》,“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语出《豳风·七月》,荀子皆用以说明“生无所息”的道理,《列子·天瑞篇》云:“子贡倦于学,告仲尼曰:‘愿有所息。’仲尼曰:‘生无所息。’”(51)景中译注:《列子》,中华书局,2007年,第19页。荀子这种诗事结合的解诗方式,后世的《韩诗》最为擅长,陈乔枞《韩诗遗说考》云:“或引《诗》以证事,或引事以明《诗》,使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虽非专于解经之作,要其触类引伸,断章取义,皆有合于圣门商赐言诗之意也。”(52)(清)陈寿祺撰,陈乔枞述:《韩诗遗说考》,《续修四库全书》(第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94页。

五、荀子与汉代《诗经》学的关系
荀子的《诗经》学术活动极大地推动了《诗经》的经典化进程,其通经致用的《诗经》理念对汉代《诗经》学的发展具有引领性意义。有学者指出,汉代四家诗“远祖皆为子夏,近则出于荀子”(54)刘毓庆、郭万金:《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文史哲》2005年第1 期。。就文献记载而言,汉代的《鲁诗》《毛诗》《韩诗》皆与荀子的《诗经》学术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鲁诗》的开山祖师申培受业于荀子的弟子浮丘伯,《汉书·楚元王传》云:“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55)(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第1495页。《汉书·儒林传》云:“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56)(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2676页。《鲁诗》之说多有附会荀子言语者,如《荀子·子道》云:“子路盛服见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风则不可涉也,非维下流水多邪?今女衣服既盛,颜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谏女矣?由!’子路趋而出,改服而入,盖犹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语女。奋于言者华,奋于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则知,行至则仁。既知且仁,夫恶有不足矣哉!’”(57)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年,第487-488页。刘向习《鲁诗》,其《说苑·杂言》杂取荀子之语而推衍曰:
子路盛服而见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昔者江水出于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滥觞。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风,不可渡也。非维下流众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颜色充盈,天下谁肯加若哉?”子路趋而出,改服而入,盖自如也。孔子曰:“由,记之,吾语若:贲于言者,华也;奋于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为能之,不能为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则知,行要则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诗》云:“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此之谓也。(58)(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第428-429页。
《韩诗》多用荀子之说,清人汪中因此谓之“荀子别子”——“《韩诗》之存者,外传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说《诗》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韩诗》,荀卿子之别子也。”(59)(清)汪中撰,李金松校笺:《述学校笺》,中华书局,2014年,第452页。如,《韩诗外传》卷3第4章云:“王者之论德也,不尊无功,不官无德,不诛无罪,朝无幸位,民无幸生。故上贤使能而等级不逾,折暴禁悍而刑罚不过,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取赏于朝也,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显也。夫是之谓定论。是王者之德。《诗》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60)(汉)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84页此论出于《荀子·王制》,其文云:
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折愿禁悍而刑罚不过,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而取赏于朝也,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显也。夫是之谓定论。是王者之论也。(61)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年,第123页。
《韩诗外传》有时称《荀子》中的文字为“传”,是作卷3第5章云:“传曰: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性为己至道,是民德也,未及于士也。行法而志坚,不以私欲害其所闻,是劲士也,未及于君子也。行法而志坚,好修其所闻以矫其情,言行多当,未安谕也,知虑多当,未周密也,上则能大其所隆也,下则开道不若己者,是笃厚君子,未及圣人也。若夫修百王之法,若别白黑,应当世之变,若数一二,行礼要节,若性四支,因化立功,若推四时,天下得序,群物安居,是圣人也。《诗》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62)(汉)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84-86页。此论出于《荀子·儒效》,其文云:
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坚,不以私欲乱所闻,如是,则可谓劲士矣。行法至坚,好修正其所闻以桥饰其情性,其言多当矣而未谕也,其行多当矣而未安也,其知虑多当矣而未周密也,上则能大其所隆,下则能开道不己若者,如是,则可谓笃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行礼要节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时立功之巧若诏四时,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博若一人,如是,则可谓圣人矣。(63)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100-101页。
《毛诗》亦与荀卿《诗经》学关系密切,俞樾《荀子诗说》云:“今读《毛诗》而不知荀义,是数典而忘祖也。”(64)(清)俞樾:《春在堂全书》(第三册),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54页。如,《小雅·小旻》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毛传》曰:“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此说源于《荀子·臣道》:“人贤而不敬,则是禽兽也;人不肖而不敬,则是狎虎也。禽兽则乱,狎虎则危,灾及其身矣。《诗》曰:‘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之谓也。”(65)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16页。又如,《小雅·鹤鸣》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毛传》曰:“言身隐而名著也。”此说源于《荀子·儒效》:“故曰: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此之谓也。”(66)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99页。又如,《小雅·角弓》云:“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毛传》曰:“爵禄不以相让,故怨祸及之。比周而党愈少,鄙争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此说源于《荀子·儒效》:“鄙夫反是,比周而誉俞少,鄙争而名俞辱,烦劳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诗》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此之谓也。”(67)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