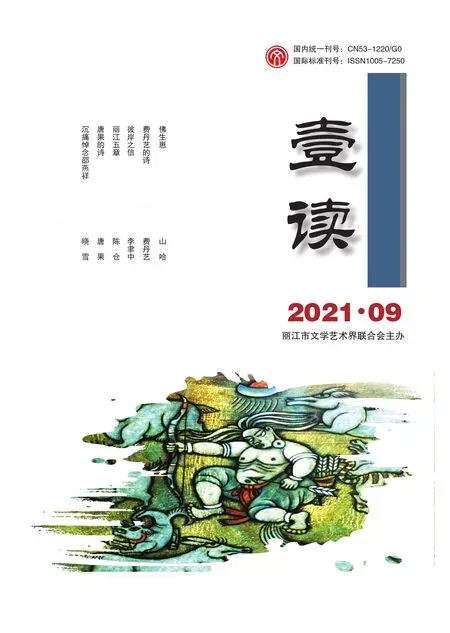河流上的野鸭
2021-04-08宗玉柱
◆宗玉柱
一只雌性赤颈鸭脱单了,于春江中追逐着华丽得有点妖艳的雄鸳鸯。雄鸳鸯躲躲闪闪,一副被骚扰又无可奈何的样子,母鸳鸯就冲上去与之缠斗。那缠斗也只是短暂的一扑,水花溅起的时候,远处的绿头鸭和鸳鸯们受到惊动,纷纷游过来,以为又有人在投食。
管理员不让给绿头鸭和鸳鸯投食,认为这样会影响它们的胃口和野性。尽可能保持原始是目前对生态有效保护的观念之一,相左的观点认为,对于野生动物来说,接近人类或许更能够有利于繁衍生存。事实上,野鸭鸳鸯等更喜欢被投食。鸳鸯也只是这几年多起来,以前偶尔才见,并且离人很远,远到让人失去兴致。绿头鸭就是常客了,往前数,大约能数到2004年,因为据科研者观察,这年冬天,绿头鸭突然不迁徙了。
不迁徙的绿头鸭让科学院的专家们感到惊奇,同时也知道这不能简单地断定是好事还是坏事。喜忧参半吧。经验老道的专业人士,对事物的变化大都保持这种态度。
最初留下的绿头鸭,在寒冷的江水中孤独无助,它们大都聚集在奶头河那片不结冰的水域,接受食肉动物,应该是水獭,还有人类的遴选。那时当地居民还没有人认为绿头鸭也需要保护。
2004年的水獭应该是在惊喜中度过冬天的,它们躲在水底仰看上面浮动的食物时,不知会发出怎样的赞叹。动植物的分类很科学,也复杂到很不好科普,有门、纲、目、科、属、种等分类,还有什么亚门、亚科,除非专业,普通人看过也记不住。比方这水獭就是脊椎动物门、哺乳纲、食肉目、鼬科、水獭亚科、水獭属、水獭。如此,其他已知动物都能找到它的谱系。
水獭的口粮主要是鱼类,当然也抓河边活动的小鸟、春秋时的哈什蚂,有时也吃应季可口的植物。它最长用的手段是伏击,尤其是冬天,常常躲在冰窟窿里,等待鱼游过来透气儿时突然冲上去捕食,估计“大快朵颐”这个词和它没啥关系,能解决温饱就很不错了。
奶头河因为特殊地理位置,冬季不结冰。在寒冷的北方,河流不结冰的地方也不很多,奶头河这一段比较著名。凛冬时节,大多数早晨,不结冰的河面上会生出雾气,雾气附着在岸边的树木上结成厚厚的冰晶,谓之雾凇。晨光透过升腾弥漫的雾气,把冰晶映成五彩颜色,变幻莫测且神秘,就有人把这里取名为“魔界”。
摄影和旅游小众的时候,魔界只有很少的人知晓,去过的人说起那里时,听者会撇嘴道,还能有雾凇岛好?尽管他未必去过吉林雾凇岛,但名气在那里。说魔界好的人如果也没去过雾凇岛,就只好闭嘴。
有一年冬末我在二道白河情人桥上遇到两位沈阳来的大哥,他们看到我脖子上挂相机,就问我当地美景。那天正赶上大雪初停,树枝上挂满厚厚的雪团,阳光明媚,这雪即将被摇落,摇落后便不是摄影者想要的景色了。这二人意犹未尽,我看他俩面相和善,就随口道,可以去魔界。
我们不熟悉地方,一路从雪乡追着雪过来的,正要去,你能带我们吗?两位满是期待地看着我。好吧,明早我来宾馆接你们。问明住处,我欣然答应。
第二天,我也是第一次领略了老魔界的早晨。从日未出时暗影幢幢,到日出后万象绮丽,真当得上人间罕有的魔幻之地。
老魔界早晨很少看到绿头鸭,绿头鸭都隐匿在上游新魔界里,也就是现在的长白山魔界景区。多年后迷上拍星空,去被“更新”严重的老魔界拍过一次,林立的枯木消失殆尽,两岸也因开发,自然丛林被绿化木置换,完全不是过去的样子。受不了光污染,随即就想到了新魔界。半夜九点左右来到河边,设置好相机参数就开始静等,偶尔,远处干苇丛后传来轻微的水声和寒夜中的鸭叫。
听着能有不少。我和同伴悄声说。突然,扑啦啦,呷呷呷!翅膀扑击水面的声音,水鸟飞离时急速带动空气的声音,惊恐而又茫然低哑鸣叫的声音同时响起。
完,是水獭,拖走一只。同伴惋惜道。
水獭肯定是悄悄潜近,然后一口咬住绿头鸭拖进水里。这家伙有獭猫、鱼猫、水狗、水毛子、水猴等很多称谓,除交配期以外,平时都单独生活。我曾查过资料,水獭一年四季都能交配,每胎产1~5仔,生育能力强,暂时不会濒危。所谓濒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种群数量降至临界点,一个是致危因素仍在持续。绿头鸭也不会,但前提是这东西既不好吃,也不值钱。水獭的保护级别是“近危”,绿头鸭的保护级别是“低危”。“近危”者袭击了“低危”者,在动物界属自然,在人类社会也一直默认。
大约过了两小时,又一阵水声和绿头鸭的惊叫声响起。又拖走一只。我对同伴说。
黑暗中互相看不出表情,多少有点不舍。这一夜,水獭总共拖走三只绿头鸭。这样算起来,整个冬天要拖走几百只,但显然不会是这样,要不然绿头鸭很快就会从“低危”晋级为“近危”。那一夜大概是个案。
查看水獭百科时一如其他随看随忘,唯记住一句:“熊食盐而死,獭饮酒而毙。”这话是李时珍在介绍作为中药时的水獭说的,因为熊和水獭都是长白山土著,所以对这句独有兴趣。刘建封《长白山江岗志略》中记载有老虎“食狗则醉,食猪则瘫”,与此十分类似,后来有人证实,食猪则瘫没人见过,食狗则醉确有实例。1947年土改时,抚松县北岗参农靳连学带狗看参园,一虎闯入,吃掉狗后醉了一两天,醒来后复入森林。由此可见古话切莫轻易否定,进而回味“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很有道理。
我对绿头鸭有些许亲近,相比那些对中华秋沙鸭情有独钟的摄友们,我对绿头鸭的兴趣多了些“土”气,前者实属“濒危”,有“鸟类中的大熊猫”之称,后来发现有着这一称谓的鸟类居然很多,能够列出的有震旦鸦雀、黑脸琵鹭、青头潜鸭、朱鹮等,总之它们都是鸟类中的贵族。
有一次与作家胡冬林老师兄妹偶遇情人桥,也就是遇到两位辽宁朋友的那个桥上。原本与他们相约第二天见,提前遇上也是欣喜。正说话间,河左岸一个年轻男子抱着孩子走向岸边,后面跟着一只宠物狗。此刻岸边一只绿头鸭妈妈带着十几只鸭雏正觅食,受到惊扰开始迅速撤离,不料宠物狗猛冲到水边,一边狂吠,一边沿着河岸上下奔走。鸭妈妈大惊,张开两翅,拼命大叫着,随宠物狗的跑动奋力游弋拦截。
青年喝止不住宠物狗,便做壁上观。我们虽然有些不高兴,但知道那狗就是虚张声势,并没有危险,遂静观其变。不料远处湖面沸腾起来,但见满湖的绿头鸭们高声叫着齐向这边飞速游来,分明是大队人马赶来增援。我们头次看到这壮观景象,震惊不已。宠物狗见势不妙,竟丢下主人转身逃之夭夭。过后我们都很惋惜没带设备,没有记录下这罕见的场面。
有一年春天,我在经过美人松林的公路上晨跑,远远看到五六个小黑点在路边快速移动,跑近后看清,原来是才孵化出的鸭雏跟着鸭妈妈过路,路边条石有点高,仅几只鸭雏蹦上去,有六只还在寻找位置奋力翻越。鸭妈妈在路边大声鼓劲,见到有人来,慌忙钻进草丛,片刻又钻出来,勇敢地冲我叫,似威吓,似求助。
见此情景我忍不住要施加援手,但却低估了鸭雏的速度——既要小心鸭雏受伤,又要在快速奔跑中拿获。幸好那时还算年轻腿脚灵便,等把鸭雏全部送上路边,竟跑出一身汗。鸭妈妈带着全部孩子很快消失在通往河边的松林里。手掌中鸭雏毛茸茸的感觉还在,让我心里也软软的,我觉得应该自豪一下,怎么说也算做了件好事,畅快之余,多次讲给别人听。
还有一年夏天,路过双桥,桥下水花飞溅,一只绿头鸭妈妈在使劲撞击一只已经长的很大的鸭雏。我觉得奇怪,趴在桥栏看究竟,原来岸边水中立有一张沾网,鸭雏的头颈不小心钻进网里无法挣脱。我赶紧攀着桥栏下到河边,鸭妈妈退后几米在我够不着的地方焦急地叫着,我费了好大劲才把鸭雏从网上摘下来,然后放到河里。鸭雏一脱手就在水面拼命奔跑,瞬间没了踪影,看来是吓得不轻。鸭妈妈没有去追,而是静静地面对我轻轻连叫,半天没有挪动,似乎是要记住我的长相。我挥挥手说,走吧走吧,赶紧去追孩子吧。那鸭妈妈这才转身离去。
随着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当地人大都以成为野生动物保护者为骄傲,在他们的溺爱下,如今二道白河的绿头鸭已经以主人自居,它们有时会大摇大摆地在人行道上走,有时会搂着鸭雏们在河边睡觉,任来往人等随意拍摄。走在河边廊桥上,桥下会有绿头鸭和鸳鸯跟随,这是夏天常见的风景。如果没有什么表示,绿头鸭会叫几声以示不满和提醒。带点面包饼干类的食品去河边喂绿头鸭,是接待远来客人的必备节目,管理员们对此头疼不已。如此方式亲近自然,这在别处是很少见的,只能表示理解。
有两个摄友来拍绿头鸭和鸳鸯,出来时只带了长焦镜头,等拍的时候就后悔了,距离太近,竟然一时间感觉困扰了。有天中午天太热,我和几个摄友坐在公园椅子上聊天,一只雄绿头鸭飞落到几米远的树荫里,看了看我们,然后抬起一只脚掌呈独立式,把头转向后背,扁嘴巴插在翅膀下睡起觉来。我们几个互相看看均觉得这家伙也太嚣张了吧。拿着相机比划着要和它合张影,后来想还是算了,别打扰人家午休。
绿头鸭和鸳鸯的关系一直是和谐的,当然也有例外。我曾见过一只绿头鸭妈妈带着宝宝们顺流而下,一只鸳鸯妈妈带着宝宝们逆流而上,狭路相逢时,绿头鸭妈妈直冲上去,打的鸳鸯母子们四散奔逃。绿头鸭母子过去后,雌鸳鸯立刻召集起宝宝们继续前行。作为观者,我竟没觉得“霸凌”气十足的绿头鸭妈妈有多可恶,这种打斗原始而纯粹。就假设人类若如此相遇,一定会互相夸赞对方的宝宝可爱,背对时便各自翻白眼——我在面对自然时的这种妄意推断大概也反应出人类心理不健康的现状,或者仅仅是我个人的现状,自觉汗颜。
先前提到的赤颈鸭以及丑鸭、斑背潜鸭、凤头䴙䴘等都是过客,它们只在春秋出现。中华秋沙鸭对人类还是保持高度警惕,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反观绿头鸭和鸳鸯,它们接纳人类的样子满含着自然的温度。梭罗在他的著作《种子的信仰》里引用古罗马科学家普林尼的话:“自然于最卑微处最卓越。”最卑微处——那些非濒危的,保护等级低以及不能列为保护的生命,它们的存在或许意义更大。如这些在近年来率性融入人类社会的绿头鸭,它们以崇尚简单直抵目的为真实,突破物候与物种界限,以身论证着生命何以繁衍承继,同时也检索出人类文明中盛赞平等却按需构建重重束缚的虚伪——当我从书本里抬起头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离走近自然还有很长很长一段距离。
我是务林人,与森林中的树木花草和动物相伴半生,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有身在其中的理解。我曾经认为,只有人类全部搬离出来,才算是真正把万物还归自然,大自然当会按照自己的法则完成自我修复。近来却想,假如这样,修复的自然是不是与人类还能有联系呢?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与自然不可分割,人对自然应保持敬畏,而自然也当为人类提供必要的所需。
我还这样想,人类的破坏在自然来看是无所谓的,放眼地球史,从上一个冰川期到下一个冰川期,很难说是因为什么生物破坏引起的,或许它就是一种自然的轮回。人类要做的是在下一个冰川期到来之前,通过对生态的保护,致力科技发展,为未来寻找到出路,为人类争取繁衍生息下去的时间。如此,适合人类生存的自然是最理想的自然状态,这个状态需要长长久久地保持,它关乎人类未来,人类为此应尽的责任更大更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