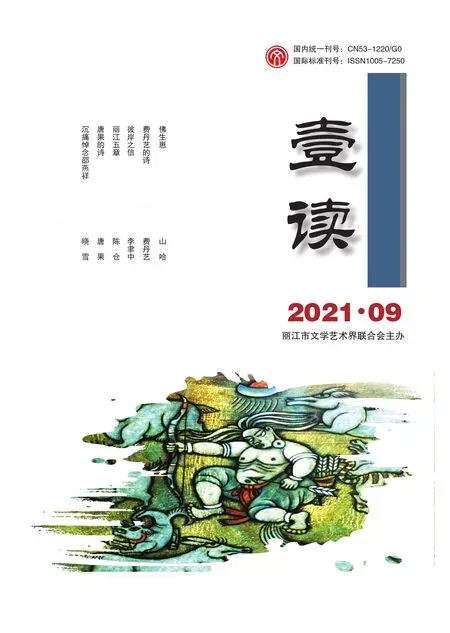获赞美的是滇西 被批判的是神性
——读何永飞《神性滇西》
2021-04-08凌之鹤
◆凌之鹤
没有人看见他踏入救赎的夜晚
他是单独的,孤零零地静坐、游荡
却常被远方的音讯和不幸弄伤
就这样沉思着、默诵着、祈祷着
在月光发黄的留言本上写下: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代题记•沈苇:《夜晚》
单就《神性滇西》这部诗集论,何永飞昭然是一个有着强烈主题意识和明晰写作方向的诗人。从另一个角度看,很少有人能像何永飞这样凝心用情,专门以一部诗集来书写故乡。该诗集以“山水经”、“灵物志”、“众生谱”和“时光令”四卷同构,以近于全景式的诗歌境像为我们展示了“人神共居的滇西”的生活图画和精神图腾。
何永飞以逆道而行之的决绝姿态,以其缠绵丰沛奔腾不息的华丽诗思,以一首首颂歌和哀歌,试图以滇西之“特异”禀赋来“清除世道的杂音,治疗人心的顽疾,救出陷于暗夜的良知和道义”。其志可嘉,其情可感,其心可鉴。阅读如此深情隽永的诗歌,不仅能唤起我们对大美滇西的向往与热爱,而且会激起我们对自己故乡的联想和省察:我们此时热恋或厌倦的所居之地,是否也具有与之相似的伟大神性,甚或比她更具文化魅力?我们此刻挡不住日新月异或正在悄然失去的故乡,是否也面临着转型嬗变的阵痛和亟待破解的现代化困境?
一
坦率说,尽管整个云岭高原、三迤大地旖旎醉人的风土人情都令我魂牵梦萦,但我确实无法掩饰对滇西的异常偏爱。我青春年少时第一次游历滇西胜境,面对苍茫的原始森林和浓郁的亚热带风情,脚踏富饶滚烫的大地,仰望辽阔的蓝天白云,便有一种宛如换血新生之快感。此后多年直到现在,不惟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和腾冲诸地,滇西甚至整个泛滇西的广大壮美疆域,依然是我乐于出行和逗留最多的地方。阅读《神性滇西》这部诗集时,我自然能与诗人高度共情共鸣而心生无比欢悦的美感,恰似:“吐出一叶新绿,激活美学的心跳”。
《神性滇西》显然具有独特的生态诗学意趣。就其温婉而颇富警谕的口吻而言,某种程度上,该诗集中的许多诗篇可作为布道词来阅读——职是之故,在都市读此诗集,宜沐浴,宜焚香,宜在星光灿烂的深夜,宜独对滇西方向:声音宜显忧郁深沉,忌悲怆;节奏宜明快清亮,忌高昂;气质宜沉着沧桑,宜童真,忌挟带功利心。随意翻阅,你会发现,这些诗歌的意义大都清晰明澈,如温情絮语,如话家常,老妪能解。何永飞偏散文化的精美句式,与他看似温和的性情既般配又相得益彰,其诗情绪饱满、飞扬而稳定,一如清溪之水因势赋形,跌宕生姿,时而温柔静流,时而婉转欢腾,不辞山高路远。他的诗歌之美,之清婉动人,不在于其深刻含蓄,寄寓深远,恰在于清新明媚,意旨如明月照积雪,如石上清泉,奔流飞溅,时或在人心上激起漂亮的思想浪花和诸多美的遐想。他诗歌里遍布着散金碎玉的诗句,俯拾即是,读来总能令人获得安宁与慰藉。此处且摘几句,以窥其美:
放下悲伤,回家,回到生命的出发地
枕着芳香的泥土,枕着大地的心跳,不再恐慌
听,流水的脚步声变轻,鱼群在产卵
看,猎人收起了枪支和弓箭,鸟在给孩子喂食
老虎放过受伤的兔子,蟒蛇放过孤独的老鼠
闪电放过矮小的山峰,神灵放过悔悟的子民
任何无辜的生命,都需要特别尊重
任何艰难的活着,都需要特别关照
铁定的法则,在心灵的柔软部位往往会失效
一条具有神性的江,改变很多既定的命运
——《神的使者》
老虎给蚂蚁让路,不会降低身份
明月装饰破屋,不会失去圣洁
——《山野偶感》
袖珍小院,不及巴掌大,却容得下满天星光
容得下四季的花香和满堂儿孙的安乐
——《诺邓》
再看何永飞的“山水经”:他说滇西的“每一座山,都是母亲的乳房,也都是佛”(《朝山》),赞美“无名孤山”,诅咒“山之劫”,也提醒“有些山是奸细”;他发现奔跑的怒江“流水不温柔/它们依旧有刀口一样的锋利,能斩妖除魔/能劈开黑夜的阴谋”,“黑水河、那曲河、萨尔温江、阿怒日美/这些名字指纹不同,但骨子里都藏着咆哮”(《神的使者》)。从这些诗歌中,我们看到,滇西的山,有善骨,也有恶相;滇西之水,有个性,也有情感。而这些拟人化的山水,俨然就是我们自身之理想形象,分明就是人类神化的骨肉与血脉。
二
为故乡立传,为世间万物命名,是所有写作者毕其一生的光荣梦想和追求。何永飞端然也具有如此雄心和抱负。但《神性滇西》既非旅游解说词,也不是诗化的地方志或神秘的滇西灵异志。它固然以滇西为背景,以“神性”为主题,以独具地方特色,绚丽多姿的、密集的意象群落集中书写了滇西的山水、民俗、风物、人情、宗教和栖身于其间的众生万物,却不能简单地以狭隘的地方意识形态去阐释。在这部诗集中,“神性”这个关键词始终像一面时隐时现的小旗子,一直引领或召唤着读者,向熟悉或陌生的现实世界和精神领域摸索前行。这里的“神性”,作为一种标签,更像黑暗中的一束高光,温柔地笼罩着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也照亮了生活于此间的一切生灵。
据某种历史诗学断言,世界是一首未竟的诗歌,所有的诗歌都只是一首诗。《神性滇西》在气象和体量上,允称一部壮观的诗集;就其主题和连绵的抒情语调而言,实则更像一首清婉幽曲、情意缠绵的长诗:何永飞以漫长舒缓的阶梯式诗行,以温和、宁静、清丽的诗句,深情款款邀请并耐心地以各种名目引领读者和他一起深入滇西的每一寸土地,驰骋游目,进而随他一道虔诚地攀登精神的圣山。
如果不是出于对宗教问题的冒犯或反感,敏感的读者难免会心生好奇,在一个无神论流行的国度谈论神性,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而有趣的话题。“神性”一词,本意指人的心灵/精神;喻指经过陶冶的人性,即摆脱兽性、获得神性而出神入化的人所具有的品性。身处一个物质过剩和物欲横流的社会,面对信仰缺失和精神困顿的危机,我们缺少的、最渴望获得的,恰好就是这种“神性”。据此而论,神性滇西实则就是“人性滇西”之美誉也。
何永飞之所以坚定地视滇西为自己的灵魂道场,不唯因其独具纯正的宗教情怀,亦有其立身世俗社会正义之上庄严敞亮的理由。这个自谓被无形之手推入滚滚红尘,在喧嚣虚伪的人群中苦苦挣扎的诗人,在“山水经”的开篇《滇西,灵魂的道场》一诗中如是写道:
从不在狂暴者面前低头,却为三斗米折腰
踩着刀尖前行,身后的跟随者,戴着面具
看不清他的意图,交出去的心
伤痕累累,最熟悉的人,下手最狠
这几行读来令人横起悲哀且惊心动魄的诗,表面上只是诗人自己对冷酷现实和人间险恶、世态炎凉、人性冷漠的激愤控诉,而他所表达的体会或感慨,其实也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共有的人生经验。如非源于所谓病理学层面上的精神强迫症,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我们确实会陷入类似的绝境,那种难以言表的间歇性紧张、惶惑、迷惘以及莫名其妙的焦虑和绝望,真的是让踩着刀尖前行的人“伤痕累累”,痛不欲生。心怀桃花源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谪仙李太白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那只是少数天才诗人的任性,我们固然钦佩和艳羡斯人风骨,但绝对鲜有人轻易率尔效法。识时务者为俊杰。何永飞坦言自己“却为三斗米折腰”,如此诚实,令人感慨。生存是第一法则。这是大多数普通人面临的困境。严峻的生存需求不允许诗性的冲动。尤为让人心寒和忧虑的是,我们慷慨无私的付出全部却未必获得相应的回报;将心比心,现实生活中——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为你两肋插刀,相反,你越熟悉和越信任的人,通常会在你失势或失意之时落井下石,冷不防在你背后得意地插上两刀。
对此险象环生的尴尬处境,何永飞毅然选择隐忍避让,从容回归自然,谦逊地向山水学习,从中汲取善与美的智慧和力量:
幸好,我还有滇西,作为灵魂的道场
那里有高过世俗的神山,有清澈的圣湖
有长过岁月的河流,有菩萨一样慈祥的草木
能化解我的怨恨,能包容我暂时的背叛
能为我打通黑暗与曙光之间的敌意
滇西,安放我最好的生,也将安放我最好的死
据此,他以“神性”二字加冕滇西,与其说是对故乡虔诚的礼赞,不如说是对真善美——对崇高人性的真诚呼唤——他在《大寒之后》,用两句诗对此作了谨慎的回应和自负的确认:
谁走正道,谁走邪道,谁在犹豫不决
被神掌握的一清二楚,而神是另一个自已
“神是另一个自己”。不错。这种清醒的指认源于内心的强大与自信。一个人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表面上像赫拉克勒斯在歧路面临两个美女时的选择:一个是浓妆艳抹,衣着锦绣华袍,体态妖娆而风情万千的“幸福女神”,承诺将给予他终生快乐无忧的享受;另一个是穿着干净白袍,端庄典雅,质朴恬美而眼神忧伤的“美德女神”,却表示不能保证他享受荣华富贵,只能给他指出为人类造福的正义之路。这两个女人,正是伟大的赫拉克勒斯——也是我们要面对的两条道路,一条通向美好,一条通向邪恶。遗憾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像赫拉克勒斯那样,最终勇敢地牵起美德女神的手,走上那条曲折坎坷的荣耀之路,也即拯救世人的英雄之路。
三
何永飞对滇西近似神化的赞美是真诚可信的。赞美之余,他对这方具有神性的土地也作了系统、深刻而颇具书生意气的诗意省察、理性批评和严正批判。毋庸置疑,这种批评/批判乃是爱之深而恨之切的心灵表达。在这部诗集中,赞美滇西的诗行灿若星辰,璀璨可观,读者检阅即可洞悉其妙,此处按下不表。而批判的诗性恰似繁花中的野刺,隐秘而尖锐,稍加留意便会刺激骄傲自大的虚弱神经。这里姑举数例,以辨其锋芒,察其机杼。
《消瘦的牧歌》是一曲农耕文明的挽歌。昔日“白云深处,青草茂盛,牛羊肥壮,牧歌悠悠”,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天然美景,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肉类市场需求的激增而消失殆尽矣;“牛羊越来越消瘦,牧歌也越来越消瘦”,深情而善良的牧人,“他知道,如果牛羊肥壮,就会顺着公路/去到外面,而公路的那一头连着很大的屠宰场”。《悼抗浪鱼》哀思清澈,愤怒溢于诗行间,激荡着强烈的生态忧患意识。因为“钢筋和水泥合谋/权利与欲望合谋,扼杀/一条江的个性/水之狂野被驯服”,导致“习惯生活在激流里的抗浪鱼,已无浪可抗”,遂使这种珍稀鱼类大量死于不洁之水环境,“没有抗浪鱼的江,没有了精气和灵魂/在日与夜之间,缓缓而流,犹如行尸走肉”。《被绑架的马樱花》既是对某种权力意志粗暴地从深山移栽到城市的花木的同情,也是对利欲熏心者野蛮行径的谴责。大树进城,幽兰入室。在城市化浪潮中,有多少野生的古树名花被无辜地移植到喧嚣的城市里,在九死一生的迁徙移栽过程中,那些大树和野花经历了怎样的摧残与折磨,似乎无人在意。那些原本“收藏最干净的鸟鸣,收藏最完好的月色”的奇花异木,无奈以死抗争,最终以反讽而荒诞的姿态,将“不朽的根和枝干,刺进这座城的软肋/有假春天不断混于人们中间”。《山之劫》是对肆意推山填湖、毁庙平坟开发房地产之举的无情诅咒,“没有葬礼,一座山就这样消失于人间/原来的位置上,很快建起好几排别墅/有人在背后悄悄说:那是祭品”。《吃田鸡》《画鱼》《发现金矿》《祖先桥》诸诗作,亦是忧伤弥漫的批判与忏悔之作。
何永飞似乎想通过他灵气氤氲的诗歌告诉人们,万物有灵,举头三尺有神明。他应该知道,即使在充满神性的土地上,居住着的人就算心怀天堂梦想也都是追求眼前利益和现世幸福的俗人。“原来的老屋,被塑料厂占去,院子里的/那棵老桃树,哭了三天三夜,然后枯死了/门前的小溪,全身溃烂,清流全无/黑色的疼痛/在漫延,村子一退再退”,丢掉故乡的人,怎么还好意思要求祖先原谅,“别怪子孙后代”?“房子更大了,家电更齐了,腰包更鼓了”,那又怎么样?“只是田野荒了,时光荒了,人心也荒了”,付出的代价如此之沉重,只怕祖先原谅了,后辈也会埋怨吧?“在他乡,怀揣无数根金条/内心,却有一种抹去的荒凉感”。发展带来的物质富足与精神荒芜,诚然值得警惕。人类在强势征服、掠夺、驯化自然的同时,也丧失了太多的悲悯与敬畏之心。这种持续上演的悲剧,迄今鲜有人理喻。“我知道,谁是凶手,谁是主谋/我也知道,谁戴着菩萨的面具,在行恶/谁在牡丹花下埋炸药,谁在与魔鬼密谈”。作为知情者,何永飞在《被冤枉的水》一诗中,以水之口吻夫子自道,不无天真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不树敌,并不是畏怯/我不揭穿,只是为了给恶退回善的机会/请放心,我不会含冤死去/就算死,也会把尸骨拆解/在天地间,拼出两个字:清白”。如此这般的用心良苦,如是善意的以死自证清白之行为,貌似富有崇高的牺牲精神,但在我看来,却是一种懦弱无为的表现,不想树敌意味着勇气的稀薄甚至妥协,没有敌人则反衬出没有胆识和力量。“我只是卑微者,卑微地活在自己的世界”。这种心安理得,自足无求的“清白”,岂能慰藉凄怆之心?不要也罢。容我直言,何永飞的置疑与批判之声因此稍嫌怯懦而微弱。像古代白面书生独对凶悍匪兵的暴行,他固然知道无法阻止,但袖手旁观又不符合读书人治国平天下的夙愿与道德追求,所以他还是缓步上前,温声劝谕。奈何,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以文犯武,无疑以鸡蛋碰石头,其势壮烈而其效甚微,其情之惨不忍直视。正如他出于某种禁忌而不食鱼,他确实努力在诗中规避开了某些不洁净的意识。恕我刻薄,他那些关于宗教神秘词汇的繁杂堆砌和某些虔诚却近于哀告的布道口吻,在诸如《放生鸡》《猎人秘史》《复仇》《遗弃的祖地》诸诗中不时闪现的因果报应的思想,以及《灵符》《桃木剑》《占卜鸟》《乱坟场》《驱鬼》《护魂人》一类诗里流露的神话/迷信意识,不仅不能揭示滇西的神奇之美,反而有损其固有的原生灵性资源。
不可否认,这些诗歌的形式和韵律都很美,也体现出诗人对乡村传统俚俗文化失传和愚昧落后的乡风依然不绝的忧思与关注,而此间现代文明与农耕文明交锋/博弈的惨烈景象,亦使其困惑无助与惶恐不安的心态隐约可感;令人惋惜的是,正如“占卜鸟”意外溢出的折财消灾的游戏与反讽意味,此类繁花似锦的诗歌美则美矣,但它们空洞却无意义,就像没有生命力的塑料花。
四
中国人文传统里有一个基本的命题,就是道法自然。我们现在回头去看《诗经》《楚辞》,读唐诗宋词元曲,你会发现古代的文人乐于歌咏自然,倾听自然,用今天的话说,可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心与自然之道相通。而自然审美之外,必然有人性的追求与考量在焉。即使涉及神仙一类题材的诗文,大多以人为本,鲜以神灵为主。换言之,古人更讲究人在天地神界之间的合法性和主体性。
阅读何永飞的这部诗集时,我注意到,即便在此神性弥漫或笼罩之奇山秀水间,也有神性/人性缺席的角落,也有令神灵不安、苦难不堪的人生。在“众生谱”一卷中,诗人让我们看到在凤羽街上卖香火、经文的老人,干净安然归去的老人,睿智敬业的通灵者,为忏悔而拯救动物的猎人,丧失独子的老人,不断赎罪的女人,皈依佛门的屠夫,担心魂魄被夺去而拒绝照相的老妇人,漂泊都市失去故乡的人,一身武艺却报国无门的陈佐才,善良的疯女人,挖墓穴的人,内心痛苦而寂寞的抗战老兵,形如虚拟的“傻女”,对自己命运无可奈何的风水先生……“一念晴空万里,一念苦海无边”,这些生活在神性之地的人,尽管都有其自身难以抗拒甚至并不般配的命运,但他们却以自己鲜为人知的方式安静或喧哗地活在人间。《卖自己》是一首悲情泣血之作:一个贫苦柔弱的女人,为了养家糊口和教育子女,她被迫卖掉祖母留下的银手镯,卖掉乌黑的长发,卖掉仅有的几块废铁,最后无物可卖,只能卖体力和血泪,卖自己的年轻和尊严,结果她依然未能走出困境,只能“彻底地将自己卖给一条大江/她纵身跳下,没惊动任何人”。这惊悚而悲摧的命运,这可怜的女人,她走投无路的死不过是一粒被残酷命运投入江中的小石子,不会引起任何回响或关注。
“坚硬的松果落下来,把春天砸得很痛/砸出一个很长的伤口,艳丽的花朵/无法缝合伤口,无法止痛”。何永飞沉重而忧郁地提醒读者,在这块神性弥漫的土地上,历史上也曾有过刀光剑影,有过国仇家恨,其隐秘的创伤与疼痛依然让人想起慷慨悲情。《松山行》《当防空警报响起》《抗战老兵》《滇西安魂曲》《万人冢》《古战场》数首诗,就是对战争苦难的追忆、考察与祭悼。“如果不是山河破裂,如果不是血染家园/滇西的土地,不会生长仇恨,只会普渡众生”。我们绝对相信诗人的判断。因为在这片净土上,“仁义和善行比金子珍贵”,“虎牙可以建造寺庙,枪管里可以栽种菩萨/墓碑上不可以有谎言,脚印里不可以设陷阱”,“血肉无毒,骨头无毒,灵魂不染丝毫尘埃”;毕竟,“胜利最终站在/正义和慈善的这一边”。
信仰之光,滋养滇西,明净无比
这里的青草有山的高度,这里的鱼儿游向明月
这里的云朵带着善意,这里的一切,不论何时
都不拆散爱,不在神的旨意里,开挖暗道
至关重要的是,历经血与火的苦难考验,滇西已拥有珍爱和平与维护和平的能力。你看,她阔步迈入新时代的飒爽和豪迈如此振奋人心:
滇西,江水斩不断,群山布阵,善者入关
奉上美酒和彩云;恶者入关,举起钢刀和雷霆
倒下的人不会白倒下,站着的人会坚守使命
稻谷飘香,瓜果满地,用丰收祭奠曾经的苦难
踏歌起舞,福禄满堂,用喜悦祭奠曾经的哀愁
白骨为笛,吹响我们的敬意,吹响我们的气魄
《神性滇西》是一个安徒生童话里的孩子在深山中孤独而赤诚的呼喊,这种天籁似的呼喊正是何永飞这部诗集中余音绕梁的忧伤旋律:永远获得赞美的只是也只能是自然属灵的滇西,而永远被批判和召唤的,恰恰是我们正在丧失的神性。何永飞有自知之明,身为诗人,首先要明善恶,辨正邪,他才能大义凛然地激浊扬清;其次要知黑白,察生死,他才能理性高昂地正视人生。
作为一个自由写作者,何永飞超然的身份足以让他的精神快意高翔;相对自由无羁的智慧书写——他的诗歌理想当然不只是绘制一个滇西版图,不止于夜郎的地域范围;他理当包括更为浩瀚的心灵世界。
立足滇西,面向辽阔的世界,他的诗歌才华将在更遥远更辽阔的地方发出炫目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