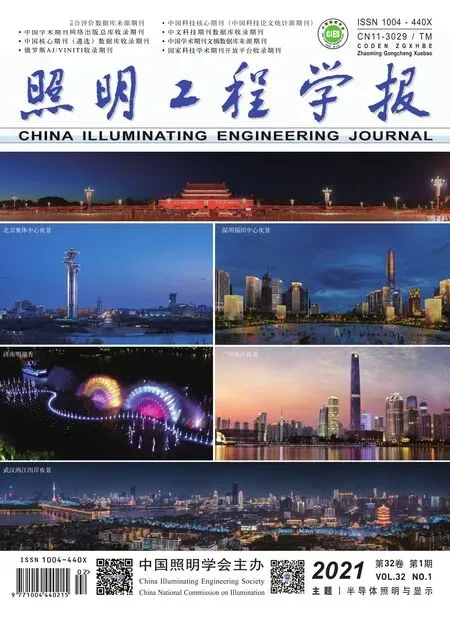现代戏曲灯光审美与古典戏曲灯光的内在联系
2021-03-30王宇钢
王宇钢
(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灯光教研室,北京 100710)
引言
戏曲是我国的艺术瑰宝,是中国传统的演剧形式。在戏曲舞台上,灯光设计也经历了较长的历史发展时期[1-5]。我们所看到的现代戏曲舞台,其所展现的视觉设计与古典戏曲舞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舞台灯光在戏曲舞台上的应用与发展进程,既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也融合了戏曲艺术发展的时代印记。戏曲现代戏灯光设计中所形成的审美特征,是古典戏曲灯光经过发展之后的延续,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特征。
1 戏曲的自身特点及其灯光设计的审美特征
中国古典戏曲在其精神实质上,和中国其他艺术形式一样,隶属于东方美学的范畴,讲究以虚带实、动中求静,以形传神、形神兼备,计白当黑,黑白互衬。戏曲的灯光设计既要考虑到戏曲艺术的特点——综合性、虚拟性和程式性;也要考虑到戏曲艺术的不同体裁——戏曲传统戏、新编传统戏、戏曲现代戏等。不同题材的设计风格和理念有较大不同,所以说戏曲的灯光设计首先要仔细分析戏曲本体,在其本体中获得设计的种子。
1.1 戏曲艺术是高度程式化的艺术
若要分析戏曲的灯光设计,我们必须首先来分析戏曲本身。戏曲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演剧艺术的一种形式,其综合性是很强的。它的综合性体现在它融合了如舞蹈、杂技等其他艺术门类,且具有其独特的新意。此外,戏曲艺术是高度程式化的艺术,体现在其唱、念、做、打等艺术程式的运用上,这四种表演技法的交替使用,将演员动作与剧作精神,凝结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将视觉与听觉艺术相统一,其表现出和谐与节奏之美的戏曲艺术独有的感染力。
在戏曲艺术的表演中,生活的动作规范化及表演的舞蹈化也是程式的组成部分。表演的程式直接或者间接地表现了生活本身,又遵循特定的规范,对生活进行提炼、概括和艺术美化。程式的形成离不开代代艺术家们艺术实践成果的积累,是新一代戏曲艺术家创作的源泉。戏曲表演中的一些生活化动作如梳妆、开关门、骑马、行舟等,皆有固定的形式。戏曲中的程式是体现在各个方面的,不仅限于舞台表演,戏曲的程式也存在于戏曲服装、脸谱化妆、角色行当以及文本形制、音乐唱腔等各个方面。当然,也体现在舞台美术上。
戏曲中的服装,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被叫做穿在身上的舞美,可服装再精美,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角色的神采传达。在戏曲艺术中独强调演员之表演,在灯光上则讲究润物无声,不去过多地追求表面的、形式上的奢华。
在灯光处理上对人物的体积感和空间造型采用减法理念。中国传统戏曲中对灯光使用是有要求的,讲究“无为而为之”,由于戏曲的高度程式性,其演员可能会从其孩童时期就开始进行一招一式的练习,以求在日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在戏曲的灯光设计中,万不可以忽略其演员表演上的要求。同时,观众在欣赏其演剧形式的过程中,也着重欣赏其表演程式的部分,故而,灯光的舞台呈现上也要让观众欣赏到起表演的程式之美。这一点与西方传统戏剧中追求幻觉表演空间的舞台理念相反,而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演员表演程式的体现上。
1.2 戏曲艺术是高度虚拟化的演剧艺术
虚拟化的表现手法是戏曲表演艺术家表演的重要手段。在戏曲表演中,演员用意象化的表演方式来刻画人物、渲染情景,以此来表现戏剧情景。在戏曲舞台上,所有的时间和空间都是虚拟化的,而这也给予戏曲演员处理时空上以非常大的自由。这种虚拟性与西方传统戏剧对于时空所使用的“三一律”以及后来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倡导的“第四堵墙”的概念截然相反,全然没有写实环境所带来的局限性。把舞台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当作不固定的、自由的、流动的空间和时间。舞台是固定的,但是在戏曲的演出中,说它是这里,它就是这里;说它是那里,它就是那里。一千里路虽然很长,说它走完了,它就走完了。从门口到屋里,说它没有走完,它就没走完[1]。
戏曲艺术的虚拟性的形成有两大原因:一是技术上即戏曲舞台技术相对比较落后的局限性带来的结果,二是传统戏曲艺术实践者与创作者们不断追求“神似”的美学理念。这种独特的审美极大地给予作家、以及二度创作者以巨大的发挥空间,也激发了观众的想象力,造就了戏曲所特有的审美特征。中国的戏曲艺术是大虚大实的艺术,舞台布景讲究大虚,很少直接交代具体的故事环境。在戏曲舞台上,拿着马鞭做出骑马的动作,即为骑马,而拿起船桨的动作,就以为正在河上划船游走;戏曲中很多小的砌末是很实的,如《贵妃醉酒》中贵妃的酒杯是实的,然而酒杯中却没有酒;醉酒的贵妃的表演也是很写意的舞蹈化动作,却让人觉得很是酒醉。中国艺术写形的目的是为了传神,最终达到形神兼备。
1.3 戏曲的不同体裁对灯光设计的不同要求
戏曲的灯光设计也会因传统剧目、新编剧目或样板戏等不同体裁而有不同的要求。一般情况下,仍然沿袭一桌二椅的传统剧目如《霸王别姬》《四郎探母》《白蛇传》等的灯光设计,基本也沿袭传统的布光格局。虽然现代舞台的灯光器材有很大进步,灯具也由原来单纯的白炽灯类光源进步为种类丰富的气体放电光源,但仍然使用以面光、耳光、顶光、脚光等传统光位,以白光为基本照明的原则,这也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传神基本原则的追求。
样板戏是文革时期对戏曲艺术内容、形式的重新阐释,如《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戏在灯光设计的要求上也会有所不同,在表现英雄人物的用色冷暖区别上、明度区别上都有所体现。如英雄人物一般用暖光,而且人物要鲜明,以区别与反面人物如《智取威虎山》中的座山雕的阴冷、灰暗的光色。样板戏中灯光对人物的处理是由当时鲜明的阶级爱恨决定的,虽然它显得有些直白和突兀。
戏曲中新编剧目和戏曲现代戏的灯光设计中,加入了很多现代的设计元素。如在灯具上使用大量新光源灯具,如电脑灯、LED灯和追光灯等。为了对角色心理空间的外化和突出,大量使用主观情感色彩及定点光区,或者使用数字影像等现代手段综合化的处理。戏曲现代戏中对新的舞美手法的探索运用一定要与中国传统戏曲的精髓不相矛盾,在其美学框架内不断探索。当今舞台灯光不仅要“使人看得见”,而且还要情景交融地塑造演出空间,使人看得美[2]。
2 现代戏曲灯光的审美特征
当下戏曲创作中的灯光设计,应当结合每出戏的本体特征来进行设计,而不应当一概而论地认为戏曲灯光要以白光为主;或是认为与话剧、歌舞剧一样,以变化多样的色光为主。在面对传统戏时,我们应当尊重传统的做法,用足够亮的白光照明舞台,因为这有利于精美的戏曲服装的展现、有利于武生演员武打动作的展开、有利于将演员的表演与切末道具的场景暗示在观众的想象中完成。
在进行新编戏曲与戏曲现代戏的灯光设计中,要结合其本身的艺术特点来进行具体分析。这些新戏的人物鲜活、故事性强,相比传统戏更加真实,更需要灯光在烘托舞台气氛、突出人物上有自己的语汇。当然,灯光语汇首先表现为营造灵动的时空气氛,突出人物,如样板戏《红灯记》、京剧《风雨同仁堂》、曲剧《茶馆》等。在京剧《骆驼样子》中,灯光设计使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即将演员程式化、虚拟化的表演合情合理地表达出来,对景物及时空氛围的表现也是合乎逻辑的。在舞台上,演员拉着的人力车是实的,同时又做出一套融合角色情绪的表演动作,虚实结合得当,使观众仿佛真的来到了角色生活的环境中,感同身受地与角色产生情感共鸣。这样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戏曲,更能够拉近现代观众与舞台的距离。
戏曲舞台上灯光在一段时间内常被描述为“大白光”,意为以高亮度、大范围布光来照明舞台。这种所谓的“大白光”,并不能说戏曲就完全不存在灯光的设计,其实这种白光的布置,常常会烘托出妙趣横生的戏曲表演,比如传统戏曲《三岔口》,两个戏曲演员在观众一目了然的视觉空间中表演“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间打斗,你一来我一往,组成了一套精妙的肢体表演,从而上演了一出好戏。观众最希望欣赏到的其实是二人模拟在黑夜中打斗的动作,从演员的表演中体会到乐趣。试想,如果这出戏是在一个模拟夜间的微弱灯光下进行的,反而削弱了演员表演所带来的艺术感染力,观众可以欣赏到的内容就大打折扣了。舞台上演戏最忌散神,即使是一出戏终了的时候,只要演员还没走进后台,就不容许松懈下来[3]。
然而,在戏曲艺术发展的长河中,舞台的灯光并不是都以白光登场的,也就是说,传统戏曲中的灯光并不都以照明舞台为目的。查阅资料可见,在明传奇中,刘晖吉为渲染丰富的舞台气氛,尝试在视觉效果上做出改变,并第一次使用特制的灯光。据记载,有一种特制的灯光被刘晖吉应用于戏曲舞台,这种灯被称为“云灯”,“云灯”又叫“羊角灯”,这是灯光在戏曲舞台上的早期应用。在《唐明皇游月宫》这部神话戏中,可以看出创作者在视觉设计上对于美的追求。创作者使用人造光创造出桃源仙境,表现唯美的、田园般的月宫;并利用色光塑造薄的纱幕,构成超世的、富有生机的、浪漫的月宫之境。在戏曲舞台灯光的应用与设计中,这是较为大胆且具有引导作用的尝试。20世纪初,我国戏曲舞台上已经出现了电光源。上海于1908年引进新光源,之后新式的灯光设备也开始在其他城市的舞台上出现。这段时间戏曲舞台上的舞台灯光主要作用有两个:一是负责照亮舞台,二是用来突出重点人物。梅兰芳先生则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灯光作为艺术创作手段,在《嫦娥奔月》这出戏中,使用了在当时十分具有创新性的追光去突出角色,利用视觉效果强化嫦娥的行动和心理表现,彻底改变了以往用灯光只来突出某一个人的局限的作用,进而去创造某一种规定情境来贴合戏剧本身发展的心理时空,同时也将演员塑造的更加饱满。梅兰芳先生创造和运用了追光,在戏曲舞台上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先河。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舞台灯光的艺术追求理念从再现实景的写实用光到表现环境的抽象写意手法用光,戏曲艺术创作者不断实践、实验,做了大量的尝试,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创造出大量的优秀作品,如新编历史剧《杨门女将》《曹操与杨修》《金龙与蜉蝣》《西厢记》等。而戏曲舞台中的灯光设计,在视觉上为戏曲艺术增色添彩,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我们进入了科技发展极迅速的人工智能时代,高级灯光器材的优化与定制,结合演出舞台场地的建设和改造,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戏曲舞台艺术的发展。
3 戏曲灯光的创新与发展
从表面上看,好像传统戏的舞台演出是不需要灯光设计做太多的工作,只要让舞台亮起来就可以了。经典的传统戏演出形式该保留的我们就要保留它,传统戏的演出要保证其时空流动、节奏紧凑、场次连贯的特点,我们不能破坏了经典的东西而一味的去求新求变。
经典的传统剧目演出了几百年,保留下来的舞台演出样式是经过了无数次演出验证了的非常适合传统戏演出的形式。舞台布景也一直没有脱离门帘台帐的基本构架,只是在这个基本构架的基础上作装饰,创新之路一直是举步维艰。传统戏之所以对灯光的应用限制得这么严格有几点原因:首先,戏曲从来讲究的是“戏以人重,不贵物也。”人物造型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戏曲传统戏服装是程式化服装的典型,有一套完整独特的服装体系,戏曲服装的美学原则与戏曲传统戏的舞台美术总风格和谐一致。传统戏的服装制作精良,多以手工刺绣,演员已经是华丽夺目、光彩照人,而灯光这时所要做的就是把演员形象进一步凸现出来,而这也只需要强烈的白光就足够了,运用色光就有可能使舞台画面看起来很燥,这是最忌讳的。其次,传统戏的演出尤其是传统京剧,节奏是非常紧凑的,情节连贯,而且讲述的故事大多是观众熟知的情节,压光是根本没有必要的,中间也不需要变换灯光颜色和强度。变换场次时尽量不要打断观众欣赏的情绪是最好,伴随着急促的锣鼓点,二幕闭合,过场戏仍然在幕外演出。即使没有过场戏,我们仍然不能用压光的方法来破坏整场的节奏。压光这种形式基本上是在话剧演出中应用的,应该是比较现代的一种换场的方式,跟传统的审美方式存在一定的冲突。再次,观众欣赏传统戏很大程度上是想回味,到剧场品味古腔古调、古色古香的韵味,而且观众群相对比较固定,他们本身对色光的运用就不持肯定态度。最后,传统戏程式化的表演方式,也是对灯光严格限制的重要原因。以《四郎探母》的演出为例,整个故事发生在晚上,尤其是《寻营》《过关》两场戏都是在室外。如果按照时间来给光,整个基调应该是夜晚的感觉,但是我们依然保持演区的白光不变,观众只需要通过演员的程式化表演就可以感受到杨四郎连夜过关的紧张情绪。再以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戏《三岔口》为例,故事发生在没有灯的屋内,两个演员表演摸黑打斗,非常有意思。在观众看来满场通亮,两人距离很近的在打斗,但通过看表演知道两人互相是看不见对方的,演员表演到位,配合得非常默契,趣味横生。而这时,如果整场灯光随着道具灯的打翻而突然压暗,虽给了观众这种环境感,却弱化了演员表演带来的情景。在黑暗的环境里这种表演变得顺理成章,反而使那种明明看得见却假装看不见的表演动作的趣味性完全消失,更使观众失去了对这种程式化表演的审美情趣。我们的传统戏需要灯光设计,但要在保证传统戏审美取向的基础上进行设计。
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对灯光的要求与传统戏有所区别,设计者发挥创造力的空间相对较大。因此,近几年演出的新戏中,灯光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新戏的演出逐渐开始运用现代的灯具和特效设备来渲染气氛、暗示剧情、营造舞台氛围。尤其是现在戏曲舞台上中性布景运用得比较多,因此灯光渲染场景气氛的作用就更为突出。如上海昆剧团的《班昭》,舞台美术设计使用了中性的布景,而灯光设计则有意着重强化历史感和文化感,利用灯光的手段塑造中性布景,打造大汉朝古朴厚实、深邃大气的时代氛围:以凝重沉静、舒缓渐变的灯光,凝聚观众焦点,创造一个静心思考的空间。设计者采用了强烈的、充满舞台空间的“光墙”和“光柱”来营造汉代皇宫的金碧辉煌,强化“汉武盛世”的磅礴气势,以具戏剧性的、激变的灯光效果呈现人物的内心情感变化,将观者带入至人物的心理空间,探寻人物的心灵深处。设计师利用明暗光影的效果,为舞台上的一面浮雕墙而精心雕琢,在视觉上创造了多层次的空间,力求强化中性布景的立体感,由此来营造出厚重的历史感。光色以简约、单纯为主。又如京剧新编《贞观盛世》中第五场的处理,李世民返回后宫到“月儿如钩,下照无眠”,此时灯光表现的两个区域使后宫与魏宅两个空间并存;直至隐去后宫、独存魏宅,再到表现释放宫女的宫门的转换,灯光一直配合布景之动作、演员之动作的变化而变化,灯光在这里起到了暗示时间变化的作用。如此一来灯光的表现力更加丰富了,真正体现出“灯光是舞台的灵魂”。
传统戏与新戏虽然在灯光的应用上有一定的差别,但二者仍然有内在的联系:其一,传统戏与新戏同为戏曲演出,自然他们必定要符合戏曲艺术的演出特点,永远不能违背“戏以人重”的原则。即使现在新科技的发达程度不断提升,在戏曲舞台上,它也不能成为追逐的对象。其二,无论传统戏或新戏的舞台,用光都要讲究剧种特色。戏曲最鲜活的特征就是它拥有丰富的剧种:有规范严谨、节奏鲜明、夸张强烈的京剧;优美、秀气,富有诗意的越剧;高亢激越的“山陕梆子”;唱腔婉转轻柔,表现悲剧内容见长的河南曲剧;富有生活气息、通俗易唱的吕剧;粗犷朴素的淮剧;欢快活泼的湖南花鼓戏;用藏语演唱、表现民间传说和佛教故事的藏剧;以及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黔剧,它是由曲艺中“文琴”发展而成、以扬琴为主要伴奏乐器。当然,还有其他历史悠久、具备独特艺术特色的地方剧种。不用刻意的体现,只要设计者在创作过程中把剧种的美作为创作素材考虑其中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形成更贴近戏曲的设计,而不会让人觉得像话剧的灯光,失掉戏曲的韵味。
4 对于现代戏曲的灯光设计的展望
随着外来文化不断进入国内大众的视野,当今的观众审美品位发生了深刻改变。尤其是在科技发展迅速、文化交流繁荣的今天,戏曲工作者更加不能固步自封,停留在一段好听的唱段、一场精堪的打出手、一套熟练的耍锤绝活的追求上,而要创造出更多更具有综合性、时代感的戏曲舞台艺术作品。而作为舞台灯光工作者,在创作上更要不断突破,在保留戏曲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超越自己。
中国戏曲艺术集美术、表演、文学等艺术手法综合于一身,因此,研究中国戏曲就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研究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渊源。每一位研究中国戏曲、从事戏曲工作的人都应该博览众彩,求索上下,如果能在这种五彩的戏剧形式中取得一点小小的成绩,也只能说是在漫天璀璨夜空中摘得一颗星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