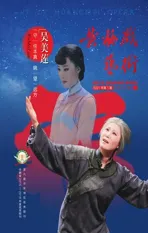黄梅戏音乐作曲家
——陈礼旺
2021-03-29邓新生
□ 邓新生

陈礼旺,好熟悉的名字。
黄梅戏曲谱、唱片、磁带、光盘、网络、报刊上经常见到他的名字。
陈礼旺,安庆市人,1944 年10 月23 日出生。兄弟姊妹四人。父亲陈新池,靠挑扁担、帮工养家糊口。大哥长大后,由二姨爹带出去谋生,后来参加了解放军,一直到全国解放才退伍回安庆工作。父亲是戏迷,喜欢唱京剧,在陈礼旺三、四岁时,父亲就常抱着他进剧场看戏了,平时嘴里总是哼着京剧唱段,其中《丁甲山》一剧净唱的“西皮摇板”[流水板]:“真宋江,假宋江,真假宋江到了俺的李逵手里就遭殃……”的唱段,父亲还亲口教过小礼旺呢(如今,陈礼旺先生对于这段唱腔张口就来,很是中听)。人小喜欢戏,学着戏里的样子,拿着家里的小木头板凳做大锤,一阵乱舞。堂轩很小,舞不开,他不管这些,还是带唱带舞。两个姐姐管不了弟弟,只好抱着头躲开。那时看戏,小孩子不买票,大人带进去,他常挤在人堆里看,不吵不闹,非常懂事,就是“戏尾子”看了也很过瘾……
家里吃饭人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父亲在米店帮工时,每月只有三块大洋的工钱,而父亲性格不急不躁,他常说:“早上没饭吃,晚上还有马骑嘞。”说的是早上穷得没饭吃,晚上说不定还能发财,日子总得慢慢过。母亲朱惠兰,家庭主妇,操持家务总是没得闲。她喜欢黄梅调,舍不得花钱,很少进剧场看戏,有时路过戏院,她站下来听戏,听多了,学会了唱许多唱段,也知道很多戏班“趣闻”:某某某原来是漆匠;某某某六岁登台,六岁唱红等等。黄梅调:“清(来)早起开柴门(呐)乌鸦飞过……”老[平词]起板句唱得是原汁原味。母亲勤劳,一刻不停地忙家务,在打鞋底、补衣服、抹桌子时就唱,唱得叶青,唱得日落,唱得贫苦生活似乎也有了点味道。
母亲经常说:“争的不香”“穷不失志”“穷人的孩子苦读书”“出门要有礼貌”“见到大人要喊”“别人敬你一尺,你要敬人一丈”等等,并伴随着某个故事讲出来,小礼旺常听得“出神”!
平地一声惊雷!1949 年底,安庆刚解放,可家里真正的顶梁柱倒了,父亲在42 岁时得病去世了。那时,陈礼旺才5 岁。有人说,父亲的病,如果有钱是可以医治好的,可是家里偏偏没钱。没钱治病,眼巴巴地看着父亲走了,走得很无奈,也很痛苦。42 岁,很年轻,劳累一辈子,带着无尽的牵挂含泪走了。家里实在太穷,因哥哥是军人,陈礼旺家是军属,所以国家出钱安葬了父亲。父亲葬在“马山”上,没钱买碑,只好立一块小木牌子,过了几年,找不到坟……说到这里,陈礼旺先生眼睛红了,他说,这是他一辈子的痛。记得母亲带着他到“马山”找不到父亲的坟,清明时只好找一个大概的地方烧纸上香。父亲走后,千斤重担一下子落在母亲的肩上:炎炎夏日带着大姐姐上街卖冰棒、过江收鸡蛋;寒冬腊月,给人洗衣、洗被子。母亲饭菜烧得可口,上海工程队来安庆施工时,经人介绍,母亲给他们烧过饭;母亲还在北门口饭店、墨子巷口“来安旅社”打过工;在仓库补麻袋,什么活都做。大姐姐当过佣人、童养媳(在江对岸“东流”);小姐姐帮二母舅摆“京货摊”;亲戚叫母亲把小儿子送到江南八都山去,母亲舍不得,始终把小儿子留在身边带着干活。
安庆解放那天,母亲牵着他,到北门城门口,在进城的队伍中,寻找着大哥。后来打听清楚了,大哥在别的部队里。在解放时,“军属家庭”获得了政府100 斤小米的救济,并能免费看病、吃药。
不知不觉,陈礼旺7 岁了。亲戚说,哥哥在战场上,弟弟一定要读书。母亲看了一眼两个姐姐,她们俩都没读书。母亲决定再困难也要让小礼旺读书。她用布头子缝了一个书包,买了两本本子,一支铅笔,在申请到学杂费全免后,陈礼旺高高兴兴地背起书包上学校读书了。在墨子巷小学时,《打猪草》《闹花灯》的改编者郑立松的爱人斯华云就是他的授课老师之一。陈礼旺人虽小,但穷人的孩子懂事早,他知道读书不易。在学校摇头晃脑地读书,在家里闭着眼睛背书,渐渐地他离不开书了,觉得念书有味道,一有空就学习。有段时间,小礼旺出麻疹,停学40 天,在家休息的日子里,他还不忘读书。期末考试,他居然考了全班第一名,学校奖了一本大本子和一支带橡皮头的铅笔。有个同学不服,在放学的路上,将本子和铅笔抢走了。小礼旺性格倔犟,“我得的奖励,你凭什么抢去?”他来回追了同学几条街巷,硬把本子和铅笔夺了回来。
1951 年,哥哥复员,分在安庆粮食局警卫班搞保卫工作,后调“储运股”任股长,兼搞宣传。他从部队带回一把二胡,在新的岗位上仍然喜欢拉二胡,班长是北方人,由于常经他手申请救济,就同哥哥开玩笑:“陈松年,家里饭都没得吃,你还有心思拉胡胡呀!(注:北方人称二胡为“胡胡”)”哥哥听了,只是笑笑,仍然拉个不停。陈礼旺五年级时,哥哥教他拉二胡,他一上手就停不下来,有段时间,像着了魔一样,一天到晚拉个不停,《良宵》《病中吟》,甚至拉不全的《光明行》《广东音乐》他也要摸摸。到了初中,他就给几个业余黄梅戏剧团拉二胡了,既丰富了业余生活,还能在剧团吃一餐饭。那时有饭吃比什么都好,何况剧团还三天两头吃猪头肉,享了口福。有一年,粮食局排黄梅戏《鹊桥》,哥哥担任导演并拉琴伴奏,郑雪老师(严凤英的琴师兼唱腔设计)的两个女儿参加了演出。哥哥教陈礼旺唱黄梅戏《家住丹阳》《卖身纸》《含悲忍泪》《我家住在大桥头》《西湖山水》、京剧《梅龙镇》生唱的“四平调”、庐剧《十八里相送》、淮北四句推子《主腔》等唱段,并教会了他简谱。
1958 年初,安庆市黄梅戏演员训练班在全省各地招生,广告上写明,安庆只招12 名学员,其中演员10 名,乐队2 名。社会上许多大龄青年都来报名。那时,找工作很难,都想考进剧团,找碗饭吃,所以竞争非常激烈。陈礼旺才13 岁,个子又矮,但不怯场,他认真地拉奏了一曲《良宵》后,又试奏了一个片段,还击节奏、试唱等,走出考场,等候通知。终于在二月中旬接到了录取通知书,陈礼旺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陈礼旺考进黄梅戏演员训练班时年龄很小,但业务过硬,他拉奏主胡音色纯正,起板落板能合拍(曾有过业余剧团的磨炼),因此,在8 月1 日后成立的“安庆市艺术学校”中,他的老师夏积成打板鼓,很是看中他,每个戏都叫他拉主音。“训甲班”演出质量好,上省城,到外地,演一地,响一地。东海舰队陶勇司令员看完演出后,点名要“训甲班”,安庆市委知道后,立即让“训甲班”毕业,分到安庆市黄梅戏一团。事情结束后,“训甲班”的演职员又回戏校继续学习,1962 年10 月正式毕业,更名“青年队”。
1960 年,同学王自诚创作的《防汛战歌》,陈礼旺用曾在安庆江边听到的“夯歌”,结合黄梅戏平词类[八板]的音调进行创作,并向安庆报社投了稿。1989 年,剧作家王自诚改编的《瞎子算命》中,原是皮瞎子上场唱两句:“赵匡胤打马下江东,人似英雄马似龙”[平词迈腔]转[落板],他觉得不行,建议作者给瞎子上场改写了四句现在用的唱词,以谱写的[安庆鼓书]结合[文南词]音调的四句唱腔,来勾勒出瞎子出场的艺术形象,盒带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果。陈礼旺好学,不放过生活中音乐元素的一点一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安庆城有很多音乐性较强的叫卖声:像“白糖饼儿,新米糖嘞!吃着嘴里拉多长啰!”、“卖茶——叶呀——”、“卖芝麻——粉哪!”,他总在留意着:乡村的“山歌”声、城乡中哄孩子入睡的“催眠曲”他都尽收其中。在各地演出,不忘访师、“采风”,记录民间音乐,随处都行。记得小时候,夏天乘凉,总有一个盲人,拉着二胡走街串巷,他的旋律糅进了陈礼旺创作的音乐中,既好听又符合人物性格,后来知道盲人拉奏的音调就是[文南词]。除《瞎子算命》外,陈礼旺在后来的很多作品中,均有所借鉴。当时安庆,有一种叫卖,在地摊前可以听到:“手巾洋袜子(哎),大小汗衫(啊),男女(的)套袜子(呀)!”这些元素,陈礼旺1962 年把它用到民乐合奏《卖杂货》里,指挥全校各班音乐科学生联合乐队排练并演出,与原主题形成鲜明对比,令人拍案叫好!
也就是民乐合奏《卖杂货》和其他几个小作品,1962 年底,寄给上海实验歌剧院全国知名作曲家商易老师(舞剧《小刀会》作曲)审阅后,给予了鼓励:“……从现在的旋律看,将来是有希望的”,它一直鞭策着陈礼旺青年时期的成长。
早在1960 年,他就与山东来的王世庆、王恩起同学合作了第一本大戏《宝莲灯》;1961 年在方集富老师指导下,陈礼旺独立完成了《白蛇传·游湖》一折小戏,演员唱了觉得很好听,至今仍有选段刊载。他还为《断桥》配乐作曲,多个声部组合在学生小乐队中使用着;1962 年在郑雪老师的支持下,为《杨门女将》专门谱写了“序曲”,正式投入演出等。1963年,他应文化馆约稿而作曲的现代两幕三场小歌剧《两块六》,运用了黄梅戏音调作为素材,那时他就知道给人物建立唱腔基调;其次在人物基调的基础上,选取合适的音调来确立全剧的配乐风格(包括前奏、间奏、各人物形象音乐、对话音乐、动作配乐等)。如唱腔中多次“让板”的处理,试图刻画醉汉的神态,小范的唱腔根据[彩腔]改编,采用多种节拍的混合,变五声为六声、七声,唱腔加入了变宫音si 的过门,还加入了清角音fa,增强了离调色彩。配乐在力求形象的同时,注重剧种风格化,小唢呐和曲笛的颤音勾勒出喜剧色彩,戏曲锣鼓有时与音乐同步配合等,达到一定高度的艺术质地。这个戏在当时影响很大,随着剧本的出版,师范学校也将曲子拿去了。原先虽是文化馆约稿的,后推荐给青年队排练,阵容很强,主演汪金才、刘广慧、周旭春、张风兰等,都是台柱子。作为一个学生能写出有“想法”的作品实属难得。同年,又与凌祖培老师合作现代大戏《血泪荡》,他写的前半场,可说是出手不凡,曲子不但黄梅戏味道浓,还特别好听,演员唱起来很是顺口,小乐队超常发挥。既有“平词音调”,又有“花腔音调”,还有[二行]音调变唱的叙述性三拍子呢!流存至今。好!现代戏很有意思!陈礼旺一股作气写下去,这一年他写了小戏《好媳妇》,又完成了大戏《瘦马记》,这个戏开始的合唱、领唱、重唱音调,“南北贯通”“乡土气息”“影响后续”“沉淀至今”;还写了个移植昆曲现代大戏《琼花》,音调上试图创新:链条式激越的大过门,女腔落mi 音的上句行腔旋法,男腔果断空半拍起唱的上句,花腔音调的“女红军队歌”,[彩腔型]的女声二重唱,以及1-5 旋法、“撒帐音调”曲牌行弦的呈现等,为后来创作音调的“自我风格”埋下了伏笔!
1964 年,现代戏持续升温,陈礼旺重点写了大戏《寻亲记》,还有小戏《空花轿》《南方来信》。1965 年他与同学王世庆合作大戏《紧握手中枪》,其中二场前的《织网谣》以[彩腔]音调,用混合节拍予以抒情性的展现,还有小戏《槟榔树下的战斗》《两垅地》《传枪》《金沙江畔》,与马自宗老师合作大戏《王杰》,独立完成大戏《双红棉》,分队排演。
1966 年大戏《长山火海》,掀起了青年队演出剧目的又一个高潮,全团上下齐心,奋力拼搏,此剧在安庆市连演数场,场场客满。安徽省文化厅艺术处于处长专程来看,盛赞全剧演出,并说主演刘广慧唱得好,音乐不错。这个戏的音乐展示了黄梅戏的另种格调,陈礼旺下了不少功夫。他说,这与马自宗老师和王世庆同学的通力合作是分不开的。文革期间,提倡集体创作,他先后参加了省《红灯记》剧组“音改组”,地区《海港》剧组“音改组”,为十多个黄梅戏大、小现代剧目作曲。其中《龙江颂》主旋律谱,在全省六个黄梅戏移植剧目中被选出,由省群众艺术馆编印,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于1976 年2 月出版;《红霞万朵》剧本附曲谱,1976 年7 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红霞万朵》前后搞了三年,拍电影时,陈礼旺刚经历母亲的去世,自己又刚做完阑尾手术,身体还在发炎。就这样,他仍然参加了电影剧组,每天到珠影医务室,照红外线、找线头、消毒、换药。工作需要他,他必须坚持。在《红霞万朵》电影中,他担任了全剧描写音乐的作曲、配器和部分核心唱段及合唱的编曲和配器。在音乐顾问时白林老师的指导下,他全力以赴,每天训练合唱一个小时,直到录音,除演员个别辅导外,全剧唱腔,尤其重点核心唱段“过关”,要集体讨论,再修订;乐队练乐他要听,录音前的“总谱”审阅,他要为时白林老师分担一部分;录音棚他还要负责监听,先期小样拍出后要反复倒片、计时,配乐作曲必须连夜完成,因规定每天上午九点乐团进棚等着“总谱”录音,不能误事。那时正在闹地震,珠影厂安排大家从二楼单间搬到一楼大厅,并要夜里打开大门,由于工作量大,加上有地震的危险,他在《红灯记》剧组犯的“梦游症”又发作了。可见,创作既伤神又伤身。剧组到肇庆游玩,他抽不出时间,也无暇观看当时流行的《红绣鞋》《黑蜘蛛》等中外电影故事,他要构思后期的音乐。在录音的最后一天,时白林老师晕倒在指挥台上,陈礼旺在监听室看到,急忙跑出,与青年演奏家李景侠一起,把时老师扶下指挥台抢救。老一辈的敬业精神,深深地感动了陈礼旺!
这一时期,陈礼旺除了黄梅戏的作曲外,还写了大型歌舞:《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大寨红花遍地开》,蒙古族小歌剧《机智的小乌兰》,指挥、整理、排演了安庆版的《长征组歌》;创作了几十首群众歌曲和语录歌,为服务本土实际需求,部分旋律中,他本能地融入了黄梅“乡音”的音调元素。舞台上的传统,哪个曲子好听,演员就唱哪个的曲子,观众就愿听哪个的曲子。陈礼旺分明就是这样的作曲家,演员喜欢唱他的曲子,观众喜欢听他的曲子。因为陈礼旺的曲子有变数,一曲一新,有创意,不呆板。
陈礼旺成年了,他的事业也成熟了。如果说他少年的曲子是小打小敲的话。那么,二十岁以后的作品则是一步一个脚印,能在黄梅戏音乐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了。
1978 年作曲的《白蛇传》,是陈礼旺在拨乱反正、恢复青年队后的第一个大戏,一共760 多句唱词,写到《断桥》已是凌晨三、四点。上午九点,陈礼旺将曲子送到排练场,刚到剧场,接到电话,说儿子晓峰的手被开水烫了。真是越急越乱,他急匆匆将儿子送到医院。儿子的手还没治好,后面几场又必须完稿。
戏曲唱腔的设计,在注意保持本剧种音乐特色的前提下,有着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以填词式套用原有现成曲调为主,必要时做些变化;一种是掌握本剧种音乐的特点和规律,根据剧情和人物情感的变化而进行编曲。黄梅戏《白蛇传》的音乐主要是后一种的做法。其中《断桥》“想起前情怒冲霄”这一重点唱段,在试图使“花腔板腔化”方面,有所突破。这个唱段在板式上借鉴了[平词]板式中的某些因素,而音调上主要是建立在花腔类曲调的素材中,开始时的散板虽有着[平词导板]的因素,然而[花腔]化了,一气呵成的快板,同哭腔糅合起来,使其更多地有着[花腔]旋法的特点,经过短短行弦式伴奏音乐的过渡,唱腔由感叹的慢板进入叙述性的中板……
主演“白蛇”的演员胡静,以她较好的润腔手法,使得开始两句的散板唱得既奔放激荡,又细致入微。特别是散板第二句的尾子,她借鉴了京剧典型的顿音唱法,同时夹入了音乐性较强的哭泣之音,完美地表达了白素贞在断桥与许仙重逢时的怨恨之情。紧接的三句快板,演唱感情真挚,字字分明,到“你竟将夫妻恩情一旦抛”时,曲调在传统“哭介”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扩展。特别是在紧接唱句“不料你会心肠狠”的“狠”字上,颇具匠心,“狠”字旋律是在板上,按一般的规律是顶板脱口而出,而她处理成把“狠”字含在口内,空出板响后的一霎那时间,才慢慢像拼音似地拼出那“狠”字来,细腻地表达了白素贞对许仙“又是恨,又是爱”的那种微妙情感。
这时的陈礼旺已经非常成熟了,对每个戏的音乐都有“想法”,因此写出的唱腔都有“个性”、都有“特点”。《白蛇传》曲子一经问世,黄梅戏演员纷纷学唱。胡静、周旭春、方宝玲、吴功敏灌了唱片,马兰、吴亚玲录了磁带;范卫红参加省级比赛获得一等奖;鲍晓霞、何玉、汪莉以及业余演员李娟都带着这个唱段参加比赛获奖,最后推荐到全国赛区;满玲玲演唱的核心唱段,在中央三台“名人名段”栏目中多年展播……
1979 年,陈礼旺谱写的大戏《孟丽君》主旋律初稿,虽只用了三天时间突击完成,但质量仍属上乘,各剧团陆续排演,名演员争相录制唱片、磁带、光盘,直至海外发行。
用黄梅戏音乐作为素材,创作纯器乐作品,是他多年来的创作追求,《卖杂货》用的是三段体,修改后的《售货员下乡来》是复三部变奏曲式,《驯山治水》是回旋曲式,独奏、重奏写过,该写奏鸣曲式了,于是陈礼旺想到了《天仙配》这个黄梅戏王牌音乐。
1979 年春,在同学毕昭贵的倡议下,陈礼旺开始构思《天仙配交响诗》,为了有别于《梁祝》的[协奏曲]样式,而采用了较自由的[交响诗]奏鸣曲式,试图在展开部能增强“交响性”。创作前,他带着时白林老师的引荐信到上海,与好友方著若一起,求教了全国知名作曲家曾加庆老师,了解其在六十年代创作的民族管弦乐《天仙配》的相关信息,后得知总谱放在上海音乐学院胡登桃教授处,录音也未听到,只得抓住机遇,聆听其它,获益匪浅。从上海回来后,作曲同行陈泽亚提供了民乐《天仙配》主部主题,单旋律小纸一张,陈礼旺如获至宝,拿来很是研究了一番!黄梅戏作曲家徐高生先生从“上音”毕业回省,寄来多种奏鸣曲式范例。各种资料的累积、研读,都是在寻找着主题音调上那个唯一的“我”。1979 年春到年底,用了近半年的时间,终于总谱脱稿。向文化局汇报后,得到大力支持,文艺科长马兆旺老领导亲自抓,由宋新木同志进行各单位协调、督办,集中全市力量,组成了43 人(弦乐稍弱)“安庆式”双管编制的交响乐队。分组、合乐排练了十三个半天,于1979 年12 月31 日,向市、部、局领导作了汇报演出。省文化厅获悉后,专派艺术处吴虎处长,同刚从“上音”毕业回省的黄梅戏作曲家徐代泉先生来安庆,调阅总谱,后省厅给市局来函:调《天仙配交响诗》参加省首届“交响乐作品试奏”,由歌舞团团长、省音协副主席叶志强老师执棒。这个作品对陈礼旺后续黄梅戏旋律和音乐格调的形成不可低估。
在1980 年,陈礼旺创作《七仙女送子》前后三稿,其中《天仙配交响诗》音乐片断就有所引用。该剧推出后,各地剧团纷纷上演,多个名演员分别录制唱片、盒带、舞台艺术片。在其后的1992 年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上,新版《天仙配》(孙娟、陈兆舜主演)的整理音乐中,唱腔主旋律基本保持原貌,为科学展示两位主演的嗓音特质,在重点场次“路遇”中,将传统调性的四度转调(♭B 转♭E),改变为五度转调(♭B 转F),在合理的音域内,男女主角润腔得以充分展现;恢复原传统“五更织绢调”,众仙女改用多声部唱、合;其它各场调性,尽力适度;新增24 段配乐,调性适当安排;为增强音乐性,每幕之间增加了《间奏曲》等。同样,《天仙配交响诗》的音乐在新版《天仙配》中得以充分展示,除零星呈现外,主部主题音乐完整地用在“路遇”“上工”两场之间的《间奏曲》中。
1986 年,安庆市黄梅戏(地方戏曲)研究院(原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与安徽电视台联合摄制六集黄梅戏电视连续剧《七仙女与董永》,编剧:濮本信;作曲、编曲、配器:陈礼旺;电视导演:吴文忠;舞台导演:罗爱祥;主演:汪静(刘红配唱)、马自俊等。播出后,全国反响很大,获大众电视金鹰奖。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陈礼旺先生拿出了当时全国各地赞誉信函,并简单介绍了该剧音乐的创作过程。
接到剧本后,陈礼旺首先与编剧濮本信反复研讨剧本结构,修定唱词,谈音乐构想,还请徐代泉先生给《梁祝》作曲何占豪老师打去电话,约请加盟,后因何先生不在上海,正忙,未能如愿,只得独自准备“案头”。一番思考后,认定《七仙女与董永》电视连续剧音乐,必须遵从原电影《天仙配》的总体音乐格调,结合当代审美需求,予以必要的延伸。
先期唱腔编曲,沿用原《天仙配》以[花腔类]音调为主,[平词类]为辅的路子,各人物建立基调,七仙女、董永特征音调重点设置;新增角色秋萍(傅小姐)用传统[菩萨调]变唱,傅公子用传统[打纸牌调]变唱,傅员外延用原平词音调“吟诵式”的叙唱,众家丁“一领众合”的抬轿子音乐,运用传统[讨学俸调](以帮腔替代了原传统中的“呀嗬锣”),众仙女以[仙腔]为主,吸收其它,另有七仙女在天宫吟唱的“摇篮曲”,旋律来自安庆民间地方歌调,这些都试图展示传统音调的魅力。为体现神话色彩,多处运用了抒情性[画外音]式的女声伴唱,最后剧终前的重点唱段“不能共唱白头吟”,引用了原《天仙配》分别“董郎前面匆匆走”唱腔旋律,变以女声多个声部合唱的烘托,以求达到音乐的“戏剧性”高潮等。唱腔写好后,吴文忠导演来安庆,在“大会堂”后台,全体剧组演职员审听唱腔整整一个上午,得以认可后,投入排练。摄影棚拍摄的同时,先期音乐配器同步进入,他用了18 天时间,平均三天一集,配完六集总谱,每天工作20 小时,只能睡4 个小时,将自己锁在书房。两个孩子由爱人宁桂英带去姐姐家暂住,时值炎夏,每日洗换衣衫,西瓜、饮食、开水必备,宁桂英来回奔波,安排得妥妥贴贴。
后期描写音乐作曲,先是去合肥看摄影小样,好在有《红霞万朵》电影拍摄的经历,一切按“序”走过。开始进入分、秒准确计时的配乐作曲,约用了五天时间,在合肥“铁四局”旁的旅馆内完成了主旋律谱。同时,将“主题歌”写的两套方案在合肥录制小样,吴导当场不表态,带回家中,据说还是女儿选定终稿。“主题歌”先经时白林老师过目,落定后,一并带回安庆,用了十多天的时间,完成六集描写音乐及“主题歌”的配器。因为后期是纯音乐,还有着“民族化”“戏曲化”旋律“黄梅音调化”等要求,既要展示民族器乐特色,又要用好西洋管弦之色彩,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其中“主题歌”前,四分之四的八小节“序奏”,就整整写了一天。开始是合成器cor 音色弱起的[天宫]幻想音调,随之,弦乐低音空半拍切分而出的董永主题,配以铜管,天庭森严,增四度叠置的[八板]音调背景,紧接顶板冲出,代表七仙女形象之小提琴solo 的,抗争音型上升,又叹息地下降,迎来鸟语花香“对歌”音调的长笛顿奏,经古筝五声性上行民族琶音的连接,加以华丽的扬琴琶音衬托,引来长笛tr渐弱,导入秀丽的女声独唱,主题歌声迎面而至。同样《天仙配交响诗》的音乐,在这部电视剧的前后期音乐中,时有呈现,每集的片尾音乐就是用了交响诗的主部主题。为了音乐的完整性,六集电视剧的作曲、编曲、配器、以及打击乐设计由一人全面完成,应予提倡。
半个多世纪以来,陈礼旺先后为黄梅戏九十多个大、小剧目作曲、配器;为二十余部(集)黄梅戏电影、电视及风光片、艺术片、广播剧作曲、配器,并指挥;出版黄梅戏磁带、唱片、光盘六十多盒(张);以黄梅戏音乐为素材,创作各类音乐作品200 余件;论文数篇;获奖数十次。

陈礼旺指挥新组建的安庆市青少年交响乐团排练。2000 年

陈礼旺为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勃南德尔一行讲黄梅戏音乐。左起:陈礼旺、王寿之、勃南德尔、王兆乾及德国女学者等。1988 年2 月26 日
陈礼旺是首部黄梅戏现代大戏影片《红霞万朵》的主要作曲,及主唱声腔编曲之一;黄梅戏音乐广播剧《春风暖融融》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优秀节目奖;六集黄梅戏电视连续剧《七仙女与董永》获全国大众电视金鹰奖;三集黄梅戏电视片《虎情》公安部门获奖;黄梅戏动画片《西厢记》在第五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获得“美猴奖”中国动画短片提名(共有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1552 件作品参赛,17 部作品获得提名);《思情记》在中国湖南第二届“映山红”民间戏剧节获奖;新版《天仙配》(配器、音乐整理)获“1992中国(安庆)第一届黄梅戏艺术节”配器一等奖;《霞飞满天》参加全国公安系统调演获奖;《爱在晨曦》参加全国“残联”文艺调演获奖;黄梅小戏音乐剧《姑苏台》获中国戏剧奖·小戏小品奖;黄梅戏音乐双人舞剧《蓝桥会》参加市文博会获奖;黄梅歌女声独唱《春满人间》参加省青年歌手大赛获奖;黄梅歌童声独唱《看姥姥》参加全省“小百灵”赛歌会获奖,报送北京六首之一(全省67 首参赛);《升起理想的征帆》选定为安徽黄梅戏学校校歌(全社会征稿、中标)报送教育部出版;中信银行约稿的黄梅歌舞《中信春风》参加省赛获奖;《黄梅新韵》(二胡与五件民乐)曾参加“2003 国际中国民乐TMS 室内乐作品比赛”,在安徽省第七届艺术节“民乐创作比赛”中获奖;民族管弦乐曲《黄梅欢歌》参加(2001 年)全国“第一届少儿民族乐队(中州杯)北京邀请赛”获“月光奖”;民族管弦乐《黄梅飘香》《茉莉花开》参加(2007 年)全国“第四届青少年民乐团队北京邀请赛”获“月光奖”“组织奖”;管弦乐作品《天仙配交响诗》1981年参加了首届安徽省交响音乐作品试奏等等。
黄梅戏音乐创作,除出版《龙江颂》全剧乐谱外,历年来在各类书刊登载黄梅戏唱段百首以上(重复登载不计);担任《安徽黄梅戏音乐汇编》(一、二、三集)和《黄梅戏唱腔集萃》(上、下卷)副主编,其中“集萃”(上、下卷)获2014 年江苏省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项目出版的三个奖项;担任“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化项目《中国黄梅戏优秀唱腔全集》(综合、舞台、影视三册)副主编(注:《汇编》《集萃》《全集》均是徐高生先生担任主编)。《安徽文化周报》(1988 年5 月8 日),及省电台多次对个人做过专题报道;1983 年参加了全国四十多个黄梅戏剧团在安庆召开的“黄梅戏音乐学术研讨会”,做了一小时四十分钟的专题发言;1988 年初,多次与德国“东方艺术研究所”所长勃南德尔教授一行四人进行学术交流,其讲学综述之一、之二分别在《黄梅戏艺术》2015 年第二、三期发表;学术论文《黄梅戏音乐纵横之联想》1996 年5 月26 日参加安徽省委宣传部、文联、文化厅在青阳召开的“黄梅戏音乐研讨会”上作了宣讲,并在2002 年9 月获“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人文科学研究所”举办的“全国新时期人文科学研究成果”征文评选一等奖,后发表于《黄梅戏艺术》2014 年第四期。
个人专著《陈礼旺黄梅戏唱腔精选》《黄梅戏器乐演奏教材》(上、中、下卷)即将面世,《黄梅戏音乐论文集》《bàn 世纪黄梅“戏歌”五十篇》已在撰写,《黄梅戏“总谱”汇编》等正在筹划中。
陈礼旺经过了安庆市艺术学校音乐科近五年的科班式严格训练,得到了黄梅戏著名老艺人丁永泉、潘泽海、陈华轩、邹胜奎、丁翠霞、严松柏、田德胜、刘正庭等老师的唱腔真传,能较系统地掌握黄梅戏的声腔传统,并用于实践。
在黄梅戏音乐作曲方面,先期受教于安庆本土黄梅戏作曲前辈郑雪、方集富老师,后期受到时白林、王兆乾、王文治、方绍墀等上辈老师黄梅戏音乐作品的影响;曾求教过全国知名作曲家商易(舞剧《小刀会》、歌剧《夺印》等作曲)、胡士平(歌剧《红珊瑚》等作曲)、邱刚强(儿童歌曲作曲家)、韩永昌(电影《风雪大别山》等作曲,安徽电影制片厂书记)等老师。六十年来,在他们的指导下,努力学习民族传统音乐及西洋音乐理论,开阔视野,博采众长,在作曲过程中,尽力运用“立体化”的思维模式,努力用全面的专业技术掌控音乐全局(风格浓郁、旋律优美的黄梅戏声腔编曲;准确表达剧情特定形象的“描写音乐”作曲,以及良好的配器效果,指挥、排练的二度创作等),以求作品相对个性化的完整、统一,且具有一定水准的艺术性。最忌“碎片化”支离破碎的松散结构和无规律的音调组合。“土而不俗”是陈先生多年来在艺术风格上的总体追求,在理论指导下的各种探索总在途中,感悟颇深!
黄梅戏音乐的可塑性很大,陈先生曾多方位地向其它领域进行了尝试:黄梅歌、黄梅歌舞、黄梅调小歌剧、舞剧、黄梅小戏·音乐剧、民族器乐独奏曲、民族管弦乐曲、电视音乐,直至交响乐的尝试等(有的在全国及省内艺术活动中得奖),目的是反过来促进黄梅戏音乐的发展,为黄梅戏做多方面的展示和宣传,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历年来,总计创作黄梅戏戏剧音乐及各类音乐作品近300 件,写作总谱两万页以上。个人传略载入《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当代创业英才》《中国音乐家名录》《安徽省高级专家人名词典》等。
陈礼旺先生早期毕业于安庆市艺术学校,后于上海音乐学院结业。历任安庆市黄梅戏剧院艺术处副处长;《安徽黄梅戏音乐汇编》副主编;并先后受聘任教于安徽教育学院、安庆师范大学。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全国文艺人才研究会会员、中国戏曲音乐学会会员、安徽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曲家协会理事、安徽省民族管弦乐学会理事、安徽省戏曲音乐协会会员、安庆市音协理事、安庆市黄梅戏音乐学会秘书长等等。
陈礼旺先生低调做人、不喜张扬、办事严谨,他将他所有的作品列成条目索引以备后人查找,索引二十多页纸、密密麻麻,摘抄得手酸。在他的书房里,一大排书架上方,整齐地摆着他创作的作品,仅是戏曲音乐磁带、光盘,足有几丈长……作品之多,令人惊叹。他的黄梅戏作品大多由黄梅戏名家演唱:韩再芬、吴琼、马兰、吴亚玲、陈小芳、刘广慧、董文霞、胡静、王富珍、郭幼华、王凤枝、李萍、孙娟、姚美美、董荣玲、方宝玲、满玲玲、郭霄珍、汪静、刘红、张萍、江霞、鲍晓霞、王琴、汪菱花、许桂枝;陈兆舜、刘国平、阚根华、周旭春、程兆林、刘义超、马自俊、潘启才、左胜利、汪金才、王胜利、董家林、杨长江、陈小成、俞士伟、黄厚生等。从17 岁到70 多岁,他一天不歇地创作,可谓硕果累累。
由于年轻时高强度脑力劳动,透支了身体,陈礼旺在2011 年11 月不幸“中风”,造成行动不便。都是妻子宁桂英无怨无悔地服侍,耐心护理,才使得他的病情得到缓解。养病期间,他仍奋力拼搏着,在单位的支持下,他撰写、整理了个人专著、理论文章百多万字以上,还在持续。
下面摘抄其写于2017 年11 月5 日的短文一篇:
有关《黄梅戏文化生态保护》中“音乐元素”的重点强调
1、黄梅戏音乐发展需要各个历史时期的“沉淀”,在戏曲面临“滑坡”的当下,黄梅戏能广泛传播,也正得益于这些“沉淀”,因此黄梅戏音乐健康的文化生态更需保护、支持、引领;
2、保护“原生态”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努力用新的格调去予以展现,以适用于当今社会;
3、“新”、“老”传统均需保护,仅声腔而言,解放以来产生了很多优秀的“新传统唱腔”,要加大宣传力度,以利传播、推广;
4、发展黄梅戏的诸多要素中,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唯独音乐需要在坚守“风格”的前提下,再去发展、变异,它好比“配方”,弄得不好会比例失调,群众就不买你的“账”,分寸在于作曲者的“拿捏”。
具体操作起来,既要作(编)曲者笔下有情(黄梅情结),还要笔下留情(能让大众乐于接受)..在发展、传承中,对作曲人员的接班,可建立“一对一”有效的传承机制,形成梯队,要抢时间!
陈礼旺
2017.11.5
陈礼旺先生在养病期间仍如此关心黄梅戏音乐的走向,令我们无限感动,更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