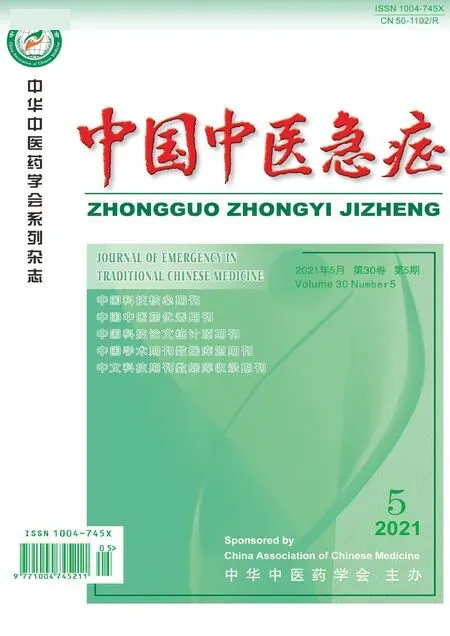麻疹源流考∗
2021-03-28姜德友韩洁茹
姜德友 俞 婧 韩洁茹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麻疹是感受麻毒时邪引起的急性出疹性时行疾病,以发热、咳嗽、流涕、目赤胞肿、眼泪汪汪、口腔黏膜出现麻疹黏膜斑、周身布发红色斑丘疹为主要临床特征[1]。中医对本病认识较早,春秋战国时期已有麻疹初期证候之记载。延至宋元,随着对麻疹诊治经验的不断积累,医家对本病的认识亦不断深入。明代以后,诸医家在前人基础上对本病不断完善,病机认识日臻全面,诊疗方法日趋多样。本病古时死亡率高,曾被列为儿科“四大要证”之一。近年来,随着麻疹减毒活疫苗预防接种的广泛推行,麻疹发病率逐年下降,流行程度减弱,但散发病例时有所见。中医治疗本病有数千年之经验,故现从病名、病因病机、治疗及禁忌入手,对历代重要医籍中麻疹的相关论述进行整理,考其源流,颇有意义。
1 病 名
“麻疹”作为独立病名首见于明代龚信《古今医鉴》。纵观历代医家所述,明代以前,诸医家虽未正式提出“麻疹”之名,但对麻疹之初期证候已有所认识。如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及王焘《外台秘要》等书中,所载“发斑”“瘾疹”“赤疹”“丹疹”之部分病证表现与麻疹皆有相似之处,但尚未将麻疹作为独立疾病分出。延至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对多种发疹性疾病予以详细叙述,然亦未进行系统鉴别,皆统称为“疮疹”。明代徐春甫于《古今医统大全》一书引晋代医僧支法存之言,载“支氏曰:疹证之发,多在天行疠气传染之时……或咳嗽喷嚏,鼻流清涕,眼胞浮肿,面肿腮赤,或觉泪汪汪,或恶心呕哕,即是疹候”[2],不仅指出疹证具有传染性,且其所述“咳嗽喷嚏”“觉泪汪汪”等疹候之状与麻疹初期证候十分相似。明代龚信《古今医鉴》将麻疹作为独立疾病分列而出,并对麻疹之诊断治疗加以记述,为后世麻疹之诊疗做出较大贡献。由此观之,古代文献中关于麻疹的记载蔚为大观,历代医家对麻疹命名所述不一,现将其命名方式归纳如下。
1.1 以病证特点分类命名 宋代庞安时《伤寒总病论》虽未提出麻疹之名,但对本病已有所认识,其载“天行豌豆疮……此病有两种,一则发斑,俗谓之麻子,其毒稍轻;二则豌豆,其毒最重”[3]。庞氏提出“麻子”一名,并将其与天花加以区分,即毒轻谓之麻子,毒重谓之豌豆(即天花)。元代曾世荣《活幼新书》亦有相似表述,言“轻者如麻,俗言麻子;重者如豆,谓之豆疮”[4]。后世医家亦有宗其说者。后至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进一步指出“麻疹”之麻,乃根据其病证特点“遍身细碎,无有空处”而命名。同时期,程云鹏于《慈幼新书》提出麻疹之别名“糠疮”,其言“麻疹发自六腑,亦曰糠疮,较痘疮似浅,有形无浆,易出易收,多实热者,然條忽变化,其症急速”[5]。宗南朝梁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中“糠乃谷皮也”之述,麻疹有形无浆,形似谷皮,由此观之,“糠疮”亦是根据麻疹之皮疹特点命名。至清代,陈复正《幼幼集成》沿袭北宋庞安时“麻疹俗呼麻子”之说,载道“麻疹俗呼麻子,盖因火毒熏蒸,朱砂红点遍身形,发自胃经一定”。此外,郑玉坛《彤园医书》引用明代聂尚恒《痘疹活幼心法》之记载,生动形象地指出“麻形如麻,痘形如豆”。清末医家陈伯坛《麻痘蠡言》亦指出“如麻絮之纷披,谓之麻”[6]。如此而言,麻疹命名实乃“象其形而名之也”。
1.2 以地域分类命名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且拥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故麻疹的命名,按照不同地域之习惯,亦四方各异。明代王肯堂《幼科证治准绳》即有“麻疹浮小而有头粒,随出即收,不结脓疱,北人谓之糠疮,南人谓之麸疮,吴人谓之痧,越人谓之瘄,古所谓麻,闻人氏所谓肤疹是也”之论述[7]。延至清代,沈金鳌《幼科释谜》亦载“方书名麻疹者,北人单谓之疹,吴人谓之痧子,浙人谓之疳子,名各不同,其实则一也”[8]。本病虽四方之名有别,其实皆一麻也。清代托滑寿《麻疹全书》所载之俗称更为丰富,言“麻证之名,各方不同,在京师呼为瘟证,河南呼为粰疮,山西、陕西呼为糠疮,山东、福建、两广、云贵、四川俱呼为疹子,江南呼为痧疹,浙江呼为瘄子,湖广、江西俱呼为麻证,又呼为艄子,闻人氏呼肤证”。综上所述,麻疹之称谓因地域不同、习惯不同有所差异,但其实质皆为麻疹也,需细辨之。
2 病因病机
麻为阳毒,属温热时邪,邪经口鼻侵入,小儿肺脏未充,主气功能未健,故易被侵袭。邪过肺卫,首先引起肺气失宣,随着疾病发展,麻毒入里,侵入脏腑,蕴于肺胃,气分热盛。且麻为阳邪,易伤津液,故麻后收没期常有肺胃阴伤之表现。现溯本求源,对历代麻疹相关医籍进行整理,将麻疹病因病机整理概括为4类:胎元伏毒,天行时邪;外感寒热,食滞痰积;阳明火毒,肺胃郁热;麻疹收没,阴血耗伤。
2.1 胎元伏毒,天行时邪 纵观古籍文献,整理本病病因之历史发展脉络,可发现在麻疹尚未以独立疾病出现之时,其包含于疮疹等出疹类疾病之中,诸医家对此类疾病多持胎元伏毒之病因学说。此后,随着麻疹以独立疾病分列而出,诸多医家对麻疹论述不断深入,逐渐认识到时行邪气致病的重要性,并形成胎毒时邪之说。北宋钱乙即持胎元伏毒之说,其于《小儿药证直诀》载道“小儿在胎十月,食五脏血秽,生下则其毒当出。故疮疹之状,皆五脏之液”[9]。此后,南宋陈文中《小儿痘疹方论》对本病病因载述更为详细,其指出小儿所患麻疹,乃因母亲孕时,饮食不知禁戒,“纵情厚味,好啖辛酸,或食毒物”,将毒邪引入胎元,传于小儿所致。延至明代,随着诸医家对本病研究的深入,对本病病因病机的认识亦日趋完善,逐渐形成天行时邪致病说。如明代鲁伯嗣《婴童百问》言“凡小儿斑疮之候,乃天行时气”。王肯堂《幼科证治准绳》载麻疹“虽曰胎毒,未有不由天行者”,明确指出麻疹既因胎毒,又因天行时邪而发。清代谢玉琼《麻科活人全书》亦宗前说,认为“麻虽胎毒,多带时行”。吴谦等撰《医宗金鉴》进一步指出麻疹发病为胎元之毒,先伏六腑,后感天地火旺之邪而诱发,其指出“惟麻疹则为正疹,亦胎元之毒,伏于六腑,感天地邪阳火旺之气,自肺、脾而出”[10]。蔡贻绩《医学指要》亦承《医宗金鉴》所言,认为“麻疹乃胎元之毒伏于六府”,后“感天地阳邪火旺之气”而发。如此观之,胎毒时邪病因学说乃于明清时期逐渐完善。
2.2 外感寒热,食滞痰积 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且小儿肺、脾常不足,故易食滞痰积。若小儿在内素患食积痰滞,在外又受风寒风热之邪,再感天行时气,则易发为麻疹。如明代程云鹏《慈幼新书》所言“麻疹之发也,有风热风痰,颗粒浮于皮肤,随出随没,没则又出。”宗元代王珪《泰定养生主论》之记载“风痰者,因感风而发,或因风热闭郁而然也,此皆素抱痰疾者”,知麻疹可因小儿素有痰积,后感风热之邪引动而成。同时代,武之望《疹科类编》亦有言“麻疹,其间或兼风,或兼痰,或伤食……即随病用对症之药,要之不乱投汤剂,则儿无事也”,指出小儿麻疹兼风、兼痰及伤食之病机。至清代,吴谦等人撰《医宗金鉴》于论麻疹轻重时指出“若素有风寒食滞,表里交杂,一触邪阳火旺之气,内外合发,而正不能制邪,必大热无汗……则为重而难治者也”。小儿初生,脾禀未充,胃气未动,运化尚弱,且小儿处于不断生长发育之阶段,因而对脾胃运化输布水谷之需更迫,故脾常不足,较成人更易伤食。若小儿平素外感风寒,内伤饮食,后又感天行时邪则可发为麻疹之重症。郑玉坛《彤园医书》亦承《医宗金鉴》之言。由此可见,清代医家多认为小儿麻疹重症属于表里夹杂之证,在里,素有痰积、食滞;在表,外感天行时邪,内外合发而正不能制邪,则难治也。
2.3 阳明火毒,肺胃郁热 肺开窍于鼻而外合皮毛,脾开窍于口而外合肌腠,脾胃互为表里。小儿初生,精血未充,体属纯阳,同感非时之气,亦从火化,毒火蕴郁肺胃,则麻患应生。明代武之望《疹科类编》中即有“麻疹,大抵主发肺经之热毒者”之论述,认为麻疹是肺经热毒所致。同时期,陈复正《幼幼集成》言“麻虽胎毒,多带时行。气候寒温非令,男女传染而成。其发也,与痘相似。不知毒起于胃……脏腑之伤,肺则尤甚”[11]。指出小儿麻疹病在肺胃。《麻疹全书》亦强调肺胃火毒之病机,其言“麻为火毒,出于肺胃。”可见明清诸多医家皆认为麻疹可见肺胃郁毒、郁热之证。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亦有部分医家提出小儿麻疹为手足太阴阳明经蕴热而致,如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曰“麻疹之证多属阳明火毒”。阳明者,乃多气多血之经,麻为阳邪,亦可见阳明火毒之病机。后至清代,陈耕道《疫痧草》言“痧,方书名麻疹……自古无专书也。至石顽《医通》始有麻疹一种,其书曰麻疹者,手足太阴阳明蕴热所致。迩来麻疹变化百出,其危有甚于痘者,书中诸论极详”,进一步提出手足太阴阳明蕴热之病机。
2.4 麻疹收没,阴血耗伤 麻为阳邪,易伤津液,故麻疹收没期常有阴血耗伤之象。明代武之望《疹科类编》载麻疹,应“调理补养病后之元气”,此乃终事也,指出麻疹容易耗伤正气,故麻疹病后调理时,宜补元气。清代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亦言“麻疹出六腑,先动阳分,而后归于阴经,故当发热,必火在荣分煎熬,以至血多虚耗”[12]。指出麻疹发病先动阳分,而后期则多耗伤血分。同时期,汪启贤等撰《济世全书》亦提到“盖麻疹属阳,血多虚耗,今滋补阴血,其热自除,所谓养阴退阳之义。”明确指出麻疹退后血多虚耗之机。
3 治 疗
麻疹之治,自古便有“麻不厌透”“麻喜清凉”之说,在麻疹治疗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钱乙主“寒凉”与陈文中主“温补”之学术观点的相互碰撞,不仅开启了儿科学术争鸣之先河[13],对后世医家治疗本病亦产生了深远影响。纵观历代医家对麻疹的治疗,多以“透、清、养”为基本治疗原则。现梳理古代医籍文献,将麻疹之治法概括如下。
3.1 辨证论治 1)透表解毒:麻疹治疗初期需以宣透为主,有“汗”方能透疹。但透疹需得法,不可过汗,因过用汗法,反耗阴液,正如明代马之琪《疹科纂要》载“麻疹得汗为妙,固不可无汗,亦不可过于汗”。同时代,张昶《小儿诸证补遗》记载麻疹初发表,可用升麻葛根汤治之,其言“小儿麻疹,以肺为主……病在于表,宜当汗之……麻证初然发表,升麻葛根汤,升麻、葛根、芍药、甘草。若见红了,再不可用葛根,恐致表虚,使其难靥不收”[14]。升麻葛根汤乃阳明发散药,麻疹初发表,宜其宣透之。至清代,吴谦等撰《医宗金鉴》言“凡麻疹出,贵透彻,宜先用表发,使毒尽达于肌表。若过用寒凉,冰伏毒热,则必不能出透,多致毒气内攻,喘闷而毙”。吴氏认为麻疹未出,治疗先用发表透邪之法,切不可过用寒凉,使毒邪闭郁难出。对于麻疹见形者,又提出治疗“贵乎透彻”,若出后细密红润,则为佳美,若有不透彻者,须察所因。吴氏亦宗升麻葛根汤治疗麻疹风寒闭塞者,且其又以所受邪毒及素体正虚情况之不同,提出“毒热壅滞者,必面赤身热,谵语烦渴,疹色赤紫滞黯”,宜用三黄石膏汤,清热解毒;“正气虚弱,不能送毒外出者,必面色白,身微热,精神倦怠,疹色白而不红”,应以人参败毒散托毒外出。《麻疹全书》对于麻疹之治法亦有“故用药之法,总不外透表宣毒”之总结。2)清解肺胃:麻疹治疗亦有“有大热者,当利小便;有小热者,宜解毒”之说,明代程云鹏《慈幼新书》云“麻疹之发也,有风热风痰……虽值严冬,亦不宜盖覆过暖,闭塞玄府,恐毒入咽喉,令人声哑。治宜清肺降痰,发表令透”,指出麻疹素有风热风痰者,治疗当清肺降痰为主。清代陈复正《幼幼集成》指出“麻疹因何咳嗽?盖由肺胃相连。肺金被火苦熬煎,以致咳嗽气喘。治法清金降火,不宜误用辛甜”,认为麻疹乃肺火所致,故治疗上提出清金降火之法。清代谢玉琼《麻科活人全书》进一步提出泻心火清肺金之治疗法则,其认为“麻属心火,必须解毒清凉”,且“麻之发,惟肺受毒最重”,故主张“当先以肺为主,总宜泻火清金”,又言泻火当用黄连、黄柏、栀子、大青叶、玄参、连翘之类;清金当用黄芩、知母、贝母、麦冬、石膏、天花粉、牛蒡子、地骨皮、桑白皮、杏仁之类。吴谦等撰《医宗金鉴》亦提出麻疹已经出透者,当用清利之品使内无余热,其云“至若已出透者,又当用清利之品,使内无余热,以免疹后诸证”。温病大家叶天士于《幼科要略》指出麻疹治疗“宜苦辛清热”,并且认为清热需分三焦用药,其言“须分三焦受邪……上焦药用辛凉,中焦药用苦辛寒,下焦药用酸寒”。《麻疹全书》亦主张“麻以清凉为主”,并且根据病程的不同阶段,治疗宜有所侧重,其曰“初潮疹宜宣发,已潮宜解毒,将收宜养阴,收后宜安胃”。值得一提的是,麻为阳邪,亦耗津液,故治疗时虽以清热为主,但当以不耗伤津液为宜。如明代张景岳《景岳全书》主张出疹时“治以清火滋阴为主”。清代周学海《脉义简摩》言“疹本出于肺,又发于皮肤肺之部也,热伤津液矣。故麻疹始终以清热养液为第一义”[15],提出麻疹治疗当以“清热养液”为要义。3)养血治疹:明代医家,程云鹏于《慈幼新书》指出麻疹“标属阴而本属阳”,易耗伤阴血,故麻疹初期及末期应注意滋养阴血。清代吴谦等撰《医宗金鉴》亦指出麻疹后期治疗应以养血为主,其曰“麻疹属阳热,甚则阴分受伤,血为所耗,故没后须以养血为主,可保万全。此首尾治疹之大法,至于临时权变,惟神而明之而已。”夏鼎《幼科铁镜》认为治疗麻疹虽然以托毒透发为宗旨,但属虚者宜益气养血佐以透发,强调麻疹“无烧不出”,宜用“天保采薇汤”清解表里。若泄泻内虚,不能送毒者,则“惟用八珍汤以托之”。若再不透者,则宜用“六君子汤循循调治自愈”。沈金鳌《幼科释迷》云“麻疹与痘疮,始似终殊,原同症异……然麻疹一症,先动阳分,而后归于阴经,故标属阴,而本属阳。其热也,气与血分相搏,故血多虚耗。其治也,先发散行气,而后滋养补血”,亦认为麻疹治疗当先发散行气,而后滋养补血。且沈氏又于《杂病源流犀烛》中提出麻疹后期须用“养阴退阳之剂”,宜四物汤加黄连、防风、连翘等,而禁用燥热升阳动气者,如人参、白术、半夏等。同时期,汪启贤等撰《济世全书》亦载“麻疹退后,若有牙根腐烂,鼻血横行,并为失血之症,急宜四物汤加山茵陈、木通、生犀角,以利小便”。此外,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脾常不足。又小儿生机蓬勃,发育迅速,脾胃负担重,故治疗小儿麻疹需时时注意顾护脾胃。清代沈金鳌《幼科释谜》即言“肺大肠表里,肠间之郁积清,肺经之毒自解,却不可犯胃气以绝生气”,强调小儿麻疹顾护脾胃之重要性。
3.2 其他疗法 1)外治法:本病外治法记载鲜少,诸医家多认可胡荽酒外用,或熏其衣被;或薄敷其身,可助麻疹透发。如清代吴谦等撰《医宗金鉴》即指出“疹出三日当收没,不疾不徐始无虞,收没太速毒攻内,当散不散虚热医,外用胡荽酒法宜……应证而施病渐离,外用胡荽酒熏其衣被,使疹透出”。2)单方治疗:值得一提的是,诸多医家亦有应用单方单药防治麻疹而取得良效者。清代青浦诸君子《寿世编》载“观音柳用枝叶四五钱,冬即枝梗,煎汤服立出,乃速痘、麻疹之神药也”[16]。观音柳即三春柳,又名西河柳,明代缪希壅《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就曾盛推其治疹之功。清代医家沈望桥于《经验麻科》一书中言“用丝瓜一个,风干,岁除日放在新瓦面上煅灰,摊地上,去火气,研末,以百沸汤冲服,每岁如此,服至三四次,小儿永不患麻疹矣”,指出丝瓜研末内服,可防治小儿麻疹。清代医家张德裕《本草正义》又指出牛蒡“最为麻疹之专药”。
4 麻疹禁忌
麻疹饮食起居及治疗禁忌,历代医家多有论述,明代程云鹏《慈幼新书》即言麻疹饮食禁忌“较痘疮更甚”,忌“一切酒肉鸡鱼之类,犯之早则发惊搐,变紫黑而死。百日内犯之,犹足生疮疖”。马之琪《疹科纂要》亦有“麻疹退后,须谨避风寒,慎戒水湿之载”。而聂尚恒《痘疹活幼心法》对麻疹饮食禁忌及治疗禁忌记载最为详备,其总结麻疹之忌有4,“忌荤腥生冷风寒”“忌骤用寒凉”“忌多用辛热”和“忌用补涩”[17],后世医家多宗其说。
综上所述,现今虽麻疹发病率已显著下降,流行趋势已基本控制,但仍见散发病例,且麻疹之流行规律及临床特征亦有所变化,中医治疗本病积累了丰富经验,且疗效显著,因此考察麻疹之源流对指导临床十分必要,遂考镜源流,整理如上,以期为临床研究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