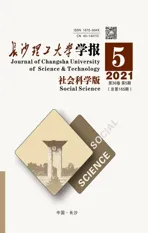我与学报的些许往事
2021-03-25成松柳
成松柳
接到《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陈浩凯主编的电话,学报即将迎来35周年庆典,嘱我写点文字。仔细想想,学报于我,确实有不少的姻缘,于是欣然应允。浩凯主编又嘱我,从学报发展的高度,写一篇理论性的文章。这我就难以从命。因为自己理论功底很浅,对于期刊建设与发展更无研究,怎么可能做高头讲章。因而只能以回忆的形式,过一过学报在我人生中的难忘印记。
一、论文情缘
与学报的交往,自然首推发表论文,虽然没有详细统计过,但三十余年来,在学报至少发了20余篇论文,这段情缘,不可谓不深也。我的学术论文写作训练过程,很有点意思。攻读研究生时的两位指导教师,石声淮先生是极力反对研究生阶段就写论文的,认为这个阶段主要就是将书读好,论文写作,是四十岁以后的事情。记得有一次,我自觉读书有点体会,向石先生报告,准备写成论文。石先生看着我说:“成松柳,你才读几句书,就想写文章。先好好读书,不要想论文的事情。”而丁成泉先生则主张我多写论文。他告诉我,很多读书的想法,一定要努力形成系统的文字,这样才会完善你的学术观点。两位导师的教导于我都是很有意义的。听石先生的教导,那几年确实读了几本书,而且都是元典,这对于我后来的教学与研究,都大有裨益。丁先生则在读书之余不断训练我的论文写作能力,因而使得我研究生阶段就以独立作者身份发表了好几篇论文,而且都是现在的所谓C刊与核心期刊。记得很多次碰到过同样一件事情,在偶然场合遇见了很早以前就熟悉但又很久没联系的相识,彼此恢复了记忆后,往往会说上一句,“你是成松柳,当年你出道很早的。”
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来到了长沙水电师范学院工作,很快也给学报投稿。没想到,学报马上就采用了。想想,学报1986年9月首刊,而我当年11月就给其投稿,真的是有缘份。这样,我很快就成为了学报的重要作者。每年,甚至更短时间,就会有文章在学报发表。因此,我自己的很多个“第一”都与学报密切相关,第一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复印转载的论文,第一篇被《新华文摘》论点摘编的论文,第一篇被《高校文科学报》摘登的论文,第一次获学校文科科研论文竞赛第一名的论文,第一次被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认可的选题,这些都出自学报。进入21世纪时,学界编了一些既往学术研究的总结性著作,我的一些入选论文,也有不少出自学报。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界曾经有个统计,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唐代文学研究论文高频次作者,我就忝列其中。我想这主要应该归功于学报对我的信任与栽培。因为当时的学术界,风气远好于现在。学界认可的是论文本身的质量,不在乎你的论文发表在什么刊物。遇到一些好的选题,写成论文,往往首选学报。因为面世快,学术成果能够较早得到学界的关注。
我当时写论文,初生牛犊,一味创新。后来读书多了一些,再看年轻时的那些论文,往往有悔其少作的感觉。觉得无论是文献的运用,还是观点的得出,都有太多可商榷的地方。如果让我重写,肯定会更成熟些。但其实,由青涩到成熟,学术的发展和人的成长都是这么过来的。青涩也有青涩的优势,不畏权威,敢于发声。由此,我想到当时的学术环境,真的是好。我们这些小年轻的论文,只要你质量过得去,什么杂志都可以发。看看现在,自己也带了不少学生,学生有时候也写了不错的论文,单独投出去总是碰壁。稍微像样点的刊物,非得加上导师的名字,而且必须成为第一作者才能见刊。虽然,学生的每篇论文,我都予以了修改,但即使这样,学生也是主要的劳动者,为什么非要挂导师名字呢?我的第一篇论文《试论杜甫的纪游诗》,发表在1984年的《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论文经过导师的反复修改,发表时我添上了导师的名字,他二话没说就删了。此后,我在《草堂》《古典文学知识》等刊物上发表的论文,都经过导师的修改,但他们始终没有成为论文作者。
我与学报由论文而结识,继而与学报的很多老师都成为了朋友,也得到了历任主编的赏识。在我的印象中,学报的编辑和工作人员,一直秉承学术良知,肩负学术责任,努力办好学报。同时,也让一批又一批像我一样的青年教师,走上了学术的道路。回想往事,真的应该感谢他们。
二、工作交结
除了与学报在发表论文上有着许多回忆,我与学报在工作上也有一些交结。
第一次大的交结,是推选学报主编。1993年,学报主编到龄退出主编岗位,学校召开了一个会议,民主推选学报主编。在座的都是校领导与部门负责人,我是唯一的教师代表。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让我做教师代表。当时猜想,可能是因为我已经在学报发表了近十篇论文,且有反响的也有好些篇的缘故。会场上,最后进入视野的两位候选人都很优秀,领导们意见也不一致。这时,主持人将目光投向了我,我只能发言了。我发言力挺其中一位候选人,也是当时学报的编辑廖小平。记得,我说了三点:其一是当时学报已经办得不错,在全国学界的影响很好,由学报内部遴选主编,有助于保持学报办刊路线的连续性;其二是廖小平是一位年轻的“老编辑”,很有经验;其三是廖小平相对更年轻,更富有活力。最后,廖小平继任学报主编。他上任后,果然不负众望,让学报更上一层楼。当然,廖小平能够继任学报主编,自然不是我的功劳。我当时一介“青椒”,人微言轻,言是发了,但起不了什么作用,这一点,我一直是心知肚明的。今天写出来,不过是与学报套套近乎。
第二次大的交结,则是1995年下半年。也不知怎么回事,我当时担任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也评上了,准备好好写几篇文章。但突然接到通知,学校党委决定任命我担任科技处副处长,分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工作,我想也没想就拒绝了。但耐不住领导,还有不少相熟的老师接二连三地劝告,就走马上任了。上任后才知道,我还有一个职责,就是分管学报社科版。为此,我还去当时的湘潭工学院、株洲工学院、衡阳工学院进行了调研,发现要想学报发展得好,办得有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科技处不要干预,让学报独立运作。于是,在我的数年任期内,除了作为编委参加学报的编委工作例会,我从来不对学报的工作发表意见。从职责角度,这可以说是不负责任。但事实上,学报坚持独立运作,越办越好,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当时的《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以至于后来的《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在全国学术界、学报界是有相当影响力的。我们出去参加学术会议,一报学校名字,很多学者都会夸奖我们学报办得不错。这一点,对我个人的影响也很大,充分意识到管理中分权的重要性。后来,我在担任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时,就始终坚持分权原则,让副手在主管的工作中有职有权地大胆工作。出了问题,我担责;有了成绩,记在他们头上。这样,班子和谐,工作也容易取得成就。
第三次大的交结,则时间跨度长达十几年,历经了三任主编,这就是担任学报编委会委员。期刊的编委是个虚衔,基本上只参加每年一度的编委会,提提建议,但我还是有些不同。一者,因为科技处分管学报;二者,与主编的私交不错。因而,经常被邀请参加一些与学报建设和发展有关的活动,比较了解学报的发展状态。所以,有时也提一些关于学报发展的建议。例如品牌栏目的设立,学报如何进一步扩大影响等。甚至,为了学报更上一个层级,也联系过相关领域的一些专家。虽然没有起到关键的作用,但也总算是我始终关心学报的建设发展。
三、未来期许
虽然拟了这么一个题目,回忆了我与学报的点滴往事,但浩凯主编的嘱咐,显然也不能违背,于是,对于学报的发展也提点个人想法,算是一个老朋友对学报的未来期许。
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殷切期望,引发了学报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讨论。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及我校学报三十五年的发展历程,我对学报的未来发展有如下建议:
一要进一步精准定位。学报三十五年的发展,在历届主编和学报同仁的努力下,一直有很好的定位。但目前世界格局、中国的发展局面和全球高等教育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所以,学报在下一步发展中进一步精准定位也就很有必要了。个人觉得,学报的定位要在三个维度中思考:一是在世界格局中的中国道路和中国发展中思考;二是在新湖南发展建设中,尤其是实施“三高四新”战略中思考;三是在新文科建设中结合我校的办学特色思考。从这三个维度出发,进一步优化学报栏目的设置。依靠栏目集结学术力量、组织学术团队,展开学术讨论,集中发表学术成果,进一步扩大学报和学校的学术影响力。比如,开设“洞庭湖研究”相关栏目就可以广泛联系经济学界、法学界、史学界、水利工程领域的相关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围绕相关主题,定期召开小型学术研讨会。从不同角度,逐步深入探讨洞庭湖治理的相关问题,让学校真正成为洞庭湖治理和研究的学术和决策重镇。其他栏目的设置也是如此。仔细思考,学校还是有很多可以进一步扩大视野、加快融合的学术增长点,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工程法”“数字艺术媒体”等,这些如果很好地借助学报的平台,借助不同形式的学术讨论,一定会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拓展学报和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力。
二要坚持学者办刊,保证期刊的学术质量。学报,归根究底,是学术杂志,学术品位是其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文史哲》杂志70年来一直享誉学术界,其中关键秘诀就是贯彻“学者办刊,造就学者”的办刊宗旨,始终坚持学者办刊,将刊物的学术质量放在第一位。我校学报三十五年的发展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这一特色应该进一步加以强化。当然,学报由于自身人力、财力所限,不可能有太多的专业学者作为全职编辑,但完全可以依靠学校的学科优势,集合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力量,实行“编辑-学者”一体化的办刊路径,使各相关学院的学者力量,参与到学报的编辑过程中。这样,既能保证全体编辑人员在编辑业务及学术研究方面都达到较高水平,也使学报编辑拥有各自的学术专长和研究方向。
三要不断发现和培养学术新苗,为学术和学校发展助力。《文史哲》杂志自创刊以来,不断重复一句话,就是“只认质量,不论出身”,以发现和培养学术新人为己任。因而,70年来,有许多学术名家,就是因为《文史哲》杂志的不拘一格而走上学术高峰,我校学报也应该有此胸怀和格局。建议设立学术新人栏目,支持优秀的青年教师、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发表自己的学术成果;就若干学术热点问题,组织专题讨论,鼓励年轻学者走向学术一线。当然,这样做,在某一阶段,可能会暂时影响学报的评价。但我相信,从长远来看,对学报及学校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更何况,在新的形势下,国家对于学术期刊的评价,肯定会有一个大的改变,那种仅仅以刊物级别,靠论文数量衡量学术水平的评价标准会从根本上得到修正。
“年去年来白发新,匆匆马上又逢春。”真真的时光荏苒,岁月不居。三十几年的时间一晃而过,许多镜头恍如昨日。自信我的回忆是真实的,我的期许也是真诚的。祝愿《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越办越好,成为长沙理工大学靓丽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