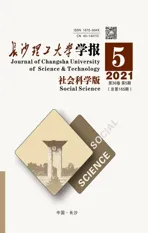《学报》琐记
2021-03-25廖小平
廖小平
不久前接到《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下简称《学报》,其前身为《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陈浩凯和编辑部邀请,说《学报》创刊35周年了,想请曾在《学报》先后担任编辑和主编的我写篇纪念文章。本来不想写这些东西,因为无非是一些平常的工作而已。但因我在《学报》编辑部先后工作了12个年头,是人生和职业生涯中一段不短的时间,同时也不好辜负编辑部同志们的好意,于是决定趁机回顾一下在《学报》编辑部工作时的点点滴滴。
1986年,我从湘潭大学研究生毕业,求职于正在筹备中的三峡省委(筹)宣传部,很快收到接收函,甚是高兴。又很快,收到中国社会科院的接收函,却很费解。原来三峡省委(筹)撤销,三峡省委(筹)宣传部将我的求职信转给了中国社会科院,于是中国社会科院主动给我寄来了接收函。但我没去成中国社会科院,主要是因为系主任和导师沧南教授软硬兼施地要求我留校任教,我不得不从。因三峡省委(筹)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院对我有无名英雄般的知遇之恩,我一直心存感恩。所以也借此机会在此掠记,当时世风、政风亦可见一斑。
1987年初,我认识了在长沙上大学的女友,于是调离湘潭大学的心又开始躁动,到处打探消息,争取调到长沙工作。1988年上半年,在一次看望寓居长沙的老师的聚会上,有位同学说《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其前身为《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要一名哲学编辑,于是我当天就去见了《学报》主编靳绍彤教授。聊了不到一个小时,靳绍彤主编就当场答应要我,并承诺接收我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友到学校财经系任教。
问题又来了。沧南教授仍不同意我调离湘潭大学哲学系。经死缠烂打,沧南教授终于松了口,但建议我调到中国社会科院去工作,我女友则通过考研去北京。但我没听“老人言”。当时我们还可以去深圳,也因少小懵懂厮守小日子而错过。湖南师大伦理学研究所唐凯麟教授,在我刚调进长沙水电师院不久,希望我再调到湖南师大任教,但我因长沙水电师院有更好的住房而作罢。我后来拜在唐凯麟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
经过以上“波折”,我终于在1988年7月来长沙水电师院报到。学报编辑部办公室在图书馆六楼西南角的一个大通间,学报社科版编辑部和自科版编辑部共用这间办公室。1988年国庆,我的婚礼也在这间办公室举行。没想到的是,我在这间办公室工作了近9年,并自此开始了从1988年至1999年长达12个年头《学报》编辑出版工作的生涯(含担任学工部长后兼任学报主编的时间),与《学报》编辑部同事及全国学报界的同行结下了深情厚谊,发生了很多美好的“编辑部的故事”。
我到《学报》编辑部上班的第一天,编辑部编务尹晓波同志就将一大摞稿件交给我审稿和编校。那时的编辑人员是审、编、校“一条龙”或“全链条”的。我从未受过编辑出版方面的培训,也没有师傅带一带,就连编校符号也只能基于平时的积累现学现用,学中用,用中学。由于有一定学术积累,爱思考以及做事比较认真和细心,包括跑印刷厂、指导排版工人拣疑难铅字等一应活儿都干,所以很快成为了编辑骨干。
《学报》创刊于1986年,第一任主编是靳绍彤,他从事美学研究。当时美学研究很热。靳绍彤主编的办刊风格不拘一格,好文章、美学栏目的文章一般都不受篇幅的限制;刊物印张也不固定,根据每期所发文章的多少而定。当时审稿没有“三审制”,一般就是按编辑所熟悉的学科领域分发稿件,编辑审稿并撰写审稿意见,在编辑部定稿会上提出是否采用的建议,通过大家讨论由主编决定是否采用。定稿会是非常认真和严谨的。由于靳绍彤主编善于交际,在学界和媒体界有一些朋友,所以一方面能组一些好稿件,另一方面逐渐扩大了《学报》的影响力。靳绍彤主编为形成《学报》的办刊特色和扩大社会影响奠定了基础,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约在1993年,靳绍彤主编在延聘几年后退休,中文系陈其相教授接任主编,基本上延续了靳绍彤主编的办刊风格和工作方式,推动了《学报》影响力的进一步上升。
1995年,陈其相主编退休,我接任主编。
担任主编后,我一方面继续坚持质量至上的用稿原则,另一方面又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一是在《学报》办刊定位上,定位于“纯学术”。现在学报都在办刊特色上做文章,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鼓励和支持。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很多学报也在办刊特色上想办法,比如一些地方高校的学报结合地域文化资源和特色,突出地域文化或人物的办刊定位和选题原则。而当时的《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在地域文化特色上无法与《湖南师范大学学报》《湖南大学学报》《湘潭大学学报》比肩;作为一所以电力为行业背景、一般工科院校主办的社科版学报,也无法在行业特色上做文章。于是,我们经过调研和思考,慎重决定,《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不应受地域和行业限制,不应只为追求行业和地域特色办刊,而应定位于“纯学术”,以“纯学术”立刊。这里所说的“纯学术”,是指在坚持正确办刊方向和办刊宗旨前提下,在选题范围上不拘一格,严格坚持学术标准以质取稿,通过不断提高《学报》的学术水平而提高办刊质量。
二是严格以质取稿。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并不从事教学和科研的领导、行政人员等也可以参评职称,或许需要“扮靓”自己,他们要求在学报发表文章,而这些文章大多数都是学术水平不高的,甚至是工作交流和经验总结之类的。我坚决顶住压力,不发表这样的文章。可以想见,一开始是很艰难的,但咬牙坚持下来,大家也就慢慢习惯了。当时《学报》还面临一种情况,就是如何处理校外作者与校内作者的关系。《学报》编委会、校内作者常为发表校外作者文章过多而指责和抱怨《学报》编辑部,并提出发表校外作者的文章不能超过30%的建议。这种限定必然影响办刊质量。虽然作为学校主办的《学报》毫无疑问要优先发表校内作者的文章,但当时校内作者不论是在投稿数量上,还是在研究水平上,都难以支撑起进一步提高《学报》质量的重担。于是,编辑部认为,还是应该不论内稿还是外稿,都一视同仁地坚持以质取稿。另外,任何刊物的编辑部都难以摆脱“关系稿”之困,对此,我们坚持的原则是尽量不发关系稿。编辑们在领导、朋友、熟人、同学的文章达不到发表水平被否决而无法解释和面对时,都可以把我作为挡箭牌,就说是主编不同意,所有得罪人的事我可以一人承担。为了做好榜样,有一次连我研究生导师的文章,我都亲自否决掉了,编辑们也就不好意思多用关系稿了。其实按我研究生导师文章的水平是完全可以发表的,我只是要率先做好“要求他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要求他人不做的首先自己不做”的垂范。
三是主动向名家约稿,而且基本都能约到。我现在还记得,在我的邀请下,邓晓芒教授每年都给《学报》写一篇文章。我也曾向张岱年先生约稿,张先生给我回了信,说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基本不写文章了,很是抱歉。虽然没约到稿,但张先生给我回信,我特别感动。这样的事,在我担任《学报》编辑,特别是主编时,是经常发生的。
四是坚持发稿费,坚决不收版面费。那时不少刊物开始收取版面费,但我坚持《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不仅不收取版面费,而且发放稿费。为了《学报》编辑部能够有些收入,我们每年办一两期增刊,可给编辑部人员发点劳务费,那时增刊的文章还可用于参评职称。另外,还可以卖一些旧报纸和过刊,得到的微薄收入,到年底可以给每位同事买一箱水果,当然也不忘给退休了的老同事送一箱去。
五是充分调动编辑人员的积极性,使大家有一种事业自觉和办好《学报》的荣誉感。我们《学报》的编辑人员素质非常高,都是“学编一体”,即编辑人员本身就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在当时国内学报界,像我们《学报》编辑部这样,编辑都有硕士学位和副教授以上职称(后来都当了教授),还是罕见的,老一辈如靳绍彤、陈其相、章惠康是这样,新生代如我、李传书、刘范弟、王新生都是这样。我担任学工部长后,学校仍然要我兼任《学报》主编,我提出配一位副主编,主持日常工作,并与副主编各负责一半栏目,实行竞赛,看谁负责的栏目质量最好、水平最高。这种机制效果很好。
在原有基础上,《学报》在编辑部同事共同奋斗、广大作者的关心支持下办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影响力,国内学界作者,不管老中青,纷纷给《学报》投稿,《学报》稿源充足。正因为《学报》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一方面高质量稿源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办刊质量培养了一批作者,校内作者如许第虎老师,因研究领域冷僻,很少有刊物接受他的文章,所以一生论文数量很少,在其即将退休之年,我大力支持他在《学报》连发两篇文章。受此激励,他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研究,论文很快就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因这篇论文,他年届花甲时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学报》还扶持了校内外大批青年学者,他们构成了《学报》的基本作者队伍,很多作者现在已是知名学者。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在《光明日报》等有关媒体每年公布国内刊物被其复印转载的排名,我主编的《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在高校学报中的排名一直比较靠前,《哲学》栏目甚至多年仅排在《哲学研究》之后,有些年份《哲学》栏目的文章转载率甚至还排在《哲学研究》之前,位居全国第一。那时国内还只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且影响也不大;CSSCI期刊的评价体系还未问世;更没有期刊影响因子一说;在学人心目中唯一或最重要的评价因素,就是转载量、学术声誉和学术界的认可。当时国内学术界都了解并认可的三大文摘刊物就是《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和《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已更名为《高校学术文摘》)。《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在这三大文摘刊物中都表现不俗。
1997年,学校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评估,专家组成员进校时说的一句话,对《学报》编辑部是一种鼓励和鞭策:“你们这个学校的文科《学报》办得不错!”2001年,我去上海大学开会,在报到时,一位与会者对我说,“你是长沙电力学院的?你们的文科《学报》办得好啊!”这位与会者知道廖小平是《学报》主编,但不知道本尊就站在这里。
还有一点特别要说一说。那时办刊人还基本上没有为了提高转载率或影响因子,而去找门子、拉关系的行为和习惯,也没有为了迎合刊物评价机构的偏好而确定办刊方向的做法,更没有目前特别流行的为了提高刊物影响因子而“自引”“互引”的做法。相反,逢年过节我还经常收到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相关分册的编辑寄来的明信片,而我们之间根本不认识。他们为什么要给素不相识的刊物主编寄贺卡呢?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对我等的鼓励和肯定,也许这是我自作多情吧!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时的社会风气和学界风气与现在大不一样。
“中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是国内一级学会中人数最多、办得最好的学会之一。湖南省在这个学会中的常务理事只有两人,一个是《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中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会长、在学报界很有影响的卜庆华,一个就是我。因《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在学报界的声誉和影响,以及因我是国内学报界最年轻的教授,所以在“中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成立青年委员会时,我还被推举为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
1999年,“中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一次开展“百强学报”评选活动,《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入列“百强学报”,且排名第26位,教育部发文通报。在强手如林的全国高校文科学报中,一所一般工科院校主办的《学报》能脱颖而出,殊为不易!在《学报》编辑部这一高校“不起眼”的岗位上,能得到这样的肯定和认可,是对我和同事们的最好回报、最大安慰和最高奖赏!我本人于1995年被湖南省委宣传部评为“湖南省十佳理论编辑”,1996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学报编辑”,并获田家炳基金奖。2005年,我调离长沙理工大学时,有人对我说:“你在长沙水电师院到长沙理工大学的18年间,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但最大贡献之一是把《学报》办得在全国有影响、有地位。”
1999年,我因担任教学部(教务处与学工部合并的机构)主任,行政事务太繁重,无法再顾及《学报》工作,于是辞去了《学报》主编职务。
我在十二年的办刊经历中,深切地感受到:要办好一份刊物很难,而要继续办好更难!
现在回想起《学报》编辑部的往事,特别是当时的同事们,感慨良多。
靳绍彤教授是把我调进《学报》编辑部的首任主编。他为办好《学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因办刊有功,他在学校是个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他在年满60周岁之后,又延聘了一年,在延聘期间,他得了一场差点夺命的怪病,因这病,他才发现自己几十年来少了一个肾,据他回忆,可能是小时候在老家唐山时被日本人割掉了。我在病房里陪护了他两晚,他长谈了自己的经历,感叹光怪陆离的人生,也谈了他对办刊的一些体会。他还说,出院后就退休,不再干了。但他出院后,又申请延聘了一年。这也许是对《学报》“有所不舍”吧。
陈其相教授是我的前任主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对我很好,很关心我。他是上海人,很精致。我送他两坨邵阳特产“猪血丸子”,一个月后我问他好吃不?他说还没吃,因为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我大笑:这是烟熏品,不管怎么洗,都会是黑的!
章惠康教授,在靳绍彤和陈其相担任主编时任副主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当时《学报》富有特色的“补白”,基本出自他手。他富有激情,对我也很好。他的孙子和我儿子是幼儿园同班。
靳绍彤和陈其相两位主编都已作古。他们去世时我不知道,不然我一定会去送他们一程。
李传书、刘范弟、王新生三位教授都是在我担任主编时与我并肩作战的战友,我们既是志同道合的同事,也是“称兄道弟”的朋友。李传书是我提议任副主编并与我开展质量竞赛的仁兄,已多年未见。最近,刘范弟在整理创刊历史资料,并频繁地向我核实一些情况,可见其严谨认真的态度。王新生后来也担任了主编,后又为文法学院院长,我们联系密切,常以“廖哥”“王哥”相呼。
1998年寒假,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我、李传书、刘范弟、王新生,还有当时身怀六甲的编务方志蓉,为了准备全国百强社科学报的申报材料,加班加点一个多星期,不仅没有一分钱的加班费,还得自掏腰包轮流做东,或买盒饭,或下馆子,虽然辛苦,但很快乐,最终收获了国家教委“百强社科学报”且位列第26名的好成绩!在一次学校的会议上,当听到校长爆出哪些处哪些系一年中吃喝了多少钱时,我心里感到对不起编辑部的同事们!2019年,当我在出差途中听到方志蓉因突发心脏病而逝世时,我忍不住留下了泪水,这泪水中就有深深的怀念和一份歉疚!
祝学报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