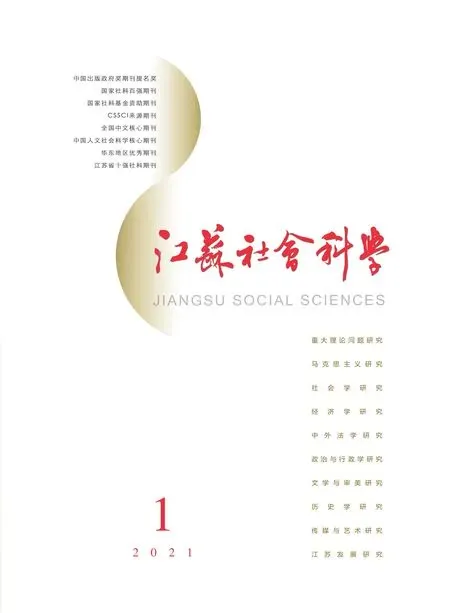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形成机理及其治理
2021-03-20
内容提要 人类社会已悄然迈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技术在给社会带来多方面积极变化的同时,其野蛮生长与广泛运用也给人们的隐私保护带来了一系列伦理困境。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的伦理困境表现为:数据挖掘与隐私信息的整合、数据预测与隐私信息的呈现、数据监控与隐私信息的透明、数据分享与隐私信息的扩散等。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生成机理,主要源于科学技术的负效应、财富创造的关联性、规约机制的滞后性、隐私观念的流变性等因素。治理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基本理路包括:重构科技伦理,促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完善制度伦理,促进法治他律与行业自律的统一;降低监控风险,促进知情同意与结果控制的统一;建构责任伦理,促进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近年来,伴随着数字化、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视频监控等技术的迅猛发展,数据类型、规模、速度与潜在价值等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几何级数增长,一个数据化的世界逐渐成形,人类社会已悄然迈入大数据时代。有学者研究发现,全球新产生的数据年增40%,信息总量每两年就可以翻番。2011年全球新产生和复制的数据量达到1.8ZB(1ZB=1 万亿GB),这大大超过了2011 年以前人类信息量的总和[1]邬贺铨:《大数据思维》,《科学与社会》2014年第1期。。大数据技术开启了人类社会治理的重大转型,就像望远镜让我们能够感受宇宙,显微镜让我们能够观测微生物一样,大数据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成为新发明和新服务的源泉,而更多的改变正蓄势待发[2]〔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大数据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很多积极变化,如提供生活便利、创造商业价值、重塑思维方式、增强预测精度、提升决策能力、解决复杂难题等。然而,大数据技术的野蛮生长与广泛运用也滋生了虚假数据泛滥、信息异化蔓延、数据鸿沟拉大等难题,尤其是人们在社交网络、智能生活、线上交易等方面留下的“痕迹”,被大数据技术过度化追踪与永久性记忆,使公众隐私信息在数据共享、挖掘、预测、监控等应用中持续性地被肆意泄露或滥用,个体逐渐丧失了自身信息的控制权,这些使公民隐私保护陷入了伦理困境。
隐私对于人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对隐私的理性认知是与人的自我意识的成长相适应的。在茹毛饮血的远古时期,人们本能地用树叶、兽皮遮挡身体私处。在聚族而居的农业文明时代,熟人社会的调节机制使彼此间既分享部分隐私信息,又使个人隐私不易受到大范围传播。在工业时代,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人的“脱域化”的加速,人们对私密空间、人格尊严、生活安宁等有着强烈的愿望,保护隐私开始从人的自我意识逐渐演化为人的自主行动。1890年,美国学者沃伦和布兰代斯第一次将隐私权界定为不受打扰或免于侵害的权利,这种独处的权利存在于私人和家庭的神圣领域[1]S.D.Warren,L.D.Brandeis,“The Right to Privacy”,Harvard Law Review,1890,4(5).。换言之,隐私是指个人不愿被他者干涉或侵入的私密领域,表现为个体不愿意或仅希望在有限范围内与他人分享的信息。这是传统意义上静态的、消极的隐私,体现信息主体的自决性。随着现代信息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当人类迈入大数据时代,世界范围内的数据呈裂变式增长,数据已经成为流动的商品,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容易被记录和监视,隐私信息越来越被透明化,人们的隐私权常常遭受侵害。此时,隐私的内涵已超越了个人不愿被他者干涉或侵入的私密领域,而拓展为收集、使用与控制数据的权益。传统的静态的身体隐私、空间隐私,逐渐转变为现代的、流动的信息隐私。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挖掘、预测、监控与分享等应用,使人的一切皆可数据化,公民对自身隐私信息或数据的掌控将更加困难。本研究基于大数据时代公民隐私难以保护的现实情境,描述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主要表征,在阐释其形成机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破解公民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基本理路。
一、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主要表征
1.数据挖掘与隐私信息的整合
在传统理论中,隐私是公民不愿为他人知晓的信息。伴随着隐私权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与被较普遍接受,关于公民隐私信息的保护在许多国家已形成了一套较有效的法律法规。传统道德准则、法律法规对隐私权的保护,主要基于个体信息自主控制的视角,针对的是公民通信、住宅、身体特征、生活癖好、不堪经历、财富状况等自然型隐私信息方面的保护。在大数据技术驱动下,公民隐私出现了新的类型——整合型隐私,即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将人们在网络上留存的数字化痕迹进行有规律整合而生成的隐私。与传统数据相比,大数据具有“4V”特征,即数据的规模(Volume)大、处理速度(Velocity)快、类型(Variety)多、价值(Value)高等。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数据规模、速度、类型与潜在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呈现裂变式增长,为数据挖掘、统计算法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奠定了信息基础。大数据技术涉及数据搜集、挖掘、分析、存储、传送等诸多环节,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遗传算法、神经网络方法、聚类分析等相关技术与方法的支撑。统计算法、数据挖掘等技术的广泛使用,使公民活动留下的原本杂乱无序、“原子化”存在、缺少信息关联、隐含用户隐私的碎片化数据,被大数据使用者二次乃至多次挖掘分析,重新排列组合,进而被采集、存储与循环再利用。这些隐含个人身份信息或隐私信息的数据模块表现为“整合型隐私”,整合型隐私更容易被泄露。“‘数据脚印’无处不在,小到个人的日常消费,大到健康、教育等重大决策,这些保存在不同系统中的‘数据脚印’,可能构不成伤害。但是一旦建立起集中的数据库,经过数据整合和信息加总,通过数据之间的印证和互相解释,就几乎能够把一个人的生活轨迹全部再现,从而导致个人隐私无处遁形。”[1]王秀哲:《信息社会个人隐私权的公法保护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29页。大数据是“一个沉默的存在”,当公民生产的数据被搜集者二次乃至多次挖掘、整合成隐私数据时,其既不知晓个人“数据脚印”是在何时、何地被何种组织或个人整合的,也不明白有关自身“生活轨迹”的数据是如何被泄露或滥用的。这种数据挖掘与隐私信息的整合,导致了包含隐私信息在内的公民数据控制权的丧失,使公民隐私保护陷入伦理困境。
2.数据预测与隐私信息的呈现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关注对自然的研究,冲破了宗教神学束缚,催生了近代科学,而科学研究的旨趣主要在于探求研究对象诸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大数据是一场新技术革命,正在重塑人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尤其使“科学从仅追求因果性走向了重视相关性,通过‘让数据发声’提出了‘科学始于数据’的知识生产新模式”[2]黄欣荣:《大数据对科学认识论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第9期。。在大数据时代,人们面对的是难以实时处理的海量数据,无法探求每个数据与其他数据之间确定的因果性,人们只能从宏观上寻找海量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换句话来说,“相关比因果更重要”[3]〔美〕冯启思:《数据统治世界》,曲玉彬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何谓相关关系?“相关关系的核心是量化两个数据值之间的数理关系。”[4]〔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在数据庞大、海量,整体数据取代有限样本的大数据时代,人们可以建立数据之间的全面相关关系,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旦我们完成了对大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而又不再满足于仅仅知道‘是什么’时,我们就会继续向更深层次研究因果关系,找出背后的‘为什么’”[5]〔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大数据时代“知道‘是什么’就够了,没必要知道‘为什么’。……相关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捕捉现在和预测未来”[6]〔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1—72页。。现实中,一些商业性机构为了实现更高效益的精准营销,便运用复杂的统计算法推导出杂乱无序、缺少联系的零星数据之间的潜在关联,而这常常会计算、预测出个人隐私信息。如保险公司根据所收集个人数据的相关关系,预测后者身体状况及其罹患重大疾病的可能性,从而决定是否为其进一步提供保险等。由此,在“整体”数据被不断二次乃至多次利用的情况下,基于大数据相关关系的挖掘与分析,包含公民大量隐私的信息就不断呈现出来。这些被预测的公民隐私关涉个体名誉,而名誉不受个体控制的情况显然与人的自主性原则背道而驰,并昭示着人的尊严未能受到应有的尊重。
3.数据监控与隐私信息的透明
20世纪70年代,受边沁“全景式监狱”思想启迪,福柯提出“全景敞视主义”理论,认为:“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公开场面的社会,而是一个监视社会。……我们……处于全景敞视机器中,受到其权力效应的干预。”[7]〔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43页。“全景敞视主义”理论表明了现代社会权力体系向整个社会的扩散,强调权力监督社会的功能。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波斯特发展了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理论,将网络社会喻为规模庞大的“超级全景监狱”:“今天的‘传播环路’以及它们产生的数据库,构成了一座‘超级全景监狱’,一套没有围墙、窗子、塔楼和狱卒的监督系统。”[8]〔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7页。由此,一种复杂的权力网络通过无处不在的视频,随时随地对公众展开系统化的隐秘监控。随着大数据浪潮扑面而来,社会治理者借助星罗棋布的监控视频,在治安、交通、商业、教育等方面实施数据监控,形成“超级全景监狱”。“社会治理者就如超级全景监狱的狱卒,网络信息系统则如监狱中的瞭望塔,公民如被监视的犯人。就公共视频监控而言,它也有监视不到的区域和时间段,但是监视惯习的养成往往令公民假定公共视频监控的存在,因而不得不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言行。”[1]顾理平、王飔濛:《社会治理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从超级全景监狱理论看公共视频监控》,《现代传播》2017年第6期。视频监控的实质是数据监控,视频监控收集到的海量数据被大数据使用者通过数据挖掘等技术,把看似杂乱无序、缺少信息关联的隐私数据析出,并将抓取的隐私数据还原为公民日常的生活场景与行为习惯。通过辨识公民的活动场域与行动轨迹,就可以很容易地获取其生活方式、生理特征、社会关系等非显性隐私数据。尽管“我们往往期待我们在公共场所里的日常活动,只是人群中的一张脸、蚂蚁窝里的一只蚂蚁”,换句话说,“我们在公共场合里的大部分活动,我们是相对匿名的。然而,辨识大大地改变这种平衡”[2]〔美〕丹尼尔·沙勒夫:《隐私不保的年代》,林铮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页。。在大数据时代的“超级全景监控”下,通过复杂的统计算法等技术,这种辨识可以轻松实现。由此,当代人已成为隐私无处安放的“透明人”,不论是否意识到,其隐私往往都被侵犯了。
4.数据分享与隐私信息的扩散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关注的隐私大多属于自然隐私,这些自然隐私相对单独存在,其泄露也较容易识别。当迈入“数据化生存”的大数据时代,人类生存发展除了依赖衣、食、住、行等基本品,健康、安全、教育等数据信息也成为重要资产。既然个体的几乎所有言论、行动都可以被数据化,则公共空间、私人空间的屏障就被打破了,边界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需要重塑。网络空间中的隐私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情况,即社会治理者的隐秘搜集、他者的有意传播以及个体的无意识分享。基于区域安全与社会治理的需要,社会治理者会隐秘搜集各种社会监控数据,如通过安装闭路电视系统对特定的公共场所的不特定公众进行监视[3]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页。。随着人的自主性的提升,公民隐私保护意识会逐渐增强。如果有人铤而走险,擅自、故意发布别人的隐私信息,将会引发违法风险。因此,他者有意传播的情形较为少见。关于第三种情况,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成熟与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热衷于把虚拟分享平台当作连接个体之间关系的社交平台。戈夫曼的戏剧理论认为,社交生活是一种表演,表演分为“前台”的自觉呈现与“后台”的不自觉流露。在网络分享平台这个“后台”,面对因虚拟而更加陌生的观众,表演者可以无意识地袒露内心深层次想法或者感受,如人们习惯于将文字、视频、照片等包含隐私的信息共享到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网络平台;在各种网络社交平台上,人们常常毫无节制地发表观点,甚至自我披露、分享包含隐私的数据。也许公民许多单次的数据分享并不足以导致隐私信息的扩散,然而数据挖掘技术会将留存在网络上的这些单次数据分享或披露的痕迹整合为公民的隐私信息。“失去隐私而赤裸裸的人类,正陷于感受不到直接痛苦的枷锁之中。这是数字信息产业不择手段取得的胜利,既不借助强迫,也不通过明显的暴力,但最终实现了对地球的控制。”[4]〔法〕马尔克·杜甘、克里斯托夫·拉贝:《赤裸裸的人》,杜燕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从某种意义上说,数据的分享、传播也是私人生活的公开化,个体无意察觉隐私信息的扩散,甚至难以感知隐私被侵害的苦痛。
二、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形成机理
1.科学技术的负效应
人类已经发生了五次科技革命:第一次是近代物理学诞生,第二次是蒸汽机和机械革命,第三次是电力和运输革命,第四次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第五次是电子和信息技术革命。每次科技革命,总会给人类历史进程与社会发展带来深刻、持久的影响。它们在“促进机器体系革命、产业革命和产品革命过程中实现了人类的财富梦,但也使人、社会和自然走向异化,人类的生存状态越来越背离健康、环保、安全”[1]苏玉娟:《从财富梦走向生态文明梦——给予人类六次科技革命的思考》,《理论探索》2014年第3期。。因此,在人类科技飞速发展、普遍应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副作用”,并不断地制造着社会风险。大数据技术的形成与发展亦是如此。随着数据规模、速度、类型与潜在价值等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几何级数增长,一个数据化的世界逐渐成形。“现在的数据量规模如此巨大,使用传统的技术和手段已无法处理和把握,所以大数据就是指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常规处理能力,必须借助新的科学技术和方法体系才能够予以处理的数据集合。”[2]黄欣荣:《大数据对科学认识论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第9期。作为一场技术革命,大数据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很多积极变化,如提供生活便利、创造商业价值、挖掘数据真相、重塑思维方式、增强预测精度、提升决策能力、解决复杂难题等。然而,大数据技术的野蛮生长与广泛运用也滋生了虚假数据泛滥、信息异化蔓延、数据鸿沟拉大等负效应。尤其是,人们的社交网络、智能生活、线上交易甚至情绪表达等这些原本看似与隐私不相关的数据痕迹,被大数据技术过度化追踪与永久性记忆,并通过复杂的统计算法、数据挖掘等技术,可以发现被忽略的有价值的联系并做出较精准的行动预测。其中,数据规模大,预示着在“数据化生存”环境下获得隐私越来越简单化;数据处理速度快,表明可以从海量数据中“打捞”出有价值的隐私信息;数据类型多,意味着在不同形式的数据中总会整合成隐私信息;数据价值高,诱导利益相关者为了高额利润而频繁使用隐私信息。这些原本属于个人隐私的信息数据,通过大数据技术被搜集、挖掘、预测、监控等,甚至被泄露或肆意滥用。科学技术的负效应是造成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技术性根源。
2.财富创造的关联性
大数据技术创新关联着财富创造,大数据技术的财富创造逻辑主要表现为:运用数据挖掘、分析等技术,预测海量数据的潜在价值;依据数学算法、技术模型等方法,解释财富前景实现的概率和风险;凭借娴熟的商业化操作,把潜在利益转变为现实财富与经济效益。在大数据产品设计与运行中,存在着许多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大数据搜集者、使用者以及生产者。其中,大数据搜集者,是基于数据利益,具有搜集、存储相关数据能力的组织或个人;大数据使用者或挖掘者,是针对大数据搜集者搜集的数据,挖掘其巨大价值并具有数据分析技术的组织或个人;大数据生产者,是在生产、生活与学习中,每时每刻、有意无意地生产着数据的组织或个人。在一切皆能数据化的大数据时代,组织或个人的海量数据成为数据世界的“新石油”、网络社会的“新货币”。在复杂的数据技术生态系统中,基于数据与财富创造的强关联性,大数据搜集者、使用者与生产者具有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往往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来开展行动。其中,大数据搜集者通常将人们生产的琐碎的数据搜集、存储并汇聚起来,以增强对市场的洞察力,抓住潜在的商机。这些海量数据被大数据使用者不断地挖掘、利用,以探测产品市场前景,并把它作为企业决策运营的关键变量。由于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优先级的差异,可能侵害到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尤其是一些组织、网站或黑客等大数据搜集者、使用者,在对待用户个人习惯、偏好、关系、社交、特质等数据时,毫无伦理责任与人文关怀,过于追逐财富创造与商业利润,常常使用复杂的统计算法技术追踪、监控、预测消费者活动,导致数据生产者的“整合型隐私”频频泄露。如谷歌常常通过搜集用户的网页浏览、购物记录,运用复杂的统计算法分析、推导出用户的购物趋势、消费倾向、休假意向等隐私信息,并向其精准投放广告,以影响其最终的消费决策行为。这样,网络用户数据在用户未授权或不知情情况下被谷歌二次乃至多次利用,进而侵犯了用户的隐私权,人们甚至难以知悉其生产的数据究竟以何目的被挖掘、利用,以及被如何挖掘、利用。由此,大数据技术与财富创造的强关联性是引发隐私问题的现实动因。
3.规约机制的滞后性
在“万物皆数”的大数据时代,公民在生产、生活、学习、娱乐中享受着大数据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其身份、通讯、社交、购物、旅游、就医等信息也通过大数据技术被持续地留痕、记录与储存,这就给公民隐私信息被肆意泄露或滥用等埋下了安全隐患。然而,原有的法律体系、道德规范无法适应大数据时代的现实需求。尤其是,隐私保护的立法规约滞后,并缺乏必要的行业自律机制与伦理底线,使现有网络隐私保护规则过于笼统、滞后与不合时宜。“不管是告知与许可、模糊化还是匿名化,这三大隐私保护策略都失效了。如今很多用户都觉得自己的隐私已经受到了威胁,当大数据变得更为普遍的时候,情况将更加不堪设想。”[1]〔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页。在面对层出不穷的大数据隐私伦理问题时,当前的规约机制缺乏现实的针对性,显得无能为力。特别是,“法律在本质上是反应性的,法律与法规很少能预见问题或可能的不平等,而是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作出反应,通常,反应的方法又是极为缓慢的”[2]〔美〕理查德·A.斯皮内洛:《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刘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难以破解大数据技术导致的公民隐私保护问题。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写道:“我觉得我们的法律就仿佛在甲板上吧嗒吧嗒挣扎的鱼一样。这些垂死挣扎的鱼拼命喘着气,因为数字世界是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大多数的法律都是为了原子的世界,而不是为比特的世界而制定的。……电脑空间的法律中,没有国家法律的容身之处。”[3]〔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页。另外,互联网企业相关职业道德准则的不完善,造成道德评价标准的模糊性,使得一些互联网企业在巨大商业利润的诱惑下,恣意泄露用户隐私数据,甚至通过地下产业链售卖公民隐私信息以获取非法利益等。总之,法律监管、行业自律等规约机制的滞后性,进一步放任了大数据技术异化与隐私保护的伦理困境。
4.隐私观念的流变性
如前文所述,隐私对于人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对隐私的理性认知是与人的自我意识的成长相适应的。从远古时代到农业文明时代再到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的隐私观念不断变化,其内容从躯体隐私扩展到物理空间隐私,再扩展到信息隐私等方面。1890年美国学者沃伦和布兰代斯首先将隐私权界定为不受打扰或免于侵害的独处的权利,并赋予其法律意义。由此,保护隐私开始从人的自我意识逐渐成为人的自主行动,“隐私”边界不断被重新定义与诠释。伴随着数字化、社交网络、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个数据化的世界逐渐形成。大数据技术的支撑、推动,正在重塑公民隐私的观念与边界。传统的静态的身体隐私、空间隐私,逐渐转变为现代的、流动的信息隐私:一方面,大数据技术驱动隐私边界跨越了空间界限,个人在不同的网络分享平台等虚拟空间中不自觉地表露真实自我,却被大数据搜集者挖掘、分析与去语境化地持续存储、传播;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驱动隐私边界突破了时间界限,隐私信息被持久地保存在网络数据中不被遗忘,大数据使用者既能够深度挖掘公民的过往信息,也可以精准预测公民的未来行动。“传统的隐私问题主要涉及私密的、敏感的、非公开的私人领域的个人信息,而新的隐私问题则主要涉及共享的、原本不敏感的、公共领域的个人信息。”[4]吕耀怀:《信息技术背景下公共领域的隐私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第1期。因此,网络资讯的透明化迫使大数据时代的公民隐私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开始从身体、物理空间隐私拓展到生活、网络空间隐私;隐私观念呈现出从静态、封闭转换为动态、开放的态势,并进入全球透明状态。隐私观念的流变性与数据分享认同,使相关组织、个人更容易搜集公众数据信息,也导致越来越复杂的隐私保护难题。
三、治理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基本理路
1.重构科技伦理,促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技术成就是人类理性发展的结果。作为认识客观事物本质与规律的思维形式,科技理性是在一定科学理论指导下,凭借一些物质技术手段,实际地支配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认知范式。科技理性通常包括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前者即以外界事物的情况和他人行动的期待为条件或者手段,希望实现自己合乎理性的目的;后者是不管能否取得成就都有意识地无条件地纯粹信仰一个特定的固有价值,比如行为伦理、美学、宗教或其他价值[1]王锟:《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当科技理性逐渐演变为现代社会无所不能的发展手段与发展目标时,其也就退化为单向度的工具理性了。大数据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是人们开展社会治理的基本工具。然而,其发展、运用中鲜明的问题导向与不断优化的内在需求,表现出了较强操作性的工具理性特质。当大数据技术从手段逐渐演变为目的时,就沦为物质生产快速发展的根本依赖性工具,从而“脱嵌”于本该制约它的价值理性,导致虚假数据泛滥、信息异化蔓延、信息鸿沟拉大、隐私保护困境等时代难题。由此,一个现代性悖论产生了:包括大数据技术在内的科技在给社会带来进步与便利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制造现实问题与伦理风险。这种令人不安的“人造风险”,主要是由大数据技术不受限制的推进与科技伦理的失衡造成的,而“科技伦理的表现形式是科技与人的相互作用这一内在本质的外化形式”[2]程现昆:《科技伦理研究论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因此,大数据技术的发展需要促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一方面,国家应当大力推进大数据安全保障技术的研发,通过互联网企业、科研院所合作攻关,推进产学研成果转化与应用,从科技层面提升大数据技术的运行安全。另一方面,在大数据的生产与收集、识别与加工、挖掘与分析等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确立人在科技发展中的全面价值,以提升人类幸福指数与美好生活质量为旨归。简言之,“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终根源;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成为所有发展的标准”[3]刘永富:《也谈哲学价值论研究的人学基础》,《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0期。。正如芒福德指出的,“人类要获得救赎,需要经历一场类似自发皈依宗教的历程:以有机生命世界观替代机械论世界观,将现在给予机器和电脑的最高地位赋予人”[4]Lewis Mumford,The Myth of the Machine:The Pentagon of Power,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0,p.413.。重构大数据科技伦理,正是基于平衡大数据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数据自由与技术向善的关系,进而维护人的自由与尊严。
2.完善制度伦理,促进法治他律与行业自律的统一
随着数据化世界的逐渐成形,人类社会已悄然迈入大数据时代。许多传统的信息安全、数据主权、资源开放、隐私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已沦为推进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的掣肘。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同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5]〔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一般来说,制度伦理包含两个理论维度,即“为制度本身的正当性、合法性提供伦理支援或道德辩护,……为社会公民实现个体权利和自由提供公正的制度安排、制度调整和制度保护”[1]李仁武:《制度伦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由此,破解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需要完善大数据制度伦理,促进法治他律与行业自律的统一。首先,要注重大数据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政府要推动资源整合,制定大数据发展战略及其体系,并由国家统筹规划,协调推进。2015年,《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2015〕50号)出台。基于这一行动纲要,我们尚需厘清产业发展目标、制定行业标准、健全市场发展机制、瞄准核心技术突破、培育新兴业态、涵养产业生态等,以顺应数据科技革命与数字产业变革浪潮的发展。其次,要启动相关大数据治理立法,从政策和法律层面调整社会资源配置、平衡利益冲突、保障数据安全与公民隐私权等。当前,亟须在确立共享价值准则与伦理底线的基础上,制订《大数据隐私保护法》及相关配套法规,明晰大数据拥有者、使用者与管理者等利益相关方的责、权、利,并完善行业伦理规范。尤其是,要建构惩罚性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制裁制度,以惩治非法采用数据或恶意泄露隐私的组织或个人,为隐私保护提供强大的法律保障和伦理辩护。最后,互联网运营企业及人员必须强化行业自律,大数据搜集者、大数据使用者必须坚持伦理准则与道德底线。当前的数据搜集者、使用者、生产者等群体,形成了一座数据“金字塔”的知识权力结构,即数据搜集者、使用者等数据挖掘专家位于塔顶,而广大数据生产者居于底部。在大数据技术应用中,互联网组织及人员掌握遗传算法、神经网络方法、聚类分析等技术,与财富创造的关联性最强,获利最多,作为数据生产者的普通用户成为“数据化生存”时代的“最少受惠者”。根据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要(按照差别原则)最大限度地增加那些最不利者的期望”[2]〔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因此,大数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要合乎正义,尤其是政府有责任帮助“最少受惠者”获得更多利益。
3.降低监控风险,促进知情同意与结果控制的统一
基于国家地区安全与社会治理的需要,世界许多国家地区开展“隐秘监视”活动存在一定合理性。现代社会能够通过作为“隐秘监视”的公共视频监控,帮助实现社会治理的目的[3]顾理平、王飔濛:《社会治理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从超级全景监狱理论看公共视频监控》,《现代传播》2017年第6期。,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生产、生活的安全、有序。然而在这种“隐秘监视”过程中,普通公众与政府机构、互联网服务商相较,在数据信息占有量、挖掘能力等方面是不对称的,存在着明显的“数据鸿沟”。如何调适公民隐私权与国家安全利益关系,成为当前各国面临的现实难题。我们认为,公共部门、互联网企业和服务商亟须降低监控风险,以更好地维护公民隐私利益不受侵犯。一方面,政府机构、互联网服务商的视频监控必须仅限于用作保护公共利益;并且,他们在公共场合收集、提取包括隐私数据在内的公民信息或者将公民信息用于其他目的时,必须遵守“知情同意”原则,即在提取用户数据时,应该使利害关系人充分知晓其数据的存储内容、使用情况以及潜在风险,并自主决定是否给出授权[4]安宝洋:《大数据时代的网络信息伦理治理研究》,《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5期。。当然,正如学者沙勒夫强调的,“我们往往不希望绝对的秘密。相反地,我们希望控制我们的信息如何被使用、透露给谁、如何传播。我们要限制信息的流动,而不是完全让它停止不动”[5]〔美〕丹尼尔·沙勒夫:《隐私不保的年代》,林铮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页。。另一方面,鉴于某些公共部门、互联网服务商在基于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需要而搜集、使用公民数据信息时可能会滥用职权,非法扩大信息收集与存储范围,使公民隐私权受到侵害,对政府机构、互联网服务商等必须加强“双重控制”原则,即“通过对视频监控安装位置、时间强度、范围以及资料的管理来解决。换言之,对公共视频监控的控制,主要是对视频监控过程进行控制,但同时还要兼顾对视频监控结果的控制”[1]刘清生、陈伟:《隐私权保护下公共视频监控的法律规制——从“双重控制论”到“结果控制论”》,《海峡法学》2015年第4期。。大数据时代公民隐私已无处安放,每个人都可能是“透明人”。也许“最重大的侵害还不是观察和摄像本身,而是对于观察到的信息的不当利用,如披露、公开和用于商业目的等”[2]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既然我们每个人的信息会被搜集、挖掘、储存、预测等,形成“整合型隐私”,则降低监控风险的关键在于促进知情同意与结果控制的统一。
4.建构责任伦理,促进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事物发展都具有两面性。任何技术系统的力量强大到一定限度,都可能会引起某种系统的反弹甚至出现一种自我毁灭的动向,进而导致科技生态系统的失衡,其主要肇因在于人们未能意识到或者根本不愿意承担技术系统整体运行中的相应责任[3]Hans Lenk,“Progress,Value and Responsibility”,PHIL&TECH,1997(2),pp.102-120.。诚然,大数据技术在给社会提供生活便利、创造商业价值、重塑思维方式、提升决策能力等方面带来积极变化的同时,其野蛮生长与广泛运用也使公民隐私保护陷入了伦理困境。追根溯源,隐私保护伦理困境主要源于参与大数据生命周期的利益相关者过于陶醉于技术变革带来的生活便捷、财富创造等,而忽视了技术系统整体运行中所需要的责任担当。破解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亟须平衡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伦理,促进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责任伦理是人们共同承担人类共生共存责任的伦理,是面向人类整体、面向未来的高科技时代的伦理[4]程东峰:《责任伦理导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在构建隐私保护责任伦理准则中,各个利益相关者都要体现权利、义务的对等与平衡。所有参与数据生命周期的行动者,既享有大数据技术发展带来的权益,又必须承担保护数据安全、公民隐私等的义务。首先,作为数据信息“金字塔”坚实基座的大数据生产者,既可以享有大数据技术带来的生活、工作便利与利益增进,又必须承担为大数据发展提供基础数据源的义务。另外,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一般都愿意牺牲一部分隐私以换取在便利或服务方面相对较小的改进”[5]〔英〕吉隆·奥哈拉、奈杰尔·沙德博尔特:《咖啡机中的间谍》,毕小青译,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94页。,因此,大数据生产者要避免以自身隐私信息泄露来交换便捷或优惠服务等。其次,作为数据生产周期重要中介的大数据搜集者,既可以享有在网络空间通过定位跟踪系统、数据共享应用程序等多种途径搜集用户数据信息以获得各种利益的权利,又必须积极履行不泄露和不滥用数据生产者隐私的义务。最后,作为数据生命周期利益链条顶端的大数据使用者,既可以使用数据挖掘、数据分析等复杂的统计算法从海量数据中推导出新关联、新知识以创造财富,又必须承担保护公民隐私、提升决策能力、推动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等方面的责任。在数据“金字塔”结构中建构责任伦理、促进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关键,在于把大数据的利益链条转化为责任链条,将“谁搜集使用谁担责”的伦理精神铸入大数据搜集者、使用者的具体行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