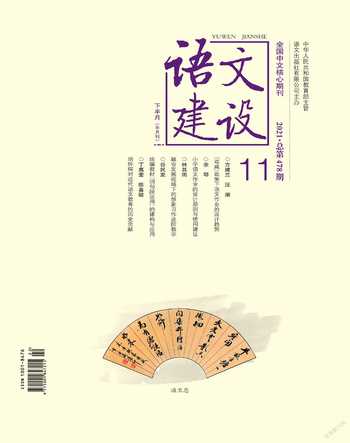《春夜喜雨》体物新变的叙事性解读
2021-03-17白松涛
白松涛
【摘要】杜甫的《春夜喜雨》被视为中国文学中具有抒情传统的经典文本,其实这首诗还隐藏着易被忽视的叙事性因素。六朝以来,咏物诗形成了“局于物”的体物困境。这首诗突破这一困境的主要路径是由“雨”写到“雨境”,即在调动时间因素、开展拟人化叙事的过程中,将“雨”塑造为历时性、行为性的“事象”。叙事性对于《春夜喜雨》的意义在于,从南朝咏物的俗套中“开拓出去”,使“雨”具备了物性与人性融合、形态与神韵兼备的艺术效果,并在整体上形成了畅快流动的文本意脉。
【关键词】咏物诗,叙事性,事象
《春夜喜雨》是杜甫咏物诗的名作,其风格浑融雅致,历来赞誉颇多。如清代集大成的杜诗注本《杜诗详注》评价此诗:“曰潜曰细,写得脉脉绵绵,于造化发生之机,最为密切。”[1]古典文学研究者关于《春夜喜雨》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意象的铺展、意境的营造、生命的情趣、儒者的关怀、律诗的体制、艺术手法尤其是炼字等方面,整体的思考框架和理论分析并没有超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而实际上,杜甫面对“雨”这一“特殊”物象时,已经不单单是从情景交融的传统路子来体物,而是调动了叙事性因素,展现出别具一格的体物方式,也由此形成了流动连贯的诗歌意脉。全诗录入如下: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一、不局于物:咏物诗的突破路径
局限于物象的写作使得六朝许多咏物诗都陷入了格调卑弱、意蕴单薄的局面。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曾指出这一写作倾向:“自近代以来,文貴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2]王夫之更是用十分犀利的比喻来指责这些诗的不足之处,他说:“咏物诗齐梁始多有之。其标格高下,犹画之有匠作,有士气。征故实,写色泽,广比譬,虽极镂绘之工,皆匠气也;又其卑者,短凑成篇;谜也,非诗也。”[3]统观来看,六朝咏物诗多专意于物象描摹,文本所呈现的内容仍是以物的外在特点及功用价值为主。后代的诗论家由此反思咏物诗创作的体式问题,如明代陆时雍说“夫咏物之难,非肖难也,惟不局局于物之难”[4],这便指向了咏物诗创作的新路:不局限于物象的外在形态,而是延伸开来写物的神韵和精神。六朝咏物诗的困境或许与交游宴集的创作环境息息相关,而唐代社会气象和文学风貌的转变一新也促使咏物诗创作呈现出新的局面。《春夜喜雨》作为杜甫的咏雨诗名作,意象玲珑、意气充沛,展现了杜甫“不局于物”的体物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咏雨”这一题材的特殊性:第一,雨本身难以描摹——物态模糊、没有色味;第二,写雨中其他景物时,容易偏离咏物的轨道,成为一首铺排写景的诗歌,这也是众多天象气候类的咏物诗面对的难题。宋人吕本中《童蒙诗训》说“义山《雨诗》:‘摵摵度瓜园,依依傍竹轩,此不待说雨,自然知是雨也。后来鲁直、无己诸人,多用此体,作咏物诗不待分明说尽,只仿佛形容,便见妙处”[5],这一写法便是由“雨”写至“雨境”,在整体意境中处处衬写中心物象。此类写法在杜甫咏物诗中颇为常见,如“河汉不改色,关山空自寒”和“关山随地阔,河汉近人流”两联,不明写月光,而是借着月下景色侧面写月;再如“秋日新沾影,寒江旧落声”不直接写雨,而是展现下雨带来的景象变化,句句又都是雨意;“暗度南楼月,寒深北渚云”一句不见“雪”字,却将雪的动态、神韵、寒冷表现得极富张力。这是杜甫独具创意的咏物写法,是“自开堂奥,尽削前规”的艺术创造。
同样,《春夜喜雨》一诗颈联“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从内在微妙的情思转移到外在的感官上来。上句写原野与天空,突出云深且黑、密布空中;下句推移到江河之上,写黑暗中的一点渔火,有模糊朦胧之感,既因为入夜渐深,也因为细雨迷蒙。诗到颈联,境界陡然开阔,将“雨境”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写“雨”字,却处处是“雨”。从“雨”写到“雨境”,突破了单一空间下的物象细描,展现出了丰厚的画面张力。这一突破路径的构建,正体现出诗人在内容连接和章法结构上对叙事性因素的调度和组织。
二、事象:历时性与拟人化叙事
在《春夜喜雨》的解读史中,“春雨”往往被作为意象看待。学界普遍认为,“意象”具有主客统一和情景交融的性质。例如袁行霈先生认为,“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6]。诗中的“春雨”不仅是客观的外在物象,还包含着“好雨”这一客体化的社会美德、“喜雨”这一主观化的热情赞美;在哲学精神层面,还包含着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意象。但仅依靠作为阐释工具的“意象说”还不足以赏出这首诗的妙处,因为意象解诗的理论根源是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这实际上忽视了“叙事性”解诗的可能。当然,这样的论断无意于说这是一首叙事作品,如果抛弃二元式的诗歌题材分类来看,抒情与叙事其实都是诗歌表情达意的方法性因素,这些因素“互相包容,互相渗透,难解难分”[7]。就《春夜喜雨》一诗而言,抒情性因素可以阐释“情、意、象”之间的关系,叙事性因素则可以阐释诗人的体物方式、观察视角和布局构思。
《春夜喜雨》的文本内在层面存在着动态的叙事痕迹,这涉及关键的叙事性因素——时间。全诗四联均有明确的“时间指向”:
首联突出两个时间点,一个是作为整体背景的时节“春”,另一个是雨“发生”之时。当然王嗣奭还认为“发生”是“万物发生之时也”[8],可作一解。但仍不可否认,作为叙事的开始,首联点示了“雨至”这一最初的时间点。颔联指出“入夜”,虽然旨在表现“雨”轻柔绵密的行为动作,但是雨势缠绵,显然有时间推移的暗示。颈联不写雨,也不明写时间,但是刻画了云层厚积、暗沉迷蒙的景象,此句所强调的“云黑”不仅仅是天气变化,更暗含着夜深雨久的时间流逝感。尾联虽然有想象的成分,但已经将时间推移到第二天早晨。三、四两联的叙事时间出现跳跃,但是以春雨不绝的行为填补了空白。由此可见,在“时间”这一重要的叙事性因素上,全诗展现了“入夜——夜深——春晓”的变化历程,勾勒出春雨从“发生”到“润物”,再到雨势变大、历宿方绝,最后雨湿花重的全部行为过程,用情景更替、视野变换来推动时间流转,形成连贯顺畅的气势。“春雨”作为中心物象,不再处于共时性的破裂片段之中,而是进入了历时性的动态变化过程里,“春雨”便由此具有了“事象”的意味,这是不能单用“意象”来阐释的。
除时间因素及其伴随的视野变化外,“春雨”还具有拟人化的叙事功能。
首先,《春夜喜雨》具有明确的拟人化表达。“好雨”是其品格定位,“知时节”“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等动作发出者都是“雨”,这使得雨具有了人格化的行为意志。
其次,“春雨”作为主体经历了完整的情节故事,包括从发生动机到最终结果的全过程,尤其是“乃”指出“雨”所有行为的因果逻辑:“雨”是看准时机,在最需要的时刻才降落人间的,而且随风飘落、润物无声,具有自己个性化的行动方式。
最重要的是,“春雨”是物性和人性的统一体。在战乱频繁的农耕社会,春雨润物的特点不仅让民众和诗人为之喜悦,更展现出博爱奉献的君子做派、中和宽容的美学精神、温柔敦厚的文化品格,这与杜甫“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密切相关。
因此,当春雨被拟人化时,就具有了更加明确的行动目的、更加灵活的行为方式、更加深厚的行为内涵,事的意味大大增强,由此便破解了陆时雍所说的“局于物”的咏物困境。可见,诗人在铺展“意象”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事象”的构造。
这种历时性、拟人化的动态叙事是杜甫咏雨的创意写法,在咏物诗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南朝的许多咏物诗仅追求形似,局限于物本身的形态细摹,精思附会、为物造文,“或体目文字,或图像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9]。对比南朝诗人同题材的作品,更能看出叙事性因素对于咏物诗创作的价值所在。如梁元帝萧绎的《咏细雨诗》:
风轻不动叶,雨细未沾衣。入楼如雾上,拂马似尘飞。
该诗分别从叶间、衣上、楼中、马身四个空间来写。“空间”也是重要的叙事性因素,然而这首诗中空间的转换只是诗人体物视角的变化,彼此断裂、各为一图,缺少内在的联系,自然构不成叙事的脉络和意味,在艺术效果上也只是作“局于物”的冷静描摹,呆板笨滞,缺少流动的气势,更没有深掘物性,展现神韵。且相比而言,《咏细雨诗》展现的是破碎的画面,《春夜喜雨》则展现出生机萌动、鲜活浑融的整体意境。当南朝诗人穷尽艺术技巧和审美观察力对事物进行细致摹写和咏叹之后,杜甫便依循、借鉴叙事手法开拓出咏物诗体物、状物的新路径。
三、章法:叙事性展开的结构奥秘
在《春夜喜雨》中,“春雨”在文本层面存在着由“显”到“隐”的变化状态,这一转变不仅与叙事过程中的视角、感官、时间有关,还与律诗的章法结构有着紧密联系。
律诗的写作常有二节式的分法,如清代金圣叹就将律诗的前四句和后四句分别作“前解”和“后解”,韩成武先生更是专以杜甫咏物律诗为例分析了二节式章法与咏物诗结构的关系,他说“前节在于描绘物象,后节在于寄托情志,物象是引发情志的缘由,情志是谋篇立意之所在。杜甫咏物律诗的章法多属于此”[10]。《春夜喜雨》的咏物写法与此并不完全相同,但也呈现出前四句与后四句的结构分隔,且早有论者指出这一现象,如浦起龙认为“上四俱流水对”,“五、六拓开,自是定法”[11],纪昀则从艺术手法的角度着意称赞了后四句的状物精妙,评曰:“通体精妙,后半尤有神”“后四句传神之笔,则非馀子所可到”[12]。当我们以“事象”作为阐释视角时,便能看出这一结构的意义所在。
《春夜喜雨》的前四句和后四句有着明显不同。前四句从整体着眼,注重的是“面”的铺展;以“春雨”为视角,展开连贯的情节,有发生动机和具体行为。后四句开始关注细节,如“野径”“云黑”“江船”“火明”“红湿花重”等,以点带面,并渐渐将“雨”的视角隐去,代之以作者的观察视角(如“看”字)。“春雨”的主体地位也在第三联的文本中隐藏起来,直到最后才浮现。此时的动态叙事仅停留在时间流逝这条线上,而“雨”的行为情节不再像前四句那样有明确的逻辑。这表明,前两联构造起来的“事象”,从第三联开始隐藏在文本之下,不再直白显露。也正是如此,“春雨”跳出了线性逻辑的连贯叙事,跳出了客观物象特征与行为状态,而进入了动态变化的意境氛围中,进入了精神审美的世界,物象的神韵、美感与价值便由此衍出。
由此可见,杜甫的《春夜喜雨》不仅是意境浑融的抒情佳作,更在体物和状物的写作方式上蕴藏着叙事性因素,抒情和叙事都对诗歌文本意脉的构造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根据葛兆光先生的观点,意脉是“诗歌在人们感觉中所呈现的内容的动态连续过程”[13],就《春夜喜雨》的意脉书写来看,在抒情角度上,“喜”作为最重要的感情线索,虽然没有在诗歌正文中出现,却渗透在文本的细节中,渗透在雨境之内的景观世界里。另外,“时间”作为关键的叙事性因素,更是帮助诗人用连贯的、动态的情节构建体物的“场域”,拟人化的写作口吻更赋予了“春雨”明确的行为逻辑和丰富的精神内涵,物象由此有了多重被观察的视角和更灵活的存在姿态,一场春雨也可以变得形态与神韵兼备、物性与人性相通。如此,在“情景交融”“叙事内伏”两条线的指引下,诗歌便有了流动的意脉和浑融的意境,南朝以来的咏物困局便由此发生新变。
参考文献
[1]杜甫.杜诗详注[M].仇兆鳌,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799.
[2][9]刘勰.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00:567,195.
[3]王夫之.姜斋诗话笺注[M].戴鸿森,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2.
[4]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1408.
[5]郭绍虞.苕溪渔隐丛话(前集)[M].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325.
[6]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63.
[7]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7.
[8]王嗣奭.杜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31.
[10]韓成武.律诗章法研究[C]//第三届世界汉诗大会会议论文.2011.
[11]浦起龙.读杜心解(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8:414.
[12]方回.瀛奎律髓汇评(中)[M].李庆甲,集评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649.
[13]葛兆光.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47.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科研资助项目“初中语文主题阅读教学研究”(项目编号:Y202148323)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