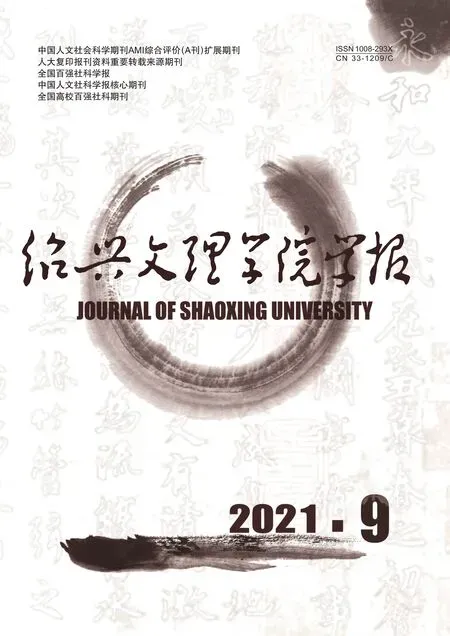民国《平阳县志》摩尼教资料新考
2021-03-10马小鹤
[美]马小鹤
(哈佛大学 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 麻州 剑桥 02138)
民国《平阳县志》不仅发现了摩尼教新资料,即今苍南县括山乡下汤村的元碑《选真寺记》和元代陈高所撰《竹西楼记》,而且作了初步考证。随着福建霞浦文书和日本藏摩尼教绘画的发现,近年来中国东南摩尼教的研究进展迅速,对这些资料可以作一些新的分析。本文先著录民国《平阳县志》的有关资料,再介绍这些资料的收集和考据者刘绍宽,并以20世纪初中外摩尼教研究为背景,评估刘绍宽考据的得失。再简要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这些资料的研究,进而对资料中讲到的“食必红蕈”“苏邻”以及“七时”等内容,作一些新的探索。
一、民国《平阳县志》摩尼教资料著录
民国《平阳县志》卷四十六《神教志二·佛教》小序曰:
……此外有明教者,陆务观谓:“始自闽中,有明教经甚多,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衔赘其后。烧必乳香,食必红蕈。男女不亲授,遇妇人所作食则不食。”(《老学庵笔记》十)陈高谓:“相传自苏邻国流入中土,瓯闽人多奉之。其徒斋戒持律颇严谨,日一食,昼夜七时呗咏膜拜。”(《不系舟渔集·竹西楼记》)孔克表亦称“为苏邻国教”。(《选真寺记》石本)盖即末摩尼教。(《老子化胡经》云:“我乘光明道气,至苏邻国,降为太子,号末摩尼。”)今万全乡尚有其教,大较流为优婆夷、塞(1)优婆夷,音译梵語Upāsikā,中译为“女居士”,即信佛的在家女子;优婆塞,音译梵语Upāsaka,中译为“居士”,即信佛的在家男子;合称“优婆夷、塞”。矣。……《老学庵笔记》引徐常侍《稽神录》云:“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是明教亦为魔。[1]卷46,1-2
又记载:
选真寺:在彭家山,元至正(1341—1370)间重建。清嘉庆、同治间(1796—1874)重修。
并引邑人孔克表《选真寺记》略云:
□平阳郭南行百十里,有山曰鹏山,彭氏世居之。从彭氏之居西北,有宫曰“选真寺”,为苏邻国之教者宅焉。盖彭氏之先之所建也。故制陋朴,人或隘之。彭君如山奋谓其侄德玉:“愿力事兹役,汝其相吾成。”乃崇佛殿,立三门,列左右庑;诸所缔构,演法有堂会,学徒有舍,语处食寝有室,以至厨井、库廪、湢圊之属,靡不具修。都为屋若干楹。即寺之东庑,作祠宇以[奉]神主。又割田如干亩,赋其金用供祀飨。继德玉而相于成,君之孙文复、文明、文定、文崇、文振也。君名仁翁。[1]卷46,17
又记载:
潜光院:在盐(炎)亭,为明教浮图之宇,见陈高《竹西楼记》(《不系舟渔集》)。[1]卷46,28
卷三十七《人物六》有孔克表传[1]卷37,5。孔克表(1314?—1385?)元明均担任过官职,学问渊博,尤精于史学。
卷六十四《文徵内编二》引元陈高《不系舟渔集》卷十二《竹西楼记》载:
温之平阳,有地曰炎亭。在大海之滨,东临海,西南北三面负山;山环之,若箕状。其地可三四里,居者数百家,多以渔为业。循山麓而入,峰峦回抱,不复见海;其中得平地,有田数百亩,二十余家居之,耕焉以给食。有潜光院在焉。潜光院者,明教浮图之宇也。明教之始,相传以为自苏邻国流入中土,瓯闽人多奉之。其徒斋戒持律颇严谨,日一食,昼夜七时呗咏膜拜。潜光院东偏,石心上人之所居也。有楼焉,曰竹西楼。当山谷之间,下临溪涧,林树环茂。楼之东植竹,其木多松、槠、桧、柏,有泉石烟霞之胜;而独以竹名焉者,盖竹之高标清节,学道者类之,故取以自况云。乡之能文之士,若章君庆、何君岳、林君齐、郑君弼,咸赋诗以歌咏之。斯楼之美,与竹之幽,固不待言而知矣。石心修为之暇,游息于是。山雨初霁,冷风微来,如挹琅玕之色,听环珮之音焉。而又仰观天宇之空旷,俯瞰林壑之幽深,翛翛然若游于造物之表,而不知人世之为人世也。石心素儒家子,幼读六艺百氏之书,趣淡泊而习高尚,故能不汨于尘俗而逃夫虚空。其学明教之学者,盖亦托其迹而隐焉者欤?若其孤介之质,清修之操,真可以无愧于竹哉!楼建于某年。石心之师曰德山,实经营之。石心名道坚。至正十一年(1351)七月望记。[1]卷64,7-8
卷三十六《人物五》有陈高传[1]卷36,23-24。陈高(1314—1367)为平阳金舟乡人,著名诗人。
一般方志众手成书,不易确定具体部分出自何人之手。不过,此书的这些资料,应该可以确定编纂者为刘绍宽(号厚庄,1867—1942)。
二、方志专家刘绍宽
平阳自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纂修县志以后,168年未曾修志,民国初年,刘绍宽等“惧邑志旷缺日久,典章堙废,益难为理”,1915年开修纂县志会议,王理孚为修志主任,符璋为总纂(后受聘往上海,实未亲任其职),刘绍宽为副纂,主持实际工作。刘绍宽为近代浙南地区杰出的教育家和著名学者,一代经学大师、地方志专家。苏步青、夏鼐、郑振铎等大批知名学者都出自他门下。遗著有《厚庄诗文钞》《厚庄诗文续集》等。民国《平阳县志》比乾隆志增三分之二,选真寺的资料明确注曰“增”。乾隆志只著录了“《不系舟渔集》[元]陈高著”,新志则将《竹西楼记》全文录入。此志不仅篇幅增加,而且质量上乘,《浙江方志考》誉之为“近代浙江方志之佳作”[2]428-429。
刘绍宽将《〈平阳县志〉篇目序(子目小序附)》收入《厚庄诗文续集》,其中有《神教志》序,附有神祀、佛教、道教、基督教小序[3]卷1,33-36,可以确证《神教志》为其所亲撰。摩尼教资料的收集与考据当出自其手。刘绍宽等拟定的凡例曰:“旧志祠祀并入寺墓,而仙释列于人物。今立神教一志,神庙寺观及仙释列传并合为篇,所谓各从其类也。墓祭本非古礼,况古墓不皆列祀,入古迹庶稍合耳。”[1]卷首,凡例全县分设采访十有四人,而刘绍宽也亲自采访,根据其《厚庄日记(手稿)》,为了编《神教志》,1916年曾有一日跑了15处。隔日,又跑了11处。到处奔波,不辞辛苦,如其所言“阅书史,访碑碣,无非为修志搜集材料”[4]1076。元碑《选真寺记》的发现与摘录就是其成果之一。
符璋对刘绍宽的评价是:“君于学无所不窥,于乡贤哲遗书无不博览及之。……其修《平阳志》也,每考一事,陈书满案,孜孜孽孽。”[5]序2,4刘绍宽撰有《缮校〈不系舟渔集〉附记》[5]卷1,30-31,熟悉此书自不待言,他是指出《竹西楼记》包含明教资料之第一人。
陈澹然(1859—1930)为《厚庄诗文钞》作序言曰:“独其诗登临赠答,雅类剑南,身世之间,或多凄凉,私窃叹之。”[5]序1,1刘绍宽对《剑南诗稿》作者陆游《老学庵笔记》中的资料自然能信手拈来。《老子化胡经》在元忽必烈下令禁毁之后,无完帙存世。但刘绍宽所引的段落,仍可见于《佛祖统纪》转引的《夷坚志》等著作。
刘绍宽所引用的数种明教资料:《选真寺记》《竹西楼记》都是他首先发现的,但《老学庵笔记》及其所引《稽神录》与《老子化胡经》则在法国汉学家沙畹、伯希和以及王国维、陈垣的摩尼教研究中都已经引用,刘绍宽是否可能参考过他们的论文呢?刘绍宽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曾入上海震旦学院,就学于马相伯;次年游历日本,考察学务,著有《东瀛观学记》;他“湛深经术,淹达时务”,不无这种可能。不过要确定其是否吸收了1925年以前摩尼教研究的成果,则尚需简要回顾一下这段研究史。
三、初期摩尼教研究与方志
伯希和1908年在敦煌获取大量文书,次年8至9月间,到北京购书,随身携带的敦煌藏经洞的一些珍本使中国学者认识到了藏经洞宝藏的巨大价值,促使清政府把藏经洞所余经卷悉数运京。罗振玉1911年在《国学丛刊》第二册上刊布了一份敦煌写经的抄本,题曰《波斯教残经》(后常称京藏《摩尼教经》)。这份文书今藏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旧编号“宇字第56”,新编号“北8470”,近来编为“北敦00256号”。罗振玉将这一册《国学丛刊》送给日本学者羽田亨,羽田亨于次年在《东洋学报》上发表论文,考订此经为摩尼教残经[6]。这件文书可谓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拣选文书中的最大失漏,他急忙和老师沙畹研究其抄本,翻译成法文,详加注释,附以敦煌发现的“伯希和文书”(后来确定是《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简称《仪略》的下半截)、《老子化胡经》残卷,并广泛收集有关摩尼教的汉文史料,包括陆游《老学庵笔记》、徐铉《稽神录》,并翻译为法文。1911年和1913年分三次发表在《亚洲报》上,题为《中国发现的一部摩尼教经典》[7]。1931年冯承钧将此文研究汉文史料的部分翻译为中文发表。
沙畹、伯希和的摩尼教研究激起了王国维的回应,在其基础上,新增11则史料,但未发展为正式论文,以《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为题,于1921年发表[8]。此后,陈垣也有意参加这场学术争胜,向王国维请教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所藏摩尼教文献《下部赞》的内容,王国维回信云:
右摩尼经赞目,伦敦博物馆所藏唐写残卷,反面写《大唐西域记》卷一,次《往生礼赞文》一卷(比丘善导愿往生礼赞文廿二拜),次《十二光礼忏文请佛作梵》(此二段疑亦摩尼教经),见日本矢吹庆辉《敦煌出佛书解题》,惜所录未完。然其中人名颇有与何乔新(“远”字之误)《闽书》所载参证,忙儞具智王即《闽书》之具智大明使,忙儞即MANI之音译也。[9]262
《下部赞》是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带至大英博物馆的敦煌文书之一,直到1916年夏,才为日本学者矢吹庆辉认定为摩尼教经,但很长时期内中国学者并无研究。1923年陈垣发表《摩尼教入中国考》[10],即引用了方志《闽书》。给学界的印象是《闽书》的此条材料由陈垣首先发现的。根据此信,极有可能是王国维最先注意到《闽书》中的摩尼教材料[11]。陈垣接着发表《摩尼教残经一、二》,点校、刊布了京藏《摩尼教残经》和《仪略》[12]。伯希和得知《闽书》这条资料后,又补充了何乔远《名山藏》中关于摩尼教的资料,于1923年发表《福建摩尼教遗迹》[13]。这进一步引起学术界对福建摩尼教遗迹的注意。
陈垣发表《摩尼教入中国考》之后,1924年胡适也为他提供了重要史料。胡适提出宋代黄震《黄氏日抄》中包含了一篇《崇寿宫记》,记载了一座摩尼教寺演变为道观的史实[9]201-202;[14]。陈垣回信感谢胡适提供资料,还说友人告知《嘉定赤城志》中有知州李谦《戒事魔诗》十首,可以推定宋代闽浙沿海地区盛行摩尼教[9]202。此友人当即王国维,王国维1921年发表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中并未引用《戒事魔诗》,而在此文收入其《观堂别集》第1册时,增补了这条资料。王国维、胡适为陈垣提供的资料与意见等于间接回应了沙畹、伯希和在摩尼教研究上的挑战。
刘绍宽看来没有接触到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果他通过陈垣之文知道《闽书》关于华表山的记载,应该知道“‘末’之言大也”,因此不会称此教为“末摩尼教”,而应该像王国维、陈垣一样,称此教为“摩尼教”。他如果知道摩尼教实际上是一种独立于佛教之外的世界宗教,恐怕就不会将其视为佛教异端,放在《神教志二·佛教》中讨论,应该另列一类。从上述学者之间的争胜与交流中,可以看到在东方摩尼教研究这个新领域中,何等重视一条方志资料的发现。可惜,他们都未能注意到民国《平阳县志》中的《选真寺记》和《竹西楼记》。
刘绍宽发现新资料对摩尼教研究的意义固不待言,但尚需对这些新资料定性。
四、新修方志与摩尼教研究
继承王国维、陈垣学术传统的刘铭恕先生于1940年发表《火祆教与摩尼教的新史料(未完)》,刊布了火祆教新史料,但未见续篇[15]。他意欲刊布的摩尼教新史料中或许就包括《竹西楼记》。他于1958年发表《泉州石刻三跋》,节录了《竹西楼记》,首先将此史料定性为摩尼教资料[16]61。刘南强先生于1977年将《竹西楼记》全文英译发表[17]。庄为玑于1983年也征引了这则史料[18]81。三位学者可能是直接从陈高《不系舟渔集》中检出的。1985年,林悟殊先生据民国十五年(1926)重刊本(民刊本)将《竹西楼记》标点刊出[19]。四位学者均未提及民国《平阳县志》。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修志,创造了一个地方史料更多地进入史学研究视野的大环境。林顺道先生为新修《平阳县志》副主编,当熟读民国《平阳县志》。林顺道不同于刘绍宽的地方在于,他不再只以传统考据方法研究地方宗教史料,而是利用当时学术界对宋元东南沿海摩尼教的研究成果来解读民国《平阳县志》中的史料。
林顺道指出:今鳌江下游之南,当地习惯称为“江南”。1981年,原平阳县析为平阳、苍南两县时,“江南”划归苍南,万全划归平阳。民国《平阳县志》没有提及明教在万全的遗迹,但却完整地保存了明教在“江南”的两座寺庙的有关史料。“江南”是摩尼教由闽入浙的重要据点。潜光院所在地炎亭和选真寺所在地彭家山分别位于现在金乡镇东西两侧,古代金乡是闽浙重要通道上的重镇。明代中叶以后,温州的明教已和佛道或其他秘密宗教相混杂,因此,民国《平阳县志》又说:“今万全乡尚有其教,大较流为优婆夷、塞矣。”根据民国《平阳县志》的记载,林顺道1988年在苍南县括山乡下汤村彭家山山麓找到了选真寺遗址,并在寺前田野中找到了《选真寺记》碑。他也确定了潜光院遗址当在现苍南县炎亭镇洪家行政村岙底自然村大岗山山麓[20]。
1990年周梦江将碑记抄录发表[21]75。1993年版《平阳县志》在人物方面介绍了陈高、孔克表,说明《选真寺记》与《竹西楼记》是研究平阳明教传播的珍贵史料[22]831-832。1993年版的《苍南县志》,在宗教方面设专章介绍摩尼教,在人物方面介绍了陈高,在艺文方面著录了《竹西楼记》和《选真寺记》(林顺道录文)[23]692,745-746,846-847。1998年版《温州市志》宗教方面也设专章介绍摩尼教,附《选真寺记》;人物方面介绍了孔克表与陈高[24]477-478,607-608。林顺道又将碑文校补标点,刊布于《中国文物报》1997年7月27日第3版上的《摩尼教〈选真寺记〉元碑》中。2005年金柏东发表此碑的一个更新录文[25]18。林悟殊以多个不同版本参校,对《竹西楼记》与《选真寺记》作了新的录文校勘,推测选真寺、潜光院应为宋时物[26],[27]242-252。林顺道通过分析温州姓氏史志、谱牒资料以及温州方言状况,认为摩尼教传入温州,可上溯至唐季五代大量闽东移民入温时。选真寺应是北宋时所建[28]。
众多学者的努力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下文尝试对民国《平阳县志》中的有关资料作一些新的分析。
五、“食必红蕈”
民国《平阳县志》所引陆游《老学庵笔记》关于明教的记载当出自陆游亲身观察。他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冬季出任福州宁德县(现宁德市)主簿,次年调官为福州决曹;三十年(1160)自福州北归,在都下任闲职。三十二年(1162)上《条对状》,其第七条请禁民间“邪教”,阴消异时“窃发”之患[29]64-97;[30]80-89。其中讲道:“伏缘此色人等处处皆有,……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名号不一。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以祭祖考为引鬼,永绝血食,用以沐浴。其他妖滥,未易概举。烧乳香则乳香为之贵,食菌蕈则菌蕈为之贵。”[31]125
贾文龙认为宋人描述江南地区的秘密宗教信仰时,没有沿袭“食素”这个俗语,而是使用了“吃菜”一词,称之为“吃菜事魔”。“吃菜”的由来并不仅因为素食,而是因宋代摩尼教的特殊教仪促成[32]。他引述著名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名著《结构人类学》中译本之《文化中的蘑菇》一文,讲到陆游谴责摩尼教徒食用红蘑菇(红蕈)和以人尿为仪式用水(“以溺为法水,用以沐浴”),而圣奥古斯丁也曾谴责他们喜欢蘑菇[33]228-230。《文化中的蘑菇》是对美国民族真菌学家罗伯特·高登·华生之《苏摩:不朽的神圣蘑菇》一书的书评。华生是通过沙畹、伯希和的《中国发现的一部摩尼教经典》一文而知道陆游谴责摩尼教徒嗜食蘑菇的。他指出,福建盛产一种可食用的红蘑菇[大红菇,Russula rubra (Krom.) Bres],福建人采集它们,供本地人和外地人食用。这应该就是陆游所说的“红蕈”[34]71-76。华生将陆游与圣奥古斯丁对摩尼教的谴责作了比较。圣奥古斯丁指责他们,以为一个人[=选民]只要吃蘑菇、米饭、块菌、糕点、葡萄汁、胡椒和咖喱,就不会发现其违背三印(即神圣的戒律)[35]82。
红蕈(菌蕈、蘑菇)无疑是福建“吃菜事魔”者所食之“菜”中最重要的一种,由于他们人数众多,经常吃红蕈,以致红蕈的价格上涨。吃蘑菇是东西方摩尼教徒的共同特征之一。“吃菜”其实就是摩尼教的圣餐,有重大的宗教含义。摩尼教教义认为,素菜中含有大量光明分子,选民(僧侣)吃下素菜,能把素菜中的光明分子解放出来。摩尼教社团生活就是选民与听者(俗信徒)之间的互惠关系,听者向选民布施瓜果素菜,使选民能将光明分子从中释放出来。听者则根据其布施的程度,灵魂获得不同的归宿,信教者免下地狱,重新轮回,投胎为选民,再得到解脱,而最虔诚者则可以直接飞升天堂。汉文资料提供了中国摩尼教圣餐仪式的证据。唐代《仪略》“寺宇仪第五”列举的五堂之一为“斋讲堂”,即布施、食斋、讲经之堂,“斋”意为“素食”“布施”,这里就意为摩尼教的圣餐。“法众……每日斋食,俨然待施;若无施者,乞丐以充。”每寺诠简三人,其三为“遏换健塞波塞”,是伊朗语rw’-ng’n‘spsg的音译,“译云月直,专知供施”,就是专门负责圣餐的供应与布施之事[36]521。京藏《摩尼教经》说选民“年一易衣,日一受食,欢喜敬奉,不以为难”,北宋宣和二年(1120)臣僚言:“今来明教行者各于所居乡村建立屋宇,号为斋堂,如温州共有四十余处。”[37]第14册,8325“斋堂”类似《仪略》所说的“斋讲堂”。陆游说:“至有士人宗子辈,众中自言:‘今日赴明教斋。’予尝诘之:‘此魔也,奈何与之游?’则对曰:‘不然,男女无别者为魔,男女不亲授者为明教’。”[31]第11册,481-482“明教斋”即明教的圣餐仪式。
宋代“吃菜事魔”后来泛指素食、崇拜非正统神祇的宗教社团,也包括了白莲菜、白云菜等佛教异端团体。到了元代,明教徒似不再讳言“吃菜”。新发现的日本奈良大和文华馆藏《冥王圣帧》榜题曰:
东郑茂头保弟子张思义偕郑氏辛娘喜舍冥王圣帧恭入宝山菜院,永充供养,祈保平安。愿(圣?王?)□□(安?)日(以下残)。[38]96-98
“菜院”之“菜”,即“吃菜”之“菜”,“菜院”即“吃菜”之斋堂。陈高说明教“其徒斋戒持律颇严谨,日一食”,“日一食”应该就是“吃菜”。
粘良图先生从《青阳科甲肇基庄氏族谱》中发现一篇庄惠龙(1281—1349)的墓志铭,说他“晚年厌观世谛,托以苏邻法”,意即皈依摩尼教。庄氏族谱记“天德,惠龙三子,从空,葬菜堂地基”。“从空”意为出家作僧人,天德卒后葬于自家的“菜堂”,亦即斋堂[39]48-50。
六、“自苏邻国流入中土”
民国《平阳县志》所引《竹西楼记》说:“明教之始,相传以为自苏邻国流入中土。”《选真寺记》说:“有宫曰‘选真寺’,为苏邻国之教者宅焉。”摩尼与苏邻的联系见于20世纪初发现的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卷一:
后经四百五十余年,我(即老子)乘自然光明道气,从真寂境,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室,示为太子,号末摩尼。[40]第1册,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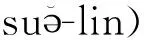

其实,苏蔺、苏剌萨傥那就在泰西封,完全可以用对音法来确定苏邻国的真实地理名称。根据泰伯里用阿拉伯文写的《历代先知和帝王史》、波斯沙普尔一世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希腊文三语碑铭、纳尔西一世中古波斯文和帕提亚文双语碑铭和菲尔多西用波斯文写的《列王记》,萨珊时代,波斯国都所在的中央省区的名字,希腊文作’Aσσυρια,帕提亚文、中古波斯文作’swrstn,读作Asūristān,阿拉伯文、新波斯文作Sūristān。汉文音译为“宿利”“苏利”“苏蔺”“苏邻”“苏利悉单”“苏剌萨傥那”,实际上都指萨珊波斯首都塞琉西亚-泰西封(马达因)为中心的地区,古称巴比伦。这一地区正是摩尼出生和活动的中心[48]320-335。
本文就“苏邻”问题欲再加探讨的是白居易“苏邻之诗”的可能性,及其与霞浦文书之关系。先著录南宋志磐《佛祖统纪》的有关记载:
述曰:尝考《夷坚志》云,吃菜事魔,三山尤炽。为首者紫帽宽袗,妇人黑冠白服,称为明教会。所事佛衣白,引经中所谓“白佛,言世尊”。取《金刚经》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以为第五佛。又名末摩尼,采《化胡经》“乘自然光明道气,飞人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宫为太子,出家称末摩尼”,以自表证。其经名《二宗三际》。二宗者,明与暗也;三际者,过去、未来、现在也。大中祥符兴道藏,富人林世长赂主者,使编入藏,安于亳州明道宫。复假称白乐天诗云:“静览苏邻传,摩尼道可惊。二宗陈寂默,五佛继光明。日月为资敬,乾坤认所生。若论斋絜志,释子好齐名。”以此八句表于经首。其修持者,正午一食,裸尸以葬,以七时作礼。盖黄巾之遗习也。(原注:尝检乐天《长庆集》,无苏邻之诗。乐天知佛,岂应为此不典之辞?)[49]第3册,1143
芮传明先生在《白居易之“摩尼教诗”的可能性》中指出摩尼教盛行于白居易时代,“安史之乱”后,唐肃宗请求回鹘军队的援助,刚成为“国教”的摩尼教借助唐廷对回鹘的“优惠待遇”而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宪宗元和二年(807),回鹘使者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许之[50]351-353。
白居易的翰林制诰中就有元和三年(808)撰写的《与回鹘可汗书》,也讲道:“其东都、太原置寺,此令人勾当,事缘功德,理合精严。又有彼国师僧,不必更劳检校。……所令帝德将军安庆云供养师僧请住外宅,又令骨都禄将军检校功德使,其安立请随般次放归本国者,并依来奏,想宜知悉。今赐少物,具如别录。内外宰相及判官、摩尼师等,并各有赐物,至宜准数分付。内外宰相、官吏、师僧等,并存问之。”[51]第3册,1174-1177此处之可汗即保义可汗,存世的突厥、粟特、汉三语哈拉巴喇哈逊(Kara Balgasun)碑即其记功碑。东都即河南府,东都、太原所置之寺即摩尼寺,师僧即摩尼师。《与回鹘可汗书》还讲到唐朝与回鹘的绢马贸易,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讨论白居易新乐府《阴山道》时曾加以引用。《阴山道》曰:“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养无所用去非宜,每岁死伤十六七。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丈余,回纥诉称无用处。”陈寅恪谓:“又史籍所载,只言回鹘之贪,不及唐家之诈,乐天此篇则并言之。是此篇在新乐府五十首中,虽非文学上乘,然可补旧史之阙,实为极佳之史料也。”[52]261-267,[53]349-352
白居易还撰有多篇与回鹘有关的中书制诰:穆宗即位,派郑权为入回鹘告哀使,长庆元年(821),白居易撰《入回纥使下军将官吏夏侯仕戡等四十人授卿监宾客咨议》,擢升随郑权出使回纥的军将官吏。同年回纥毗伽保义可汗薨,白居易撰《祭回鹘可汗文》。四月,白居易撰《册新回鹘可汗文》,册封君登里罗羽录没密施句主录毗伽可汗,此为回鹘九世可汗,亦称崇德可汗。接着又撰《册回鹘可汗加号文》,加册其为信义勇智雄重贵寿天亲可汗,并告诉他“请仍旧姻,誓嗣前好”。保义可汗生前曾遣使求婚,唐朝答应过,五月,崇德可汗遣使请迎所许公主。朝廷遂封穆宗第五妹为太和公主以降[51]第2册,603-611、836-837。白居易显然熟知回鹘与摩尼师的情况。
白居易撰写过“苏邻之诗”还有旁证。宋末四明(宁波)崇寿宫主持张希声告诉儒生黄震:“吾师老子之入西域也,尝化为摩尼佛。……吾所居初名道院,正以奉摩尼香火,以其本老子也。”他请黄震为崇寿宫写记。黄震认为“吾儒与佛老固冰炭,佛与老又自冰炭,今谓老为佛,而又属记之于学儒者,将何辞以合之,且何据耶?”因书诘之。张希声回答时给出的一个证据是:“白乐天晚年酷嗜内典,至其题摩尼经,亦有‘五佛继光明’之句,是必有得于贯通之素者矣。则释氏之据如此。”[54]第7册,2311-2313张希声为了说服儒生黄震为此宫写记而将“苏邻之诗”作为证据,说明他确信此诗是白乐天之作;黄震看到张希声的多重证据之后,欣然为其写《崇寿宫记》则说明他并未怀疑“苏邻之诗”乃白乐天诗。志磐说其“假称白乐天诗”,且加上双行夹注来论证其“假称”,恐怕是出于对摩尼教的偏见。
霞浦文书《摩尼光佛》的刊布,为此问题的深入探讨提供了新的证据与角度。《摩尼光佛》多处将摩尼与苏邻联系在一起:“志心信礼,长生甘露王(即摩尼)。从真实境下西方,跋帝苏邻国,九种现灵祥。”[55]60这显然套用《仪略》。“摩尼佛下生时,托荫于苏邻。”“一,那罗初世人;二,苏路神门变;三,释迦托王宫;四,夷数神光现。[众和]救性离灾殃,速超常乐海。一,摩尼大法王;二,最后光明使;三,出现于苏邻;四,救我有缘人。”[55]66,72根据《摩尼光佛》,可以肯定“苏邻之诗”中的“五佛”,对应上文“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以为第五佛,又名末摩尼。”但是与《金刚经》无关。摩尼教五佛各有自己的活动地域:一佛那罗延(简称那罗)“降神娑婆界,国应波罗门”,二佛苏路支(苏路)“以大因缘故,说法在波斯”,三佛释迦文(释迦)“四生大慈父,得道毗蓝苑(蓝毗尼园)”,四佛夷数和(夷数)“无上明尊子,降神下拂林”。又说:“第一那罗延,自洪荒世下西方。”“第二苏路支,救净风性下波斯。”“第三释迦文,下天竺国号世尊。”“[第四]夷数和,……神通验,拂林国,圣无过。”[56]81-84那罗延为印度婆罗门教之大神,故称“国应波罗门”。苏路支即琐罗亚斯德,其活动地域是波斯;释迦文即释迦牟尼,其活动地域为天竺,即印度;夷数即耶稣,其活动地域为拂林,即罗马帝国。二、三、四佛都是在摩尼教文献中反复颂扬的摩尼的先驱者,活动范围都是可以用对音法来确定其真实地理名称。教主五佛摩尼的出生和活动中心苏邻,更加应该是一个可以用对音法来确定的真实地理名称,即古代的巴比伦,萨珊波斯首都所在的直隶省,而不是一个道教杜撰的乌托邦。
七、七时
民国《平阳县志》所引《竹西楼记》说:“其徒斋戒持律颇严谨,日一食,昼夜七时呗咏膜拜。”民刊本作“昼夜七时咸瞑拜焉。”《敬乡楼丛书》本作“昼夜七时诵膜拜”,另据校注,一本作“昼夜七时呗咏膜拜”。《四库全书》本作“昼夜七时咏膜拜”[27]147。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清代据明成化元年序刊本抄写的精钞本同四库本。“七时”见于多种摩尼教资料。《七时偈》是《宋会要辑稿》宣和二年(1120)“臣僚言”中所列举的明教经文之一。志磐也说道:明教徒“以七时作礼”。白玉蟾在《万法归一歌》中说:“明教专门事灭魔,七时功德便如何?不知清净光明意,面色萎黄空自劳。”[56]《摩尼光佛》也说明教僧“七时礼忏”。根据比鲁尼的记载,摩尼教选民每天要做七时礼忏,时间是:拂晓、日出、中午、下午三点左右、黄昏、半小时后和子夜[57]。
八、余论
京藏《摩尼教残经》与民国《平阳县志》的明教资料相比,包含的信息量相去悬殊,但是,两者的发现、定性、研究仍有可比之处。1911年罗振玉刊布京藏《摩尼教残经》时,在按语中写道:“然考火祆、摩尼与景教颇类似,未易分别,且皆由波斯流入中土,故姑颜之曰波斯教经,以俟当世之宗教学者考证焉。”[58]1265他未能确定此文献之宗教属性。刘绍宽在1925年出版的《平阳县志》中披露并考证有关资料时,称之为“末摩尼教”,也并未厘清其宗教属性。
但是,两者此后的遭际却大相径庭。所谓《波斯教残经》立即被羽田亨、沙畹、伯希和诸人考定为摩尼教经文,沙畹、伯希和的精深研究很长时期无人能够超越,陈垣又很快刊出了此文献的校点本。民国《平阳县志》中的相关资料却被冷落了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修方志的环境下,才重新引起重视,定性为摩尼教资料,得到研究与探讨。
20世纪90年代,对京藏《摩尼教残经》的研究有了比较大的进展。德国学者宗德曼检出与京藏《摩尼教残经》内容相关的安息语、粟特语残卷凡四十九号,著成《〈[明使演说]惠明经〉——东传摩尼教的一部说教作品:安息语和粟特语本》[59],系统地探明了《摩尼教残经》的伊朗语原本。最近,刘南强、米克尔森、埃克尔斯等学者吸收其成果,将汉文与相应的安息文、粟特文、回鹘文相对照,翻译成英文,详加注释,已出版了第一卷[60]。这是国际摩尼教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成果。
同时,民国《平阳县志》中的摩尼教资料也尚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本文就是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个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