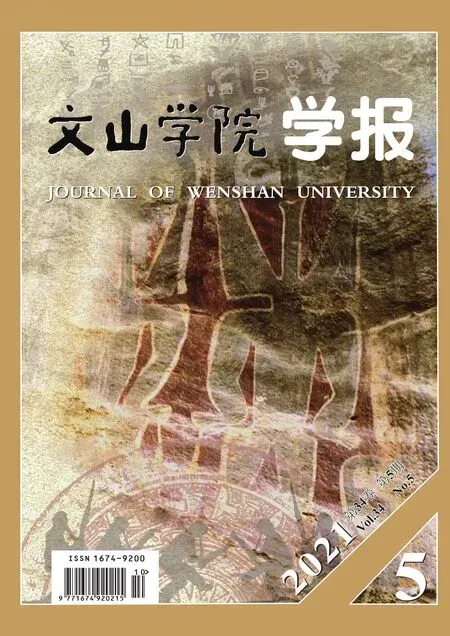邓小平在百色起义时期的策略思想与实践
——以灵活应对上级“左”倾错误指示为例
2021-03-08赵连跃
赵连跃
(百色学院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西 百色 533000)
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1929年7月,应主政广西的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广西编遣特派员李明瑞等国民党左派军人请求,邓小平作为党中央代表,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到广西领导革命斗争。在敌强我弱且上级党组织作出严重“左”倾错误指示的情况下,邓小平领导的党组织大胆探索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正确的应对策略,对百色起义的成功举行和西南边疆最早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的创建,以及革命基干力量的保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扬弃共产国际和中央“左”倾阶级政策,与国民党左派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并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错误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背叛民族革命运动,国民党的一切派别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影响,1928年中共六大决议中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之一。1929年6月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虽然承认当时的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根本矛盾,但没有制定如何加以利用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中仍对中间阶级和国民党左派实行关门政策。为此,中共中央和领导广西党组织的广东省委虽应俞作柏、李明瑞请求派党员干部前来广西,但仍把广西新政府称为军阀政府,认为“即使俞、李本人,主观上是愿以士兵群众为其投身革命之基础”,“即使这些当权分子中,有倾向于我党的人,但其在位一天,我们总不能与之发生正式的组织关系”,要求广西党“总的是破坏他,绝对不是巩固他”,“必须公开党的面目与之对抗”。中央还批评广西党的指导机构中已埋下机会主义的危险根苗,要予以无情打击、给予组织上的严重制裁[1]68。如果以邓小平为首的广西党组织盲目执行上级的“左”倾错误指示,与俞、李进行公开对抗,派到广西工作的共产党人将无法立足,更谈不上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
面对上级党组织关于国民党左派的错误分析,以及共产国际和党内的“左”倾阶级政策,邓小平没有机械执行指示。在多方调查了解的基础上,用全面、发展的观点剖析从第一次蒋桂战争中派生出来的广西新政权的特殊性,以及主持新政权的俞、李的政治态度。邓小平认为广西新政权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具有民主政权色彩;俞、李是国民党左派军人和北伐名将,虽曾利用蒋介石力量倒桂,但与蒋、桂都有矛盾,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情革命。俞作柏曾暗助枪械与我党领导的农军及广州起义,反对新桂系清党屠杀政策;李明瑞曾在其部队秘密掩护过被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员;二人在策划反桂之初,曾将倒桂后反蒋的意图告知广东省委,为巩固主政地位而主动请求中共派干部协助其工作。同时,蒋、桂、汪各派系也设法争夺他们,中共如不加紧争取,将丧失在广西开展革命的契机。为此,邓小平制定了对广西国民党左派进行统战的策略:既把他们与国民党右派区别开来,实行团结、争取、教育的方针,与之共谋反蒋反新桂系大事,又坚持我党独立自主基本原则不动摇;对亲蒋分子、新桂系中的顽固派和汪精卫改组派则予以坚决打击。事实证明,邓小平领导下的广西党组织与俞、李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在广西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必要的、正确的、成效显著的,解决了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但没有解决好的争取中间阶级成为革命同盟者问题,更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展壮大了革命队伍。正是有了对“左”倾阶级政策的扬弃,党得以在俞、李的默许和保护下半公开活动,为在大革命失败后元气大伤的广西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环境。
二、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将广西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看,只有城市工人起义而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因此,大革命失败后较长一个时期内,以城市作为革命工作的中心是全党的共同认识。尽管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其影响力仍较为有限,“城市中心论”依然存在于党内,广西的革命斗争也深受影响。如1929年8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给广西特委的信》中认为“你们决定以南宁、柳州、梧州三大城市为全省工作的中心是对的。但是省委还要向你们指出,在三大城市中更须以梧州为中心之中心”,并指示“必须集中力量注意三大城市(指南宁、柳州、梧州)的职工运动”[2]30。同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中要求广西党组织“应立即加紧梧州、南宁及沿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2]36。据此,广西特委确定了“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主要商业区城市及政治中心的城市为最重要的中心工作”的总路线,不切实际地提出应集中人力和财力建立起这三个中心城市的工作,“尤其梧州为中心城市中的重要工作”,并“要集中精神于最短期内,建立起来”[3]53,呈现出明显的“城市中心论”烙印。
邓小平抵达广西后,对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也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首先是执行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指示,把党组织工作的重心放在南宁,随即开展统战工作和兵运工作。与此同时,主动汲取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教训和秋收起义队伍放弃攻打大城市、转向井冈山地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注意考察广西各地尤其是左右江地区的斗争形势,逐步认识到在非中心城市开展革命的重要性、必要性,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农民运动:一是劝说俞、李开放农民运动,恢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取缔的农会组织;二是组织召开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省农协筹备处,共产党员雷经天、韦拔群担任正副主任,指派一批党员干部负责组建省农协右江办事处和左江农运指导委员会;三是加强党对左右江地区工作的领导,如指示广西特委派出一半委员到左右江地区开展工作,组建了中共右江工作委员会,推荐1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各县担任县长,以合法方式掌握政权;四是劝说俞、李拨给东兰、凤山农军200余支枪,至10月中下旬,“(东兰)有组织的农民十六万,可以号召二十万的农民。有经常的武器一千一百”[3]49,为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农村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广西革命形势出现较好转机之时,俞、李没有接受广西党组织的劝说,于1929年9月执意参与联合反蒋战争。邓小平等预料到他们必然失败,广西政局将急剧变化,如继续以城市斗争作为工作重心,将给广西革命带来巨大危害。为此,邓小平相继派党在南宁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各一个营,到右江及左江地区开展先期工作。果然,俞、李的反蒋仅10多天就宣告失败,南宁的政治气氛骤然紧张。在紧要关头,邓小平等没有机械遵循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以最得力的工作同志”去“立即加紧梧州南宁及浔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的指示,坚决反对部分同志关于在南宁举行武装起义的主张,果断率领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分赴左右江地区,与当地工农运动相结合,积极做好武装起义前的各项准备。
实践证明,邓小平将工作重点从南宁兵变及时转变为左右江地区游击战争的策略,完全符合当时广西的革命斗争形势。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在《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建立》一文中如是说:“我们选择在这块地区创建根据地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到右江和当地的革命群众会合,便很难在短时间内建成红七军和得到巩固、发展”[4]。究其主要原因,一是该地区地处滇黔桂交界处,与越南接壤,具有地势险要,可攻可守;二是各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2年,韦拔群就开始领导右江地区东兰、凤山的农民运动,即使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农民运动依然坚持不倒;三是该地区反革命的力量相对薄弱,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具备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条件。正是借助于以上有利条件,党组织得以发展壮大革命队伍, 1929年12月11日成功举行百色起义并创建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第二年2月1日龙州起义胜利举行并创建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土地革命逐步展开。这是继湘赣边界起义等武装起义之后,共产党人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新道路的又一次探索,揭示了敌强我弱形势下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客观必然性。
三、逐步抛弃中央关于攻打大城市的冒险主义错误指示,保存了革命武装
1930年6月至9月,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占据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曾一度掌握中央实际权力的李立三等人不切实际地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6月16日,中央通过军委南方办事处指示红七军“坚决的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1]316。9月3日,中共南方局在发出给红七军前委和右江特委的指示信中命令红七军立即到柳州和桂林创建工作,迅速组织地方暴动、士兵暴动,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组织,建立新的红军 。[3]229然而,9月24至28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批判“立三路线”,停止了调集全体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由于时间紧急,信息极为不畅,中共南方局和广西党组织对此毫不知情。9月30日,南方局代表邓岗(邓拔奇)携带六届三中全会之前的相关上级指示和决议精神到右江地区进行传达,要求红七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北上夺取柳州、桂林、广州等中心城市,消灭两广军阀,阻止南方军阀进攻武汉,实现“会师武汉”计划。
由于事关重大,邓小平于10月2日在平马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邓小平、张云逸等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实际情况,对红七军能否完成中央的任务持怀疑态度,不太赞成攻打大城市。张云逸曾在1960年的《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中谈到:“记得那时邓小平就不大赞成打大城市......我也认为我们的部队只有一万多人,力量还不够大,也不大同意”。但当时持这种正确意见的占少数,邓岗和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等多数主张坚决执行中央命令。经过激烈争论,为团结一致对敌、避免党内分裂给敌人以可乘之机,邓小平等同意执行党的决议,提出不能盲目执行中央命令,而是灵活机动地根据实际需要做出调整,行不通时将及时纠正。在踏上北上征程后,邓小平力主避开强敌,避免攻坚战,尽量减少损失。但前委的一些领导人受“立三路线”影响,认为红七军力量比敌人大,批评邓小平等的正确意见是“缺乏进攻精神”[1]378,一些干部战士亦迷惑不解,故红七军先后猛攻邓小平不主张攻打的湖南长安、武冈,共伤亡1000多人仍无法攻下,不得已于1931年初退回广西全州休整。
从离开根据地执行中央进攻中心城市指令起,仅两个月时间,红七军就经历了大小数十次战斗,不仅没有攻下一座城市,而且遭受敌人围追堵截,武器弹药消耗殆尽,减员近半,甚至发生叛逃事件。残酷的事实使广大指战员对中央指示产生了普遍怀疑和不满,迫切要求解决“部队往何处去”的问题。1月2日,前委在全州关帝庙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停止执行中央关于攻打大城市的命令和改变部队进军方向问题。尽管当时前委仍未得到中央关于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指示,但邓小平、张云逸和红七、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等在分析敌我态势和总结北上以来的沉痛教训后,认为“攻桂林已不可能,七军的迫切需要是迅速找一个地方发动群众,休养补充,安置伤兵”。在邓小平、张云逸的耐心说服下,极力主张执行中央指示的邓岗和陈豪人等也转变了认识。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的冒险计划,由硬拼攻坚战略转变到游击战略,挥师沿湘粤赣边发展,以期建立粤北根据地并相机会师朱毛红军。全州会议成为红七军北上征途中的重要转折点,此后,红七军主动避开强敌,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稳步前进,逐渐摆脱被动局面,保存了有生力量,并于1931年7月实现了与中央红军的会师。
综上所述,百色起义时期,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对广西和左右江革命工作做出了不少正确决策,但在指导上也存在过较明显的“左”倾错误。邓小平等共产党人既严守党的组织纪律、服从上级命令、顾全大局、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又立足于实际,没有机械地执行这些“左”倾错误指示,而是采取了灵活应对的策略,将革命引向正确轨道,也为党以后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