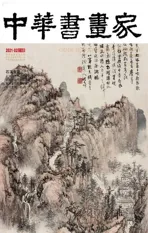《黄流巨津》与陈洪绶晚岁画风
2021-03-08朴城君
□ 朴城君 杨 雪
《黄流巨津》是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陈洪绶杂画册》中的八幅之一,纵30厘米,横25厘米。画家在不大的尺幅上对奔涌河流中激荡的浪花进行细致的刻画,两岸的景物则用简略的笔墨带过。对比陈洪绶内容丰富的长卷作品,《黄流巨津》的画面显得过于简单,然而其大胆的构图、细密流畅的线条、颇有意趣的装饰意味,有着令人过目难忘的魅力,可谓古代画水作品中颇具特色的一幅佳构。
以陈洪绶所撰《宝纶堂集》,黄湧泉整理的《陈洪绶年谱》等为文献资料依托,作品的年代可考,应作于1643年至1646年间。此时正值明末清初之际,也是画家一生中最动荡的时期,画家经历了仕途尽毁、家国倾覆、颠沛流离、偷生苟活。这一特殊时期的经历对陈洪绶晚岁绘画风格的嬗变有极大影响。本文将结合《黄流巨津》创作的时代背景、画家个人经历,分析陈洪绶晚岁画风的嬗变在《黄流巨津》中的体现。
在《黄流巨津》尺幅不大的画面中,奔涌的河流是占据画面的绝对主体。在翻涌的巨浪间,数只帆船在舵手的把控下漂摇于水面。左下角根根耸立的桅杆昭示着停满驳船的港口,河对岸密林丛生,屋宇隐现其间。画面右下角画家自题“黄流巨津”,并署款“老迟洪绶”。画面采用对角构图法,由左下及右上翻滚的洪流贯穿其间。画家着重笔墨塑造翻腾的浪花,两岸景物则用精简的笔触带过,相对虚化,使画面构成十分鲜明的虚实对比,意在突出“巨津”的主体地位。观者的目光紧紧地被这巨浪洪流所吸引,线条的排列细密流畅,强烈的装饰意味,使画面逸趣横生。学界普遍认同此幅画作诞生于晚明,应是陈洪绶南下时途经黄河,见壮阔之景,有感而作。
陈洪绶为考取功名,曾两次北上进京。第一次在天启三年(1623),此年陈洪绶发妻来氏病逝,陈洪绶怀着悲痛的心情北上参加科举,最终落败而归。第二次北上是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穰梨馆过眼录》中记载陈洪绶所作《临丁南羽祖师待诏图》,并题款:“庚辰春仲客燕京,临丁南羽祖师待诏图”,可知此时的陈洪绶已在北京。崇祯十五年(1642),陈洪绶通过入赀取得功名,进入国子监,召为中书舍人。历经二十多年的努力与期盼,怀才不遇的陈洪绶终于得偿所愿。此时他已经44岁,他心系的明王朝早已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破潼关,明朝政权危在旦夕。虽在京中为官仅一年,陈洪绶凭借画艺,已是名声显赫①。明朝覆灭之际,陈洪绶只能离京返乡,他一生对功名的渴望,终究还是破灭了。亦是此次沿运河南归途中,陈洪绶再次经过黄河,对奔涌的洪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流巨津》署款“老迟”,清顺治三年(1646),陈洪绶在山中躲避战乱时在云门寺出家,改号悔迟、悔僧。孟远《陈洪绶传》载:“大兵渡江东,即披剃为僧,更名悔迟,既悔碌碌尘寰致身之不早,而又悔才艺誉名之滋累,即忠孝之思,匡济之怀,交友语言,昔日之皆非也。”可见,陈洪绶借以“悔迟”二字,抒发对明王朝、对自己多舛的仕途的感慨。所以“老迟”应为陈洪绶晚年所用字号,由此推断,此画应作于1643年至1646年间。这段时期正处于明末清初之际,面对山河破碎,清军暴虐,陈洪绶在动荡的岁月作《黄流巨津》,借以洪流巨浪中渺小的舵手自比,只能随着乱世的狂浪颠沛流离,以“老迟”为号抒发自己的故国之殇。
陈洪绶晚岁画风的嬗变在《黄流巨津》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从点缀到主体:装饰意味的强化
陈洪绶作品中蕴涵的装饰性美感见诸山水、人物、花鸟等各个领域。作品《无法可说》中以变形夸张的手法表现古拙奇崛的特征,描写罗汉拄杖坐于大石上,对面跪拜一人,衣饰长摆,充满异国情调,表现衣纹的线条颇具装饰趣味。《湘夫人》画面中湘夫人以背影示人,画家夸张地表现飞舞的衣裙飘带,使得画面逸趣横生。装饰性的美感表现虽是陈洪绶一贯使用的艺术手法,但早期多在画面中作为别有心意的点缀出现。而在《黄流巨津》中,陈洪绶却用大面积的装饰手法表现翻涌的浪花,占据了主要的画幅,这是陈洪绶前所未有的尝试,同样也为观者带来以往中国画从未有过的视觉冲击。
类似这类大胆地尝试,在陈洪绶晚年的作品中多次出现。同样以“老迟”署款的《老莲洪绶仿赵千里笔法》,与《黄流巨津》应作于同一时期。画面中仿宋人赵伯驹青绿山水的创作手法,以石青、石绿表现山石,特别的是在天空的部分却以空白几块分割的飘带形式表现云,让整个画面兼具重彩和淡彩,色彩简约概括却富有装饰性。另一幅作品《高梧琴趣图》,高居翰推断为陈洪绶晚年的作品,画家以夸张的手法处理,平面化的宽叶树,连同以装饰性线条所勾勒的盘旋在林树之间的云雾,作为画面的主体,颇有荒谬讽刺的意味。这种风格的变化,与陈洪绶晚年悲惨的经历不无相关。经历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家国覆灭、仕途无望,战乱与躲避中苟活的陈洪绶只能寄情笔墨,用尖酸古怪却又不落俗套的风格抒发心中的愤懑。
2.曲折到圜转:线描风格的成熟
《黄流巨津》中大面积的装饰图案,带来的视觉冲击实则发端于陈洪绶线描风格的成熟。他的弟子陆薪曾经称其师线描为“无粉本,自顶至踵,衣褶盘旋,常数丈一笔勾成,不稍停属”②。《黄流巨津》中线条的表现值得仔细品味,大面积地单纯用线条塑造浪花,线条的粗细、浓淡,排列的疏密、方向,用笔的疏朗、回转,都显得至关重要。稍有差池,画面便会显得杂乱,而失了水流翻腾的运势。这对画家对画面的掌控能力亦是极大地考验,可见陈洪绶晚年对线条的把握和理解愈加精深。
陈洪绶19岁时创作的《九歌》,其中《屈子行吟图》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画作中屈原衣褶的线条表现采用“莼菜条”的线描方法,行笔提按节奏鲜明、迅捷、粗细有致,翻卷过渡自然,停顿曲折有度,线形饱满。随着画家对线条运用的成熟,这类线描的运用逐渐减少,更多运用承袭顾恺之、李公麟的“游丝描”。1642年,陈洪绶被召为中书舍人后,皇帝命他临摹历代帝王像,他因此机缘得以遍览宫中藏画,画技有了极大提升。陈洪绶晚年作品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这种变化,线条由粗阔柔软变得细劲内敛,如蚕之吐丝,高古超忽,富有装饰性。《黄流巨津》中线条的表现谨细均匀,婉转流畅,尽显“运毫圜转,一笔而成”之意。陈洪绶虽师顾恺之之法,却并未全盘效仿,圆转重复的线条更具装饰性原则。在另一幅山水册页《仿李唐笔意》中,山石、河流的表现均用纤细流畅、反复圜转的线条勾勒,高古奇骇的韵味充盈在画面当中。
3.化俗为雅:创作手法的羽化
陈洪绶作为版画艺术家,在《九歌》《水浒叶子》等贴近市民生活的版画作品中皆有精彩绝伦的绘稿。叶子作为纸牌、行酒牌的娱乐用途,使陈洪绶的艺术风格也被贴上了“通俗”的标签。在晚明画坛,董其昌“南北宗论”的思想一度占据主流位置。在董其昌看来,南宗画是文人画,注重天趣;北宗画是院体画,注重功力。他认为画的最高标准是“淡”,要以静气写胸中丘壑。北宗画虽然精致,但却缺乏趣味,因此他崇南抑北。赞成董其昌一派,注重天趣的文人画家对“俗气”的主题、内容更是贬抑的。陈洪绶却不以为意,那些画家们避之不及的“粗俗”,却是他的一大“追求”。他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通俗文化在他的笔下变得更具深度,更精致,流露出的叛逆和讽刺意味使画面奇趣无穷。正如《黄流巨津》,一反前人画水的程式,创作独特的图案化装饰纹样表现波浪,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工艺美术作品中的纹样表现,总是难以摆脱庸俗、板滞的桎梏。陈洪绶却再发挥他点石成金的能力,“粗俗”化为雅趣,装饰性的画面让他经营的如此灵动、活泼。诚如高居翰所说,那些无知拙劣的画风,在他的笔下呈现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艺术形式③。

[明]陈洪绶 黄流巨津 30×25cm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到了1651年,陈洪绶再一次为木刻版画《博古叶子》绘稿,线条的老辣、布局的平衡,他“化俗为雅”的艺术造诣已经是更上一层楼,将通俗的市民文化拓展了更深刻的内涵④。在他晚年所作画论中,或许能对他的艺术思想窥探一二:“然今人作家,学宋者失之匠,何也?不带唐流也。学元者失之野,何也?不溯宋源也。如以唐之韵,运宋之板;以宋之理,行元之格,则大成矣。”⑤这篇画论中明确地表达了陈洪绶对董其昌“南北宗论”的不赞同,也是他艺术思想的进一步深入。他认为精致细腻的宋画是可取的,今人仿宋画显得刻板、矫饰是缺失唐代灵动的风韵。陈洪绶推崇和模仿宋画的同时,亦蕴涵他深刻的思考,细腻精致的宋画之风经他之手,虽具装饰意味,但不板滞、不淫巧、不媚俗,高古奇骏、妙趣横生、气象万千。
创作于明末清初之际的《黄流巨津》是昭示陈洪绶晚岁画风嬗变的代表作品。装饰性画法从画面中的点缀到成为主体,画家在现实生活中压抑与苦闷只能寄情笔墨,绘画风格愈发乖张、大胆。从曲折凌厉的“莼菜条”到细劲圆转的“游丝描”,线描的成熟是画家体悟世事、磨去棱角后的融通洞察。化俗为雅的不懈追求,是画家艺术思考的升华,如同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虽处身乱世,仍洁身自好。陈洪绶人生最动荡时期的心路历程,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皆有迹可循,这也是艺术史彰显的意义。■
注释:
①樊烨《陈洪绶生平事迹考》,浙江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
②樊烨《陈洪绶的绘画风格与晚明装饰艺术》,《艺术设计研究》2019年第3期。
③高居翰《山外山:晚明绘画(1570-1644)》,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
④周凯盈《陈洪绶〈博古叶子〉与晚明市民美学研究》,台湾成功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⑤[明]陈洪绶著、[清]陈字辑《宝纶堂集》,康熙四十四年(1705)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