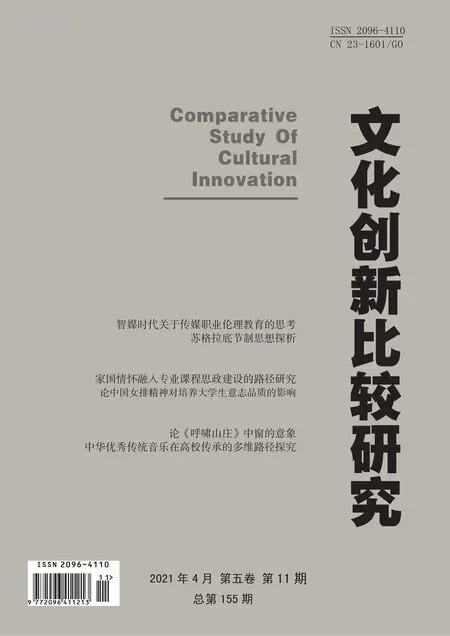文化比较视阈下看辛弃疾的自我救赎
2021-03-07范萌
范萌
(宁夏大学,宁夏银川 750000)
关于辛弃疾的赋闲之词尤其是农村词历来有颇多争议。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该文所指赋闲之词,是辛弃疾退居带湖和瓢泉期间所作之词,这些词作是词人情绪抒发的直接窗口,具体词做参考了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通过较权威的平台如“中国知网”等检索相关文献,有近百篇关于辛弃疾农村词的研究著述,其中收录最早的是王永健在1978年发表的题为“试论辛弃疾及其《稼轩词》的局限性”,文章中关于辛弃疾在江西赋闲期间“消沉感伤,逃避现实,产生消极虚无主义”的思想倾向和内容上“美化农村生活,粉饰太平”的看法代表了一类学者的观点;除此之外,更多的学者则将关注点放在了这些赋闲词的背后意蕴上,他们从词人的爱国情怀出发,着眼于对词人进退维谷的矛盾和痛苦心理的探究,认为词人表面悠闲自得的赋闲生活实则充斥着一腔忠愤的呐喊。
《约翰·克里斯多夫》 是罗曼·罗兰构思于1890年,创作于1902年至1912年的英雄主义长篇小说。克里斯托夫虽是以贝多芬为原型创造的文学形象,但他身上表现出的斗争精神和宛若莱茵河般蓬勃的生命力却是作家着意塑造的“文学典型”,而其所具有的英雄主义精神也成为“统摄其整个生命的‘总特征’”[1]。
联想到同为英雄的克里斯托夫在痛苦中淬炼最终完成的自我救赎,辛弃疾被迫赋闲的20 余年是否始终如上述观点认为的那样消沉感伤,充满痛苦?他在这段时光中是否也有过类似的自我救赎? 下面运用文化比较的方法,通过运用探究得到的克里斯托夫在痛苦中完成自我救赎的启示,结合争议较多的辛弃疾在带湖、瓢泉赋闲期间表现出的思想倾向和所作农村词从自我救赎的角度展开分析,对上述疑问做出探究。
1 沉浮痛苦中
罗曼·罗兰这样描述婴儿时期的小克里斯托夫,“一种说不出的痛苦从小生命的内部向外迸发了……痛苦就像他自己的生命一样漫无边际”[2]。痛苦似与生俱来,甚至构成了他的生命:给予他启蒙的祖父去世;初尝爱情的甜蜜在羞辱和奚落中戛然而止;想唤醒德国艺术的追求被所有人嘲讽;父亲醉酒溺亡,朋友、母亲的相继离世。极端的痛苦让他不止一次想过逃避,在与命运抗争的你来我往中,克里斯托夫走向了“自我救赎”之路。
同样辛弃疾“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失意痛苦也早已被注定。“辛弃疾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3]深受儒家修身治国和祖父誓收国土思想的影响,辛弃疾不仅有着比平常儒士更强烈的进取心和民族责任感,还有着难得的英雄意识。可这样一位文武兼备将“收复故土” 作为毕生追求的爱国英雄,注定无法在宋、金双方长期对峙和南宋朝廷软弱虚伪的时代悲剧下实现抱负。
辛弃疾自北方南归后,虽有雄心壮志但怎料宋廷始终对他不够信任,与他希望的“可以用之尊中国”[4]相差甚远;与此同时,朝野上下也对他充满歧视,词曰“长门事,拟准佳期又误。峨眉曾有人妒”[5]这些都让他倍感愁苦。淳熙八年末(1181年),时年四十一岁的辛弃疾被弹劾罢官至带湖退居,此后22年里除一次短短3年的出仕外,这位有着鸿鹄之志的英雄词人只得与山水为伴到生命末刻。从四十一岁到六十三岁,从带湖到瓢泉,英雄词人辛弃疾生命的悲剧色彩愈加浓重,虽然他在极力用“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儒家经义宽慰自己,但长达十余年的闲置还是给予了他难以愈合的创伤,这点从词风的转变上便可窥探。“辛弃疾退居带湖后的创作与此前的一个明显不同,是在其雄奇刚健的词风中出现了疏旷、谐谑和幽默的色彩。”[6]叶嘉莹先生也在《论辛弃疾词的艺术特色》中论证了这一点“借俗语之游戏性质表现了自己的嘲讽和悲凉……表现出一种反讽的作用”。内心的无限悲郁在当时“娥眉曾有人妒”的严峻政治生态下无法直接纾解,便以一种自我嘲笑的态度和方式一一道出。退居之初所作[水调歌头](“白日射金阙”)便是体现:“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杯……白发宁有种? 一一醒时栽! ”初居带湖的辛弃疾心中就是这样的苦闷,正值壮年看着时间染白头发却无法“谈笑挽天回”的他,在酒醉中逃避现实和痛苦,词风也带着饱含辛酸苦涩的谐谑。
2 万事几时足,日月自西东
罗曼·罗兰曾说: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命的真相后依然选择热爱它。克里斯托夫便是穿越痛苦中获得重生:将要自尽时,山光水色的感召唤醒了他对生命的热爱;醉酒沉沦时,不甘堕落的纯洁内心制止了他;遭受爱情伤害时,舅舅帮助他指明前路;朋友亲人们的相继离世,投身音乐创造给予了他无限力量与宽慰。这些或源自内心或来自外界帮助的力量,都是克里斯托夫为实现“自我救赎”所作的努力。没有人可以无限制地承受和化解痛苦,曾经的克里斯托夫把与痛苦斗争当作掌握自身命运的方式,直到他于世再无牵挂和束缚,终于体悟到和谐宁静时才认清生命的本质: 原来痛苦和欢乐就是生命的两面,正如光明和黑暗在一天中的此消彼长,痛苦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克里斯托夫终于明白了,“只靠意愿并不能斗争。一定要向高深莫测的上帝低头……人的意志不能胜天”[7]。认清这一事实后,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在内心向痛苦和生命的无常臣服,顺随生命流动,并在当下时刻尽可能地采取积极行动来避免深陷痛苦之中[8]。这才是唯一结束痛苦的方式,也是最终的救赎。
带湖赋闲的时光转眼过去了多半,同克里斯托夫一样,辛弃疾也在与痛苦的抗争中逐渐接受痛苦,开始懂得所谓“世事无常”的真谛。作于绍熙二、三年(1191 或1192年)的[水调歌头](“万事几时足”)体现了这种改变。这时,距离他初到带湖已经过去了十年:
“万事几时足,日月自西东。无穷宇宙,人是一粟太仓中。一葛一裘经岁,一钵一瓶终日,老子旧家风。更著一杯酒,梦觉大槐宫。
记当年,哧腐鼠,叹冥鸿。衣冠神武门外,惊倒几儿童。休说须弥芥子,看取鹍鹏斥鷃,小大若为同?君欲论齐物,须访一枝翁。”
可以从词中看出,老庄和佛教思想对辛弃疾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大来帮助他平复心绪。词的上片词人即表达了宇宙无穷,时光飞逝,不必太过于执着万事满足和得失的思想。词的下片“记当年,哧腐鼠,叹冥鸿”两句,词人回忆了自己当年“壮声英概”南归面圣的壮举和后来归隐的曲折人生,接着发出“休说须弥芥子,看取鹍鹏斥鷃,小大若为同? ”的感叹。词人认为,不要比须弥和芥子谁大谁小,也不要说鹍鹏和斥鷃谁高谁低,它们应该都被同等看待。这里词人对小大之辨的看法,其实也是自我对生命认知的转变,从前认为戎马一生是光荣,而归隐山水是落寞,心里自然充满不甘失落;如今在山水中渡过了近十年,在老庄思想和自然的陶冶下对生命追求的高低、大小也有了新的看法,在不同的境遇顺随生命而为,大小自然无异。这时的辛弃疾已逐渐向痛苦臣服,倾向老庄思想不是逃避反而是积极找寻的自我救赎。
除了寻求思想上的救赎,辛弃疾也像克里斯托夫一样在对生命的热爱中找到了慰藉和解脱。备受争议的农村词正是辛弃疾为摆脱痛苦而采取积极行动的例证。在老庄思想中寻到豁达平静思想的辛弃疾,用热爱生命的眼睛在农村生活发现了美与感动,正如这首[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
“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殷勤谢却甑中尘。
啼鸟有时能劝客,小桃无赖已撩人。梨花也作白头新。”
这首词作于词人闲居瓢泉六年后,是少有的展示农民生活的词作。上片的叙述与下片的写景相结合,表达了词人和农民的快乐心情。“村中的父老们争着说今年的雨水均匀,眉头也不像去年那样紧蹙。甑中有了粮食,由衷地高兴起来。鸟儿欢快地鸣叫仿佛在劝我多喝几杯,初生的桃花顽皮可爱惹人喜爱,梨花也多了一头雪白的头发”。词的上片再现了风调雨顺时农民的激动心情,下片运用拟人的手法,借乐景更衬托喜悦心情,足也感受到词人发自肺腑的高兴。这首农村词正是词人完全融入农村生活,热爱生活的表现。类似的农村词还有[玉楼春](“三三两两谁家女”)中重现农村女子的生活场景,也体现着词人观察生活,积极适应农村生活的转变。对生命的热爱让辛弃疾在农村生活中找到了慰藉,这点从山水景物词也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因此,辛弃疾在与自然的相处中愈发从容自在。直到六十四岁的再次被召打破了他好不容易寻得的宁静,一生的理想和愿望在最后一次宦游中破灭,这位心怀天下,文韬武略的英雄词人在无尽的悲愤和遗憾中走完了曲折起伏的一生。
3 比较与反思
通过回忆分析克里斯托夫和辛弃疾的救赎之路,我们不难发现其异同点。同样具有英雄主义精神的二人,在遭遇痛苦中都会经历由消极逃避到接受现实并积极采取行动,最终不再畏惧痛苦从而收获内心宁静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正是“自我救赎”。他们顺势而为,在逆境中尽其所能地行动起来,或投身于音乐创作在创造中感受欢乐,或倾心于哲人思想在探求中找到治愈心灵的良方,同时二者也都展现出了热爱生命的力量,即在痛苦中发现美的力量以重审他们的人生。因此,辛弃疾投身于乡村生活,歌颂山水自然的词作并非是“消极懈怠”,反而是在逆境中不消沉,尽可能排解痛苦适应现实的表现。
但与克里斯托夫不同的是,辛弃疾并未完全获得内心的宁静完成他的自我救赎之路。与前者相比,后者的“救赎”之路更具有阶段性和反复性,这更像是在岸边短暂停泊便再次投入风浪的帆船。这点是有现实原因的,一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纵然其中有进退有适的通达思想,但其着眼点还是在于强调儒士们入世以平天下的担当意识,因此纵然有老庄思想的慰藉和陶潜为标榜,深沉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责任感还是让他无法彻底在归隐中静心,自然他的情绪和痛苦也会随着一次次入世,被弹劾而起伏,这时的救赎只是短暂的歇息,而非永久的宁静。二是由于多变的外部环境。克里斯托夫需要战胜的只是不知如何从痛苦抽离的自己,而辛弃疾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情况。这痛苦不仅来源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还有屡次启用却未对之真正信任的南宋朝廷。试想,经过赋闲生活逐渐平和的内心,因重新被启用而看到希望重燃斗志,却又在短时间内被再次罢免,政局的风云变幻让词人原本和缓的心态难以安定,逐渐看清南宋朝廷的辛弃疾在第三次出世和罢免的转换间内心已不再似原来那般起伏,但从他的绝笔“[洞仙歌]《丁卯八月病中作》”中“差以毫厘缪千里”可见,辛弃疾在临终时回忆自己的一生:开始相差一点,结果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这错误不论是年轻时选择离乡南归,还是第三次宦游选择相信权相韩侂胄,抑或是归隐时的大量饮酒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总之,这位伟大的英雄词人在生命结束前的这一刻,心里仍饱含痛苦和悔恨。因此,相比于克里斯托夫,辛弃疾并未完成“自我救赎”之路,终身在与现实造成的痛苦里相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