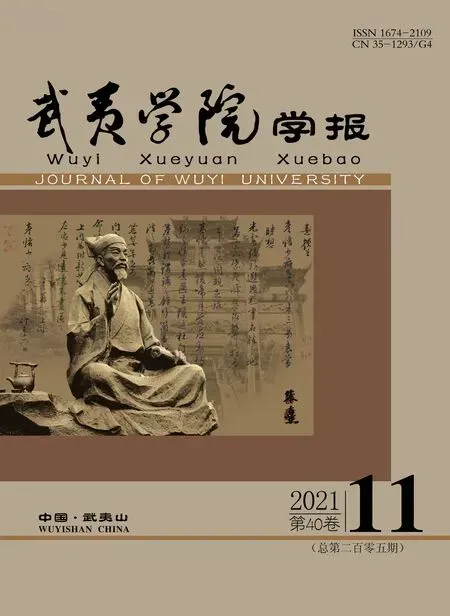董天工《武夷山志》版本流传及整理略论
2021-03-07陈迟
陈 迟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董天工《武夷山志》,汇集(明)衷仲孺《武夷山志》、(明)徐表然《武夷山志略》、(清)王梓《武夷山志》、(清)王复礼《武夷九曲志》编撰而成,是目前收集资料最全面、体例最完备的《武夷山志》,是了解武夷山地方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作者清人董天工(1703-1771),字村六,号典斋,福建建宁府崇安县曹墩(今福建省武夷山市星村镇曹墩村)人,民国《崇安县新志》第二十六卷《文苑》有传,董天工自幼生长在武夷山中,对武夷山的人文、地理环境十分熟悉。清乾隆十六年(1751),董天工因“旧志有四而板存其一,故多缺略不全,今汇辑四志合为一志,删其繁芜,补其缺漏”[1],在前代四部《武夷山志》的基础之上编撰了新《武夷山志》。
一、《武夷山志》之流传版本
董天工《武夷山志》于书目中著录情况如下。
《持静斋书目》卷二:“《武夷山志》二十四卷,乾隆十六年刊本,国朝董大工①修辑。”[2]
《八千卷楼书目》卷八:“《武夷山新志》二十四卷,国朝董天工撰。原刊本,罗氏重刊本。”[3]
《清史稿·艺文志二》:“《武夷山新志》二十四卷,董天工撰。”[4]
《崇安县新志·艺文》卷十八:“《武集山志》②二十四卷,清董天工撰。”[5]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武夷山志》二十四卷,道光丁未(1847)重刻本,清董天工撰。天工字典斋,福建崇安人。武夷山在崇安县南三十里,道书以此为第十六升真元化洞天。山周围百二十里,溪九曲,大峰三十六,相传昔有神人武夷君居此,故名。汉武帝尝祀之,见《史记·封禅书》,祀以干鱼,不知果何神也。是书据其凡例称,盖合衷穉生、徐德望、王适菴、王草堂,四种《武夷山志》,互参详订,汇成一编,共为二十四卷。其卷一曰总志上;卷二曰总志中;卷三曰总志下;卷四曰星野、形胜、祀典、敕封、九曲全图、九曲棹歌;卷五曰一曲上图附;卷六曰一曲中;卷七曰一曲下;卷八曰二曲图附;卷九曰三曲图附、四曲图附;卷十曰五曲上图附;卷十一曰五曲下;卷十二曰六曲图附;卷十三曰七曲图附、八曲图附;卷十四曰九曲图附;卷十五曰山北图附;卷十六曰名贤、理学、官守、主管;卷十七曰寻胜、卜筑、隐逸;卷十八曰方外、仙佛、羽流、释子;卷十九曰古迹、杂录、附录、物产;卷二十曰艺文、山记、游记;卷二十一曰艺文、杂记、序赋、赞、杂著,卷二十二曰艺文、骚曲、四言古、五言古、七言古、诗余;卷二十三曰艺文、五言律、七言律;卷二十四曰艺文、五言绝、六言绝、七言绝。篇中于九曲山北诸胜,既以诗文分隶,而后卷又出艺文者,缘此诸作,并浑题武夷则不能分隶于九曲山北诸胜之下,非重复也。至于卷首贤儒仙之绘像,实踵明徐表《武夷山志略》之谬,清《四库总目存目》,已讥其近于儿戏矣。”[6]
检《中国古籍总目》,《武夷山志》二十四卷首一卷,清董天工撰,今可考版本有:
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本;
清道光九年(1829)刻本;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五夫尺木轩刻本;
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清木活字印本。[7]
检索各大图书馆馆藏目录,可考版本还有:
《武夷山志》二十四卷首一卷,乾隆十九年(1754)刻本;
《武夷山志》二十四卷首一卷,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夫木轩刻本。
此外,《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武夷山志》二十四卷首一首卷,清董天工撰,清乾隆刻本。[8]
以上可知,董天工《武夷山志》书目著录版本与今本所存者同,无阙失之故。
据笔者考察,今存各类版本基本情况如下。
(一)乾隆十六年刻本
二十四卷首一卷。觐光楼藏板。版式:10行22字,小字双行,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卷首依次收入乾隆十六年来谦鸣《汇编武夷山志序》,乾隆十六年史曾期《重修武夷山志序》,乾隆十六年何瀚序,乾隆十六年董天工自序。其后为目录:卷首曰凡例、绘像;卷一曰总志上;卷二曰总志中;卷三曰总志下;卷四曰星野、形势、祀典、敕封、颁赐、九曲全图、九曲棹歌;卷五曰一曲上图附、诗文附;卷六曰一曲中诗文附;卷七曰一曲下诗文附;卷八曰二曲图附、诗文附;卷九曰三曲图附、诗文附,四曲图附、诗文附;卷十曰五曲上图附、诗文附;卷十一曰五曲下诗文附;卷十二曰六曲图附、诗文附;卷十三曰七曲图附、诗文附,八曲图附、诗文附;卷十四曰九曲图附、诗文附;卷十五曰山北图附、诗文附;卷十六曰名贤:理学、官守、主管;卷十七曰名贤:寻胜、卜筑、隐逸、节烈;卷十八曰方外:仙、佛、羽流、释子;卷十九曰古迹、杂录、附录、物产;卷二十曰艺文:山记、游记;卷二十一曰艺文:杂记、序、赋、赞、杂著;卷二十二曰艺文:骚曲、四言古、五言古、七言古;卷二十三曰艺文:五言律、七言律;卷二十四曰艺文:五言绝、六言绝、七言绝、诗余。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藏有乾隆十六年刻本。
按:天津图书馆影印本,来谦鸣《汇编武夷山志序》旁,有盱眙王氏十四间书楼藏书印,可知此书曾为王锡元藏本,现已经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七百廿四册。
(二)乾隆十九年刻本
二十四卷首一卷。觐光楼藏板。版式:10行22字,小字双行,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卷首序言依次为:乾隆十七年(1752)孙嘉淦序,乾隆十八年(1753)蒋溥序,乾隆十六年何瀚序,乾隆十六年来谦鸣序,乾隆十九年叶观国序,乾隆十八年史贻直序,乾隆十六年史曾期序,乾隆十九年杨锡绂序,乾隆十六年董天工自序。其后目录,编次与乾隆十六年刻本相同。目前,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陕西省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藏有乾隆十九年刻本。
按:笔者于陕西省图书馆亲见著录为乾隆十九年刻本的董天工《武夷山志》,以上版本信息均据陕图藏本。陕图藏本内封缺失,无法直接判定准确的版本信息,但其中最晚的序言为乾隆十九年,因此不可能为乾隆十六年刻本,且下文介绍道光年后出刻本均有道光年间新序,据此可排除为乾隆以后刻本的可能。又因陕图著录为乾隆十九年刻本的序言顺序与乾隆二十五年刻本不同,推断此藏本应为乾隆十九年刻本。根据陕图所提供的藏本电子信息:内封面镌“乾隆辛未新编/觐光楼藏版”,可知陕图藏本或许之前内封尚存,后不知何种原因导致缺失。如若陕图藏本确为乾隆十九年刻本,我们对照乾隆十六年刻本内容可知,乾隆十九年刻本应为乾隆十六年(即内封所题乾隆辛未年)刻本附上乾隆十九年新序刊刻而成。关于陕图藏本是否为乾隆十九年刻本,还应该亲阅其他图书馆著录的十九年刻本确定。鉴于目前笔者尚无法查阅其余著录为乾隆十九年刻本的电子版本或纸质版本,故此处存疑。
(三)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二十四卷首一卷。内封题觐光楼藏板,乾隆庚辰新编。版式:7行13字,黑口,四周单边,双鱼尾。卷首序言分别为:乾隆十七年孙嘉淦序,乾隆十八年史贻直序,乾隆十八年蒋溥序,乾隆十九年杨锡绂序,乾隆十六年来谦鸣序,乾隆十九年叶观国序,乾隆十六年何瀚序,乾隆十六年董天工自序。序言之后为目录,编次与乾隆十六年刻本相同。以上版本信息据哈佛燕京图书馆提供的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电子影像,卷首孙嘉淦序旁,有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珍藏印。哈佛燕京藏本无乾隆十六年史曾期序,疑为脱落或其他原因造成。乾隆二十五年刻本较为罕见,目前,上海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有收藏。
(四)道光九年刻本
二十四卷首一卷。版式:10行22字,小字双行,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检中文古籍数字图书馆提供的道光九年刻本电子版可知,卷首序言顺序为:乾隆十八年史贻直序,乾隆十八年蒋溥序,乾隆十九年杨锡绂序,乾隆十七年孙嘉淦序,乾隆十六年来谦鸣序,乾隆十九年叶观国序,乾隆十六年史曾期序,乾隆十六年何瀚序,乾隆十六年董天工自序,道光九年罗良嵩重刻序。卷首之后的目录编次,除诗余部分由乾隆十六年刻本置于第二十四卷调整为第二十二卷外,其余内容编次与乾隆十六年刻本相同。中文古籍数字图书馆提供的刻本目录中第二十四卷末提示有跋,但此本卷末并未见跋。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等均能查到道光九年刻本的馆藏信息。
按:笔者于陕西省图书馆亲见著录为道光九年刻本。此本内封缺失,因此无法通过内封判断刊刻时间。陕图藏本卷首序言编次为:乾隆十八年史贻直序,乾隆十八年蒋溥序,乾隆十七年孙嘉淦序,乾隆十九年杨锡绂序,乾隆十六年来谦鸣序,乾隆十九年叶观国序,乾隆十六年史曾期序,乾隆十六年何瀚序,乾隆十六年董天工自序,道光九年罗良嵩重刻序。其中,孙嘉淦序与杨锡绂序与前文所述道光九年电子版序言顺序颠倒。卷首后为目录,诗余著录在二十四卷,与前述电子版位于二十二卷不同。卷末有跋,为道光二十七年罗才纶重刻跋,其余部分与乾隆十六年刻本相同。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供的道光九年刻本信息可知,国图藏本卷末有罗才纶跋。据此跋可知,中国国家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所题为道光九年刻本实为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其余多家图书馆著录藏有道光九年刻本,根据其提供的刻本信息看,多数卷末有跋,我们可以推测多数图书馆可能将道光二十七年刻本误录为道光九年刻本,读者查阅时应予留意。
(五)道光二十六年五夫尺木轩刻本
二十四卷首一卷。内封题五夫尺木轩藏版,道光丙午年重刻。版式:10行22字,小字双行,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卷首序言次序为:乾隆十八年史贻直序,乾隆十八年蒋溥序,乾隆十九年杨锡绂序,乾隆十七年孙嘉淦序,乾隆十六年来谦鸣序,乾隆十九年叶观国序,乾隆十六年史曾期序,乾隆十六年何瀚序,乾隆十六年董天工自序,道光九年罗良嵩重刻序,卷末有道光二十七年罗才纶重刻跋。除第二十四卷末多出跋语外,道光二十六年刻本的目录编次与乾隆十六年刻本相同。据罗才纶重刻跋,称其父罗良嵩曾想重刻《武夷山志》,序言已写好,不料随后不幸逝世,没有刊成。因此罗才纶为完成父亲未竟之志,将《武夷山志》刻于羊城(今广东省广州市)。因刻本内封题为道光二十六年重刊,而罗才纶跋撰于道光二十七年,因此在著录时,根据不同的标准,或题为道光二十六年刻本,或题为道光二十七年刻本。但笔者于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查阅题为道光二十七年刻本时发现,罗才纶重刻跋置于卷首而非卷末,然而陕师所藏刻本的目录信息却与道光二十六年刻本完全一致,第二十四卷末仍提示有跋语。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推测是后来重刻,将原本置于卷末的跋语放置于卷首。目前,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均著录收藏。道光二十六年刻本在各类流传的董天工《武夷山志》版本中最为常见。
(六)同治十一年刻本
二十四卷首一卷。内封题五夫尺木轩藏版,道光丙午年重刻。可知同治十一年刻本根据道光二十六年书版重刻(罗才纶重刻跋置于卷首,与二十七年刻本同),但内容编次与二十六年刻本略有不同,诗余置于二十二卷而非二十四卷,与上述道光九年刻本同。卷末有同治十一年丁承禧重刻跋。
(七)清木活字印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供的清木活字印本版式信息为:11行24字,黑口,四周双边,单鱼尾。国图存卷11-24,共14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清木活字印本完整的二十四卷首一卷,无奈尚无电子版信息,笔者暂无法亲见,无从进行考述,仅留以存目。
二、《武夷山志》整理略论
整理出版古籍,应当挑选一个善本或通行本为底本,再以别本或有传抄因袭关系的其他古籍精校整理,现今整理董天工《武夷山志》亦如是。
从前文版本流传情况和现今尚存版本考察可知,清乾隆十六年刻本为最早刻本,多地图书馆均收有,较为易得,且被《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因此应当以乾隆十六年刻本作为出版点校整理本的底本。后出的几种刻本在全书的体例内容上没有作出大的改动,只增补了后人的序跋,因此整理本可参考后出的刻本补上其余序跋内容。
1997年方志出版社出版了点校本董天工《武夷山志》,在《点校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前言》中说明:“由于我们据以点校的董志重刻本,或漫漶、或残缺,或由于书匠、刻工的疏误,致有舛误疑难之处。为此,我们参阅对照了董志据以修撰的四本书——(明)衷仲孺《武夷山志》、(明)徐表然《武夷山志略》、(清)王梓《武夷山志》和王复礼《武夷九曲志》。”[9]整理本选用董志根据的四本山志进行对照,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然而,美中不足的是,1997年的整理本采用的底本是道光丙午年重刻本,不知何种原因,未能采用乾隆十六年刻本为底本进行点校。此外,整理本还保留了重刻本全部卷首序跋,但遗憾的是未收入同治十一年丁承禧重刻跋,出于保存原书面目的考量,再版或重新整理时应将丁跋收入。2007年方志出版社再版点校本董天工《武夷山志》,为尊重原刻本,将原来序跋中作者篆刻印章按原样补上,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是再版董志时,并未抽换底本,只是对原来点校中出现的讹误以及部分断句进行修订。
综上,今若重新整理董志或再版董志,笔者以为应当更换点校底本为乾隆十六年刻本,利用其余刻本进行对校整理,同时应补上同治十一年丁承禧重刻跋,力图保留董志后出刻本序跋全貌。笔者囿于学力,论述或有不当之处,敬请校正。
注释:
① 此处“董大工”应是“董天工”之误。
② 《武集山志》应为《武夷山志》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