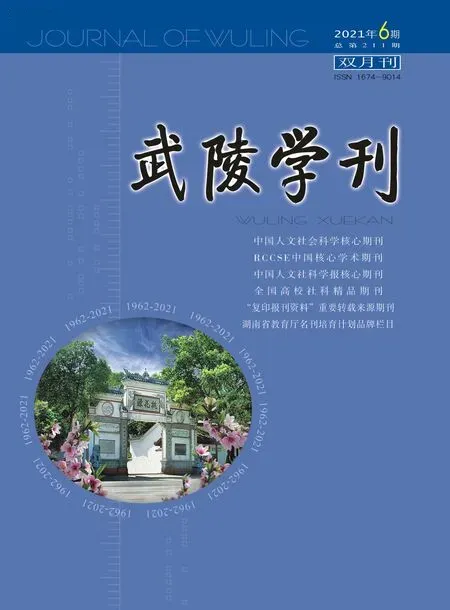论僧肇“有无之辨”对佛玄的融摄
2021-03-07张彤磊
张彤磊
(湖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0)
僧肇是我国东晋十六国时期著名的佛学理论家。他系统地阐发与弘扬了罗什所译传的“三论”及般若中观学理论,被罗什誉为“秦人解空第一”[1]。在印度大乘空宗般若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交流融汇的背景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色的僧肇,运用般若中观学理论与方法阐释魏晋玄学“有无之辨”,有效实现了般若学与魏晋玄学的深度融合,故会通华梵,“上承魏晋以来玄佛合流的遗风,下开佛教哲学在中土相对独立发展的先河”[2]46,其思想和思维方式对中国佛教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魏晋玄学“有无之辨”本体论思维的逻辑演进
魏晋玄学上承两汉儒道思想,下启东晋、南北朝佛学,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承环节。以“有”“无”概念自身的内在逻辑矛盾为中心,魏晋玄学“黜天道而究本体”[3],通过辨析“本末”“体用”“动静”“言意”“名教与自然”之关系,力求透过形而下的经验现象而直探天地万物之本体,从而摆脱了两汉经学神学化、形而下思维(宇宙生成论)的束缚,形成了以本体论思维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以魏晋玄学自身兴衰的历史为线索,根据魏晋玄学不同时期对“有”“无”关系的探讨,魏晋玄学经历了贵无论、崇有论、独化论三个发展阶段,并且,这三个阶段在魏晋玄学发展的历程中又构成了一个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历程[4]。
贵无论形成于正始年间(240—249),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主张“以无为本”。贵无论通过对“有无”“本末”“体用”“动静”等一系列范畴的辨析,论证现象世界纷纭变幻的“有”之所以为“有”,在于“有”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支撑“有”存在的真实不变、超言绝象的“无”。贵无论虽然突破了汉代宇宙生成论的思维模式,虚略于具体人事之知而究心于万物抽象玄理,把思辨的重心转移到形而上领域,形成了本体论思维方式。但贵无论的本体论思维还羼杂着“有始于无”的宇宙论生成论思维余绪,使得贵无论的本体论思维并不十分纯粹。定“以无为本”为基调,贵无论通过“崇本息末”沟通形而上和形而下、本体和现象以论证“名教出于自然”,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但形而上、抽象的“无”何以能作用于形而下、具体的“有”?贵无论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间存在的逻辑悬隔,使其割裂了有无之间的辩证关系而重无轻有,导致“口谈虚浮,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5]成为一时风尚。
贵无论之后兴起的玄学思潮是以裴頠为代表的崇有论。裴頠反对贵无论“以无为本”,认为“有”是宇宙万物的终极依据,“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6]328。针对贵无论“有始于无”的观念,裴頠认为“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6]328,认为绝对虚空的“无”不可能生成有具体内容的“有”。所以,裴頠认为“有”是“自生”,“有”自己就是自己存在的依据,“有”既是现象又是本体。然而,如果“有”既是现象又是本体,那么现象与本体之间复杂的关系如何通过这个孤立无耦的“有”来展开呢[7]?崇有论确立形而下的“有”为本体以维护名教,但因截断了有无之间的概念转换、混同了本体与现象之间的辩证关系,自然也无法从理论上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冲突。
面对贵无论和崇有论在“有无之辨”上的逻辑问题和理论对立,郭象以“独化”论对贵无、崇有之说进行了扬弃之后的综合。郭象深刻地剖析了贵无论“有始于无”的逻辑问题,认为“若无能为有,何谓无乎”[8]50,一方面,如果“有始于无”,那么作为这个能生成“有”的“无”必然从逻辑上要求有另一个能生成这个“无”的“无”,而这个“无”因被生成则成为了“有”;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无穷推论中我们根本无法寻求出作为世界万有终极依据的、绝对的“无”。同时,郭象也清晰地揭示了崇有论以现象之“有”为本体的逻辑矛盾,认为“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8]112,任一具体之“有”的存在需以其他具体之“有”为依据,所以“有”不能作为其他之“有”生成的依据或本体。郭象认为,“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8]112,“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8]251,万物皆是不假外物、绝对独立、自足其性的“独化”,且每个“独化”的“有”之间无本质的差别;而只有在“玄冥之境”才能洞见各个“独化”之“有”的无差别本质,从而体察天地万物俱一、名教自然和谐。这种“玄冥之境”也就是绝对的“无”。从魏晋玄学“有无之辨”本体论思维的逻辑进程看,“独化”论既贵无又崇有,形式上把“有无之辨”推向了高峰,但其“玄冥之境”也渐渐把魏晋玄学的本体论思维转向了对人生境界的追求与体验,在淡化了“有”“无”概念思辨的同时,部分放弃了对宇宙人生本质的形而上探求。
二、魏晋玄学“有无之辨”的境界论意义指向
以王弼为代表的贵无论在有无关系的辨析中已经涉及到概念自身的矛盾,“有”是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指一般或共相,而这个“有”因为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定性,所以又是“无”。但是,贵无论的“有无之辨”并没有像黑格尔构建的融辩证法、逻辑学、本体论为一体,从概念自身逻辑运动发展而来的纯粹原理系统那样发展。并且,贵无论“有始于无”的宇宙论生成论思维仍保留着道生万物、道先物后的经验性思维,使贵无论的本体论思维并不纯粹。裴頠的崇有论立足于经验世界的抽象之“有”来辨析有无,已经偏离了概念思维方式。郭象的“独化”论虽然以概念思辨的方式批判了贵无论“有始于无”、崇有论以现象之“有”为本体的逻辑矛盾,但作为“独化”论本体的绝对的“无”——“玄冥之境”,已经不再是通过概念思辨、逻辑推论而构建的纯粹原理系统,而是以主体之精神来泯灭客观现象之差别,超越本体与现象的悬隔。
由于概念思维始终受到经验性、形而下思维的制约,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辨”无法在理论上突破有无之间的概念转换,并未构建出一个依靠纯粹概念推演的逻辑体系来对待有与无、本体与现象的关系,导致以“有无”为中心而衍生的“本末”“体用”“动静”“名教与自然”等哲学范畴之间也缺乏必然的逻辑推论。所以,魏晋玄学家虽然追求本体与现象的圆融无碍、“体用一如”,但事实上采用了“举本摄末”“以体统用”的思维方式来对待有无本末、本体与现象。但作为纯粹的、超验的、形而上本体如何作用、显现于经验的、形而下的世界?经验世界的主体又何以、如何获得对本体的认知?这既是本体论思维,也是魏晋玄学“有无之辨”面临的共同问题。
面对上述问题,魏晋玄学以主客合一、超言绝象的一元性整体思维来直观世界万有、超越有无差别,实现本体与现象的圆融无碍,并在这一历程中体悟生命意义而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无论王弼的“得意忘言”探求的超言绝象的精神性本体“道”或“无”,还是郭象追寻的无言无意、无彼无此的“玄冥之境”,都是植根于超越语言、概念和逻辑的主客合一的直觉思维。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辨”从有无概念思辨转向主客合一的直觉思维,预示着魏晋玄学的致思方向由外逐步向内转移,即由讨论外在的客体问题转向内在的主体问题,亦即由客体本体论的探讨转入对主体本体论的探讨[9]。这种致思路径实质上是复归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习惯,即把部分经验性的认知以直觉的方式升华为客观普遍性真理、宇宙万物之“道”而贯穿于自然、社会和人生,主体以主客合一的直觉思维在体“道”的历程中,以直观化解矛盾、以境界取代认识,“与道为一”“体道成圣”,从而体悟超越的精神生活和人生境界。
三、僧肇对魏晋玄学“有无之辨”本体论思维的般若化阐释
僧肇是什门高足,深谙般若中观学要义。在玄佛合流的背景下,僧肇对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辨”进行了般若化阐释,以般若中观学的理论与方法批判了“六家七宗”解空的“偏而不即”,消解了魏晋玄学有无悬隔的逻辑问题。
般若中观学是通过“缘起性空”和“性空幻有”两个同时互存的命题,阐明诸法的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关系,来探究“诸法”的最高真实——“诸法实相”。“缘起性空”是指世间万象都依赖一定的条件而存在,故缘起事物既无独立、实在的自体,也无恒常、主宰的自性,所以缘起事物本质性空。“性空幻有”是指缘起事物虽然本质性空,但缘起事物的现象(假有)存在故非绝对的虚空。基于“诸法实相”原理,般若中观学以“中道思维”作为方法论原则,通过荡相遣执,双遣双非,破邪显正,不落两边,层层破斥缘起事物之自性以及人类理性思维之虚妄,逼显出诸法“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空有相即的真实本相。
对于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辨”,僧肇是以“诸法实相”作为“真”的判断标准,将魏晋玄学“有无”问题纳入“真假”视域之中,通过辨析“有”与“真有”、“无”与“真无”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来阐明般若中观学之有无相即、本质与现象不二义。僧肇说:
欲言其有,有非真生;欲言其无,事象既形。形象不即无,非真非实有。然则不真空义显于兹矣。[10]146
寻夫立文之本旨者,直以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耳。何必非有无此有,非无无彼无?[10]144
缘起事物本质性空,故非有;缘起事物的现象存在但不是真的存在,故非“真有”;“非有非真有”是否定缘起事物有之自性而并非否定有之现象。缘起事物的现象存在,故非无;缘起事物本质性空但不是绝对虚空,故非“真无”;“非无非真无”是否定绝对虚空而并非否定缘起事物本质性空。所以,缘起事物是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有非定有,无非实无,故“不是真空”。
僧肇阐明的是,空有是“诸法实相”的一体两面,只有运用“中道思维”从空有相即、现象与本质不二的角度,以“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方法对待有无关系,才能真正地把握“诸法实相”。所以,僧肇指出本无宗“触言以宾无”[10]144,是因为本无宗把有无关系归于“无”,肯定“真无”而把“无”实体化、本体化;批评心无宗视有为“真有”,只是以心虚物,没有认识到万物本质性空,故“失在于物虚”[10]144;认为即色宗虽然主张“色不自色”、有非“真有”,但“未领色之非色”[10]144,与“当色即色、当色即空、色空不二”的“中道思维”尚存距离。
虽然“僧肇的‘不有不无’的‘不真’之‘空’……都没有提到过有既是有,同时又不是有,而是有的自我否定即无”[11],并没有从概念思辨上讨论“有”“无”关系,但是当僧肇以般若中观学“诸法实相”作为真假判断标准,并引入“真有”“真无”概念,对于破斥“六家七宗”乃至魏晋玄学或以“有”为“真有”,或以“无”为“真无”的观念,是具有巨大的穿透力的。因为当“有”非“真有”,“无”非“真无”时,偏执于有无任何一方自然就失去了理论依托。同样,当僧肇基于“诸法实相”原理和“中道思维”原则以空有不二、本质与现象相即来对待魏晋玄学有与无、本体与现象之间的悬隔时,横亘于魏晋玄学“有无之辨”的逻辑矛盾,也自然迎刃而解了。在此理论背景下,由魏晋玄学“有无之辨”衍生而来的动静、本末、体用乃至主客等诸多对立都可以在有无相即的背景下以即动即静、即本即末、即体即用、即主即客等予以消解;而且,本质即现象、现象即本质,也为“体用”架构下由用显体,以体摄用,体用之间的互回、相即提供了理论资源。所以,从理论和理论应用层面看,僧肇无疑将魏晋玄学以本体与现象关系为核心的“有无之辨”推向了新的高度,故汤用彤先生评价僧肇之学“已谈至‘有无’‘体用’问题之最高峰,后出诸公,已难乎为继也”[12]。
四、僧肇般若化“有无之辨”的魏晋玄学境界论致思理路
涅槃是佛教修行的最终目的,也是解脱的最高境界。僧肇对魏晋玄学“有无之辨”的阐释也最终落脚于证悟涅槃的致思方式上。般若中观学基于“中道思维”原则将涅槃与世间的关系表述为“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13],涅槃与世间相即不离。僧肇以般若化“有无之辨”进一步阐述了涅槃超越有无又不离有无的体性。僧肇说:
是以论称出有无者,良以有无之数,止乎六境之内,六境之内,非涅槃之宅,故借出以祛之。庶悕道之流,髣髴(仿佛)幽途,托情绝域,得意忘言,体其非有非无,岂曰有无之外,别有一有而可称哉?经曰:三无为者,盖是群生纷绕,生乎笃患。笃患之尤,莫先于有;绝有之称,莫先于无。故借无以明其非有,明其非有,非谓无也。[10]162
涅槃非有非无、超言绝象、非俗谛所能言诠,“岂曰有无之外,别有一有而可称哉”?并不是说在有无之外存在一个真实的涅槃。言涅槃无,是借以阐明并非存在一个真实的“涅槃”,“故借无以明其非有”;说涅槃非有,也不是彻底否定涅槃不存在、是真的无,故“明其非有,非谓无也”;所以涅槃非有非无而又不离有无,并非离开有无之外另寻一个涅槃妙道。
既然涅槃与现实世界相即不离、涅槃和现实世界之间并非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证悟涅槃无须如小乘佛教视涅槃和现实世界决然对立,执著于灰身灭智、断灭生死而苦求涅槃。僧肇说:
是以圣人乘千化而不变,履万惑而常通者,以其即万物之自虚,不假虚而虚物也。故经云:甚奇,世尊!不动真际,为诸法立处。非离真而立处,立处即真也。然则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10]146
圣人之所以乘顺现象的千变万化而不受影响,身处世间万般惑见之中而始终通达无碍,是因为圣人洞鉴“即万物之自虚”,非否定万物来明空。所以佛经说:世尊,真是奇怪。诸法实相才是诸法的依据。不变的真际(诸法实相)是诸法的依据。并非离开真际(诸法实相)而为诸法别寻依据,诸法当下即真际(诸法实相)。既然如此,道是否遥不可及?诸法当下即诸法实相。圣人是否遥不可及?若能体悟诸法当下即诸法实相,随时随处就可洞鉴圣人玄妙的精神。
僧肇阐明的是,诸法即现象即本质即空,诸法实相并非外在于事物,而就在事物自身中呈现,任何事物都体现诸法实相,故“立处即真”“触事而真”;那么,世俗世界和真实世界亦无悬隔,证道成佛也并非遥不可及,只要洞彻诸法实相妙理,随时随处即可体道成圣——“体之即神”。通过即空即有、真俗不二的“中道思维”,僧肇把神圣的彼岸世界拉回到世俗的此岸世界,同时也具有把世俗的此岸世界转化为神圣的彼岸世界的可能。所以,在当下现实世界证悟涅槃、成就解脱大道,也自然成为逻辑的必然。
经过上述转换,僧肇以般若智慧在世间直观“诸法实相”而证悟涅槃、“体空成佛”,与魏晋玄学追求“与道为一”“体道成圣”的境界论就具有类似的思维方式与内涵。但是,僧肇基于般若学诸法非有、毕竟空义,与老庄玄学主张万物非无、道体恒存有着根本的差异,所以,僧肇“体空成佛”、证悟涅槃在思维方式与境界表述上虽类似于魏晋玄学的“体道成圣”,但二者对宇宙人生追求的意境可谓同工而异曲。魏晋玄学表达的是以物我两忘而物我玄同而体“玄冥之境”;僧肇表达的是以物我俱空而物我俱一而悟涅槃空境。对此,洪修平指出:“僧肇使用了老庄‘物我俱一’的命题,表达的却是冥心真境、有无皆空的佛教般若思想。他的‘物我俱一’是‘相与俱无’,是主客观的泯灭,也叫做‘智法俱同一空’。佛教般若学虽然讲物我俱空,但一般并不讲物我为一。老庄讲物我为一,却并不说俱同于一空。僧肇的思想把老庄的命题和佛教的思想融合到了一起。”[2]51
综上所述,僧肇将魏晋玄学“有无之辨”的本体论思维纳入般若中观学“诸法实相”原理和“中道思维”原则下,以有无相即、本质与现象不二消解了魏晋玄学有无二分的逻辑问题,把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辨”推向了最高峰。在证悟涅槃方式上,僧肇沿着魏晋玄学“有无之辨”的境界论意义指向,将魏晋玄学在世间实现精神超越的致思理路渗透于般若中观学的解脱之道,从而把魏晋玄学“体道成圣”的人生追求转换为般若中观学“体空成佛”的涅槃境界。经过上述两层异同之间的相互融摄交流,僧肇般若化的“有无之辨”成功地实现了般若学与魏晋玄学在思维方式和内容上的深层转换,也标志玄佛融合汇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