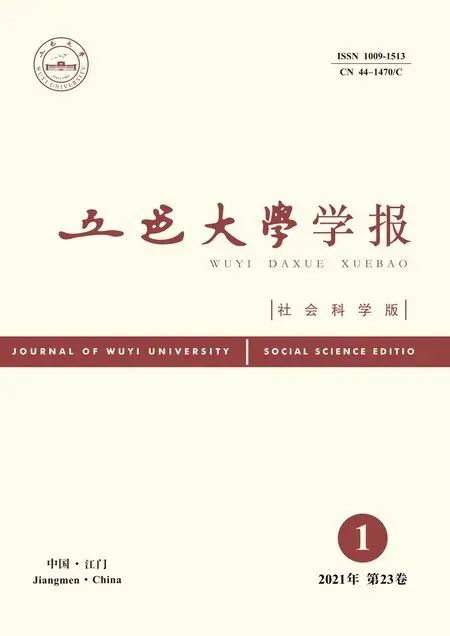陈白沙的家风与学风
2021-03-06刘红卫
刘红卫
(五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陈白沙在教育子弟与学生方面是相一致的,陈白沙的家风与学风是相贯通的。陈白沙的家风与学风对江门学派及明朝中后期儒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江门学派继承了陈白沙的家风与学风,在明朝中后期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江门学派与阳明学、阳明后学是明代心学的两大流派。江门学派与阳明学、阳明后学产生分歧的焦点是儒学的体认、体证工夫与学风的不同,阳明学以单提直指、直接指向良知为特点,在工夫论上以正念头为核心,强调儒学体证的易简性。江门学派则以“随处体认天理”为治学的基本方法,遵循以道体诠释心体的路径,强调笃实的体证对成就圣人人格的意义。阳明学、阳明后学以正念头为核心的工夫论体系具有重内轻外的倾向,这种倾向在道德实践过程中容易产生一种弊端,即有可能认知觉为性,进而造成工夫论上的浮光掠影、本体论上的玩弄光景。明朝晚期阳明后学中出现的流禅、狂肆倾向,就与阳明学易简的教法有关。江门学派在随处体认天理的治学方法及以道体诠释心体的体认路径下,以道体中正、自然的特质阐释心体中正、自然的理念,科学地阐发了心体的内涵和本质。同时,笃实的体认、体证使江门学派避免了工夫论上的浮光掠影。对工夫论及本体论的科学阐发使江门学派沿着正确的路径健康发展,黄宗羲最终在江门学派中正、自然的理念基础上提出了反君主专制的民主思想萌芽,将儒学的发展推向高峰。在陈白沙的家风、学风中,学风是贯彻孝、义的保障,体证的笃实性保障了孝、义的切实贯彻,充分体现了陈白沙及江门学派一以贯之的学术风格。
一、 孝道思想是陈白沙家风与学风的哲学基础
陈白沙以“敬”作为孝的本质内涵,主张孝敬父母或者长辈要尽心适可,强调“善养”重于“禄养”。孝敬父母是陈白沙家风、学风最基本的内涵。陈白沙是遗腹之子,他的母亲含辛茹苦将其养大,他对母亲的感情很深。陈白沙的《乞终养疏》云:“臣父陈琮年二十七而弃养,臣母二十四而寡居,臣遗腹之子也。方臣幼时,无岁不病,至于九岁,以乳代哺。非母之仁,臣委于沟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视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爱虽一,未有如臣母忧臣之至、念臣之深者也。”[1]2陈白沙九岁时,母亲仍然以乳代哺,这使陈白沙母子之间的情感更深一层。陈白沙母子之间母慈、子孝的情感之真切,必然蕴涵了陈白沙对母亲的敬仰之情。敬既是孝之真的呈露,又是孝之真的扩充而升华至人性之本真,是对人性本真、本质的敬重与敬仰。陈白沙认为敬是孝的本质内涵,它既源自于血缘亲情,又超越了血缘亲情而成为对人性的敬仰。因此,主敬是陈白沙心学的核心工夫。张诩在《白沙先生行状》中描述了他敬以侍母的情状。《白沙先生行状》云:“孝悌出于天性,事太夫人甚谨。太夫人非先生在侧则不食,食且不甘。先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辄心动急归,果然。母爱子慕,惟日不足。”[1]873陈白沙不仅谨慎地侍奉母亲,对兄长同样如此,张诩云:“事伯兄如父,坐必隅坐。”[1]874为什么陈白沙强调要以“敬”作为孝的核心内涵呢?这是因为一个人从小受父母的哺育之恩,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在娶妻生子之后,对父母的情感会渐趋淡薄。惟有敬方能使孝的真情实感得以升华。一方面,敬是对父母、长辈的尊敬、敬仰,另一方面,敬是对人性本质、本真的敬仰、敬畏,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对父母或长辈的“永慕”之情。陈白沙《永慕堂记》曰:“予幼时读《孟子》:‘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羡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窃疑孟子之言扬抑太过。爱亲,人子之至情也,不待教而能,不因物而迁,人之异于圣人也,岂相悬绝若是耶?比弱冠求友于四方,多识当世之士,择其贤者能者而师之,其不可者而改诸,内外轻重之间,盖以孟子之论,其役志于功名,其徇情于妻子,其思慕其亲,不以皓首而愧垂髫者希矣。然后信孟子之知道,不苟于言也。”[1]44陈白沙认为“役志于功名”、“徇情于妻子”是一个人对父母的哺育之情渐趋淡薄的主要原因。那么如何做到“大孝终身羡父母”呢?陈白沙曰:“人各有所慕,仁者慕亲,义者慕君,士慕学,农慕稼穑,百工慕能,商贾慕贸迁,无无慕者。慕之至死而勿替,乃至形乎动静,接乎梦寐,通乎幽明,皆性之所发而为情,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此之‘永慕’是也。夫孰得而夺之!”[1]45“性之所发为情”是“永慕”父母的根源。“性之所发为情”即程子所谓“性其情”,而“性其情”是相对于“情其性”而言。“性其情”即《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的意思。“性其情”有两重含义,一重是非自觉的“率性”,亦即“百姓日用而不知”;另一重含义是在工夫纯熟的意境下有自觉的“率性”,由性之中正,必然发为情之中正。很显然,工夫纯熟意境下的“性其情”是德性贞定意境下的“性其情”,亦即江门学派“先立其大”的意境下的“性其情”,此情已经由父母的哺育之情升华为发自人性本真的敬仰、仰慕之情,此情得以贞定,故而能“永慕”父母。“役志于功名”与“徇情于妻子”则是“情其性”,情之荡而渐渐离却人性本真,如陈白沙所说:“彼幼而慕,壮而衰,老而遂忘,慕之不至而迁于物,是之谓情。其性非知内外轻重之别者也。”[1]45因此,“性其情”与“情其性”的本质区别即孝养是否具有“敬”的内涵并以之贞定德性。主敬是陈白沙心学的核心工夫,孝养之敬自然属于主敬的范畴。以人性的本真作为主敬工夫所指的对象,在此背景下的分殊工夫可以“一以贯之”。陈白沙《风木图记》云:“夫孝子之事其亲,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致爱则存,致愨则著,著存不忘乎心,奚存殁间哉?……具足于内者,无所待乎外;性于天者,无所事乎人。又非但事亲一事为然也,一以贯之。”[1]48在“一以贯之”的工夫论体系下,由孝亲可推至忠君,乃至治国、平天下,陈白沙云:“夫忠孝之推也,不孝于亲而忠于君,古未有之也”[1]45,“惟所存孝悌心益诚益推”,“存乎孝悌,形于事君为良,临大节为忠,感于人心、措诸天下为事业”[1]74。因此,以敬作为孝养的内涵,是陈白沙孝养观念的本质特征。
在“善养”与“禄养”的关系上,陈白沙提出了“善养”重于“禄养”的观念。陈白沙在给罗一锋的信中谈到庄孔旸因家贫,奉亲之命出仕,不得已为禄而仕。陈白沙《与罗一峰》云:“庄孔旸家贫,既无以为养,又其亲命之仕,便不得自遂其志。应魁止于贫而已,若能进退以道,甚佳。至于甚不得已为禄为仕,亦无不可,但非出处之正也。孔旸承亲之命而仕,不如此则逆亲之命以全己志,殆非所安。”[1]158针对此两难境地,陈白沙根据尹和靖和他的老师程颐的一段对话,提出了“善养”重于“禄养”的理论。《与罗一峰》云:“尹和靖一日告伊川曰:‘吾不复仕进矣。’伊川曰:‘子母在。’尹归以此意告,其母云:‘吾知汝以善养,安知汝以禄养乎?’尹遂得不仕。”[1]158所谓“禄养”就是以出仕之俸禄来孝养父母,所谓“善养”就是在经济窘迫的境遇下,尽其所能,以心为孝,尽心适可。在“善养”与“禄养”二者之间,“善养”既符合儒家孝养父母的经论思想,符合人性的本质,又符合陈白沙孝养的权论思想。因此,陈白沙认为“善养”重于“禄养”。陈白沙晚年以教书育徒为事,徜徉于江门美丽的湖光山色之间,与张诩等弟子作诗论学,自在洒脱。而他的学生林光为了禄养,在外作教授。陈白沙委婉地批评了林光,就是出于“善养”重于“禄养”的观念。
二、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是陈白沙家风与学风的德性内涵
陈白沙从人性自由、德性自由两个方面阐发义、利关系,形成了以义为上、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不见小利的义利观。义利观是陈白沙家风、学风的核心修养。追求人性自由是陈白沙心学的崇高理想和人生价值的终极目标,与此相比,功名、利禄与荣华富贵则显得微不足道。在陈白沙心学的理论体系中,功名、利禄与荣华富贵统称为“物”。陈白沙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人性自由的框架下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即人与物浑然同体,人对物的态度是“情顺万物而无情”[1]710。第二个层次是在德性自由的框架下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以“揆于道义”[1]218为尺度,以“道义”作为评判人与物关系的标准。在人性自由的框架下,世人往往被功名、利禄与荣华富贵所引诱,是因为只见“小我”不见“大我”。陈白沙《藤蓑之五》诗云:“新蓑藤叶青,旧蓑藤叶白。新故理则然,胡为浪忻戚?扁舟西浦口,坐望南山石。东风吹新蓑,浩荡苍溟黑。须臾月东上,万里天一碧。安得同心人,婆娑共今夕?”湛若水注曰:“因言物有新旧,其理固然,何必以此动心为之忻戚哉?以比贵贱荣辱之不同,不宜以此动心也。我乘扁舟往坐南山之石,而东风吹蓑。适日将幕,苍溟已黑矣。须臾月出,则见苍溟万里一碧,以喻人为富贵利达所蔽,则不见此道之大。至于本体,复明其真境,可乐如此。安得同心之人,共此今夕之乐哉?盖勉人同进大道之意也。”[1]729“东风吹新蓑,浩荡苍溟黑”意即人被功名、利欲所引诱而不见本心,不见此道之大。只有通过澄心见性的工夫,祛除私欲、私见,方能见“道之大”,方能弃“小我”而见“大我”。所谓“万里天一碧”,就是指人的至善的本心、纯净之心、自由之心,也就是“复见天地之心”。通过澄心见性的工夫,实现“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就自然能做到“情顺万物而无情”,实现与物浑然同体。陈白沙《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上》云:“天地之大不得与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君子之所得者有如此,则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无所增;天地之终,吾之终也,而吾之道无所损。”[1]54-55“君子得之”即是实现了“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如此,富贵、贫贱、死生、祸福只是“小我”的增损,而“大我”则无所增损,富贵、贫贱、死生、祸福于“大我”而言,不足道,即“铢视轩冕,尘视金玉”。
在德性自由的层面,陈白沙以“揆于道义”为标准,提出了义以为上、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所谓德性自由,就是人摆脱了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等各种贪欲的困扰,实现了心体之中正、自然的品质而无所愧怍、心安理得。陈白沙称自己早年从事于科举,对儒学的义利之辨没有深刻的理解,自从师从吴与弼之后,才有了长足的进步。他说:“予少无师友,学不得其方,汩没于声利,支离于秕糠者,盖久之。年几三十,始尽弃举子业,从吴聘君游。然后益叹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汩没而支离者,洗之以长风,荡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复长也。坐小庐山十余年间,履迹不踰户阈,俯焉孳孳,以求少进于古人,如七十子之徒于孔子。盖未始须臾忘也。”[1]34“汩没于声利”意指将科举制度当作谋求功名利禄的工具,而没有将儒学当作为己之学。在陈白沙的心学体系中,陈白沙特别重视出处、进退与去就。陈白沙曰:“人出处、进退、去就之节不可苟也。非但不可苟仕,亦不可苟止。”[1]150出处、进退与去就的理论根据就是义利之辨,“出处、语默、去就之权,操而存之,必概乎义。苟如是,荣辱之至自外者,斯任之而已。仆之所以守如此”,[1]149“必概乎义”就是“揆于道义”,以“义”作为行为规范的准则。陈白沙《赠林汝和通判》诗云:“丈夫重出处,富贵如浮烟。行则为在田,止则为在渊,劳劳夫何为,赠子千金言。”湛若水注云:“丈夫所重者出处之义,如富贵则如浮烟之无有。在田在渊,惟其时耳。又何棲棲如是之劳乎?吾赠子以此言,等千金之重,所以敬之者至矣。”[1]723“千金言”指出处、去就以义作为标准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富贵如浮烟”,即陈白沙引用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云:“谓薄不义也,非薄富贵也。”[1]55无论是富贵、贫贱,对于追求道义而言,对于为己之学而言,都是无足轻重的。如果人的一生只是追求功名、利禄与荣华富贵,便只是将人的生理欲望扩充而已,将极大地贬损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因此,陈白沙《李子高墓铭》云:“生不足,归于天;义不足,何有于年?”湛若水注曰:“言人生夭折而不足于年,则归之天命。然朝闻道夕死可矣。若义不足,则虽长年,亦和用哉?谓夭寿不足计,惟当尽道于己也。”[1]704也就是说,如果连人生的道义都不晓得,空活百岁,人生又有什么价值呢!
陈白沙既是义以为上、重义轻利的宣道者,又是实践者。张诩在《白沙先生行状》中称陈白沙“为人豁达大度,不见小利。”[1]874《白沙先生行状》云:“巡抚湖广都御史谢某遗先生寿木甚美。一日,其交厚陈某者卒,遗言必得木如先生者。其子以告,先生即举以畀之。林良者,以画名天下,尝专意作一图为先生寿。惠州同知林某至,阅之爱甚,先生亦即畀之无吝色。知县赵某颇著贪声,惧先生遇当道露其事,遗白金数铤为太夫人寿。先生不得已受之,戒家人勿启。后某以赃去官,先生追而还之,其人感泣。提举汪某慕先生特甚,在海北特作怀沙亭以寓仰止,亦数以白金为先生寿。其卒于官也,先生尽封还以为赙。参政伍某、佥事戴某辈以次各遗白金欲新先生居,却不可,乃营小庐山书屋以处四方学者。初年甚窭,尝贷粟于乡人,佥事陶鲁知之,遗田若干顷。晚年,按察使李白洲仿郑富公故事,破数百金买园一区于羊城,先生皆却不受,封券至于三四往返。御史熊某仿洛阳故事,欲建道德坊于白沙,以风士类。先生力止不可。乃议创楼于江浒,为往来嘉宾盍簪之所,榜曰嘉会。先生曰:‘斯可矣。’先是,某亦以疏荐于朝。都御史邓某仿林逋故事,檄有司月致米一石,岁致人夫二名。先生却之以诗云:‘孤山鹤啄孤山月,不要诸司费俸钱。’行人左某出使外夷,以其师某意,致白金三十星,先生亦却之。太夫人兄弟之子林某,幼无依,先生收育教之成人,至割田庐以树其家。尝买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叹曰:‘良家子也。’命内人抚育之如己女,及笄择婿嫁之。友人庄昶病,遗书求先生门人知医范规者往。规贫不能赴,先生即备行缠服食津遣。与人交无生死炎凉之别。”[1]874-876由以上的记述可以看出,陈白沙不愧为儒家学者的楷模。陈白沙何以能如此?张诩曰:“盖其学初则本乎周子主静,程子静坐之说,以立其基。其自得之效,则有以合乎见大心泰之说。故凡富贵、功利、得丧、死生,举不足以动其心者。”[1]880“大心泰”即在江门学派“先立其大”的德性进路下,经过渐次扩充的工夫,在工夫纯熟的境界下以“复见天地之心”,从而得以贞定德性。“见大心泰”非指向朱子学体系下的心或性体,而是指向生生不息的心体,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心体的自然流行即承体起用、即体即用,人与万物打成一片而浑然同体,自然能作到“不离于形器而不滞于形器”[1]779,即所谓“情顺万物而无情”。陈白沙认为人生的最大快乐是无愧于心,他在《湖山雅趣赋》中说:“富贵非乐,湖山为乐。湖山虽乐,孰若自得者之无愧怍哉!”[1]275在义利之间做出精当选择,即无愧于心,也就是陈白沙所说“揆于道义,无不安也”[1]218。
三、 笃实的体认、体证是陈白沙家风与学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工夫保证
笃实的体认、体证工夫是陈白沙家风、学风最显著的特征和最宝贵的品质,这一品质是江门学派保持强劲生命力而长盛不衰的最根本原因。吴与弼在明代心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从《伊洛渊源录》中洞察了北宋新儒学的理论体系,对新儒学的诠释基本上奠定了明代儒学发展的框架。笃实的体认、体证工夫是吴与弼儒学的显著特征。《日录》曾经记载了他的家里丢失了一只鸭子之后他由愤怒到原谅、自责的心理过程。吴与弼曰:“人患不知,反求诸己,书自书,我自我,所读之书,徒为口耳之资,则大失矣。”(《康斋集·复日让书》)一个人在求学时,若不反求诸己,而是仅仅以书本知识作为标准,不进行实践体验,不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那只能成为空谈而已。吴与弼曰:“徒讲说,得纸上陈言,于身心竟何所益,徒敝精神,枉过岁月,甚可惜也”(《康斋集·与友人书》)孔子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就是这个意思。所谓“为己之学”就是成就自己的学问,就是要把先贤书籍里记载的学问与自己的身心实践结合起来,贯彻到自己的心灵之中。吴与弼注重笃实体证的学风对陈白沙影响很大,对江门学派的传承与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陈白沙曾经以《周易》疑义质询吴与弼,吴与弼为了让陈白沙有深刻而透彻的理解,并没有直接向他讲解,而是让他历经曲折去找龙潭老人。《明儒言行录·吴康斋》云:“清江有陈海雍,号龙潭老人,潜心古学,遁世无闷,公雅敬重之。白沙尝以周易疑义质公,公曰:‘过清江可叩龙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谒,适龙潭雨中蓑笠犁田,乃延至家,与之对塌,信宿辨析疑义。白沙叹服而去。”受吴与弼儒学体认、体证工夫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体认、体证,在生活中悟道成为陈白沙心学的显著特征。例如,陈白沙为了体认、体证儒学的静坐工夫,曾经在春阳台静坐十余年,几乎导致心疾。“随处体认天理”是陈白沙家风、学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陈白沙对湛若水说:“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处也。”[1]194随处体认天理囊括了内外、动静,即合内外、合动静,尊重世界的客观性,从实践出发,在感性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体认、体证心体之中正、自然,进而渐次扩充,以达致至仁、至善。随处体认天理亦体现了陈白沙心学体认、体证的笃实性。
陈白沙心学体认、体证工夫的笃实性,对江门学派影响深远。陈白沙在勉励林光时说:“上蔡云:‘要见真心,所谓端绪,真心是也。’ 缉熙后一札已具此意,但恐工夫不能无间断耳,更企勉之。”[1]970又曰:“缉熙今认得路脉甚正,但须步步向前,不令退转,念念接续,不令间断,铢累寸积,岁月既久,自当沛然矣。”[1]970“不令退转,念念接续”就是在见真心的基础上的勿忘工夫,是儒学修养工夫的把柄、用力处,是最笃实处。湖北嘉鱼人李承箕先后四次到江门师从陈白沙,陈白沙送别他时,语重心长地说:“自首夏至白沙,至今凡七阅月,中间受长官聘修邑志于大云山五十余日,余皆在白沙,朝夕与论名理。凡天地间耳目所闻见,古今上下载籍所存,无所不语。所未语者,此心通塞往来之机,生生化化之妙,非见闻所及,将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爱于言也。”[1]16陈白沙为何不与李承箕谈论生生不息之道体、心体?原因在于李承箕尚未悟及于此,如果体认、体证工夫不笃实,就有认知觉为性而流禅的风险,而这也正是学者最常犯的错误,因而陈白沙十分谨慎,待到李承箕有所领悟之后,再循循善诱。由此可见体认、体证的笃实性对于成德的重要意义。陈白沙曾评价过他的弟子,但论及张诩时特别谨慎。湛若水问陈白沙,为何不与张诩谈论心体之自然,陈白沙曰:“东所好求之高远”[1]779,“弗问弗讲,且顺其高谈,然几禅矣。”[1]885陈白沙认为张诩虽然机敏,悟性比较高,但好高骛远,有流禅的风险,因而与其很少谈及心体之自然。陈白沙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陈白沙去世后,张诩撰写了《墓表》,其中有“右脸有七黑子如北斗”的字句,继承了陈白沙笃实学风的林光对此进行了驳斥,他说:“此朱子相也。若云白沙亦有,何吾辈之未见也?”《墓表》又云:“卓卓乎孔氏道脉之正传,而伊洛之学盖不足道也!”将陈白沙凌驾于二程之上,林光驳斥道:“呜呼,斯言之过甚矣。!”(《林光集》)概而言之,陈白沙心学的笃实学风影响了江门学派的学术风格,湛若水、冯从吾等人处于与阳明学、阳明后学辩学的历史背景下,他们顺承白沙心学的笃实风格,并做了进一步的修正。在陈白沙“本体自然”的基础上,湛若水提出了天理流行,冯从吾提出了道心流行,将江门学派与阳明学、阳明后学严格区分开来,使江门学派沿着正确的路径科学发展。
孝道思想是陈白沙家风与学风的哲学基础,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是陈白沙家风与学风的德性内涵,笃实的体认、体证是陈白沙家风与学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工夫保证,三者相互贯通,形成有机的统一体。家风与学风是一个学派的标志性特征,江门学派与阳明学、阳明后学是明代心学的两大流派,家风与学风的不同,特别是学风的不同,是两个学派的本质区别。阳明学以单提直指、直接指向良知为德性进路,以正念头为核心修养工夫,以易简性为体认、体证的特征。这种易简性的教法有导致认知觉为性的风险,从而造成流禅或狂肆。尽管王阳明生前强调笃实体证的重要性,但是,阳明后学的晚期还是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流禅或狂肆的倾向。江门学派则不然,以随处体认识天理为德性进路,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证工夫的恰到好处,既注重儒学体证的易简性,又注重儒学体证的艰辛性,使江门学派避免了工夫论上的浮光掠影、本体论上的玩弄光景。作为江门学派的殿军,黄宗羲在江门学派中正、自然的理念的基础上提出“君主是天下大害”的反君主专制的民主思想萌芽,将儒学的发展推向高峰。两家学派在本体论、工夫论上的分歧及最终的传承与发展,彰显了江门学派的科学性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