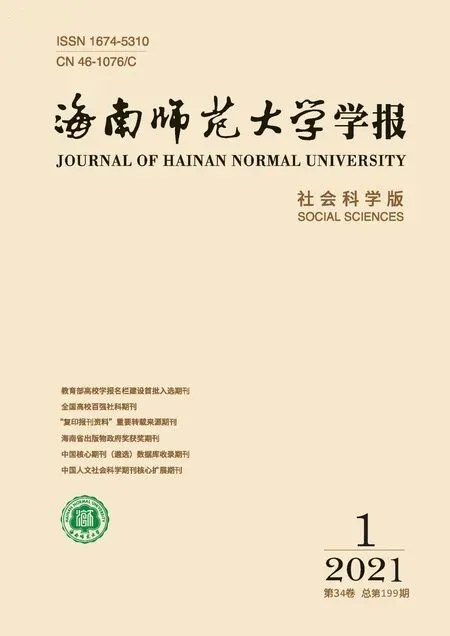国粹运动中作为朴学学者形象的孔乙己
2021-03-05梁结玲
梁结玲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彰州 363000)
鲁迅一生除了文学创作上有非凡的成就,在学术上也颇有建树。他早年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受其影响,一度热心于国故的整理。许寿裳说:“自民二以后,我常见鲁迅伏案校书,单是一部《嵇康集》不知校过多少遍。参照诸本,不厌精详,所以称为校勘最善之书。”(1)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9页。章太炎是晚清国粹思潮的干将,鲁迅的学术研究与当时的国粹思潮密不可分,鲁迅也自称“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2)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鲁迅的第二篇小说《孔乙己》是埋头学术时创作的,他在这篇小说的附记中说道:“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3)鲁迅:《孔乙己附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1页。鲁迅要描写的是社会上的一种生活,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其实在《孔乙己》写作之前,保存国粹运动已如火如荼地进行,鲁迅说要描写的“一种生活”,其实就是在学问里讨生活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孔乙己一直被视为旧式知识分子的典型,这样的分析不免笼统。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与国粹思潮紧密相关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不擅长应试科举的旧式知识分子。孔乙己这一形象正是对沉迷于国粹中的知识分子的反思,蕴含了鲁迅对国粹思潮与新文化运动的思考。
一、孔乙己作为朴学学者的形象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将中国学术研究的门径分为汉学(即朴学)和宋学两种,并认为二千多年的学术就是两者争胜的过程。“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4)[清]永瑢等纂:《经部总序》,《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页。宋儒追求义理,以天理压抑人性,汉学重训诂考据,中国历代学术不出此二途,纪昀对中国学术门径的划分基本符合中国学术发展的历程。清代的主流学术是汉学(朴学),晚清国粹一派所用治学方法基本上是朴学的治学方法,章太炎可以说是朴学最后的终结者,鲁迅的学术门径也正是师承了章太炎。仔细分析《孔乙己》,我们不难发现,孔乙己正是典型的朴学学者。

基于朴学学者的视野,我们就不难理解孔乙己另类的行径了。孔乙己“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他的那些“伤痕”多是因为偷书所致。孔乙己进入别人家只去一个地方——书房,“时常夹些伤痕”,说明他进入书房的次数不少,他的勤奋好学与朴学重博学是一致的。朴学研究需要广博的学识,章学诚说道:“博学强识,儒之所有事也。以谓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8)[清]章学诚:《博约》(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7页。学识的广博需要丰富的书籍,孔乙己乃一介寒儒,自身的温饱尚成问题,买书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了,因此偷书便不可避免。孔乙己认为自己偷书是从事儒经的研究,是读书人的正途,是高尚的事,“学而优则仕”,当别人说是“偷”,将他视为窃贼时,他“睁大眼睛”反驳:“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丁举人打断他的腿,他也不承认自己的行径是偷窃。同为寒窗苦读的丁举人不理解孔乙己潜入书房偷书的行径,他将书视为个人财产,而孔乙己却将孔孟之道视为读书人共同的财富。从对待书籍的态度,我们不难看出两人在治学上其实相去甚远。从丁举人的行径可以得知,他是理学的信徒,认为有悖天理就可以被任意处置。“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9)鲁迅:《孔乙己》,《鲁迅全集》第1卷,第460页。丁举人的刻薄、狠毒正是借助了程朱理学的“天理”,这就难怪清儒戴震批评:“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10)[清]戴震:《与某书》,《戴东原集》卷九,清经韵楼台刊本。孔乙己没有理学的固执、刻薄,倒有不少可爱之处,这与朴学重人的自然情感是一致的。同为读书人,孔乙己与丁举人代表了朴学与理学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孔乙己何以在帮别人写字时偷书籍纸张笔砚?《论语》有:“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意即大德无亏,有点小庛也无妨。圣贤尚且如此,孔乙己偶有此种行径也就不为过了。程朱理学严守天理,只要于德有亏便严厉批评,先儒倒是比较融通,孔乙己的这些举止也正好说明他是孔孟的信徒而不是理学的信徒。孔乙己自负有学问,却在科举上没有建树,造成这一结果,也与他的治学有关。清代的科举考试采用明制,以朱注四书为标准,考卷多程式化,只要暗中多摸索,一般都会把握其门道。丁举人中举,而孔乙己却没有成功。其中原因:一是朴学考证需要大量的时间;二是经史考证与八股文并不合辙,两者旨趣、方法不一样,不擅长科举考试在清代朴学学者中也是比比皆是。朴学学者多以博学自负,当别人问及为何没有考取功名时,自视博学的孔乙己就难免“显出颓唐不安模样”了。
二、孔乙己与晚清国粹派
鲁迅在《孔乙己》文后有一段附记:“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候——便是忽然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塌的是谁。这实在是一种极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11)鲁迅:《孔乙己附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61页。鲁迅在与孙伏园的谈话中自认为《孔乙己》是写得最好的小说,而在附记中却说“很拙”,这也许是不想激起太大的争议。在文后鲁迅特别强调《孔乙己》的写作并非人身攻击,这说明他在当时是有所顾虑的,这一顾虑正是源于当时的国粹思潮。鲁迅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钱玄同就说道:“其时,与董特生、康心孚、龚未生、朱逖先、朱蓬仙诸人请太炎师讲小学,自是直至十六年之春,专以保存国粹为职志。”(12)钱玄同:《日记》(1917年9月12日),《钱玄同日记》(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5页。在鲁迅的周围,弥漫着一股朴学的风气。据孙伏园的回忆,鲁迅写作《孔乙己》并非完全虚构,“文中所提的‘鲁镇’,在作者的小说中有好几处提到,实在是创造的地名;我想这个地名所包含的内容就是作者的父系故乡(绍兴墟内都昌坊口)和母系故乡(绍兴东皋乡安桥头)的混合体,我们到那两处附近去,一定可以寻到许多迹象。而‘咸亨酒店’却是一个真店号,就在都昌坊口,作者故里的斜对门,我还见过多少回,大概至今还在,这种小规模的老字号是不大容易倒闭的。《孔乙己》中的主角孔乙己,据鲁迅先生自己告我,也实有其人,此人姓孟,常在咸亨酒店喝酒,人们都叫他‘孟夫子’,其行径与《孔乙己》中所描写的差不多。”(13)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13—1983)》第3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第791页。可见鲁迅所说的“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正是现实中的朴学或国粹思潮。清代朴学到扬州学派而集其成,随后浙江学派又蔚然兴起,章太炎在俞樾传中说道:“浙江朴学晚至,则四明、金华之术茀之,昌自先生。宾附者,有黄以周、孙诒让。”(14)章太炎:《俞先生传》,《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2页。浙江学派自俞樾、章太炎后兴盛,孟夫子以“夫子”自居,其学术与浙江学派相吻。可见,鲁迅的《孔乙己》并非一般性的写作,而是有浓厚的现实基础。废名曾评论:“我读完《孔乙己》之后,总有一种阴暗而沉重的感觉,仿佛远远望见一个人,屁股垫着蒲包,两手踏着地,在旷野中慢慢地走。我虽不设想我自己便是这‘之乎者也’的偷书贼,但我总觉得他于我很有缘法。”(15)冯文炳(废名):《呐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13—1983)》第1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51页。与孔乙己有“缘法”的可能就不止废名一人了,孔乙己这一形象在当时引起时人共鸣并非他是科举屡试不中者,而是鲁迅所说的“一种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写作《孔乙己》的前后,他在日记里写得最多的是关于中学与西学的问题。在《孔乙己》发表前几个月,鲁迅的《随感录三十五》专门讨论了“国粹”问题:
从清期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
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
……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16)鲁迅:《随感录三十六》,《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2页。
国粹的讨论其实由来已久,晚清的保存国粹运动直接源于日本的国粹思潮。1901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道:“即如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起。”(17)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8页。黄节1902年在《政艺通报》上发表《国粹保存主义》一文,也介绍了日本的欧化主义和国粹保存主义:
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当是时,入日本国民思想界而主之者,纯乎泰西思想也。……文部大臣井上馨特倡此义,大呼国民,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和之,其说以为,宜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不宜醉心外国之文物,并其所短而亦取之,并我所长而亦弃之。其说颇允,虽然以论理上观之,不能无缺点焉。(18)邓实辑:《光绪壬寅政艺丛书》第5卷,《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180-181页。
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激发了中国人保存国粹的热情。晚清时期,不管是保守的清朝官员,还是改良派、革命派,都提出并积极践行清政府在1903年颁布的《学务政纲》中明确提出的:“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此即保存国粹之一大端也。”(19)舒新城:《学务纲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204页。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之下,国粹保存运动一时蔚然大观,各种团体、报刊、书籍层出不穷,“近数年来,中国之号称识者,动则称国粹。环海内外,新刊之报章书籍,或曰保存国粹,或曰发挥国粹,甚者则曰国粹之不讲则中国真不可救药。”(20)张栅、王忍之编:《国粹之处分》,《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192-193页。晚清国粹思潮一直延续到民国,与后来“整理国故”可谓一脉相承。不管是国粹思潮还是“整理国故”,在治学方法上都延续了清儒的治学方法。“学宋学皆有其真,得其真而用之,皆可救今日之中国。夫汉学解释理欲,则发明公理;掇拾遗经,则保存国学。公理明则压制之祸免,而民权日伸;国学存则爱国之心有以依属,而神州或可再造。宋学严夷夏内外之防,则有民族之思想;大死节复仇之义,则有尚武之风。民族主义立,尚武之风行,则中国或可不亡;虽亡而民心未死,终有复兴之日。”(21)邓实:《国学今论》,《国粹学报》第一卷第五号,1905年。这一时期,程朱理学其实已没有太大的市场,保护国粹、整理国故在治学上基本都是采用汉学即朴学的治学方法。梁启超在评价章太炎的治学时认为:“其治小学,以音韵为骨干,谓文字先有声然后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史》及《国故论衡》中论文字音韵诸篇,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22)梁启超:《太炎儒学学案》,《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5页。国粹思潮的中坚力量多与乾嘉朴学有渊源,章太炎是俞樾之弟子,俞樾乃乾嘉学派的后期代表性人物。刘师培的曾祖刘文淇为扬州学派的后劲,他的祖父、父亲也沿承了朴学的治学方法,至刘师培“未冠即耿思著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任。”(23)尹炎武:《刘师培外传》,《刘申叔遗书》(影印本)上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页。国粹思潮虽然是有激于现实而发,但如果从学理上追问,可以说是朴学的延续。不管是保守阵营还是革命阵营,多数人对保护国学、国粹持肯定的态度。在写作《孔乙己》前后,鲁迅也正处于朴学研究的生活之中,而且成绩还不小,他在金石、墓志的收集、整理上可以说是国粹研究的典范。蔡元培评价鲁迅的学术研究:“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鉴赏家所未曾著手。”(24)蔡元培:《〈鲁迅全集〉序》,《蔡元培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14页。鲁迅在学术研究上可谓用功至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粹整理也是他的爱好。孔乙己这一形象与当时“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是相吻的,鲁迅描写的孔乙己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知识分子,而是有其特定的时代性,即鲁迅生活的时代,也有其特定的指向性——国粹思潮。
三、孔乙己形象的意义
鲁迅能够将孔乙己刻画得如此深入,与他当时正在进行的学术研究不无关系,我们且从《呐喊·自序》了解他当时的心迹:“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25)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0页。在鲁迅“回到古代去”,从事朴学研究的时候,“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这到底是什么事?如果看看鲁迅写给钱玄同的一封信,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录)、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26)鲁迅:《180705 致钱玄同》,《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3-364页。这一封信疑是针对袁世凯称帝、刘师培计划复刊《国粹学报》和《国粹汇编》而发,写在《孔乙己》前几个月(即1918年7月)。袁世凯大力倡导“尊孔读经”,刘师培等人随声附和,以“国粹”的名义进行复古,这让激进的知识分子难以接受。作为《新青年》的推动者,鲁迅自然对这一思潮进行抵抗,鲁迅说的“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正是针对“尊孔读经”的行径。其实,在《孔乙己》写作之前,关于国粹保存就有争议。钱玄同在1918年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又独秀、叔雅二人皆谓中国文化已成僵死之物,诚欲保种救国,非废灭汉文及中国历史不可。此说与豫才所主张相同,吾亦甚然之。”(27)钱玄同:《日记》(1918年1月2日),《钱玄同日记》(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26页。可见当时鲁迅对国粹保存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国粹”与保国、新文化运动都已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孔乙己》的写作很难说与这一社会问题脱离关系。
既热心于文史考证,又对国粹思潮进行抨击,这是鲁迅写作《孔乙己》时的心态,我们该如何来理解这种心态?我们可以从鲁迅对章太炎的评价里找到答案。“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28)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65页。章太炎逝世后,作为弟子的鲁迅认为章氏在革命运动中的贡献要大于学术上的贡献。我们暂且勿论鲁迅的这一评价是否公允,至少从价值取向上,鲁迅认为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比书斋要有现实意义。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鲁迅一方面沉浸于考古的朴学研究,另一方面为新文化运动呐喊了。孔乙己这一形象表现了鲁迅对复古不前的批判和对传统文化的持保留性的态度。“但是不能革新的人种,也是不能保古的……他们活有余力,则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帮同保古就可怕了。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这虽然可恶,却还不奇,因为他们毕竟是外人。而中国竟也有自己还不够,并且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鉴赏者,则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但是,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现状就是铁证,比保古家的万言书有力得多。”(29)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47页。保护国粹固然有其价值,但改变国计民生更是当时社会急切解决的社会问题。可见,鲁迅对保古持的是扬弃的态度,这是比较客观的。
作品的主人公是孔乙己,而在叙述这一形象时,作者却是通过刚进酒店打杂的店小二的视角来展开,如此构思也是颇有心思。通过这样的视角,孔乙己的“国粹性”就比较客观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一“国粹”与民众无关,对当时的社会丝毫起不到作用。“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没有孔乙己,世人生活依旧,孔乙己的生死不关世人,却关作者,“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作者在书写这一形象的同时,嘲笑与同情与俱,反思与痛骂并存,“大约”“的确”这一矛盾的语气背后,蕴含了作者深沉的情感。孔乙己虽然迂腐可笑,但在他的身上,既有对传统知识分子身份的坚守,也有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这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对于苦人是同情,对于社会是不满,作者本蕴蓄着极其丰富的情感。”(30)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13—1983)》第3卷,第791页。孙伏园是与鲁迅交流《孔乙己》距离最近的人,他的评述应该说是深得鲁迅之意,这与作品表现出的情感态度是相吻合的。孔乙己是一个悲剧,而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31)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3页。,鲁迅何以要毁掉这有价值的东西?这与国粹运动食古不化,盲目自大有关,“中国废止读经了,教会学校不是还请腐儒做先生,教学生读‘四书’么?民国废去跪拜了,犹太学校不是偏请遗老做先生,要学生磕头拜寿么?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不是最反对五四以来的小改革么?而外国总主笔治下的中国小主笔,则倒是崇拜道学,保存国粹的!……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32)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第46-47页。国粹主义一味地退回古代,无视社会的巨大变化,这无疑是将中国带回落后挨打的时代,鲁迅对这一倾向严厉批评。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引发了国人崇洋媚外的心态,在《拿来主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杂文里,鲁迅对这一倾向也进行了批评。其实鲁迅对国粹运动和西化一直持比较复杂的心态,这一复杂的心态一直影响到他晚年的小说和杂文的写作。《故事新编》是鲁迅的最后一个小说集,共8篇小说。小说主人公以历史人物为主,如女娲、大禹、墨子、孔子、老子、伯夷、叔齐、庄子等,这些人物是中国文化最初的构建者,在对这些文化奠基人物的叙述中,鲁迅的态度也是相当复杂。在《理水》与《非攻》中,鲁迅表现出了对传统人物、传统文化的敬重,而在《出关》《采薇》《起死》等作品中却持反讽、批判的态度,爱恨交加的态度与对孔乙己的叙述如出一辙。孔乙己这一形象已不仅仅是传统知识分子悲剧问题,鲁迅通过孔乙己的学术路径、人生路径对国粹思潮进行反思,而这一层却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这是值得学界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