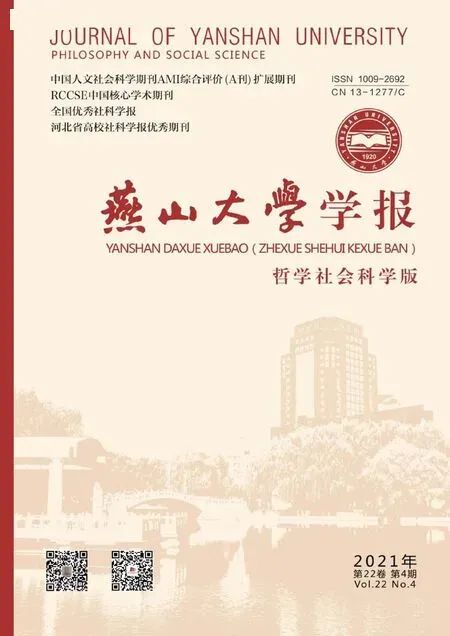多维视角下《韩非子》英译本在西方的传播及启示
2021-02-28孙亚鹏
孙亚鹏
(北京语言大学 比较文学所,北京 100083)
《韩非子》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是反映我国古代法律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典籍。自19世纪末期汉学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开始起,此书从未脱离过汉学家的视野。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翟理思(Herbert A.Giles)、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华兹生(Burton Watson)、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葛瑞汉(A.C.Graham)、顾立雅(Herrlee G.Creel)、龙德(Bertil Lundahl)、金鹏程(Paul R.Goldin)、吴国桢、廖文奎等中外学者都对《韩非子》进行了翻译(包括节译)和研究。这些成果虽称不上盈床满箧,但也是为数不少的。然而,国内对《韩非子》的译介则关注较少,还只是停留在一两篇极简短的综述和书评上①,尚未有学者对《韩非子》的译介和传播情况进行深入介绍,殊为可惜。本文旨在对《韩非子》英译本在海外的传播情况进行分析,通过个案研究,在传播效果的研究范式上有所创新。
一、“经纬相交”的传播效果评价机制
谢天振教授曾指出:“我们今天在讨论中国文学、文化外译问题时,不仅要关注如何翻译的问题,还要关注译作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1]然而,由于地域阻隔,通过实地调研、访谈进行数据收集并不方便,所以一些学者另辟蹊径,以考察图书馆藏为进路来评估译本在海外的传播情况。②从逻辑上讲,一本书在图书馆界的保有量越多,就意味着其有可能被更多的人所获取,传播范围越广。于此,“馆藏数据”的开创者何明星教授指出,“图书馆馆藏量能衡量图书的文化影响,被认为是检验出版机构知识生产能力、知名度等要素最好的标尺。”[2]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馆藏数量只是传播介质、传播渠道的体现,图书馆并不是传播的终端。一本书被图书馆采编后依然有可能遭遇借阅率低,甚至无人问津的冷遇。传播的终端是读者,所以我们有必要构建一个多维度的而非单一的指标体系,这个体系要将读者的反馈纳入其中,作为评价译本传播的关键要素。对于《韩非子》这样的中国哲学严肃读物来说,其接受者/读者对象大体分两类,一类是研究型学者,他们的接受反馈多以学术书评的形式体现。在西方,学术书评有着长久的传统,它的批判性促成了不同观点的交锋,促进了学术共同体思想的交流,直接助力了学术作品的广泛传播,所以学术书评在西方语境中不仅直接反映了接受情况,而且还对图书的流通产生了重要影响,书评理应纳入考察传播情况的要素之一。《韩非子》的另一类接受者是普通读者。在印刷时代,普通读者很少能以“白纸黑字”的形式抒发己见,然而在数字人文时代,互联网给予了普通读者一个表达意见的空间,不仅如此,这个空间还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它没有学术壁垒,不强调学术规范,这样的评论更具有生命力和创造性。特别一些读书网站兼具社群功能,品味相近的读者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众声喧哗、唱和应答的“意见场”,这个“意见场”是书籍传播效果在数字时代的投射,我们也应当给予关照。由此,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由海外馆藏(机构)、学术书评(学者)和网络意见(一般读者)三个维度构成的、相对全面的传播效果评价机制。
此外,单一的《韩非子》的译本并不能完全反映该典籍在海外的传播情况,所以我们还有必要将不同译本/版本并置于观察的视野之中,对各个文本的接受程度进行比较,在“长短相形”中发现问题,思考传播策略。于此,笔者选取了三个译本,分别是华兹生的节译本HanFeiTzu:BasicWritings、廖文奎的全 译本TheCompleteWorksof HanFeiTzuVol.Ⅰ&Ⅱ,还有根据廖文奎的全译本和张觉的《韩非子全译》合成的《大中华文库:〈韩非子〉(汉英对照)》(LibraryofChineseClassics:HanFeiZi(BilingualChineseandEnglish))③这样,以三个评价维度为“经”,三个文本为“纬”,经纬相交,《韩非子》的传播状况就可得见全豹了。
二、《韩非子》英译本在西方的传播情况
在前文所述的研究范式下,笔者对《韩非子》英译本在西方的传播情况进行了考察。首先我们看一下西方图书馆馆藏情况,对于这一基础数据的来源途径,本文参照了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的WORLDCAT(全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WORLDCAT是世界上最大的书目记录数据库,内容涵盖170个国家、72 000所图书馆,能够快速检索到图书在世界各国图书馆的馆藏数据,该数据库实时更新,本文使用的数据更新至2020年7月10日,根据检索,数据库显示的《韩非子》各个英译本在西方图书馆馆藏数量情况见表1:

表1 《韩非子》英译本海外图书馆馆藏数量(含电子版本)
由表1可见,美国汉学家华兹生的译本排名第一,半个世纪以来再版了4次,图书馆目前登记的保有量为1 013册,这还不包括收录此节译版本的合辑本(BasicWritingsofMoTzu,HsunTzu,and HanFeiTzu,1967)。廖文奎的译本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出版于1939年,下卷出版于1959年,两卷均只发行过一版,共计314册。《大中华文库:〈韩非子〉(汉英对照)》共四卷,其在西方的传播效果差强人意,只有美国的密歇根州立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佛蒙特大学图书馆、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伯克利大学图书馆有馆藏。
其次,国外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海外专家学者的书评情况也是译本传播效果的重要体现。对此,吕敏宏曾指出:“翻译文本能够进入异域阅读层面、赢得异域行家的承认和异域读者的反响才有译介效果。”[3]笔者借助EBSCO和JSTOR数据库,对发表在西方学术期刊上的相关书评进行了调查(本文使用的数据更新至2020年7月12日)。其中,书评的数量本身就反映学术界对此译本的关注程度,书评的内容对译本的接受、传播更是直接发挥着推介推广的作用,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学术书评情况
从数量上看,关于廖译本的书评一共有5篇,关于华译本的书评一共有4篇,目前西方没有对《大中华文库:〈韩非子〉(汉英对照)》的书评。就廖译本的书评而言,发表时间主要集中在下卷出版的1959年之后的两年内。④尤其令人侧目的是,对廖译本进行点评的都是汉学界名家,如卜德、葛瑞汉、高佩罗、陈荣捷都是专攻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著名学者,所以其见解的公信力、影响力和传播力都非常大,是一般书评在效力上所不能企及的。就点评中的具体意见来看,五位学者都对廖译本在填补《韩非子》的英译空白以及向西方读者推介中国法家思想的积极意义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卜德说:“廖译本的上卷发表于1939年,在UNESCO的帮助下,二十年后下卷本得以付梓出版,使得我们今天看到了首部用西方语言翻译的《韩非子》全本,这是令人高兴的事。”[4]陈荣捷说:“考虑到韩非子作为法家之大成者的历史地位,这个全译本显得有一些‘姗姗来迟’。这个译本另外一个受欢迎的原因是西方学者想了解新中国的治国理政是否和法家思想存在联系。”[5]当然,作为严肃的学术批评,学者们也指出了廖译本中的不足:高罗佩认为廖文奎在翻译的过程中,忽视了早期日本学界对《韩非子》的研究成果。《韩非子》在幕府时代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其中一些日语校释版本是值得仔细关照的,因为他们所用的底本是在中国稀少且不为人所知的明代版本,例如津田凤卿的《韩非子解诂》,这个校评本融合再现了十多位明代学者的研究成果。⑤此外,高罗佩指出廖译本的另一个不足之处就是上卷本缺少对关键术语的索引。
高罗佩认为,由于古汉语的简洁特征以及许多有关思想的关键术语在先秦时期不同文本中的互通互用,所以有必要对这些术语有一个总体性的整理,从而方便读者查询术语的出处,分辨哪些术语是借用的,哪些表述是后来的学者所补充加入的,这样的译本才称得上是一个可信度高的译本。[6]廖译本的索引问题在下卷出版时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卜德、Alexander Soper在书评中都对此有所诟病。卜德认为,这部书在思想层面和文学层面都有很大的价值,但是没有被《哈佛燕京学社引得丛刊》收录,殊为可惜。一部668页的翻译作品就以不到4页的索引草草结束了,的确看起来有虎头蛇尾之嫌,但是在考证之后我们发现原来这索引是殁后续笔,情有可原。⑥但无论如何,我们可见西方学者对于典籍翻译中索引部分的重视。在他们看来,没有一个完备的索引,一部学术译著就是缺失而不完整的。而2015年在廖译本基础上整理出版的《大中华文库:〈韩非子〉(汉英对照)》依然没有做索引,这种做法使得该译本的学术性有所折损。
关于华译本的书评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和对廖本的书评相仿,皆是名家之论。刘殿爵和Alexander Soper均称赞了华兹生译本中的Introduction部分是点睛之笔——对韩非的时代背景、生平、以及思想学说所做的铺陈可以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鲁惟一认为华译本可读性很强,不仅有学术价值,也适用于一般读者。John L.Bishop认为译文在语言风格上也符合原作冷峻有力、广作譬喻的文风。但是批评的意见也是存在的:虽然John L.Bishop认为此节译本中的12章是明智的选择,涵盖了韩非的主要观点以及他在透彻说理时所运用的贴切的历史例证,但是刘殿爵质疑了华兹生选篇的角度。刘认为从体现《韩非子》的文学性上讲,《内储说上七术》《外储说下六微》《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左下》《外储说右上》《外储说右下》这些富含寓言的篇章都应该被翻译。从思想体系上讲,《定法》篇反映了韩非所因循的商鞅的“法”治理念,《难势》篇论述了韩非所因循的慎到的“势”治理念,可惜这两篇都未被选译。然而韩非“法”“术”“势”是三位一体的,相辅相承不可偏废,所以其篇章选取并不合理。此外,对于Introduction部分,刘殿爵认为此处缺乏对前期法家,特别是慎到的叙述。其中对于申不害之“术”,译成policies也是欠妥的,不能反映“术”的内涵。鲁惟一则建议在这一部分中要交代一下自汉朝起封建王朝对待法家的态度(即阳儒阴法),以免西方读者产生“法家思想颇受欢迎,为中国的统治者所普遍采用”的误解。在具体错译漏译方面,刘殿爵的书评还做了一些勘误的工作,他指出了华译本中的翻译错误在廖译本中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在华译本中被“沿袭”了下来,没有得到改进。同时,在对元典的释读上,华兹生还盲从了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中的某些错误校注,也导致了一些错译。
从以上对书评的介绍来看,英语学界对廖译本和华译本还是比较关注的,自1939年廖译本上卷发表到1965年华兹生节译本出版,26年间陆续发表了7篇书评,说明《韩非子》在西方汉学界还是有一席之地的,同时由于这些书评自身的权威性,也进一步推动了《韩非子》及法家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但是这些书评所反映的传播情况有其局限性:第一,书评都是发表在学术杂志上,我们无法得知英语世界中一般读者对译本的阅读经验和评价;第二,书评一般都是在图书出版之后的近一两年内所发表的,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之久,那么当下一般读者的接受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基于此,笔者进一步调研了网站goodreads.com和amazon.com上的网络意见。
goodreads.com是国外权威的书评类SNS网站,类似于国内的豆瓣或知乎等网站,可供用户搜索、分享书籍,或发表书评、更新读书进程,用户数量庞大。amazon.com是全球最大零售的电商,它起步于网上书店,改变了图书销售的整个业态。亚马逊在每一个图书商品下都设有开放式的读者评论专栏,从中我们可以收集整理一些读者的接受情况。具体情况见表3(本文使用的数据更新至2020年7月15日)。

表3 网络意见情况
这里需要说明几个问题:第一,评论的数量并不是购买或者阅读此书的数量,读者的数量应该远高于主动撰写评论者的数量。以goodreads.com提供的数据为例,1996年版HanFeiTzu:Basic Writings的读者评论虽然只有5篇,但是网站显示有69名读者在读完之后对这本书进行了评分,正在阅读此书的有209人。第二,由于这本书是思想类的严肃读物,并非畅销书,所以少有水军以商业目的撰写评论,评论都是真实有效的。很多书评都是用心之作,有三篇800字以上的书评,其中一篇长达2 000字。这些书评不仅反馈了个人的阅读体验、为他人阅读提供指导帮助,还对韩非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评价。就书评的内容来看,观点各异,呈现出多元化的接受效果。有的读者认为《韩非子》一书是一本“chilling classic”(令人不寒而栗的典籍),书中的观点是“sign of tyranny”(暴政的标志),有的读者认为这本书在商业管理层面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大多数读者都对此书非常推荐,认为韩非子的学说非常有价值,值得一读。有50%的读者都能在书评中使用诸如“Qin”(秦朝)、“Fa-chia/legalist”(法家)、“Confucian”(儒家)这类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术语,还有20%的评论将韩非与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进行了类比,可见一些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读者对此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细读和思考。
三、传播情况对典籍译介的启示
以上调查基本上能反映出《韩非子》英语译本在西方的传播情况。从整体上讲,如果我们认为《韩非子》在英语世界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那显然是不现实的。要知道《韩非子》一书即便是在国内也不是一本普及读物,所以英语世界能有这样的馆藏、学者评价和读者反馈,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另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当下的传播语境,即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排头兵依然是儒道思想而不是法家学说。这个原因可以追溯到二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对待法家“阳儒阴法”的态度,其影响深远至今,即法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在场,但也从未以“显学”的面貌示人。考虑到典籍在海外的传播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和域内的关注程度是同频共振的,我们就可以对《韩非子》的传播现状报以同情之理解,毕竟像《寒山诗》那样墙外开花的例子是少数。
从单个译本上讲,调查数据所显示的译本之间传播效果差异还是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华兹生的节译本再版了4次,其销量和被关注程度远大于廖译本。是廖文奎的翻译质量不尽人意吗?从专业学者给出的书评来看,事实似乎并非如此。高罗佩对廖本的评价是:“语言运用良好,学术研究扎实”[6],卜德也毫不吝惜地赞誉道:“这是一个智慧和汗水的结晶,充分利用了文献研究的成果,没有漏译,对大部分原文都进行了准确且通顺的翻译……他对一些法家术语的翻译要比亚瑟·韦利、戴闻达和我本人有所提高。”[4]在笔者看来,廖文奎译本的相形见绌其实是翻译主体问题的外部映射,即廖文奎的华人背景是否导致了其在中西文化对话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华兹生的国籍及文化身份是否有助于其译本在母语世界被接受?这些译本背后的非显性因素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毕竟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以《墨子》的英译为例,第一本较为详细的节译本出自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者梅贻宝(梅贻琦之弟),三十年后(1963年)华兹生选取了他所认为“墨家十论”的精华部分进行了再次翻译。华兹生的翻译工作和英译《韩非子》一样,属于福特基金会所资助的“Program of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ental Classics”项目。两个译本相比较,梅贻宝的《墨子》节译是根据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在翻译中重视学术考据和语义对等,用词风格十分雅致和考究。但是由于华兹生的译者身份所占据的强势地位,西方一般读者或者墨家思想的研究者都是选用华兹生的译本进行阅读和开展研究的。又如以《孙子兵法》的英译本为例,根据学者李宁的调查,世界范围内收藏格里菲斯(Samuel B.Griffith)译本的图书馆多达985个,是收藏中国译者林戊荪译本图书馆数的28.1倍[7]80,这不能不说是由于译者的文化身份所导致的传播差异。而这种差异的造成是主观的,非客观的。在“东学西渐”的过程中,即便是这些东方译者所接受的是西方的学术训练,使用的也是地道的英语,但是西人仍然在心理认同上更加倾向于接受西人自己的译作。
同样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大中华文库:〈韩非子〉(汉英对照)》,此书的英文部分是在廖文奎译本的基础上改编而来,旨在钩沉稽古,再现经典,通过官方背书,对旧本拂尘去垢,扩大《韩非子》的传播效果,丰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谱系。然而,似乎此版本在西方受到了冷遇。当然,这个成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作者此处无意过多置喙于发行和推广等非译介活动,这里主要就《大中华文库:〈韩非子〉(汉英对照)》一书对于“副文本”的处理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此书全部删除了原译本中的注释(即廖译本)。廖文奎译本中一个显著的特色是其所做的精细的注释,上下两卷共计1 487个。这不仅是译者异化翻译策略的重要手段,亦是其心血的体现,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我们知道,先秦典籍语言凝练,含义隽永,加之《韩非子》一书中又运用了大量的历史典故,所以即便是译文在字面上力求与原文本语义对等,但缺乏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西方读者仍会在某些问题上感到“莫名其妙”。而注释可以为整个译本提供丰裕的文化语境,为读者省去了查找背景资料的繁琐,起到了弥隙填补译文文化空缺的重要功用,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下句的翻译即为一例:
例1: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韩非子·奸劫弑臣》
廖译:The sage who makes laws in the state is always acting contrary to the prevailing opinions of the age,but is in accord with Tao and Teh.[8]
廖注:道德here as elsewhere cannot be rendered as “reason and virtue” or “morals” or “morality”.Inasmuch as 道 refers to the natural course of the cosmos and 德 to the standard of conduct derived from it,transliteration seems preferable to translation.[9]
“道德”这组文化核心负载词,具有丰富且深厚的哲学内涵,在英语中很难找到与其语义完全对等的词汇,为了能正确传播作品的思想主旨,降低作品文化价值在传播过程中的损耗,廖文奎采用了音译加注释的方法。但是,在《大中华文库》版本中,所有的注释都被删去了,此处仅把原译文中的“Tao and Teh”改成了现代汉语拼音“Dao and De”。试问没有了注释的补充阐释,“道德”只是由指示语音的拼音字母所取代,西方读者的阅读如何得以顺利进行?这样的改编意义何在呢?举例说明如下:
例2:彼又使谲诈之士,外假为诸侯之宠使,假之以舆马,信之以瑞节。《韩非子·说疑》
廖译:They also disguise deceitful men as favorite envoys from the feudal lords and equip them with coaches and horses,provide them with jade and bamboo.[10]
廖注:瑞节.In ancient China credentials carried by envoys and messengers were made of 瑞 “jade tablets” or 节 “bamboo tablets”.[11]
同样,在《大中华文库》版本中,由于删去了所有的注释,读者无从得知“瑞节”是中国古代邦交礼仪的一种指代,一些和异质文化相关的内隐信息就这样流失了,jade and bamboo在西方读者看来就是一个突兀出现、不知所以的器物。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千余条注释被一笔勾销实在是令人扼腕,而编者也并没有交代这样做的理由。
其次,《大中华文库》版本的不足之二是对书后索引的删除。索引(Index),也称“引得”,是查阅图书中的知识、信息而编制的检索工具。索引由“西学东渐”而来,是西式治学的产物。1910年,王国维发表《世界图书馆小史》一文,首先将“索引”一词介绍给国人。[12]58在随后的“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明确提出,国学系统整理的第一步”是“索引式的整理”[13]1,引导国人重视编制索引、利用索引。这期间,最大的硕果就是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Sinological Index Office)在1930年至1950年期间所做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引得丛刊》共64种81册。这些编撰成果不仅对国内传统文化的整理与研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也受到了欧、美、日等地区和国家海外汉学家的重视,美国和法国对此项工作持续给予资助。⑦国际汉学界之所以对此表现出非常大的热忱,是因为索引是符合国际学术界检索通例的,也省却了汉学研究者翻检古籍之苦,有助于他们使用中国典籍开展专题性研究,大大便利了国际汉学研究。
笔者手头的几部英译典籍,如《墨子》英译本、《庄子》英译本、《孟子》英译本、《论语》英译本、《商君书》英译本、《申子》英译本都有索引部分,有的索引还相当细致,有十几页之多,译本和学术著作后面附加索引在西方已然是一种常规现象。就《韩非子》在英语世界的两个英译本而言,华兹生的节译本是有索引的,廖文奎的全译本,也是有索引的,而四卷本的《大中华文库:〈韩非子〉(汉英对照)》却删去了廖本中的索引。要知道《韩非子》一书十万余字,字数在“子部”(先秦时期)是最多的。如此巨著如果没有索引就好像一个城市没有了地图,学界又如何在这样一张由论说和典故所编织而成的庞大的信息网络中寻得研究线索?更何况,如前文所言,高罗佩、卜德、Alexander Soper已经在对廖译本的书评中对其索引不够完备的现象进行了指谪,《大中华文库》译本理应做出相应的改善。很可惜,《大中华文库》版本对这些意见不仅没有重视,反而删去了廖本中的索引,这种做法不符合学术惯例,也不方便国际汉学专家的研究,影响了这个译本的传播。
四、结语
综上,海外图书馆的馆藏量是评价中华典籍传播效果的重要指标,但并不是唯一的。实际上,根据传播学学者拉斯韦尔的5w传播过程模式,图书馆属于传播的渠道/媒介,而并不是传播的受众。一本书在图书馆中是有可能被束之高阁、珠玉蒙尘的。这正如明季金尼阁辗转将七千余卷西洋书籍引入北京南堂图书馆,只可惜这批介绍当时欧洲先进知识的图书大部分都无人问津,否则中国“开眼看世界”至少能提前一百年。所以,除了馆藏以外,我们必须将传播受众,即对读者的调查纳入进来,将评价方式多维化。此外,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在中华典籍外译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对诸如注释、索引、序跋等“副文本”的把握,使之符合国际学术规范,以如琢如磨的态度处理细节,精益求精,以期取得更为理想的传播效果。
注释:
①在译本研究方面,通过以“韩非子”“法家”“英译”“译介”“西方”等关键字组合在CNKI和CALIS的进行检索筛查,并未发现有任何以《韩非子》的英译本研究为主题的或涉及英译本研究的学位论文和专著。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出现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是寥若晨星,如蒋洪新教授和尹飞舟博士发表的《伯顿·华兹生的〈韩非子〉英译本漫谈》(1998)一文。在韩非子思想译介方面,也只有一篇宋鸿兵教授的《英语学界的“韩非像”》(2013)。
②如姜智芹:《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影响力——基于中英文本海外图书馆藏的考察》,《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40-45页。林广云,王贇,邵小森:《中国科技典籍译本海外传播情况调研及传播路径构建》,《湖北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第150-161页。
③《大中华文库:〈韩非子〉(汉英对照)》是在廖文奎译本基础上改编而来的,但本文将其做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是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大中华文库》是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指导下的“中国文化外译工程”项目,赞助者层面上强烈的官方色彩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原译者的主体性,笔者希望能探究此类“再生产”的译本的接受效果;其二,廖本于上世纪中叶由伦敦Arthur Probsthain出版,是著名的普罗赛因东方文学丛书之一(Probsthain’s Oriental Series),是一种典籍译介的“译入”行为。《大中华文库》版本对其的改编则可看作是“由入转出”,这种出版行为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观察。第三,《大中华文库》版本并不是对廖本简单的拂尘去垢,其对细节的处理值得商榷,因此此文将其列为独立的研究对象。
④廖译本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出版于1939年,后因作者辞世,在UNESCO的帮助下,下卷本于1959年出版,所以上下两卷相隔20年。
⑤晚清及以后的《韩非子》校释版本的底本多为南宋“乾道本”在清代的影抄本和仿刻本。而明代凌瀛初《韩非子订注》本、天启年间王道焜与赵如源同校本、赵如源之子赵世楷重订本等却流传到了日本学界。因此,日本学者依据明代校释版本所做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日本对于《韩非子》“西渐”的影响可参见拙作:《追根寻源:〈韩非子〉海外传播“经过路径”中的放送者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20年第2期,第161-171页。
⑥由于廖文奎博士在下卷发表之前就已经去世了,所以整部书的索引是由汉学家Dr.Neville Whynant所做的。
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闭校,引得编纂处被迫停止工作,乃至被撤销。在法国驻华大使戈思默的号召下,法国与中国学术界合作组建了中法汉学研究所,设立了“通检组”,继续编纂古籍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