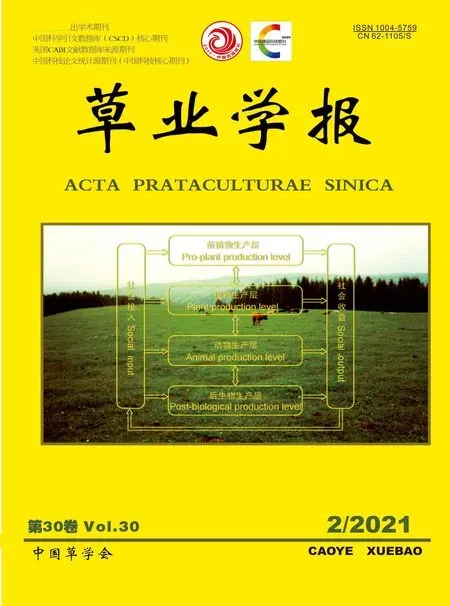明清时期苜蓿的地域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2021-02-27刘爽惠富平
刘爽,惠富平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00)
一般认为,苜蓿(Medicago sativa)起源于“近东中心”的小亚细亚、外高加索、伊朗和土库曼斯坦高地,常提到的苜蓿地理学中心应为现在的伊朗[1]。苜蓿最初作为观赏植物和养马饲草在长安宫廷中栽植,经过两千余年的传播,种植范围逐步扩大。时至今日,中国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西起新疆,东到江苏北部均有苜蓿种植。然而,这种分布格局并非天然形成,而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与社会变迁,且呈现出显著的时代与时空特征。目前所见的苜蓿史研究成果以孙启忠团队的系列论文最为突出,相关论文首先考察中国古代苜蓿物种的差异问题[1],综述中国古代苜蓿的植物学研究以及近代苜蓿的生态学研究[2−3];其次,根据古代文献对苜蓿的记载,比较详细地梳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明代以及清代等不同历史时期的苜蓿栽培利用情况[4−7];第三,对苜蓿在汉代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进行了分析[8],并基于苜蓿的起源探析其传播路径[9]。此外,邓啓刚等[10]从农牧文化角度探讨了苜蓿的本土化问题;李鑫鑫等[11]研究了紫花苜蓿引入中国的时间段及其起源的中心区域。以上研究虽然囊括了整个苜蓿史,成果内容丰富,涵盖了历史上苜蓿在中国引种及栽培的各个方面。但其研究重心偏重于苜蓿引种之后的中古时段,研究资料也较少涉及明清方志,对于苜蓿在明清时期的名实流变、传播历程的关注尚显不足。本研究基于古籍尤其是明清方志中关于苜蓿的记载与分布情况,试图从历史地理和社会经济的角度,呈现出苜蓿在明清时期的分布与传播的基本趋势,并进一步探究其影响因素。
1 苜蓿名实的流变
目前中国最早对苜蓿的记载见于司马迁[12]《史记·大宛列传》:“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萄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苜蓿自汉武帝时期传入中国,在后来的传播历程中出现了诸多异名,且与中国本土的植物相混淆,使得苜蓿名实问题一直以来没有定论。
1.1 古籍中苜蓿名实记载情况
古籍记载中苜蓿名实相对单一明了,对苜蓿花色的指向相对明晰。苜蓿在引种初期的称谓源于引入地域的大宛语bux sux 或伊朗语的buk suk 的音译名称,在唐代以前出现了诸如目宿、牧宿这类同音异字的称谓。在这些音译名的基础上,苜蓿称谓逐步定型。据清代王鸣盛[13]考证:“大宛以蒲陶为酒,马嗜目宿,蒲陶之陶作萄及苜蓿等字亦皆起于隋唐”。可知“苜蓿”名称的出现与定名在唐代方才完成。这一时期,苜蓿还出现了怀风、光风、连枝草等以苜蓿形态命名的异名。据葛洪[14]《西京杂记》记载:“苜蓿,一名怀风,时人或称之光风,茂陵人谓之连枝草”。这段文字在后世古籍中辗转传抄,成为对苜蓿的一种模式化描述。虽然这些记载都未指明苜蓿的花色,但农史学家研究认为,《四民月令》《齐民要术》《尔雅注疏》等古籍中所载“牧宿”、“苜蓿”实际上就是指紫花苜蓿[15]。虽然直到唐代《四时纂要》中方才出现明确指出苜蓿开紫花的记载:“凡苜蓿,春食,作干菜,至益人。紫花时,大益马”[16]。但是《四时纂要》对《齐民要术》的内容承袭颇多,而且皆是反映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农学著作,二书记载的苜蓿栽培技术基本相同。故而,贾思勰笔下的苜蓿当是紫花苜蓿无疑。后世农书中如《农桑辑要》《群芳谱》《农政全书》等皆记载苜蓿开紫花[17−19],所以,中国古代在北方大量种植的苜蓿即为紫花苜蓿。
苜蓿开黄花的记载首见于梅尧臣咏苜蓿的诗:“苜蓿来西域,蒲萄亦自随……黄花今自发,撩乱牧牛陂”。此后,关于黄花苜蓿的记载主要见载于《本草纲目》[20]与《三农纪》[21]。李时珍所谓黄花苜蓿很可能是黄花草木樨(Melilotus officinalis),这一点清代学者程瑶田[22]在《释草小记》中已有论证。学者多以《三农纪》中苜蓿开黄花的记载来讨论花色,张宗法[21]对苜蓿的记载转述了《本草图经》:“春生苗,一科数十茎,一枝三叶,叶似决明而小,绿色碧艳,夏深及秋,开细黄花,结小荚,圆扁,旋转有刺”。张氏首先引述《本草图经》中关于黄花苜蓿的植物学特性的记载,再引其“塞毕力迦”的异名,该异名出现于《翻译名义集》[23],最后罗列《西京杂记》《史记》之记载,唯一自己的表述在于“生产北方高厚之土,卑湿之处不宜其性也”[21]。由此可知,张氏前面所描述的实际上指黄花苜蓿,后部分则是紫花苜蓿,并不是单一地指向苜蓿只是开黄花。张氏所论,其实是清晰地陈述了紫、黄两种苜蓿的客观存在。直到清末吴其濬[24]的《植物名实图考》中清晰地记载了紫花苜蓿和两种开黄花的野苜蓿,近代日本学者松田定久[25]认为,此3 种苜蓿分别为紫苜蓿(Medicago sativa)、野苜蓿(Medicago falcata)和南苜蓿(Medicago den⁃ticulate),后两者开黄花。综上所述,古籍中所见苜蓿基本上花色分明,也少有其他异名相淆,呈现出一条比较清晰的苜蓿载录线索。
1.2 地方志中苜蓿名实记载情况
地方志中见到的苜蓿记载则是另一番景象,其名实相对复杂,对苜蓿花色多未指明。以往研究对苜蓿名实的考察多在古籍这一条线索中寻觅,难免会流于片面。若以方志中出现的苜蓿异名来反观苜蓿名实,或许会得到一个相对清晰的认知。笔者基于中国方志库对苜蓿异名记载予以整理与分析(表1)。

表1 明清方志中所见“苜蓿”部分异名Table 1 Alfalf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records of the chorography
总体而言,苜蓿异名在南方地区出现较多。如苜蓿在四川的传播中多与本土植物相混杂,《简阳县志》记载:“苕菜即苜蓿,俗呼紫云英”[26]。这里苜蓿明显与苕菜(Vicia hirsuta)和紫云英(Astragalus sinicus)相混淆,紫云英与苜蓿同属豆科,常为方志同载,在云南却区分鲜明:“今玉溪农田用之肥草,亦即紫云英。一类邓川饲牛之盘龙草,亦即苜蓿”[27]。据《金堂县志》:“巢菜,俗音或呼巢,如潮音,又讹为韶”[28]。苕菜是巢菜的别称,又据《滇志》:“别有马豆,蜀之巢菜,北方之苜蓿”[29]。可见苜蓿讹为苕菜,是由于“苕”“巢”“韶”之音误,这种被误为“苕菜”的苜蓿在植物学性状上与紫苜蓿相近。记载更多的是南苜蓿,“大宛苜蓿,宿根,饲牧牛马。一种南苜蓿,俗呼马苜须,皆野生无种者”[30]。“马苜须,亦名金花菜,又名盤岐头”[28]。这里紫苜蓿与马苜须分列记载,马苜须即为南苜蓿,即黄花苜蓿的一种。
在东南地区,黄花苜蓿的异名更多。据《吴县志》:“苜蓿种类甚多,吴地所有只两种。其一农家所植曰家苜蓿,开紫花者,其茎可食。俗名荷花郎。……其一为野苜蓿,又曰南苜蓿,土名或称金花菜”[31]。金花菜为南苜蓿,即野苜蓿的一种。此外,表1 所列黄花菜、三叶菜、磨盘草、秧草、草头、草子、盘岐头等异名大都可归为黄花苜蓿。这些异名,有的是与其他植物相混淆所致,有的则是地方语言差异造成的称谓。如湖南永州称苜蓿“一名马齿苋,自生无种”[32],很显然苜蓿的野生状态使得人们将马齿苋(Portulaca oleracea)与之混为一谈;湖南湘阴则称苜蓿为“木耳菜”[33],广东吴川称之为“蒲藤菜”[34]。广东《大埔县志》说明了苜蓿异名在当地产生的原委:“苜蓿一物,豆科植物,埔人曰鰗鳅豆。盖物非素识,必非土生,外至之物,必先询名”[35]。可见,苜蓿异名就是在这种“询名”的过程中,以本土植物相比附,再加上方言音译的差异,从而使得苜蓿名实出现了这种复杂的文本记载。
2 明清时期苜蓿的地域分布
基于古籍与方志中关于苜蓿异名的记载,可看到苜蓿名实的流变实际上是苜蓿在中国引种与传播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缩影。时至明、清、民国时期,关于苜蓿的记载大量见诸方志,使得本研究在考察苜蓿的具体地域分布时有据可循。虽然仅凭静态的文本记载难以清晰地认识苜蓿在各省的具体传播情况,但通过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因素予以分析,可以从总体上呈现出苜蓿在全国分布与种植的基本态势(图1)。

图1 苜蓿在明清民国方志中记载次数分布Fig.1 Alfalfa’s records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an period
2.1 西北地区
陕西自汉武帝时苜蓿引种之后,先是在长安宫苑内小范围种植,然后向四周辐射传播,渭河附近的咸阳、临潼、栎阳一带形成了较大范围的集中种植。到了明代,“陕西甚多,饲牛马,嫩时人兼食之”[36]。清代陕西苜蓿记载次数约51 次,广泛分布于30 多个州县。关中地区依旧是苜蓿分布的集中区域,华县、澄城、陇县、蒲城、扶风、咸阳、凤翔、汧阳、临潼、蓝田、富平、周至、鄠县等地均有分布,一路由宜川、延长、延川、绥德、榆林、神木达到最北端的府谷,陕南地区仅见商南县有载。甘肃苜蓿在明代时集中于平凉、临洮、庆阳三府,即甘肃东部与南部。平凉“其地千二百三十顷,树苜蓿茼麦用牧,奚三千官僚无饥,衣食皮毛足资,……牧专其事,不杂以耕”[37],这些地区专种苜蓿用于畜牧。清代时进一步由陇东南延至陇西的张掖、敦煌,基本沿河西走廊一带分布。新疆苜蓿在明清以前主要沿天山山脉南麓分布,且塔里木盆地的南缘绿洲也有分布。清代时随着疆域扩展,苜蓿分布除上述区域外,伊犁府治所绥定有“苜蓿沟”,以种植苜蓿得名。嘉庆《回疆通志》所记喀什噶尔有专门的苜蓿地亩牧放牛马,每年饲喂马匹牛只所需的苜蓿达四十八万五千六百八十斤,其中回民交纳四十万五千斤,其在城郊园所种苜蓿有八万零六百八十斤[38],可见苜蓿种植数量很大,并有严格而精细的管理。因产量巨大,苜蓿已经成为南疆地区的一宗货产,嫩时可食,烘干后可为饲料,与其他货物一样,莎车府“皆本地所产,不独商人专利于中国,且多转贩于外洋”[39]。宁夏苜蓿集中于中卫、固原;青海苜蓿主要分布于东部的西宁、循化。
2.2 华北地区
河北苜蓿在明清方志中记载次数最多,共计约126 次。明代时,主要由北而南散布于宣化、固安、河间、雄县、清苑、赵县、南宫、广平等地。清代则遍地开花,记载次数约80 次,除上述州县外,清代苜蓿分布由北到南,如唐山、遵化、丰润、滦州、赤城、涿鹿、霸州、保定、阜平、博野、蠡县、行唐、深泽、正定、灵寿、任丘、沧州、献县、饶阳、衡水、阜城、巨鹿、南和、清河、邢台、鸡泽、永年、邯郸、魏县、大名等地,都有苜蓿的分布。京津地区的大兴、密云、静海、蓟县也有苜蓿记载。山西苜蓿记载次数仅次于河北,明代时主要分布于太原、怀仁、泽州,三地分属于晋中、晋北、晋南,以上区域同样在清代呈现出大面积种植,遍及40 余县。太原府有“苜蓿村”“苜蓿渠”,皆在村田之中,为农家常产[40]。河北、山西两省苜蓿在明清时期总体上呈现出由点及面的传播态势。山东苜蓿在明代时记载仅见于鲁西的夏津、汶上、济阳、邹县、历城、郓城诸县,皆用于蔬食。清代仍以鲁西最为集中,并向东推进,遍布多数州县,一直到胶东半岛。河南苜蓿明代时主要分布于濮阳、安阳、开封、兰阳等地,清代已经遍布30 余州县。
2.3 江淮地区
江淮地区的苜蓿从明代开始,得到显著推广。安徽苜蓿在明代方志中记载次数约20 次,分布于凤阳、徽州、阜阳、寿州、泾县、定远、天长等地,到了清代则“郡邑皆产”[41]。除上述地区外,黄山、亳州、蚌埠、舒城、铜陵、砀山、萧县、怀远等地皆有。江苏苜蓿在明代见载于兴化、徐州、靖江、沛县等地,清代时,江宁、江浦、上元、句容、江都、徐州、邳州、沛县、铜山、城武、丰县、睢宁、丹徒、荆溪、南通等地皆有。
2.4 东南沿海地区
东南沿海各省中就方志记载次数而言最多的是浙江,广泛分布于浙东、浙西的平原山地之中。沿海其他省份苜蓿分布较为零散,福建苜蓿在明代时散见于南平、延平、南安,清代时则延至相邻的古田、福州、漳州、连江。广东苜蓿,明代时主要见于新会与封川,清代时由珠三角向周围地区延伸,西边吴川,东边惠来、大埔、始兴,北边清远、佛冈皆有分布。广西苜蓿到民国时期方有同正、隆安两县记载。
2.5 云贵地区
云南苜蓿在明代时“惟澄江一郡于初芽时采为菜,余郡间有,青时以饲马”[29],清代时见于石屏、陆凉、普洱、玉溪、蒙自等地,主要分布于滇东南。贵州明确记载苜蓿的是道光《松桃厅志》[42],厅治在今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
2.6 华中地区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是现存最早的涉及湖北、湖南两省范围的省志,其《土产》部分载有苜蓿[43]。湖北苜蓿最早记录出现于唐代郢州(今湖北钟祥),此后万历《承天府志》、同治《钟祥县志》亦有载,可见钟祥是湖北最早也是相对稳定的苜蓿分布区。到了清代,苜蓿记载广泛见诸于湖北其他州县,鄂中除钟祥外,荆州、监利等地;鄂西如郧西、房县、光化(今老河口)、竹山、枣阳等地;鄂东如黄州、蕲州、红安等地,以上地区都是苜蓿分布区。湖南苜蓿,元代时多为野生,明代时却未见载于方志,清代时,乾隆《湖南通志》列苜蓿于“蔬属”[44],但多集中于湘西的辰州府(今属怀化)、辰溪、凤凰、吉首、慈利、永定(今属张家界)、沅陵地区,其他则散见于零陵、澧州、湘阴。江西苜蓿,明代主要见载于南安府(今南康、大余、上犹、崇义4 县),府境4 县的物产中皆有苜蓿。清代时,宁都、新城、进贤、安福、吉州(今吉安)等地散见。
3 明清时期苜蓿传播的影响因素
苜蓿在中国传播的前提条件是其生理适应性与功用多样性,其优良的性状极大地适应了古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时至明清,苜蓿已经广泛分布于西北、华北、江淮、东北地区,在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西南边疆等地也有一定的分布,苜蓿在明清时期的利用与传播有着特定的历史因素。
3.1 明清卫所与苜蓿种植
苜蓿作为大宛马的饲料被配套引入中国,不仅改良了中国畜牧的饲料结构,增强了马匹体质,同时其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军备物资,与历代马政兴衰息息相关。贯穿明清两代的卫所制度成为苜蓿传播利用的一大动因,苜蓿成为卫所屯田的重要物资。据笔者观察,明代卫所分布与明清苜蓿分布有着一定程度的吻合(图2)。
结合明清卫所的分布与变迁以及明清厅县方志具体考察,可见这种吻合并非偶然。以漕运卫所的仓储、转运、屯田3 项职能来看,苜蓿与卫所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沿布于京杭大运河一带的卫所一般拥有相应配置的仓储体系,苜蓿草就是其中重要的囤办物资。据成化《中都志》记载:“本府(凤阳府)总数岁办……苜蓿种子九石三斗五升一合八勺”[46];谈迁[47]在《枣林杂俎》中也记载了南京贡船每年运往京城的用度,其中包括“御马苜蓿种四十扛”,苜蓿即为仓储体系中重要的转运物资之一。此外,《漕运通志》中所载漕运系统的屯田处包括3 处草场,京卫、中都、直隶各一处,都属于清江漕运行府管辖,即今江苏宝应、淮阴一带。江南漕运卫所共54 个,凤阳卫所38 个,都有大量草场[48]。在这些军屯草场中,苜蓿是重要的生产项目。
兹以江宁府为例,考察府属各县草场地与苜蓿田地的科则与征税情况。1)江宁县:草场田地六则,每亩三分到八分不等;苜蓿地三则,一则科银七分,一则科银六分,一则科银五分四厘。原额草场田地180 顷19 亩,共租银999 两;原额苜蓿地4 顷99 亩,各科不等,该银35 两[49]。2)上元县:草场田地,科租银四分;苜蓿田地二则,一则科租银七分,一则科租银五分[50]。3)江浦县:草场田地若干则,苜蓿田地科租银七分[51]。4)六合县:草场田地若干则。崇祯三年,清理六合新涨洲场征租银项,包括御马监征收苜蓿银1000 余两[52]。5)高淳县,草场地科银五厘有奇[53]。6)句容县:荒熟草场170 处,约36983 亩,成熟地14341 亩。原额每亩科银四分,共银576 两[54]。由江宁府的苜蓿田地数以及输纳课税时的科则情况,研究可得到如下3 点信息。首先,方志中将草场与苜蓿田地并列,是因为草场之中往往包括大量苜蓿种植,甚至以苜蓿为主。其次,草场与苜蓿田地皆属于军屯官田,苜蓿田地被作为征税对象,由于其效益较高,故而苜蓿田的平均科则要高于一般草场,说明苜蓿的集中种植产出高于一般草场的效益。再者,这些草场、苜蓿田地属于“归并省卫实在田地”[55],说明在清代卫所陆续裁撤之前,它们都属于卫所屯田,苜蓿则是卫所屯田中不可或缺的经营项目。
山东文登、威海、即墨3 地,其中的巡检司与卫所参差分布;浙江绍兴、上虞、宁波,明代松江府和清代川沙厅;福建漳州府、福州府有诸多千户所;广东新会之广海卫,大埔、佛冈、始兴等地,以上地区苜蓿都是“极普通之物”,为当地物产[56]。在明清边疆卫所中,大多为实土卫所,如乾隆初创建的黔东南九卫为军屯,目的在于弹压当地民众,新疆三所则是以民屯为主,将戴罪之人迁徙于此,使其从事生产。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苜蓿在充实边疆的过程中,不仅促进了边疆开发,也使得苜蓿传播与分布更加广泛与深入。清代厅制的设置在空间分布上呈现“边缘性”,且多由明代卫所演变而来,此举促进了国土开发利用和汉族文化播迁[57],而以厅志所载物产可以窥见,偏远地区在设置卫所时,苜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黔东北的松桃厅、湖南的凤凰厅、永绥厅、乾州厅,招募军民屯垦,用以弹压苗民,开发当地土地,发展农耕经济[58],这些都离不开苜蓿的种植与利用。其中的贵州松桃厅于雍正八年(1730 年)设置,嘉庆二年(1797 年),升松桃厅为直隶军民厅,该地以苜蓿为蔬食;湘西的凤凰厅有苜蓿冲汛驻兵70 人,苜蓿在厅境分布广泛,“所生多有”[59];还有乾州厅常设苜蓿园,属辰州府。总之,苜蓿伴随着明清卫所制度的设置与变迁,在边疆地区、漕运沿线广泛传播,卫所作为一种军事制度,往往伴随着屯田与移民,苜蓿则发挥着马之饲料与人之蔬食的功用。

图2 明末卫所分布热区图[45]Fig.2 Garrison heat distribution area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3.2 明清“灾区社会”与苜蓿利用
有学者指出,一部人类社会史,也是一部灾害史,并同时又是一部“灾区社会史”,尤以明清时期的“灾区社会”最为显著[60]。苜蓿的广植与利用可以看作是明清灾区社会的写照,亦可视作明清社会对灾荒的应对。明清荒政类书对苜蓿的记载比比皆是,如《救荒本草》中将苜蓿列为野菜之“上品”,其“苗叶嫩时,采取煠食”[61]。明清方志多将苜蓿与瓜、韭、菘并列于“蔬部”,虽然农家种植规模不大,但据《汲县志》所载几乎每家种二三亩[62],而且野生苜蓿十分普遍,与蒲、莎、苇等并列于“草部”,大量野生苜蓿多自生无种,人们可随时收取。可见,苜蓿不仅是农家春季常备的栽培蔬菜,更成为一种重要的救荒野菜。清人吴其濬[24]有言:“世祖初令冬社防饥年种苜蓿,未审其为騋牝为黔黎也”。清初举人冯应晋曾以家中二百亩苜蓿救民饥荒,家人说苜蓿本是养畜之用,如何能给人吃?冯氏言:“吾忍以畜故饥我乡里耶?”于是,立命传呼,苜蓿顷刻而尽[63]。这里所谓“騋牝”与“黔黎”的看法,实际上反映了苜蓿的食用在人畜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界限。
由马嗜苜蓿到人食苜蓿,反映了在灾荒频仍的年代,苜蓿更加普遍地用于食用与救荒。在江南地区,苜蓿“春初民间遍食之”[64];在广大北方地区更是如此,河南汲县“其贫者春月掘野菜,凡柳絮、榆叶、榆钱、苜蓿,嫩时皆采以为食”[62];安徽黟县“民生啖为羮俱佳,此物长生,种者一劳永逸,贫郭尤宜种之”[65];《息县志》以苜蓿为“野菜”,如乾隆五十年(1785 年)大饥,山东东昌府人赵作柱“出粟济饿者,种苜蓿十余亩,听人采食”[66];江苏邳县“邳人多于村旁种之,以饲牛马,亦间有采为蔬者”[67];甘肃地方志中,苜蓿被列于“草属”5 次,列于“蔬属”17 次,苜蓿多数时候都用来充饥,“值岁荒,有百余人采食苜蓿”[68];湖北枣阳“盖其苗叶既堪为蔬,而子又可炊,诚备荒之良品也”[69]。可见,苜蓿成为当时贫苦人家的“救荒奇菜”和贫困城邑的“备荒良品”。
3.3 苜蓿融入了耕作栽培体系
明清时期,随着精耕细作农业的深入发展,苜蓿更加广泛地与农业相结合。苜蓿融入农耕技术体系不仅使得与苜蓿相关的农艺技术走向成熟,并且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苜蓿的本土化和农耕化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尤为显著,具体而言体现在如下3 个方面。
栽培技术和深加工技术的成熟。东汉崔寔[70]在《四民月令》中最早记载了苜蓿的分期播种和“一年三刈”的收割方式,北魏贾思勰[71]的《齐民要术》则进一步阐述了种苜蓿之法,“地宜良熟,畦种水浇,一如韭法”。明清农书大都沿袭此法,苜蓿栽培技术的简易与传统蔬类成法的套用,使得苜蓿能够持续、长久、便捷地在中国传播。苜蓿饲蔬两用,不仅限于马匹,还可用于其他畜禽的饲料。清人杨屾[72]《豳风广义》认为猪羊鸡鸭等家禽要想繁衍生息,“惟广种苜蓿”,在诸种食料中,“唯苜蓿最善,采后复生,一岁数剪,以此饲猪,其利甚广”,并且详言苜蓿的加工与贮藏,收割晒干后,“用碌碡碾为细末,密筛筛过收贮”,以冬月贮藏的干苜蓿来饲养家禽已为农家常态。
苜蓿作为绿肥植物不仅增加了土壤肥力,其根瘤菌固氮的生态学特性也极大地改良了盐碱地。最早记录苜蓿肥田的是贾思勰,“每至正月,烧去枯叶。地液则耕垄,……则滋茂矣”[71]。明清时期苜蓿作肥愈加普遍,在华北地区,“苜蓿能暖地,不怕碱,其苗可食又可牧放牲畜,三四年后改种五谷,同于膏壤矣”[73];在江浙地区,专门种植苜蓿用作肥料,江苏阜宁“沿海垦殖公司多植之以作绿肥,亦可食”[74],江阴县有“金花菜,花细而黄,俗称秧草,因乡人刈之,以粪秧田,四乡无不种此”[75];浙江鄞县“有紫黄二种,刈后水浸淹之用以肥田,甚资其利”[76],奉化“草子皆以粪田,农家多植之”[77];湖南辰溪苜蓿“野生,农家采以肥田,亦有食者”[78]。以苜蓿治碱的特性用于改良盐碱地的技术则出现在清中叶以后,最早记录以苜蓿治碱地的是清人盛百二[79]的《增订教稼书》,该书是作者在山东为官时所写,成书于1778 年,盛氏自言“苜蓿法得之沧州老农”,具体方法是在碱地上“先种苜蓿,岁夷其苗食之,四年后犁去其根,改种五谷蔬果”。另据《山东通志》所载:“苜蓿平原一带,碱地所在皆是”[80]。可知至迟在清代中叶后,采用苜蓿治理盐碱地已经在河北、山东普遍实施。
苜蓿与其他作物的轮作。早在唐代就有苜蓿与小麦(Triticum aestivum)间作套种的初步方法,“苜蓿若不作畦种,即和麦种之不妨,一时熟”[16]。此后,元代《农桑辑要》、清代《农桑经》均有记录,但更加细致高效的轮作方法在清末陈恢吾的《农学纂要》中才有详尽叙述,其中原理也论述清晰。如陈氏所论,苜蓿为深根,甘薯之类为中根,禾类为浅根,“深根为浅根者吸氮气”,即苜蓿的根瘤菌固氮作用能给土壤补充氮素营养。故而,有苜蓿与冬小麦的套种;具体轮作之法有:莱菔—大麦—苜蓿—小麦;莱菔—小麦—大麦—苜蓿—小麦;芦菔—大麦—苜蓿—雀麦—番薯—小麦[81],以上诸法皆宜。
4 小结
苜蓿在中国有着漫长的传播史,明清方志中出现了大量苜蓿异名,这种复杂的文本记载也充分反映了苜蓿在明清时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基于各地方志中的苜蓿记载次数进行计量分析,可以直观地看到,明清时期的苜蓿分布主要集中于西北、华北、江淮等地,其次是在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西南边疆等地。苜蓿的广植与利用是各种历史社会关系的综合产物。首先,明清时期卫所的设置是一大动因。一方面,苜蓿作为军马草料成为卫所屯田中不可或缺的经营项目,明清时期江宁府存在数量不少的专门苜蓿田地和草场,其较高的效益产出和科则增加了国家税收,使苜蓿在江淮地区与漕运沿线深入传播;另一方面,边疆卫所的设置使得苜蓿在游牧区进一步传播,为历代边疆开发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其次,明清灾区社会促发了苜蓿功用发生了一定的转变,由马嗜苜蓿到人食苜蓿,反映了在灾荒频仍的年代,苜蓿更加普遍地用于食用与救荒,成为贫苦农家的“救荒奇菜”和贫困城邑的“备荒良品”。再者,苜蓿栽培技术的简易与传统蔬类成法的套用,使得苜蓿能够持续、长久、便捷地在中国传播。苜蓿饲蔬两用,不仅限于马匹,还可用于其他畜禽的饲料。在清中叶后,采用苜蓿治理盐碱地已经在河北、山东普遍实施,苜蓿与其他作物的轮作原理与方法已经颇为成熟。总之,与苜蓿相关的农艺技术已经形成体系,并被广泛应用,苜蓿的本土化与农耕化进一步加深。
《全闽诗话》对苜蓿文化属性有一精准概论:“汉贵武,则以饲马;唐贱文,则以养士,一物足以观世矣”[82]。苜蓿在中国的传播史不仅仅是物质层面,在文化与精神上,苜蓿或能成为观世之变迁的重要载体。苜蓿兼具“草”与“禾”,饲料与蔬食,游牧与农耕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历代马政与军事屯田已经将苜蓿作为“草”的属性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农家将苜蓿融入农耕体系之中,使其作为“禾”的属性大放异彩。汉唐时期的苜蓿更多时候扮演着“草”的角色,明清时期,苜蓿则渐渐地转为“草”“禾”兼具的角色。然而,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只是农耕地区种植业与家庭畜牧业在个体家庭范围内的有限结合[83],苜蓿的传播利用栽培史则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对苜蓿史的研究不仅要从科学与技术层面加以挖掘,对于苜蓿物种的传播历程及其文化属性亦要有所把握,从而为当下的苜蓿栽培利用提供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