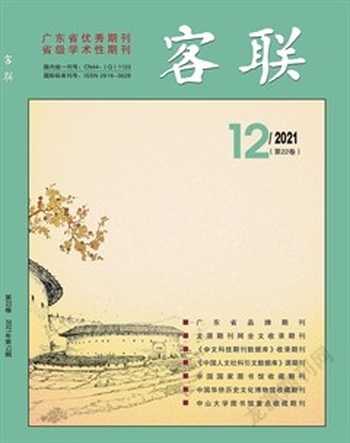浅论海子的抒情短诗的精神世界
2021-02-25常思扬
常思扬
摘 要:海子诗学博大、独特、自成体系,是基于海子对人类精神艺术这一大空间综合考察的结晶,它不仅吸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汲养,更因其对存在与生存的深切关注而具有了世界性的眼光。通由海子诗学,不仅可以切近海子其诗其思,也可透视当代中国诗歌甚至世界范围内的一些重大诗学问题。本文将就海子的抒情短诗,从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面全面展开论述,展现海子在诗歌中构筑了一个丰富而自足的精神世界,以及死亡意识。
关键词:海子;诗歌;死亡;意识
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關至龙家营之间的铁道上卧轨身亡,随身带着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新旧约全书》和《康拉德小说选》等四本书,这一事件被第三代诗人视为一次神圣的献祭。陈晓明说,“海子死了”——这是那个时期任何一次关于诗歌的、乃至关于文学的讨论会的开场白。足见海子之死在当代诗坛所造成的影响。自那以来,“海子的死亡”一度成为评论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争议的焦点在于海子之死有无“形而上”的意义。一种观点认为海子的死亡是以身体和诗歌为牺牲对缪斯女神的献祭。
一、宿命论的悲剧意识
从浪漫型诗歌的特点来看海子的诗歌,它将生命的意义隐喻到一种叫“远方”的空间、介质或乌托邦之中,它所要做的,“并不是把事物表现得很明确,一目了然,而是把疏远现象进行隐喻式的运用看成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情感成了中心,巡视自己的丰富多彩的周围,就把它吸引到这个中心里来,很技巧地把它转化为自己的装饰,灌注生气给它,而自己就在这种翻来覆去中,这种体物入微,物我同一的境界中得到乐趣”。海子希望把语言从道统束缚中解放出来,修复诗歌与神性意旨剥离之伤,生成语言的诗意,还原其思想载体的本质,从而达到“藻雪精神”的审美效果。海子为神性复原、人性复苏和艺术复兴的理想倾尽心力,孤注一掷,他对这一努力的悲剧性也有所认识,像希腊悲剧和意大利文艺复兴一样,它们“是两个典型的创造亚当的过程。带有鲜明的三点精神:主体明朗、奴隶色彩(命运)和挣扎的悲剧性姿态”。在这种宿命论的悲剧意识中,海子认为自己已经“走到人类的尽头”。
爱情的经历带给海子心理上的灼伤,他将思想的锋芒指向自己的内心,形成郁积和创伤,并将其转嫁给他所处的时代。他通过情欲的道路进入哲学思考的大门,在幻觉中洞见了真理。对他来说,一切似乎不曾存在,却又像所罗门的鞭子一样抽打在他的“哑脊背”上。他希望“活在珍贵的人间”,生活的现实却是在传统的夹缝中求生存。他所追求的生活模式和创作方式一方面表现出对传统的潜在认同,但另一方面,他革新的锐气极为刚猛以至渴望脱离既有的传统模式,自己也从中被割裂。海子对其所处的时代的感受是:“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秋》)。
二、以死亡来宣告过去的结束和未来的开启
海子多次在诗歌中提到“最后一夜的抒情”,表明他作为“诗歌皇帝”的野心——以死亡来宣告过去的结束和未来的开启。这样以来他既享有像撒旦那样进行破坏的末世快感,又享有上帝最初创造世界的那种荣光,这样的死亡也就无可畏惧。
在书写《太阳七部书》的过程中,海子对“太阳”的信仰和追逐已经达到“迷狂”状态,一种类似肉体的兴奋,这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纵欲狂欢的时刻,理性简化为单纯的情感。时间“通过轮回进入元素”,世界回到一个共时性的原点。联想其他在思想和艺术领域做出巨大成就的人物,尼采在幻觉中肯定自己就是火焰,是太阳,他说:“走向太阳是你最终的行动;对知识的欢呼是你最终的呐喊”。
三、成为太阳的一生——“心的青春是献给太阳的祭礼”
在海子看来,“死亡比诞生更为简单”(《土地篇》)。事实上,海子一直纠缠在矛盾的状态里,不加区分地对待艺术和现实生活。他渴望像凡·高给弟弟提奥写信时所表示的那样,兼做画商与圣徒。既被他人阅知又不牺牲艺术的神圣和纯粹性;既期待《旧约》中的严苛与复仇,又向往《新约》宣示的宽容与救赎。他一成不变地对美加以追求,几乎达到自恋的程度,除了对艺术本身的关注以外,他表现出对一切的漠视。海子在谈到《太阳·断头篇》时说:“诗中的事迹大多属于诗人自己,而不是湿婆的。只是他的毁灭的天性赐予诗人以灵感和激情”(《太阳·断头篇》)。然而面对没落的世界,他又试图拯救出“应该救出的部分”;诗人应该“关心粮食和蔬菜”,关注生命存在本身。他像温克尔曼那样沉迷在古希腊世界的理想里,但相对于那个古老的文明,他只是一个“迟到者”,因而为此唏嘘不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大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他们“解析了生活中的烦恼,并将对它的感觉直接传达到我们心中,它不是一种巨大的悲伤或激情,而仅仅是对时光流逝的感觉,是必须置身于凡间琐事的梦幻者的厌倦,是生活于真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是一种对休息的渴望,一种怀旧病,一种思病,那是一种非常孩子气但又富有寓意的悲伤,它与全体人类对于熟悉的地球和有限的天空的最终的悔恨具有相同的意义。
黑夜使人向往太阳的初生、光芒、朝霞以及那个居于夜空之上的神秘实体,黑夜使人得到还原。如歌德所说,“混合一切形态为一的黄昏和黑夜很容易生出崇高之感,而使一切事物区别和隔离开来的白昼却把它驱除”。顾城的短诗《一代人》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说出了那个时代的心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对比海子在《太阳·诗剧》中的诗句:“两只乌鸦飞进我的眼睛。/无边的黑夜骑着黑夜般的乌鸦飞进我的眼睛。”如果说顾城对时间和光明还抱有期望的话,海子则对黑夜的呼唤和追求更加彻底,对白昼的反叛更加决绝,像他在1986年8月的《日记》中所说的,“黎明并不是一种开始,她应当是最后到来的,收拾黑夜尸体的人”。黑夜在海子笔下成为时间的象征,“黑夜是什么?黑夜之前是什么?黑夜之后紧跟着谁”(《桃树林》)?这些疑问其实是对古老的“斯芬克斯之谜”的重复。他说,所谓的黑夜就是“让自己的尸体遮住了太阳,上帝的泪水和死亡流在了一起”(《太阳·弥赛亚》)。黑夜和黎明,在80年代的文化记忆中,成为对一种遥远的文化理想的祭奠或呼唤。在诗人的思维中,它们成为神的意志的体现:上帝既是破坏者又是创造者。
参考文献:
[1]西川.海子诗全编[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773页
[2]西川.海子诗全编[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9页
[3]刘小枫.诗化哲学[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7页
[4]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