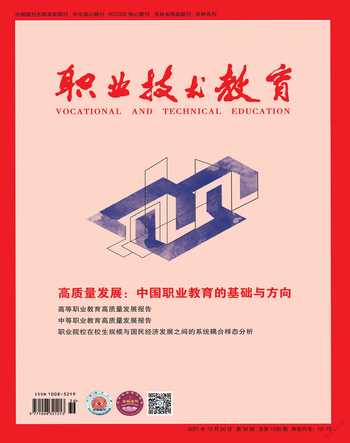壬戌学制确定过程中职业教育地位确立研究
2021-02-23王志兵
摘 要 1922年北洋政府实施壬戌学制,职业教育作为民国教育体系中的一种教育类型,确立了法律上的地位。在壬戌学制的提出、起草、议决和实施过程中,以全国性民间教育组织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为首的教育团体,各类学校及民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不遗余力地大力推进,特别对职业教育体系在壬戌学制中的设置进行了全面、深入、广泛的讨论,推动了职业教育在壬戌学制中的地位确立,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性教育改革,打破了千百年以来封建陈腐教育思想的桎梏,完善了民国的教育体系,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的职业发展需求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 壬戌学制;职业教育体系;地位;学制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36-0073-08
1922年,北洋政府实施壬戌学制(即一般称为新学制),将职业教育纳入新学制系统,职业教育作为民国教育体系中的一种教育类型,确立了法律上的地位。此后,民国教育界、实业界的团体和有识之士等为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开展了不懈的探索、研究和实践,践行着“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1]的职业教育目的,极大地促进了人的职业发展,推动了经济社会的进步。应该说,职业教育纳入新学制系统经历了一个探索酝酿、积极推动、深入讨论、审慎决定的过程,使职业教育一开始就有较高的起点,形成了较为完整和完善的体系架构。
一、实业教育向职业教育转向的起因
1912年1月,民国政府成立后,教育部即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明确将清政府时期的学堂改称为学校,特别是把学校中带有封建遗存及满清政府遗留的思想和内容,一律废止清除,并确定将在多方征集各地教育人士的意见后,实施学制改革。其后,民国教育家们对如何进行学制改革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并向教育部提出意见和建议,教育部对学校系统草案三易其稿。同年,教育部正式颁布《教育宗旨令》《学校系统令》和各类学校令及规程,正式实施壬子癸丑学制。
根据《学校系统令》和后续颁布的各类学校令及规程中的培养宗旨来看,将学校由低到高分为了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初等小学校(即国民学校),是义务教育,为启蒙、初始教育阶段;第二层次高等小学校(同时可设补习科,兼承担职业上的预备教育)、乙种实业学校,为初等教育阶段;第三层次中学校(同时可设补习科)、师范学校、甲种实业学校,为中等教育阶段;第四层次大学、高等师范学校、专门学校,为高等教育阶段。正式独立设置了乙种实业学校、甲种实业学校,但对前三个层次其他学校都明确规定了学生毕业后,可进入后续高一级教育阶段继续学习深造;而实业学校的学生,只到甲种实业学校毕业,就无后续升学的规定和途径了。1913年8月,教育部公布《实业学校令》,明确实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为“以教授农、工、商业必需之知识、技能为目的”,甲种实业学校实施“完全之普通实业教育”,招收14岁以上、高等小学校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乙种实业学校实施“简易之普通实业教育”,招收12岁以上、有初等小学校毕业的学力者[2]。由此可见,实业教育的类别比较单一,只是为了使人能获得职业工作,培养面向工作一线的,有一定实际知识、技能的操作人员,这为实业教育的层次提升和实业人才的高水平发展带来了极大制约,实业教育实际上是“断头教育”。
再从壬子癸丑学制中实业教育实施的情况来看,虽然对清政府时期的壬寅癸卯学制的实业学堂进行了改革,但由于受“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思想影响,教育思想固化,教育方法僵化,其面向生产生活一线培养有一定实用知识技能人才的目标并未能很好实现,还是陷入了知识理论教育的泥潭,学生所学知识不能实施训练并进行实际操作,学用不能合一,缺少操作技能训练,严重脱离社会生活的问题[3],致使学非所用、学非所能,用非所学、用非所能,实业教育成为事实上的“失业教育”。同时,受世界职业教育大潮涌动的影响,以黄炎培先生为代表的教育界先驱们,敏感地认识到职业教育对社会和人的职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开始了由实业教育向职业教育转向的研究、探索和实践。虽然在1922年壬戌学制实施前,职业教育并未得到法律地位的认可,但以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和中华职业学校的创立为引领,在推动和发展职业教育方面,开展了探索性的理论探讨和创新实践,这也为后续壬戌学制改革,确立职业教育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教育必须与社会的进步发展相适应,支撑、促进与服务社会发展进步,在壬子癸丑学制实施过程中,其不完善的弊端也逐步显现。1915年《教育公报》第九期刊发了教育部的《整理教育纲要》,提出要改革小学中学学制。同年4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湖南省教育会提出了《改革学校系统案》,列举现行学制的六点弊端:“(一)学校之种类太简单,不足谋教育多面之发展;(二)学校之名称不正确,名误实受其害矣;(三)学校的目的不贯彻,致令求学之人三四年一易其宗旨;(四)学校的教育不完成,依规定之学科时间,恒有充其所教,磬其所学,不能得具足之生活力者,而毕业反为社会之累;(五)学校的阶段不衔接,非失之过则失之不及;(六)学校的年限不适当,全系学年失之长,而各校分配又不适当。”同时指出,如果在整个学校系统中只是先改革小学中学学制这一部分,姑且先不谈其改革难以完善,即便是能完善,而后期其他部分需要改革时,势必与已经改革的部分有关联,致使已经改革的部分还要再行讨论更改,“教育百年事業,岂能枝枝节节乎?”[4]湖南省教育会的《改革学校系统案》,对学校系统进行了重新设计,几乎是全盘推翻了壬子癸丑学制的学校系统体系。其中,对实业教育部分,建议在小学教育改为一级制,分国民教育四年(针对仅只要接受义务教育者)和预备学校三年(针对有能力接受初级以上的受教育者)两类平行设置的基础上,从预备学校毕业的学生,可进入文科学校、实科学校九年毕业,或进入副文科学校、副实科学校六年毕业。实业学校招收副文科学校、副实科学校毕业学生,或文科学校、实科学校学习满六年的学生。此种对实业学校的设计,与壬子癸丑学制的学校系统相比,取消了实业学校的甲种、乙种的分层,统一了招收对象的标准,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实业学校教育的起始水平基准线,但同样的问题是无后续升学的规定和途径,实业学校也更显单一,缺乏递进层次。
二、推动改革学制系统过程中对职业教育体系的设计
对湖南省教育会提出的《改革学校系统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一次会议认为,现行学制是否应该改革,涉及国家教育体系构建的重大问题,应通过审慎、郑重的程序进行。因此,并未提交大会讨论作出决议,只是提出“征集各省意见,以三个月为限,详细备具意见书,送由教育部解决;一面由联合会陈请教育部,在未解决以前,暂勿变更现制”[5]。这次会议第一次正式提出学制改革,表明民国教育界改革壬子癸丑学制的愿望,学制改革被正式提上研究、推动的日程,由此开启了推进新学制改革的进程。为了在学校系统改革中确立职业教育地位的高度,职业教育界在此后从理论和实践上开展了深入的研究,思考设计在改革学校系统中的职业教育架构。
1919年,在太原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次会议确定第六次会议把改革学制作为提案的主要内容之一。1920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六次会议,依据第五次会议的提案方针,提出学制议案的有安徽2件,奉天、云南、福建各1件。会议讨论后认为,这种重大议案,还是不能在会议期间,根据少数意见,骤然进行决议。为认真对待和研究改革学制系统的提案,会议形成了四点处置意见,并函告各省区教育会。一是请各省区教育会在召开第七次会议的两个月前,先组织学制系统研究会,将研究的结果以议案的形式,分送各省区教育会和第七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事务所;二是在第七次会议上应将学制系统案议决,再议其他各案;三是在第七次会议召开时,请教育部派专员到会上发表关于学制改革的意见;四是将联合会历次会议收到的关于学制议案及会外意见书汇编成册,送各省区教育会,以便于研究[6]。学制改革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进入了实质性的推动阶段。
1921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次会议在广州召开,重点研究讨论了改革学制系统,共收到省区教育会提交的关于改革学制系统的提案11件。经前期的深入调查、研究,会议的广泛讨论,综合考虑、吸纳各方意见,最终通过了第七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关于《学制系统草案》的决议,通告向各省区教育会、各教育行政机关和高等教育机关征求意见,并在全国各教育杂志刊发,公开征求意见。同时,要求各省区如认为可行,应拟定方案,在有关学校试行。《学制系统草案》将整个学校系统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段,在每段上都设计了职业教育系列。其中,初等教育段为六年制小学教育,规定在第四学年后,斟酌考虑地方情形的需要,增设职业准备教育;同时,对年长失学者设补习学校。中等教育段分类较多。一是独立设立一年期、二年期、三年期的完全职业科。二是独立设立渐减普通学科、渐增职业学科的四年期、五年期职业科。三是在六年中等教育段分三年的初级中学和三年的高级中学(即“三三制”),初级中学为完全的普通教育,三年高级中学实行选科制,分为职业科、完全普通科、师范科。在初级中学毕业后,由学生根据需求选择对应升学的高级中学科类。对于职业科,根据各种职业需要的普通学识要求不同,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也可除“三三制”外,实行“四二制”或“二四制”。另外,为推行职业教育,需要培养职业教育师资,规定于高级中学职业科内设职业教员养成科。四是专门为做工儿童开设的补习学校,凡半天、夜间、周日上课的都属于补习学校。在高等教育段规定,高级中学的职业科、完全普通科、师范科毕业的学生,都可以进入大学或高专的相关学科继续深造学习;同时,大学需附设专科(指面向某一专业方向或领域的),不定学习年限,主要面向志愿对大学某学科的一个方面或其他职业需要学习的学生[7]。此草案对职业教育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设计,贯通了职业教育从初等、中等到高等教育段提升的系统渠道。
民国教育的相关团体和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只有将职业教育纳入学制系统之中,职业教育的发展才有教育体制上的保证和法律地位上的保障,也才能构建出完善的教育体系。他们以超前的意识、创新的思维、改革的精神,为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据不完全统计,到1921年全国甲乙种农工商业学校、男子职业学校、女子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慈善性质的职业学校、职业教员养成所已有719所。研究职业教育的人员队伍不断壮大,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从成立之初的800多人增加到4179人,社员覆盖全国及南洋群岛的华侨和英、美、德、日等国的留学生[8]。这些都为职业教育列入学制系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对新学制系统草案中职业教育体系的讨论
第七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学制系统草案》的发布,在全国各地教育界引发了讨论的热潮,许多教育类杂志专辟了学制改革研究专号。《教育与职业》1921年第9期设计了讨论草案中职业教育部分的专刊。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看,草案中的规定是否适当,对四方面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一是中等教育段的职业科设置,一年期、二年期、三年期的完全职业科,渐减普通学科、渐增职业学科的四年期、五年期职业科,完成三年的初级中学普通科后继续三年职业学科的职业科,这三种与选科制度的采用是否完全符合?二是专为做工儿童而设的补习学校,归入中等教育段是否适当?三是初等教育段中职业准备教育的设置,限于小学第四年后是否适当?是否应该仅限于职业准备教育?四是职业教员养成科的设置,限于附设于高级中学是否适当?”[9]同时提出,如果草案实行后,现在的农、工、商业学校应该怎样改革?教育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全面、广泛、深入地进行探讨,对草案提出修改建议。
(一)关于中等教育段职业科年限设置的建议
由于职业教育的职业应用和实用属性,中等教育段的职业科设置是最为复杂和详细的,因而成为讨论和关注的重点。讨论中普遍认为,中等教育段的职业科既要类别全面,又要层次完整,更要年限灵活伸缩。
陈浚介提出,中等教育段的职业教育年限分类太复杂,“虽则要能顾及各地方的伸缩自由,也应当有个限制,只要求得不相差太甚就是啦”[10]。同样,李步青认为,职业科分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五种制度,期限以年为限,极不适当,“旧制以整齐划一最为世人所诟病,不如规定最短最长之年限,在此最短最长之限度中,任其自由伸缩,以便实施”[11]。而且,对于其中一年期的完全职业科,陈浚介认为,学生所学的完全达不到所需要用的程度,不如不要设置;章欽亮也认为,所学甚少,不如归并到补习教育内,为职业补习的一种形式。李步青更是对一年期、二年期、三年期的完全职业科提出质疑:“此特称为完全职业科,似以完全纯粹职业之义,这完全之义是否适当?”其指出,人的生活中应具备两种能力:一是日常生活的道德、知识和技能,这应当在普通教育中培养;另一是从事职业的能力,应该以特别的教育培养,而职业的能力中,大部分为职业的技术技能,完全是在职业科培养出来,还有一部分为职业的品德、性格,应在职业科和普通科中各自实施特别的训练。草案中的“完全”二字,容易让人误解认为普通科与职业无关,如果以“完全”之意,职业科中全部除去普通学科,不仅会阻碍职业学业的学习,而且即便能培养得技术技能熟练,“似此机械式技术,恐不足以谋人类之幸福,且亦何须设学校以养成之”。所以,在职业科中学习普通学科,是为了应用于职业生活之中,并不是在所谓完全职业科中剔除普通学科就能达到职业教育的目的[12]。
对中等教育段中的渐减普通学科、渐增职业学科的四年期、五年期职业科的设计,职教界在讨论中持比较一致的反对意见。王舜成认为,类似于原学制中的甲种实业学校,既然要改革旧学制,就不应该再有此类似的不适应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为了多给学生入学选择考虑的机会,可以将此四年期、五年期职业科改为高级中学段的一年期和二年期的职业科,这样,则在中等教育段的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期间,都有1~3年期的不同程度的职业科[13]。陈浚介指出:“既嫌其杂,而学程又特殊,论其学力,普通科不及普通的初级中学,职业科又不及三年期的完全职业科,效率小而费时多,非驴非马,没有道理!这二种不如改了一种三年普通二年职业的职业科。”[14]李步青提出,按这种方式机械地渐减普通学科而对应的渐增职业学科,是根本错误的。因为,有的普通学科应当在职业学科前修学完毕,而有的应当在各学年都要学习,所以,并非单纯的以渐减、渐增为标准来考量普通科目及占比的多少,应看职业科的特性和学习年限,也要根据对学习者设定的预期目的而定,是随职业科不同而不同的[15] 。
(二)关于扩大补习教育的建议
在中等教育段设立专门招收做工儿童的一年期、二年期补习学校,职教界在讨论中也普遍不赞成。
首先,设在中等教育段不合适。陈浚介认为,做工儿童的知识程度很低,而且水平不一,补习学校设在中等教育段,则必须要求做工儿童的文化程度要在小学水平之上,这是不现实的。“像这种复杂的,没有一定编制、设备、课程……的学校,怎能强之使一律特定在初级中学里边呢?并且将来义务教育普及之后,也可无须设的了”,所以这种补习学校在学制系统中“既无相当位置,而又暂时的,可以不必列出来”[16]。潘文安认为,补习学校在初等教育段之上,所定的起点太高,实际上绝大部分做工儿童是没有小学毕业程度的,没有受过教育和受了一、二年教育就出校做工的不在少数,因此,“程度一层,与其失之过高,毋宁降低一些”,“应该放低眼光,从浅的着手,循序渐进,庶几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17]。潘吟阁提出,由于草案中的初等教育段不是完全为义务教育,所以很多人是不可能接受到整个初等教育的,只接受了一部分初等教育的人,后面必定都会去从事职业,从事职业后,如果没有补习教育以补充其缺少的初等教育部分,和适用于其职业应用的职业教育,这部分人就永远不能享受到教育惠及的利益。因此,将补习教育的起点放在六年完全初等教育之后,应予以变化,可以更为灵活,既可以在四年的义务教育之后的第五年开始,也可在六年完全初等教育之后的第七年开始,通过放低补习教育的起点,给予各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以选择的余地空间[18]。江苏省立第二女师附属小学也提出:“与其提高而不实际,宁使降格而求普及,这种补习教育可以移在初等教育段的后二年,或者可以比较的普及。”[19]
也有观点提出,补习教育在新学制系统中可独立设置,从初等教育开始到中等教育为止,如果学习者还想提高水平,可进入高专或大学的各种分科。陆规亮分析认为,年长失学的人情况差异很大,学识程度上,不可能整齊一致,有一字不识的,有识字少许的,有已经工作但缺乏相当职业知识的;年龄跨度大,各自的思想认识、观念不同,日常习惯也各有差异,自我提高的进度也不一致。对这种参差不齐的状况,不可以统一授以初级中学的课程,也不适宜与一般小学生在一起上课。此特别属性的补习教育,应该独立设置与小学、中学平行并列的补习教育系列,“无论半日、半夜、日曜,与那中等程度的学校选科等,纵横斜度,量程插入,均无妨碍”,使得分类条理更为清晰[20]。
其次,适用对象只对做工儿童不合适。王舜成提出,补习教育的范围很广,形式各有不同,不能仅限于对象为做工儿童,社会上年长失学的,为境遇所困而急于谋生的,有升学的愿望但无经济能力和空余时间的,比比皆是,这些对象都要依靠补习教育的帮助,得到知识、技能的提升,这也是体现平民教育的目的[21]。李步青认为,设立补习学校的宗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延长初等教育的含义,使通过初等教育培养而未达到国家期望的一般国民应具备能力标准的对象,由补习教育使之达标;另一方面是为受义务教育后,不能升入正式学校或辍学的对象,为提高其本人工作岗位的能力,利用工作外的闲暇时间,通过补习教育学习相关学科,以能在其工作中得到应用,提升工作能力水平。补习教育的作用是,既能补充普通教育又能补充职业教育的知识技能,都是为了弥补不能升入正式学校学习的不足,而给予适当的学习机会。所以,补习教育既是为了年长失学者,也是为了做工儿童,“蓋补习之人以受义务教育后或有同等学力,不能入正系学校者为主。正不必问其年龄尚为儿童与否”,而且“补习科目以切近职业为主,普通修养副之”[22]。章钦亮、季云等也纷纷发表意见,赞同以上观点,认为应扩大补习教育的对象范围,才能符合社会的现实状况。
再次,学习年限设定为一、二年不合适。年限应根据实际需要有伸缩的空间,王舜成认为,补习教育在四年义务教育之后就应该设立,而且不必限定为一年期、二年期,尽可延长到初等教育段以上,让受过完整六年初等教育者也有选择补习的机会和余地。李步青也提出,在草案中规定了,初等教育段宜为年长失学者设补习学校,和在中等教育段专为做工儿童而设补习学校,应该是两种不同的补习学校,但是这两种针对的对象是不可能明确区分开来的。因此,初等教育段的补习学校规定在四年义务教育之后,如果义务教育年限延长了,则补习教育随之后延。同时,中等教育段的补习教育限定为二年是不适当的,一是因为盛行科目制的选修,较完备的补习学校在补习知识技能的程度上,分了高等、中等、普通三级水平层次,使得不能进入正式学校学习者有多重选择的机会,所以,按照这种情形是不应该限定二年的;二是因为补习学校设立的本意,就是面向已工作者利用闲暇时间补充学习,由于工作的缘故,他们可能是每周修学一些时数,或是在休息日学习,或是在工作不忙的季节集中一段时间学习,由此,补习教育应该根据其课程学习的实际时数进行累计,而不是按年计算,所以,限定二年也是不符合实际的[23]。
(三)关于灵活考量职业准备教育的建议
对于初等教育段四年义务教育后的二年职业准备教育的讨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要扩大范围,一种认为可以取消,两种观点虽然各异,但一致的是对草案中职业准备教育的规定并不赞同。
职业准备教育需要扩大范围的观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层次可以多一些。王舜成认为,从社会的实际情况来说,最基层劳动者的职业知识技能最为缺乏,以致工作效率低下,因此,初等职业教育有很大的推广发展空间,如果“仅籍职业准备为设施初等教育之唯一方法,匪但范围太狭,实使职业教育不能普及于社会”,在初等教育段应该“于职业准备教育、补习教育以外,再设一种相当之初等职业学校(如工徒学校、乡村农业学校之类),亦不嫌其多也”[24]。“至于在初等教育段的后二年,实在可以有一种完全职业教育,不必限于职业准备”[25]。季云也认为,“可视地方情形而异其办法,倘一地学校少,则此校既须为技术的教授,不独准备已也;若一地而有数校,则分准备、实施二者,分校教与,较易施行”[26]。
二是内容要相对广泛一些。“小学课程得就地方情形,酌量授以职业上必需之智”[27]。陈浚介指出,真正的职业教育范围很广泛,不是教会儿童做成一件好的物品、学成一种完美的技能,就是职业教育的全部了,“凡是增进儿童职业的兴味,养成儿童职业的习惯等,都是职业教育主要的目的”,所以,职业准备教育“当注重职业陶冶”[28]。季云认为,由于职业种类的不同,职业准备教育的实施也应切合职业种类的特点和儿童的接受能力,比如,工商科目的技术性较高,也较为精细,应在初等教育四年以后才可开展;而对于农科,儿童们从小就接触拔草、栽菜等,有直观的感性认识,则在二年级便可以开展农科的职业准备教育[29]。
三是时间应该提早一些。陆规亮建议在小学二年或三年后就可以进行职业准备教育,理由是:一从年龄上看,初等教育入学年龄有六、七岁的,有八、九岁的,差距较大,在小学二年或三年后,学校可因地、因时、因人根据实际情况,开展适当的职业准备教育;二从现实境遇上看,社会生活日趋艰难,十岁以上的儿童很多不能在校学习,而直接开始谋生了,在他们接受了二年或三年的初等教育后,实施职业准备教育,对他们到了谋生的时候必定是有益处的[30]。潘吟阁也认为职业准备教育应稍稍提早,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只读完小学四年义务教育毕业的,在第四年就接受一年的职业准备教育;另一种是读完初等教育六年小学毕业的,从第五年开始接受二年的职业准备教育,这样小学无论是四年毕业还是六年毕业的,都能受到职业准备教育和职业教育,便以培养其生活的能力[31]。
认为职业准备教育可以取消的主要理由是:一是概念内涵不清。李步青提出,职业准备教育是“为学习职业之准备乎?抑从事职业之准备乎?”“惟其主义含混,易令实施者迷惑其趋向”。而且,入小学的儿童将来是否必须学习职业科并不确定,并且职业科目繁多,学生的志愿各不相同,“断非同一之准备所能达其目的”。加之,“惟设职业科者始可附职业准备之实,然既为职业科又不当更有职业准备之名”[32]。二是无实际意义。潘文安认为,小学中儿童所学习的各种功课,已经带有几分职业陶冶内容,况且职业准备教育不是完全职业教育,程度上降低也可以,提高些也可以,灵活度比较大,既然在小学里已带有几分职业的陶冶,而小学以上又设置了各类职业科,广义上都是为职业而准备的,所以,职业准备教育“在学制系统上可以删去,只要在说明中提及一句罢了”[33]。
(四)关于广设职业教员养成科的建议
由于职业教育处于发展之初,又是发展的当务之急,但师资的异常缺乏,成为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职教界一致认同,草案中将职业教员养成科仅附设在高级中学职业科过于狭窄,必须要扩大培养的学校范围,大力培养职业师资。
陆规亮提出,由于各层次职业教育的程度、要求不同,可在初级师范和各类各层的职业科广设职业教员养成科,培养适应不同层次职业教育所需要的职业教员。陈浚介认为,不仅是初级中学和职业准备科的教员急需培养,而且高级中学职业科的教员也急需培养,因为“现时的甲种实业学校里的教员,他的学理虽很高深,但是在技术方面、实验方面、制造工程方面……等能力,大都是很薄弱的”。同时,如果僅在高级中学职业科附设职业教员养成所,“便利的所在,不过在技术方面而可得些联络,而于教育研究方面,可谓完全落空。但是职业科的教员,须要技术和教学法两全才好,倘使有了技术而不懂教育,是不行的”。由于职业教员要具备专业的理论知识、教育的技艺和较高的技术技能水平,对职业教员的培养要求就很高。陈浚介建议,职业教员养成科附设在师范学校,因为“在教育研究方面既得联络,而在技术学习方面也无缺憾,何以呢?今后之师范教育是行选科制的,对于职业科方面,必定有所建设,决不是现在的状态,所以无须顾虑的”[34]。
潘文安认为,面对职业教育师资缺乏的事实,“造就的路不妨稍广”,以应急需。也可在初级中学暂时设置职业教员养成科,专门招收小学毕业或中等学校学满一、二年的学生,“使他们半天上课,半天上工,毕业以后,即供各地初级职业学校或职业科的需用,未始不是一时治标的办法”;对于高级中学毕业的学生,可仿照旧制中师范二部的办法,设职业教员养成科,再学习一年,担任较高职业学校的教员。从长远来看,职业教育日益发达,师资问题要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考虑,“造就师资的机关,尽可因时因地,自由斟酌,不必要一定的”[35]。李步青建议:一是“师范有力者亦得兼办职业教员养成科”,二是师范可“依旧制之二部办法,设讲习科,专收纳毕业于四年制以上职业科之生徒”,三是“大学师范科或高等师范得附设职业教员养成科或设讲习班”[36]。
四、新学制对确立职业教育法律地位的作用
职业教育界基于现实,面向发展,对职业教育在新学制草案中如何设置的深入分析、广泛讨论,不仅理清了职业教育的体系脉络,明确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和实施的方法,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明晰了思路和要求,而且通过积极参与新学制草案体系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学制改革的进程。在高涨的教育改革呼声浪潮中,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迫于形势,于1922年9月在北京召开“学制会议”,邀请多名教育专家和各省行政负责人对新学制草案进行论证、修改、审订,充分考虑和吸纳了教育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其后,正式颁发实施壬戌学制。
对职业教育讨论的意见,壬戌学制中基本都予以了采纳,职业教育体系的规定与原草案相比有了较大变化,使职业教育发展有了更为宽泛的自由度和灵活度,有利于职业教育的探索性、创新性发展。在初等教育段,删除了四年后职业准备教育的设置,规定:一是“小学课程得于较高年级,斟酌地方情形,增置职业准备之教育”;二是“初级小学修了后,得予以相当年期之补习教育”;三是“对于年长失学者宜设补习学校”。在中等教育段,对职业教育的分类进行了简化、归并,不再细分年限规定,使中等教育段的职业教育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规定中变化为:一是“初级中学施行普通教育,但得视地方需要,兼设各种职业科”;二是“高级中学分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但得酌量地方情形,单设一科,或兼数科”;三是按原来旧学制设立的甲种实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或高级中学农、工、商等科;四是“各地方得设中等程度之补习学校或补习科,其补习之种类及年限视地方情形定之”,与初等教育阶段的补习教育相衔接;五是“职业学校之期限及程度,得酌量各地方实际需要情形定之”;六是按原来旧学制设立的乙种实业学校酌改为职业学校,收高等小学毕业生,但依据地方情形,亦得收有相当年龄而学习完初级小学的学生;七是“为推广职业教育计,得于相当学校内酌设职业教员养成科”。在高等教育段,扩大了高等职业教育的范围和放宽了入学对象的资格条件,规定“大学及专门学校得附设专修科,修业年限不等(凡志愿修习某种学术或职业而有相当程度者入之)”[37]。
壬戌学制为职业教育多元发展提供了条件和依据,如何推动新学制落实,以求得职业教育的稳步推进和迅猛发展?潘吟阁提出,在职业教育的设置上,各地要“视地方职业状况与教育经费而酌定职业科之办法。地方重要职业其性质繁复难习者、教育经费充裕者,可办六年期或四、五年期职业科,地方重要职业其性质较简易者、教育经费较少者,可办一年期或二、三年期职业科”,当然,既然能办六年期职业科的,也可兼办一年期的简易职业科,总之,“宜视地方情形而活用学制,不可稍抱拘墟之见”。同时,各职业学校必须注重职业研究先行,才能使职业教育有现实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充分发挥出服务社会进步、服务职业岗位需求、服务人的职业发展的作用。要研究“地方上何种职业最为重要?何种次之?衣食于是业者有若干人?是业之关系何如?是业之所为者何事?能详知其一切内容否?是业一切职务如分析要目、列为教程、果须若干时间,方可使天资中等之人完全习熟?”这些都是关注和从事职业教育,实施新学制者,不可不知的,“职业教育知地方职业最难,能打破此难关,新学制方有生气”[38]。
王舜成以农工商科职业教育为例,认为落实新学制应从四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分科趋重实用而不广泛偏狭”,即,农工商科是专业类别,每一专业类别内又分若干不同的具体专业科,既不能把专业类别就作为一个专业科,致使“科目繁杂,修业难专,发生应用困难之结果”,也不能把具体专业科分得过于细狭,导致“一专科内必需之相关科学缺漏必多,于实地致用时,亦必应付为难”,提出了具体专业科的设置要科学、适宜的观点。二是“教科中宜多与以应用经济学上之必需常识”,因为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除了从事一线的技术技能操作,也可能从事生产经营管理,则“普通经济学以外,凡农工商各分科内所有之应用经济学,自宜增加份量,详为教授。因指挥管理等业务上之种种常识,皆由应用经济学而来也”。三是“实习与经营场所应分别设备”,即,实习与经营不可混为一谈,采取同一种方式方法,“学校中之设备,不但注意技术上之练习,并宜示以经营上之模范”,要做到对学生技术上的训练,和对学生实际经营管理能力的提升与积累并重,通过实习熟练专业技能,通过经营掌握实际工作的经验。四是“学校应取公开主义谋与社会相接近”,职业学校直接服务于社会生产生活一线,要主动让社会了解学校的办学宗旨、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的实际状况,不能闭门办学,脱离社会实际。要与社会、实业界密切联系与合作,争取支持,职业教育才有生命力,才能取信于社会[39]。这些都充分体现出职业教育必须坚持切合实际、务实推进、以求实效、服务社会的思想导向。
五、余论
应该说,壬戌学制对职业教育具有开创性的里程碑意义,郑汉文总结道,“从漠视职业教育,达到重视职业教育”,“从职业科附设在普通学校内,达到独立设立一贯的职业学校”,“从以普通学校教师充职业科教师,达到设专科训练职业学校师资”,“从立在旁枝的地位,达到与普通教育并列的地位”[40]。究其原因:一是世界职业教育发展、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给人们教育思想和认识带来的震撼性的冲击和影响;二是对实业教育弊端的深刻反思而产生出求变的强烈责任愿望;三是社会经济发展对职业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四是为解决社会失业问题,促进人的职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纵观壬戌学制的提出、起草、议决和实施,经过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讨论和研究过程,由全国性民间教育组织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会议提出和积极推动,有民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和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首的教育团体及各类学校,大力提倡和不遗余力地推进,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地位,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性教育改革。其意义更在于,打破了千百年以来封建陈腐教育思想的桎梏,完善了民国的教育体系,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了人的职业发展需求。
参 考 文 献
[1]中華职业教育社.职业学校设施标准[J].教育与职业,1931(4):535-543.
[2][4][5][6]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732.850.848.863.
[3]王志兵.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工读结合”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践探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3(10):77-82.
[7]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学制系统草案[J].新教育,1921(2):307-310.
[8]黄炎培.民国十年之职业教育[J].教育与职业,1921(8):1-4.
[9]中华职业教育社.征求教育界对于新学制草案职业教育一部分意见的问题[J].教育与职业,1921(8):6.
[10][14][16][28][34]陈浚介.学制草案关于职业教育的我见[J].教育与职业,1921(9):12-15.
[11][12][15] [22][23][32][36]李步青.对新学制草案之一部分的意见[J].教育与职业,1921(9):16-24.
[13][21][24]王舜成.对新学制草案职业教育一部分的意见[J].教育与职业,1921(9):7-11.
[17][33][35]潘文安.学制与职业教育[J].教育与职业,1921(9):25-28.
[18][31][38]潘吟阁.对新学制草案职业教育一部分的意见[J].教育与职业,1921(9):29-32.
[19][25]江苏省立第二女师附属小学.初等教育与职业教育[J].教育与职业,1921(9):66-67.
[20][30]陆规亮.对新学制草案职业教育一部分的意见[J].教育与职业,1921(9):37-39.
[26][29]季云.对新学制草案职业教育一部分的意见[J].教育与职业,1921(9):35-36.
[27]章钦亮.对新学制草案职业教育一部分意见[J].教育与职业,1921(9):33-34.
[37]学校系统改革案[J].新教育,1922(5):1031-1034.
[39]王舜成.对于新学制草案实行后甲种农工商业学校改革之意见[J].教育与职业,1921(9):53-56.
[40]郑汉文.职业教育在学制上的地位[J].教育与职业,1932(1):3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