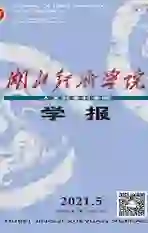民族旅游发展促动民族村寨振兴研究
2021-02-09吴海平
吴海平
摘要:发展民族旅游能有力契合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是民族村寨振兴的重要推手。西江民族旅游通过民族文化资本再生产、景村融合与现代化升级、文化自觉与利益诉求、多元共治与民间智慧、产业共建与利益共享的发展模式有力促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同时,面临大众文化的繁荣、民族文化的真实化、文化景观的消弭与冲突等问题时,应当以人为本,释放权利空间;增强文化认同,实现价值主体性互动;重构公共文化空间,推进城乡一体化振兴民族村寨。
关键词:民族旅游;民族文化;民族村寨;乡村振兴
基金项目: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民族旅游产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研究”(2019SYCX JJ203)
一、导言
民族旅游作为新兴的旅游发展模式,“异文化”体验服务呈现繁荣之势。2019年全年国内游客60.1亿人次,较2018年增长8.4%,旅游收入增长11.7%,仅贵州省一地2019年全年接待游客11.3亿人次,居全国第一,全省旅游总人数比上年增长17.2%,全年旅游总收入增长30.1%,占全年GDP的73.5%①。由此可见,民族旅游带动区域产业兴旺在民族地区着力于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已成为强力推手。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新时代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1]。民族村寨振兴是民族地区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必经之路,是传承优秀民族文化的关键举措,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基础保障,是民族地区共同繁荣的根本所在。民族地区特色村寨众多,享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旅游资源,新时代的民族村寨在文旅融合的进程中不断焕发出自己新的活力。民族旅游发展有力的契合了乡村振兴战略,能增进城乡交融、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加快多产业升级、建设宜居生态、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是振兴民族村寨的核心动力。
二、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动力机制
瓦伦·L·史密斯于1977年首次定义“民族旅游”为“销售给公众的离奇有趣的本土且具异族情调的民族习俗”,民族旅游主要以地方独特民俗和地域奇异吸引他人拜访、观看民族表演、购买当地特殊产品[2]。周大鸣指出民族旅游是旅游形式的一种,游客在少数民族的居住地体验独特文化和生活方式。[3]光明囧认为民族旅游的本质应表征为族际间的交流或是跨文化的体验与观察[4]。三者共同强调了民族旅游的“流动”式的异文化体验,其一是受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吸引,其二是文化之间的互动。除此之外,李忠斌,文晓国侧重于游客参与感知的角度,民族旅游是旅游者具有目的倾向性,去到民族聚居区域,体验当地文化,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领略其文化特质,参与生产、体验生活状态的活动[5]。杨昇,王晓云等从民族旅游功能出发,民族旅游则不仅利于发展民族文化,也会促进民族村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6]。由此可见,民族旅游是一种旅游者来到旅游目的地体验异文化,进行文化交流的旅游活动。
民族旅游的本质以民族文化为内核,衍生出整合生态、交通、饮食、农耕、建筑、休闲娱乐等产业的经济活动。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与城市社会网络资本的重构,市民的“乡土”性在消逝,村庄成为最后留守的精神家园。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人们开始寻找精神生活的满足,增加自己的幸福满意度与获得满足感。民族旅游的关键驱动分为两个方面。DANN在“旅游动机”这一问题进行了社会学处理,集中于民族旅游“推—拉”理论的讨论[7]。郭景福,赵奥也认为市场化需求的拉力与旅游资源的拉力是民族旅游的关键动力[8]。民族村寨拥有独特魅力的文化旅游资源刺激了旅游市场,形成对游客的巨大吸引力。民族村寨最根本的生命源泉是民族文化,民族旅游的核心竞争力是“异文化”的体验与互动,民族旅游在不断塑造文化品牌产生的虹吸效应是民族旅游保持持续旺盛生命的内在核心動力。旅行者通过“异文化”体验的形式刺激旅游市场需求的外在拉力与民族村寨村民对自身主体利益诉求的内在推力共同作用于民族村寨旅游,形成了民族旅游的外在核心动力。这种内外耦合的驱动是民族旅游基础和持续的核心动力。
三、“西江模式”促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表征
西江千户苗寨拥有原生态的自然资源,差异化“乡土性”资源,稀缺的民族文化资源,具备较为丰厚的文化旅游资源。多元共建共享的“西江模式”不断促进多产业的融合与发展。西江民族旅游发展在振兴民族地区民族村寨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成功塑造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品牌效应,使得“西江模式”成为民族村落乡村振兴战略的示范区[9]。西江民族旅游在打造宜居生态、加强乡风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村民共同富裕发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各个层面积极促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
(一)民族文化资本再生产促动产业兴旺
在内部诉求和政策主导下,伴随西江苗寨从自足自给的小农经济到民族旅游为主导的商品经济转变,民族文化资源被资本化与民族旅游共生共融,并在外部市场需求下进行文化资本再生产[10]。西江苗寨年游客接待量从2005年的7.5万增幅至2018年的753万,翻了近百倍,吸纳了超过1300户生产经营户,这些多元融合的产业链带动本地和就近就业人数近3000人。仅2019年上半年,千户苗寨接待游客712.68万人次,同比增长18.67%,旅游收入60.58亿元,同比增长23.19%②。民族文化的变迁是民族旅游发展的必然结果,蓬勃的旅游市场的推动下,西江民族文化旅游衍生出了“食、住、行、游、购、娱”的多元化融合产业链。苗族的酸汤鱼,鼓藏肉、酒文化礼仪、吊脚楼民宿等引爆了住宿业和餐饮业的发展;直达景区的公路使得黔东南首府凯里市到苗寨的路程比以前缩短了四倍,景区的发展促动四方建构有效串联整域交通脉络,不断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建设。“美丽西江”歌舞专场、民族博物馆动静态的文化展示点、苗族银饰锻造、刺绣、蜡染制造等专业合作社的出现将民族工艺品纳入旅游活动中,民族文化产业蓬勃旺盛。除了就业红利,旅游产业兴旺也带来了本地的创业,创富浪潮。寨内超过三分之一的农家乐为西江本地人所经营,“后粮仓”“阿幼民族博物馆”“西江饭店”等本土自创品牌年营业额均超百万元,极大增强了村民的创富信念。旅游市场直接刺激电子商务业的发展,以雷山银饰、雷山银球茶为主打,带动辐射区域加工业和本土手工业的兴旺。
(二)景村融合与升级促动生态宜居
“景村融合”,景与村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二者互构形成一个完整体———“西江式”景村融合。民族的原生态性不仅是民族旅游的本质特征,也是苗寨美丽乡村建设的灵魂。西江苗寨作为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区,在保留村寨的基础上,以和谐生态旅游景区的要求建设苗寨,通过民族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苗寨的整体建设,实现苗寨景点化。苗寨充分贯彻协调发展的理念,从而形成了旅游景观、原始生态景观、苗寨村落景观三位一体的景村融合模式。与此同时,苗寨作为村民生活环境,生产环境,生态环境的基本场所,也完成了现代化升级。寨内村民依然保留着传统的耕作习俗,在西江的春耕季节保持着传统农耕民俗活动。得以保存的梯田农耕文化与田园观光结合,形成了独特西江风貌,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到观光农业的现代化生态环境的升级;从“靠月亮”换成“千户灯火夜景”,村寨空间与文化的融合重构不仅实现了村民生活环境的升级,也成为西江民族旅游新的名片。民族旅游的本质便是对当地生活的亲身体验,景村融合对于村民最直接的改变是生产环境与生活环境的重叠,村民在实现生产方式生活化的转变后,也使得生产环境得到现代化的升级。环境整治、厕所革命、街巷平整、配套灯光、完善对外交通等一系列的升级提质改造工作,原生态的美丽并未因现代化的转变而消逝,不断提升的人居环境,和谐生态观的村寨建设,使得苗寨焕发出新时代民族村寨的独特魅力。
(三)文化自觉与利益诉求促动乡风文明
民族文化的资本化使优秀传统民俗文化得以继承,为村寨乡风文明建设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苗寨集群行为的民俗规范是文明乡风的基本构成,传统民俗与自我文化的自觉意识是民族村寨乡风文明建设的灵魂。全民参与不断提升寨内居民的民俗文化自觉意识与集体凝聚力构成了民俗文化变迁的内在诱因,民族旅游场域中游客和寨民对自身的主体利益诉求构成了民俗文化的外在诱因。旅游市场的需求使得传统民俗活动以商业化的形式展现,这不仅加强了寨民的族群认同,也是对苗寨民风的整体性重塑。民族文化资本的积累与游客的体验需求促使寨内民俗文化自觉意识不断高涨,村民自觉移风易俗,在实现民俗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中,重构文明乡风。注重民俗文化与传统节庆日函育文明的价值,发扬优秀本土价值观念,是苗寨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从蔽塞落后到开放交融、从思维保守到放眼世界,民族旅游的多样性民族文化互动交流中,原生态的优秀品质传承历史的厚重满足游客目的与期望。
(四)多元共治与民间智慧促动治理有效
苗寨多元共治的格局源自现代社会治理与传统民间智慧的有机结合,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使得村民,政府,社会三者在旅游场域中构建了新的权利空间。西江已经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治理模式的过渡,权利主体从基层政府转递到旅游公司。从制度设计层面来看,政府和旅游公司的职责部门制定规范的法律法规对苗寨发展规划、基层设施建设、经营生产管理到民族文化保护等进行规范化制度保障,随着管理制度完善与升级,市场运行与发展已逐渐成熟。从文化供给层面来看,西江苗寨充分运用苗族习惯法、村规民约、传统民俗,对村民、游客、商户等多个利益主体进行约束。寨老制、议榔制和民间歌谣处理寨民纠纷,鼓藏头、活路头等协商发挥“扫寨”“议榔”等传统活动的治理机制[10]。传统组织运用民间智慧处理多方权利主体博弈的过程中产生的矛盾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民间智慧的运用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和角色,不但可以调动寨内村民的积极性,赋予村民更多话语权,使社区组织产生约束力,加强社区治理能力,也凸显出文化主体性使传统治理智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命。现代化治理与民间智慧的有机结合构筑了良好的社会管理机制,法治、德治、自治的结合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内外部环境。
(五)产业共建与利益共享促动生活富裕
苗寨村民即是西江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组成,是民族旅游产业的基石,也是旅游产业发展的行动主体。从住宿餐饮到文化娱乐休闲,各个层面村民个体的发展驱动整体产业的建設。旅游公司与村民之间在实现了产业共建的格局后,同时完整了利益共同体的模式。苗寨每年从景区门票收入中提取份额作为民族文化保护经费分配给全体村民,从最初的15%提升到现在的18%。民族文化保护经费取决于家庭人口和吊脚楼的保护程度以及年限进行分配,每年发放两次,每户均受益从2011年的3600元增长到2017年的21000元,至今累计发放超过1.2亿元③。西江苗寨现有人口超过6000,所属雷山县2019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2378元和10273元,增长9%、10.5%④。2008年贵州省第三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西江苗寨举办,只用了十年时间寨内人均年收入便达到22100元,户均86190元,人均年收入较2008年相比增长了13倍,是2019年雷山县农村居民收入的两倍,寨内全部村民基本实现脱贫创富⑤。村民个体建设与民族旅游产业发展实现互惠互利良性循环,村民共享产业发展带来的利益,实现了西江民族旅游共建共享的格局。
四、民族旅游发展中的问题分析
在取得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西江民族旅游不可避免的面临着民族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如何协调民族文化保护与民族旅游发展的关系,如何面对民族文化的失真的现象,如何整合要素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西江民族旅游可持续发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大众文化的繁荣
巨大的经济效益带动下,苗寨产业的发展呈现过度商业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大众文化的繁荣。这种杂乱的、多元素的大众文化产品是依附于本土文化的象征性的大众符号,在本土文化产品的供给无法有效满足游客体验需求时而获得生机,失去本地文化的支持将荡然无存。首先是娱乐的现代化,酒吧、歌厅等大众娱乐文化的火爆与传统苗寨格格不入,在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之外,现代化的大众休闲场所与娱乐活动极大的迎合了年轻游客的需求,非民族性的供给服务在苗寨扎根生长不可避免地冲击了游客对于异文化的体验满足感。其次是传统民俗性的消弭,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建筑结构的转变,也体现在住宿体验的转变。寨内民宿以位置与视野形成了明显的居住空间隔离与分层。在可利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木质吊脚楼民宿被混凝土材质替代以满足几何式增长的游客量,山脚以外新建民宿则完全变成了现代式酒店,完全失去了传统民俗感。最后是民族文化产品的竞争力不足,优秀苗文化产品被非本地的多元外来文化不断侵袭。一方面表现在本土文化产品供给形式的同质化与创新性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当地文化衍生出的特色产品无法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满足旅游市场的需求,无法保持有效的市场竞争力。
(二)民族文化的真实化
长期沿袭的村落规模和独特乡土性赋予的文化强度造就了苗寨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苗寨拥有苗族鼓藏节、吊脚楼营造技艺、银饰锻造技艺、苗族刺绣、苗族飞歌等10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博物馆⑥。苗寨在与旅游市场实现双赢的时机下,旅游市场的冲击迫使苗族文化不断变迁,在保持民族文化真实性的同时,迎接民族文化融入新鲜元素形成新的西江苗文化,这将是本民族文化真实化的过程,在此过程苗文化的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第一,传统民族文化的变迁。传统文化在民族旅游的发展中进行再生产,这种再生产的民族文化与现代旅游开发治理相适应,不断迭代。村民以自身文化资本化形式获取经济收益,大量生产手工艺品出售与各种习俗活动的展示,违背了民族发展原有的生活轨迹,加速民族文化变迁。第二,民族文化的商品化。民族文化成为一种满足游客需求的表演形式,成为一种获得性体验的交易产品。文化商品化固然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发展,增进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但随着文化商品化程度的加深,为迎合经济发展规律而被现代化艺术形式包装后逐渐丧失民族文化内涵,促使本民族文化无法被正确理解,从而使本民族文化庸俗化。同时,民族文化资源的过度开发,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也将被扭曲。第三,民族文化的失真,民族文化的商品化的过程,就是在掠夺民族真实性的过程。曹妍雪等人认为文化的形成需要几代人的传承,文化的商品化是对文化的利用,是对本地人的剥削,对少数民族文化而言更是如此[12]。苗寨传统的民俗活动如铜鼓舞、高排芦笙、反排的木鼓舞变成反复的商业汇演,削弱了游客们的体验感知,民族文化的真实性来源于人们的感受,当民族文化被错误性的理解与感知的时候,其真实性也将遭受破坏。
(三)文化景观的消弭与冲突
西江苗寨居住人家超过1900户,苗寨古屋作为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与苗寨居民生产、生活的基本单元,传统观念为适应苗寨发展也在被妥协,苗寨的传统文化景观正在消逝与被替代。第一,市场的“建造与破坏”,山下人保护,山上人破坏。苗寨的景区核心将山下店铺、民宿、山水、古屋融为一体,是游客最集中的享受体验所在。景区的兴旺,山下人在获得大量红利后修缮古屋景观来吸引游客。由于居住空间与位置的差异,山上的村民无法享受到山下的便利,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山上的居民无法维持原生态的景观想要改造和重建老房,以满足致富的渴望。第二,内生动力的发展危机,共享机制下的不平衡。共享机制无法带来村民共同富裕,山上破旧古屋显然无法满足游客对于文化景观的需求。部分村民获批进行拆旧建新获得了可观利益,谋求自身发展的内生动力演变成了拆建成风。错落有致的传统民居变成了突兀而出的新房,这也是对传统苗族建筑文化的挑战。第三,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冲突。村民和游客都想住上新房子满足自身居住需求,古屋宜看不宜居,原生态的传统文化景观的保护面临着旅游产业发展需求的挑战。代际流动新老观念的冲突,古屋拆建与建造新房的冲突,苗族文化传统的保护与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冲突也是传统文化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化发展所要解决饿深层次问题。
五、文化保护视阈下的发展建议
以民族文化为核心衍生出的“西江模式”的民族旅游坚持产业融合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实现脱贫创富、社会有效治理的现代化转变从根本上契合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西江民族旅游的未来在于对苗族文化的保真,传承、保护、发扬苗族文化即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出发点也是民族村寨振兴的归宿。
(一)以人为本,释放权利空间
苗民是苗族文化的创造者,西江民族旅游的灵魂是苗寨文化。民族村落乡村振兴实践,任何时候、任何方式的发展都要以人为本,以民族文化为核心促进竞争。马梓认为实现民族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坚持“人”可持续性,人作为开发民族旅游的主体,对于推动民族旅游持续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11]。在面对民族旅游过度商业化与大众化的同时,要开发有度,积极释放权利空间,给予村民足够的自主性,重视当地村民的利益,肯定村民利益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一方面,通过开办专业的培育机构,培养旅游知识技能,促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提升文化自觉意识,同时加强基层社区治理与宣传,培育可持续化发展观念,从内部提升参与的意识与能力。另一方面,从制度上明确当地居民的权利与职责,完善社区参与的制度规范,将制度规范纳入村规民约,从外部保障社区参与的积极性。
(二)增强文化认同,实现价值主体性互动
民族旅游发展是把双刃剑,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具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协调好民族旅游与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在保護文化的根本上思考发展策略,用发展的眼光审视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与外来旅游者带来的大众文化不断地互动形成了一个民族旅游场域[12],在场域中,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与保护形成“文化资本”,民族文化商品化再生产形成“经济资本”,苗文化与游客大众文化的互动形成的“社会资本”。首先,场域中的三种资本相互竞争,“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是共生存在,可促动两种资本向“文化资本”转化,增加其竞争力。其次,我们要明晰三种资本的空间顺序,构建“经济资本”在外围、“社会资本”缓冲、“文化资本”在核心的民族文化村模式[13]。最后,增进游客的探索式互动与主动式理解,实现民族文化价值的最大体现。一方面探索式互动可直接催动村民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主体性创新,发展与繁荣民族文化产业,提成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另一方面是采取主动式的理解,实现让游客对苗族文化价值的主题判断,更清晰的认知苗寨民族文化,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与“异文化”认知力。通常旅客是被动式的体验,使得民族文化的商业化愈加严重,造成“经济资本”的增加。开办更多能以游客为主导的民俗互动,在强调体验感参与感同时,更加注重游客的获得感,增加苗文化被大众的认同度,使得“社会资本”起到积极地缓冲作用的同时削弱“经济资本”,降低民族文化的商业化。
(三)重构公共文化空间,推进城乡一体化
苗寨的发展需要创造性的保护,旅游产业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是相互成就,二者之间的冲突在于空间结构的分割与资源配置的失调。苗寨的未来既不是空荡荡的博物馆,也不是纯粹旅游目的地的世外桃源,应当是独一无二的“西江源”。一方面,应当重构苗寨公共文化空间,实现空间与文化的有机融合,降低内部发展压力。苗寨的公共文化空间既涵盖村民生活、生产空间,又是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场域,集中体现村民的文化价值取向。针对传统文化的景观的冲突,既要传承苗族优秀文化考虑传统居住习性,又要考虑居住环境适应新时期的生存发展。首先,健全苗寨房屋拆建制度,有效引导拆建成风,最大限度保全原始风貌。其次,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培育全寨文化自觉意识,调动村民自主保护的积极性,实现均衡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最后,满足多种价值取向需求,构建新型文化景观。发展有破坏也有创新,寻找民居特色与现代建筑的有机融合以契合原生态的苗寨风貌,满足游客,村民的多元需求。另一方面,推进城乡一体化,扩大外部发展容量转移空间压力,。第一,城乡资源要素配置一体化。苗寨的产能足够促动全州市场要素无障碍流动,以苗寨为发展引擎,进行市场引流,推进全域均衡发展。第二,城乡服务设施一体化。建立畅通的旅游交通网络,为游客提供便捷的出行工具、住宿条件,让游客有更多的自主性选择。第三,城乡旅游服务标准一体化。在城乡间设立统一的服务规则和监督机制,提高旅游业整体服务质量和水平。第四,城乡旅游市场机制一体化。为建立统一开放的旅游市场,各地政府要创造制度环境,制度统一,保持良性的竞争与合作。
注释: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0,02.28,《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贵州省统计局,2020.04.09,《贵州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数据来源:西江千户苗寨官网,2020.09.06,《西江旅游公司2019年旅游旺季工作总结会》。
③数据来源:雷山文化旅游园区工商局和综合执法局,《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十年发展报告(2008—2018)》。
④数据来源:雷山县人民政府网.2020,1,21,《雷山县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⑤数据来源:雷山文化旅游园区工商局和综合执法局,《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十年发展报告(2008- 2018)》。
⑥数据来源: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2019年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在贵阳召开》。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瓦伦·L·史密斯.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M].张晓萍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3]周大鸣.人类学与民族旅游:中国的实践[J].旅游学刊,2014,29(2):103- 109.
[4]光映炯.旅游人类学再认识———兼论旅游人类学理论研究现状[J].思想战线,2002,(6):43- 47.
[5]李忠斌,文晓国.对民族旅游概念的再认识[J].广西民族研究,2012,(4):177- 184.
[6]杨昇,王晓云,冯学钢.近十年国内外民族旅游研究综述[J].广西民族研究,2008,(3):194- 202.
[7] DANN G M, ANOMIE S.Ego- enhancement and Tourism[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77,4(04):184- 194.
[8]郭景福,趙奥.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制度与路径[J].社会科学家,2019,(4):87- 91.
[9]张洪昌,舒伯阳,孙琳.民族旅游地区乡村振兴的“西江模式”:生成逻辑、演进机制与价值表征[J].贵州民族研究,2018,39(9):165- 168.
[10]吴忠军,宁永丽.民族乡村经济振兴的“西江模式”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8,(6):115- 121.
[11]马骍.关于民族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思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7(6):126- 130.
[12]宋秋,杨振之.场域:旅游研究新视角[J].旅游学刊,2015,30,(9):111- 118.
[13]田敏,撒露莎,邓小艳.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村寨文化保护及传承比较研究———基于贵州、湖北两省三个民族旅游村寨的田野调查[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4(5):88- 94.